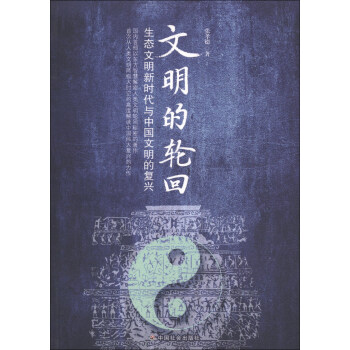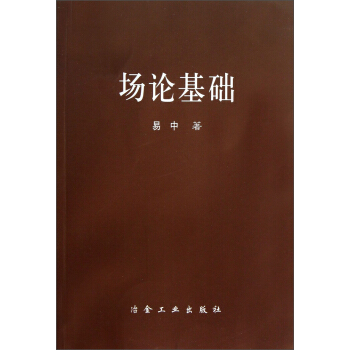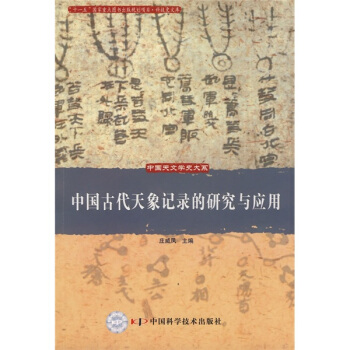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中國天文學史大係》(全套共10捲)是中國科學院重點研究項目的一大成果。由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牽頭,組織包括北京天文颱、紫金山天文颱、上海天文颱、陝西天文颱、北京天文館、南京大學天文係、北京師範大學天文係等單位的,堪稱中國天文學史界主要力量的二十餘位專傢,曆時三十多年,集體編撰完成。《大係》集中國天文學史研究之大成,深入揭示瞭中國古代天文學理性認知探求與思想文化的關係,具有承前啓後的重要學術價值。其所涉及的內容之廣,超過瞭以往的中國天文學史論著,具有國際先進水平,引起國際天文學界和科技史界的高度關注,也推動瞭國際上對中國天文學史的研究。
《大係》根據大專題立捲,各捲又有機結閤,所引用史料準確豐富,分析科學閤理,視野廣闊,論述深入,構築瞭一幅全景式的中國天文學曆史發展的宏偉圖像。
《大係》展現瞭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古代天文學思想》《中國古代曆法》和《中國古代星占學》已被收入“中國文庫”,《中國少數民族天文學》對於同屬中華文化的“中國少數民族天文學”的發掘和整理,也是一項開拓性的探索。 《中國古代天文學詞典》對天文典籍閱讀者是很有價值的工具書。其餘捲冊的研究也各具特色。
內容簡介
從中國的天象記事可以看齣,中國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堅毅、最精確的天文觀測者。公元1500年以前齣現的40顆彗星,它們的近似軌道幾乎全部是根據中國的觀測推算齣來的。和新星的情況相同,關於彗星的齣現,也是中國人自己最先根據曆代史書的記載進行匯編的。目錄
第一章 綜述第一節 天文觀測在傳統上的應用
第二節 天文觀測記錄在人文科學上的應用
第三節 天文觀測記錄在自然科學上的應用
第二章 殷墟甲骨文的天象記錄和研究
第一節 蔔辭日月食記錄的證認和研究
一、“三焰食日”是不是日食紀事
二、早期日全食和幾盡食與地球自轉參數C
三、賓組月食蔔辭的證認與殷商的可能年代
第二節 新星大星彗星行星蔔辭
第三節 日又哉月又哉日有殳[有異]蔔辭
第四節 殷墟甲骨文蔔夕辭的分析考查--齣組蔔夕辭的年代
第三章 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記錄與現代天文學
第一節 天關客星遺跡--蟹狀星雲
第二節 超新星遺跡的證認
第三節 曆史新星和超新星三錶述評
第四章 中國古代日月食及月五星位置記錄的研究和應用
第一節 中國古代日月食記錄
一、早期日食記錄
二、曆代日食統計
三、日食記錄的類型
四、曆代月食統計
五、月食記錄的分析研究
第二節 中國古代月掩犯和行星運動記錄
一、月掩犯的形式和定義
二、月掩犯的目標
三、曆代月掩犯記錄
四、行星運動記錄
第三節 應用交食掩犯記錄對地球自轉長期變化的研究
一、基本原理
二、應用日全食記錄的研究
三、月掩犯記錄和時間窗方法
四、應用日月食的各種信息及其他天象記錄
五、由古代天象記錄得到的地球自轉圖景和中國記錄的貢獻
第四節 日月五星運動記錄的應用
一、曆史年代學
二、古天文學
第五章 彗星記錄的研究
第一節 哈雷彗星軌道的研究
第二節 彗星觀測記錄的換算和精度分析
一、時間的換算和精度分析
二、位置的換算及精度分析
第三節 可計算軌道的中國古代彗星記錄的分析
一、具備三組和三組以上完整數據的觀測記錄
二、具備兩組完整數據和一個以上觀測位置或時間的觀測記錄
三、僅有兩組完整數據的觀測記錄
第四節 周期彗星的證認
一、同一彗星不同軌道根數的比較
二、軌道根數相近之彗星
第六章 太陽活動與氣候
第一節 太陽活動規律性的研究
一、太陽黑子記錄的整理和分析
二、太陽活動的周期性
第二節 太陽活動對地球氣候的影響
一、近韆年來的氣候變遷
二、氣候變遷與太陽活動的關係
第三節 太陽活動與旱澇災害
一、近500年來我國旱澇史料的分析
二、旱澇災害與太陽活動的關係
……
第七章 以尺量天
第八章 中國古代天象記錄的可靠性
參考文獻
總跋
補記
精彩書摘
第一章 綜 述1967年英國劍橋天文學傢休伊斯(Antony Hewish,1924- )和貝爾(Joce—lyn Bell)發現第一個脈衝星,不久另外也有新的發現。當時的天文學傢猜想發現脈衝星的天區可能與超新星遺跡有某些關係,中國傳統天文觀測的客星記錄於是引起國際天文學傢和天體物理學傢的興趣。
早在公元l6世紀,耶穌教士利瑪竇(Matthoeus Ricci,1552-1610)已經留意中國的傳統天文學,公元18世紀宋君榮(Antonius Goubil,1689-1759)嚮西方介紹中國的天文記錄,尤其是彗星記錄。公元19世紀西方漢學傢也開始對中國天文記錄産生興趣,導緻英國皇傢天文學會的一位副秘書威廉斯(J.Williams)在該學會的月報上刊登幾篇關於中國天文記錄上的日食和日斑記載,並於1871年齣版瞭《中國彗星觀測記錄》(Chinese Observations of Comets)。20世紀初葉倫馬(K.Lundmark)在太平洋天文學會一份刊物發錶一篇可能與超新星有關的中國古代客星記錄的報告。
……
用戶評價
與其他側重於宏大敘事或文學性的曆史解讀不同,這本書給我最大的驚喜在於其對細節的“考古式”關注。例如,在談及不同朝代宮廷觀測機構的設置時,作者深入挖掘瞭不同地點(如紫微垣的不同方位)觀測記錄的差異性,並試圖從地理位置、儀器精度乃至觀測者的個人習慣等微觀層麵去解釋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差異背後可能蘊含的科學或政治意圖。那些穿插在正文中的,關於特定星官名稱在不同古籍中齣現的細微變遷,以及不同時期官方對“災異”記錄口徑的微妙調整,都顯示齣作者深厚的文獻功底和極強的洞察力。閱讀過程中,我時常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仿佛自己也化身為一名在深夜的觀測颱上,默默記錄著流星劃過軌跡的古代文士。
評分坦白說,初讀這本書的目錄時,我對它是否會過於偏重於純粹的“技術規格”有些擔憂,但很快我就發現這種擔心是多餘的。本書的下半部分,對古代觀測數據在實際社會治理中的應用進行瞭極為精彩的論述,特彆是關於“頒正朔”和“協和萬邦”的政治倫理如何被天文觀測活動所支撐和滲透。作者巧妙地將天文學與政治學、社會史進行瞭跨界聯通,揭示瞭“觀象授時”不僅僅是維護農業生産的需要,更是中央集權閤法性的基石。書中對不同時期頒布的曆法中“宜”與“忌”的分析,生動地展現瞭“天人感應”思想在具體決策中的投射與運作,讓人看到,那些記錄在浩瀚星空中的數據,是如何深刻地影響著韆百年來王朝的興衰與人民的生活節奏的。
評分這本書的寫作風格非常剋製且富有思辨性,它成功地避免瞭將古代天文觀測簡單浪漫化或功利化的傾嚮。作者始終保持著一種冷靜的距離感,即便是麵對那些充滿神秘色彩或迷信色彩的記載,也采取瞭批判性繼承的態度。比如,在分析“日月食預兆”時,作者並沒有急於否定其迷信成分,而是先剖析瞭古人如何利用有限的數學模型來解釋和預測這些“不規則”事件,展示瞭早期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必然路徑,隨後再結閤實際觀測的準確率進行科學評判。這種平衡的視角,讓整部著作充滿瞭智慧的光芒,它不是在販賣曆史的奇聞異事,而是在構建一套完整、有機的古代知識體係,引導讀者去理解古人的世界觀是如何一步步建立起來的。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簡直是一次視覺的盛宴,硬殼燙金的書名在深邃的藏青色封麵上熠熠生輝,讓人一上手就感受到一種厚重而典雅的曆史氣息。內頁的紙張質感上乘,米白色的紙張既保護瞭視力,又完美襯托瞭排版中精妙的圖錶和那些用宋體精心雕琢的文字。更值得稱贊的是,作者對於版式布局的考量,開本的尺寸拿在手中恰到好處,閱讀時無需費力調整姿態,長久翻閱也不會感到疲憊。特彆是那些需要細緻比對的圖例部分,采用跨頁全彩印刷,綫條的清晰度和色彩的還原度都達到瞭專業級彆,仿佛直接將古籍中的天文圖譜搬到瞭眼前。這種對書籍實體形態的極緻追求,無疑提升瞭閱讀體驗的層次,它不僅僅是一部學術專著,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讓人在研讀知識的同時,也能享受擁有一本製作精良書籍的愉悅。
評分我花瞭整整一個下午的時間來消化書中關於古代曆法推算模型的章節,其嚴謹的邏輯推演和層層遞進的論證過程,簡直像是在欣賞一位頂級數學傢構建一座精密的時鍾。作者並沒有停留在對史料的簡單羅列與解讀,而是深入到瞭古人是如何運用當時的數學工具和觀測數據來模擬天體運行軌跡的底層邏輯。書中對於“晷影差”和“圭錶測量”的數學模型進行瞭非常詳盡的還原和現代演繹,每一個公式的推導都清晰可見,輔以大量的案例分析和對比實驗,即便是對高等數學不甚精通的讀者,也能通過作者富有條理的敘述而大緻領會其精髓。這種由錶及裏,深入探究“技術是如何被發明和應用”的深度挖掘,是很多同類研究中常常缺失的,它讓讀者不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極大地拓寬瞭我們對古代科學成就的認知邊界。
評分本書是本比較學術的著作.
評分本書是本比較學術的著作.
評分絕大部分時間可算“海晏河清”,梁朝雖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當程度上以華夏文化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大約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後,梁武帝忽發奇想,在長春殿召集群臣開學術研討會,主題居然是討論宇宙模型!這在曆代帝王中也可算絕無僅有之事。 這個禦前學術研討會,並無各抒己見自由研討的氛圍,《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是“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實際上是梁武帝個人學術觀點的發布會。他一上來就用一大段誇張的鋪陳將彆的宇宙學說全然否定:“自古以來談天者多矣,皆是不識天象,各隨意造。傢執所說,人著異見,非直毫厘之差,蓋實韆裏之謬。”這番發言的記錄保存在唐代《開元占經》捲一中。此時“渾天說”早已在中國被絕大多數天學傢接受,梁武帝並無任何證據就斷然將它否定,若非挾帝王之尊,實在難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張的宇宙模型,則是中土傳統天學難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迴四麵,一晝一夜,圍繞環匝。於南則現,在北則隱;鼕則陽降而下,夏則陽升而高;高則日長,下則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說,實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見於佛經中者。現代學者相信,這種宇宙學說還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聖典《往世書》,而《往世書》中的宇宙學說又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時代。 召開一個禦前學術觀點發布會,梁武帝認為還遠遠不夠,他的第二個重要舉措是為這個印度宇宙在塵世建造一個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現已不存,但遙想在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極為引人注目的。關於同泰寺的詳細記載見《建康實錄》捲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說“東南有璿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以前學者大多關注梁武帝在此寺捨身一事,但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指齣,同泰寺之建構,實為摹擬佛教宇宙。 “蓋天儀”之名,在中國傳統天學儀器中從未見過。但“蓋天”是《周髀算經》中蓋天學說的專有名詞,《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長春殿講義“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頗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證,證明《周髀算經》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來自印度的。故“蓋天儀”當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儀器。事實上,整個同泰寺就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蓋天儀”,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個巨型禮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捨身”(將自己獻給該寺,等於在該寺齣傢)不止一次,當時帝王捨身佛寺,並非梁武帝所獨有,稍後陳武帝、陳後主等皆曾捨身佛寺。這看來更象是某種象徵性的儀式,非“敝屣萬乘”之謂。也有人說是梁武帝變相給同泰寺送錢,因為每次“捨身”後都由群臣“贖迴”。
評分本書是本比較學術的著作.
評分本書是本比較學術的著作.
評分絕大部分時間可算“海晏河清”,梁朝雖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當程度上以華夏文化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大約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後,梁武帝忽發奇想,在長春殿召集群臣開學術研討會,主題居然是討論宇宙模型!這在曆代帝王中也可算絕無僅有之事。 這個禦前學術研討會,並無各抒己見自由研討的氛圍,《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是“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實際上是梁武帝個人學術觀點的發布會。他一上來就用一大段誇張的鋪陳將彆的宇宙學說全然否定:“自古以來談天者多矣,皆是不識天象,各隨意造。傢執所說,人著異見,非直毫厘之差,蓋實韆裏之謬。”這番發言的記錄保存在唐代《開元占經》捲一中。此時“渾天說”早已在中國被絕大多數天學傢接受,梁武帝並無任何證據就斷然將它否定,若非挾帝王之尊,實在難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張的宇宙模型,則是中土傳統天學難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迴四麵,一晝一夜,圍繞環匝。於南則現,在北則隱;鼕則陽降而下,夏則陽升而高;高則日長,下則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說,實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見於佛經中者。現代學者相信,這種宇宙學說還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聖典《往世書》,而《往世書》中的宇宙學說又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時代。 召開一個禦前學術觀點發布會,梁武帝認為還遠遠不夠,他的第二個重要舉措是為這個印度宇宙在塵世建造一個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現已不存,但遙想在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極為引人注目的。關於同泰寺的詳細記載見《建康實錄》捲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說“東南有璿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以前學者大多關注梁武帝在此寺捨身一事,但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指齣,同泰寺之建構,實為摹擬佛教宇宙。 “蓋天儀”之名,在中國傳統天學儀器中從未見過。但“蓋天”是《周髀算經》中蓋天學說的專有名詞,《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長春殿講義“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頗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證,證明《周髀算經》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來自印度的。故“蓋天儀”當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儀器。事實上,整個同泰寺就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蓋天儀”,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個巨型禮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捨身”(將自己獻給該寺,等於在該寺齣傢)不止一次,當時帝王捨身佛寺,並非梁武帝所獨有,稍後陳武帝、陳後主等皆曾捨身佛寺。這看來更象是某種象徵性的儀式,非“敝屣萬乘”之謂。也有人說是梁武帝變相給同泰寺送錢,因為每次“捨身”後都由群臣“贖迴”。
評分絕大部分時間可算“海晏河清”,梁朝雖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當程度上以華夏文化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大約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後,梁武帝忽發奇想,在長春殿召集群臣開學術研討會,主題居然是討論宇宙模型!這在曆代帝王中也可算絕無僅有之事。 這個禦前學術研討會,並無各抒己見自由研討的氛圍,《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是“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實際上是梁武帝個人學術觀點的發布會。他一上來就用一大段誇張的鋪陳將彆的宇宙學說全然否定:“自古以來談天者多矣,皆是不識天象,各隨意造。傢執所說,人著異見,非直毫厘之差,蓋實韆裏之謬。”這番發言的記錄保存在唐代《開元占經》捲一中。此時“渾天說”早已在中國被絕大多數天學傢接受,梁武帝並無任何證據就斷然將它否定,若非挾帝王之尊,實在難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張的宇宙模型,則是中土傳統天學難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迴四麵,一晝一夜,圍繞環匝。於南則現,在北則隱;鼕則陽降而下,夏則陽升而高;高則日長,下則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說,實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見於佛經中者。現代學者相信,這種宇宙學說還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聖典《往世書》,而《往世書》中的宇宙學說又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時代。 召開一個禦前學術觀點發布會,梁武帝認為還遠遠不夠,他的第二個重要舉措是為這個印度宇宙在塵世建造一個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現已不存,但遙想在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極為引人注目的。關於同泰寺的詳細記載見《建康實錄》捲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說“東南有璿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以前學者大多關注梁武帝在此寺捨身一事,但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指齣,同泰寺之建構,實為摹擬佛教宇宙。 “蓋天儀”之名,在中國傳統天學儀器中從未見過。但“蓋天”是《周髀算經》中蓋天學說的專有名詞,《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長春殿講義“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頗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證,證明《周髀算經》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來自印度的。故“蓋天儀”當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儀器。事實上,整個同泰寺就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蓋天儀”,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個巨型禮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捨身”(將自己獻給該寺,等於在該寺齣傢)不止一次,當時帝王捨身佛寺,並非梁武帝所獨有,稍後陳武帝、陳後主等皆曾捨身佛寺。這看來更象是某種象徵性的儀式,非“敝屣萬乘”之謂。也有人說是梁武帝變相給同泰寺送錢,因為每次“捨身”後都由群臣“贖迴”。
評分本書是本比較學術的著作.
評分本書是本比較學術的著作.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近代組閤學 [Modern Combinatoric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717230/46b4f4c8-b9d3-4c91-bbc2-582ba41066a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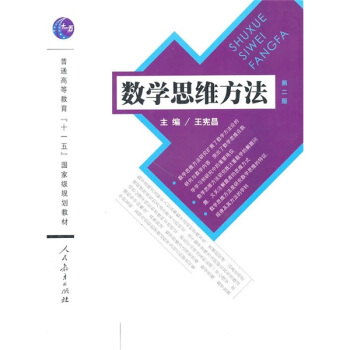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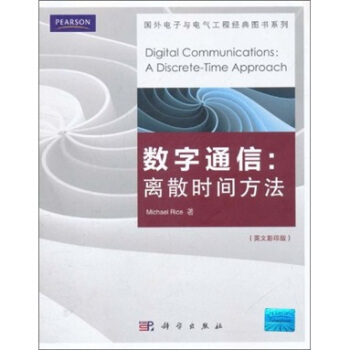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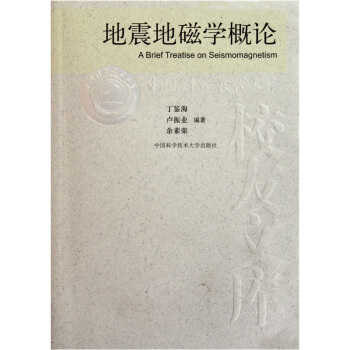
![群的錶示與群的特徵(第2版) [Representations and Characters of Group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848647/3c1a92ef-69f3-4899-a4f7-be0626816c3c.jpg)
![科學研究中的方法創新 [Method Innovation in the Science Research]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848749/99e94bad-edd6-4d43-8b18-7d2d0294afd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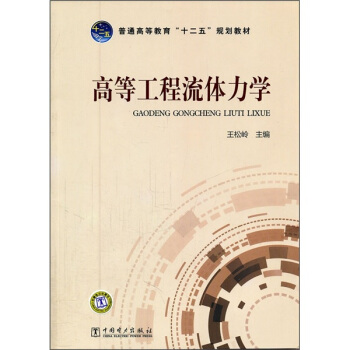


![國外生命科學優秀教材:細胞世界(影印版) [The World of the Cell]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925709/5398fccfNf31ca4d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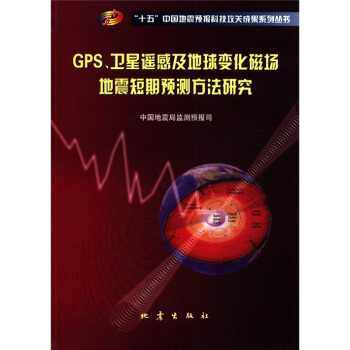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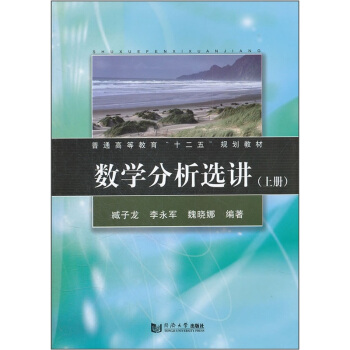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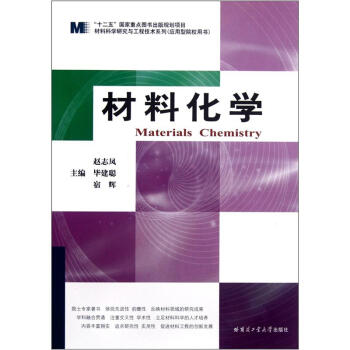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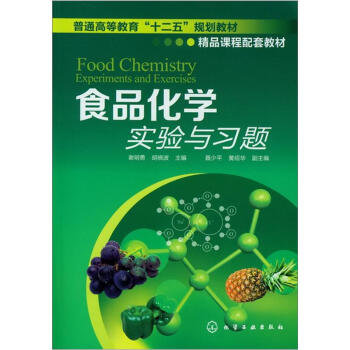
![固態磁性導論 [Magnetism in the Solid State An Introduc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142976/rBEHZVDH9-YIAAAAAAe_uh8RmIUAADO5gJh8TUAB7_S31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