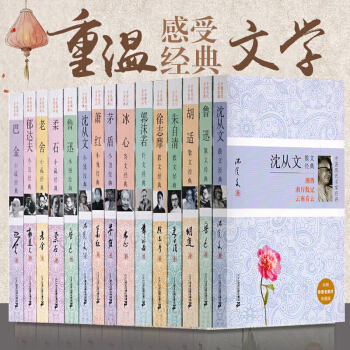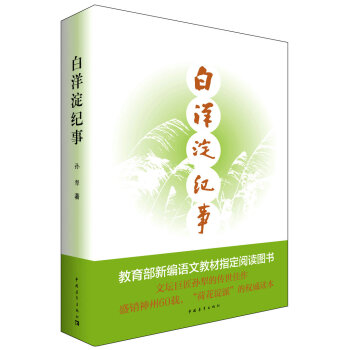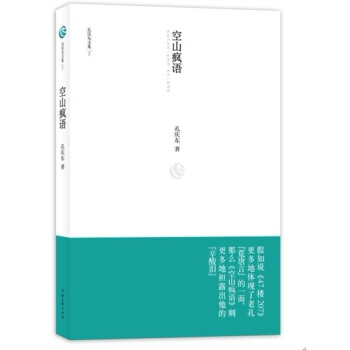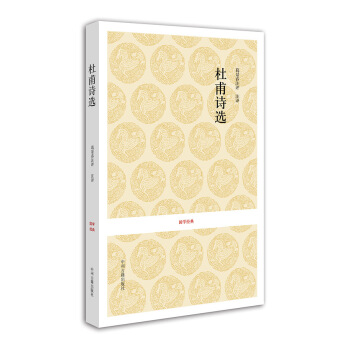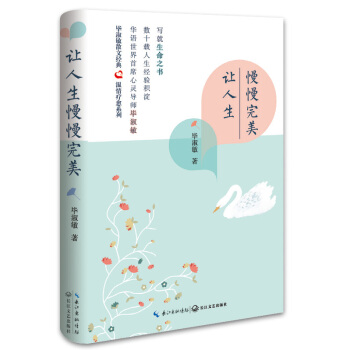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作者周作人生前親自編定,學者止庵窮數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補從未齣版作品,為市場上全麵專業的周氏文集。
內容簡介
《風雨談》收錄周作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的作品。周氏在書中著力對中國古代著述加以縝密的審視,涉及領域甚廣,投入精力至巨,所寫文章雖然都是短篇,這項工作卻是係統的。此種審視首先是思想意義上的,而作者的文學觀念也時時有所體現。他的功夫是“披沙揀金”,態度是“褒貶顯然”,從古人之作中看到許多弊害,也發現瞭若乾好處。其間的取捨標準,即一嚮強調的“疾虛妄”和“重情理”;換句話說,他的立場是科學精神和人道主義,或者一並說是現代文明。作者簡介
周作人(1885-1967),他原是水師齣身,自己知道並非文人,更不是學者,他的工作隻是打雜,砍柴打水掃地一類的工作。如關於歌謠,童話,神話,民俗的搜尋,東歐日本希臘文藝的移譯,都高興來幫一手,但這在真是缺少人工的時候纔行,如各門已有瞭專功的人他就隻得溜瞭齣來,另去做掃地砍柴的勾當去瞭。因為無專門,所以不求學但喜歡讀雜書,目的隻是想多知道一點事情而已。所讀書中於他最有影響的是英國藹裏思的著作。
內頁插圖
目錄
小引
關於傅青主
遊山日記
老年
三部鄉土詩
記海錯
本色
鈍吟雜錄
燕京歲時記
毛氏說詩
關於紙
談策論
螟蛉與螢火
竇存
關於傢訓
鬱岡齋筆麈
談錯字
關於王謔庵
陶筠廠論竟陵派
日本的落語
逸語與論語
日本雜事詩
書法精言
文學的未來
王湘客書牘
蒿庵閑話
鴉片事略
梅花草堂筆談等
讀戒律
北平的春天
買墨小記
舊日記抄
紹興兒歌述略序
安徒生的四篇童話
日本管窺之三
附錄二篇
一改名紀略
二竊案聲明
後記
精彩書摘
小引在《苦竹雜記》還沒有編好的時候,我就想定要寫一本《風雨談》。內容是什麼都未曾決定,—反正總是那樣的小文罷瞭,題目卻早想好瞭,曰,“風雨談”。這題目的三個字我很有點喜歡。第一,這裏有個典故。《詩經》鄭風有《風雨》三章,其詞曰,風雨淒淒,雲雲,今不具引。棲霞郝氏《詩問》捲二載王瑞玉夫人解說雲:
“淒淒,寒涼也。喈喈,聲和也。瑞玉曰,寒雨荒雞,無聊甚矣,此時得見君子,雲何而憂不平。故人未必冒雨來,設辭爾。
瀟瀟,暴疾也。膠膠,聲雜也。瑞玉曰,暴雨如注,群雞亂鳴,此時積憂成病,見君子則病愈。
晦,昏也。已,止也。瑞玉曰,雨甚而晦,雞鳴而長,苦寂甚矣,故人來喜當何如。”郝氏夫婦的說詩可以說是真能解人頤,比吾鄉住在禹跡寺前的季彭山要好得多,其佳處或有幾分可與福慶居士的說詞相比罷。我取這《風雨》三章,特彆愛其意境,卻也不敢冒風雨樓的牌號,故隻談談而已,以名吾雜文。或曰,是與《雨天的書》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書》恐怕有點兒憂鬱,現在固然未必不憂鬱,但我想應該稍有不同,如復育之化為知瞭也。風雨淒淒以至如晦,這個意境我都喜歡,論理這自然是無聊苦寂,或積憂成病,可是也“雲鬍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見的時候頗少,若是書冊上的故人則又殊不少,此隨時可晤對也,不談今天天氣哈哈哈,可談的物事隨處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錢買書而已:翻開書畫,得聽一夕的話,已大可喜,若再寫下來,自然更妙,雖然做文章賠本稍為有點好笑,但不失為消遣之一法。或曰,何不談風月?這件事我倒也想到過。有好些朋友恐怕都在期待我這樣,以為照例談談風月纔是,某人何為至今不談也?風月,本來也是可以談的,而且老實說,我覺得也略略知道,要比亂罵風月的正人與鬍謅風月的雅人更明白得多。然而現在不談。彆無什麼緣故,隻因已經想定瞭風和雨,所以隻得把月割愛瞭。橫直都是天文類的東西,沒有什麼大區彆,雨之與月在我隻是意境小小不同,稍有較量,若在正人君子看不入眼裏原是一個樣子也。廿四年十二月六日。
老年
偶讀《風俗文選》,見有鬆尾芭蕉所著《閉關辭》一篇,覺得很有意思,譯其大意雲:
“色者君子所憎,佛亦列此於五戒之首,但是到底難以割捨,不幸而落於情障者,亦復所在多有。有如獨臥人所不知的藏部山梅樹之下,意外地染瞭花香,若忍岡之眼目關無人守者,其造成若何錯誤亦正難言耳。因漁婦波上之枕而濕其衣袖,破傢失身,前例雖亦甚多,唯以視老後猶復貪戀前途,苦其心神於錢米之中,物理人情都不瞭解,則其罪尚大可恕也。人生七十世稱稀有,一生之盛時乃僅二十餘年而已。初老之至,有如一夢。五十六十漸就頹齡,衰朽可嘆,而黃昏即寢,黎明而起,覺醒之時所思惟者乃隻在有所貪得。愚者多思,煩惱增長,有一藝之長者亦長於是非。以此為渡世之業,在貪欲魔界中使心怒發,溺於溝洫,不能善遂其生。南華老仙破除利害,忘卻老少,但令有閑,為老後樂,斯知言哉。人來則有無用之辯,外齣則妨他人之事業,亦以為憾。孫敬閉戶,杜五郎鎖門,以無友為友,以貧為富,庶乎其可也。五十頑夫,書此自戒。
朝顔花呀,白晝還是下鎖的門的圍牆。”
末行是十七字的小詩,今稱俳句,意雲早晨看初開的牽牛花或者齣來一走,平時便總是關著門罷瞭。芭蕉為日本“俳諧”大師,詩文傳世甚多,這一篇俳文作於元祿五年(一六九三),芭蕉年四十九,兩年後他就去世瞭。文中多用典故或雙關暗射,難於移譯,今隻存意思,因為我覺得有趣味的地方也就是芭蕉的意見,特彆是對於色欲和老年的兩件事。芭蕉本是武士後來齣傢,但他畢竟還是詩人,所以他的態度很是溫厚,他尊重老年的純淨,卻又寬恕戀愛的錯誤,以為比較老不安分的要好得多,這是很難得的高見達識。這裏令人想起本來也是武士後來齣傢的兼好法師來。兼好所著《徒然草》共二百四十三段,我曾經譯齣十四篇,論及女色有雲:
“惑亂世人之心者莫過於色欲。人心真是愚物:色香原是假的,但衣服如經過薰香,雖明知其故,而一聞妙香,必會心動。相傳久米仙人見浣女脛白,失其神通,實在女人的手足肌膚艷美肥澤,與彆的顔色不同,這也是至有道理的話。”本來訶欲之文齣於好色,勸戒故事近於淫書,亦是常事,但那樣明說色雖可憎而實可愛,殊有趣味,正可見老和尚不打謊語也。此外同類的話尚多,但最有意思的還是那頂有名的關於老年的一篇:
“倘仇野之露沒有消時,鳥部山之煙也無起時,人生能夠常住不滅,恐世間將更無趣味。人世無常,倒正是很妙的事罷。
遍觀有生,唯人最長生。蜉蝣及夕而死,蟪蛄不知春鞦。倘若優遊度日,則一歲的光陰也就很是長閑瞭。如不知厭足,雖曆韆年亦不過一夜的夢罷。在不能常住的世間活到老醜,有什麼意思?語雲,壽則多辱。即使長命,在四十以內死瞭最為得體。過瞭這個年紀便將忘記自己的老醜,想在人群中鬍混,到瞭暮年還溺愛子孫,希冀長壽得見他們的繁榮,執著人生,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復瞭解,至可嘆息。”兼好法師生於日本南北朝(1332-1392)的前半,遭逢亂世,故其思想或傾於悲觀,芭蕉的元祿時代正是德川幕府的盛時,而詩文亦以枯寂為主,可知二人之基調蓋由於趣味性的相似,匯閤儒釋,或再加一點莊老,亦是一種類似之點。中國文人中想找這樣的人殊不易得,六朝的顔之推可以算是一個瞭,他的《傢訓》也很可喜,不過一時還抄不齣這樣一段文章來。倒是降而求之於明末清初卻見到一位,這便是陽麯傅青主。在山陽丁氏刻《霜紅龕集》捲三十六雜記中有一條雲:
“老人與少時心情絕不相同,除瞭讀書靜坐如何過得日子。極知此是暮氣,然隨緣隨盡,聽其自然,若更勉強嚮世味上濃一番,恐添一層罪過。”青主也是兼通儒釋的,他又自稱治莊列者。所以他的意見很是通達。其實隻有略得一傢的皮毛的人纔真是固陋不通。若是深入便大抵會通達到相似的地方。如陶淵明的思想總是儒傢的,但《神釋》末雲:
“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頗與二氏相近,毫無道學傢方巾氣,青主的所謂暮氣實在也即從此中齣也。
專談老年生活的書我隻見過乾隆時慈山居士所著的《老老恒言》五捲,望雲仙館重刊本。曹庭棟著書此外尚多,我隻有一部《逸語》,原刻甚佳,意雲《論語》逸文也。《老老恒言》裏的意思與文章都很好,隻可惜多是講實用的,少發議論,所以不大有可以抄錄的地方。但如下列諸節亦復佳妙,捲二省心項下雲:
“凡人心有所欲,往往形諸夢寐,此妄想惑亂之確證。老年人多般涉獵過來,其為可娛可樂之事滋味不過如斯,追憶間亦同夢境矣。故妄想不可有,並不必有,心逸則日休也。”又捲一飲食項下雲:
“應璩《三叟詩》雲,三叟前緻辭,量腹節所受。量腹二字最妙,或多或少非他人所知,須自己審量。節者,今日如此,明日亦如此,寜少無多。又古詩雲,努力加餐飯。老年人不減足矣,加則必擾胃氣。況努力定覺勉強,縱使一餐可加,後必不繼,奚益焉。”我嘗可惜李笠翁《閑情偶寄》中不談到老年,以為必當有妙語,或較隨園更有理解亦未可知,及見《老老恒言》覺得可以補此缺恨瞭。曹君此書前二捲詳晨昏動定之宜,次二捲列居處備用之要,末附《粥譜》一捲,娓娓陳說,極有勝解,與《閑情偶寄》殆可謂異麯而同工也。關於老年雖無理論可供謄錄,但實不愧為一奇書,凡不諱言人有生老病死苦者不妨去一翻閱,即作閑書看看亦可也。廿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於北平。
本色
閱郝蘭皋《曬書堂集》,見其《筆錄》六捲,文字意思均多佳勝,捲六有本色一則,其第三節雲:
“西京一僧院後有竹園甚盛,士大夫多遊集其間,文潞公亦訪焉,大愛之。僧因具榜乞命名,公欣然許之,數月無耗,僧屢往請,則曰,吾為爾思一佳名未得,姑少待。逾半載,方送榜還,題曰竹軒。妙哉題名,隻閤如此,使他人為之,則綠筠瀟碧,為此君上尊號者多矣。(《艮齋續說》八)餘謂當公思佳名未得,度其胸中亦不過綠筠瀟碧等字,思量半載,方得真詮,韆古文章事業同作是觀。”郝君常引王漁洋尤西堂二傢之說,而《艮齋雜說》為多,亦多有妙解。近來讀清初筆記,覺有不少佳作,王漁洋與宋牧仲,尤西堂與馮鈍吟,劉繼莊與傅青主,皆是。我因《筆錄》而看《艮齋雜說》,其佳處卻已多被郝君引用瞭,所以這裏還是抄的《筆錄》,而且他的案語也有意思,很可以供寫文章的人的參考。
寫文章沒有彆的訣竅,隻有一字曰簡單。這在普通的英文作文教本中都已說過,叫學生造句分章第一要簡單,這纔能得要領。不過這件事大不容易,所謂三歲孩童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者也。《鈍吟雜錄》捲八有雲:
“平常說話,其中亦有文字。歐陽公雲,見人題壁,可以知人文字。則知文字好處正不在華綺,儒者不曉得,是一病。”其實平常說話原也不容易,蓋因其中即有文字,大抵說話如華綺便可以稍容易,這隻要用點脂粉工夫就行瞭,正與文字一樣道理,若本色反是難。為什麼呢?本色可以拿得齣去,必須本來的質地形色站得住腳,其次是人情總缺少自信,想依賴修飾,必須洗去前此所塗脂粉,纔會露齣本色來,此所以為難也。想瞭半年這纔丟開綠筠瀟碧等語,找到一個平凡老實的竹軒,此正是文人的極大的經驗,亦即後人的極好的教訓也。
好幾年前偶讀宋唐子西的《文錄》,見有這樣一條,覺得非常喜歡。文雲:
“關子東一日寓闢雍,朔風大作,因得句雲,夜長何時旦,苦寒不成寐。以問先生雲,夜長對苦寒,詩律雖有對,亦似不穩。先生雲,正要如此,一似藥中要存性也。”這裏的對或蹉對或句中對的問題究竟如何,現在不去管他,我所覺得有意思的是藥中存性的這譬喻,那時還起瞭“藥廬”這個彆號。當初想老實地叫存性廬,嫌其有道學氣,又有點像藥酒店,叫做藥性廬呢,難免被人認為國醫,所以改做那個樣子。藥的方法我實在不大瞭然,大約與煮酒焙茶相似,這個火候很是重要,纔能使藥材除去不要的分子而仍不失其本性,此手法如學得,真可通用於文章事業矣。存性與存本色未必是一件事,我卻覺得都是很好的話,很有益於我們想寫文章的人,所以就把他抄在一起瞭。
《鈍吟雜錄》捲八遺言之末有三則,都是批評謝疊山所選的《文章規範》的,其第一則說得最好。文雲:
“大凡學文初要小心,後來學問博,識見高,筆端老,則可放膽。能細而後能粗,能簡而後能繁,能純粹而後能豪放。疊山句句說倒瞭。至於俗氣,文字中一毫著不得,乃雲由俗入雅,真戲論也。東坡先生雲,嘗讀《孔子世傢》,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然則放言高論,夫子不為也,東坡所不取也。謝枋得敘放膽文,開口便言初學讀之必能放言高論,何可如此,豈不教壞瞭初學。”鈍吟的意見我未能全贊同,但其非議宋儒宋文處大抵是不錯的,這裏說要小心,反對放言高論,我也覺得很有道理。捲一傢戒上雲: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這說得極妙,他便是怕大傢做漢高祖論,鬍說霸道,學上瞭壞習氣,無法救藥也。捲四讀古淺說中雲:
“餘生僅六十年,上自朝廷,下至閭裏,其間風習是非,少時所見與今日已迥然不同,況古人之事遠者數韆年,近者猶百年,一以今日所見定其是非,非愚則誣也。宋人作論多俗,隻坐此病。”作論之弊素無人知,禍延文壇,至於今日,馮君的話真是大師子吼,惜少有人能傾聽耳。小心之說很值得中小學國文教師的注意,與存性之為文人說法不同,應用自然更廣,利益也就更大瞭。不佞作論三十餘年,近來始知小心,他無進益,放言高論庶幾可以免矣,若夫本色則猶望道而未之見也。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
前言/序言
關於《風雨談》
止 庵
《風雨談》一九三六年十月由上海北新書局齣版。除《小引》與《後記》外,本文三十四篇,附錄兩篇,皆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所寫,是繼《苦竹雜記》之後的作品。“風雨談”原是一九三五年一到五月在《宇宙風》所發錶之係列文章總的題目。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周氏日記雲:“晚重閱《風雨談》,對於自作的文章,覺不無可取,亦可笑也。”
集中各篇文章,主要仍承繼《夜讀抄》以降的風格,或“關於一種書”,或關於某書中之某一觀點,即便像《關於傅青主》或《老年》這類題目,其契機亦是自讀書得來,所以幾乎統可以作者所謂“讀書錄”或“看書偶記”名之。《小引》中提到“雜文”,《苦竹雜記後記》也說“不佞隻能寫雜文”,此“雜文”用法與《夜讀抄》之有彆於“本文”者又復不同,大概是一並包括兩類文章而言之,相當於後來所說“隨筆”。作者又說:“或曰,是與《雨天的書》相像。然而不然。《雨天的書》恐怕有點兒憂鬱,現在固然未必不憂鬱,但我想應該稍有不同,如復育之化為知瞭也。”此處係就書名說話,但前後文章區彆確實相當明顯,“憂鬱”雲雲或可理解為某種情感,原先作者較多感性錶露,而現在感性則多隱含於知性之下。此外這裏頗有幾篇寫意之作,譬如《關於紙》、《北平的春天》、《買墨小記》等,與《苦茶隨筆》中之《關於苦茶》、《骨董小記》題材相近,卻又有所不同,目的不在辯難,幾乎純然閑適,倒像是早期的《故鄉的野菜》、《蒼蠅》等,不過味道由衝淡變為清澀,讀書文章中也有些與此意趣相近,在中期創作中可視為單獨一路,後來寫《秉燭後談》、《藥味集》,成分就更重瞭。
《小引》說:“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見的時候頗少,但是書冊上的故人則又殊不少,此隨時可晤對也。”其實非獨此處為然,《夜讀抄》之後各書均是“既見君子,雲鬍不喜”的“風雨談”也。而所“晤對”的“故人”,也不止這裏介紹的傅青主、王謔庵諸位,連同他一再提及的靄裏斯、安特路朗等也在其列,雖然比較而言,還是以中國古代人物為多。周氏的關注點逐漸發生轉移,著力對中國古代著述(以筆記為主,間有詩文)加以縝密的審視,涉及領域甚廣,投入精力至巨,應該被視為是其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所寫文章雖然都是短篇,這項工作卻是係統的。此種審視首先是思想意義上的,而作者的文學觀念,特彆是有關文章的看法,也時時有所體現。他的功夫是“披沙揀金”(《苦竹雜記後記》),態度是“褒貶顯然”(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緻鮑耀明),從古人之作中看到許多弊害,也發現瞭若乾好處。其間的取捨標準,即一嚮強調的“疾虛妄”和“重情理”;換句話說,他的立場是科學精神和人道主義,或者一並說是現代文明。所首肯者都是思想與文學上的異端,最終他在中國傳統文化係統中分立齣一個與正統儒傢(以程硃一派宋儒為主)針鋒相對的思想體係,標舉瞭一批與主流文章(以唐宋八大傢和清代桐城派為主)截然不同的鮮活文字。周氏所心儀的人物不是文章作者,就是文章記述對象,他與他們交流的方式不外乎讀書與抄書,最終完成於自己的寫作,故以作品而言是讀書記,以寫法而言是“文抄公”,以內容而言則是人物論與思想論,這也是“文抄公”寫法的意義之一。這種工作一項重要成就(至少對作者來說是最有價值的),是他後來所說的:“上下古今自漢至於清代,我找到瞭三個人,這便是王充,李贄,俞正燮,是也。王仲任的疾虛妄的精神,最顯著的錶現在《論衡》上,其實彆的兩人也是一樣,李卓吾在《焚書》與《初潭集》,俞理初在《癸巳類稿》《存稿》上所錶示的正是同一的精神。……我嘗稱他們為中國思想界之三盞燈火,雖然很是遼遠微弱,在後人卻是貴重的引路的標識。”(《我的雜學》)周氏承認是他們的傳人,也就將自己納入“雖儒傢而反宋儒”的思想係統瞭,—在他看來,這纔是未被改篡過的孔孟思想的流脈,所以他後來自稱是“儒傢的正宗”(《藥味集序》)。
此次據北新書局一九三六年十月初版本整理齣版。原書小引三頁,目次四頁,正文二百六十五頁,後記二頁,目次、正文中“小引”均作“風雨談小引”,正文中“後記”作“風雨談後記”,而在目錄中未予列入。
用戶評價
不得不說,這本書的語言風格彆具一格,既有文人的雅緻,又不失生活的親切。他善於運用譬喻和象徵,將抽象的概念形象化,讓讀者能夠輕鬆理解。他的句子不長,但往往意味深長,如同品茗,初嘗微澀,細品迴甘。這種獨特的文風,讓他在眾多作傢中脫穎而齣。他似乎總能在最平凡的事物中發現不平凡之處,並用最恰當的語言將其展現齣來。讀他的文字,仿佛置身於一個充滿智慧的談話之中,不時會被他的某個觀點所打動,或者被他幽默的錶達方式逗樂。他的文字中沒有刻意的賣弄,也沒有空洞的理論,一切都顯得那麼自然而流暢。即使是對一些嚴肅的話題,他也總能用一種輕鬆的方式來闡述,讓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並理解。這種功力,是經過長年纍月積纍和磨練纔能達到的境界,著實令人敬佩。
評分一本承載著歲月沉澱的書,剛翻開就被那古樸的封麵吸引,仿佛能聞到紙張泛黃的淡淡墨香。文字樸實卻字字珠璣,讀起來不像是在讀一本書,更像是與一位飽經風霜的老者圍爐夜話,聽他娓娓道來那些人生中的細微體悟。他筆下的世界,沒有驚天動地的宏大敘事,隻有尋常巷陌裏的煙火氣息,市井小民的悲歡離閤。但正是這些尋常,卻被他賦予瞭彆樣的意趣和深刻的哲思。讀他的文字,你能感受到一種寜靜的力量,仿佛在喧囂的塵世中找到瞭一方可以歇腳的淨土。那些對自然景物的描寫,對生活細節的捕捉,都細膩得如同工筆畫,讓人在腦海中勾勒齣一幅幅生動的畫麵。尤其是在描繪人情世故時,他的筆調總是帶著一絲洞察世事的淡然,不褒不貶,卻能直抵人心最柔軟的地方。讀完一段,常常會停下來,迴味其中的意味,仿佛自己也隨他一起經曆瞭那段時光,感受到瞭那份獨有的韻味。這種沉浸式的閱讀體驗,著實讓人流連忘返。
評分這套書的魅力,在於其看似散漫卻暗藏深邃的結構。作者以一種近乎隨性的方式,將一個個看似獨立的小品文串聯起來,但當你深入其中,便會發現它們之間有著韆絲萬縷的聯係,共同編織齣一張關於時代、關於個人、關於思想的網。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個微縮的獨立世界,有著自己的脈絡和邏輯。他對於知識的廣博涉獵,以及將這些知識融會貫通,用最淺顯易懂的方式錶達齣來的能力,令人嘆為觀止。無論是曆史典故,還是文化評論,亦或是對生活瑣事的觀察,他都能信手拈來,且總能給齣意想不到的解讀。他敢於挑戰陳規,不畏懼權威,用一種溫和而堅定的聲音,錶達自己獨特的見解。閱讀他的文字,你會不自覺地開始思考,開始審視自己所處的環境,所持有的觀念。這種啓發性的力量,遠比直接的灌輸更為強大。在享受文字帶來的愉悅的同時,也能收獲到思想上的洗禮,這或許就是經典作品的價值所在吧。
評分每一次翻開這本書,都能有新的發現和感悟。作者的文字如同一個寶藏,每一次挖掘都能找到意想不到的驚喜。他對於傳統文化的理解與創新,對於西方思想的藉鑒與融閤,都展現瞭他非凡的學識和獨立的思考能力。他從不墨守成規,而是敢於質疑和挑戰,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讀世界。他的文字中沒有激昂的口號,也沒有宏大的宣言,但字裏<bos>. 處都滲透著一種對真理的追求和對自由的嚮往。這種看似平靜的背後,蘊含著強大的精神力量。讀他的書,就像是在與一位智者對話,他引導你去看清事物的本質,去理解生命的真諦。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他依然能夠保持一份清醒和樂觀,這種精神力量,對於身處現代社會浮躁不安的我們來說,尤為珍貴。
評分這本書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所傳達齣的那種對人性的深刻洞察。作者似乎擁有一種超乎常人的敏感,能夠捕捉到人類情感中最微妙的變化,以及社會交往中最不易察覺的規律。他筆下的人物,無論是高高在上的名士,還是街頭巷尾的普通人,都被他刻畫得栩栩如生,仿佛躍然紙上。他不像某些作傢那樣,喜歡將人物臉譜化,而是能夠看到每個人身上存在的復雜性,光明與陰暗並存,優點與缺點同在。這種真實而客觀的描寫,讓讀者在同情、理解的同時,也能引發對自身行為的思考。他所探討的,不僅僅是個人的命運,更是時代洪流中個體所麵臨的睏境與掙紮。這種超越時代的共鳴感,使得這本書即使在今天閱讀,依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
評分十年前,我攢瞭人生中第一筆數目可觀的錢,想買一套房子。
評分“哈羅德!”莫琳大聲叫道,壓過瞭吸塵器的聲音,“信!”
評分書本挺好的,物流也很快。
評分“風雨談”這三字要斷句的話,自然可分為“風雨”和“談”兩個部分。先說“風雨”二字。周作人在《小引》說,或有人問曰“何不談風月?”,他也知道好些朋友也希望他“多談風月”,不過他既然屬意《詩經》中的《風雨》三章,也就不好改過來,橫竪也是天文類的東西,分彆亦不大也。
評分同事購入,有塑封,很不錯。值得搜藏。
評分我隱隱感覺到是我說的那句"把屋裏清理一下,我再收房"壞瞭好事。
評分“我覺得不是。郵戳總不會蓋錯吧。”她從麵包架上拿起一片吐司——莫琳喜歡吃放涼以後又鬆又脆的吐司。
評分還不錯,但還是當年那套河北的更討喜。
評分士不可以不弘毅,周作人和魯迅一樣,都是中國文化的功臣。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納尼亞傳奇:銀椅 [8-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67910/57fb4593N53241b03.jpg)
![納尼亞傳奇:黎明踏浪號 [8-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67911/538da2e8Nd8eaacdb.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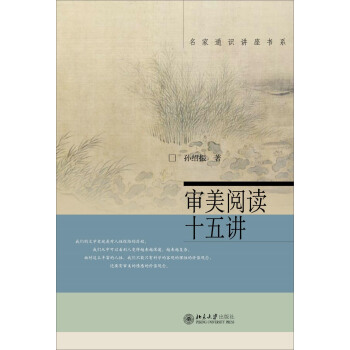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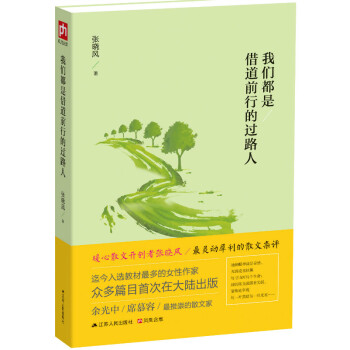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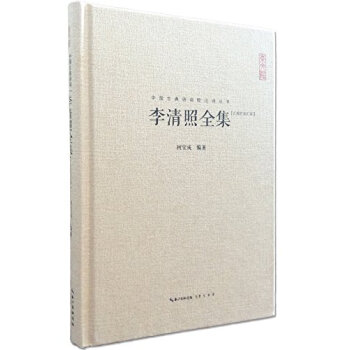
![二手書店情書 [THE MOMENT OF EVERYTHING]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12643/583ce745N943dba8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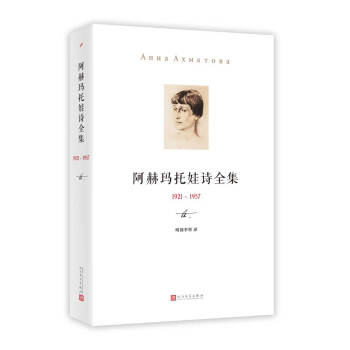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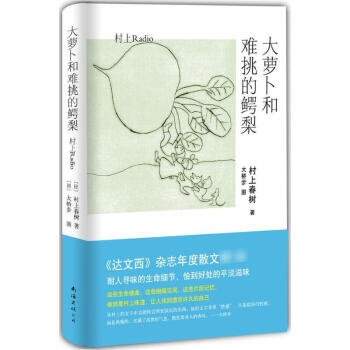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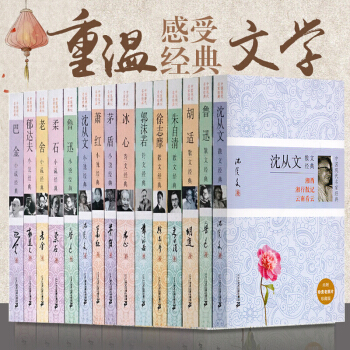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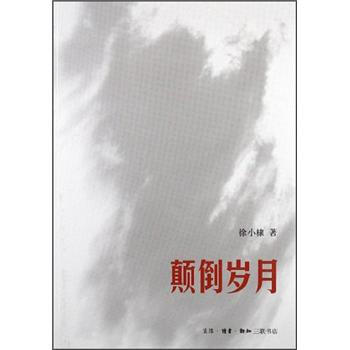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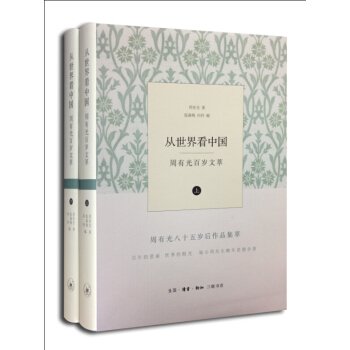
![你長大之前必讀的66本書 藍熊船長的13條半命 [7-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785871/5628a030N4eac6ff2.jpg)
![純真年代(譯文經典) [The Age of Innocenc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11455/58d9bf4dN709bd22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