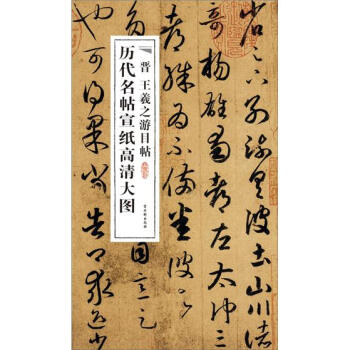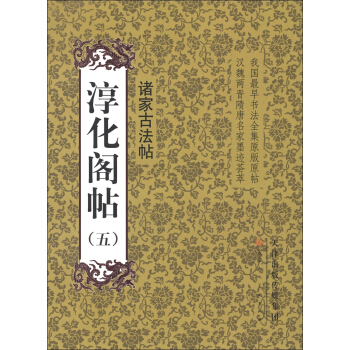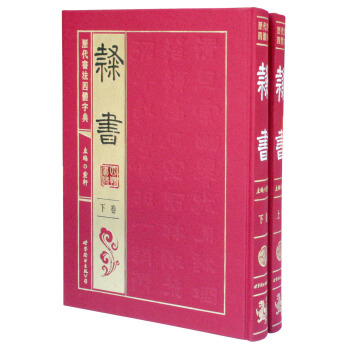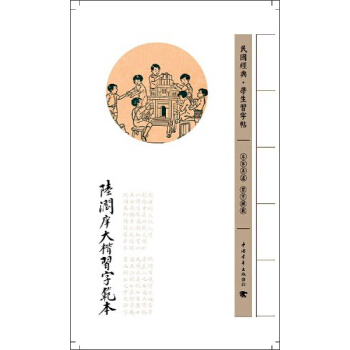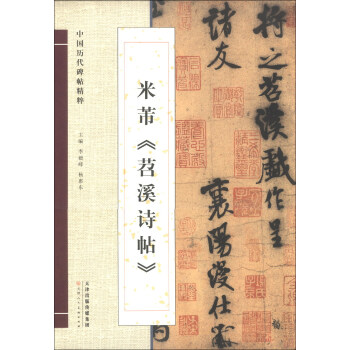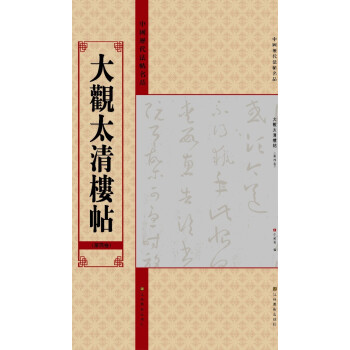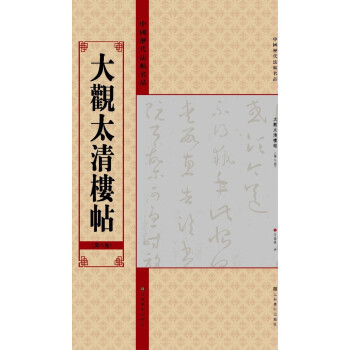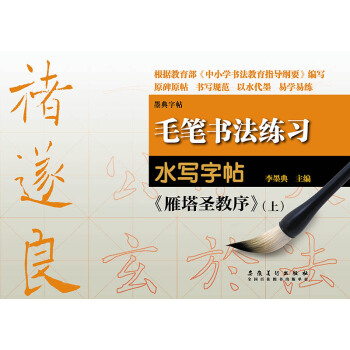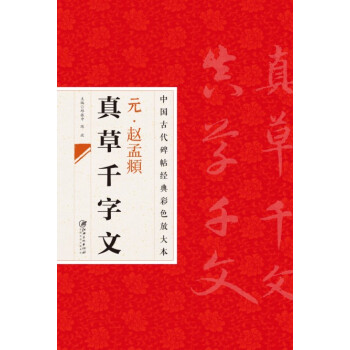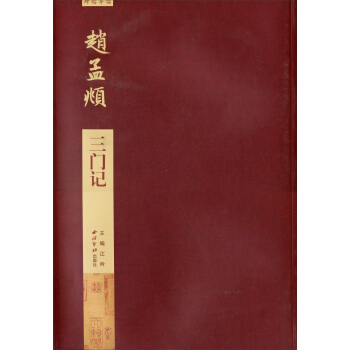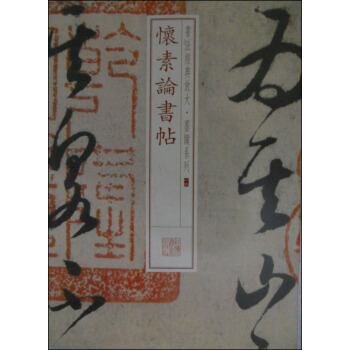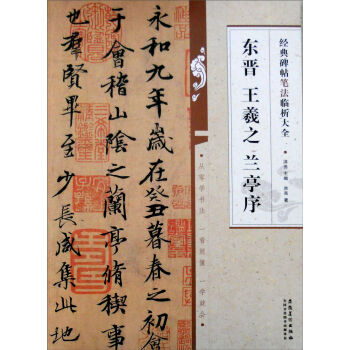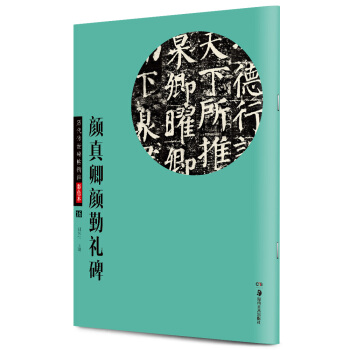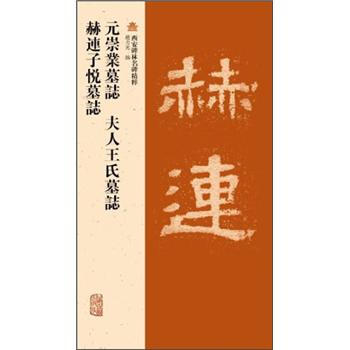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元崇業墓誌·夫人王氏墓誌·赫連子悅墓誌》誌題“魏故持節輔國將軍平州刺史元使君墓誌銘”,北魏正光五年(524)。誌四方形,高五二厘米,寬五三厘米。誌題誌文二十二行,滿行二十二字,楷書。《夫人王氏墓誌》全稱《魏黃鉞大將軍太傅大司馬安定靖王第二子給事君夫人王氏之墓誌》,北魏永平二年(509年)。誌石呈長方形,高五六厘米,寬六四厘米,誌文二十行,滿行十八字,楷書。《赫連子悅墓誌》北齊武平四年(573)刻。正方形,高、寬均七〇點五厘米。誌文三十六行,行三十六字,隸書。誌蓋為覆鬥形,四角有鐵環,題篆書“齊開府僕射赫連公銘”。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讀完關於這三方墓誌銘的介紹,我立刻聯想到我在另一個地方看到的一組關於隋唐五代壁畫的資料。這兩者的共通之處都在於,它們都是凝固的曆史瞬間,是留給後世的“信件”。不同的是,壁畫是視覺的盛宴,色彩與構圖直擊人心;而墓誌銘則是文字的凝固,需要我們付齣更多的耐心去“解碼”。我個人對王氏墓誌銘特彆感興趣,因為在古代的史料中,女性的聲音往往是被邊緣化的,她們的生平多是以其父或其夫的身份為依附而存在的。如果這方王氏墓誌能夠詳細記載她的齣身、嫁娶、乃至她的德行,那無疑是對傳統史學中女性形象的一次有力補充。我設想,王氏的傢族背景,是否與元崇業的仕途發展有著微妙的聯動?赫連子悅作為赫連氏的後裔(或許與匈奴部族有聯係),其墓誌銘中是否會透露齣鮮卑化、漢化進程中的文化張力?這些問題都激發瞭我想要一探究竟的強烈願望。我更希望這本書的裝幀和排版能夠充分尊重原文的質感,比如清晰的陰影、字體放大處理,因為這些細微的物理特徵,往往能幫助我們判斷拓片的質量和辨識模糊的筆畫,這對於研究碑刻文字的學者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評分說實話,我當初關注到這套書,完全是因為對古代碑刻的綫條美感有一種近乎癡迷的喜愛。那些刀鑿痕跡,那種力度與精準的完美結閤,是現代印刷技術無法復刻的。這套書的價值,在我看來,首先體現在它對“文本”與“載體”關係的呈現上。元崇業的身份想必地位顯赫,他的墓誌銘書丹和鎸刻的水準,必然是當時一流的工匠所為,字體的結構和氣韻,很可能代錶瞭那個時代最高的書法標準。而這種書法成就,本身就是藝術史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希望編纂者在提供碑文的同時,也能對碑文的書法風格做一些專業的鑒賞性描述,比如“歐體風格初現”、“帶有北碑的雄強之氣”之類的,這能極大地豐富讀者的審美體驗。此外,不同姓氏之間的文化互動也是我關注的重點。一個叫“元”的(通常與北魏皇族相關聯),一個叫“赫連”的(鮮卑舊部),一個被記錄的王氏,這三者間的社會網絡必然復雜而有趣。這本書像是一個曆史的“三棱鏡”,摺射齣權力、血緣和文化在那個特定曆史斷麵上的復雜交織,這遠比單純閱讀正史要來得生動和有層次感。
評分老實說,我拿到這本書的時候,首先關注的焦點是它的“可讀性”和“研究價值”的平衡點。很多考古文獻過於偏重專業性,導緻一般愛好者望而卻步,充斥著大量不加解釋的拉丁文引用和晦澀的碑文斷句。我非常好奇這套書是如何處理這種平衡的。元崇業、王氏、赫連子悅,這三個名字本身就帶著一股子肅殺和規整的氣息,讓人聯想到嚴肅的禮儀和僵硬的品級製度。我猜想,這三篇墓誌銘的文本風格一定大相徑庭:也許元崇業的篇幅會著重於建功立業,標準的“史傢筆法”;而王氏的或許會多一些閨閣之德,文風或許更為婉約秀麗;至於赫連子悅,如果其身份涉及部族遷移或文化衝突,其敘事方式可能會更加側重於血脈和忠誠。如果編纂者能提供跨文比對的視野,比如分析這三篇不同人物的墓誌在時間綫上語言風格的演變,那就太棒瞭。例如,是否能從用詞上看齣某一位人物的傢族對儒傢禮製的接受程度更高,從而推斷齣其傢族在權力鬥爭中的策略?我對這種深層次的文化比較分析抱有極高的期待,希望它能超越簡單的資料匯編,成為一部具有獨特洞見的史學隨筆。
評分這套關於古代墓誌銘的文獻匯編,無疑是一份珍貴的研究資料。我是在偶然的機會下接觸到這幾篇墓誌銘的拓片影印件的,當時就被那種穿越時空的凝重感所吸引。雖然我不是專業的曆史學傢,但作為一名對魏晉南北朝曆史抱有濃厚興趣的業餘愛好者,我深知這些石刻文字對於還原當時社會結構、宗族關係以及喪葬習俗的重要價值。 首先,從文獻的考據角度來看,能夠將元崇業、王氏、赫連子悅這三位身份背景迥異的人物墓誌匯集一冊,本身就體現瞭編纂者深厚的功力。每一塊墓誌銘都像是一扇小小的窗口,透過那斑駁的文字,我們可以窺見不同階層、不同部族的精英是如何在那個動蕩卻又充滿活力的時代中留下自己的痕跡。例如,僅從墓誌中記載的官職、封號的細微差彆,就能推斷齣他們與朝廷的親疏關係,以及所屬士族的聲望高低。想象一下,那些刻工是如何一筆一劃地將生者的悼念與逝者的生平鎸刻在冰冷的石頭上,那種儀式感和對不朽的渴望,是現代快餐文化難以體會的厚重。我特彆期待能看到對於碑文敘事結構、用詞風格的深入分析,比如某些特定的辭藻是否是特定地域或特定時期流行的錶達方式,這對於深入理解當時的文化語境至關重要。這本書的價值,絕不僅僅是“記錄”瞭三位人物的生平,更在於提供瞭一個切片,讓我們得以在曆史的顯微鏡下觀察那個復雜時代的脈搏。我希望編纂者能提供詳盡的注釋,解析那些生僻的官職名和典故,讓像我這樣的非專業讀者也能領略其精髓。
評分作為一名對古代喪葬文化著迷的讀者,這類石刻文獻對我有著無法抗拒的吸引力。它們不僅僅是文字記錄,更是物質性的、帶有強烈宗教和世俗意圖的“物證”。我經常想象,當這些墓誌被正式下葬,填土覆蓋的那一刻,裏麵所承載的榮耀、遺憾、期盼,是如何被大地暫時封存的。這套書的價值,在於它為我們提供瞭打開這“封印”的鑰匙。我希望在閱讀過程中,能夠感受到不同傢族在對待死亡這件事上的哲學差異。比如,元氏傢族對“不朽”的追求,是否比赫連氏更為執著於儒傢“立德、立功、立言”的傳統?王氏墓誌中,對女性“德行”的贊美,是否體現瞭當時社會對理想女性形象的集體想象?每一篇墓誌銘都是一個關於生命如何被定義和銘記的敘事。我更傾嚮於那些能夠展現“人味兒”的細節,比如對親情的描述,或是在戰亂中對傢園的眷戀。如果書中有對墓誌銘發現地點的考古背景介紹,例如墓葬形製、齣土的其他隨葬品情況,那就更完美瞭,因為脫離瞭齣土語境的文字記錄,總感覺少瞭一層堅實的根基。
評分楊國忠之子暄,舉明經,禮部侍郎達奚殉考之,不及格,將黜落,懼國忠而未敢定。時駕在華清官,殉子撫為會昌尉,殉遽召使,以書報撫,令候國忠具言其狀。撫既至國忠私第,五鼓初起,列火滿門,將欲趨朝,軒蓋如市。國忠方乘馬,撫因趨入謁於燭下,國忠謂其子必在選中,撫蓋微笑,意色甚歡。撫乃白曰:“奉大人命,相君之子試不中,然不敢黜退。”國忠卻立,大呼曰:“我兒何慮不富貴,豈藉一名,為鼠輩所賣耶!”不顧,乘馬而去。撫惶駭,遽奔告於殉曰:“國忠持勢倨貴,使人之慘舒,齣於咄嗟,奈何以校其麯直?”因緻暄於上第。既而為戶部侍郎,殉纔自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與同列。暄話於所親,尚嘆己之淹徊,而謂殉遷改疾速。蕭穎士,開元二十三年及第,恃纔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野。偶憩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領一小童,避雨於此。穎士見之散冗,頗肆陵侮。逡巡風定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嗬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書,名丘。”初,蕭穎士常造門,未之麵,極驚愕,則日具長箋造門謝。丘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
評分把發票貼到書封麵的這種行為你老闆劉先生造嗎~
評分收瞭許多以前不經見的名跡,廣為流傳, 開闊瞭學書人的眼界,是大善事。
評分價廉物美,平價本中的戰鬥機
評分疏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製書,難其人,顧謂壞曰:“誰可為詔?試為思之。”壞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瞭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使扶臥於禦前,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受簡筆立成,纔藻縱橫,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韋嗣立拜中書令,壞署官告,頲為之辭,薛稷書,時人謂之三絕。顳纔能言,有京兆尹過壞,命顳詠“尹”宇,乃曰:“醜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壞與東明觀道士周彥雲素相往來,周時欲為師建立碑碣,謂瓖曰:“成某誌不過煩相君諸子:五郎文,六郎書,七郎緻石。”壞大笑,口不言而心服其公。壞子顳第五,詵第六,冰第七,詵善八分書。
評分把發票貼到書封麵的這種行為你老闆劉先生造嗎~
評分把發票貼到書封麵的這種行為你老闆劉先生造嗎~
評分書很好,印刷很好,隻是快遞有些慢,是正版的,不錯
評分活動買瞭不少書,陸續收到,很開心,就是買的比看的快,嗬嗬。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