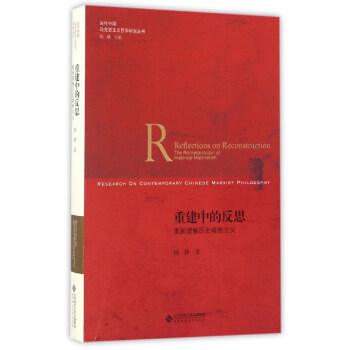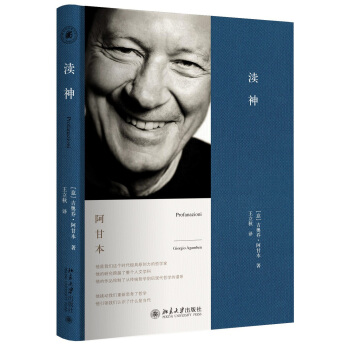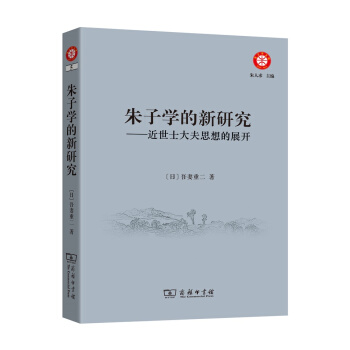![莱布尼茨 [Leibniz]](https://pic.tinynews.org/11256159/rBEhU1HELgQIAAAAAAQvqfMmVMsAAAacAPWXesABC_B798.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晦涩难懂有两个原因。一,他著名的单子论和另外一个观点,即现实世界是所有可能被创建的世界中好的一个,听上去似乎是无稽怪谈。第二,他的哲学思想都是从他的无数篇散文和信件中提炼出来的。尽管他的哲学论述形式上比较支离破碎,莱布尼茨也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中有一个取自于新柏拉图主义的主导观点:宇宙是存在体的集合,反映了它们的创造者上帝。这个论点贯穿于他的形而上学观,而他的形而上学又主要试图寻找“世界上到底有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莱布尼茨给出了一个成熟的理想化的答案,即宇宙的基本构建模块是单子或类灵魂的实体,它们是简单的,非物质的,并具有始因自给自足的特性,这些也反映了上帝的特点。“上帝的镜子”的主题在莱布尼茨对人类心灵的研究中尤为凸显,也极大影响了他的知识理论、对自由的探究甚至他对恶的问题的答案的找寻。接下的章节讨论了“上帝的镜子”的主题构建了他“综合”的基础:因为所有的心灵都反映了上帝的无所不知,所以所有的哲学家都对真理有一定程度的认知理解。本着这种精神,莱布尼茨试着去整合各个不同的哲学流派的观点。笛卡尔在莱布尼茨之前试着去调和新科学与传统宗教教义间的矛盾,莱布尼茨除此之外还试着去调和古代人和现代人思想上的矛盾,以及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观点冲突。引言的结尾部分介绍了莱布尼茨“系统的哲学家”的称号最近受到了质疑,并为他进行了辩护。莱布尼茨的确从未像斯宾诺莎一样用几何学的方式展开哲学论述,而且在一些核心问题上和观点上,他的思想还在不断地变化发展,没有形成定论。比如说,物体在形而上学中的地位问题等。然而莱布尼茨能意识到他的思想对他哲学的其他领域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例如,他关于真理的理论并不是孤立的,而对他解决恶的问题有着重大的影响。目录
英文著作缩写表莱布尼茨年表
导言
上帝的镜子
综合之策
一个系统的哲学家?
总结
拓展阅读
第一章莱布尼茨:生平与著作
早年岁月
汉诺威市:身份和职责
《论形而上学》及与安托万·阿诺德的书信来往
新体系
莱布尼茨、洛克与《人类理智新论》
《神正论》
《单子论》及相关作品
莱布尼茨与克拉克的通信:与牛顿学派的论争
结论
总结
拓展阅读
第二章实体的形而上学:整体性与能动性
整体性:对笛卡尔的评论
能动性:对偶因论的评论
逻辑学策略
因果性与创造
本体论的问题
总结
拓展阅读
第三章单子论
单子的特性
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单子
身体的地位
有形实体与实体链
时间、空间、单子
总结
拓展阅读
第四章心灵、知识和观念
非物质的心灵
心灵、身体及前定和谐
先天说(1):天赋观念
先天说(2):天赋知识
倾向及对先天说的辩护
无意识的知觉
总结
拓展阅读
第五章人类和神性自由
知识背景:笛卡尔和斯宾诺莎
自由:基本分析
偶然性和人类自由
偶然性与神性自由
法则,解释和目的因
总结
拓展阅读
第六章关于恶的问题
新形势下“伊壁鸠鲁的老问题”
可能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世界
评价的标准
恶的种类
总结
拓展阅读
第七章伦理与政治
道德心理学
上帝之城
正义
政治共同体
莱布尼茨对霍布斯的批评
总结
拓展阅读
第八章遗产与影响
莱布尼茨同时代人的反馈:法国与英国
反体系运动
伏尔泰、乐观主义与神正论
莱布尼茨、康德与德国唯心主义
重新发现莱布尼茨
总结
拓展阅读
术语表
参考文献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非常精妙,它不是那种线性推进的传记体,也不是单纯的理论堆砌。作者巧妙地将历史背景的描绘、关键人物的生平轶事,与他们哲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交织在一起。读起来有一种强烈的“沉浸感”,仿佛我们不是在阅读一本关于过去思想家的书,而是亲历了那个思想孕育和爆发的时代。特别是在描述其思维方法的演变时,那种层层递进、不断自我修正的“心路历程”,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能感受到作者在引用原始文本和进行现代诠释之间的微妙平衡,他没有过度“美化”或“简化”那些古老的争论,而是保留了其原始的复杂性与火花。这种处理方式,极大地避免了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符号化、脸谱化的风险。每当读到某个关键转折点,我都会忍不住合上书本,走到窗边,望望远方,思考着:如果我身处那个时代,面对同样的问题,我的答案会是什么?这种被激发出的主动思考,才是衡量一本思想类书籍价值的最高标准。
评分这本书的知识密度令人惊叹,但更难得的是它所构建的“知识网络”的韧性和广度。它不像某些专业著作那样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的领域内,而是像一个多功能的枢纽,将数学、形而上学、逻辑学乃至神学等看似不相关的领域,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串联起来。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在脑海中建立新的联想:一个关于无限的概念,突然联系到了我先前读过的关于几何学的片段;一个关于实体论的讨论,又影射出当时社会政治的某些张力。作者的功力在于,他让这些连接自然而然地发生,而不是生硬地进行跨界嫁接。这使得阅读体验非常充实,仿佛我不是在阅读单一的知识点,而是在参与构建一个微缩的知识宇宙。对于那些渴望全面理解一位思想家全貌的求知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多维度的框架,足以支撑起未来深入研究的各种可能路径。
评分这本书的魅力还在于它提供的“历史定位感”。作者并未将这位思想家置于真空中进行神化,而是将其置于其所处的时代洪流之中,描绘了他如何回应前人的挑战,又如何为后世埋下了伏笔。通过作者细腻的笔触,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知识精英之间复杂的互动与较量。这种历史的纵深感,使得书中的理论不再是孤立的教条,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智慧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做出的最精妙的尝试之一。更令人感到亲切的是,作者在书的收尾部分,对该思想家思想在当代的“遗留问题”和持续的影响力进行了审慎的探讨。这提醒了我们,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并非尘封的古董,而是不断与当代问题产生共振的活水源头。这本书成功地架起了一座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桥梁,让读者在阅读完后,依然能感受到那股思想力量的余温,久久不散。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本身就透露着一股沉静而深刻的气息,厚实的纸张,带着微微的纹理感,让人在捧起它的时候就能感受到一种知识的重量。内页的排版非常考究,字体选择典雅而不失现代感,大段的文字在留白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清晰易读。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概念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近乎艺术家的耐心与精准。他似乎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比喻和最清晰的逻辑链条,将那些看似晦涩难懂的哲学思辨,化为可以被日常语言捕捉的形态。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反复琢磨某个句子,感受那种思想的张力。这不是那种快餐式的阅读体验,它更像是一场漫长的、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对话,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推开了一扇通往更深层理解的大门。那种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错综复杂的星图前,虽然暂时迷失了方向,但每当找到一颗明确的星体(一个清晰的论点),整个宇宙的结构便又清晰了一分。这种阅读的“阻力”非但没有让人却步,反而成了吸引我不断前行的动力,因为它预示着,彼端等待我的,是真正有价值的洞见。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对读者的认知负荷是相当大的。它毫不留情地挑战了我们习惯性的思维定势。作者在阐述其核心方法论时,所使用的语言风格是高度精确和内敛的,几乎没有多余的情感渲染,一切都建立在严密的逻辑推理之上。这要求读者必须保持高度的注意力,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否则很容易在复杂的定义和前提中迷失方向。然而,正是这种“毫不妥协的严谨”,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近乎科学文献的可靠性。一旦你成功地跟上了作者的思路,那种“啊哈!”的顿悟时刻是无与伦比的——它带来的不是简单的信息获取,而是一种思维模式的彻底重塑。我用了比预期多得多的时间来消化某些核心章节,但这绝不是浪费,而是必要的“打磨”过程,它迫使我提升了自己的思维清晰度和逻辑辨识能力。这本书,与其说是在讲述思想,不如说是在训练读者如何进行高强度的理性思考。
评分《韩非子》全书,若按涉及人群划分,可分为五类:君主、官员、民人、知识分子、法术之士。五类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类,互有交叉、交融,但分类的界限,是存在的。韩非属不属于法术之士,韩非自己,没有像“我是共产党员”那样,明确说过;但韩非在《问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透过此言,假如说韩非对于法术之士,正像鲁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一样,视己为其中一员,应当不是什么牵强、穿凿之论(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的那段话,也应视为此意)
评分殖民地的原始边界是在英格兰划分的,而划界的那些人从来没去过美洲,甚至连合适的地图都没有。他们的决定是基于政治便利的考量,而不是经济。然而,一旦建立起殖民地,在那些边界内部的转运点就出现了城镇。问题是:“运送什么东西?”这就是由经济现实决定的了。自然禀赋——气候、土壤分布、地形、树木和矿产的种类和数量——都是给定的。使用当时的知识、技术和机械设备对它进行开发都遵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原则(任何人都专门生产自己效率相对较高的生产和服务)。这决定了它们的基本发展方向。
评分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书很好,我已经快速读一遍了在商店里我们可以看看新出现的商品,不一定要买但可以了解他的用处,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广度,扩宽我们的视野,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不断更新,新出现的东西越来越多,日益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而我们购物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分析,不要买些外表华丽而无实际用处的东西,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爱对新生的事物好奇,会不惜代价去买,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京东商城的东西太多了,比淘上的东西还要多,而且都是正品,我经过朋友的介绍来过一次,就再也没有去过别的购物网站了。书不错 我是说给懂得专业的人听得 毕竟是小范围交流 挺好,粘合部分不是太好,纸质还是不错的,质量好,封装还可以。虽然价格比在书店看到的便宜了很多,质量有预期的好,书挺好!之前老师说要买 但是是自愿的没买 等到后来说要背 找了很多家书店网上书店都没有 就上京东看看 没想到被找到了 好了,我现在来说说这本书的观感吧,一个人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腔调,不论说话还是写字。腔调一旦确立,就好比打架有了块趁手的板砖,怎么使怎么顺手,怎么拍怎么有劲,顺带着身体姿态也挥洒自如,打架简直成了舞蹈,兼有了美感和韵味。要论到写字,腔调甚至先于主题,
评分由于私人利益是大多数殖民地经济活动——开发那些由特许授予的产权——的主要目标,因此人们最希望的是收益最大化。最初的发展是在试错的基础上进行的。正如我们讨论过的,第一批英格兰殖民者面对的是一个新的环境,这里有不同的气候和各种未知数。这里适合种哪种小麦?哪种本地作物,比如玉米和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被殖民者引入到北美)和南瓜可以作为人类的食物?烟草最适合在哪里种植?什么可以作为牲畜的饲料?以及哪种牲畜最适合殖民地使用?这些问题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去一件件尝试,从失败中学习经验,然后再次尝试。由于英格兰人急于摆脱对他们的欧洲竞争者的依赖,因此他们对引种新作物比如桑树(为了养蚕)和姜实行了补贴和保护性措施。在南方,水稻和靛青这两种引种作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另外,殖民者仍然抱着寻找黄金和白银的希望;少量的黄金不时被找到,一起被发现的还有大量低值金属矿藏。
评分李斯能不成为他的目标?
评分如果说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是已下定决心,要投身秦帝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加入到历史的洪流铁蹄,那韩非与李斯的矛盾,就顺理成章。
评分微博上多了有个副作用,长篇大论的文字看不大下去了。近日一直在读吴藕汀的《孤灯夜话》,小品文,多是短短几行,类微博。文字却相当有趣,地理风俗,典故食材,信笔写来。里面对一些书与前人的评价多与世俗迥异,如李清照晚年不曾改嫁,水浒诲盗诲淫,红楼,三国与封神作者问题等等,读来甚觉新鲜。
评分微博上多了有个副作用,长篇大论的文字看不大下去了。近日一直在读吴藕汀的《孤灯夜话》,小品文,多是短短几行,类微博。文字却相当有趣,地理风俗,典故食材,信笔写来。里面对一些书与前人的评价多与世俗迥异,如李清照晚年不曾改嫁,水浒诲盗诲淫,红楼,三国与封神作者问题等等,读来甚觉新鲜。
评分吴藕汀先生自幼家道殷实,过着左琴右书的生活,但成年之后,太半人生处动荡之世,个人命运便如一叶处江流之中。即便如此,先生仍能保持“自由之思想,人格之独立”,这于生者而言,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孤灯夜话》是吴藕汀先生的又一本随笔集。由于时代的原因,先生的大部分文字都是写在烟盒纸上,或小学生的方格本上,字体大小不一,他人难以辨认,整理这些文字的繁重任务,大部分由其哲嗣吴小汀先生承担。小汀先生说:“先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曾表示,就这样随意地写,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为尊重藕公的想法,保持作品原貌,编辑只根据文字量的多少简单分了九卷,修正了一些整理稿中明显的错讹文字,通过查询相关资料补充了一些整理稿中缺失的文字。《夜话》内容涉及金石书画、版本考据、填词赋诗、种药养虫、人物故实、京昆弹词、社会变迁,可谓琳琅满目。文字处处见性情,像日记,又像时评。面对这样一位知识渊博又有真知灼见的文化老人,就如同坐拥一座格调不俗、藏品丰富的图书馆,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打开这本书,安安静静地读下去。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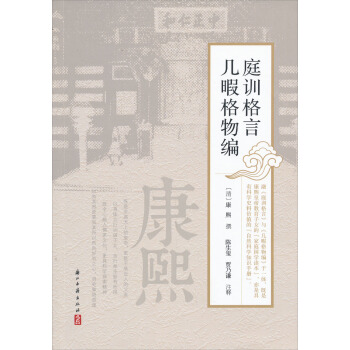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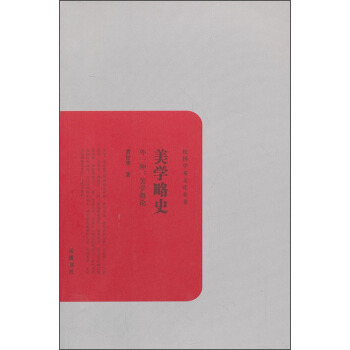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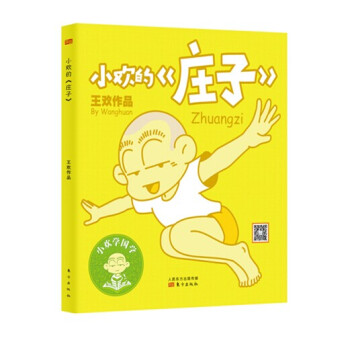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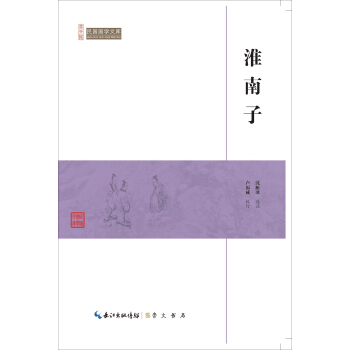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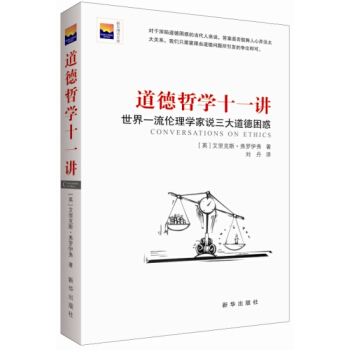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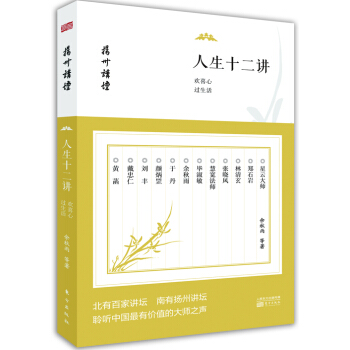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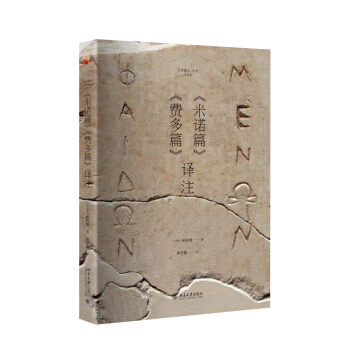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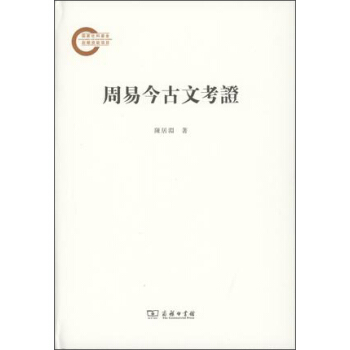


![素描的愉悦 [Le Plaisir au dessi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86035/583fe901N4f1bb7c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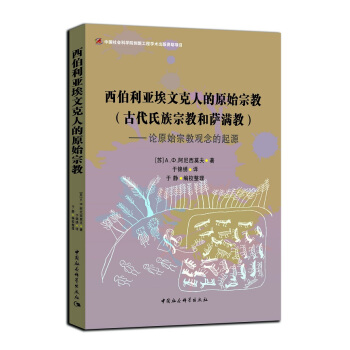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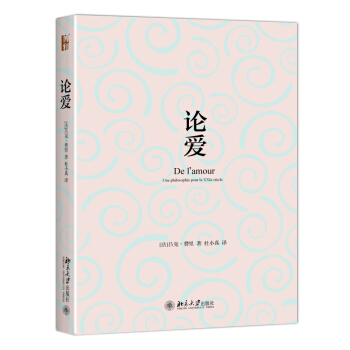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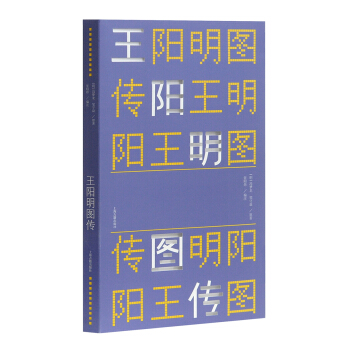
![伦理学中的非认知主义 [Noncognitivism in Ethic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10022/587c9fa8N88c69ad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