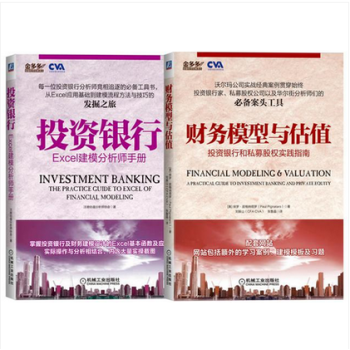![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 [A Study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 Clean and Honest Administration in China]](https://pic.tinynews.org/11407561/rBEhVFMOxdsIAAAAAAF9x2CZIZEAAJJmwGKN2AAAX3f620.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依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地考察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产生、主体内容及其特征;逻辑地分析了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动力、路径、目标及其具体实现;最后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进行了探索性的建构。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历史考察
第一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 农耕社会中的自然经济基础
二 宗法血缘关系下的政治条件
三 古代关于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文化思考
四 中国古代贪贿盛行的社会现实
第二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主体内容
一 廉政教育文化
二 古代清官文化
三 廉政制度文化
四 廉政监督文化
五 反腐惩贪文化
第三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 廉政取向的君本性与廉政价值的工具化
二 廉政主体的单一性及廉政基础的薄弱性
三 廉政模式的德治主导性与廉政治理的人治化
第二章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动力分析
第一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何以必要
一 社会历史条件变化的时代需要
二 传统廉政文化克服自身局限走向现代化的需要
三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夯实传统根基的需要
第二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何以可能
一 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可遗传性特质
二 廉政文化建设具有内在的规律性
三 中华文化当代传承者的科学理论指导
第三章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路径设计
第一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原则
一 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
二 科学性与价值性相协调的原则
三 大众性与先进性相统一的原则
第二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方式
一 文化形式的转换
二 文化内容的转换
三 文化功能的转换
第三节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方法
一 批判继承法
二 借鉴改造法
三 综合创新法
第四章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目标定位
第一节 由廉政取向的君本性向民本性转换
一 传统廉政取向以君为本的政治末路
二 当代廉政取向以民为本的时代呼唤
第二节 由廉政主体的单一性向多样性转换
一 廉政主体的单一性致使古代廉政回天乏力
二 主体的多样性是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
第三节 由廉政价值的工具化向目的化转换
一 工具价值:传统廉政文化价值特性的迷茫
二 目的价值: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理性选择
第四节 由廉政模式的德治主导型向德法并重型转换
一 德治主导型的传统廉政模式之缺陷
二 当代廉政模式之德法并重的价值选择
第五节 由廉政治理的人治化向制度化转换
一 传统廉政治理人治化弊端丛生
二 当代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化趋势
第五章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的具体实现
第一节 传统廉政教育文化的现代转换
一 教育目的由培养廉吏忠臣转换为培育公职人员廉洁奉公的品质
二 教育对象由面向官僚贵族转换为面向党员干部与社会大众
三 教育内容由道德教育向理想信念与道德法制教育转换
四 教育方式由单向的廉政教化向全方位的廉政教育渗透转换
第二节 中国古代清官文化的现代转换
一 廉政榜样的引领由塑造清官向树立现代公仆形象转换
二 廉政信仰的树立由人格化的清官信仰向制度化的法律信仰转换
第三节 传统廉政制度文化的现代转换
一 从选官用廉制度向完善党政干部选拔制度转换
二 从考核促廉制度向完善党政干部廉政责任制转换
三 从俸禄养廉制度向完善公务员的工资福利制度转换
四 从廉政刑罚制度向完善现代廉政法律制度体系转换
第四节 传统廉政监督文化的现代转换
一 监督关系由官对官的监察向权力对权力的监督转换
二 监督形式由监察机构一体化监督向多种监督并存转换
三 监督体制由自上而下的垂直监察向多种监督形式的互动转换
第五节 传统反腐惩贪文化的现代转换
一 反腐理念由突出事后惩处向惩防并举、重在预防转换
二 对贪贿罪的惩处由传统刑罚的野蛮性向现代刑法的文明性转换
第六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
第一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理论资源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思想基础
二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的廉政理论指导
三 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后的价值资源
四 西方社会关于廉政建设的文化资源借鉴
第二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内容体系
一 清明廉洁的政治文化
二 清廉公正的行政文化
三 清正廉明的干部文化
四 服务公道的职业文化
五 廉荣贪耻的社会文化
第三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时代意义
一 为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提供文化支撑力
二 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文化引领力
三 为营造廉荣贪耻的社会氛围提供文化凝聚力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首先,从文化形态的表现形式看,传统廉政文化的表现形态有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等。其中,以物质文化为表现形态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通过直观的器物文化表现出中国古代的廉人廉事。如纪念被誉为“包青天”的北宋清官包拯而分别在开封与合肥建立的包公祠;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海瑞墓,其中便建有“扬廉轩”和“清风阁”;明代万历年间为表彰清官赵邦清而在甘肃正宁县建立的“清官坊”。陕西蒲城县博物馆石刻艺术室内的“清官碑”(为纪念清道光年间时任蒲城知县的蔡信芳而立。蔡信芳任蒲城知县期间,重土爱民,操守清廉,秉公办案,颇有善政,深受百姓爱戴。在他离任回乡时,当地绅民写诗赞他:“罢郡轻舟回江南,不带秦中一寸棉。”);等等。又如反映三国时期郁林(今广西玉林)太守陆绩为官清廉的“廉石”(即陆绩在郁林任太守时,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在任满回家时,除了简单的行装和几箱书籍外,再无别的东西可带。为了行船安全,陆绩买了一担笋干、两大瓮咸菜,并让船工搬了一块大石头用来压舱,得以平安返归故里。后人为了纪念陆绩,将其压舱石称为“廉石”。)等。这些器物文化成为古代清官为政清廉的有力佐证。其次,以精神文化为表现形态的传统廉政文化,主要是通过观念的形式体现出对廉政的认知。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不同层面的人物对廉政的认知。如统治者对廉政的认知:“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①思想家对廉政的认知:“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②“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③百姓对廉政的认知:“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等等。这些无不表达对为人为官廉为本的观念认识。再次,以制度文化为表现形态的传统廉政文化,则是通过确定性的法律形式来保证廉政价值实现所形成的文化。最后,从文化载体的表现形式来看,传统廉政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官方的档案文献、经史子集等著作、楹联、谚语、歌谣及民间故事等。如历代廉政制度文化的载体为官方的档案文献;历代思想家廉政认知的载体乃经史子集著作。而一些廉人廉事或一些廉政认知,则通过楹联、谚语、诗歌、歌谣及民间故事等形式表现出来。……
前言/序言
廉,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是指“堂之边”或“厅堂上方有棱角的横梁”。如《仪礼·乡饮酒礼》日:“设席于堂廉,东上。”郑玄注日:“侧边日廉。”段玉裁注《说文解字》肯定了“廉”为“堂之边”或“厅堂上方有棱角的横梁”之说法。其中日:“堂之边日廉”、“堂边皆如其高”、“廉远地则堂高,廉近地则堂卑”、“堂边有隅有棱,故日廉”。又日:“廉之言敛也”、“廉,隅也;又日廉,棱也。引申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由于“堂之边”或“厅堂上方有棱角的横梁”,均具有平直、方正、棱角分明等特点,于是,“廉”被赋予“清正、堂正、洁净”等道德内涵,并常常与“清”、“洁”、“正”、“明”等词搭配,组成“清廉”、“廉洁”、“廉正”、“廉明”等固定的用语,表示清白不污、堂正不邪、公正不偏、廉洁不贪等道德含义。正因为“廉”具有上述道德规范属性,人们自古以来便将“廉”与“政”连用,组成“廉政”一词,表达了对政治、行政或政府等与“政”相关联的一切活动的价值期待。“廉”与“贪”相对立而存在。作为“贪”的对立面而存在的道德规范,“廉”的基本含义是“不贪”。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贪”就是“妄取”、“苟得”。所以,“廉”就是不妄取、不苟得、不受无义之财。如《楚辞·招魂》日:“朕幼清以廉洁兮。”王逸注日:“不受日廉,不污日洁。”在这里,“受”,就是“妄取”,就是“贪”。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①在这里,“取”,就是指“妄取”。在孟子看来,廉,就是不取身外之物,不贪不义之财;否则,会伤害到廉洁的品性。韩非子认为,廉,就是不贪财、洁身自爱。他说:“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②“贤士者修廉而羞与奸臣欺其主。”③韩非子甚至把那种不求廉德而贪财者斥为盗跖之人。他说:“毁廉求财,犯刑趋利,忘身之死者,盗跖是也。”①庄子也认为,求己之利而不损人之利是谓廉者。他说:“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②在庄子看来,“廉”即是“不贪”,而社会上之所以出现混乱不堪的局面,主要是因为一些人太贪的缘故。即“不足故求之,争四处而不自以为贪……廉贪之实,非以迫外也,反监之度”③。就是说,人之廉洁与贪婪,并非迫于外力造成,而应该回过头来反思自己是否总是与人争利,是否为了一已之私利而损害人之利。可见,不贪为廉,在中国先秦思想家那里已成为一种共识。
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家也普遍认为,“廉”就是“不妄取”、“不苟得”,即“不贪”。汉代经学家刘向认为,廉洁之士不妄取,即“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④。并劝导世人“临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⑤。晋代道学家葛洪认为,廉,就是不苟得。他说:“睹利地而忘义,弃廉耻以苟得者,贪人也。”⑥隋代思想家王通认为:“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⑦就是说,廉洁之士没有非分之想,贪婪之人则常常为无法填平心中的欲望而烦恼。元代史学家徐元瑞认为,尚廉、尚勤、尚能,此“三尚”是为官者应当树立的三种品质。所谓尚廉,就是要甘心淡薄,洁身自好,不受不义之财,即“谓甘心淡薄,绝意纷华,不纳苞苴,不受贿赂,门无请谒,身远嫌疑,饮食宴会,稍以非义,皆谢却之”⑧。明代思想家薛瑄认为,廉,就是不妄取、不苟取、不贪婪,并将“廉”划分为“不妄取”、“不苟取”、“不敢取”三个层次。他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⑨在薛碹看来,“不妄取”是“廉”的最高层次,也是“廉”的最高境界,因为它代表了一种理性的自觉行为;“不苟取”是“廉”的第二个层次或较高境界,它也是一种自觉行为,不过这种自觉是在权衡了利害关系之后作出的道德选择,即“名节”比“苟取”更重要;“不敢取”是“廉”的三个层次中的最低层次。它也是在权衡了利害关系之后作出的道德选择,不过这种选择主要是在他律作用下的结果,即出于畏惧法律以保禄位而进行的选择。尽管如此,这依然属于清廉之列。毕竟,这种在他律作用下而发生的“廉”之行为,也带有一种自律的因素(即被动式自律),但其自我约束的功能依然存在;而不像贪者那样,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损人利己。正所谓“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必腹人以肥己”①。
“廉”之所以被界定为“不贪”,这是基于对人们在实现自己的欲望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中的道德诉求。欲望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原初动力,也是社会实践活动的动力源。但是,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人的社会关系性质表明,人类欲望的满足不可能脱离社会关系来实现,人类满足生存和发展欲望的活动,必须超越纯粹的自然存在而达到社会存在。就是说,欲望必须具有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前提是,欲望必须是现实可行的,而且实现欲望的手段必须是正当的。对此,在两千多年前的中西方思想家那里,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求利手段的正当性问题。在中国,孔子就主张“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③,并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④。在古希腊,苏格拉底认为,只有以“公道、审慎、虔诚”,即道德手段的方式取得财富,才是美德。⑤可见,突出实现欲望(即求利)手段的正当性,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认识。恩格斯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必须受到双重的矫正。一是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二是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即我们在追求幸福的欲望时,必须承认他人也有着追求幸福的欲望。如果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么势必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因此,“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另一方面还必须承认他人有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①。恩格斯的论述表明,欲望之价值合理性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基础。即人在实现自身的利益欲望时,必须考虑手段的正当性,做到“见利思义”、“见得思义”。这种正当性正是对实现欲望手段的道德考量,“廉”乃是对这种欲望之正当性的道德规定。诚如《吕氏春秋·忠廉》篇日:“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就是说,不因利益的追求而失其道义,不因求富贵而辱没名声,这才是廉之品性。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书名《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眼球。作为一名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变迁都充满兴趣的读者,我深感好奇。书名中的“恒道”二字,暗示着一种超越时空的普适性,而“廉政文化”又是中国社会治理中一个绕不开的重要议题,尤其是在当下我们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我设想,这本书一定深入探讨了古代那些关于清正廉洁的智慧和原则,是如何在现代社会,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它或许会追溯历史的脉络,从儒家思想、法家理念,乃至历代清官的典范中汲取营养,然后细致地分析这些传统元素如何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如何与现代法治精神、市场经济原则、以及公民道德要求相结合。我期待书中能够呈现出一种辩证的视角,既不照搬照抄,也不全盘否定,而是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廉之恒道”。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哲学思辨和现实关照,让我迫不及待想一窥究竟。
评分《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这个书名,让我联想到了一种古老智慧与现代挑战的碰撞。我猜想,这本书的写作一定是建立在一个扎实的学术基础之上,它可能细致地梳理了中国历史上关于“廉”的各种思想流派,比如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廉”,以及法家强调的“以法治国、严惩腐败”的思想。更吸引我的是“现代转换”这个概念,这意味着作者并不满足于仅仅复述历史,而是要探讨这些古老的智慧如何能够被重新解读,以适应当今社会复杂多变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它是否会涉及到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来监督和防范腐败?又或者,如何在新时代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契约,让廉洁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社会风尚?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指导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能够创新发展,真正实现廉政文化的“恒道”,让它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发挥作用,并且真正做到“恒久”而“有效”。
评分这本书名《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听起来就充满了厚重感和现实意义。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作者大概率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和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研究的专家,他/她将把我们带回那个讲求“德治”与“礼法”并存的年代,去体味古人对于“廉”的深刻理解。但更让我期待的,是“现代转换”这个关键词。这暗示着,这本书将不仅仅是一部历史书,更是一本关于如何将古老智慧注入现代灵魂的指南。 我好奇,面对信息爆炸、全球化浪潮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廉政文化中的哪些元素依然具有生命力? 又有哪些需要被重新审视和改造? 这种“转换”的过程,是否会涉及到如何培养新一代的廉政意识,如何建立更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又或者,如何在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中,真正将“廉”作为一种不可逾越的底线? 我相信,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从中汲取力量,应对当下的挑战,构建一个更具公信力和可持续性的廉政体系。
评分读到《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这个书名,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许多画面。我想象着,作者一定是在为如何让古老的廉政理念在现代社会焕发新生而苦苦思索。它可能是一部充满历史考据的学术著作,也可能是一本启发大众思考的通俗读物。但无论如何,我坚信它会聚焦于“现代转换”这一核心概念。这意味着,这本书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古代的廉政故事,更在于它如何解读这些故事背后的精神实质,并将其转化为一套能够指导我们当下行为的现代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我期待看到书中关于“文化”的讨论,它不仅仅是制度的约束,更是渗透到人们思想深处的价值认同。它如何与现代化的治理体系相结合?是否会触及到权力监督、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等诸多现代廉政建设的关键领域?我猜测,书中可能会提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观点,挑战我们对廉政文化的传统认知,并为构建一个更加清明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这种对“转换”的深入探索,让我对这本书的价值充满了期待。
评分《廉之恒道: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现代转换研究》——这个书名,简洁有力,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时代意义。当我看到它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本书一定非常有深度。我设想,作者很可能是一位对中国历史和哲学有着深刻理解的学者,他/她将传统文化中的“廉”字,视为一种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这本书或许不会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会深入到实践中,去探究如何在现代社会,特别是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乃至整个社会层面,去践行和推广这种“恒道”。 我很好奇,书中会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 它会是如何理解并应对现代社会可能出现的新的腐败形式? 对于“恒道”这个词,我理解它意味着一种持久不变的原则,那么这种持久不变的原则,在快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中,又该如何体现? 我预感,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提供一套超越短期政策的、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体系,帮助我们理解和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廉政文化。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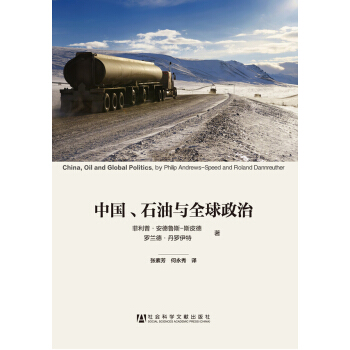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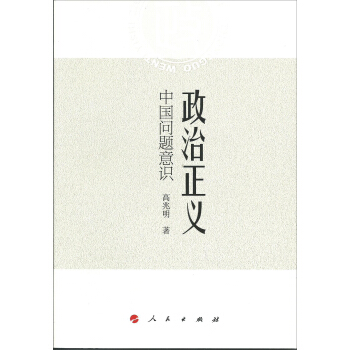

![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 [The Research of Modern Japan's Political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42936/54d48a5aN7e785a7c.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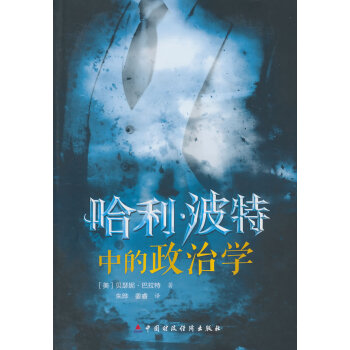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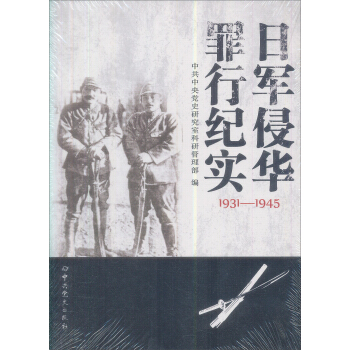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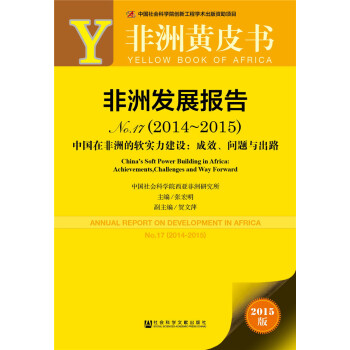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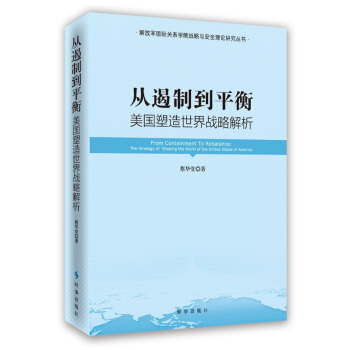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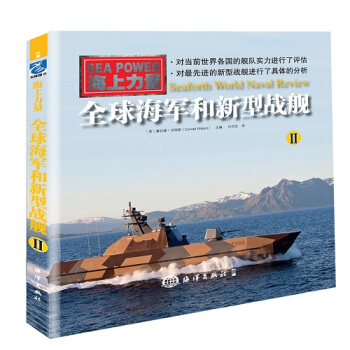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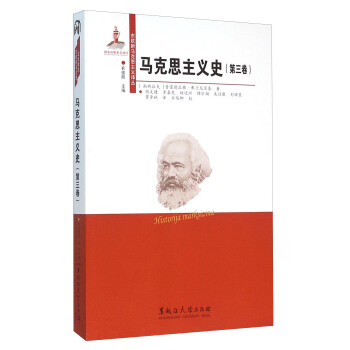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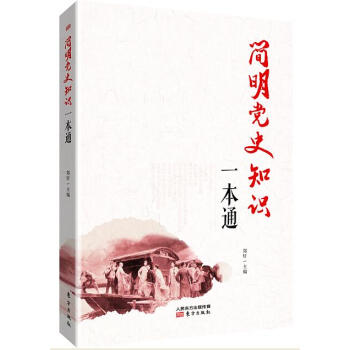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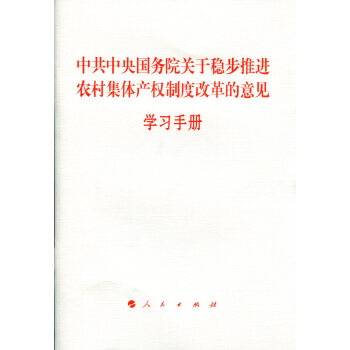
![中共中央党校教材:当代世界科技 [Contemporary 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1952/585ce823N7453f7e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