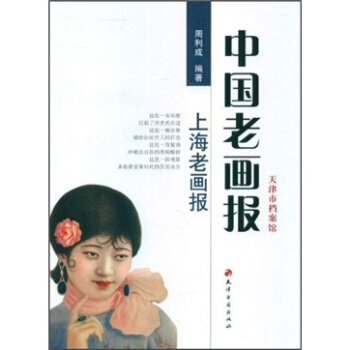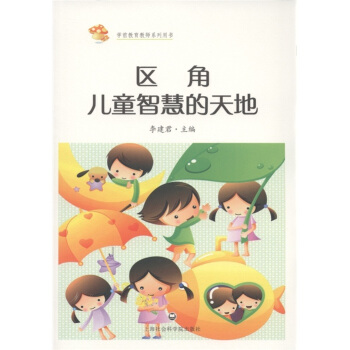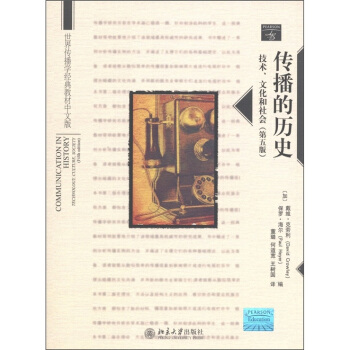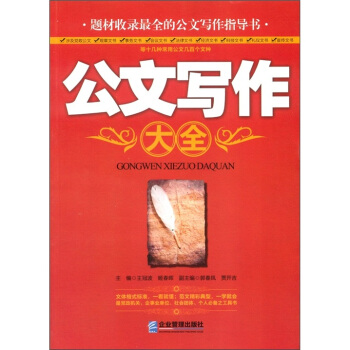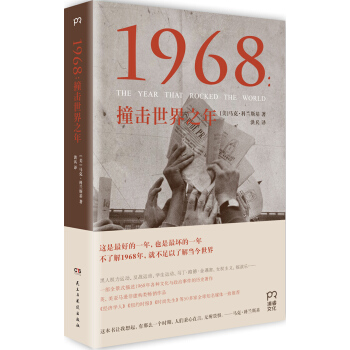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四个历史因素共同造就了1968年:当时的民权运动新颖而有独创性,形成了示范效应;整整一代人自视与前辈截然不同、与社会格格不入,进而拒斥一切形态的威权;当时的越南战争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了一个理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时电视仍足够新锐,无法像今天这样被操控、提纯和包装。在1968年,在当日收看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电视转播,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技术奇迹。作者简介
马克·科兰斯基(Mark Kurlansky),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经常为《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媒体撰写文章。著有《1968:撞击世界之年》《巴斯克人的世界史》《被选择的少数:欧洲犹太人的兴起》《非暴力主义:一种危险观念的历史》等畅销作品。此外,他的专著《鳕鱼:一部改变世界的鱼的传记》获得了具有“美食奥斯卡”之称的詹姆斯·比尔德奖。洪兵,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未媒介社会学、国际新闻传播。出版有译著《分割美国》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引人入胜,令人回味,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观察家报》
很好看,这本书将会让引发人们对特殊的1960年代中特殊的一年的大量回忆。
——《经济学人》
阅读这本书是一次奇妙的体验。
——丹·拉瑟 (美国超级金牌主播)
通俗易懂、视角丰富。马克·科兰斯基是拥有非凡天分的作家。
——《旧金山纪事报》
马克·科兰斯基收集海量的信息,以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告诉读者1968年是怎样的一年。
——《丹佛邮报》
在马克·科兰斯基之前,没有谁能以如此精彩、具有启发的叙述将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系列事件做集中展示。难得的是,还让人读起来意犹未尽。
——《芝加哥论坛报》
这是关于那个传奇年代的一部色彩丰富、饱满,具有高度启迪性的非虚构作品。
——《西雅图时报》
这一年有如此之多令人震撼的事,就像一张经典唱片重现于世,或者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的档案公布于世。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如果时光倒流,人们是多么愿意重放1968年。
——《亚特兰大宪法报》
目录
导 言 震撼世界之年第一部 我们怨愤的严冬
第一章 1968年的第一周
第二章 与蚊帐争辩的人
第三章 令人生畏的浓眉一展
第四章 吹进波兰人的耳朵
第二部 布拉格之春
第五章 在令人憎恶的机器齿轮上
第六章 英雄
第七章 一个波兰人的绝对律令
第八章 诗歌、政治与艰难的第二幕
第九章 新国土上的儿女们
第十章 瓦格纳式弦外之音:关于一场时髦和蓄须的革命
第十一章 4月里的混蛋
第十二章 先生,我们认为你烂透了
第十三章 理想之地
第三部 夏季奥运会
第十四章 禁足之地
第十五章 无趣政治的艺术
第十六章 肉类加工厂旁幽灵般的警察
第十七章 东布拉格之殇
第十八章 可怕压力下的微笑
第十九章 在阿兹特克人的地方
第四部 尼克松的秋天
第二十章 秋季学期的理论与实践
第二十一章 最后的希望
致谢
精彩书摘
导言震撼世界之年
中年的乐事之一在于发现自己曾经是正确的,并且一个人在17岁或者23岁这种年纪时,远远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为正确。——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阅读入门》,1934年
从来没有一个年份像1968年,以后也不大可能再会有这样的年份。那时各个国家和文化仍相互独立、形神迥异—1968年时的波兰、法国、美国和墨西哥的差别远比今日显著—然而却在世界范围内同时出现了反叛精神的自燃。
历史上曾经有过其他的革命年代,例如1848年,但是与1968年形成对比的是,1848年的那些历史事件局限于欧洲,它的反抗同样也局限于一些相似的议题。作为全球帝国体系建立的后果,也有过其他全球性的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影响巨大、波及全球的悲剧事件。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民针对各种议题进行反抗,其共同之处仅在于那种强烈的反抗愿望、对反抗方式的理解、对现存制度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深切厌恶。在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地方他们就反抗社会主义,在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就反抗资本主义。这些反抗指向大多数的机构建制、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党派。
许多反抗活动并非有预谋或者有组织的,往往是通过匆忙召开的会议指挥的;一些最重要的决定则是在兴之所至时做出的。由于运动是反专制的,因此它们缺乏领导,或者只是拥有拒绝作为领袖的领导人。运动的意识形态通常也不清晰,仅在为数甚少的议题上达成了普遍共识。1969年,当一个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八位激进活动分子与1968年芝加哥的抗议示威活动有联系时,阿比·霍夫曼 作为其中的一员,描述这个群体时说道:“甚至关于午餐我们都意见不一。”虽然各处都在发生反抗运动,但是罕有这些力量的联合;即使在美国曾有过像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权运动的结合,或者在法国和意大利曾有过劳工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结合,但大都是出于一时之需,并且很快就瓦解了。
四个历史因素共同造就了1968年:当时的民权运动新颖而有独创性,形成了示范效应;整整一代人自视与前辈截然不同、与社会格格不入,进而拒斥一切形态的威权;当时的越南战争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了一个理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时电视仍足够新锐,无法像今天这样被操控、提纯和包装。在1968年,在当日收看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电视转播,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技术奇迹。
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不特别,它当然也不比无数其他的战争更应该受到谴责—包括此前法国在越南的战争。但这次它是由美国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霸权所发起的。当时正值殖民地人民试图通过“反殖民斗争”重建民族国家,此举激发了全世界人民的理想主义;但是当这片贫瘠、弱小的土地在争取独立的时候,却遭到了一个“超级霸权”的新型实体的狂轰滥炸—美国在这片狭仄国土上投下的非核弹炸弹(non-nuclear bombs),数量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投放在亚洲和欧洲的总和。在1968年越战的高峰期,美军每星期的杀戮数量至少相当于“九一一”事件中的遇难人数。虽然在美国、法国、德国和墨西哥的运动中有着惊人的分裂和众多的派系—但是由于美国的霸权和威望,以及越南战争的残酷和不义的性质—所有人都反对越南战争。1968年,当美国民权运动在非暴力的倡导者和黑人权力的倡导者之间分裂,两个阵营还是能够就反对越战保持共识。只要挺身反对越南战争,全世界的异议运动就能据此建立。
当异议者们试图抗议,他们知道如何行事,他们知道如何游行和静坐,而这些都拜美国民权运动所赐。从密西西比民权运动的电视报道中他们看到了一切,现在他们迫切希望自己成为争取自由的游行者。
对于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代人而言,“大屠杀”还是个新词,而原子弹才刚刚引爆,他们出生在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的一代人,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中成长的那代人大异其趣,以至于为寻找共同点而产生的龃龉屡见不鲜。甚至,他们对同一个笑话的反应都是不同的。鲍勃·霍普(Bob Hope)和杰克·本尼(Jack Benny)这样的喜剧演员大受老一代的欢迎,对新一代却毫无吸引力。
1968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现代主义的年度,而现代主义总是令年轻人着迷,使老年人困惑,但是回首望去,那又是一个古朴纯真的年代。想象一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和巴黎大学的学生隔着大西洋发现他们相似的经历,然后他们会面,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试图找出彼此间是否有共同之处。他们惊愕而激动地发觉,无论是在布拉格、巴黎、罗马、墨西哥,还是纽约,他们采用的是同样的策略。利用通讯卫星和并不昂贵、可重复使用的录像带等新的工具,电视使得每个人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知晓其他人的作为;在人类的经验中,当日在远方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第一次可以即时传播,这真是令人兴奋不已。
再也不会有像1968年那样出现如此多新奇事物的年度了。“地球村”是马歇尔·麦克卢汉 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的词汇。这个星球日益扁平化,任何事都不会再像第一次看到在月球上拍摄的照片、第一次听到来自外太空的广播那样使我们感到震撼。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每天都期待新突破的世界。如果还能够造就另一批1968年的那代人,那么他们所有的运动都将利用网络,而当他们彼此用电子邮件进行联系、更新时,会被执法部门严密监控。毫无疑问,人们会发明其他工具,但即使是关于新发明的概念都变得陈腐了。
我生于1948年,属于痛恨越战和对之抗议的那一代人。我对威权的理解来自记忆的塑造:催泪瓦斯的胡椒味,警察在进攻前不动声色,他们慢慢从侧翼逼近示威者,然后以警棍开始杀戮。我从本书的一开始就表明我的成见,是因为即便到了30多年后的现在,我仍认为试图在“1968年”这个主题上保持客观是不诚实的。在阅读了1968年的《纽约时报》《时代》《生活》《花花公子》《世界报》《费加罗报》,一份波兰的日报和一份波兰的周刊,以及几份墨西哥的报纸后—其中一些声称是客观的而另一些则声明其成见—我确信“公正”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观”是不可能的。1968年,所谓的“客观的”美国新闻界,远比它自己认识到的要主观得多。
写作本书使我回想起曾经的那个年代,人们能够直言不讳并不忌惮冒犯威权—而从那之后,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湮没无闻。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如同心跳,忽而急促如鼓点,忽而又沉潜如深思。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宏大叙事时所展现出的细腻笔触,他没有让冰冷的日期和条文淹没掉人物的鲜活。那些游行示威的学生、那些在幕后摇摆的政治人物,甚至是那些在家庭内部经历思想冲突的普通人,都被赋予了复杂的动机和真实的情感挣扎。比如书中对某次关键性国际事件的侧述,表面上是外交辞令的交锋,但作者深入挖掘了参与者私下的焦虑与算计,一下子就把历史的厚重感转化成了你我都能理解的人性困境。这种写法,使得那些看似遥远的事件,突然之间变得触手可及,甚至让你代入其中去思考:如果是我,在那样的压力下,我会如何选择?我发现自己开始反思,我们今天所享受的一些权利和自由,其代价究竟有多么沉重,又是在怎样的混乱与不确定性中诞生的。这本书不仅仅是历史记录,它更像是一面棱镜,折射出现代社会结构中那些尚未愈合的裂痕和持续回响的冲突基因。
评分这本书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成功地营造了一种“临界感”。读完全书,我没有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或者一个被总结好的教训,反而被推入了一种持续的不安和追问之中。作者似乎故意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留下了一些空白,或者说,留下了许多尚未解决的张力,这迫使读者不能轻易地合上书本就结束了这场思考。我尤其赞赏它对于“理想的代价”这一母题的处理,那些怀揣着最纯粹信念的行动者,他们的牺牲和最终的结果之间所存在的巨大鸿沟,被描绘得如此真实而残酷。它让你明白,那些轰轰烈烈的“撞击”,很多时候是带着巨大的阵痛和不完美的收场的。这反而增加了这本书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因为它拒绝了任何廉价的乐观主义。它更像是一个严厉的导师,告诉你历史是如何发生的,而不是它应该如何发生。对于任何想要深入理解现代社会起源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不可替代的、充满力量的视角。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带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息,那种粗粝的质感和略显模糊的印刷风格,一下子就把你拽回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我拿起它的时候,手里仿佛还能感受到街头巷尾的喧嚣和那种冲破旧秩序的渴望。作者对于时代情绪的捕捉极其敏锐,他不仅仅是在罗列事件,更像是在重现一种集体的“感觉”。读到关于青年运动的章节时,那种压抑已久的激情和对既有权威的集体性反叛,透过文字直抵人心。它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对“变革”二字的理解,原来那些看似瞬间爆发的社会剧变,背后是长久以来社会肌理被不断摩擦和拉扯的结果。书里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矛盾爆发点的描述,虽然地理上分散,但内在的逻辑却是惊人地一致——那是人类共同对更自由、更平等生存状态的呼唤。阅读过程中,我时不时会停下来,不是因为文字晦涩,而是因为被某种强烈的共鸣击中,仿佛亲身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感受着每一条可能的未来路径在眼前交错、撕裂。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它让你明白了,历史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一系列充满张力和偶然性的“撞击”。
评分阅读体验非常像是在翻阅一本精心剪辑的地下电影蒙太奇。文字的跳跃性和画面感极强,作者在不同场景之间切换得毫无预兆,却又在潜意识里构建起了一种强烈的时代关联。时而是巴黎的街垒,时而是布拉格的坦克履带声,转瞬又是越南丛林中的迷雾,这种多线程的叙事策略,完美地捕捉了那个“全球同步爆发”的特性。它迫使读者的大脑必须高速运转,去建立这些看似不相关的点之间的隐形联系。我感到自己仿佛在不同的时区里奔跑,试图跟上那个世界加速旋转的步伐。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处理“失败”和“挫折”的方式。他没有将那些未能成功的运动简单地归咎于外部镇压,而是深入探讨了内部理想主义的自我耗竭和路径选择的困境。这使得整本书的基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赞美”或“控诉”,而是在一种更加深沉的悲剧性反思中完成了对那个年代的致敬。这种复杂性,是读后久久难以忘怀的关键。
评分我必须承认,这本书的学术功底是扎实的,但它绝非那种枯燥的学院派著作。作者的语言风格极其老练,带着一种知识分子的犀利和洞察力,同时又极富文学性。他擅长使用那些精准到位的比喻,一下子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比如说,他形容某种社会思潮的蔓延如同“看不见的真菌在温暖的土壤中扩散”,这种表达不仅生动,而且准确地描绘了观念渗透的微妙过程。全书的结构设计也颇为精妙,看似是时间线索的推进,实则是在主题的螺旋上升中展开:从对旧体制的反思,到对新世界可能性的想象,再到最终回归到个体在巨大历史洪流中的无力感与坚韧。这种由外而内、再由大及小的结构,使得读者在理解时代背景的同时,也能体会到微观个体的挣扎。读完后,我感觉自己对“时代精神”这个抽象概念有了更具象、更具重量的理解,它不再是教科书上的一个标题,而是由无数次碰撞、无数种声音、无数种失败的尝试所共同构成的复杂场域。
评分京东的品质值得信赖,加上活动给力!
评分四个历史因素共同造就了1968年:当时的民权运动新颖而有独创性,形成了示范效应;整整一代人自视与前辈截然不同、与社会格格不入,进而拒斥一切形态的威权;当时的越南战争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了一个理由;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电视逐渐发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时电视仍足够新锐,无法像今天这样被操控、提纯和包装。在1968年,在当日收看来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的电视转播,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个扣人心弦的技术奇迹。
评分一直觉得那是个神奇的年代,特意买的精装版。
评分质量很好用了券之后非常划算,速度很快,给快递小哥点赞呀。
评分书很好,值得阅读,图书品质没的说,京东小哥服务很好!
评分发货速度很快,商品质量好
评分1968年是一个充满反叛、骚乱和动荡的年代,本书就是那个年代的全景式记录。反叛,却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严密的组织,只有叛逆的欲望和方式,矛头指向大多数机构、政治@和政党;骚乱,波及欧亚和南北美洲;动荡,越战、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奥运会前夕墨西哥大开杀戒、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而那个年代撞击了整个世界,并决定了今天的世界面貌。
评分好书,特别值得仔细读,活动买的。。。!
评分我们很满意,以后有需要还会继续购买的,希望以后优惠多多哦,哈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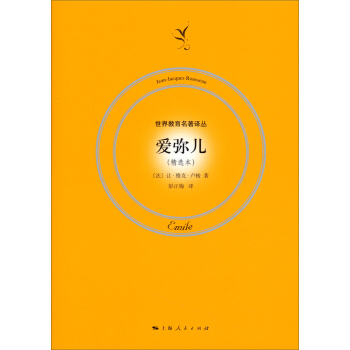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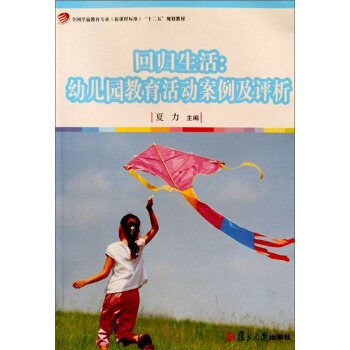

![设计·制作·游戏:培养下一代STEM创新者 [Design Make Play:Grow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TEM Innovator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73106/58a28e78N716ad2a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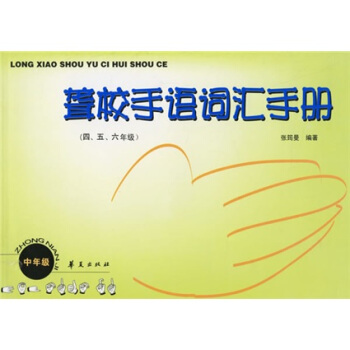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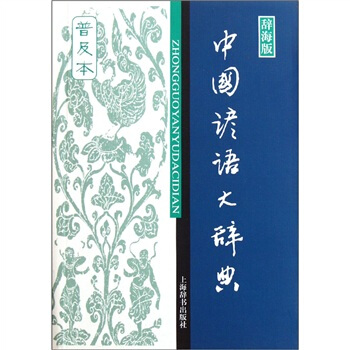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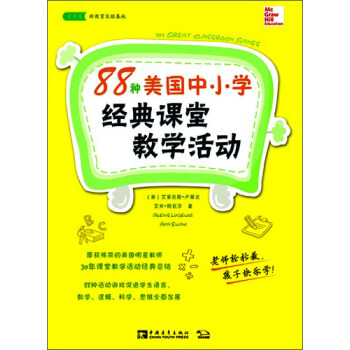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与达尔文:海外(新)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67326/53951c3eN5add1c9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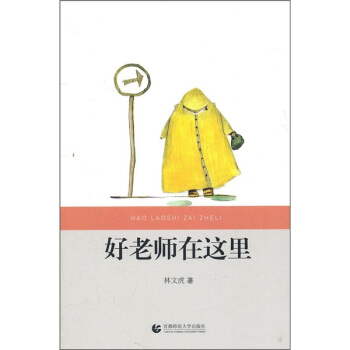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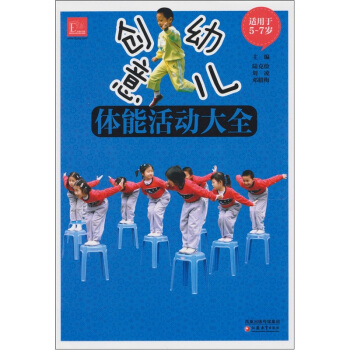


![发展的受害者 [Victims of Progres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794958/b7a7c892-1d21-4dc6-88e4-20a7eba0fa61.jpg)
![私有化:成功与失败 [Privatization:Successes and Failur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845691/2fa52f56-100f-480d-bcca-1968ee90a93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