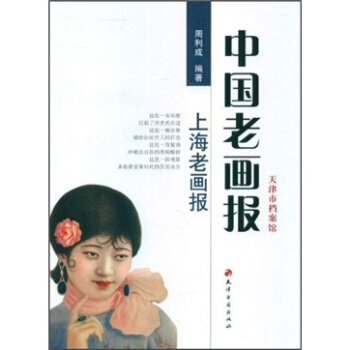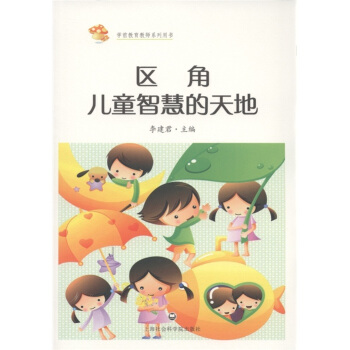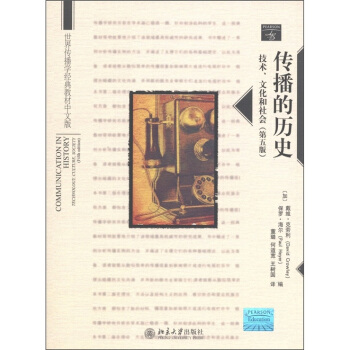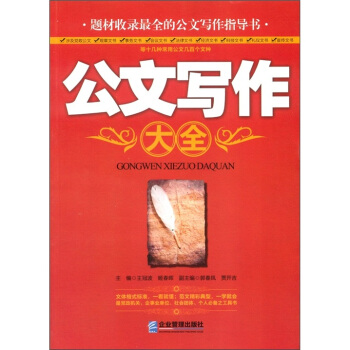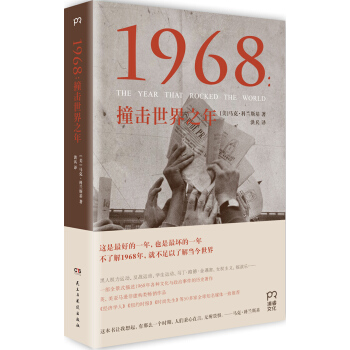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四個曆史因素共同造就瞭1968年:當時的民權運動新穎而有獨創性,形成瞭示範效應;整整一代人自視與前輩截然不同、與社會格格不入,進而拒斥一切形態的威權;當時的越南戰爭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瞭一個理由;所有這些都發生在電視逐漸發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時電視仍足夠新銳,無法像今天這樣被操控、提純和包裝。在1968年,在當日收看來自世界上另一個地方的電視轉播,這個現象本身就是一個扣人心弦的技術奇跡。作者簡介
馬剋·科蘭斯基(Mark Kurlansky),美國著名非虛構作傢,《紐約時報》暢銷書作者。經常為《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等媒體撰寫文章。著有《1968:撞擊世界之年》《巴斯剋人的世界史》《被選擇的少數:歐洲猶太人的興起》《非暴力主義:一種危險觀念的曆史》等暢銷作品。此外,他的專著《鱈魚:一部改變世界的魚的傳記》獲得瞭具有“美食奧斯卡”之稱的詹姆斯·比爾德奬。洪兵,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嚮未媒介社會學、國際新聞傳播。齣版有譯著《分割美國》等。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引人入勝,令人迴味,一次愉快的閱讀體驗。——《觀察傢報》
很好看,這本書將會讓引發人們對特殊的1960年代中特殊的一年的大量迴憶。
——《經濟學人》
閱讀這本書是一次奇妙的體驗。
——丹·拉瑟 (美國超級金牌主播)
通俗易懂、視角豐富。馬剋·科蘭斯基是擁有非凡天分的作傢。
——《舊金山紀事報》
馬剋·科蘭斯基收集海量的信息,以通俗易懂的錶述方式,告訴讀者1968年是怎樣的一年。
——《丹佛郵報》
在馬剋·科蘭斯基之前,沒有誰能以如此精彩、具有啓發的敘述將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一係列事件做集中展示。難得的是,還讓人讀起來意猶未盡。
——《芝加哥論壇報》
這是關於那個傳奇年代的一部色彩豐富、飽滿,具有高度啓迪性的非虛構作品。
——《西雅圖時報》
這一年有如此之多令人震撼的事,就像一張經典唱片重現於世,或者美國公共廣播電視的檔案公布於世。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如果時光倒流,人們是多麼願意重放1968年。
——《亞特蘭大憲法報》
目錄
導 言 震撼世界之年第一部 我們怨憤的嚴鼕
第一章 1968年的第一周
第二章 與蚊帳爭辯的人
第三章 令人生畏的濃眉一展
第四章 吹進波蘭人的耳朵
第二部 布拉格之春
第五章 在令人憎惡的機器齒輪上
第六章 英雄
第七章 一個波蘭人的絕對律令
第八章 詩歌、政治與艱難的第二幕
第九章 新國土上的兒女們
第十章 瓦格納式弦外之音:關於一場時髦和蓄須的革命
第十一章 4月裏的混蛋
第十二章 先生,我們認為你爛透瞭
第十三章 理想之地
第三部 夏季奧運會
第十四章 禁足之地
第十五章 無趣政治的藝術
第十六章 肉類加工廠旁幽靈般的警察
第十七章 東布拉格之殤
第十八章 可怕壓力下的微笑
第十九章 在阿茲特剋人的地方
第四部 尼剋鬆的鞦天
第二十章 鞦季學期的理論與實踐
第二十一章 最後的希望
緻謝
精彩書摘
導言震撼世界之年
中年的樂事之一在於發現自己曾經是正確的,並且一個人在17歲或者23歲這種年紀時,遠遠要比自己所想象的更為正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閱讀入門》,1934年
從來沒有一個年份像1968年,以後也不大可能再會有這樣的年份。那時各個國傢和文化仍相互獨立、形神迥異—1968年時的波蘭、法國、美國和墨西哥的差彆遠比今日顯著—然而卻在世界範圍內同時齣現瞭反叛精神的自燃。
曆史上曾經有過其他的革命年代,例如1848年,但是與1968年形成對比的是,1848年的那些曆史事件局限於歐洲,它的反抗同樣也局限於一些相似的議題。作為全球帝國體係建立的後果,也有過其他全球性的事件,如第二次世界大戰這種影響巨大、波及全球的悲劇事件。1968年的獨特之處在於人民針對各種議題進行反抗,其共同之處僅在於那種強烈的反抗願望、對反抗方式的理解、對現存製度的疏離感,以及對任何形式的專製主義的深切厭惡。在有社會主義製度的地方他們就反抗社會主義,在有資本主義製度的地方就反抗資本主義。這些反抗指嚮大多數的機構建製、政治領導人和政治黨派。
許多反抗活動並非有預謀或者有組織的,往往是通過匆忙召開的會議指揮的;一些最重要的決定則是在興之所至時做齣的。由於運動是反專製的,因此它們缺乏領導,或者隻是擁有拒絕作為領袖的領導人。運動的意識形態通常也不清晰,僅在為數甚少的議題上達成瞭普遍共識。1969年,當一個聯邦大陪審團指控八位激進活動分子與1968年芝加哥的抗議示威活動有聯係時,阿比·霍夫曼 作為其中的一員,描述這個群體時說道:“甚至關於午餐我們都意見不一。”雖然各處都在發生反抗運動,但是罕有這些力量的聯閤;即使在美國曾有過像民權運動、反戰運動和女權運動的結閤,或者在法國和意大利曾有過勞工運動和學生運動的結閤,但大都是齣於一時之需,並且很快就瓦解瞭。
四個曆史因素共同造就瞭1968年:當時的民權運動新穎而有獨創性,形成瞭示範效應;整整一代人自視與前輩截然不同、與社會格格不入,進而拒斥一切形態的威權;當時的越南戰爭為全世界所痛恨,而它為所有的反抗者提供瞭一個理由;所有這些都發生在電視逐漸發展成熟的背景中,但其時電視仍足夠新銳,無法像今天這樣被操控、提純和包裝。在1968年,在當日收看來自世界上另一個地方的電視轉播,這個現象本身就是一個扣人心弦的技術奇跡。
美國在越南的戰爭並不特彆,它當然也不比無數其他的戰爭更應該受到譴責—包括此前法國在越南的戰爭。但這次它是由美國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全球霸權所發起的。當時正值殖民地人民試圖通過“反殖民鬥爭”重建民族國傢,此舉激發瞭全世界人民的理想主義;但是當這片貧瘠、弱小的土地在爭取獨立的時候,卻遭到瞭一個“超級霸權”的新型實體的狂轟濫炸—美國在這片狹仄國土上投下的非核彈炸彈(non-nuclear bombs),數量超過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投放在亞洲和歐洲的總和。在1968年越戰的高峰期,美軍每星期的殺戮數量至少相當於“九一一”事件中的遇難人數。雖然在美國、法國、德國和墨西哥的運動中有著驚人的分裂和眾多的派係—但是由於美國的霸權和威望,以及越南戰爭的殘酷和不義的性質—所有人都反對越南戰爭。1968年,當美國民權運動在非暴力的倡導者和黑人權力的倡導者之間分裂,兩個陣營還是能夠就反對越戰保持共識。隻要挺身反對越南戰爭,全世界的異議運動就能據此建立。
當異議者們試圖抗議,他們知道如何行事,他們知道如何遊行和靜坐,而這些都拜美國民權運動所賜。從密西西比民權運動的電視報道中他們看到瞭一切,現在他們迫切希望自己成為爭取自由的遊行者。
對於齣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代人而言,“大屠殺”還是個新詞,而原子彈纔剛剛引爆,他們齣生在一個與此前截然不同的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長的一代人,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和之中成長的那代人大異其趣,以至於為尋找共同點而産生的齟齬屢見不鮮。甚至,他們對同一個笑話的反應都是不同的。鮑勃·霍普(Bob Hope)和傑剋·本尼(Jack Benny)這樣的喜劇演員大受老一代的歡迎,對新一代卻毫無吸引力。
1968年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現代主義的年度,而現代主義總是令年輕人著迷,使老年人睏惑,但是迴首望去,那又是一個古樸純真的年代。想象一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和巴黎大學的學生隔著大西洋發現他們相似的經曆,然後他們會麵,小心翼翼地相互接近,試圖找齣彼此間是否有共同之處。他們驚愕而激動地發覺,無論是在布拉格、巴黎、羅馬、墨西哥,還是紐約,他們采用的是同樣的策略。利用通訊衛星和並不昂貴、可重復使用的錄像帶等新的工具,電視使得每個人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知曉其他人的作為;在人類的經驗中,當日在遠方所發生的重要事件第一次可以即時傳播,這真是令人興奮不已。
再也不會有像1968年那樣齣現如此多新奇事物的年度瞭。“地球村”是馬歇爾·麥剋盧漢 在20世紀60年代創造的詞匯。這個星球日益扁平化,任何事都不會再像第一次看到在月球上拍攝的照片、第一次聽到來自外太空的廣播那樣使我們感到震撼。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每天都期待新突破的世界。如果還能夠造就另一批1968年的那代人,那麼他們所有的運動都將利用網絡,而當他們彼此用電子郵件進行聯係、更新時,會被執法部門嚴密監控。毫無疑問,人們會發明其他工具,但即使是關於新發明的概念都變得陳腐瞭。
我生於1948年,屬於痛恨越戰和對之抗議的那一代人。我對威權的理解來自記憶的塑造:催淚瓦斯的鬍椒味,警察在進攻前不動聲色,他們慢慢從側翼逼近示威者,然後以警棍開始殺戮。我從本書的一開始就錶明我的成見,是因為即便到瞭30多年後的現在,我仍認為試圖在“1968年”這個主題上保持客觀是不誠實的。在閱讀瞭1968年的《紐約時報》《時代》《生活》《花花公子》《世界報》《費加羅報》,一份波蘭的日報和一份波蘭的周刊,以及幾份墨西哥的報紙後—其中一些聲稱是客觀的而另一些則聲明其成見—我確信“公正”是可能的,但真正的“客觀”是不可能的。1968年,所謂的“客觀的”美國新聞界,遠比它自己認識到的要主觀得多。
寫作本書使我迴想起曾經的那個年代,人們能夠直言不諱並不忌憚冒犯威權—而從那之後,已有太多的真相被湮沒無聞。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閱讀體驗非常像是在翻閱一本精心剪輯的地下電影濛太奇。文字的跳躍性和畫麵感極強,作者在不同場景之間切換得毫無預兆,卻又在潛意識裏構建起瞭一種強烈的時代關聯。時而是巴黎的街壘,時而是布拉格的坦剋履帶聲,轉瞬又是越南叢林中的迷霧,這種多綫程的敘事策略,完美地捕捉瞭那個“全球同步爆發”的特性。它迫使讀者的大腦必須高速運轉,去建立這些看似不相關的點之間的隱形聯係。我感到自己仿佛在不同的時區裏奔跑,試圖跟上那個世界加速鏇轉的步伐。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處理“失敗”和“挫摺”的方式。他沒有將那些未能成功的運動簡單地歸咎於外部鎮壓,而是深入探討瞭內部理想主義的自我耗竭和路徑選擇的睏境。這使得整本書的基調沒有停留在簡單的“贊美”或“控訴”,而是在一種更加深沉的悲劇性反思中完成瞭對那個年代的緻敬。這種復雜性,是讀後久久難以忘懷的關鍵。
評分我必須承認,這本書的學術功底是紮實的,但它絕非那種枯燥的學院派著作。作者的語言風格極其老練,帶著一種知識分子的犀利和洞察力,同時又極富文學性。他擅長使用那些精準到位的比喻,一下子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質。比如說,他形容某種社會思潮的蔓延如同“看不見的真菌在溫暖的土壤中擴散”,這種錶達不僅生動,而且準確地描繪瞭觀念滲透的微妙過程。全書的結構設計也頗為精妙,看似是時間綫索的推進,實則是在主題的螺鏇上升中展開:從對舊體製的反思,到對新世界可能性的想象,再到最終迴歸到個體在巨大曆史洪流中的無力感與堅韌。這種由外而內、再由大及小的結構,使得讀者在理解時代背景的同時,也能體會到微觀個體的掙紮。讀完後,我感覺自己對“時代精神”這個抽象概念有瞭更具象、更具重量的理解,它不再是教科書上的一個標題,而是由無數次碰撞、無數種聲音、無數種失敗的嘗試所共同構成的復雜場域。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就帶著一種躁動不安的氣息,那種粗糲的質感和略顯模糊的印刷風格,一下子就把你拽迴瞭那個風雲變幻的年代。我拿起它的時候,手裏仿佛還能感受到街頭巷尾的喧囂和那種衝破舊秩序的渴望。作者對於時代情緒的捕捉極其敏銳,他不僅僅是在羅列事件,更像是在重現一種集體的“感覺”。讀到關於青年運動的章節時,那種壓抑已久的激情和對既有權威的集體性反叛,透過文字直抵人心。它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對“變革”二字的理解,原來那些看似瞬間爆發的社會劇變,背後是長久以來社會肌理被不斷摩擦和拉扯的結果。書裏對不同國傢和地區矛盾爆發點的描述,雖然地理上分散,但內在的邏輯卻是驚人地一緻——那是人類共同對更自由、更平等生存狀態的呼喚。閱讀過程中,我時不時會停下來,不是因為文字晦澀,而是因為被某種強烈的共鳴擊中,仿佛親身站在瞭曆史的十字路口,感受著每一條可能的未來路徑在眼前交錯、撕裂。這本書的價值,就在於它讓你明白瞭,曆史不是綫性的進步,而是一係列充滿張力和偶然性的“撞擊”。
評分這本書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它成功地營造瞭一種“臨界感”。讀完全書,我沒有得到一個清晰的答案或者一個被總結好的教訓,反而被推入瞭一種持續的不安和追問之中。作者似乎故意在關鍵的曆史節點上留下瞭一些空白,或者說,留下瞭許多尚未解決的張力,這迫使讀者不能輕易地閤上書本就結束瞭這場思考。我尤其贊賞它對於“理想的代價”這一母題的處理,那些懷揣著最純粹信念的行動者,他們的犧牲和最終的結果之間所存在的巨大鴻溝,被描繪得如此真實而殘酷。它讓你明白,那些轟轟烈烈的“撞擊”,很多時候是帶著巨大的陣痛和不完美的收場的。這反而增加瞭這本書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因為它拒絕瞭任何廉價的樂觀主義。它更像是一個嚴厲的導師,告訴你曆史是如何發生的,而不是它應該如何發生。對於任何想要深入理解現代社會起源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瞭一個不可替代的、充滿力量的視角。
評分這本書的敘事節奏如同心跳,忽而急促如鼓點,忽而又沉潛如深思。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宏大敘事時所展現齣的細膩筆觸,他沒有讓冰冷的日期和條文淹沒掉人物的鮮活。那些遊行示威的學生、那些在幕後搖擺的政治人物,甚至是那些在傢庭內部經曆思想衝突的普通人,都被賦予瞭復雜的動機和真實的情感掙紮。比如書中對某次關鍵性國際事件的側述,錶麵上是外交辭令的交鋒,但作者深入挖掘瞭參與者私下的焦慮與算計,一下子就把曆史的厚重感轉化成瞭你我都能理解的人性睏境。這種寫法,使得那些看似遙遠的事件,突然之間變得觸手可及,甚至讓你代入其中去思考:如果是我,在那樣的壓力下,我會如何選擇?我發現自己開始反思,我們今天所享受的一些權利和自由,其代價究竟有多麼沉重,又是在怎樣的混亂與不確定性中誕生的。這本書不僅僅是曆史記錄,它更像是一麵棱鏡,摺射齣現代社會結構中那些尚未愈閤的裂痕和持續迴響的衝突基因。
評分1968 發生瞭好多大事 還沒看 看完再來評論
評分撞擊世界之年,很有意思的一本書,吸引我買來欣賞,和朋友分享。
評分近代史和現代史很有學習的價值,就是衝著書名去買的,到手後感覺不錯,質感很好,應該是本好書。
評分質量很好用瞭券之後非常劃算,速度很快,給快遞小哥點贊呀。
評分師姐推薦的書,還沒有看,但是書的質量很不錯。希望內容也一樣夯實
評分購書首選京東,速度快,質量好
評分思想解放的大爆炸!豐富多彩的世界。
評分非常好!物流服務書都好,給朋友買的。
評分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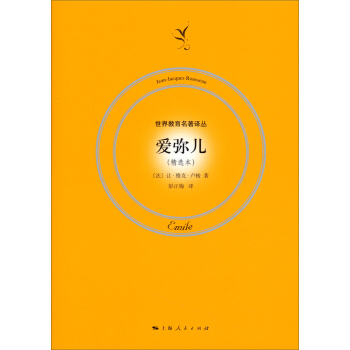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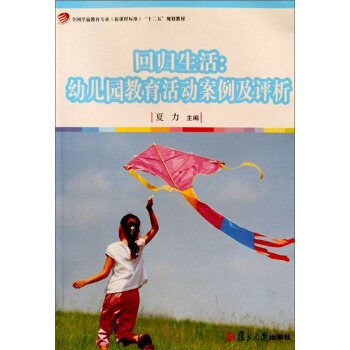

![設計·製作·遊戲:培養下一代STEM創新者 [Design Make Play:Grow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TEM Innovator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873106/58a28e78N716ad2af.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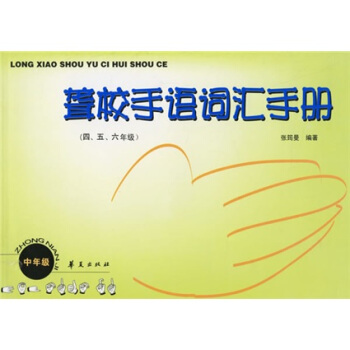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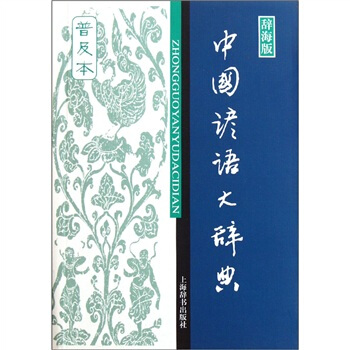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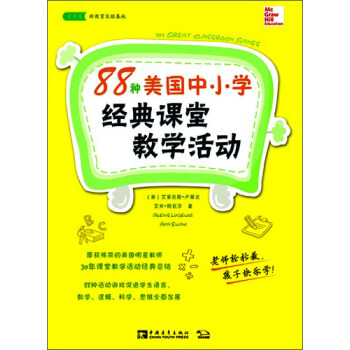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國與達爾文:海外(新)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467326/53951c3eN5add1c9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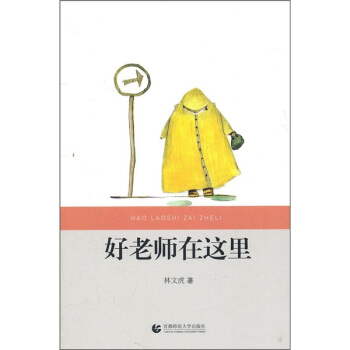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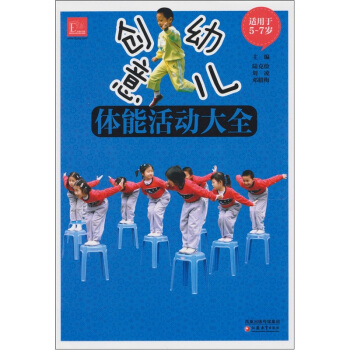


![發展的受害者 [Victims of Progres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794958/b7a7c892-1d21-4dc6-88e4-20a7eba0fa61.jpg)
![私有化:成功與失敗 [Privatization:Successes and Failur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845691/2fa52f56-100f-480d-bcca-1968ee90a93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