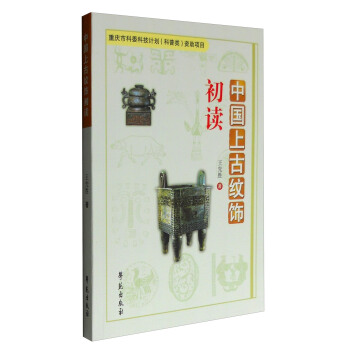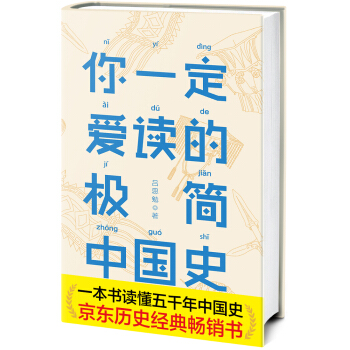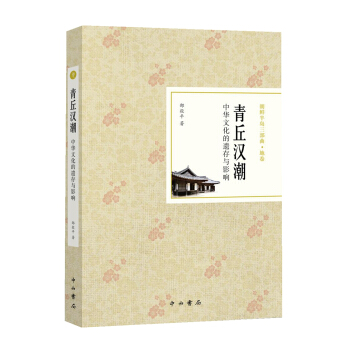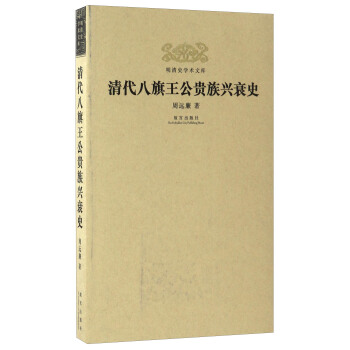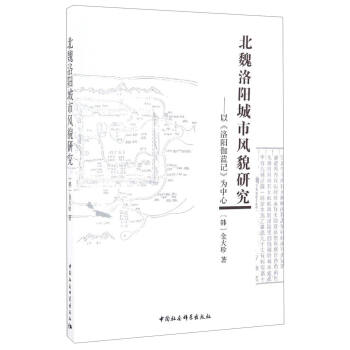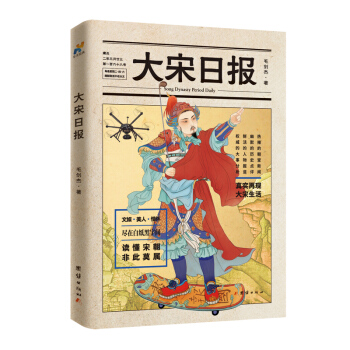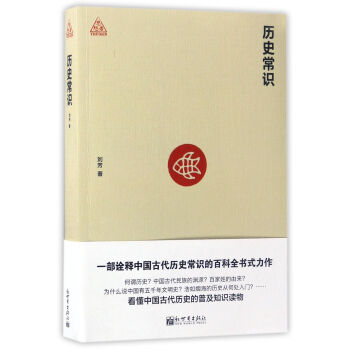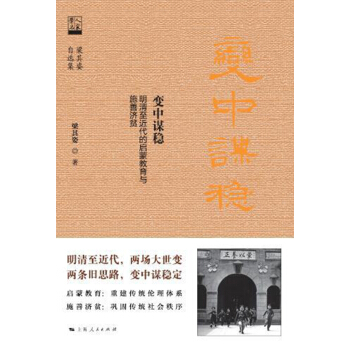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广大读者或许政治经济社会不断的、无常的变化,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常态。但人总是缅怀过去或力求保持熟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对变化所意味着的风险与未知充满疑虑。因此说,明清至近代时期的家族、地方社会,乃至于中央政府致力于谋求稳定、预防变化,或在激变的形势里力图维持平稳的表象,不足为奇。
启蒙教育和施善济贫是明清至近代的家族地方社会与国家谋求稳定的两个着力点。在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之时,这两种活动被用来稳定急变中的社会,它们特别有利于宣扬经典中的理想世界与伦理关系,以合理化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秩序。
内容简介
该书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梁其姿的新力作,该书围绕了明清至近代大变局中的两个着力点——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讲述了家族、地方社会与国家谋求稳定的重要关系。本书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是有关启蒙教育的三篇论文,讨论了明清至近代蒙学的形式与内容,兼具慈善性质的义学制度在清初世变时期开始普及。第二部分的七篇有关施善济贫的论文,则从不同角度探讨济贫的论述与活动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变中试图重整甚至巩固传统伦理与社会秩序。语言引人入胜。
作者简介
梁其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香港大学人文社会研究所所长兼讲座教授,学术专长为明清社会史、近世社会文化史,并为中国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推手之一。出版有:《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麻风:一种疾病的医疗社会史》。
目录
序...............1
明清时期的启蒙教育
17、 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基础教育...............3
《三字经》里历史时间的问题...............32
明清中国的医学入门与普及化...............64
明清至近代的济贫与信仰
“贫穷”与“穷人”观念在中国俗世社会中的历史演变...............83
清代的惜字会...............108
19世纪中国的婴孩救济机构...............129
民族尊严、男女平等,还是无私救济?首批中国女医生的选择...............149
道堂乎?善堂乎?清末民初广州城内省躬草堂的独特模式...............171
近代中国医院的诞生...............198
广州近代善堂的现代性(1870—1937)...............219
前言/序言
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是明清至近代的家族、地方社会与国家谋求稳定的两个着力点。在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时,有关蒙学与济贫的讨论与活动特别热烈与频繁。这两种活动为何、如何被用来稳定急变中的社会?似乎仍然值得再思考。
明清至民初这个长时期包括了两段激烈变化的历史过程,即明清世变、清末至民国的世变。明清之交的深层变化,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分析与铺陈之。有从经济角度切入,如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或人口快速增长、放缓的社会流动所产生的阶级变化等论说。也有强调族群的因素,如满族入主中原带来的地方社会组织变化、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以至清王朝疆域的空前扩展所产生的新的国家管治文化等。至于清末至民国的世变就更深远与激烈了。其中主要的因素当然是西方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冲激及随之而来的殖民主义的挑战。这些空前的变化最终摧毁了清王朝的经济与政治堡垒,而近代西方政治思潮与革命理想更颠覆了传统中国的天下观。面对着影响全球发展的政治论述、经济手段与科学技术,中国在位者左支右绌、穷于应付,社会每一层面都得承受前所未有的、急剧而深远的变化。
可以说从明清至近代,中国社会其实不会享受过长时段的所谓“稳定”日子。虽然清中期以前的变化仍然在相对传统的政治与文化体制中发生,没有给人翻天覆地之感,而且一些变化也曾为部分人的经济生活带来了改善,但是其中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化与政治暴力所引发的焦虑甚至恐惧,仍不容低估。
或许政治经济社会不断的、无常的变化,其实是人类历史的常态。但人总是缅怀过去或力求保持熟悉的社会秩序与价值观,对变化所意味着的风险与未知充满疑虑。因此说,明清至近代时期的家族、地方社会,乃至于中央政府致力于谋求稳定、预防变化,或在激变的形势里力图维持平稳的表象,不足为奇。在这个经历了至少两次重大世变的历史长时段里,有权力者赖以谋求稳定的手段不多,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是其中较常见的两种,而且往往并肩而行。其中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两者均特别有利于宣扬经典中的理想世界与伦理关系,以合理化现存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而施善组织更让在世变中的富人与贫人产生同舟共济的共生关系。
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序本文集里有关启蒙教育的三篇论文讨论了明清至近代蒙学的形式与内容。兼具慈善性质的义学制度在清初世变时期开始普及。义学教育的特色是以儒学伦理与历史教育为核心内容,培养“贫贱子弟”温、良、恭、俭、让、勤、孝、礼、善、诚等品质,确定层层相扣的权力来源(从父权到皇权),与灌输正统的历史记忆,包括朝代迭替的建构与历史人物的臧否。塾师的循循善诱、勤讲勤学忠孝故事不单是蒙学讲学的标准方式,也成为教化一般民众的方法,明清乡约的宣讲方式,亦不离此形式。甚至为成人撰写的明清医学入门书也模仿蒙书的基本学习方法,以重复背诵来内化源自经典的专业知识与伦理。
第二部分的七篇有关施善济贫的论文则从不同角度探讨济贫的论述与活动如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世变中试图重整甚至巩固传统伦理与社会秩序。济贫活动的出现不一定是由于社会整体陷入经济匮乏。明清之际的贫穷问题首先是由财富带来的道德问题。当时新财富的出现不但冲击着原有的社会关系,而且更动摇了贫穷的中立道德定位,人会怀疑贫困者的厄运是否来自他们道德上的缺憾。这些价值观的变化引发前所未有的社会失衡。善堂透过富有善人的施与贫者受的仪式与过程,重塑松动了的社会秩序与价值以平抚焦虑的情绪。而清初以来盛行的惜字会等民间组织则进一步说明了看似单纯的各种俗世善举其实融合着丰富的通俗信仰内容,以善恶各有报应的逻辑安慰着在激烈竞争环境中挣扎的人心,乃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原素。
最后四篇有关近代施善与济贫的论文均以清末民初这第二段世变中的施善济贫为讨论重点。此时期的慈善机构,包括各种综合性的善堂、新式医院等,与清前期的善堂相比(拙作《施善与教化》(1997)比较集中讨论清早期的善堂),已有极大的转变。经历过十多年动乱后,同治以还的中央政权的实力与威望已大不如前,地方社会百废待举。善堂成为重建秩序的主要力量。当时除了传统的由中央政府背书的普济、育婴两个善堂外,每个都市都各自推动了配合当地社会情况的各式各样慈善组织。这些机构除了要解决表面上的社会失序、贫困问题外,更要面对各种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如国族认同、女权意识、科学主义、基督教问题等,后者不但引入了截然不同的施善理念与方式,更成为中国济贫机构的主要竞争对手。可以说在清末民初这个世变过程中,施善组织的转型不但充分反映了当时在激变中的社会环境,同时也因而成为都市社会主要的稳定力量。
清末民初都市善堂与清初善堂主要的分别在于主导者已名正言顺为地方绅商。虽然早期的善堂已经多由士绅管理,但朝廷的背书、官府的推动与监督仍不可或缺。而近代都市的商团势力已成熟,由他们出资建立与管理的善堂已不再代表皇朝的恩典。商人在地方社会的财力、人脉关系与管治能力,已足以让他们独当一面地挑起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责,而善堂正是他们施展实力的最合适平台。清末舆论甚至称广州的善堂如同西方的“小议会”。足见主事者的实力已渐盖过了政府。广州善团总会在1926年的总结为“须知慈善事业,为政治之一端”。南京国民政府对各地慈善组织的种种规范,更加说明了这些组织所牵涉的各种现实利益关系。或说,近代善堂本身就反映了世变的过程。
近代善堂主要的施善活动之一就是推动义学,以教育贫困子弟。而此时的义学教育除了灌输传统的德育外,还有更实际的目标:让学子能获一技之长,以在乱世中谋生糊口。这个现实的考虑,把义学与育婴救济合而为一,成为清末施善的特色。近代善堂另一个有别于清初善堂的特点,就是重视医药救济。虽然清初也有施药局等善局,但近代慈善医院的规模、组织与影响力已远远超过传统施医的模式与方法。其中一个明显的指标就是女性在医疗领域里日益重要的角色。渐多女性受训练成为医生、护士或接生妇,在善堂或慈善医院服务。受完整西医训练的女性甚至成为梁启超眼中新中国的标杆。这个变化当然与基督教会自清末以来在中国以医学吸收女性信徒,以及女权主义的抬头有关,同时也让医疗救济的面貌起了重大的变化。透过医疗救济,大部分本土善堂逐步兼容西医,让这门近代西方科技与其相关制度,渐渐渗透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改变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
然而,近代都市善堂与施善活动并不应被视为挟西方文明与科技以推展中国“现代化”的单纯平台。善堂之所以能作为在近代世变中的稳定力量,也紧扣着传统的一端:宗教信仰。清初的“官方”善堂标榜着皇朝的恩惠,其宗教信仰不公开,也不录入史籍。只有民间的惜字会组织让人清晰看见其宗教性质。而近代善堂则多公开其信仰。清末广东的广仁善堂宣扬“孔教”以抗衡基督教为其使命。广州城中的省躬草堂则公开进行扶乩、书符、膜拜神仙等仪式,犹如清初惜字会的延续。这些宗教活动与草堂施药施棺种牛痘等救济活动相辅相成。在疫灾发生时,草堂也应官衙要求安排神祇出巡以清疫。另一例子是郑观应这位影响深远的清末维新思想家与慈善家、精明的买办与实业家。近代以来,学界只重视其作为社会政治改革者与实业家的深造影响力,而忽略了他同时也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郑观应最终的心愿竟是要修道成仙。他行善、经商、参政以改革中国的动力到底来自他对西方文明的向往?还是如省躬草堂的信徒一样,也来自传统修道成仙的信仰给予他的力量?虽然答案不会太简单或清楚,但是施善者将传统宗教信仰——如被视为“落后”或“迷信”的佛教、道教、孔教——融合着发展西洋新事物的特殊能力,的确让近代善堂在世变中扮演了稳定社会的角色。
在施医济贫等公益活动与传统宗教仪式之间无疑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省躬草堂在进入民国时期之后其宗教仪式与活动被迫退到其私领域。有关郑观应的宗教信仰问题,也一直被外界有意无意地忽视。在诸多善堂之中,只有基督教会所办的善堂能名正言顺、公开而有效地以济贫推动传教。这当然是因为基督教不像传统中国信仰一样被革新者视为“迷信”。然而洋教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却又正是近代乱世的主因之一。都市善堂是否能有效地稳住社会,视乎其主事者处理这些紧张关系的能力与策略。广州民初的方便医院是一个有趣的成功例子。方便医院在辛亥革命之后一方面保留传统施医服务,但又顺从革命政府的要求引进西医。医院虽然并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在几个重要的反帝国主义侵华的纪念日,积极举办大型而隆重的“醮”,结合佛道两教的势力,以传统礼忏仪式来让广州市民集体宣泄“尽国民一心”的爱国情绪。这些策略不但让方便医院在经济萧条期间募得所需要的善款,同时也摆脱了“迷信”标签的纠缠,成为民国时期团结广州各界的重要稳定力量。换言之,变世中的都市里各种新旧事物间的角力与紧张性可以让传统善堂失去原来定位而没落,但也可以让有应变能力的新式善堂在当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与确立位置,有效地稳定地方社会。
本文集结合了笔者20世纪90年代至2015年的论文,部分沿着拙作《施善与教化》的思路,进一步探讨近代善堂发展的历史过程,仍未成系统。望读者指正。明清时期的启蒙教育17、 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基础教育*本文原为英文,最早发表在B.Elman & A.Woodside, eds.,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pp.381—416。
罗友枝(Evelyn Rawski)对清代中国的基础教育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综述。自此之后,关于这一重要问题几乎没有任何更深入的研究。Evelyn S.Rawski,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a,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9.与罗友枝明显的乐观主义相比,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对大众识字教育的看法相对悲观,这是少数几个鼓舞性地回应罗友枝的研究的作品之一。不过必须承认,对受教育比例这一难题作出定论为时尚早。Alexander Woodside, “Some Mid�睶ing Theorists of Popular Schools: Their Innovations, Inhibi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the Poor”, Morden China 9, no.1(January, 1983), pp.3—35.罗友枝在她的书中对基础教育的其他方面的研究所设定的事项——教育内容,以及国家、社会和家庭的角色——也需要研究。Sally Borthwick, 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China: The Beginning of the Modern Era, Hoover Institute Press, 1983。这一杰出作品,大致包含清末民初。除此之外,与现代法国的对比,请参考Francois Furet and Jacques Ozouf, Reading and Writing: Literacy in France from Calvin to Jules Ferry, French original, 197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本文尝试追溯明末清初时期国家、社会、宗族或家庭在基础教育问题上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同样会密切关注6—15岁左右儿童的学校教育的形式和内容,以探寻国家、社会以及家庭在儿童教育上各自的目的。本文涉及的调查仅限于长江下游地区,此区域在经济上是中国无可争辩的最富裕的地区,在文化上也是17和18世纪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长江下游地区虽不是“具有普遍性”的区域,但它的基础教育情况,应该最接近中国的理想状态。
一、 国家、社会和宗族的教育政策
现代化以前的中国基础教育学校主要由三种机构创建:国家、社会、宗族或家庭,它们有各自的优先任务,但有时也有重叠。例如,通过科举考试是许多儿童和家庭的终极目标。的确,尽管踏入小学的儿童在具备参加科举考试的能力之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这一终极可能性确实影响了基础教育的课程设置。而多数儿童无法参加科举考试这一事实,让许多教育家认为小学教育的内容应该独立于科举考试制度的要求,应该着眼于道德教育和社会纪律教育。在科举考试制度下的整个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基础教育的中心极具模糊性。这也导致了国家、社会和家庭在这一问题上的目标、需求和政策的不同。关于明清时期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实现文化再生产的过程的完整讨论,参见Benjamin A Elma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via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no.1(February, 1991), pp.7—28。
变中谋稳:明清至近代的启蒙教育与施善济贫17、 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基础教育(一) 国家和社学制度
社学(社区学校)制度由明太祖于1375年发布诏令创建。推翻蒙古人的野蛮统治之后,兴建社学的明显宗旨是通过反精英主义的大众运动,维护帝国的正统儒家价值观。“社”是一种古老的行政管理单元,包含25个家庭。明代时期,不再严格考虑家庭的数量。“社学”可大致翻译为“社区学校”。关于明朝成立之后社会秩序重建这一问题,参见Edward L.Farmer, “Social Order in Early Ming China: Some Norms Godified in the Hung�瞱u Period”, in B.E.Mcknight, ed., Law and the State in Traditional East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7, pp.1—36,其中进行了详细论述。社学无固定形式。一道1504年的圣谕(可能是对当时情况的陈述)规定15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入学学习礼仪。《大明会典》(1587年),卷78,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3页上。当时规定农村社群尤其需要建立社学,这样即使是乡村儿童也能得到儒教文化的浸润。《明实录》,卷96,洪武八年正月,第4页上。洪武帝及之后的皇帝于1375年、1436年、1465年、1504年反复颁布这条诏令。关于对这一系列诏令的描述,参见王兰荫:《明代之社学》,《师大月刊》1935年第21期,第49—52页。地方志中也有地方官员在整个明朝不断地恢复并资助地方社学的相关记载。但是,国家政策中的这一创举不应被视为实现普及教育的尝试。这一举措更像是庆祝儒教正统及其政治秩序基础回归的象征性表示。但是少部分官员确实把这些社学作为有志参加科举的儿童的预备学校。王兰荫,第53页。无论如何看待这些社学,实际上社学制度并未一直受到持续的政策支持。有两点可以证明:国家无力也不愿克服这种制度首要的困难;社学在许多地方明显处于边缘地位,并且时开时停。
明太祖在兴建社学制度之后不久就发现了实施的困难性。在1385年颁布的大诰中,洪武帝把社学制度的失败归咎于地方官员的无能和腐败,称他们“有愿读书者,无钱不许入学,有三丁四丁不愿读书者,受财卖放,纵其愚顽,不令读书”。由于无法管理地方官员的行为,他随即暂停了社学制度。《社学》,《大诰》,1385年,第44篇,第23页下—24页上。诏令停办的命令实际颁布于2年前的1383年。参见王兰荫,第50页。
国家的支持疲软无力,地方社学的稳定就完全依赖于地方官员的支持。有一个典型的例子,1375年,据方志资料,皇帝发布诏令在高邮建立了172所学校。到1467年,没有一所存留,地方官不得不又在此创建了5所学校。但是根据记载,到1572年,这5所学校也都不存在了。《高邮县志》,卷4, 1572年,第16页下—17页下。据记载,陈于王(1606年进士)——明末嘉善著名学者陈龙正(1585—1645)之父——在句容做官时,于1597年恢复了句容的这5所学校,而这些学校自1570年重建后就处于停学状态。陈龙正:《几亭外书》,载《几亭全书》(序言日期1631年,出版社未知),卷3,第18页上;《江宁府志》,卷16, 1880年(1811年),第15页下。从该地方志中可知,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当地(包括乡村)原有16所学校。金坛也是相同情形,1375年兴建了一批学校,此后开开停停,分别在1462年、1466年以及15世纪80年代分别复学,最后一次复学是在1515年。每次都是地方官发现有必要重建这些被荒废的学校。到16世纪20年代初期,这些学校再一次处于荒废状态。《金坛县志》,卷6, 1921年,第9页下。尽管这些学校时开时停,难以管理,但是必须注意,恢复和资助它们的总是地方官员。他们认为维系国家的学校是他们的职责。在这种意义上,尽管缺乏连贯的政府支持,这些社学仍是国家的存在以及关心基础教育的证据,是文化控制的工具。
但到明末,一些官员在学校问题上开始采取新政策,当时学校也正在获得不同的意义。1599年,浙江布政使张朝瑞在两名地方官员的帮助下尝试把学校、乡约、保甲和本地粮仓融合为一个大型的地方系统。这次尝试旨在简化繁文缛节,落实保甲制度,所体现的新态度非常清晰。但实际上,这次尝试仅仅是通过加强保甲恢复地方对社会的控制,恢复意识形态的灌输,实质上是由地方官执行的。《保约仓塾》,载《皇明经世实用编》(万历版),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26页。这次尝试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但最终结果却是给学校带来了新气象。类似的事例,1570—1574年任福建惠安县县令的叶春及(1552年进士)在他编纂的著名县志中,在详细描述当地的地理状况之后,只提及了四个地方机构:乡约、保甲、里社、社学。叶春及:《惠安政书》(1573年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显然,社学当时被认为是地方系统的一部分,而地方系统不可避免地把社区民众领导者置于负责的地位,它的实质目的是巩固社会。
这种变化不是意外。当时社学的数量越来越多,它们被用作乡约宣讲地或社区粮仓。例如,上海的上洋社学于16世纪20年代早期由地方官重建,官员们也将此地用于乡约宣讲。青浦的社学建于16世纪90年代初,后被改用为粮仓。《松江府志》,卷32, 1815年,第17页上;《青浦县志》,卷9, 1879年,第29页上。更为显著的是明末一些社学已经开始实现一个新的功能。较早时期,学校普遍只教育“有天分的儿童”,在1465年,皇帝甚至下诏禁止官府强迫穷人家的孩子入学。关于吴县1447—1466年的社学,参见《苏州府志》,卷26, 1883年,第25页下—26页上;关于15世纪后期建立的学校,参见《溧阳县志》,卷7, 1813年,第7页下;关于1497年恢复的学校,参见《江阴县志》,天一阁版(明末),卷7,第5页上。关于1465年的诏令,参见王兰荫,第52页。自16世纪后期以来,有一些学校称教学对象是“地方社区贫困子弟”。常熟有一所建立于万历年间的学校即是这种情况;常州府官于1530年建立了一所学校,名称便是“义学”。常熟的这所学校在1586年和1587年自当地民众处获得了大量捐助。地方民众也接手了一些学校,比如如皋民众在1617年接手了当地社学。《苏州府志》1883年,卷26,第46页下—47页上,卷27,第36页上;《如皋县志》,卷9, 1808年,第63页下。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这些变化在全国零零散散地出现,说明了当时国家基础教育学校的不稳定,也表现了国家开始小心翼翼地把学校融入社会系统。
明末的官员、思想家吕坤(1536—1618)大概属于最后一批呼吁国家再次尝试恢复原本的社学制度并强化国家权威的人。他鼓吹恢复社学的著名论断实质上有两个新观点:国家系统地资助教师培训项目;对所有儿童实行三年义务教育。吕坤建议每个县选出20名左右40岁以上的正直人士,教授他们朱熹的《小学》、《孝经》以及一些简单的语言学。一年学期结束后,考试测评,将成绩好的分配至当地社学。他还建议,每年10月收割季节过后,所有的孩子均至少参加3个月的学校学习,持续3年。成绩好的可以继续学习,成绩差的允许最终离校。参见吕坤:“复兴社学”,《实政录》,云南图书馆编:《吕子全书》(20世纪初),卷3,第7页下—8页上。与吕坤同时代的叶春及对社学改革的建议是把社学制度化地与科举考试联结在一起(只有社学学生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叶春及:《惠安政书》,第361页。这些变化需要更严密的国家控制,需要制定更具持续性的中央政策。但是这样一种政策既缺乏社会需求,又缺少国家激励。吕坤和叶春及的改革建议与时代格格不入,统治者听而不闻。
(二) 社会和义学制度
许多清朝文献认为“社学”和“义学”这两种不同的术语表示的是同一种制度,明代称社学,而清代称义学。罗友枝(Evelyn Rawski)认为它们是相同的;cf. Rawski, 35,注释56。Benjamin Elman似乎认为义学与学院属同一级别,参见Benjamin A.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19—120。但是我认为他高估了政府对此区域的控制,高估了清朝时期义学的知识重要性。一些当时的人也认为义学和社学是一样的,参见《宜兴荆溪县志》,卷4, 1882年,第15页上。关于各种清代义学的组织者、财务以及规条的详细描述,参见小川嘉子:《清代に方シける义学设立の基盘》,载林友春:《近代中国教育史研究》,东京国土社1958年版,第273—308页。这种简化的方式处理掩盖了两种制度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而这种不同是理解学校的社会发展的关键:与国家的社学相比,义学更是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学校,而且义学的慈善因素很关键。(关于18世纪前十年东南地区义学与国家的特殊关系的描述,参见罗威廉的著作。)义学是明末社学发展的自然结果。
清初的地方官黄六鸿(1651年举人)是最早一批了解义学新特征的人之一。在写给准地方官们的著名手记《福惠全书》中,黄六鸿对义学取代社学表示赞赏:
今者富贵子弟,有力而多不学。贫贱子弟,无力而不能学……而有司又视教化为迂阔不急之务,财力为有限之资,而社学之制,不能修复于今日……然则斟酌于塾庠之间,合力于绅袊之乐助,而有司先为之倡者,其惟义学乎。夫义学者,专为贫穷无力之子弟而设也……大约城厢视民贫富之多寡而置之。至于乡视镇集邨庄之大小而置之。少则或一或二,多则或四或五……黄六鸿:《福惠全书》,小畑行简训诂,山根幸夫解题,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版,卷25,第12页下—13页上。
……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它成功地将原本割裂的“教育史”“社会史”和“政治史”熔铸一炉。以往的论著往往将“施善济贫”视为一种慈善行为,而将“启蒙教育”视为一种精英运动。然而,本书深刻揭示了两者之间共生共荣的内在机制。在缺乏健全国家福利体系的古代社会,通过教育手段进行的道德重塑,本质上就是一种成本最低廉的社会控制与资源分配方式。贫者因受教而获得秩序感,富者因施教而巩固其道德合法性,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作者对清代地方乡绅设立“义学”的动机的挖掘,尤其发人深省——这种善举,与其说是无私奉献,不如说是一种精明的“公共关系投资”。这种对历史动机的深度挖掘,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公益”二字的理解边界,让我开始审视今天许多公共项目背后的驱动力,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评分这部著作的深度与广度着实令人惊叹。作者以一种近乎手术刀般的精准,剖析了传统社会结构在面对“变”与“稳”这一永恒悖论时的内在张力。书中对明清之际商业资本积累与传统宗族伦理相互消解过程的论述,尤为精彩。它不单是罗列史料,更像是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动态模型,展示了社会权力如何从土地向新型财富形态转移,以及这种转移如何反作用于社会治理的基层逻辑。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义庄”“社学”等机构运作机制的微观考察,这些看似边缘化的民间组织,实则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润滑剂”和“减震器”。通过对这些细微之处的描摹,我们得以窥见宏大叙事背后,普通民众如何在制度的缝隙中寻求生存之道,以及精英阶层如何以“济贫”之名行“维稳”之实的微妙平衡术。阅读过程如同在迷宫中寻找出口,每一步都充满了智识上的愉悦和对历史复杂性的敬畏。它让人意识到,历史的演进并非单向的线性发展,而是在不断的拉扯与妥协中螺旋上升的。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克制的美学”。作者的文字精准、凝练,几乎没有一句多余的渲染或情绪化的表达。然而,正是这种冷静的笔调,反衬出所描绘历史图景的波澜壮阔与人类命运的无奈。他擅长使用那种看似平铺直叙的句式,来承载极为复杂和具有颠覆性的历史观点,这使得读者必须全神贯注地去咀嚼每一个动词和名词的指向。例如,在讨论近代地方自治的萌芽时,作者对“绅士”与“士绅”在不同语境下的微妙权力差异的界定,细致到令人拍案叫绝。这种对学术严谨性的极致追求,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研究成果,更像是一部精工细作的学术工艺品,值得每一位对社会变迁的深层逻辑感兴趣的读者,细细品味、反复研读。
评分我必须承认,初读此书时,我对其标题中包含的宏大跨度感到些许担忧——从明清到近代,时间轴拉得太长,会不会流于空泛?但阅读下去才发现,作者采用了一种巧妙的“锚定点”策略。他并没有试图面面俱到,而是紧紧抓住几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如商品经济的渗透、西方思潮的冲击,以及国家权力结构的微调,作为分析的支点。每一次分析都像是一次深入的钻探,将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那种感觉就像是沿着一条古老的河流向上溯源,虽然河道时而宽阔,时而狭窄,但水流的源头和方向始终清晰可辨。对于那些习惯于碎片化阅读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具有整体性和贯穿性的历史视野,非常有助于培养系统性的思维能力。
评分读完此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历史学家终于摆脱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全景式”叙事陷阱,转而沉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作者的笔触极为细腻,对于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在面对社会变迁时的反应,有着惊人的洞察力。比如,书中对江南士绅在遭遇地方灾荒时的不同应对策略的对比分析,就生动地展现了“教化”与“实用主义”之间的张力。他们一方面要遵循儒家圣贤教诲,表现出热心公益的姿态;另一方面,面对日益增长的贫困人口,其资源和能力又显得捉襟见肘,最终不得不诉诸于更具排他性的地方性网络。这种对“理想”与“现实”的细致解构,使得历史人物不再是扁平的符号,而是拥有真实困境的行动者。全书的论证逻辑严密,引证扎实,但叙事风格却绝不枯燥,仿佛有一位博学的朋友在为你娓娓道来,让你在沉浸于历史细节的同时,也能不断地反思当下。
评分这次在京东的购物经历很不错,书是正版的,价格上还算比较实惠,而且品相上还是不错的。此外在送货上,物流比较快,比较及时。因为这个书有时候购买下来有时效的需要,送的及时了,对于使用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所以综上来说,这次还是挺好的,以后也会继续在京东购买。
评分在錢塘縣南咸淳志在定山北鄉勅賜功徳□額曰旌忠朱弁墓在錢塘縣西湖智果寺後
评分中卜塟積善峯下張九成墓在海寜州西五里陳
评分岳武韓世忠墓在昌化縣西四十里義于山劉錡墓
评分这个书不一定要买
评分在錢塘縣南咸淳志在定山北鄉勅賜功徳□額曰旌忠朱弁墓在錢塘縣西湖智果寺後
评分书不错,喜欢文史的朋友可以看看!!
评分梁的论文读起来总是很有意思,美中不足的是这本书收录了两篇其他书里有的内容,感觉重复了
评分很好的一本书,深受启发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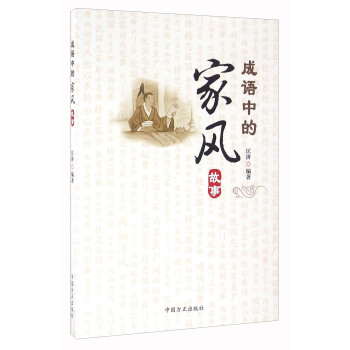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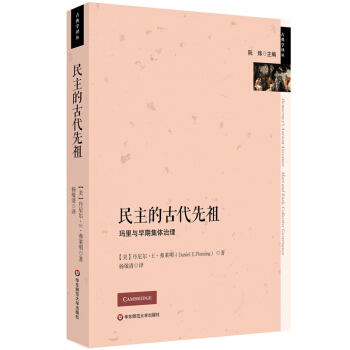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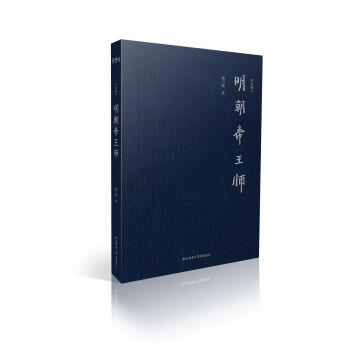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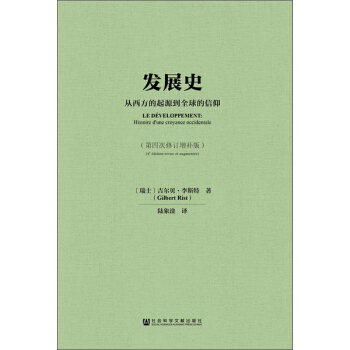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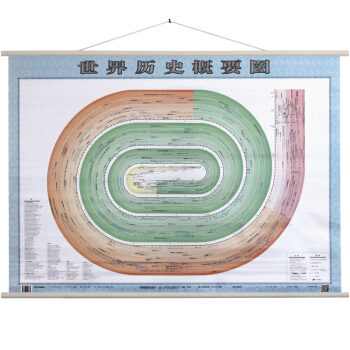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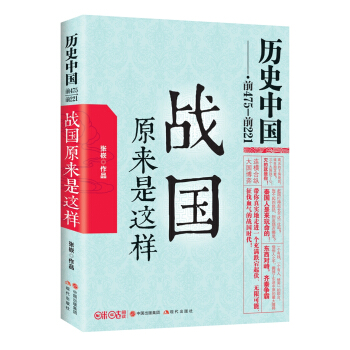

![陈舜臣说史记:帝王业与百姓家 [ものがたり史記]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75961/59425a7aN01a96f1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