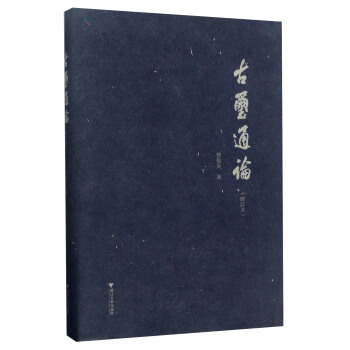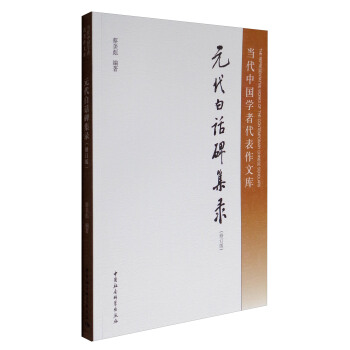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元代白话碑的碑文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是一种有价值的原始史料。元代白话碑的价值,可以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两方面来说明。第1是语言学上的价值。元代的各种公牍,大都是先用蒙古文写成,然后再译为汉文白话。这种白话,虽然由于翻译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和当时的实际汉语完全一致,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元代的白话口语状况,成为研究元代汉语史的一种很好的资料。《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就是此类资料的相关整理。《当代中国学者代表作文库: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收录的白话碑文,依年月先后顺序编序。金石目录书传统的著录体制,备列撰人、书体、年月、所在地、题解等项,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必要说明。
内页插图
目录
1.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1223年)2.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面奉成吉思皇帝圣旨(1223年)
3.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窝阔台圣旨(1235年)
4.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窝阔台圣旨(1235年)
5.凤翔长春观公据碑(1238年)
6.济源紫微宫懿旨碑(1240年)
7.户县草堂寺碑——阔端令旨(1243年)
8.林州宝严寺碑——碑阴茶罕文告(1244年)
9.汲县北极观懿旨碑(1245年)
10.孟州王屋灵都观碑——全真道给文(1245年)
11.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阔端令旨(1245年)
12.户县草堂寺碑——阔端令旨(1245年)
13.户县草堂寺碑——阔端令旨(1247年)
14.户县草堂寺碑——帖哥钧旨(1247年)
15.周至重阳宫累朝崇道碑——弥里杲带令旨(1250年)
16.安邑长春观劄付碑(1252年)
17.平遥崇圣宫给文碑——李志常给文(1252年)
18.平遥崇圣宫给文碑——全真道给文(1253年)
19.毫州太清宫令旨碑(1257年)
20.毫州太清宫圣旨碑(1261年)
21.林州宝严寺碑——元世祖圣旨(1261年)
22.周至重阳万寿宫碑——元世祖圣旨(1280年)
23.龙门建极宫碑——安西王令旨(1276年)
24.莱州石真人墓令旨碑(1279年)
25.莱州长生万寿宫令旨碑(1280年)
26.蔚州飞泉观碑——道士具结文书(1281年?)
27.蔚州飞泉观碑——抄录世祖圣旨(1280年)
28.户县东岳庙令旨碑(1282年)
29.永寿吴山寺执照碑(1283年)
30.大都崇国寺文书碑——总制院劄付(1284年)
31.大都崇国寺文书碑——僧录司执照(1284年)
32.无锡庙学圣旨碑(1288年)
33.赵州柏林寺圣旨碑——世祖圣旨(1293年)
34.荥阳洞林大觉寺碑——成宗圣旨(1295年)
35.赵州柏林寺圣旨碑——成宗圣旨(1296年)
36.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世祖圣旨(1260年)
37.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世祖圣旨(1272年)
38.周至太清宗圣宫圣旨碑——成宗圣旨(1296年)
39.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世祖圣旨(1285年)
40.邹县孟庙文书碑——断事官劄付(1237年)
41.灵寿祁林院碑——成宗圣旨(1298年)
42.灵寿祁林院碑——皇太后懿旨(1298年)
43.林州宝严寺碑——成宗圣旨(1298年)
44.平山永明寺碑——成宗圣旨(1300年)
45.灵寿祁林院碑——皇后懿旨(1301年)
46.荥阳洞林大觉寺碑——帝师法旨(1301年)
47.灵寿祁林院碑——帝师法旨(1301年)
48.河中栖岩寺圣旨碑(1302年)
49.济源紫微宫圣旨碑(1304.年)
50.长清灵岩寺法旨碑(1341年)
51.长清灵岩寺下院榜示碑(1306年)
52.曲阜加封孔子致祭碑(1308年)
53.荥阳洞林大觉寺碑——晋王甘麻刺令旨(1297年)
54.济源紫微宫圣旨碑(1309年)
55.荥阳洞林大觉寺碑——皇太后懿旨(1309年)
56.荥阳洞林大觉寺碑——“皇太子”令旨(1309年)
57.平遥太平崇圣宫圣旨碑(1309年)
58.平山永明寺碑——仁宗圣旨(1311年)
59.大理崇圣寺圣旨碑(1311年)
60.荥阳洞林大觉寺碑——仁宗圣旨(1312年)
61.赵州柏林寺碑——仁宗圣旨(1312年)
62.林州宝严寺圣旨碑(1313年)
63.元氏开化寺圣旨碑(1314年)
64.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1314年)
65.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1314年)
66.周至重阳万寿宫碑——仁宗圣旨(1314年)
67.荥阳洞林大觉寺碑——晋王也孙帖木儿令旨(1314年)
68.邹县孟庙文书碑——户部关文(1314年)
69.周至太清宗圣宫圣旨碑——仁宗圣旨(1315年)
70.昆明筇竹寺圣旨碑(1316年)
71.荥阳洞林大觉寺碑——小薛大王令旨(1318年)
72.邰阳光国寺圣旨碑(1318年)
73.周至重阳万寿宫碑——仁宗圣旨(1318年)
74.溶州天宁寺法旨碑(1321年)
75.易州龙兴观懿旨碑(1309年)
76.泰山东岳庙圣旨碑(1324年)
77.许州天宝宫圣旨碑(1326年)
78.周至太清宗圣宫圣旨碑——文宗圣旨(1330年)
79.曲阜颜庙请封奏疏碑(1334年)
80.淇县文庙圣旨碑(1334年)
81.辉县颐真宫圣旨碑(1335年)
82.邹县万寿宫圣旨碑(1335年)
83.邹县仙人万寿宫圣旨碑(1335年)
84.均州灵应万寿宫圣旨碑(1337年)
85.平山天宁万寿寺圣旨碑(1337年)
86.周至重阳万寿宫碑——顺帝圣旨(1341年)
87.长安竹林寺圣旨碑(1343年)
88.平山天宁万寿寺碑——顺帝圣旨(1357年)
89.周至重阳万寿宫碑——顺帝圣旨(1351年)
90.大都崇国寺圣旨碑(1354年)
91.平山天宁万寿寺碑——皇太子令旨(1356年)
92.大都崇国寺刳付碑——宣政院劄付(1363年)
93.周至重阳万寿宫圣旨碑(1363年)
94.大都崇国寺劄付碑——宣政院劄付(1366年)
编余散记:白话碑诸问题
碑文索引
前言/序言
本书初版于1955年,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次修订没有增加碑文,只是重写了碑文的注释,增补了拓本图影,改正了错字。对一些碑题酌加修订,增入题解。我留意元代碑拓,始于1950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室工作时期,是在罗常培所长领导下工作的。本书的编纂,曾得到陈垣前辈的鼓励和支持,又承吕叔湘、邵循正两先生指教。现在修订本出版,各位先生都已辞世,谨在此敬志我的感念与景仰。
用户评价
这部书的装帧设计简直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又不失典雅的气质,仿佛能从封面就感受到内容的厚重。纸张的选择也格外考究,触感温润,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让人对即将展开的阅读之旅充满期待。排版布局清晰明了,字体大小适中,阅读起来非常舒适,即便是长时间沉浸其中,眼睛也不会感到疲惫。可以看出,出版社在制作这本书时投入了极大的心血,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对知识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关怀。尤其是那种经典的内敛风格,没有丝毫浮夸的装饰,完全将焦点集中在了文字本身,这对于我们这些追求深度阅读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这本书的实体形态本身,就具有了一种收藏的价值,它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更像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评分这本书的内容深度和广度都令人称奇,它如同一个深邃的知识海洋,每翻开一页,都能感受到作者们在各自领域内精湛的学识和独到的见解。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因为某个观点豁然开朗,或是对某个传统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作者们并非只是简单地陈述事实,而是通过严谨的逻辑和丰富的史料,构建起一套完整而富有洞察力的认知体系。这种论证的层层递进,使得即便是初涉此领域的读者,也能逐步领会其中的精髓。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那种追求真理、勇于批判的学术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我。它鼓励我们不要盲从前人,而是要带着审慎的态度去探索未知,这种治学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呈现出一种令人愉悦的交织感,有些篇章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将复杂的概念阐述得深入浅出,如同与一位睿智的长者在促膝长谈,让人如沐春风;而另一些部分则笔力遒劲,论证犀利,犹如精雕细琢的宝剑,直指问题的核心,读来令人精神为之一振。不同作者之间的叙事节奏和语感差异,非但没有造成阅读上的断裂,反而丰富了整体的阅读体验,仿佛置身于一场高水平的学术对话之中。这种多维度的声音和表达方式,极大地拓宽了我的思维边界,让人体会到学术探讨的活力与魅力。文字的张力拿捏得恰到好处,既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又兼顾了可读性,使得每一次阅读都成为一次充满发现的旅程。
评分我特别欣赏这本书在案例选择和论证材料上的独到眼光。它所引用的实例和数据,都经过了精心的筛选和核实,极大地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许多细节的呈现,都是以往阅读其他相关著作时所未曾注意到的盲点,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细节之中藏着魔鬼”的道理。从宏观的理论框架到微观的具体分析,这本书构建了一个立体而坚实的知识结构。对于我们这些需要将理论付诸实践的读者而言,书中提供的那些经过检验的分析方法和参考系,具有极高的操作价值。它不是停留在空泛的理论探讨,而是扎根于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展示了学术研究如何能够真正有效地指导和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复杂现象。
评分这本书的价值,绝非仅限于它所承载的知识本身,更在于它所激发出的后续思考和联想。读完之后,我的脑海中仿佛打开了一扇扇新的窗户,对许多既有观念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重构。它像一把钥匙,开启了我通往更深层次理解的大门,让我开始主动去探索那些尚未触及的领域和交叉学科的知识。这种“被点燃”的求知欲,才是真正好书带给读者的馈赠。它不像快餐文化那样短暂满足即刻需求,而是具备长久的生命力,每一次重读,都会带来新的感悟和理解层次的提升。这本书已经成为我书架上被经常翻阅,并被标记得密密麻麻的重要参考资料。
评分京东购书就是实惠,快递速度还贼快。朋友喜欢看书,喜欢收藏书,总是让我帮忙买买买。哈哈。我乐意。
评分買来放著当參考书。。。。
评分好看,速度很快,下次还会再买。
评分宋代的思想与学术,是热门研究话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从唐宋社会转型、佛道二教影响等多个角度,对之进行了深入探讨。
评分好看,速度很快,下次还会再买。
评分好看,速度很快,下次还会再买。
评分读元代白话文很带喜感
评分元代用白话来写公文,很有意思。
评分为元代的执政者发布的内容,兼具史料与观赏价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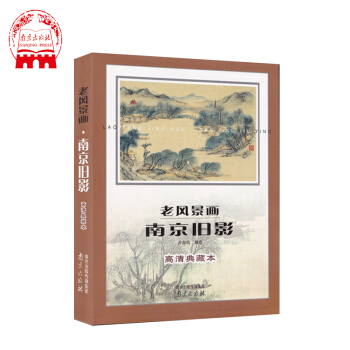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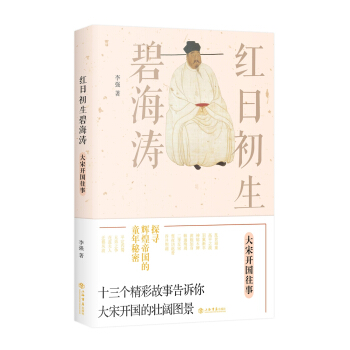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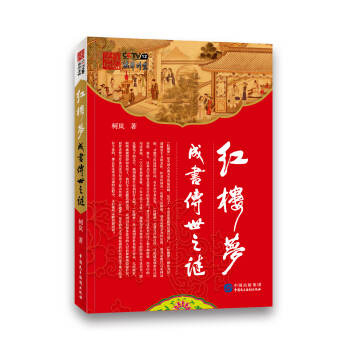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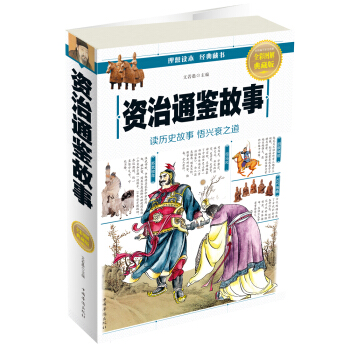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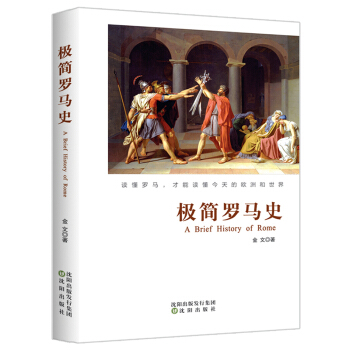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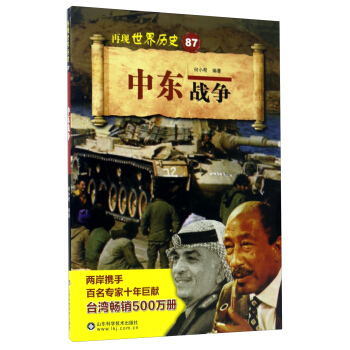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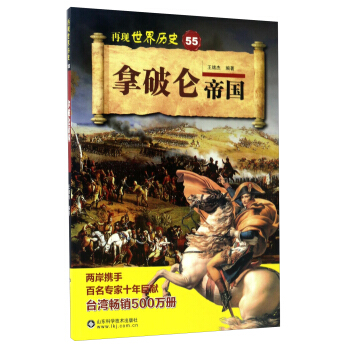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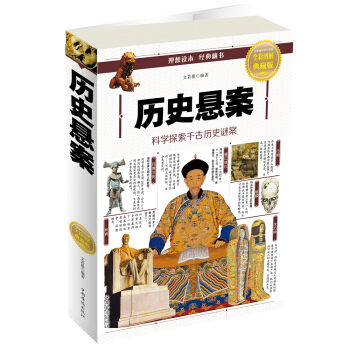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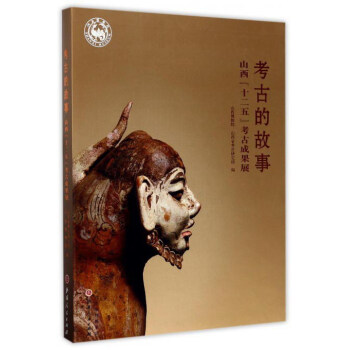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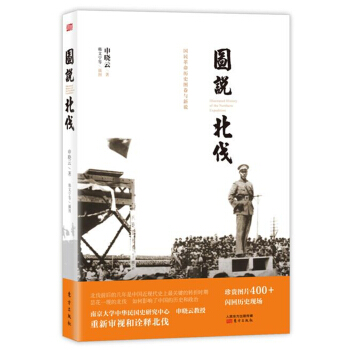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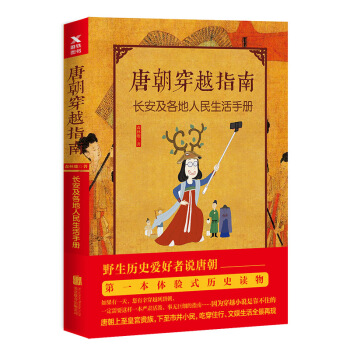

![太平天国兴亡录 陈舜臣作品 [ものがたり史記]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55311/5996a623N8e47bc4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