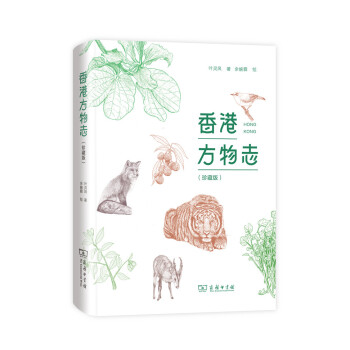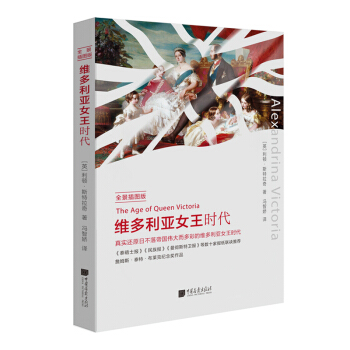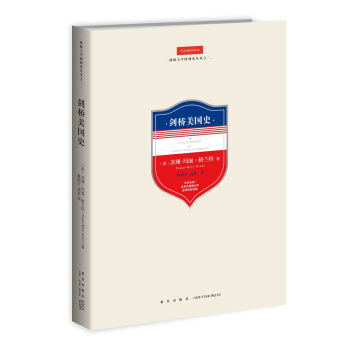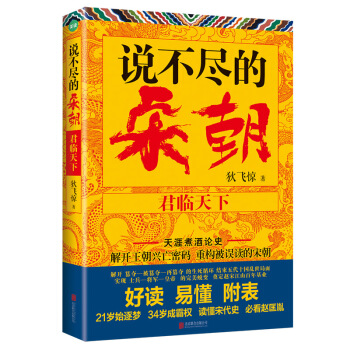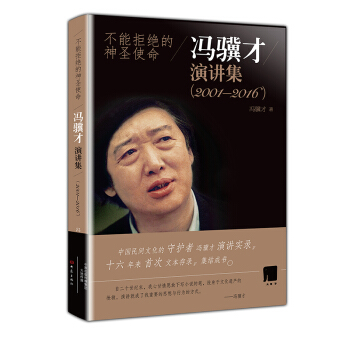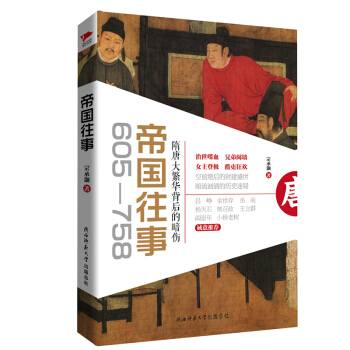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帝国往事:(605-758)隋唐大繁华背后的暗伤》描绘了中国的7世纪和8世纪,也就是隋唐之交的百年。在那里,盛世就像是一个精心炮制、虚幻而又深刻的镜中世界。在这本小书里,你看见的同样是帝王将相,可又不是你所熟悉的面孔。在那散落的尘埃里,隐逸着别样的风情。它不仅仅属于某一个人,更属于投身其间的每一个人。它对你的魅惑有多大,你对它就有多少的好奇与怕。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功德簿,更不是这个大帝那个大帝的起居注。对于那些毫无头绪的历史叙事,那些天地间的号哭、月光下的阴谋、酒宴上的酣畅,无不是人情利害在时间里降妖捉怪。对于那些历史上肯定发生过而史书没有记载的事情,你要看到它们,嗅到它们,*好能触摸到它们的心跳。
作者简介
宗承灏,作家,在国内多家刊物设有专栏。文字如刀,抽茧剥丝,专注于分析和解构中国历史上各大利益集团的生存竞争与博弈规律,往往一针见血切中问题之要害。已出版《武则天帝王笔记》《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权力的智慧:冰与火的中国历史定律》《大明朝(1368—1644):从洪武到崇祯的权力变局》等作品。
目录
一 两个王朝,一个时代1.来自南方天空的诱惑/002
2.患上癫狂症的权力诗人/006
3.杨广活在谁的幻想里/013
4.与烈火烹油的时代共舞/018
5.唐朝是机会主义者的果实/041
二 盛世来临前的血色黎明
1.一座盛大的赌场/047
2.一场趋利避害的游戏/061
3.帝国的权力均衡论/069
4.博弈:靠人不靠天/073
5.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078
6.玄武门,一个盛世的密码/081
三 贞观年的困守与突围
1.凶险还是不期而至/093
2.他宁愿选择自由/104
3.被王朝绑架的人质/111
4.储君危机的临界点/118
5.谁的道义和良心债/124
四 以一个女人的名义出发
1.阴谋者的假面与誓言/133
2.后宫世界的攻守之道/141
3.无处不在的情报网/145
4.内廷与外廷的交锋/156
5.天下有了新的女主/169
五 酷吏时代:无路可退的战局
1.非常规打造“权力清道夫”/177
2.赤裸裸的施恶白皮书/188
3.逃不开的权力宿命/201
六 盛世:华美锦袍上的虱子
1.少年精神/216
2.亲情带来的伤害/222
3.李隆基的“圈养”策略/230
七 天宝十四载的罪与罚
1.为盛世敲丧钟的人/241
2.帝国的农夫与蛇/246
3.转折/251
精彩书摘
一两个王朝,一个时代大业元年(605年)春天的某个早晨,黄河流域某个村庄的王大和王二两兄弟,正在享用野菜糊糊做的早餐。也就在此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拥进屋子里的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他们二话不说,抓起两人就往门外拖。
“官爷,我们犯了什么事?给个理由。”两兄弟一头雾水地问道。
“没犯事,也没有理由。”官兵吼道,“皇帝要修房子,还要挖一条沟,人手不够用,抓你们去帮帮忙。你们是要建房子还是挖沟?这是一道必选题,二选一。”
“我喜欢建房子。”老大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抢先答道。
“那好,你去建房子吧!”老大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官兵带走了。
“请问官爷,皇帝要建什么房子啊?”老二看上去似乎精明一些,也谨慎得多。
“少废话!说了你也不知道,东都洛阳!”
“那我还是挖沟吧。”精明的王二认为,自己挖沟肯定要比哥哥建房子有活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挖的沟要比村东头那条沟大得多得多,那已经不能算是沟了,而是一条大运河。小人物王二至死也不清楚有这样一组数据,属于这条大运河: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长两千余里,三月二十一日动工,同年八月十五日皇帝就要乘着龙舟前往江都,前后只有一百七十一天的时间。
小人物王二就这样无奈地上路了,数百万像他一样的农夫此时也正从各州各县各村向着同一个工地聚集。我们可以想象,绵延千里的工地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笼,身陷其中的王二在绝望中一锹一镢地开掘,开掘又使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他只能看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他身边倒下。历史就是用数以亿计的小人物的牺牲,来换取时间深处那些屈指可数的功与名。布衣小民的生命从来都上不了历史的台面,一句“隋民不胜其害”也就交代了过去。
1.来自南方天空的诱惑
大业元年八月十五日,此时江南正是大好的风光、大好的时节。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款步登上岸边的龙舟,文武官员紧随其后。桅杆上锦帆次第张开,武士的刀剑在空气里散发着凛冽的光泽,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倒映在运河的清波里,时间深处晃动着暧昧的脂粉香气。
在这明媚的秋光里,每个人身后的影子都比他的实际身量伸长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垂杨依依,天涯迢迢,整个画面流淌着现代派画家浓艳而疯狂的意象。那领头之人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器宇轩昂地走进了龙舟的头舱。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大隋王朝的第二代君王,死后谥号“炀帝”的杨广。“炀”是一个很生僻的字,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好的词汇,昭示不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还有一个皇帝,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讽刺的是,陈后主能够得到这一谥号正是拜杨广所赐,但后人习惯称陈叔宝为“后主”。如此一来,“炀帝”也就成了杨广的专用标签,再没人和他去抢。
南下的船队从洛水入通济河,其中包括官船二千八百四十五艘,兵船二千四百艘,外加纤夫八万人,这八万名纤夫中,有专门为皇帝的龙舟拉纤的“殿脚”九百人。有着九百人的“殿脚”,我们可以想象杨广乘坐的龙舟有多么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一座水上行走的宫殿,而不是舟。这样一支船队首尾相连,绵延二百余里,可谓气势浩荡。
龙舟乘风破浪,也直接将杨广送往政治事业的巅峰时刻。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不安分的他先后八次出巡,留在京城长安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杨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水平还算过得去的诗人,还是一个在金粉与铁血中肆意妄为的非主流君主?没有人只戴着一副面孔行走于世,可是能将几幅面孔背后的身份都做到极致的却不多。杨广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写道:“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有文学评论家说,这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帝王对诗歌艺术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表现出了明显的融合南北诗风的特色。
诗人与帝王,一个是精神世界的无冕之王,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冠冕之王。如果我们将杨广的政治经历也视为一首诗,那么这首诗的开篇显现出了万丈豪情的气象。历代帝王大多定鼎于北方,并将更多的精力与关注点放在了北方或者更北方。与他们不同,杨广却将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了烟雨迷蒙的中国南方。之所以如此,与他的政治经历密不可分。开皇八年(588年),身为晋王的杨广率五十万大军平定南陈。也由此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将近三百年的纷乱格局,中华文明就此实现了自秦汉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此时的杨广只是一个十九岁的翩翩少年,意气风发,立马扬威,野心勃勃的皇子在政治舞台上迎来一个完美的开局。随后,他被封为扬州总管,在江都一待就是十年。
在江都的十年时间,杨广正值二十岁到三十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性格形成的关键十年,也是为事业打基础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杨广和隋朝的军界重臣们有了更多沟通与合作的机会。也正因为这十年,让他后来对江都尤其偏爱。这种偏爱既包含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篇布局,更体现了一个普通人对第二故乡的眷恋。
一个流淌着北方血统的皇子长期浸淫于江南的清风明月,这难免会让他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一边是重重关山和漠漠大野的硬朗,一边是山温水暖和稻香鱼肥的灵秀。北方的阳刚与南方的阴柔在杨广的血液里碰撞,然后融合。他不是生在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而是一个无限接近权力巅峰的皇子。在扬州的十年时间里,杨广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收敛得接近于无形,身居风花雪月之地,不但没有声色之好的享乐主义倾向,而且天天穿着打着补丁的王服,就连手下婢女也都是一副相貌平平、蓬头粗服的样子。
六年前,离开江都的杨广不过是一个处处都得藏着锋芒、留着小心的藩王,而今天去往江都的是在人间可以翻云覆雨的君王,他的内心也有着普通人的衣锦还乡的情怀。
他问身边的大臣:“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胭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大臣回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样的回答正是杨广想要的结果,他哈哈大笑。
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刚刚登上帝位的杨广就将自己巡幸的第一站定在了东都洛阳。自古以来,帝王们在长安的粮食接济不上时,才会想到“就食东都”,或是在长安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才会想到来这里寻求政治避难。
置身于东都的杨广问身边的大臣,洛阳居天下之中,北临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近江淮有渔盐之利,西接渑淆有关河之胜。如此上佳之所,为何没有君王在此建都?
尚书右仆射苏威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这句话是在赤裸裸地拍皇帝的马屁,古往今来的那些帝王不是不知道洛阳是龙门宝地,他们之所以没有在此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天只能将建都的机会留给你杨广。
在大隋王朝的旗帜下,南北财货争奇斗胜,八方衣冠尽显风流。杨广登基之初,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帝国的命运走向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有任何的假设可言。
杨广的性格深处有着古今文人的通病,那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自视甚高。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的竞赛,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不知道杨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此番话的,是对自己自视过高,还是对天下士子过于失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杨广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魏晋文人的孤傲孑然。他将文人的自由与帝王的刚霸融于一体,权力的游龙剑由此锻造而生。
杨广的身上有着难以根除的诗人气质,正因为如此,他那不合时宜的政治理性充满了浮华糜烂的气息。诗人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着近乎疯狂的完美追求。他登基之前,十年江都总管的任职履历让他对南方有着别样的情怀,或许是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原乡。等到他将那套象征权力的龙袍披挂在身,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就迫不及待地裹挟着权力狂奔而去。
如果说诗人与政治家是两种分工不同的职业,那么杨广更接近于一个完美的诗人;如果说,时势造就了他,将他送上权力的巅峰,那么坐在龙椅上的他,最后还是成为从龙椅上出走的诗人。说得好听一点儿,他的出走,是以诗人的方式在这块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杨广是个喜欢折腾的主,而且这种折腾,完全遵从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不管不顾搏命似的折腾。
折腾,是非主流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折腾,往往又是一个执政者的命运死穴。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权力之巅是什么感觉。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兴衰。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从诗人到皇帝,这种角色转换造成的落差,让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诗人擅长用文字构筑精神世界的乌托邦,而帝王则用权力改变现实世界的国与家。
杨广,他要将诗人与帝王这两种角色的特质集于一身,并且要做到完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权力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美学家”更加合适。权力成了非主流诗人手中的一支笔,杨广运笔如风,在帝国这张华丽的纸上挥毫泼墨。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严重倒错,甚至是完全背离时,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靠谱的执政者。
不靠谱的执政者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只能做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诗人。
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营建东都、凿通运河、修筑长城、开凿驰道,他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折腾,每一项投入都不惜血本,倾全国之力。他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张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像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应该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都在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竖起一道坚硬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杨广希望能够通过征伐高丽,使他的权力在秦汉版图的基础上得以延伸,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超越秦皇汉武,成就属于自己的千秋霸业。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结构布局非常清晰,章节之间的过渡衔接得非常自然流畅,没有那种生硬的“为了凑字数”的尴尬感。作者似乎对叙事节奏有着近乎本能的把握,总能在关键时刻抛出一个悬念,或者进行一次深入的专题探讨,从而牢牢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我尤其欣赏它在引入不同史料源头时的坦诚态度,它会明确告诉你,哪些是确定无疑的史实,哪些是基于现有证据的合理推测。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信度。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不仅是获取了一批历史信息,更像是完成了一次严谨的学术训练,这种阅读的满足感是无可替代的。这本书绝对是值得反复翻阅的佳作,每次重读都会有新的体会。
评分坦白说,我一开始对这类题材的书兴趣不大,总觉得会枯燥乏味,但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的看法。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其批判性的视角,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歌颂某个盛世,而是用一种近乎解剖学的严谨,去审视繁荣背后的结构性矛盾。书中对某些重要历史节点的解读,充满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洞察力,它敢于挑战一些约定俗成的历史定论,并提供了扎实的论据支撑。这种思辨的深度,让阅读过程变成了一场智力上的探险。读完之后,我对于如何看待“成功”和“失败”这些概念都有了新的思考。它教会我,评价一个时代,不能只看它光鲜亮丽的表象,更要深挖其内部的张力与隐患。这本书无疑是历史爱好者进阶的必备读物,它提供的远超于知识的累积,更是一种思考方式的提升。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功力着实了得,那种叙事节奏的把握,简直像在听一位功力深厚的说书先生娓娓道来,但又绝非简单的故事堆砌。它巧妙地在宏大叙事和微观细节之间切换,让人在感受时代洪流的磅礴之余,也能捕捉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生活场景的质感。我特别欣赏作者处理细节的方式,那种对当时风俗、器物乃至衣着服饰的考据,都显得非常讲究,可见下了大功夫去查阅一手资料。读到某些场景时,我仿佛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的气息,听到街市上的喧哗声。这种沉浸感是很多历史书难以企及的,它不是把历史摆在你面前让你看,而是让你真真切切地“走进去”体验一番。这种细腻的笔触,让冰冷的历史变得有血有肉,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挣扎。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和排版也值得称赞,看得出来出版社在制作上也投入了相当的心思。纸张的质感很好,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更重要的是,书中的地图和插图的运用,简直是点睛之笔。它们并非简单的装饰,而是作为辅助理解复杂地理变迁和军事调动的有力工具。特别是那些详尽的图注,很多时候能把文字中描述的模糊空间概念,瞬间具象化。对于我这种有“路痴”倾向的读者来说,没有这些视觉辅助,理解某些关键的战略部署和行政区划变动,难度会大大增加。这本书在提供优质内容的同时,也极大地优化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从触感到视觉,都传递出一种对知识的尊重和对读者的体贴。
评分最近偶然翻到一本历史类的书,内容居然这么扎实,读完之后感觉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它不像那种纯粹的帝王将相的流水账,而是更注重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普通人生活状态的描摹。尤其是一些关于地方豪强和士族阶层兴衰的论述,逻辑性很强,让人忍不住一页一页地往下看。作者在梳理复杂史料的时候,那种抽丝剥茧的劲头,读起来非常过瘾。比如,书中对某一时期赋税制度改革的分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梳理,把前因后果和实际影响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让人豁然开朗。我过去对这个阶段的认知大多停留在零散的片段上,这本书就像一个强大的搜索引擎,把所有散落的知识点整合起来,构建了一个立体而生动的历史画面。它没有过度煽情,而是用一种冷静而深邃的笔触,去探讨历史进程中那些必然与偶然的交织点,值得反复品味。
评分更棒的!溜达溜达吗!!!
评分不错的书,很喜欢,哈哈哈哈
评分不错 值得阅读
评分面对纷繁复杂的人与事,要有一颗从容与淡定的心,也就是不动心,不动心才能最顺心。
评分很不错,相当快,慢慢看
评分这套书还没集齐、好多都断货了
评分不错的书,很喜欢,哈哈哈哈
评分不错 值得阅读
评分好书,讲述了历史的情节,可以看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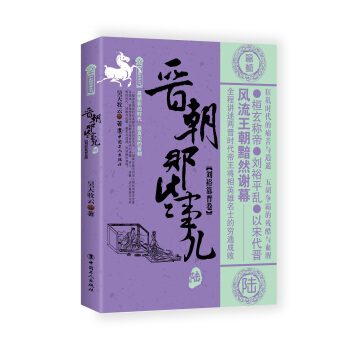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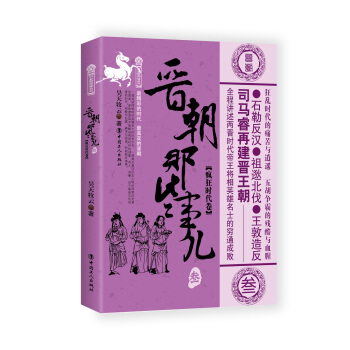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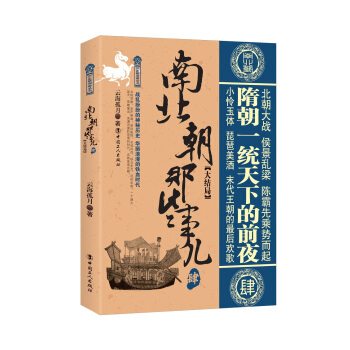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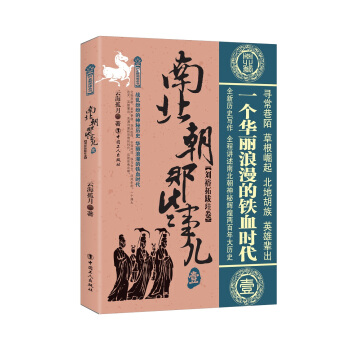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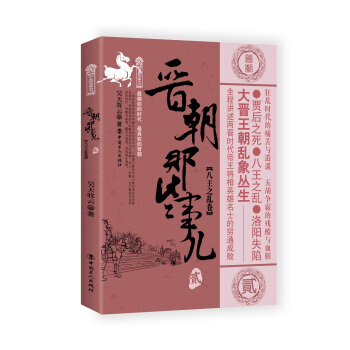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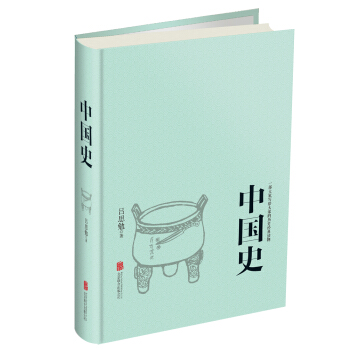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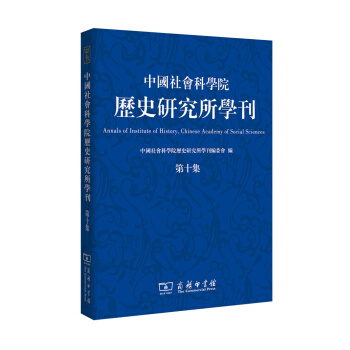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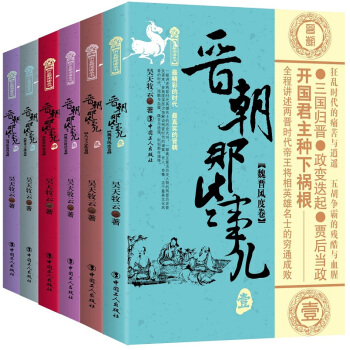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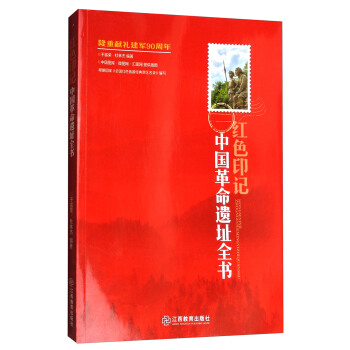
![十字军的故事(套装全4册) [十字軍物語]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83067/5aa0a0cbN4fe4d1f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