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半生缘》收录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初载一九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亦报》,题《十八春》,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亦报社出版单行本;经张爱玲改写后,以《惘然记》为题连载于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七月《皇冠》月刊,一九六九年七月皇冠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改名《半生缘》。 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份。 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 我们回不去了。作者简介
张爱玲(1920-1995),中国女作家。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1943年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和散文《烬余录》等。1952年离开上海,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1969年以后主要从事古典小说的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已出版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以及长篇小说《十八春》、《赤地之恋》等。
精彩书评
“你有次信上说《半生缘》像写你们,我说我没觉得像,那是因为书中人力求平凡,照张恨水的规矩,女主角是要描写的,我也减成一两句,男主角完全不提,使别人不论高矮胖瘦都可以identify with自己。翠芝反正没人跟她 identify,所以大加描写。但是这是这一种恋爱故事,这一点的确像你们,也只有这本书还有点像,因为我们中国人至今不大恋爱,连爱情小说也往往不是讲恋爱。 ——一九六九年六月廿四日张爱玲致邝文美书《十八春》就是《半生缘》的前身。她告诉我们,故事的结构采自J. P. Marquand的“H. M. Pulham, Esq.”。我后来细读了一遍,觉得除了二者都以两对夫妇的婚姻不如意为题材外,几乎没有雷同的地方。 ——宋淇《私语张爱玲》
《半生缘》对《十八春》的改写,凸显了张爱玲新的艺术构思,是张爱玲式“倾城之恋美学”的灿烂重现,虽与《十八春》同源共根,结出的却是不同的更为艳异的果实。 ——陈子善
张爱玲受到通俗小说的影响很大,但《半生缘》却把通俗小说升华到了高雅深沉的程序。 ——止庵
年岁渐长渐体会,这《半生缘》, 恐怕更是你、我今生同样难解之缘。 ──李昂
缘只半生,都成了前尘往事。就从那个“我们都回不去了”的地方,开始了张爱玲不朽的文学世界! ──南方朔
《半生缘》脱去张腔一贯的辛辣嘲讽,转而变得温柔、多情且善良,真正道出了人世间的无可奈何。苍凉惆怅之余,又透出一股平和的理解与宽容。 ──郝誉翔
我始终觉得,“我们都回不去了”是张爱玲在心底对胡兰成说的话。被绑架囚禁于黑屋的不是曼桢,而是张爱玲的余生。 ──张瑞芬
半生的缘份,注定一世的沧桑。这世间男女,这爱恨交错,在张爱玲冷澈透骨的笔锋之下,无所遁形。 ──彭树君
这是一部普通人的爱情故事。唯因为普通,所以靠近。因为靠近,所以知道那些得到中的疏远,重逢里的永别,都是真实。 ──杨佳娴
《半生缘》是我二十岁左右启蒙我极深的一本小说,当时读完只觉得天摇地动,“世界的光度变得不一样了”。 ──骆以军
世界上有华人华文的地方,就有人谈论张爱玲。 ——陈克华
张爱玲的写作风格独树一格,不仅是富丽堂皇,更是充满了丰富的意象。 ——白先勇
许多人是时间愈久,愈被遗忘,张爱玲则是愈来愈被记得。 ——南方朔
她称得上“活过”“写过”“爱过”。 ——木心
张爱玲以诅咒的方式让一个世代随她一起死去。像一个大上海的幽魂,活在许多爱她的人的心中,她是那死去的蝴蝶,仍然一来再来,在每朵花中寻找它自己。仿佛因为她的死,月光都像魂魄了。 ——蒋勋
与张爱玲同活在一个世上,也是幸运,有她的书读,这就够了。 ——贾平凹
她有足够的情感能力去抵达深刻,可她没有勇敢承受这种能力所获得的结果,这结果太沉重,她是很知道这分量的。于是她便觉攫住自己,束缚在一些生活的可爱的细节,拼命去吸吮它的实在之处,以免自己再滑到虚无的边缘。 ——王安忆
她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们一样,或是觉得张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天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痴心人在白白地等待她的下一部小说。 ——叶兆言
五四以来,以数量有限的作品,而能赢得读者持续支持的中国作家,除鲁迅外,只有张爱玲。 ——王德威
她的时代感是敏锐的,敏锐得甚至觉得时代会比个人的生命更短促。 ——杨照
我读张爱玲的作品,就像听我喜欢的音乐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交响乐,而是民谣流派,可以不断流传下去的。 ——苏童
时间过去,运动过去,再看张爱玲,必须认可她的优越性。 ——李渝
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海风韵犹存。 ——余秋雨
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 ——李昂
谁说张爱玲是避世的呢?她难道不是一直藉作品对读者推心置腹吗?那么,我们又怎么能说斯人已逝?在生活中、在作品中、在文学史中,我们注定还会时时遇到她,谈到她—张爱玲。 ——艾晓明
女人大都不珍惜自己的才华,以男人的喜好为喜好,以男人的价值为价值,张爱玲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她顽强地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处处有她的“此在”。 ——刘川鄂
精彩书摘
第一章 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象是指顾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彷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 曼桢曾经问过他,他是什么时候起开始喜欢她的。他当然回答说“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说那个话的时候是在那样的一种心醉的情形下,简直什么都可以相信,自己当然绝对相信那不是谎话。其实他到底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见她的,根本就记不清楚了。 是叔惠先认识她的。叔惠是他最要好的同学,他们俩同是学工程的,叔惠先毕了业出来就事,等他毕了业,叔惠又把他介绍到同一个厂里来实习。曼桢也在这爿厂里做事,她的写字台就在叔惠隔壁,世钧好两次跑去找叔惠,总该看见她的,可是并没有印象。大概也是因为他那时候刚离开学校不久,见到女人总有点拘束,觉得不便多看。 他在厂里做实习工程师,整天在机器间里跟工人一同工作,才做熟了,就又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去了。那生活是很苦,但是那经验却是花钱买不到的。薪水是少到极点,好在他家里也不靠他养家。他的家不在上海,他就住在叔惠家里。 他这还是第一次在外面过阴历年。过去他对于过年这件事并没有多少好感,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家里例必有一些不痛快的事情。家里等着父亲回来祭祖宗吃团圆饭,小公馆里偏偏故意地扣留不放。母亲平常对于这些本来不大计较的,大除夕这一天却是例外。她说“一家人总得像个人家”,做主人的看在祖宗份上,也应当准时回家,主持一切。 事实上是那边也照样有祭祖这一个节目,因为父亲这一个姨太太跟了他年份也不少了,生男育女,人丁比这边还要兴旺些。父亲是长年驻跸在那边的。难得回家一次,母亲也对他客客气气的。惟有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大约也因为这种时候她不免有一种身世之感,她常常忍不住要和他吵闹。这么大年纪的人了,也还是哭哭啼啼的。每年是这个情形,世钧从小看到现在。今年倒好,不在家里过年,少掉许多烦恼。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了急景凋年的时候,许多人家提早吃年夜饭,到处听见那落落的爆竹声,一种莫名的哀愁便压迫着他的心。 除夕那一天,世钧在叔惠家里吃过年夜饭,就请叔惠出去看电影,连看了两场──那一天午夜也有一场电影。在除夕的午夜看那样一出戏,彷佛有一种特殊的情味似的,热闹之中稍带一点凄凉。 他们厂里只放三天假,他们中午常去吃饭的那个小馆子要过了年初五才开门。初四那天他们一同去吃饭,扑了个空,只得又往回走。街上满地都是掼炮的小红纸屑。走过一家饭铺子,倒是开着门,叔惠道:“就在这儿吃了吧。”这地方大概也要等到接过财神方才正式营业,今天还是半开门性质,上着一半排门,走进去黑洞洞的。新年里面,也没有什么生意,一进门的一张桌子,却有一个少女朝外坐着,穿著件淡灰色的旧羊皮大衣,她面前只有一副杯箸,饭菜还没有拿上来,她彷佛等得很无聊似的,手上戴着红绒线手套,便顺着手指缓缓地往下抹着,一直抹到手丫里,两只手指夹住一只,只管轮流地抹着。叔惠一看见她便咦了一声道:“顾小姐,你也在这儿!”说着,就预备坐到她桌子上去,一回头看见世钧彷佛有点踌躇不前的样子,便道:“都是同事,见过的吧?这是沉世钧,这是顾曼桢。”她是圆圆的脸,圆中见方──也不是方,只是有轮廓就是了。蓬松的头发,很随便地披在肩上。世钧判断一个女人的容貌以及体态衣着,本来是没有分析性的,他只是笼统地觉得她很好。她的两只手抄在大衣袋里,微笑着向他点了个头。当下他和叔惠拖开长凳坐下,那朱漆长凳上面腻着一层黑油,世钧本来在机器间里弄得浑身稀脏的,他当然无所谓,叔惠是西装笔挺,坐下之前不由得向那张长凳多看了两眼。 这时候那跑堂的也过来了,手指缝里夹着两只茶杯,放在桌上。叔惠看在眼里,又连连皱眉,道:“这地方不行,实在太脏了!”跑堂的给他们斟上两杯茶,他们每人叫了一客客饭。叔惠忽然想起来,又道:“喂,给拿两张纸来擦擦筷子!”那跑堂的已经去远了,没有听见。曼桢便道:“就在茶杯里涮一涮吧,这茶我想你们也不见得要吃的。”说着,就把他面前那双筷子取过来,在茶杯里面洗了一洗,拿起来甩了甩,把水洒干了,然后替他架在茶杯上面,顺手又把世钧那双筷子也拿了过来,世钧忙欠身笑道:“我自己来,我自己来!”等她洗好了,他伸手接过去,又说“谢谢。”曼桢始终低着眼皮,也不朝人看着,只是含着微笑。世钧把筷子接了过来,依旧搁在桌上。搁下之后,忽然一个转念,桌上这样油腻腻的,这一搁下,这双筷子算是白洗了,我这样子好象满不在乎似的,人家给我洗筷子倒彷佛是多事了,反而使她自己觉得她是殷勤过分了。他这样一想,赶紧又把筷子拿起来,也学她的样子端端正正架在茶杯上面,而且很小心的把两只筷子头比齐了。其实筷子要是沾脏了也已经脏了,这不是掩人耳目的事么?他无缘无故地竟觉得有些难为情起来,因搭讪着把汤匙也在茶杯里淘了一淘。这时候堂倌正在上菜,有一碗蛤蜊汤,世钧舀了一匙子喝着,便笑道:“过年吃蛤蜊,大概也算是一个好口彩──算是元宝。”叔惠道:“蛤蜊也是元宝,芋艿也是元宝,饺子蛋饺都是元宝,连青果同茶叶蛋都算是元宝──我说我们中国人真是财迷心窍,眼睛里看出来,什么东西都像元宝。”曼桢笑道:“你不知道,还有呢,有一种'蓑衣虫',是一种毛毛虫,常常从屋顶掉下来的,北方人管牠叫'钱串子'。也真是想钱想疯了!”世钧笑道:“顾小姐是北方人?”曼桢笑着摇摇头,道:“我母亲是北方人。”世钧道:“那你也是半个北方人了。”叔惠道:“我们常去的那个小馆子倒是个北方馆子,就在对过那边,你去过没有?倒还不错。”曼桢道:“我没去过。”叔惠道:“明天我们一块儿去,这地方实在不行。太脏了!” 从这一天起,他们总是三个人在一起吃饭;三个人吃客饭,凑起来有三菜一汤,吃起来也不那么单调。大家熟到一个地步,站在街上吃烘山芋当一餐的时候也有。不过熟虽熟,他们的谈话也只限于叔惠和曼桢两人谈些办公室里的事情。叔惠和她的交谊彷佛也是只限于办公时间内。出了办公室,叔惠不但没有去找过她,连提都不大提起她的名字。有一次,他和世钧谈起厂里的人事纠纷,世钧道:“你还算运气的,至少你们房间里两个人还合得来。“叔惠只是不介意地“唔“”了一声,说:“曼桢这个人不错。很直爽的。”世钧没有再往下说,不然,倒好象他是对曼桢发生了兴趣似的,待会儿倒给叔惠俏皮两句。 还有一次,叔惠在闲谈中忽然说起:“曼桢今天跟我讲到你。”世钧倒呆了一呆,过了一会方才笑道:“讲我什么呢?”叔惠笑道:“她说怎么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只有我一个人说话的份儿。我告诉她,人家都说我欺负你,连我自己母亲都替你打抱不平。其实那不过是个性关系,你刚巧是那种唱滑稽的充下手的人材。”世钧笑道:“充下手的怎么样?”叔惠道:“不怎么样,不过常常给人用扇子骨在他头上敲一下。”说到这里,他自己呵呵地笑起来了。又道:“我知道你倒是真不介意的。这是你的好处。我这一点也跟你一样,人家尽管拿我开心好了,我并不是那种只许他取笑人,不许人取笑他的。……”叔惠反正一说到他自己就没有完了。大概一个聪明而又漂亮的人,总不免有几分“自我恋”吧。他只管滔滔不绝地分析他自己个性中的复杂之点,世钧坐在一边,心里还在那里想着,曼桢是怎样讲起他来着。 他们这个厂坐落在郊区,附近虽然也有几条破烂的街道,走不了几步路就是田野了。春天到了,野外已经蒙蒙地有了一层绿意,天气可还是一样的冷。这一天,世钧中午下了班,照例匆匆洗了洗手,就到总办公处来找叔惠。叔惠恰巧不在房里,只有曼桢一个人坐在写字台前面整理文件。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 世钧笑道:“叔惠呢?”曼桢向经理室微微偏了偏头,低声道:“总喜欢等到下班之前五分钟,忽然把你叫去,有一样什么要紧公事交代给你。做上司的恐怕都是这个脾气。”世钧笑着点点头。他倚在叔惠的写字台上,无聊地伸手翻着墙上挂的日历,道:“我看看什么时候立春。”曼桢道:“早已立过春了。”世钧道:“那怎么还这样冷?”他仍旧一张张地掀着日历,道:“现在印的日历都比较省俭了,只有礼拜天是红颜色的。我倒喜欢我们小时候的日历,礼拜天是红的,礼拜六是绿的。一撕撕到礼拜六,看见那碧绿的字,心里真高兴。”曼桢笑道:“是这样的,在学校里的时候,礼拜六比礼拜天还要高兴。礼拜天虽然是红颜色的,已经有点夕阳无限好了。”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说实话,一开始有点担心篇幅会让人望而却步,但一旦翻开,便完全停不下来。作者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佳,张弛有度。它没有那种刻意制造的戏剧冲突,一切矛盾的爆发都源于人物自身的性格和环境的必然,显得非常真实可信。书中对于情感的描绘非常克制,却又极其有力,很多时候,人物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所表达的情感比大段的独白更为震撼。这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文学手法,体现了作者极高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读罢,心中涌起的不是简单的感动,而是一种对世事无常的深深共鸣。
评分这部作品简直是一部关于人性和命运的史诗,文字功力深厚,每一个场景都仿佛能让人身临其境。作者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入木三分,那些纠葛的情感、难以言喻的挣扎,读起来让人不禁为之动容。我尤其欣赏它那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不急不躁,却能将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时代背景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故事中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让整个故事充满了温度和厚重感,让人在为书中人物的悲欢离合唏嘘不已的同时,也能从中体悟到一些人生的哲理。读完之后,那种挥之不去的余韵,久久不能散去,感觉自己仿佛也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深刻的人生旅程。
评分这部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的“真”。它毫不避讳地展现了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不完美。书中没有绝对的英雄或恶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处境下做着艰难的抉择。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使得书中的人物形象立体饱满,让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每一份挣扎与坚持。叙事视角时不时地在不同人物间切换,让读者能从多维度的角度去审视同一个事件,极大地丰富了阅读体验。我为其中一些人物最终的宿命感到惋惜,但同时也明白,这正是生活本来的面貌,带着一丝苦涩,却又无比坦荡。
评分初读此书,便被其行文的典雅和韵味所吸引。语言的运用简直是炉火纯青,既有古典文学的含蓄美,又不失现代叙事的流畅性。情节的推进如同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每一个转折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书中对社会风貌的描摹细致入微,仿佛能闻到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像是一幅描绘特定时代群像的工笔画,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我特别喜欢作者对白的处理,那种不动声色的机锋和深藏的无奈,读起来韵味无穷,让人忍不住要反复咀嚼。
评分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细品的佳作。它的文字密度很高,信息量丰富,初读可能会觉得有些沉重,但只要坚持下去,便会发现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作者构建了一个宏大而又精微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里,大时代的洪流如何裹挟了个人的命运,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欣赏作者在描绘日常琐碎时所流露出的那种对生活的细腻观察,正是这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最终汇聚成了磅礴的情感力量。读完后,我感觉自己的心境似乎也沉淀了不少,对“缘分”和“了断”有了全新的认识。
评分共买啦三本,还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围城,昨晚先看啦围城,实在是太好看啦,看到12点才睡觉……看完再买……
评分正版很好很快京东最棒,
评分很喜欢,虽然还没有拆开,但是感觉不错
评分《西西弗神话》是加缪的代表作之一,文中收集了加缪对于荒诞哲理最深入、最透彻的考察与分析。《反与正》由五篇散文构成,记录了加缪对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切身感受和哲理思考,内容多取材于作者自己的生活和家人。《婚礼集》由四篇文章组成,记录了作者在阿尔及利亚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中所体味到的生活乐趣。《反抗者》全面阐释加缪反抗思想的理论力作。在书中,加缪提出“我反抗故我在”的论断,其体现出来的精神和勇气,足以与《西西弗神话》前后辉映,足以为加缪“在荒诞中奋起反抗”的一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评分东东不错,正版图书,快递小哥很给力,下次还会光顾。
评分包装完整,没有破损,这次活动力度够大,一下收了好多,都很满意!
评分家有金毛一只,狗龄一岁,朋友寄养,只能在我家待一个多月。总结金毛的特点:智商高:听得懂不少话,并且很快明白家里几个人的名字服从性好:坐下 停 握手 跳 不准吃/吃 能100%执行
评分非常感谢京东商城给予的优质的服务,从仓储管理、物流配送等各方面都是做的非常好的。送货及时,配送员也非常的热情,有时候不方便收件的时候,也安排时间另行配送。同时京东商城在售后管理上也非常好的,以解客户忧患,排除万难。给予我们非常好的购物体验。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e excellent service provided by Jingdong mall, and it is very good to do in warehouse management, logistics, distribution and so on. Delivery in a timely manner, distribution staff is also very enthusiastic, and sometimes inconvenient to receive the time, but also arranged for time to be delivered.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mall management Jingdong cust
评分书收到了厚厚的一摞,仿佛就是寄托自己的精神食粮。希望可以很认真很用心的拜读下去,置身于书的世界去汲取书中的价值和营养。很有幸很开心!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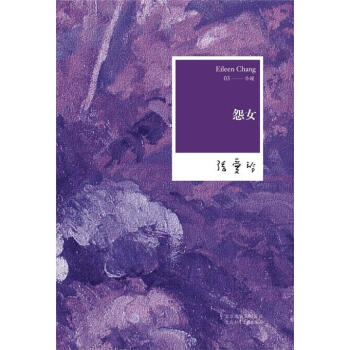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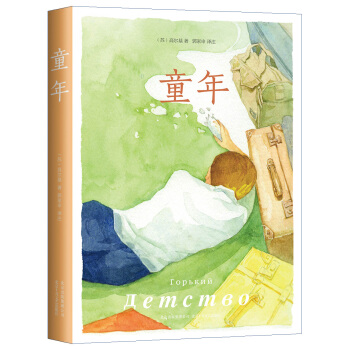


![世界上的另一个你(修订版) [Same Kind of Different as M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45072/59ad0579N97be17e2.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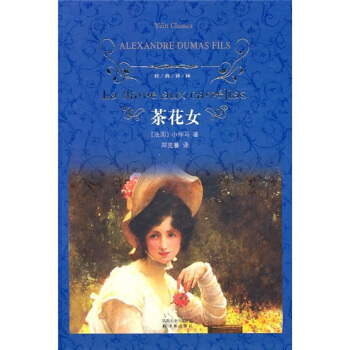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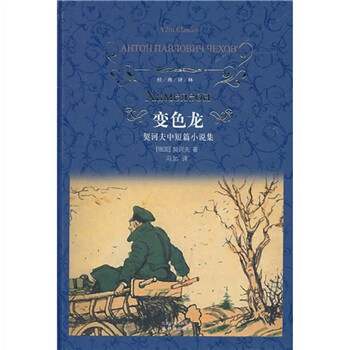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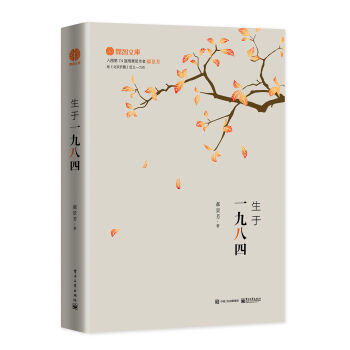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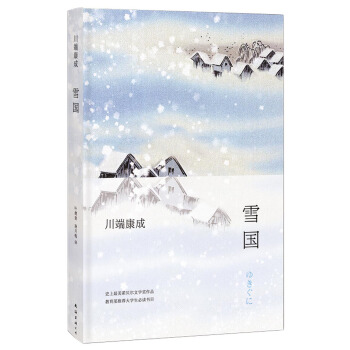


![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2014版) [伊豆の踊子]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498857/53bdfce5N13000ab1.jpg)
![川端康成:阵雨中的车站 [掌の小説]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77584/5464143dN5f77fb7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