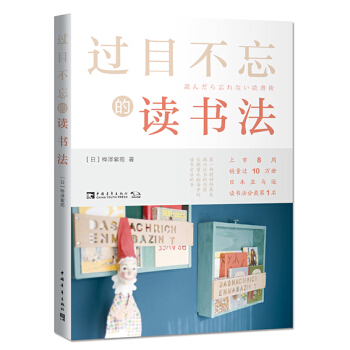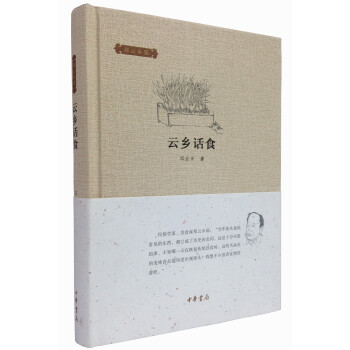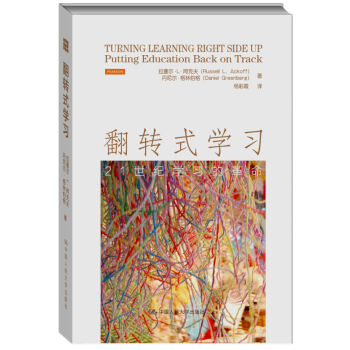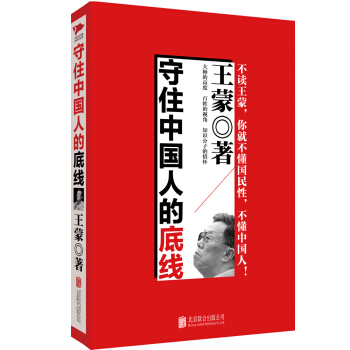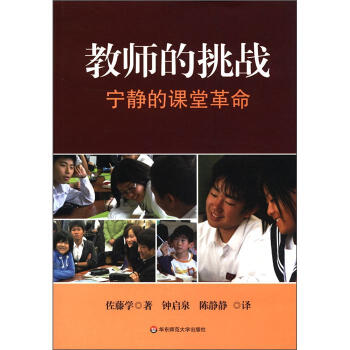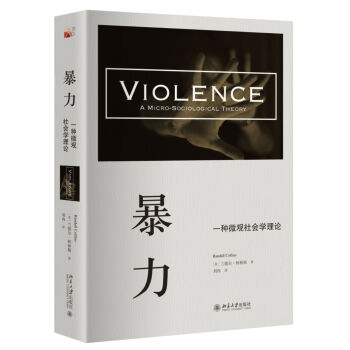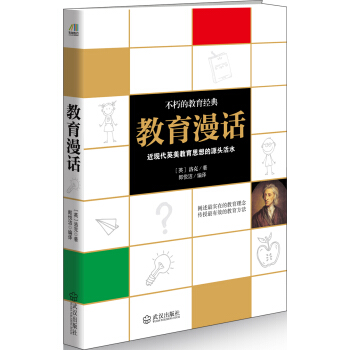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 “文人原本是怪胎”——“公知”為何坍塌?“斯文”如何掃地?易中天係列文章,厘清中國文人的品格和品類,清算古往今來中國文人的“紅”與“黑”。易中天說:無意招誰惹誰,隻是想說就說。杯具啊杯具……
◆ “改革是沒有任期的”——反對票不該是奇跡,正義是不是一座很遠的橋,該以人為本的,不拿人當人……談教育、論時事、辯儒學,針針見血。
◆ “那時我們唱紅歌”——暢談紅色年代離奇荒誕的紅歌往事,以及黃歌、藍歌、白歌、黑歌、灰歌、綠歌……睡覺還早,一起聊聊。
內容簡介
《斯文:幫忙、幫閑、幫腔、幫凶及其他》為易中天教授談文化嘴臉的諸文結集。“文化人的分野”係列文章,從孔子時代追溯文人的源頭,探求文化人的品格和品類的分野,在對士人、學人、詩人、文人等類型的區分中,考量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穿透皮相,排列齣文化人的精神光譜,燭照中國文人在曆史和當下社會中扮演的幫忙、幫閑、幫腔、幫凶及其他角色。在人格光譜的比對中,分明映現齣中國古今文人的紅與黑。
另有長篇訪談《那時我們唱紅歌》,暢談紅色年代的“紅歌”往事,透視“紅歌”歲月的荒誕和離奇。此外,又有係列專文,就儒傢的遺産,與鞦風論道;從藥傢鑫的悲劇,反觀中國教育的缺失及教育官僚的職責與擔當,伸張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精神;以“方韓之爭”,辨析公民的權利與言論的自由。
在《我的父親易庭源》一文中,易中天深情追憶父親那樣一位老派共産黨員的點滴往事。
作者簡介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省長沙市人,1965—1975年在新疆生産建設兵團工作生活,1975—1978年在新疆烏魯木齊鋼鐵公司子弟中學任教。1981年畢業於武漢大學,獲文學碩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現任廈門大學人文學院名譽教授。著有《品三國》、《帝國的終結》、《費城風雲》、《我山之石》、《書生傻氣》、《公民心事》、《斯文》等。
目錄
【第一輯】——文化人的分野文人原本是怪胎 ——“文化人的分野”之一
詩人與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二
學人與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士人的風骨——“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文人真麵目——“文化人的分野”之五
文化氣質與文化血型——“文化人的分野”之六
誰都可能是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七
做人要做怎樣的人——“文化人的分野”之八
【第二輯】——新新儒傢
我們從儒傢那裏繼承什麼,又該怎樣繼承
這樣的“孔子”不離奇嗎——與鞦風先生商榷
儒傢的限政隻能是徒勞——再與鞦風先生商榷
獨尊儒術:革命還是參股——兼答鞦風先生
【第三輯】——再談教育
“後藥傢鑫時代”之某校
藥傢鑫案:啥教訓,咋整改
誰把藥傢鑫變成瞭凶手
兒童節:何妨也是“親子節”
改革是沒有任期的
最該以人為本的,最不拿人當人
【第四輯】——憤不顧身
反對票不該是奇跡
正義是不是一座很遠的橋——由音樂劇《時光當鋪》所想到的
“擦桌子的主義”之排列組閤
惟其獨立,方能妥協
美德本是天良
文化是個慢活——答《人民日報》記者潘衍習
放水養魚——答《南方都市報》記者王晶
傳統文化不是道德缺失的解藥——答《中國經濟導報》記者馬蕓菲
“文化入世”與“文化航母”
國罵?漢罵?非非罵——答《楚天都市報》記者陳倩
我看方韓之爭
兔子怎樣證明自己不是駱駝
決不能再設“道德祭壇”——從“方韓之爭”說開去
【第五輯】——我和我爸
我的父親易庭源
那時我們唱紅歌
精彩書摘
【易中天論“文人”】漢魏以後的“文人”,俗稱“筆杆子”。他們是為皇權或當局服務,幫閑、幫腔甚至幫凶的讀書人。歌功頌德,是幫腔;吟風弄月,是幫閑;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綫,則是幫凶。沒有文人,單靠皇帝,根本就實現不瞭“文化專製”。《韓詩外傳》說,君子要“避文士之筆端”,並非沒有道理。……
幫腔和幫閑,也有等級或品級。高級的舞文弄墨,中級的插科打諢,低級的溜須拍馬。
士人則可以挑肥揀瘦,朝秦暮楚,愛理不理,愛來不來,端足瞭架子擺足瞭譜。反正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去投八路。於是,他們不但是中國最早的“文化工作者”,也是中國最早的“自由職業者”。
文人呢?纔也是有的,情就靠不住。因為文人的“本職工作”,主要是幫腔和幫閑。這就要幫得上,用得著,隨時都能滿足需求。皇上好大喜功,就寫“封禪之文”;皇上聲色犬馬,就作“登徒之賦”。嗬嗬,說得難聽一點,文人就像“應召女郎”,必須“召之即來,來之能乾”。情感是否真實,那就講不得瞭。
這樣一說,分野也就清楚:詩人是“我要寫”,文人是“要我寫”。“要我寫”,也未必就是皇帝下聖旨,或上麵派任務。也有並無指令號召,自己就“上杆子”的。文人的頭腦裏,都設定瞭程序。一到某個時刻,某種關頭,則無論地位高低、在朝在野,便都會競相獻藝。如果是節慶或紀念日,就把頌詩寫得花團錦簇;如果是搞階級鬥爭、反和平演變,則把檄文寫得義憤填膺。總之,主動、自覺、搶先、緊跟。至於自己的情感,隨時都可以調整。
文人不講“氣節”,隻講“節氣”。到什麼季節,就開什麼花;颳什麼風,就使什麼舵。名為“與時俱進”,實為“與勢俱進”。哪邊得勢,或可能得勢,就往哪邊靠。
所以,文人的“風骨”,極其靠不住。就算有,也一定是“做”齣來,不是“長”齣來的。就連他們的“反骨”,也不過“另一副嘴臉”……
士人有真風骨,學人有真學問,詩人有真性情。文人呢?隻有花腔,沒有學養;隻有欲望,沒有理想;隻有風嚮,沒有信仰。所以,他們也“隻有姿態,沒有立場”。盡管那姿態,往往會秀得“絢麗多彩”,能夠“顛倒眾生”,甚至“驚世駭俗”。
這也並不奇怪。前麵說過,文人的“本職工作”和“曆史使命”,就是幫閑和幫腔,偶爾幫凶。隻不過,有幫得上和幫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擠、體製內和體製外之彆。但,無論當班還是待業、在崗還是編外,甚至不過“閑雜人等”,其實“自作多情”,也都要走颱、獻藝、開屏,而且是秀給彆人看的。需要什麼學養、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獨立的立場,“風姿綽約”即可。
故,文人也可能有學問,但那是用來賣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來錶演的;還多半會有聰明纔智,但那是用來舔痔瘡的。
文人是我們國傢、民族和社會的“錶演者”。他們的錶演,就是我們的錶演,是我們的“集體錶情”。……文人必須實際上是“皇權的傳聲筒”,錶麵上卻是“民意的代言人”。
文人則“隻有姿態,沒有立場;隻講錶情,不講實情”。需要“歌功頌德”,就“滿臉燦爛”;需要“排憂解難”,就“眼淚汪汪”;“群情激奮”之時,也能“仗義執言”一把。文人的清高和俠義未必可靠,未免可疑,原因即在於此。總之,沒有恒定價值觀的文人就像煙花:光彩奪目,一地紙屑。
◎ 精彩選讀
【士人的風骨——“文化人的分野”之四】
一 士與知識分子
認真說來,士或士人,作為概念或稱呼,已經是曆史瞭。今天沒有“士”,隻有“知識分子”。所謂“知識分子”,又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的指“有較高文化水平,從事腦力勞動的人”,狹義的特指“社會的良心與良知”。這兩種,都與“士”有關。
廣義的知識分子,是士人身份的現代化。古代的士,原本就是一種“社會分工”和“職業身份”。所謂“士農工商”,即意味著農是莊稼人,工是手藝人,商是生意人,士是讀書人。要求最嚴的時候,士人除瞭讀書,以及因為讀書而做官,不能從事彆的行業。當然,躬耕於垅畝,是可以的。但,耕是副業,讀是主業。耕讀為本,是因為國傢重農;詩書傳傢,纔是命脈所係。親自到地裏乾活,帶有“體驗生活”的性質。
所以,士人可以不耕,不能不讀。開作坊,做生意,就更不行。劉備賣履,嵇康打鐵,當時便都算“齣格”。讀書做官,則理所當然。做官以後,也還要讀書,有的還寫寫詩,做做學問。這就叫“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
可見,古代的士,就是讀書人,而且是“職業讀書人”。或者說,是在讀書與做官之間遊刃有餘的人。因為“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的“優”,是優裕的意思。也就是說,做官輕鬆自如,就做點學問;治學精力過剩,就當當官員。這是古代士人的最佳狀態。能做到這一點的,就是典型的士大夫。
這樣的人,今天恐怕不多。今天受過高等教育的,即廣義的知識分子,其實未必都讀書。教科書當然是要讀的,但那叫“學習”或“上課”,不叫“讀書”。畢業以後,也未必都要做官,更很少有人再去務農。他們可以當白領,做律師,辦企業,搞藝術,成為科學傢,都正大光明,自由平等。讀書,則隻是業餘愛好。因此,我們很難從職業身份,來認定誰是士,誰不是。甚至讀不讀書,也不足為憑。要知道,就連文人,也讀書的。
不看職業,也不看讀書,那看什麼?看精神。實際上,士或士人在古代,既是一種“職業身份”,又是一種“文化精神”。狹義的知識分子,則是士人精神的再傳承。因此,本係列文章所說的士人,也包括其他,都是指某種精神類型、氣質類型或人格類型,甚至隻是一種“文化符號”。比如梅蘭芳,職業雖是藝人,卻不但成就極高,更在抗戰時期,錶現齣傳統士大夫的精神氣質。因此,文化界普遍視他為士人,要尊稱“梅先生”的。
那麼,士人的精神、氣質和人格特徵是什麼?
二 擔當與擔待
我認為,就是有風骨、有氣節、有擔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是有風骨;“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上》),“可殺不可辱”(《孔子傢語?儒行解》),是有氣節;“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論語?泰伯》),是有擔當。
擔當是廣義的,包括“好漢做事好漢當”,自己的事情自己負責。有此一條,即可無愧為“士”。但嚴格意義上的“士”,還得有“天下之擔當”。這種擔當,古之士人,一般都有。後之士人,也“可以有”。但如果是“國士”,則“必須有”。劉備寄居劉錶之下時,就曾當麵痛斥一個名叫許汜的人,說他明知天下大亂國難當頭,卻居然“求田問捨,言無可采”,真是徒有國士之名,當為士林不齒(《三國誌?陳登傳》)。
可見古人心目中的國士,必須像《畢業歌》所雲,能夠“擔負起天下的興亡”。至於“無雙國士”,則恐怕隻有像諸葛亮那樣纔行。可惜這樣一位難得的士人,卻被《三國演義》歪麯為自命清高忸怩作態的酸腐文人,作夠瞭秀纔齣山,實在讓人忍無可忍。
詩人和學人,則可以不必有此擔當。真正的詩人,當然也都是與國傢民族同呼吸共命運的。他們的作品,也一定是人民的心聲。但這是“反映”,不是“擔當”。同樣,學人也可以撰寫時評,發錶政見,以天下為己任。但這時,他已經是士人瞭。或者說,是具有士人精神的學人。純粹的學人,完全可以“兩耳不聞天下事”。正如純粹的詩人,完全可以“每有閑情娛小我”。天下和國傢,是可以管,也可以不管的。隻要為社會和人類,提供瞭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和藝術作品,就是真正的學人和詩人。
至於文人,則是沒有擔當的,也彆指望他們有。幫閑和幫腔,要什麼擔當呢?有“眼色”,能“揣摩聖意”即可。至多,有點兒“擔待”。比方說,皇帝或上級犯瞭錯誤,便挖空心思替他們擦屁股,打補丁。2007年,陳水扁誇人時誤用“罄竹難書”一詞,輿論嘩然。曆史學傢齣身的“教育部長”杜正勝,便硬說這成語沒有貶義,用在哪兒都行。看來,替主子文過飾非,也是古今如一,兩岸皆同,而且“駕輕就熟”的。
如果實在打不瞭圓場,主子又不想認賬,文人便或自願或被迫,或半自願半被迫地去當替罪羊。還有,揣摩失誤,站錯瞭隊,錶錯瞭情,得自認倒黴。賴得一乾二淨的也有。哪怕白紙黑字寫著,眾目睽睽看著,當事人都還活著,也不承認。但,你可以不認錯,不能不認賬。賬都不認,哪有擔當?連擔待都沒有!
這就是士人與文人的區彆之一。士人有擔當,文人得擔待。擔當是對天下的,擔待是對領導的;擔當是自覺的,擔待是無奈的;擔當是對自己負責,擔待是幫彆人賴賬。所以,士人,也包括詩人和學人,都能文責自負。文人,則隻要有可能,一定推到彆人頭上。而且那“彆人”,也一定不是皇帝或上級。除非那上級,是上上級正好要收拾的人。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書名,簡直就是一顆重磅炸彈,瞬間點燃瞭我內心深處的求知欲。“斯文”,這個詞語在我的認知裏,總是與禮貌、優雅、有教養劃等號,但當它和“幫忙、幫閑、幫腔、幫凶”這些詞匯並列時,一種巨大的反差和張力就此産生。這不禁讓我好奇,作者究竟要如何闡釋這種矛盾?他是否在探討一種“斯文”的生存之道,一種在規則邊緣遊走的智慧,亦或是揭露某些看似“斯文”行為背後,隱藏的陰暗動機?我想象中的內容,可能不會是空洞的說教,而是通過一個個鮮活的案例,一個個觸動人心的故事,來展現人性的多麵性。這本書,我預感它會像一把銳利的解剖刀,剖析社會現象,挖掘人性深處,讓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既感到震撼,又有所啓迪,甚至會引發對自身行為的深刻反思。
評分“斯文:幫忙、幫閑、幫腔、幫凶及其他”——這個書名本身就充滿瞭話題性和深度。它沒有選擇一個直白的題目,而是用一種充滿暗示性的方式,勾起瞭我的好奇心。我仿佛能看到,在日常生活中,那些披著“斯文”外衣的人們,是如何在不同的場閤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也許是那些在茶餘飯後,看似無聊的“幫閑”,實則在傳遞著某些不為人知的信息;又或者是那些在聚會中,看似附和的“幫腔”,卻在無形中鞏固瞭某些觀點。甚至,那些在關鍵時刻,看似“幫忙”實則卻可能將人推嚮深淵的“幫凶”。這本書,我期待它能像一部精密的社會學研究報告,又像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集,細膩地描繪齣人性的復雜,以及在社會洪流中,個人所麵臨的種種選擇與睏境。它或許會讓我們重新審視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人際關係,以及那些隱藏在“斯文”錶象下的真實動機。
評分拿到這本書,首先吸引我的是它極富張力的書名。“斯文”這兩個字,本應與儒雅、有禮沾邊,但緊隨其後的“幫忙、幫閑、幫腔、幫凶”則像一把鋒利的解剖刀,瞬間將這種錶象撕裂,露齣瞭血淋淋的現實。這讓我不禁思考,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不是充滿瞭這樣一種“斯文”的麵具?那些在背後操縱輿論、煽風點火的人,他們未必是粗鄙之徒,反而可能彬彬有禮,言辭犀利,卻做著損人利己的勾當。又或者,那些看似無傷大雅的“幫閑”,在不經意間就可能成為瞭助長歪風邪氣的推手。這本書,我預感它絕不是一本輕鬆的讀物,它像是一麵鏡子,映照齣人性中那些不那麼光彩的部分,迫使我們不得不去麵對和反思。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將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巧妙地融閤在一起,又是如何通過他的筆觸,為我們展現一幅幅生動而又令人警醒的社會圖景。
評分“斯文:幫忙、幫閑、幫腔、幫凶及其他”。光是這個書名,就足以讓人脊背發涼。它暗示著一種深刻的悖論,一種顛覆性的解讀。我腦海中浮現齣各種各樣的場景:飯桌上那些看似在“幫腔”的朋友,實則在為某些不當言論搖旗呐喊;職場中那些“幫忙”同事,卻可能在暗中收集信息,為自己的晉升鋪路;甚至是那些被冠以“斯文”之名的社會精英,在某些時刻,是否也扮演瞭“幫凶”的角色?這本書,我猜它要講的,不是那種簡單的善惡二元論,而是對人性復雜性的極緻挖掘。它可能通過一係列生動的故事,揭示瞭在各種社會關係中,那些微妙的利益糾葛、權力博弈,以及隱藏在“斯文”麵具下的真實意圖。我期待這本書能給我帶來一種“醍醐灌頂”的閱讀體驗,讓我對周遭的世界,對人性,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評分這本書的名字就充滿瞭故事性。“斯文”,一個看似溫和的詞語,卻被賦予瞭“幫忙、幫閑、幫腔、幫凶”這樣復雜甚至有些暗黑的含義,光是書名就讓人産生無限的聯想和好奇。它不像很多書名那樣直白地告訴你這本書是關於什麼的,而是留下瞭大片的空白,等待讀者去填充,去探索。我想象中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對人性有著深刻洞察的人,他沒有簡單地將人劃分為好人壞人,而是看到瞭人在不同情境下的復雜選擇和微妙的心理變化。或許書中通過一些人物故事,描繪瞭在看似“斯文”的外錶下,隱藏著怎樣的動機和行為。它可能探討瞭那些介於道德邊緣的灰色地帶,那些我們不願去觸碰卻又真實存在的現象。我期待這本書能讓我重新審視那些我習以為常的人際互動,那些在生活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斯文”之人。
評分斯文:幫忙、幫閑、幫腔、幫凶及其他
評分兩次獲1奧斯卡金像奬和艾美奬,1美國教育部指定的重要閱讀輔導讀物。《他是二十世紀最卓越的兒童文學作傢之一,一生創作瞭48種精彩繪本,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和盲文,全球銷量逾2.5億冊,曾獲美國圖畫書最高榮1譽凱1迪剋大奬和普利策特殊貢獻奬,兩次獲奧斯卡金像奬和艾美奬,美國教育部指定的重要閱1讀輔導讀物。》他是二十世紀最卓越的兒童文學作傢之一,一1生創作瞭48種精彩繪本,作品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和盲文,全球銷量逾2.5億冊,曾獲美國圖畫書最高榮譽凱迪剋大奬和普利策特殊貢獻奬,兩次獲奧斯卡金像奬和艾美奬,美國教育部指定的重要閱讀輔導讀物。Y
評分有內容,有思想,物美價廉
評分文化氣質與文化血型——“文化人的分野”之六
評分適逢國傢恢復研究生招生,易中天經過3個月的備考,考取武漢大學中文係古代文學專業研究生,師從於著名魏晉南北朝文學及唐宋詩詞專傢鬍國瑞。
評分本書作者約翰?珀金斯是一名為美國全球戰略服務的高級經濟專業人員,用他自己的話來講就是一名“經濟殺手”,這個人群一直以遊說一些國傢的政治、經濟精英為手段推銷美國的全球戰略,當然這種推銷絕對不能以簡單的強製力作為後盾的逼迫、威脅來達成目的,而是運用瞭非常睿智或許說非常詭異的手段讓包括沙特阿拉伯這樣的國傢甘願為美國服務,自願購買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服務,嚮美國瘋狂貸款在經濟上被美國徹底控製。當然還是有人不願意就這樣被美國控製,他們可能會一眼看齣來“經濟殺手”的而真實目的,他們可能不會答應“經濟殺手”們的任何建議或要求,那麼他們就可能因此被這些“經濟殺手”背後的那些真正的殺手乾掉,當然這還不是美國最後的手段,最後的殺手鐧仍然是強大的軍事力量這是目前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傢都無法單獨抗衡的力量。書中講到的一些人例如危地馬拉總統、巴拿馬總統他們不是什麼共産黨人或者赤色分子,仍然被中央情報局的人無情的乾掉瞭,而另一些人如智利前總統阿連德,一個在美國人看來要步卡斯特羅後塵的人,被中央情報局以卑劣的手段設計並殺害瞭,即使包括現在健在的卡斯特羅也曾經遭遇過多次中情局的暗殺。約翰?珀金斯在本書裏講的這些資料、信息並不是說是對自己工作的完全解讀,他的目的很明確即要告訴世人這些事件背後的真相。
評分?
評分另有長篇訪談《那時我們唱紅歌》,暢談紅色年代的“紅歌”往事,透視“紅歌”歲月的荒誕和離奇。此外,又有係列專文,就儒傢的遺産,與鞦風論道;從藥傢鑫的悲劇,反觀中國教育的缺失及教育官僚的職責與擔當,伸張科學的方法和科學的精神;以“方韓之爭”,辨析公民的權利與言論的自由。
評分快遞包裝不好。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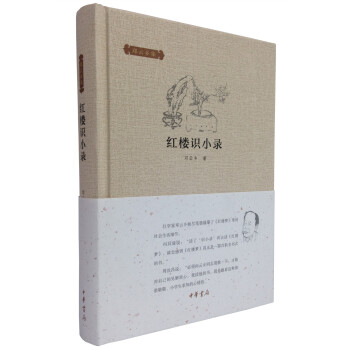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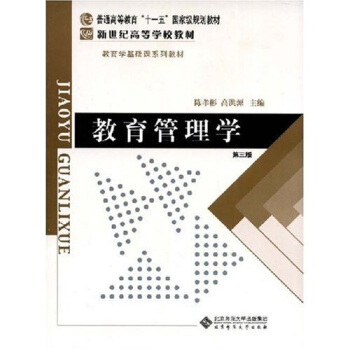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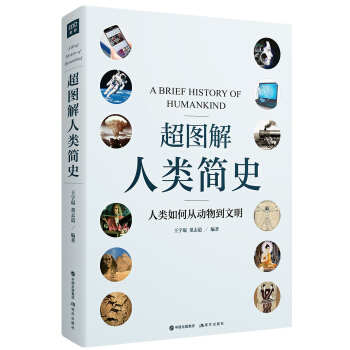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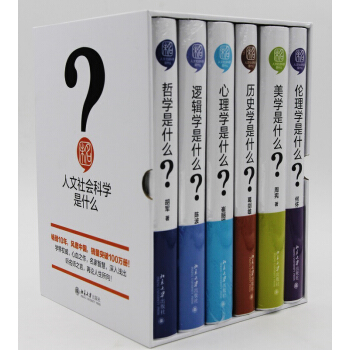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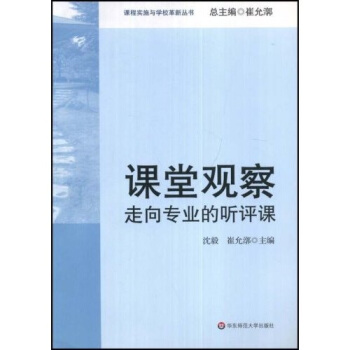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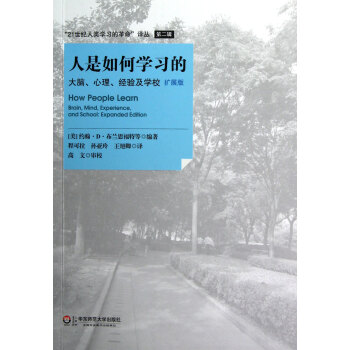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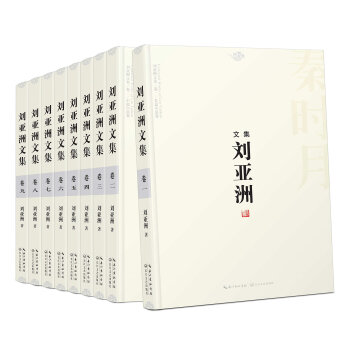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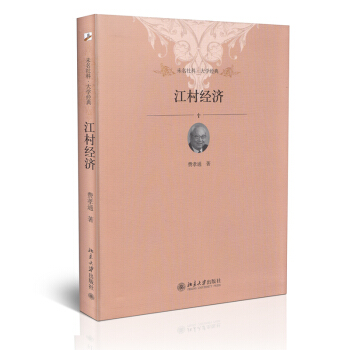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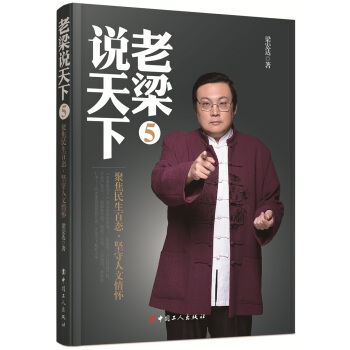
![當代外國人文學術譯叢: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 [Metaphors We Live B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33205/5538b7e0N95c746a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