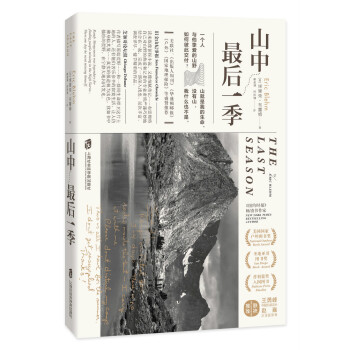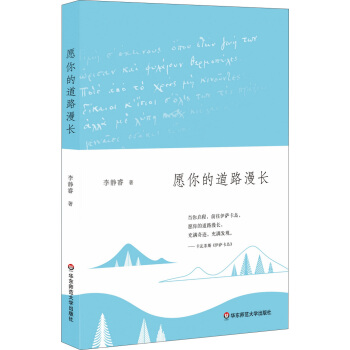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我们都在世界上到处游荡,你别说不是这样。”冯古内特在《没有国家的人》中的这句话,几乎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包括阿花这个年轻人。她从四川出发、到南京读书、广州工作、跳槽到北京、又走到了纽约。在自由的召唤下出发,在时间里前程远大。
作者简介
李静睿,毕业于南京大学,做了八年记者,从广州来到北京,现居纽约,暂时失业,写过一些发表过的专栏和没有出版过的小说。新浪微博是@阿花的伊萨卡岛。目录
每个人的双城记01 不被阅读的城市
02 谁能像梭罗一样生活
03 不要对纽约失望
04 有没有一座城市属于你
05 每个人的双城记
06 人人都到纽约来
07 被神召唤的人是幸福的人
08 配菜人生
09 失败之书
10 过去的房客
11 拥抱
12 碎屑
13 旅行的意义
14 所有的第一场雪
读不完的逝水年华
01 幻觉
02 下水的春天
03 问号
04 中等就好
05 双生花
06 夏天
07 高跟鞋
08 限度
09 时间
10 厨房的故事
11 读不完的逝水年华
12 十年
13 月满轩尼诗
14 钥匙
15 搬家
16 过敏
17 神魂颠倒
18 眼前的世界
故乡的情话
01 红颜
02 李安的师弟
03 灾难时的意乱情迷
04 阿瓦达北京
05 硬盘里的心
06 妹妹的选择
07 抱抱你吧
08 情书
09 挣钱及其所失去的
10 人生排行榜
11 技术型寂寞
12 敌我之间
13 工人妈妈
14 故乡的情话
15 退步的呼唤
16 兰姐和七哥
17 别人的生活
生活的可能性
01 乱纪元
02 最好的时光
03 股票的暗示
04 胸怀天下
05 当我们谈论明年时我们谈论什么
06 康德的理由
07 生活的可能性
08 偶像的黄昏
09 狐狸精的故事
10 酒的声音
11 看不见的城市
12 单身保质期
精彩书摘
不被阅读的城市到纽约那天没有想象中的小雨,走出JFK机场(肯尼迪国际机场)的时候我们满头大汗,推着一辆需要五美元的手推车,第一次看到了这里的蓝天。然后我就每天都看到它,这样无穷无尽的蓝天,就像小时候用过的纯蓝墨水,连白云的点缀都显得多余,无处不在的灰黑色鸽子会在闹市中突然扑腾着飞到这没有终点没有余味的蓝色中去,它们的翅膀下面则是这个说不清楚喧嚣还是孤独的超级城市。
纽约有八百万人,所以劳伦斯·布洛克那本著名的小说名为《八百万种死法》,他试图想象这座城市里每一个人的故事与结局,各种颜色的人们像各种颜色的鸽子一样地扑腾着来了又去,大部分人寂静得没有留下一点痕迹。黄色的我在今年最后的碧蓝夏日里加入了进去。
我在纽约认识的第一个地名是Flushing Meadows(法拉盛草地公园),《纽约客》文风的缔造者E·B·怀特写过,几百年来上面都漂浮着灰色雾气。台湾房东老太太一边开车一边指着那个传说中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地球仪说,这是世博会留下的。那是1964年,战后的美国或者说纽约正如日中天,所以他们有最高的楼和最大的地球仪。而E·B·怀特在这里看到的世博会其实是在1939年,他在《未来的世界》中想象未来的客厅,有“宽幅地毯、人造康乃馨、电视播放机,连续播放别的什么地方什么人或什么事的影像、玻璃鸟、铬钢灯、陶制斑马、几个贴面书柜,装了无形的书、另一个书柜,绵延不断地吐出新闻小报的字条,还有新月状的丝绒小双人椅”。然而除了在《这就是纽约》的开篇那个对911几乎精确的预测,E·B·怀特对未来最笃定的想象大概还是“事事没有商量。你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的确,事事没有商量。无处可逃的烈日。热风袭来的地铁口。曼哈顿里必须用UPTOWN和DOWNTOWN区分的方位。进一次超市不容分说塞给你的七八个塑料袋和纸袋。一包巨大的、感觉可以吃到永生永世的糖。八美元就可以打1000分钟的国际长途,却也有八十美元上门一次的人工,他可能只是给你的门把手拧紧一下螺丝。九美元吃12只大螃蟹,然而包扎一根吃螃蟹时刺伤的手指需要1000美元……统统要么接受,要么拉倒。最没有商量的是,在这烈火烹油般沸腾的城市中,那些若无其事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的,不过都是些孤独的人。
有一天我去了East Harlem,哥大之前在官网首页上介绍了这里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因为奥巴马曾经住在那里,租金3100美元。这个几乎没有白种人的区域让我政治不正确地紧张,何况公交车上永远站着看上去比我更紧张的警察,别着鼓鼓囊囊的枪。我遇到体积庞大的黑人老太太努力地把自己塞进一个公交座位里,漂亮的黑人姑娘把一副真正的手铐戴在耳朵上,梳着不计其数的辫子长得很像乔丹的男青年大声地叫我Hi Sexy……
然而他们此时此刻的轻松被签注在这里,几个街口就是另外一个陌生世界,就像英文再好的华人也要固执地去一团混乱毫无美感的华人聚集区Flushing,固执地把Main Street翻译成缅街,吃那里6.5美元且不用小费的肥肠麻辣烫,肆无忌惮地打着伞以及大声说话。Main Street再往下走又属于印度人,我试图买点布做沙发套的时候千辛万苦找到这里。披着宝蓝色拖地纱丽的店主絮絮叨叨地打着一个漫长的电话不给我结账,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我突然原谅了她,因为我们都在试图和这个与己无关的世界维持一点微弱联系。就像我在几个街口之前,看见一对在路边买杂货的华人严肃地讨论国内局势,听到了“时不我待”这样隆重而不可翻译的词语。而他们身后,是明显产于温州附近的劣质小商品,一只掉了漆的招财猫售价三块,在微风中对我招手。
爱伦·坡在1840年写下了The Man of the Crowd。那时候他刚举家从纽约迁到费城,这篇披着伦敦外衣的短篇小说被评论家们认为事实上是关于纽约的。篇首他引用了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那句“无法孤独的人是痛苦的”,小说的开头则说“它不允许自己被阅读”(It does not permit itself to be read)。在写完这篇小说的四年后,爱伦·坡搬回了纽约,他在这里失去妻子、酗酒、沉迷于鸦片以及精神错乱。在这座不允许自己被阅读的城市里,他不见得不痛苦,但是一定孤独,而我们这些在自由的召唤下来到这里的人,首先学会的不是享受自由,而是承受孤独。这件事是如此没有商量,你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不要对纽约失望
纽约正在摇摆不定地进入秋天,灼灼烈日下隐藏着会突然袭来的飒飒秋风。中央公园里每一棵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大树都是一种穷途末路的绝望的深绿色,它们很快就要开始变成每一部关于纽约的老电影中的样子,就像整座城市都被Instagram的滤镜调成了模模糊糊的暖黄。比如《当哈利遇上莎莉》里,梅格·瑞恩穿着复古高腰灰色西裤和黑色平跟鞋,踩在无穷无尽的黄色落叶中,和比利·克里斯托讨论那无穷无尽的话题:男人怎样思考女人,以及女人怎样思考男人。陈冲为纽约的秋天拍了一部同名电影,虽然里面有薇诺娜·瑞德和理查·基尔,很多人却坦白地评价,这部电影唯一美丽的地方,也不过是这纽约的秋天。史铁生写过,北京的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现在这风铃响到了纽约。
只是这样美丽的季节还是没能阻挡那些来路和去向统统不明的失望。已经在美国待了三十年的朋友有一天给我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在据说曼哈顿新开盘的大楼基本上都被中国人买下来的今天,他却正在打算卖掉那栋代表美国梦的房子离开这里,“这个国家要完了”。电话那头是轰隆隆的火车声,他尽可能提高音量,尽可能给我解释为什么这个国家快完了,涉及了民主党、共和党、爱国者法案以及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他想象中的黄金年代。虽然他也明白,美国快完了这件事对一个刚从中国来的我来说是如此超出了想象力,他还是反反复复像背诵标准答案般讲述自己的失望,不知道是想说服我还是他自己。说到最后自己似乎都开始迷惑这失望的起点,逻辑退隐在结论之后,他只需要“失望”这两个字在中文里的音节。
又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急促地询问我“左边三点水右边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而的那个字到底怎么读”。我愣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在这个他生活了三十年的国家里,我大概是他唯一一个能想到询问“湍”到底怎么读的人,而我只来了这里一个月。我是一个终于出现的人,一个在这湍急的美国生活里可以和他慢吞吞讨论中文的人。然后我终于明白,他所有的失望都可以落脚于一个你拼命想读出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的发音。这个电话挂得很快,他大概很高兴自己终于在键盘上打出了这个用英文无法取代的美丽汉字,他看着这个字就看到了江南或者四川或者云南的潺潺小溪。
太多咬噬性的小失望侵蚀了这充满暖黄色憧憬的新生活,纽约或者美国用下划线黑色粗体再加重音符号反复提醒你,你不属于这里不属于这里,不管你到了一个月,还是三十年。纽约公共图书馆里展示的中文书皮上赫然写着“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就像在这华丽的大厅里开了一个荒谬的玩笑。在中文书最多的法拉盛图书馆里,我在翻烂了的郭敬明和盗墓笔记中间找到一本菲利普·罗斯的《我嫁给了共产党人》,彻底崭新,毫无疑问我是第一个借它的人。
有一天,我们在一个破败的中餐馆里吃饭,买了个咸肉粽子和一份叉烧肠粉,一共不到5美元,这是在纽约能想象的最廉价午餐。坐在对面的黑人几乎是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剥开粽子叶,仔细询问了我“粽子”的中文发音,然后说,在他们那里,有一种类似的食物。他叽里呱啦地描述了它:用豆子磨的粉做成的,外面包着叶子里面包着海鲜的,辣的,但是也是甜的,最后,它必然是fabulous(极好的)。我礼貌性地各种点头,礼貌性地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出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单词,然后很体谅地加了一句“Africa”。大概早就习惯了说出自己国家后对方的茫然,在这个Google Maps可以查到每一栋高楼每一个门牌号的地方,他是一个仅仅能被含混地定位于Africa的人,我想,他一定是快迷路了。
菲茨杰拉德让《了不起的盖茨比》发生在纽约,大概是因为只有这个混乱城市担得起他对这个混乱世界所有的希望和失望。他还写过一篇My Lost City,当然是送给纽约,因为那座他记得有渡船在黎明时缓缓开出的城市已经永恒失落,而“我对纽约的那些巨大的梦想全都染上了污迹”。在这篇长文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菲茨杰拉德说,“是纽约忘掉了我们,才使我们得以留在这里”。不要对纽约失望,它不过是忘记你甚至从未记得你,而你所有的失望,最终不过是指向自己,城市并没有充满失望,人生才是。
……
前言/序言
一日长于百年这本书里的文字,大都是2009年到2012年之间写的,还只是这三年中我各种自言自语的一小部分。事实上,这次整理旧文,才知道自己大学毕业后这八年累积了如此数量庞大的自言自语。最开始是在Blogcn,后来搬去天涯博客。起初每天的点击率超过十次我就会紧张,现在大概稳定在每天两三百,我也慢慢习惯了这些自言自语也有读者。此外,我有一个作为普通人来说粉丝不算太少的微博,但我还是默默地在博客上写,然后我发现好多人也在博客上默默地看。他们不大评论,也不和我互动,就是每天上来看看,这让我有一种同样不想评论的暖意。
之所以基本只选了这三年的文字,是因为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诸多变化。我结了婚,然而生活却由稳定变为动荡,两次辞职,从北京来到纽约,写了二十万字至今没有出版的小说,而且正在写另外十万字,收入不断下降,在纽约把自己花掉的每一美元都记下来。奇怪的是,我在这样剧烈的动荡中慢慢安静下来,既完全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会是如何,又完全知道接下来的人生应当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MSN签名都是帕斯捷尔纳克《唯一的日子》:“情人们仿佛在梦中,彼此急切地吸引/在高高的树梢上,椋鸟晒得汗涔涔/睡眼惺忪的时针,懒得在表盘上旋动/一日长于百年,拥抱无止无终。”既然一日长于百年,那我就把百年看作一日,只要今天做好了一桌回锅肉红烧排骨海带鸡汤,我就暂时不忧虑明日的卤猪蹄酱鸭翅酸菜鱼头。
书名来自卡瓦菲斯那首《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岛,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这也是我的博客和微博名。有时候再美丽的诗重复多了,也似乎变得俗气,还好伊萨卡岛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无处不在。有一天我看纽约地图,意外地发现我住的地方附近,就有一条小街叫Ithaca,你看,哪里都是奥德赛的故乡,哪里都可能道路漫长。
谢谢我的责任编辑顾晓清,这几年我有一些机会把这些琐碎的文字结集出版,但我总是犹豫退缩,觉得它们不值一出,是她几次鼓励我,让我有了人生的第一本书。也谢谢我的父母和先生萧瀚,是他们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地多次偏离人生正常轨道,也让我在每一日的琐碎生活中明白何谓拥抱无止无终。
李静睿
2013年1月7日于纽约
用户评价
最近淘到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叫做《寂静的海岸线》。初看书名,以为会是那种关于海边风光、宁静惬意的描写,结果却出乎意料。这本书的写作风格非常有特色,它似乎是一种意识流的表达方式,没有清晰的叙事线,更像是一种情绪的碎片,思绪的跳跃。作者用一种极其跳脱的语言,将一些零散的意象、片段式的回忆、以及一些模糊的感受串联起来。读这本书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想象力,你不能期待它能给你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如果你愿意沉浸其中,你会被它独特的美学所吸引。它就像是一幅印象派的画作,你看到的不是清晰的轮廓,而是色彩和光影的碰撞,你需要自己去脑海中拼凑出它的整体。书中描绘的那些场景,虽然模糊,但却有一种强烈的感染力,能够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情感。它让我体会到,文学的表达方式可以如此自由和多元。
评分我最近偶然翻阅了一本关于历史的著作,名为《尘埃中的回响》。这本书并没有聚焦于那些波澜壮阔的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那些被时代洪流所淹没的普通人。作者以一种近乎考古学的方式,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文献、书信、日记,甚至是口述历史,然后将这些零散的信息,编织成了一幅幅生动的人物群像。它让我看到了历史并非只有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更充满了无数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奋斗和情感。我尤其被书中那些朴实却又充满力量的文字所打动,那些来自尘埃中的声音,虽然微弱,却有着穿越时空的韧性。它让我重新认识了历史,不再是冰冷的年代和事件列表,而是充满了温度和人性的鲜活故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一面向着更深处、更细微处挖掘,让我们对过去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评分我最近读到了一本让我有些难以释怀的书,它的名字叫《时间的缝隙》。这本书的内容,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一连串哲学式的探讨,但它并没有生涩难懂的理论,而是通过一个个充满想象力的小故事,将那些关于时间、记忆、存在与虚无的思考巧妙地融入其中。书中的每一个小章节,就像是一扇开启不同维度世界的门,让我得以窥探那些平时我们很少会去触碰的深层问题。作者的文字如同水一般,流畅而富有张力,但又带着一种淡淡的疏离感,仿佛在观察着一切,却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我时常会在阅读的过程中,陷入沉思,去追问那些被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真相。这本书没有给我明确的答案,但它给了我无数的问题,这些问题如同种子,在我脑海中生根发芽,让我对周遭的世界有了全新的审视。它让我明白,我们所感知的时间,可能只是一个极其有限的切面,而在这之外,还存在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广阔。
评分我最近在一家独立书店里偶遇了一本名为《星辰坠落的低语》的书,虽然它的名字听起来有些浪漫主义,但读起来却远超我的预期。作者以一种极其细腻和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个边缘小镇的生活图景。镇上的人们,每个人都背负着各自的命运,他们的生活琐碎而又真实,充满了小小的挣扎和微弱的希望。书中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每一个角色都有着鲜明的个性和复杂的内心世界,仿佛就是你我身边活生生的人。我尤其喜欢作者对细节的刻画,比如微风吹过落叶的声音,清晨阳光透过窗棂的斑驳,甚至是人们在日常对话中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情感,都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这些人物的处境,体会他们的喜怒哀乐。它让我意识到,即使是最平凡的生活,也蕴含着深刻的意义和动人的故事。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但它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触动了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就充满了哲思,一种古老而神秘的质感扑面而来。封面上绘制的,或许是一条蜿蜒曲折的山间小径,又或者是浩瀚星河下的一叶孤舟,总而言之,它暗示着一段旅程,一段充满未知和探索的旅程。翻开书页,扉页上并没有洋洋洒洒的引言,而是简单地印着作者的名字和出版信息,这让我对作者的自信和作品本身的份量有了初步的感知。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幅精心设计的封皮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又将引领我走向何方。我期待着书中能够描绘出那些足以触动灵魂的场景,那些能让我暂时忘却现实烦恼,沉浸在另一个世界的文字。我希望作者能够以其独特的笔触,构建一个既真实又充满想象力的空间,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找到共鸣,也能够收获新的视角。毕竟,一本好的书,不仅仅是消遣,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一种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我希望这本书能带给我这样的体验。
评分我在纽约认识的第一个地名是Flushing Meadows(法拉盛草地公园),《纽约客》文风的缔造者E·B·怀特写过,几百年来上面都漂浮着灰色雾气。台湾房东老太太一边开车一边指着那个传说中全世界最大的钢铁地球仪说,这是世博会留下的。那是1964年,战后的美国或者说纽约正如日中天,所以他们有最高的楼和最大的地球仪。而E·B·怀特在这里看到的世博会其实是在1939年,他在《未来的世界》中想象未来的客厅,有“宽幅地毯、人造康乃馨、电视播放机,连续播放别的什么地方什么人或什么事的影像、玻璃鸟、铬钢灯、陶制斑马、几个贴面书柜,装了无形的书、另一个书柜,绵延不断地吐出新闻小报的字条,还有新月状的丝绒小双人椅”。然而除了在《这就是纽约》的开篇那个对911几乎精确的预测,E·B·怀特对未来最笃定的想象大概还是“事事没有商量。你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评分周日订单,周一就收到了,京东的物流真是赞啊。
评分提高效益,亦可谓“教学相长”。
评分书还不错,比较薄,价格稍高,不满意的地方时封皮没有塑料膜,有些脏
评分《龙族II:悼亡者之瞳》是一个关于屠龙者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少年们成长的传奇。
评分全世界的混血精英纷纷飞往北京,而酒德麻衣团队也在北京不下了“杀龙之局”:魔兽世界副本、英雄级路明非账号、全方位监控。路明非和他的伙伴们纷纷潜入北京地铁,开始了新一轮的屠龙历程。
评分《愿你的道路漫长》,书名取自希腊诗人卡瓦菲斯的诗《伊萨卡岛》:当你启程,前往伊萨卡岛,但愿你的道路漫长,充满奇迹,充满发现。作者在读不完的逝水年华中,书写从一座城奔到另一座城的感受,试图抓住窸窣生活本来的样子。因为,“所有的宏大叙事都会崩溃解体,我用以确认某时某刻生命的证据,也不过是这些碎屑而已”,所以,抱抱你吧,在微博之外的世界,在我知道你的温度,你知道我的气味的世界。
评分不错 可以当枕边书漫漫看
评分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童话梦工场:带小鱼儿去旅行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30900/rBEhUlJo8YQIAAAAAAE8g5NfyqIAAEjDQJsdiIAATyb901.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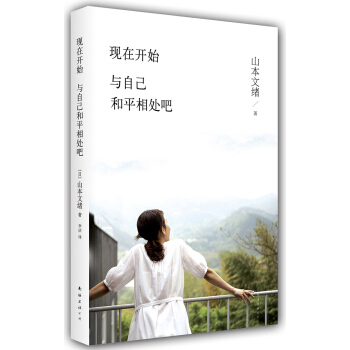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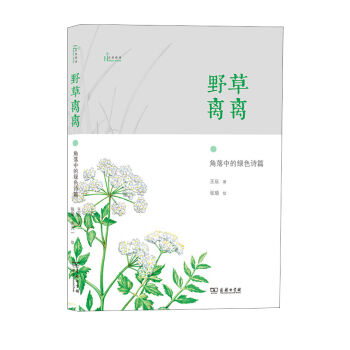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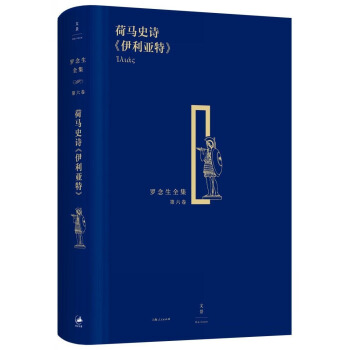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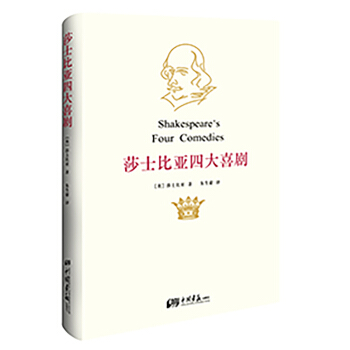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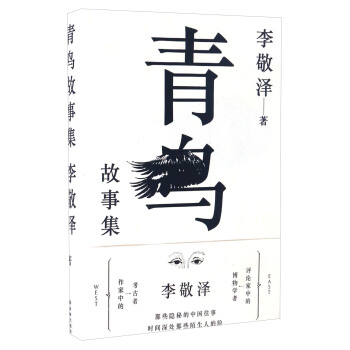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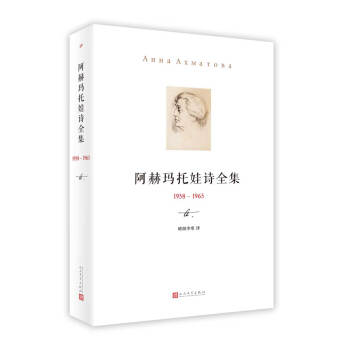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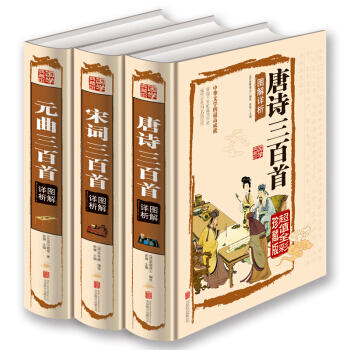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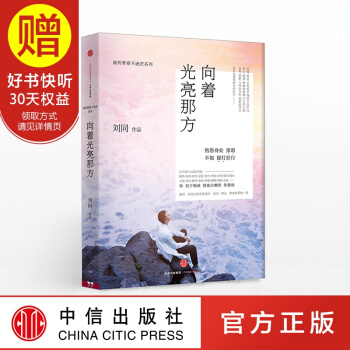
![启发童话小巴士:无聊公主 [7-10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58337/rBEGF1D30jkIAAAAAAdrB9IXfoEAABXHgOOPzoAB2sf127.jpg)
![10元读书熊·儿童文学名家名作:老爱哭和不在乎(注音版) [5-8岁]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63325/591bf915N050aa89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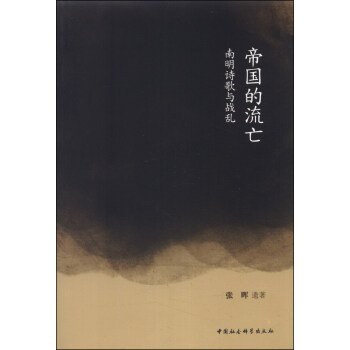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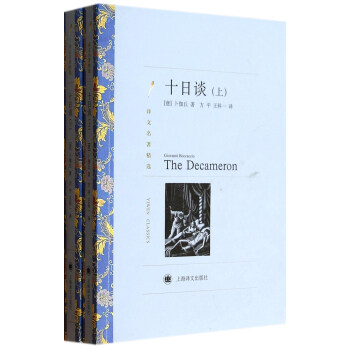
![查理日记5:怪盗侠的魔术预告 [8-14岁] [The Detective Diary:Odd Swashbuckle′s Magic Forenotic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88341/55c1ac3dNd6e5136a.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