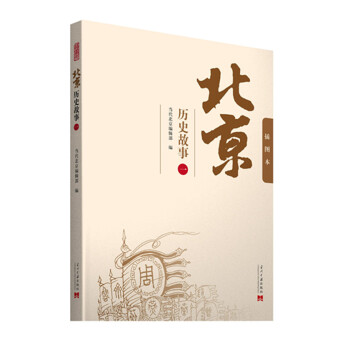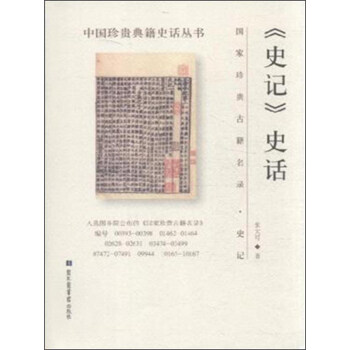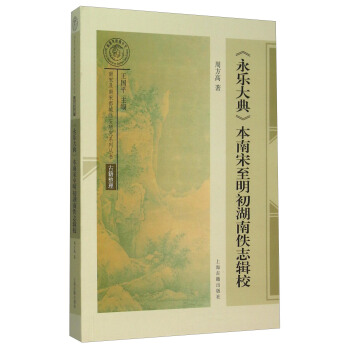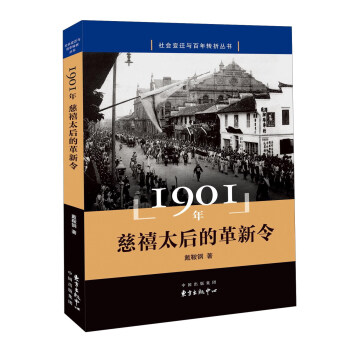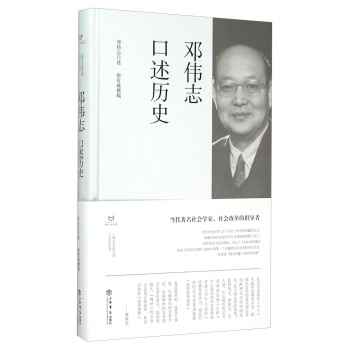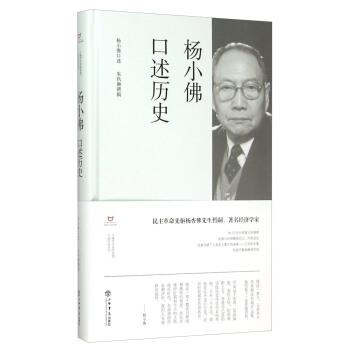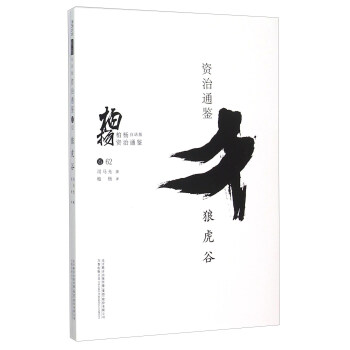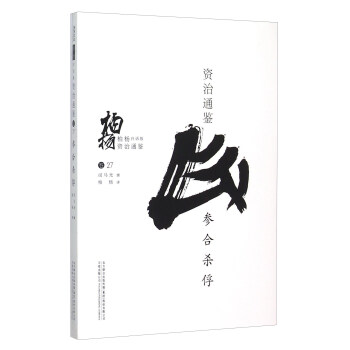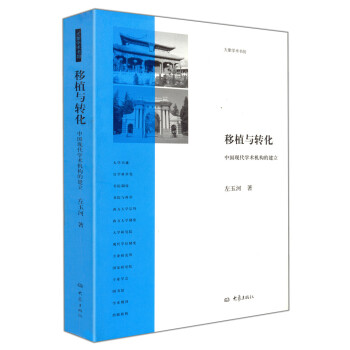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古代中国有无类似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学术机构与古代学术机构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效仿西方近代学术体制而设立的中国现代学术机构有着怎样的中国特色?现代学术机构与现代学术研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现代学术机构对现代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及专业化起了怎样的推进作用?……诸多问题,阅读完本书即可知答案。内容简介
《移植与转化: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建立》著者运用翔实的资料,细致考察和论证了中国的大学、大学研究院、独立的专业研究所、国家研究院等现代学术机构以及专业学会、图书馆、出版社等相关学术附属机构的渊源、流变及特色。体例严谨,史论结合,学术价值高,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简介
左玉河,原籍安徽淮北,1964年10月于河南新乡,历史学博士。1998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昕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留所工作。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帅,社会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及社会文化史研究。出版有《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利与近代中同知识系统之创建》、《失去的机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再认识》、《近代中国婚丧嫁娶》等专著。土编有《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近代启蒙思潮》(1924—1949年)等书。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充》等刊物上发表《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等学术论文50余篇。目录
引 言第一章 太学体制及官学科举化
一、"学为官守"及学术下移
二、两汉太学之兴盛
三、官学体制的确立
四、科举引导官学
五、官学科举化
六、"官学一体化"格局
第二章 书院制度及其学术功能
一、不绝如缕的私学传统
二、新型书院制度的创立
三、书院是古代中国的重要学术机构
四、书院的多种学术功能
五、书院官学化
六、书院与科举之勾连
第三章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构
一、西方大学的演进
二、近代大学理念之阐述
三、研究高深学术的大学宗旨
四、西方大学制度的最初引入
五、美国大学模式的移植
六、大学学科及院系设置
七、蔡元培的北大学科改革
八、大学学科及院系的整顿
九、"教授治校"之制度设计
十、"教授治校"原则的维护
第四章 大学研究院及学位制度
一、大学创设研究所之设计
二、北大尝试创办研究所
三、北大国学门研究所的筹办
四、创办清华国学院
五、大学研究院之制度规划
六、大学研究院的普遍设置
七、现代学位制度的建立
第五章 创办独立的专业研究所
一、西方研究所体制与清末"通儒院"
二、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设想
三、创建专业研究所的呼吁
四、专业研究所的筹办
五、外国人在华创办研究所的刺激
六、掀起创办专业研究所的热潮
七、别具特色的中国西部科学院
八、专业研究所对学术研究之推进
第六章 国家研究院及其评议体制
一、两种科学体制化模式
二、国家研究院之酝酿
三、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创建
四、中央研究院的学术宗旨
五、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研究
六、中央研究院与其他学术机关的合作
七、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建立
八、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功能
第七章 近代学会及其学术事业
一、中国传统社团的特性
二、西方近代学会的引入
三、创建各种专业性学会
四、大学学术社团的普遍建立
五、中国科学社及其学术事业
第八章 图书馆及相关学术辅助机构
一、中西藏书特性的比较
二、西方图书馆制度的引入
三、专门图书馆的学术辅助功能
四、大学图书馆的创设
五、新式学术期刊的创办
六、大学学报的创办
七、出版机构成为学术文化之重镇
八、出版界对学术研究的推进
参考文献
后 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太学体制及官学科举化
一、 “学为官守”及学术下移
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孟子?滕文公卜》日:“夏日校,殷日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表明殷周之时已有“校”、“序”、“庠”等类学校,用以教化人伦。这些学校均为'官府所设,学术、知识亦被官府垄断。掌握学术文化乃为贵族特权,此即谓“学在官府”。既然学校由官府控制、学术为贵族垄断,必然导致“官学台一”、“官师合一”,职事之官同时兼职事之师。贾谊《新书?保傅》载:周成王幼时,“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又设少师、少傅、少保为副职,陪读太子。此种情况表明,官吏兼任教师职责在殷周时代甚为普遍。
殷周时代,学在官府,学为官守。《周礼》对各种职事之官的设定,实乃对“官学合一”体制的认定。《札记‘王制》云:“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日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日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日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对士之逐级选拔,乃士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
“诸子起于王官”,既是对春秋时期私学来源之表述,亦为对春秋之前学术状况之合理表达。清人章学诚云:“自官师分而教法不台于一,学者各以己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师既分,则肄习惟资简策,道不著于器物,事不守于职业,其不同者二也。古学失所师
承,六书九数,古人幼学皆已明习,而后世老师宿儒,专门名家,殚毕生精力求之,犹不能尽合于古,其不同者三也。”①又云:“道欲通方而、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于《诗》、《书》,或疏或密,途径不同,而同归于道也。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②
如此看来,“学在官府”而又“官学合一”,乃殷周时期学术体制的基本特征。这种学术体制,随着周室衰落、官制解体而日趋崩溃官府创办的各种学校业已衰败,而且作为周室各种职守之官吏亦流散各地,此乃孔子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官学因周室衰微而散落
民间,遂形成私人讲学制度。
春秋时期私学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私家学派;二是私人教育团体。私学兴起与士阶层之形成密切相关。作为西周王官中之士,其官爵系世袭,当属贵族中之位卑者。王朝衰落后,出现了《孟子‘告子下》中所谓“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之局面,士逐 渐沦为一个独立社会阶层,开始寻找新的生存途径。他们或为食客,或为读书人。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禄位在大夫;其失去官位后乃致力治学从教,变“王官之学”为“私家之学”,遂为私学之师。私学之兴起,弥补了官学衰微所带来的学术真空,并通过私人讲学及学术团体之活动,形成了学术研究上“百家争鸣”的局面。
殷周时代的学术固然系官府之学,学术重心在王室;春秋时代散落于民间之学术,亦同样为官府之学,只是学术重心从王室下移到各地诸侯;学术研究主体已非昔日之王室官吏,而是新崛起的士阶层,由此出现“礼失而求于野”现象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论语?子张》载:“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日:‘仲尼焉学'’子贡日:‘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土人承担着延续“文武之道”不坠之重任。
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官俨然成为东方学术中心。据刘向《别录》载:“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齐王不仅大兴土木、广建学宫,“开第康序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①,而且为聚集此地的学者提供优厚的生活待遇,依据其学术成就及资历授予其俸禄以资鼓励。当时来稷F学宫讲学的各派名士,包含了儒、道、法、阴阳诸家代表人物及其门徒“数百千人”。其中 重要者有邹衍、孟子、田骈、慎到、伊文、接予、彭蒙、季真等人。他们受到齐王的优厚款待和恩宠,自由辩论,来去由己,促进了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各地诸侯扶植的士阶层,遂成为战国时期学术文化的主要承担者。
二、两汉太学之兴盛
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战国时期私学兴盛局面不复存在。秦始皇禁止私学、“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乃是以官府之法律规为教学内容,以各级官吏充任教师。以吏为师,实乃变相的“学在官府”。秦始皇以压制私学的强硬方式,使学术知识的中心重新卜移,学术重心再次回归官府控制的各级官学。学术知识为官府所严密控制,遂难免使学术文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注解。汉初虽仍承袭秦之吏师制度,但准许民间讲学。一些老儒聚徒讲学,私学再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文礼……于是喟然叹兴于学”,出现了汉初私学复兴的局面。专攻《诗经》、《毅梁传》的鲁人申公,“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其弟子申章昌还充任专掌儒家经学传授的学官博士,广收门徒,讲授学问。据《汉书》载:他“任长沙太傅,徒众尤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重
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学。近人张正藩云:“中国的官学,直到汉代董仲舒请立太学,置博士弟子,而后才有正式的教育,也就是才有正式的官学。”①
汉代中央官学谓“太学”,设于京城长安,选择德高博学之经师大儒担任教职,称“博士”;学生称“博士弟子”,主要研习儒家经典。其研习的经典,除《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外,尚研习《论语》、《孝经》等。-博士”各以其专精之一经教授弟子,学生则严守“师法”,精通一经,考试成绩优异者可授予官府官职。
地方官学多按行政区划设立,在郡国者称为学,在县、道、邑、侯称为校,在乡者称为庠,在聚者称为序。其学、校分别设经师一人,庠、序各设孝经师一人,主掌地方官学之讲授。中央太学设立后,郡国负有举荐博士弟子的职责,因而推动了郡国学校的发展。
汉武帝创立的这套官学制度,在当时得到迅速推行。以孔孟为正宗之儒家经典,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从京师太学到地方郡国乡聚的学校庠序所构成的官学体制,则成为汉代学术传承及学者研习学问的主要机构。
汉代官学体制中的太学,堪称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太学以五经为研习的主要课程,官府以其为策士抡才之标准。博士制度的创立及完善,使太学成为汉代学术研究中心。“博士”作为一种官职,在战国时期业已出现。据司马迁《史记》载,战国时齐国置有博士官,掌管典籍、图书以备顾问。应劭《汉官仪》日:“博士,秦官也;博者,博通古今;士者,辩于然否。”王国维的《汉博士考》亦云:“博士之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汉兴,因秦制员至数十人。”汉代以降,“博士”成为学官之名:“古之立太学,将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①据《汉书》载: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经博士。《易》、《书》、《礼》、《春秋》各一家,《诗》有齐、鲁、韩三家,共为七家,其职责是以儒家“五经”教授生徒,复以其淹博之学识备官府策问。
……
前言/序言
任何一个时代的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总是无法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环境限制,更无法超越特定的思维模式、思想框架、语言文字限制及相关制度化的规范。其中,制度化的规范,就是所谓学术体制。学术体制是学术研究正常运行的制度性建构,是一代学者学术思想得以产生的制度性保障。中国传统学术有没有制度化的规范,即中国传统学术是否为体制化学术,乃为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近代以来的中国学术是一种体制化学术,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是一种制度化研究,这应当是没有疑问的。这种体制化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标志,就是现代大学、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等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现代学术机构是构成现代中国学术体制最重要的元素。既然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创建的重要标志,那么便不能不令人追问: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是怎样建构起来的?古代中国有无类似的研究机构,中国现代学术机构与古代学术机构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效仿西方近代学术体制而没立的中国现代学术机构有着怎样的中国特色?现代学术机构与现代学术研究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现代学术机构对现代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及专业化起了怎样的推进作用,这是考察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及中国现代学术体制建构问题时必须解决的问题。
如果用现代学术眼光去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则会发现'古代中国确实没有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学术体制,但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机构和相应的学术中心。有人研究后认为:“如果制度架构给生产活动报酬则将诞生企业以从事生产活动。西方知识生产组织的出现是以大学
科学学会(协会)、科学院为标志的,中国则潜伏在太学、国子监、书院等教育组织中。”①古代中国的学术体制,显然不同于近代以来以大学和研究所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学术体制,而是以各级官学和各种书院为中心的古典式学术体制。学术研究的承担者,是士绅等所谓“读书人。;其基础在各种书院、各级官学(大学、府学、州学、县学、社学)及民闻私塾义学;其研究内容主要限定于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官学、书院与科举制度相结合,构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古代中国学术体制。官学体制、书院制度及科举制度,构成了古代中国学术体制的主干:太学、国子监、各级官学及各种书院,便是古代中国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 中心。
所谓学术机构,是指学术研究成建制的单位。它有狭义与广义两种:狭义的学术机构,也称学术研究机构,或学术研究机关,指独立的专业性研究院所;而广义的学术机构,除了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之外,辽包括现代大学及其附设的研究院所,新式学会及其创办的研究所,近代 图书馆及出版机构附设的学术编研机构,甚至包括政府部门附设的专门研究机关。笔者此处所谓“学术机构”,就是指广义的学术研究机构:除了包括现代大学及专业研究院所外,还包括新式学会、近代图书馆、出版机构及其附设的学术机构。换言之,本著所讨论的“学术机构”,除了现代大学及独立的专业研究院所外,还包括新式学会、近图书馆、现代出版机构、学术杂志社等直接或间接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学术辅助机构。
……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深度,似乎在于它挑战了我们对“现代性”的预设理解。我们常常习惯于将西方模式视为唯一的“正确答案”,但阅读这些关于中国本土化实践的记载,会促使我们反思:中国在吸收外来学术体系时,究竟是全盘照搬,还是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本土适应与改造?从材料学的角度看,早期中国机构在资金、设备乃至原材料上的极端匮乏,迫使研究者们发展出不同于西方的、更具“在地智慧”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这种“被迫创新”的历史,正是中国学术精神的独特印记。作者能否清晰地勾勒出这些“本土化策略”的轮廓,将决定本书能否从优秀的学术史著作提升到思想史的层面。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建构”的历史,更是一部关于“抵抗”与“适应”的生动写照。
评分从装帧和排版来看,这本书显然是面向专业读者和资深历史爱好者的,印刷的字体清晰,注释详尽,这为深度阅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阅读这类严肃的历史作品,最怕的就是“浮光掠影”,但从其对某一时期某一机构的细致剖析来看,作者显然是下足了“笨功夫”的。我期待书中能有更多关于早期大学校长的、充满个人色彩的文献引用,那些关于经费申请、人事任命、甚至学生运动的往来信函,往往比官方的法令更能展现那个时代的“温度”。真正的学术机构的诞生,是无数次微观的、人与人之间的博弈与合作的累积。如果这本书能够将这些看似零散的“微历史”有效地整合进宏大的制度变迁叙事之中,那么它就成功地捕捉到了中国现代学术“活的历史”,而非仅仅是僵硬的“建制史”。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风格乍一看是极其严谨的学术语言,充满了规范化的术语和精准的年代标注,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档案气味的资料室。但是,透过那些冷静的叙述背后,我似乎能捕捉到一种隐秘的、燃烧着的热情。作者似乎并不满足于仅仅罗列事实,而是试图挖掘出那些推动机构诞生的内在驱动力——是民族危机的紧迫感,还是对“富强”的集体渴望?书中对早期留洋学生回国后在体制内外的挣扎与适应的描摹,无疑是极具张力的。他们带着西方的先进理念和实验方法,却必须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孱弱的财政支持中寻找立足之地。这种“水土不服”的张力,恰恰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我尤其期待看到作者如何处理不同地域、不同学科机构之间的横向比较,比如南方沿海与北方内陆在机构建设上的差异,以及理科与文科在争取资源上的博弈,这能让历史的层次感更加丰富,避免了单一线性的叙事陷阱。
评分翻阅此书时,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仿佛能听到百年前那些大学教授们在简陋的实验室里争论学术规范的声音。作者对“机构建立”的定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盖楼立校”,它必然包含了对人才培养模式、学术共同体精神的塑造,甚至是学科意识形态的构建。那种对早期学术规范的执着和对专业精神的坚守,在今天的快节奏科研环境中显得尤为珍贵。我很好奇,书中是如何平衡个体命运与宏大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的?是机构塑造了杰出人才,还是顶尖人才的聚集才催生了有影响力的机构?这种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往往是历史研究中最精彩的部分。此外,如果书中能对那些被忽略的“边缘机构”——比如工科院校、师范学堂,甚至早期的私人研究所——给予足够的关注,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将大大提升,因为它更能反映出那个时代“百花齐放”却又“根基未稳”的真实面貌。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充满了厚重感,那种深沉的靛蓝色调配上烫金的书名,立刻让人联想到历史的沉淀与学术的庄严。我拿到书后,首先被其装帧的精良所吸引,纸张的质地细腻而富有韧性,显然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内容上,虽然我尚未深入阅读,但从目录的编排来看,作者显然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和科研体系的演变有着深刻的洞察。那种试图梳理从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在资源匮乏、政治动荡的大背景下,艰难地构建起现代科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努力,让我对即将展开的阅读充满了期待。尤其关注到其中关于特定学派或人物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迁徙与机构重塑的论述,这绝非简单的历史叙事,而更像是一幅关于“知识地理学”的宏大图景。它似乎在揭示,一个国家的学术骨架是如何在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中被锻造出来的,而这其中必然蕴含着无数次的妥协、坚持与创新。我预感,这会是一部需要静心沉思、反复咀嚼的佳作,它不仅仅是关于机构的“硬核”历史,更可能触及到“中国如何学习并改造西方科学”这一深刻的文化议题。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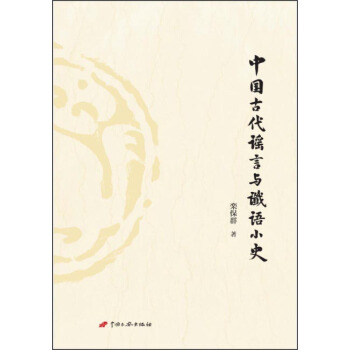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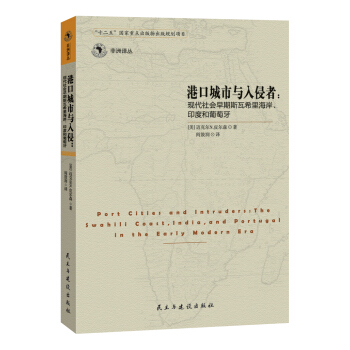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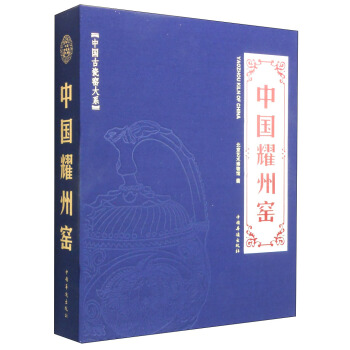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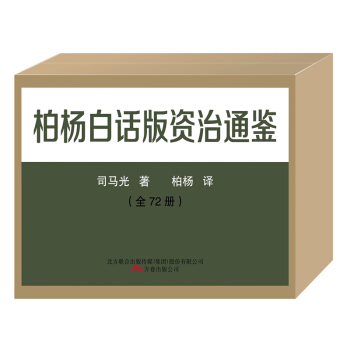
![新史学·第十三辑:艺术史与历史学 [New History:Art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62833/551e01c5N82f2c17e.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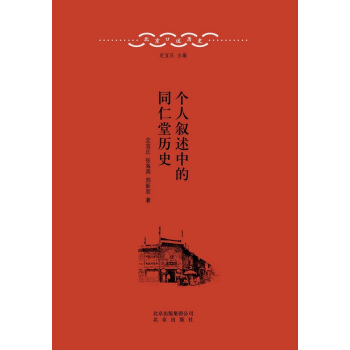

![山西故事 历史事件 [Shanxi Story Books Historical Even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25832/55b60696N316ec46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