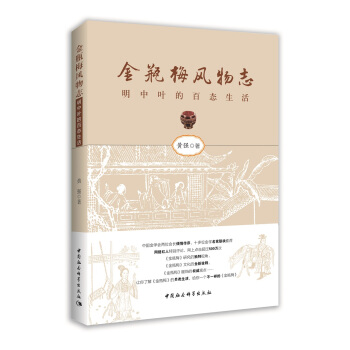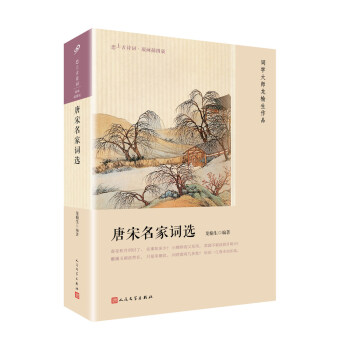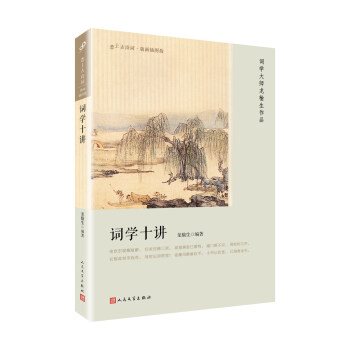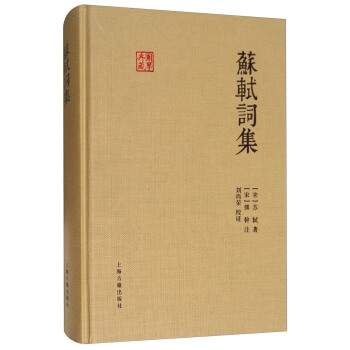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神圣家族》作者李敬泽、崔永元、李洱竭诚推荐
梁鸿首部长篇力作
中国文学崭新农民形象同时却是典型中国父亲和儿女
是“这一个”也是被长久忽视和遗忘的“这一类”
究竟谁是梁光正?
一个除了瘫痪的妻、四个幼子、还不清的风流债及用不完的热情外无足称道的梁庄农民。
他要做什么?
寻亲。报滴水恩。念故人情。
为啥?
因为他对自己说,要有光。
故事以梁光正晚年寻亲为起点,其子女也被迫随之回溯父亲如西西弗般屡战屡败却向光而行的一生。
他是梁庄的堂吉诃德。四村八乡闻名的“事烦儿”。却笃信世间一切必遵循“道理”发生。
如同一团孤独的乱麻,热情地席卷所有人,给子女空留下一地烦恼。
在他棺材落地的一瞬间,人们才突然觉得,这世界过于空旷。
《梁光正的光》是在“梁庄三部曲”等影响极大的非虚构作品之后,梁鸿首部挑战自我完成的长篇虚构力作。故事同样发生在并非实有的“梁庄”,并以她的父亲富有典型意义的一生为原型;不仅继续保持了作者在非虚构写作中表现出来的对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现实的关切和介入精神;还因首次采用小说方式,文本飞扬的想象力和厚重现实性得以真正比肩,这部小说可以说彻底释放了作者在声名卓著的“非虚构”写作中长久被压抑和稀释的虚构才华。
《梁光正的光》看似是发生在农村的故事,又不全是我们想象中司空见惯的乡土文学。当我们跟随作者生动耐心的讲述逐步深入文中,随着梁光正报恩行为的一再重复和失败,这位如西西弗般屡败屡战的梁庄农民令人动容的奋斗史和情感史就渐渐显出轮廓;一个常见中国家庭父母子女间的爱恨恩怨,及其背后折射出的典型中国式家庭情感勾连模式也便如浮雕般逐步凸显;并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主角梁光正何以会被戏谑地定义为“中国的堂吉诃德”,梁庄的西绪福斯。这是一个时刻把自己当成救苦救难的上帝、却永远力所不逮甚至滑稽可笑的“事烦儿”、一个看上去处处似曾相识、此前却又从未在任何文本出现过的崭新中国农民形象。
也许每个中国家庭中都有这样一个“梁光正”,正直到近乎偏执、多管闲事到令子女厌烦、不识时务而屡屡碰壁,却不见棺材不掉泪;时刻用毫无必要的道德准则束缚自己,更困扰家人;然而却是我们无法与之彻底断绝关系、更无法不被他的“道理”打动与蛮暴热情裹挟的家庭成员,永远难以割舍的骨肉至亲。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唯有不断往更深和更远处看,才能看到一点点真相。”梁光正,也许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中国人心底隐藏Z深的,那个永远自以为是的亲人和“中国好人”。
作者简介
梁鸿,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著作《出梁庄记》和《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黄花苔与皂角树》《新启蒙话语建构》《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文学著作《神圣家族》。曾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3年度中国好书”等多个奖项。
精彩书评
从未见过这样的“农民”:他是圣徒,他是阿Q,他是傻瓜,他是梦想家,他是父亲是土地,是顽劣的孩童是破坏者。他对自己说,要有光,于是他的生命分出了明亮与晦暗。在现代性的农民形象谱系中,这是个“新人”,其意义颇费参详。不必急于界定他,也不一定仅仅只是农民,梁光正的光或许就在我们的父辈、我们自己身上。所以,让我们先认识这个活生生的人,认识有趣的“这一个”。
——李敬泽
梁家儿女觉得父亲是用一生做了场春秋大梦。将现实执拗地过出魔幻感,不被人理解也无妨,这种感觉在我生命中也常有。梁鸿不止写出了梁光正的光,还映出她心里那束梁庄的光、父辈的光。透过坚实的文字,这光葳蕤自生。
——崔永元
让小说透过耐人寻味的道路回到自身真实及情感,而终向人的魂灵和爱,这是梁鸿对写作路径的校正和野心。
——阎连科
他们生不如死,他们在爱中死,他们虽死犹生:他们就是我们的父兄。梁鸿首部长篇,以肉写灵,以黑暗写光明,以农民写国民,以芜杂抵达纯净。凡此种种,都将在当代小说史上留下回声。
——李洱
目录
开始麦冬麦冬
蛮子
豆角
小峰来了
妈妈
油菜油菜
呓语
爱情
葬礼
后记
精彩书摘
1.风是突然来的。勇智记得很清楚,他正用力往上提卷闸门,那闸门被轨道里的陈年老灰吸着,很难拉起。突然,他感觉胳膊上的肱二头肌鼓起的地方被什么轻扫了一下,里面的青筋一阵猛烈弹动,像一排细针轻轻扎下,又迅速拔起,点点烧灼般的疼。紧接着,门左边的大盆针叶松微微动了几动,密密的针叶相互碰撞,搅在一起,右边的
芍药大绿叶也晃了一下,一片腐烂的黄叶飘到大花盆的边缘。
起风了。
勇智抬头往远处看,门前路上,风卷着地上的垃圾,塑料袋麦秸杆干菜叶脏布条,跳着转着,卷过对面的百货店烟酒店热干面店,梭成一个个小三角堆,堆在春天新栽的小树根部。勇智感觉积攒了整夜的汗液瞬间消失,垂到胯部的肚子减轻了一点分量,呼吸也畅通起来。
这是一条“工”字形路,勇智家在那条竖“1”上,上边的横“一”是繁忙的省道,通向全国各地,“一”外是平展展的田野,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下边的横“一”是吴镇内部的一条街道,镇政府邮政所电信营业厅和各种小商店都在这条街道上,是吴镇年头最久也最繁忙的老街道。风从上边的横“一”方向浩荡着吹过来,把一辆辆大卡车卷起的灰尘扬到空中,弥天盖地。从勇智这边看,声势很大的样子。
是要下雨啊。
话说不及,从上面横竖“一”交叉的大路转弯处传来了声音,
“嗯——”,音调微微上扬,拖长着,运行到鼻腔最后部,把那里的粘稠物质紧紧吸住,然后,再从鼻腔后部往前运行,“咔——呸——”,中间一气呵成,无一丝停顿。父亲来了。在勇智脑子里,一口浓痰正从父亲口中飞出,滑出优美的足有几米长的抛物线,准确地落在路边的垃圾堆旁,拖车边,树根下,院子外的粪堆上,客厅的墙角里。反正,从来不会在垃圾桶里。
父亲穿着他的白短袖衬衫、黑短裤、白袜子和黑色千层底布鞋,迈着八字步,挺着腰,于灰色小旋风中浮现,施施然朝勇智走过来。
2父亲的名声已经败坏。父亲不务正业、不好好种庄稼,父亲好大喜功、惹是生非,父亲敢说敢骂、爱出风头,父亲热嘲冷讽、蔑视那些勤勤恳恳的人,父亲那身终年不变的白衬衫,都早已让人们看不惯。但是,有一项人们无法抹煞父亲,那就是,他的老婆躺在床上七年,依然活着。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背着这可怜的女人到遥远的城市去看病,身无分文时再回来,挣一些钱后,再背着她去找医院,他心无旁鹜、一心一意,好像那女人是世间最珍贵的财宝。人们忘记了当年他们彼此间怎样吵架,忘记了他怎样因为常年到处跑而惹得女人生气,忘记了他怎样爱打官司而让女人担惊受怕。人们看着这个男人,一会儿背着女人出去了,一会儿又抬着副担架回来了,女人总是躺在那里,而他,专心低头看着,就好像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人们被他感动了。在说起他时,人们会说,人家梁光正,也只有那样了。
3.她能看到他们的一举一动,看到他们的伤心和怨恨,看到埋藏很深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爱。
4.她把过去存在箱子里,就像存一个百宝箱,闲时拿出来,慢慢翻看,看着,笑着,哭着。这些写信的人,怎么和她眼前的人都不一样啊?她们到底弄丢了什么?冬竹喜欢他们每一个人,她希望他们还是他们。可是,他们肯定忘记了自己说过什么话干过什么事,它们藏在各自心里,藏着藏着,就忘了,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5.他带着我们四处寻亲,不断上路,考验我们到底爱不爱他,爱不爱人们,爱不爱这世界。其实,是他自己还天真地抱着幻想,他也想再爱一次,以弥补他的愧疚。他比我们谁都天真。
6.妈要死了。大家只是凭着惯性日复一日,例行公事般地照顾她,放开她,忘掉她。很难说没有懈怠所致。蛮子的事情刚好掩盖住了我们的懈怠,我们借此原谅了自己,又找了一个可以恨的对象。谁都清楚,即使没有那次的事件,妈也快要死了。
7.说到“爱”,父亲对“爱”的理解和通常人不一样。勇智一个人在心里来回琢磨父亲行为的缘由。对父亲而言,对自己亲生子女的爱,就像动物的自然本能,是谁都有的行为,不值一提。对他人的爱,则是一种道德行为的展示,是对人的品行的衡量。他之所以一生都热衷于对别人好,是因为那是他的道德标准,是最低的道德限度,是他生之为人的重要标志。这样看来,父亲忽略自己的子女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自然伦理下的产物。唉,谁知道呢?也许父亲只是热爱女人而已。
8.父亲怒视冬雪,“好不容易咋了?好不容易当个小官就该欺压百姓,就该说假话办假事?那算个啥官?!我被批斗,你说都是我的错了?我不该偷东西让你们吃?我不该给你妈治病?不该让你们上学?不该说实话?这个社会都坏透气了,都不说,那大家活着还好干啥?”
9.父亲提高声音,说,“特殊年代就不认自己爹妈了?自己爹妈都不认了,还配是个人?你说说看,哪朝哪代,不认爹妈的那个人会是个好人?”父亲压低了声音,说,“也不是没有报应。现在,他们再回村里,谁搭理他们?别看他们是啥美籍,啥大老板,都看不起他们。”
冬雪说,“那是你顽固不化,村里多少人请他们吃饭,巴结他们,你又不是不知道。”
19.父亲眉眼乱飞,话语尖刻,奇思妙想,又句句关涉现实,病房很快就成为他的表演场所,病床就是他的舞台,所有人都面朝他,被他牵动。从ICU出来,父亲又在病房里住了将近一个月。在这期间,父亲教两个老人和不孝子女斗争,调解三起家庭矛盾,批评了四五个晚辈粗心,为前后住进来的六七个病人打气。除了睡觉、昏迷和极为痛苦的时刻,他都在忙着为大家操心。他的听众越来越少,家属们避之唯恐不及,不敢对病人高声大气,不敢离开,也不敢翻手机,一脸死相地坐着。那些病人想要休息,又被父亲缠着,只好斜侧着脸,假装听的样子。
11.“都啥时候了?你那套斗争经验不起作用了。”
“咋不起作用?当年能把家斗败斗散,现在再把儿子工作给斗没,把自己的命也斗没,作用可大了。”勇智阴阳怪气加一句。
12.父亲开心地笑着,任由振华握他的手。他喜欢振华,他喜欢活跃的、离经叛道的、有各种想法的人,父亲喜欢和他们在一起愤世嫉俗,骂骂权威,嘲笑嘲笑老实人,呸几声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春天父亲鼓动大家告状时,振华是中坚力量。他负责联系梁庄在外的打工者,游说大家反对征地,又花钱打印复印告状信,快递到全国各地的梁庄人,收集签名。他使用的名词也比父亲更时髦更新鲜,什么公民啦、法制啦、地权啦。他兴致勃勃,一张大嘴到处奔洒唾沫,劲头比父亲还足。也难怪他太阳能生意做不成。
13.他想干啥?冬竹猜不出来。想让我们大家的手都握在一起,来一个大和解大团圆?这符合父亲的风格。他喜欢煽情也擅长煽情,他喜欢让大家看到他的伤心,只要能让我们跟着他哭,能让我们心怀内疚,他什么举动都可以做出来。
14.梁光正的世界,梁光正的儿女们知道得并不多。
15.她狠狠摇晃着,想把梁光正摇醒,她要和他大吵一架,让他看看他制造的慌乱,看看他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和负担,让他承认他的糊涂和犯下的错误。
16.她要扒出梁光正的棺材,把他摇醒,看着他的脸,让他给她一个办法,给她指条明路。他一生为别人出了那么多点子,可为什么留给自己的子女却是难题。
17、他们听到了风的声音,空气流动的声音,阳光照射的声音,树叶碰撞的声音,听到了坟里的低语和哭泣。他们看到了那条大河,就好像第一次看见。春天的水刚刚来临,它们从遥远的山涧下来,一点点汇聚,沿着万千年冲刷而成的河道奔腾向前,那浪花在每一个弯角盘旋徘徊,回返往复,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个多情的情人,不愿意舍弃和每一处泥沙亲吻的机会,涌上去,下来,再涌上去,白色的水花溅起,飞腾出一个个水珠。阳光穿透而过,形成一个个五彩团球。每一个彩球里都包含着万千世界,山川、长城、蚂蚁草、合欢树、微尘、巴别塔、金字塔、尸骨、矿物、杜鹃花,以至无穷。
他们重又看见父亲和过去的一切。就好像第一次看见。
……
前言/序言
后记白如暗夜
毋庸讳言,写这本书,是因为我的父亲。
在父亲生命后期,我和他才有机会较长时间亲密相处。因为写梁庄,他陪着我,拜访梁庄的每一户人家,又沿着梁庄人打工的足迹,去往二十几个城市,行走于中国最偏僻、最荒凉的土地上。没有任何夸张地说,没有父亲,就没有《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这两本书。对于我而言,因为父亲,梁庄才得以如此鲜活而广阔地存在。
那是我们的甜蜜时光。但是,我想,我并不真的了解他,虽然父亲特别擅长于叙说,在写梁庄时,我也曾把他作为其中一个人物而做了详细访谈。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太过庞杂,我无法完全明白。
父亲一直是我的疑问。而所有疑问中最大的疑问就是他的白衬衫。
那时候,吴镇通往梁庄的老公路还丰满平整,两旁是挺拔粗大的白杨树,父亲正从吴镇往家赶,我要去镇上上学,我们就在这路上相遇了。他朝我笑着,惊喜地说,“咦,长这么大啦。”在遮天蔽日的绿荫下,父亲的白衬衫干净体面,柔软妥帖,闪闪发光。我被那光闪得睁不开眼。其实,我是被泪水迷糊了双眼。在我心中,父亲和别人太不一样,我既因此崇拜他,又因此充满痛苦。
他的白衬衫从哪儿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全家连基本的食物都难以保证,那青色的深口面缸总是张着空荡荡的大嘴,等待有人往里面充实内容。父亲是怎么竭力省出一点钱来,去买这样一件颇为昂贵的不实用的奢侈品?他怎么能长年保持白衬衫一尘不染?他是一个农民,他要锄地撒种拔草翻秧,要搬砖扛泥打麦,哪一样植物的汁液都是吸附高手,一旦沾到衣服上,很难洗掉,哪一种劳作都要出汗,都会使白衬衫变黄。他的白衬衫洁净整齐。梁庄的路是泥泞的,梁庄的房屋是泥瓦房,梁庄的风黄沙漫天。他的白衬衫散发着耀眼的光。他带着这道光走过去,不知道遭受了多少嘲笑和鄙夷。
在讲述当年被批斗的细节时,父亲说,“白衬衫上都沾满了血。”在他心中,“白衬衫沾满了血”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严重到过了几十年之后,在随意的聊天中,他还是很愤怒。对他来讲,那件白衬衫,到底意味着什么?尊严,底线,反抗,或者,仅仅只是可笑的虚荣?
为了破解这件闪光的白衬衫,我花了将近两年时间,一点点拼凑已成碎片的过去,进入并不遥远却已然被遗忘的时代,寻找他及他那一代人所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赋予他一个名字,梁光正。我给他四个子女,冬雪勇智冬竹冬玉,我重新塑造梁庄,一个广义的村庄。我和他一起下地干活,种麦冬种豆角种油菜,一起逃跑挨打做小偷,一起寻亲报恩找故人。我揣摩他的心理。我想看他如何在荒凉中厮杀出热闹,在颠倒中高举长矛坚持他的道理,看他如何在无限低的生活中,努力抓获他终生渴望的情感。
时间永无尽头,人生的分叉远超出想象。你抽出一个线头,无数个线头纷至而来,然后,整个世界被团在了一起,不分彼此。也是在不断往返于历史与现实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一个家庭的破产并不只是一家人的悲剧,一个人的倔强远非只是个人事件,它们所荡起的涟漪,所经过的、到达的地点,所产生的后遗症远远大于我们所能看到的。唯有不断往更深和更远处看,才能看到一点点真相。
小说之事,远非编织故事那么简单。它是与风车作战,在虚拟之中,把散落在野风、街市、坟头或大河之中的人生碎片重新勾连起来,让它们拥有逻辑,并产生新的意义。
然而,梁光正是谁?即使在写了十几万字之后,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他,甚至,可以说,是更加迷惑了。我只知道,他是我们的父辈。他们的经历也许我们未曾经历,但他们走过的路,做过的事,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所昭示的人性,却值得我们思量再三。
这本书,唯有这件白衬衫是纯粹真实、未经虚构的。但是,你也可以说,所有的事情、人和书中出现的物品,又都是真实的。因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相互的争吵索取,人性的光辉和晦暗,都由它而衍生出来。它们的真实感都附着在它身上。
我想念父亲。
我想念书中那个十六岁的少年。他正在努力攀爬麦地里的一棵老柳树,那棵老柳树枝叶繁茂,孤独傲立于原野之中。他看着东西南北、无边无际的麦田,大声喊着,麦女儿,麦女儿,我是梁光正,梁庄来的。没有人回应他。但我相信,藏身于麦地的麦女儿肯定看到他了,看到了那个英俊聪明的少年——她未来将要相伴一生的丈夫。
那一刻,金黄的麦浪起伏飘摇,饱满的麦穗锋芒朝天,馨香的气息溢满整个原野。丰收的一年就要到来,梁光正的幸福生活即将开始。
用户评价
这本《梁光正的光》犹如一位老友,娓娓道来,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子沉静的力量。初读时,我被它那娓娓道来的叙事节奏所吸引,仿佛置身于一个悠长而宁静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下斑驳的光影,耳边是细碎的风声和远处的蝉鸣。作者的笔触细腻得如同水彩画,将那些寻常巷陌、人间烟火勾勒得活灵活现。我尤其喜欢其中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那种不动声色的悲喜,那种深埋心底的牵挂,都以一种含蓄而动人的方式呈现出来。读着读着,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那些青涩的梦想,那些不经意的错过,那些曾经的执着与迷惘,都在这个故事里找到了共鸣。它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惊心动魄的冲突,但正是这种平淡中的真实,才更能触动人心。它像一杯陈年的老酒,需要慢慢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醇厚的滋味。每一次重读,我都能从中发现新的细节,新的感悟,仿佛在反复品味一幅意境深远的画卷。
评分《梁光正的光》的魅力在于其独特的叙事视角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它没有设定一个明确的“主角”,而是将笔触分散在多个似乎互不相干的个体身上,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他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同无形的丝线,将他们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壮丽的时代画卷。作者的叙事方式非常克制,不滥用形容词,也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而是用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勾勒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这种“少即是多”的艺术手法,反而使得故事更具张力和感染力。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的关注,它没有回避问题,而是以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态度,展现了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挣扎与希望。读这本书,我不仅仅获得了一种阅读的愉悦,更获得了一种对生活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
评分从《梁光正的光》的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一种超越时间的力量。它不像许多 contemporary 的小说那样,急于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留给了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作者似乎在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引导你去思考,去探索,去发现。我喜欢这种留白的处理,它让每一个读者都能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属于自己的解读。书中对“光”的描绘,不是那种耀眼夺目的光芒,而是温暖而持久的,如同生命本身一样,在黑暗中默默燃烧。它让我想到,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内心深处也总会有一盏灯,支撑着我们前行。这本书不是那种会让你热血沸腾的读物,但它会让你在静默中,感受到一种力量的涌动,一种对生活的热爱,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它像一本写给所有普通人的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哲理。
评分这本《梁光正的光》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生活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角落。我很少会被一本虚构作品中的细节如此打动,但这本书做到了。从一杯茶的温度,到一句无心的问候,再到一次偶然的相遇,作者都赋予了它们特殊的意义。它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煽情,但正是这种朴实无华的表达,才显得如此真实可信。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人与人之间微妙情感的捕捉,那种欲言又止的默契,那种不经意间的关心,都让人感受到人性的温暖。读这本书,仿佛回到了那个没有太多喧嚣的年代,那时的人们虽然物质不富裕,但情感却显得更加纯粹和浓烈。它让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回忆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身边的人,那些已经远去却依然鲜活的记忆。这本书不是那种读完就忘的读物,它会在你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让你在日后的生活中,不自觉地去回味,去品味。
评分《梁光正的光》给我带来的阅读体验,可以用“惊喜连连”来形容。原本以为会是一本平淡无奇的都市生活片段集,没想到作者却在看似日常的叙事中埋下了许多引人深思的伏笔。它不像那种快餐式的文学作品,一目了然,也没有刻意制造的悬念,而是像一个精心设计的迷宫,需要读者一步步去探索,去体会。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于社会变迁和个体命运之间关系的描绘,那种时代的洪流如何裹挟着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在不经意间改变着他们的轨迹,这种宏大叙事与个体情感的结合,显得尤为真挚动人。书中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闪光点,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妥协,他们的无奈,都构成了这个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读这本书,我不仅仅是在阅读一个故事,更是在审视一段历史,一段关于我们自己,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记录。它让我开始思考,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们如何才能保持住内心的那份“光”。
评分京东正品,东西很实惠,物流一如既往的快,满意!
评分不错,期待阅读…………~
评分书的质量不错,物流也很快
评分精美好书,值得拥有,宜读宜藏。
评分梁老师写的真好,几乎拜读了所有作品
评分囤书,还没看
评分东西不错!物流刚刚的!
评分包装大哥能否多来点包装吗?四书一个袋都要裸奔了。
评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纽约派诗选 [New York School of Poe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213535/5a1d40cbNdda1cec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