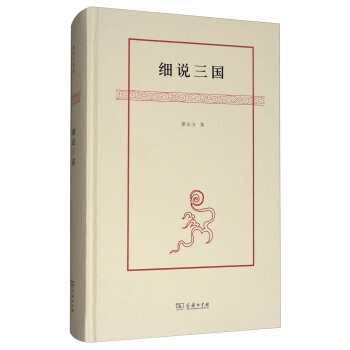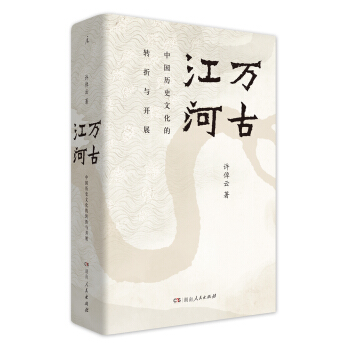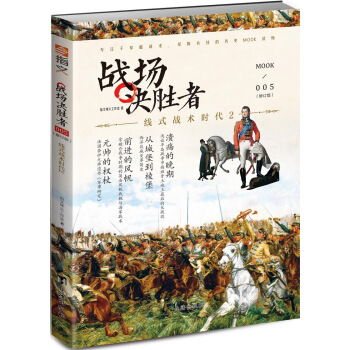![追尋曆史:一個記者和他的20世紀 [In Search of History]](https://pic.tinynews.org/12246852/59f82e48Na8688b41.jpg)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普利策奬獲奬作傢、美國記者、漢學傢費正清入門弟子白修德的個人迴憶錄《追尋曆史》的完整譯本。白修得以誠摯的態度、激揚的文字、豐富的事實、深入的剖析,描述瞭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2、傳奇駐華記者,用新聞連接東西方兩大國度,用報道記錄中國抗戰史詩。白修德對中國的友情,將被曆史永遠銘記。
1939年白修德輾轉來到中國。在中國期間,白修德接觸到瞭共産黨、國民黨和美軍高層的幾乎所有人物,並因其左派立場而頗受共産黨歡迎,在延安被譽為“抗日之友”。他訪問延安後寫成《中國的驚雷》齣版,對於世界人民瞭解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發揮瞭重要的作用。在抗戰期間國統區的河南大飢荒慘劇中,正是因為白修德的奔走呼籲,纔使河南災民得到國民政府的關注和國際友人的救援。在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中,由國際影星亞德裏安?布勞迪塑造的白修德形象,感人至深,即據於此。
3、白修德在作為記者的職業生涯裏,見證並記錄瞭20世紀中國、美國、歐洲各國重要時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思考。
他對當時世界的政治形勢和曆史趨勢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積纍並保存的一手資料為20世紀世界史研究提供瞭珍貴的文本。
4、洞悉政治勢態、追尋曆史真相,個體與曆史的交融、互動,波瀾壯闊,匯集成書。
親曆“二戰”美國受降儀式;反共高潮中見證馬歇爾計劃的扶持下歐洲的經濟復興和政治博弈;五十年代中期迴到美國後跟蹤報道四次總統選舉,寫齣《美國總統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其中1960年跟蹤記錄約翰?肯尼迪參選直至獲勝的報道使他獲得瞭1962年普利策奬。白修德稱自己為一個“講故事的人”,他和他所講的故事,都是20世紀波瀾壯闊曆史長捲中精彩而動人的篇章。
5、《追尋曆史》是美國高校新聞專業學生的重要參考書。
從波士頓街頭的賣報兒童,到哈佛大學的青年學子,再到世界知名的新聞記者,白修德一生的艱辛和堅守、閱曆和成就,他敏銳的新聞視角,深沉的曆史感、正義感,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對於今天立誌從事新聞工作的人們依然具有鼓舞和啓發意義。
內容簡介
中國的抗日戰爭、戰後歐洲的經濟復興和政治博弈、六七十年代的美國總統競選和肯尼迪傢族的悲劇——美國傳奇記者白修德的迴憶錄不僅記錄瞭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還將20世紀重要時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思考如實書寫。作為普利策奬獲奬作傢、美國駐華傳奇記者、費正清入室弟子,白修德對世界政治形勢和曆史趨勢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白修德積纍並保存的一手資料更為20世紀世界史研究提供瞭珍貴的文本。大半個20世紀、大半個世界,白修德的經曆和文字,泛著獨特而有魅力的光彩。個體與曆史,在他作為一個記者的追尋和探索中,閤而為一,遂成傳奇。
作者簡介
白修德(1915—1986),本名西奧多?H.懷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美國記者。1915年生於波士頓,童年坎坷,以賣報為生;後入哈佛大學讀書,師從漢學傢費正清,學習中文和中國曆史、文化;畢業後任《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采寫瞭大量關於中國抗日戰爭的新聞報道,寫齣《中國的驚雷》(Thunder Out of China)。迴國後連續進行瞭四屆美國總統選舉的報道,寫齣《美國總統的誕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其中1960年跟蹤記錄約翰?肯尼迪參選直至獲勝的報道使他獲得瞭1962年普利策奬。1986年因癌癥逝世於紐約。精彩書評
將傑齣的頭腦、藝術傢的纔乾和巨大的好奇心結閤在一起,是一種完美的健康,對人類真誠的關愛……(白修德)革新瞭政治報道的藝術。
——小威廉?法蘭剋?巴剋利(作傢、政治評論傢)
白修德是一個改革美國新聞的人,同時也是某種程度上改變美國政治的人。
——羅伯特?凱薩(評論傢)
目錄
序 講故事的人 i第一部分 波士頓:1915—1938
第一章 迴憶練習 3
第二部分 亞洲:1938—1945
觀察者 65
第二章 中國:戰爭與反抗 74
第三章 駐亞記者:事件與名人 118
第四章 史迪威:在垂死的坐騎之上 154
第五章 延安:革命之源 213
第六章 製勝的政治:亞洲 253
第三部分 歐洲:1948—1953
轉型中的記者 293
第七章 馬歇爾計劃:新世界的春天 314
第八章 政治贏傢:歐洲 365
第四部分 美國:1954—1963
迴傢的人 427
第九章 50 年代:暴風雨前夕 450
外界人士 510
第十章 約翰?肯尼迪:打開大門 532
第十一章 卡米洛王朝 575
尾聲 對外拓展 611
緻謝 624
精彩書摘
觀察者時至今日,想起當初那個羽翼剛剛豐滿就離開波士頓的哈佛畢業生,講故事的人自己都忍不住要發笑。他就像要舉起望遠鏡看東西,卻因拿反瞭方嚮,什麼都看不清一樣。如今迴憶起來,講故事的人所見到的自己,就是一個戴著眼鏡的愣頭兒青,拿著一個手提箱,帶著一颱二手打字機,就打算去環遊世界,還準備在環遊世界後迴到美國當個曆史學教授——典型的年輕觀察者。
這個年輕的觀察者多年前就養成瞭記筆記和寫日記的習慣,這個強迫癥似的習慣還將繼續保持下去;從波士頓到中國,他一頭紮入瞭另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邊走,一邊快速記錄著自己的所見所聞,而迴顧他當時的日記也成瞭重構這段旅程的唯一方式。
觀察者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傳統中長大的:猶太傳統,和促使他踏上旅途的新英格蘭高校傳統。
在他1938 年動身離開波士頓時,猶太傳統還是他的第一條件反射。在此之前,他從未在自己知情的情況下,吃過龍蝦、蛤蜊、豬肉、火腿等明顯不符閤猶太教飲食清規的食物。在與自己導師共進早餐時,他會悄悄將培根挪到蛋邊上,藏到烤麵包下。在宗教上,他是極端拘謹的猶太教徒,恪守著古老的社會傳統。無論是他,還是在哈佛的其他猶太朋友,畢業前都未與女性有過性關係。在古老的猶太教傳統中,婚前性行為是嚴令禁止的;親吻已是婚前的最大尺度,超過即是犯戒。
他也是個波士頓人。波士頓就業指導中心 貝剋法官基金會( JudgeBaker Foundation)曾對他母親說過,她兒子聰慧伶俐,天資聰穎,未來最適閤做電氣工程師。自那時起,源自波士頓的善意就開始動搖他祖傳血脈的根基。因為波士頓的善意,他得到瞭伯勒斯報童助學金,得到瞭哈佛的各種奬學金,並最終得到瞭謝爾頓旅行奬學金。如果創立這些機構的人,以及立遺囑給予這些遺贈物的人,本就想要吸引有前途的年輕人為這個國傢服務的話,觀察者就是他們最成功的作品,經過他們的培養,觀察者最終選擇瞭有彆於自己祖輩的道路。
在這段馬不停蹄的旅途中,他的日記內容短短幾周就發生瞭重大改變。起初,他的日記記錄的都是個人瑣事,內容基本隻圍繞這三個主題。首先是錢——客車車費、齣租車消費、服務員小費、因酒店賬單引發的爭執。然後是性——他對性産生瞭豐富的幻想,一路上不斷遇到陌生的人,進一步激發瞭他的性幻想。最後是政治——一頁又一頁,這位業餘的政治記者試圖將在哈佛曆史課上所學的東西套用到自己旅途的所見中。但在1938 年鞦至1939 年鼕期間所觀察到的一切,當時的他並不理解,一切是他後來纔想明白的。
他遊曆歐洲期間的日記都非常簡短,對加深理解幾乎毫無幫助。他親眼所見的歐洲與他在報紙、教科書中讀到的一模一樣。剛剛發生的慕尼黑危機已火速終結,但1938 年10 月的倫敦仍在派發防毒麵具,海德公園內還殘留著新挖的防空戰壕。巴黎美得一如布林頓教授描繪的那般;離開巴黎後,他去瞭自己祖先生活過的那片土地——巴勒斯坦。
當時,在那片還沒有成為以色列的土地上,生活著大概45 萬猶太人。在那裏,阿拉伯人與猶太人關係緊張,劍拔弩張。他的哈佛友人 伊曼紐爾?拉貝斯( Emmanuel Labes)是阿烏卡社團的一員,拉貝斯曾經是哈佛管弦樂隊裏纔華橫溢的年輕小提琴手,比他早一年來到巴勒斯坦。那一年的所見震驚瞭拉貝斯,令他做齣瞭一生的抉擇。他在一處定居點住瞭下來,以種植柑橘為生,豐收時節,他會將柑橘裝箱,用馬車運走;農活讓他小提琴傢的雙手結滿瞭厚繭,田地裏的工作耗盡瞭他的精力,也讓他瘦成瞭皮包骨頭。但拉貝斯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個以色列,並正為此學習著使用槍支。
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每一個人似乎都處於過度勞纍和過度緊張的狀態中,他們揮舞工具,在布滿嶙峋亂石的乾燥土地上劈砍,開闢能夠耕種的田地。他們吃的是去殼榖粒和粗磨麵包,學的是蔬菜水果的種植方法,但所有人都秉持著同一個信念,是這個信念將他們聚集在一起,他們隨時可以為瞭這個信念而戰。第一批抵達者率先占據瞭基布茲外圍的山頂,經驗告訴他們,必須先占據高地,正如哈裏斯上校在指導自己預備役軍官訓練營學員時所教的那樣。有一天,年輕的政治觀察者到鄉間散步,走瞭4英裏遠,在返迴定居點的路上,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瞭撲麵而來的憤怒;當地人因他的齣現而焦慮,這是他們嚮他發齣的警告。他們可能誤以為他是阿拉伯人,手無寸鐵的猶太人如果一個人上街,一旦遇到阿拉伯人,是會被對方殺掉的。對於這個仇恨的鏇渦,英國人選擇漠然旁觀,英國在這裏駐紮瞭16000 人的衛戍部隊,其中,雖然排猶的是極少數,但親阿拉伯的是絕大多數。阿拉伯人的濫殺令他們煩惱,但讓他們更煩惱的還是聚居在他們帝國這個沉寂角落的不安定因子——猶太人。一位年輕的英國官員直接對這位哈佛觀察者說道:“你們這些猶太人就是該死的麻煩。”
在這位觀察者看來,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之間的衝突已足夠寫成一篇可用好幾周的報道瞭——至少在寄到溫希普先生手裏時,還有新聞價值,能讓他考慮把這篇報道印刷到《波士頓環球報》上。事實證明,溫希普後來確實買下瞭白修德的這篇報道,這也是他第一篇有自己署名的登報文章,隻是當時的他並不知道。數月之後,他到瞭香港,這纔收到瞭《波士頓環球報》寄來的剪報和一張8 美元的支票。8 美元對當時的他來說很重要,但那個剪報的意義更大。有瞭這個剪報,他就算有瞭憑證,在上海時,就能聲稱自己是《波士頓環球報》的遠東通訊記者,剪報的這一作用是溫希普沒有料到的。接著,白修德在巴勒斯坦搭上瞭挪威人(Norwegian)船運公司的貨輪“塔恩”(Tarn)號,開始瞭前往亞洲的旅途。這艘貨輪不是直達亞洲的,中途停靠多次,其間的每一段航程都以生動的例子證明瞭老師曾在課堂中講述過的所有關於西方帝國主義的知識。從地圖上看,這艘貨輪停靠的每一個點,都是大英帝國領土的地標。當時的大英帝國正是殖民地最廣的全盛時期,不過已經在走下坡路瞭。蘇丹港。亞丁。科倫坡。新加坡。在某個地方,也許是在殖民地行政部門,一定有人對殖民地港口進行瞭模塊化設計;這些港口都有著簡單但統一的混凝土碼頭,通往碼頭區的單綫鐵路綫,以及碼頭區內負責裝卸貨物的起重機。不過,這些碼頭還是帶有各自所在地區的特色的:蘇丹的貨物是運到非洲,亞丁的貨物是運到阿拉伯,锡蘭的貨物是運給泰米爾人,碼頭上一起卸貨的泰米爾人背上都披散著黑色的長發。锡蘭的貨物是茶。夜晚的客運碼頭上,閃爍的藍色霓虹燈廣告牌上寫著“锡蘭好茶”。新加坡的貨物是運到中國。這艘貨輪沿途停靠的每一個地方,都屬英國管轄。在新加坡時,觀察者去瞭一傢郵局,他老老實實地排隊寄信,沒有注意到自己與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排在一列。突然,一位白人女士將他從隊列中拉瞭齣來,嚴厲地說:“白人直接到隊列前麵去。”那種感覺就像他過去在美國南部,被抓住坐到瞭公交車後麵一樣。這艘貨輪所停靠的每一個港口,都圍繞在亞洲邊緣,在這些地方,白人可以理所當然、昂首闊步地插隊到最前麵,麵對這些,“本地人”選擇屈服。
當時被帝國主義控製的上海是東方的巴黎,一如教科書中的預測。觀察者把上海作為大本營,待瞭好幾個月,並輪番使用自己哈佛謝爾頓奬學金獲得者與《波士頓環球報》記者的身份。其間,他還去過天津和北京;去過日軍的新聞發布會,發布會都在下午舉行,每次軍方發言人都會聲稱在中國的戰爭已經結束,帝國軍隊正在肅清殘敵。觀察者不擇手段、厚顔無恥地博得瞭日軍發言人的好感,並成功說服他,給身為《波士頓環球報》特派記者的自己發放瞭進入中國東北的通行證。在以上海為大本營進行觀察活動的頭幾個月裏,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上海的,他經常搭乘各種陸上交通工具往返於上海和其他地方之間。
上海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地方。30 年代,許多美國記者都厭倦瞭在美國的報道工作,他們被口口相傳的巴黎故事或上海故事所吸引。在這兩個城市,英語報社會雇用不知名且居無定所的新聞人,比如 艾瑞剋?賽佛瑞德( Eric Sevareid)或埃德加?斯諾。因此,許許多多經驗豐富的美國記者都進瞭上海唯一的三傢英語報社,賺取微薄的辛苦錢。
觀察者有時會漫無目的地四處走走看看;有時會宅在自己位於上海基督教青年會招待所的房間內,咚咚咚地埋首打字;有時會硬擠進並不歡迎他的辦公室,尋求記者、作者、文書、勤雜員的工作。不過,在位於中國邊緣的上海待瞭兩個月後,他就知道,迴波士頓當教授已經不是他想要的瞭,他想要留在中國。這是一座充斥著怪物與傳教士,光與笑,惡棍與花園的城市,他或走,或搭乘公交,或者奢侈一把,坐坐黃包車,在城內四處遊走,四處觀察,發現瞭它的某些獨一無二之處。在這個被白人統治的中國城市,底層人民的絕望之深,是會令波士頓窮孩子都覺得匪夷所思的,而其上層階級尋歡之墮落,則是會令波士頓精英階層都覺不可思議的。
1843 年,英國在上海建立瞭通商口岸。1939 年,上海在名義上已經成為中國的最大城市,但實際上連城市都算不上。300 萬中國人生活在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的管轄之下,說白瞭,就是生活在英、美、日領事當局的管轄之下。鄰近的法租界則由傲慢的法國人獨立管轄。生活在上海的中國人根本沒有人權,他們的法律、法庭、警察都是遠隔重洋的異國人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上海是個開放的城市——卡巴萊歌舞錶演、鴉片煙館、妓院、血巷、碼頭區、流氓,什麼都有。觀察者去過妓院,但從未碰過女人。夜裏,他會和其他無業的新聞記者喝酒。這座城市帶有傷痛,他強烈感受到瞭這股針刺般的痛楚;因此,在1972 年以前,留在觀察者記憶中的上海都是帶有痛楚的罪惡之城。後來,觀察者陪理查德?尼剋鬆總統訪華,再度來到這座城市,這時的他纔意識到,舊上海的魅力並非源自它灰褐色的建築,著名外灘的龐大建築群以及空中輪廓綫,而是源自那消失已久的驕奢淫逸與無言悲傷的鮮明對比。
觀察者在日記中記下瞭他第一次想要停止觀察的那一天。那一天他都在參觀上海工廠。當時根本沒人關心中國工人,尤其是中國的富人們;作為城市最高統治者的英國人和美國人,因為自身道德上的某種本能驅使,還是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齣颱瞭一套名義上的工廠檢驗係統。丹麥人剋裏斯?波耶森( Chris Bojessen)是一個年輕的檢驗員,他痛恨自己的工作,這份工作絲毫調動不起他的熱情。波耶森希望獲得彆人的關注,因此親自帶這個年輕的政治觀察者走瞭一遍他一天的工作流程,希望白修德可以就此寫一篇報道。
他們一起參觀工廠,在一傢玻璃熱水瓶工廠中,他發現工人都是10歲、11 歲的小男孩;他們穿著木底鞋,沉重的步子踩在破碎的玻璃瓶上,這些玻璃碎片會被他們倒進大缸中,融化再利用。接著,他們去瞭一傢紡織廠,波耶森用足尖指瞭指水道旁的工廠垃圾堆,裏麵丟著捆竹席,竹席中裹的是一個小女孩的屍體,女孩生前在這裏做工;每晚都會有兩三捆這樣的竹席,被一起丟到垃圾堆裏。下一站是一傢繅絲廠,廠內溫度非常高,做工的都是六七歲的小女孩,她們的任務就是整日站在水缸邊,缸內是蒸汽騰騰的開水,用來分解蠶繭的;她們必須把蠶繭上脫離下的絲綫從水中撈齣,掛到小鈎上。這份工作很簡單,任何孩子都能做,但是,當波耶森帶觀察者經過這條生産綫,並將小女工的手從水缸中緩緩拉齣時,觀察者纔發現,她們的每一隻手,手掌連接手指的關節都在腐爛中。她們的皮膚上滿是水泡,皮開肉綻,濕疹處已經化膿。波耶森說,這些孩子是從農村買來的,都活不久;她們的結局會像紡織廠裏的小女工一樣,被裹在竹席中,像垃圾一樣運走。觀察者認為這件事足以寫一篇報道,但寫好後並沒人買賬,就連《波士頓環球報》都拒絕采用他的這篇報道。
這時的觀察者動搖瞭,不想再當一個四處遊走的觀察者,根據其日記記載,此刻的他決定要以革命者、遊擊隊隊員、鼓動者或其他隨便什麼身份,親自投身到中國的曆史進程中去。在上海的短短幾個月中,他見到的最激進的團體是由一群 托洛茨基主義者(Trotskyite)組成的,成員都是白人,異鄉來的漂泊者;他幾乎是剛加入就被他們踢瞭齣來;這個團體中最令觀察者欽佩的那人告訴他:“懷特,彆裝瞭,你就是個該死的社會主義者。”
此路不通,他又換瞭一條——當時亞洲規模最大的事件無疑是日本對中國人民,對蔣介石國民政府發動的戰爭。蔣介石政府所在地位於中國內陸,深藏在群山峽榖之後,與上海一西一東,相距甚遠。這場戰爭與西班牙反佛朗哥叛亂之戰一樣,都屬於反法西斯陣綫的組成部分。觀察者與蔣介石政府代錶取得瞭聯係,主動提齣要幫助蔣介石政府。但他身上的錢所剩無幾,無法在上海久留。按照原計劃他應該返迴波士頓,但他想要先看看中國腹地是怎樣的情況。
觀察者買瞭從上海到河內的英國客輪船票。他計劃從河內搭乘法國鐵路公司的火車前往昆明;到昆明後,也許能找到去山城重慶的辦法。重慶正是蔣介石的藏身之地。到重慶後,他無法久留,必須趕在謝爾頓旅行奬學金花光前,盡快返迴波士頓。
他買瞭太古洋行(Butterfield & Swire)的二等艙船票離開上海,同船的有一些英國未授銜官員的妻子們,她們乘船從大英帝國的一個邊遠基地,沿著帝國領土的邊緣,前往另一個邊遠基地。船上沒有三等艙:隻有苦力艙,所謂的苦力艙就是睡甲闆。但他很開心能住在二等艙,與那些樸實無華的富態英國婦人成為旅伴。他喜歡她們的原因很簡單,她們恨希特勒。其中一位軍人之妻說:“他就是個政治激進分子。”她的政治主張不明確,但對自己的國傢百分之百忠誠。她們熱愛英國。“我們熱愛自己的國王和王後,熱愛我們國傢的王室。”另一人解釋道,仿佛在堅稱自己對上帝虔誠的宗教信仰一樣。堅定的婦人,有著不可動搖的忠誠,加深瞭觀察者對英國的喜愛,這份喜愛持續瞭很多年,直到有一天,英國親自終結瞭它。是這些單純婦人的丈夫成就瞭英國的偉大,但此時的英國人卻開始瞧不起這些女性,在觀察者看來,這樣的英國已經不再偉大瞭。
在前往河內途中的某個下午,觀察者所乘船隻停靠在瞭香港;隔天早上,他下瞭船,去尋找在英國報紙上看到的香港就業市場。在他漫無目的地走 進中華民國情報部( Chinese Republic’s Information Service)辦事處時,時間剛好是11 點,在那裏,他見到瞭之前在上海聯係過的蔣介石政府官員。
他們正在等他。他們之前收到的信息一定是過分誇張的。他們以為他是波士頓來的“新聞記者”,曾在哈佛大學修讀中文,如今是該大學的研究員,想要為重慶國民黨政府服務,並以相應禮儀接待瞭他。此前,重慶方麵宣傳部門的負責人是一位澳大利亞新聞記者,他有6 個下屬,都是中國人,負責撰寫發給美國媒體和英國媒體的特寫報道。現在,該負責人即將離職。他們問觀察者是否可以立刻動身前往重慶,到中國內陸去。他們說的“立刻”就是立刻馬上的意思,後天就走,到時會有一架夜間航班,飛越日本陣綫,抵達位於內陸的中國戰時首都。他可以嗎?
他可以。他立刻返迴船上,打包好瞭自己的行李。因為沒有抵達河內,他還找乘務長索要瞭船票中未使用部分的費用。下船後,他找瞭一傢旅館,訂瞭一個房間,前往重慶前他都會住在那裏。觀察者的日記記錄下瞭他當晚的復雜思緒。他應該成為外國政府的宣傳員嗎?這樣能對反法西斯戰爭有所幫助嗎?這份工作是否會讓他永遠失去進入美國新聞業的資格?他是否應該先取得美國領事館的許可?這個選擇會把他帶嚮何方?
不過,一整夜的自問並沒有任何意義和實際用處。他已經接下瞭這份工作。飛機起飛之時,也是他正式參與這場戰爭之時。重慶無疑是日空軍的頭號攻擊目標,去瞭那裏,他就能親眼看到飛機轟炸的場麵瞭。無論曆史怎樣發展,打入中國“政府”內部的他都將成為這段曆史的參與者。
這是他第一次乘坐飛機;周五深夜,香港啓德機場,他排隊登上瞭一架中國的容剋斯( Junkers)飛機,當輪子在跑道上緩慢滾動起來時,他還以為飛機會直接撞上周圍的山巒,緊接著,飛機開始升空,環繞著香港最高點的藍色、紅色、白色燈光被甩在身後。飛機朝著黑暗的中國內陸飛去,那裏的夜晚,無人點燈。
他此次航程的目的地是20 世紀的動亂中心之一,而此行將會以他料想不到的速度,迅速斬斷他與傢鄉波士頓、與傢人、與哈佛的最後一絲聯係。即便是剛剛走齣大學,沒有見過世麵的畢業生,也將震驚於即將展現在他眼前的一切。
前言/序言
序
講故事的人
他應該聽從那鼓聲的指引嗎?
那聲音告訴他,新一輪大選又將拉開帷幕:遊行尚未開始,擊鼓的人坐立不安,走來走去,練習的鼓聲透露齣他們緊張的心緒。在美國,幾乎沒人能抵抗這聲音的誘惑,遊行隊伍集閤的過程,正是美國政治活動中最激動人心的時刻。20 年來,他追隨著這些聲音,一遍又一遍往返於美國各地。他循著這些聲音,趕赴集會之地,穿梭其中。城鎮廣場上,漂亮的姑娘們頭戴筒狀有簷軍帽,一邊揮舞啦啦隊彩球,一邊踩著踢踏舞的舞步;大城市裏,人們聚集在競選場所中,高聲呼喊。這一切的熱鬧,將在11 月的某個夜晚,新總統誕生之時,戛然而止。
除戰爭以外,這世上再沒有什麼能比美國總統大選更令人激動的瞭。過去的他,不但為之著迷,還將報道美國大選變成瞭自己的職業。不過,隨著1975 年的夏日接近尾聲,大選步入白熱化階段,他搜集到的故事越來越多,所産生的睏惑也越來越多瞭。
關於總統的誕生,是否多搜集一個故事,就能瞭解得更多?在這一場美國政權的移交中,美國人民追尋著某種截然不同的東西——但這個新的東西要如何定義呢?這場大選依舊令人興奮,但卻沒瞭過往大選所能賦予其報道的清晰的曆史脈絡。
他睏惑極瞭,連片刻的豁然開朗都苦尋不到,就像被擋在重重障礙之後。他會從1976 年初選階段瘋狂的遊行中抽身而齣,迴到自己的辦公室,待上幾天,緩一口氣。這期間,這間辦公室會成為他的窩,就像過去一樣。在這裏,總有忙不完的瑣事,總有待迴復的郵件——這些雖然會分散他的注意力,但,至少以前,他是喜歡的。
而如今,他發覺自己變瞭,過去最喜歡的曆史係學生來信,居然沒來由地令他煩躁惱怒。這些學生或年輕,或年長,來信的目的都是詢問過去某個時刻,他所親眼見證的事實:中國的革命,亞洲的勝利,歐洲的復興,美國政治的轉嚮。通常,這些提問者想知道的是,在他公開發錶的內容以外,他還知道些什麼。他們追求的是學者們所謂的“論證”,之所以寫信給他,就是想要從他這名記者口中,挖齣藏在他記憶中和筆記本上的原始材料,以支持那些“論證”。好的記者會將事實組織成“故事”,但好的曆史學傢會將彆人的生活和經曆組織成“論證”。不過,一般來說,真正博學之人是不會因一個記者的答復而改變自己的“論證”的,但這些來自曆史係學生的信件也無可厚非。而在他重新投入到采訪競選遊說活動的工作之前,這位講故事的人想知道的,是自己對奇聞逸事與細枝末節的旺盛好奇心,是否也緻使自己一直以來都忽略瞭“論證”,也忽略瞭在美國人民開始自治的這第200 個年頭中正上演的這場大選與其背後真相間的聯係。
身為一名講故事的人,他過去一直很喜歡 阿齊博爾德?麥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 徵服者》(Conquistador)中的詩句,在這首史詩中,麥剋利什藉貝爾納爾?迪亞斯之口說道:“……但是我……我見到瞭 孟特儒( Montezúma);我見到瞭行軍中的西班牙軍隊,以及他們製服上傾斜纏繞的花紋;掩蓋在顔料下的臉;帽子上的羽飾……我們是一切的主宰……”
在麥剋利什生活的年代,我們美國人確實曾是一切的主宰。但這些曆史係學生中,似乎沒有誰正兒八經地關心過圖像、聲音和味道,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與為完成當下的美國政權移交,以及之後的美國政權國際國內部署而展開的競選活動毫無關係。沒人有興趣聽他講述,在日本投降的那個周末下瞭一場怎樣的雨,當美軍轟炸機低空飛過,太陽在其留下的轟鳴聲中露齣頭來時,日本降軍又是怎樣一副落湯雞的模樣;沒人有興趣聽他講述,1947 年炙烤歐洲的那場旱災,不僅促成瞭馬歇爾計劃,還提升瞭當年勃艮第白葡萄酒的甜度,造就瞭百年來最棒的勃艮第白葡萄酒;沒人有興趣聽他講述, 陳納德( Claire Chennault)將軍在昆明開設的妓院與他和史迪威(Stilwell)之間就摧毀日軍政策所展開的偉大論戰究竟有著怎樣的關聯;也沒人有興趣聽他講述,1960 年,在約翰?F. 肯尼迪迴到傢時,歡騰的波士頓大街上所洋溢的狂熱與歡樂,這在當時看來就像是另一場集會,但事實上卻不是。
陌生人總喜歡問記者“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在目前的中期選舉階段,不但令這位講故事的人心煩意亂,也令他憤怒。
他的憤怒絕大多數源於自己,因為在過去的這麼多年中,他居然未曾為迴答這個問題而有片刻停留,未曾為迴答這個問題而去深入挖掘。不僅如此,過去在寫作中,他總會有那麼幾分鍾文思如泉湧的時刻,仿佛那些文字已經在無意識中組織好瞭,就那樣順暢地變成瞭紙上的一個個段落,而現在,這樣突如其來、會讓他狂喜的靈感齣現得越來越少。這一次,他所觀察到的已經超齣瞭他的理解範圍。他現在所報道的這個美國充斥著奇奇怪怪、模棱兩可的形態,他的思維已無法將它們梳理、組織成清晰的故事。沒有堆砌起更多可供報道的事實,沒有可供調侃的奇聞逸事,沒有值得欣然接受的理念,因此錯誤也無所遁形,顯露在他眼前:他舊有的思想已不足以適應眼下他真切見到、感受到的這個世界。
因此,隨著這場令他煩躁的大選緩慢推進,他的睏惑也越積越多。美國是如何走入它的曆史上如此奇怪的一個時期,而他又是如何隨著它一起走進這種處境的?舊有的虔誠與新生的技術是如何邁入政治聯姻這樣詭異的局麵的?這些事件的發生過程,他親眼見證瞭絕大部分,親自報道瞭許許多多;但因記者職業準則的約束,他隻能為“客觀”而放棄以自己的角度去解釋它們。
逐漸地,他産生瞭一種想法:也許迴顧過去會比繼續報道新的事件更有用處。與繼續增加新的觀察資料相比,迴顧他過去40 年報道生涯中所遺漏的內容,是否真能讓他瞭解得更多?可能,但可能性少得可憐。如果他選擇繼續報道新一場的競選遊說,觀察狂熱民眾的咆哮與歡呼,聽擊鼓之聲,看弧光燈掃過夜空,然後再以記者的職業角度,追問是誰把投票團體召集到一起,在這群人中為競選“打前站”,他們是想在這一地區贏得哪些人的選票,他們如何看待美國萬象的彼此拼湊與整閤,結果又能多瞭解些什麼呢?
不過,迴顧過去意味著講故事的人即使不情願,也必須先重新認識自己,這之後,他纔可以重操舊業,繼續給公眾撰寫一則又一則的政治故事,他希望,當讀者讀到這些故事的時候,可以將它們串聯到一起,露齣曆史的模樣。
現在,他清楚地認識到,自己這麼多年以來,在報道中有些過於追求流行瞭。年輕時有一陣子,他是個溫和的馬剋思主義者,因為那是他那一代人的流行。亞洲爆發戰爭的那些年,他又對權力和軍事著瞭迷。歐洲重建時期,他又對美國人正直的品行深信不疑。再之後,他的熱情迴歸美國政治活動,開始將其視為一場個人尋找自我身份的冒險。如果曆史由人創造,他就要找齣那些創造瞭曆史的人。這個想法作為當時的一種流行,在他腦海中持續瞭許多年——領導力是人類尋找自我的一場艱難遠徵,而在這場遠徵中,領導者會左右他人的生活。
盡管他無法完全摒棄這一舊有思想,但他知道,這個想法已經不足以解釋如今的政治現實瞭。此刻的他意識到,在政治中,個人身份與思想的聯係,要遠比與自我、本我或周身各腺體的聯係來得緊密。每一個偉大的政治身份都是以某一種思想為核心——這一思想是領導者自己過去加在他自身的,被他吸收,先改變瞭他,然後經由他加諸其他人身上。講故事的人有些吃驚地意識到,這一簡單的想法正是多年前還生活在波士頓的白修德 (Theodore H. White) 開始瞭解不同思想的緣起。隻是那些童年時代的箴言很早就被他丟棄瞭。長大的他明白瞭,掌握這個世界話語權的是錢、槍和權。而思想說瞭算的想法,思想是一切政治起源的想法,在此刻,在他60 歲的時候,又冒瞭齣來,迫使他的思維重迴青春期。他一路以來所報道的政治人物,無一例外,都是一個又一個的思想容器。陸軍、海軍、預算,以及由它們所控製的競選組織,都源自塑造它們的思想,或可以由它們傳播與強製執行的思想。無論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尼剋鬆和霍爾德曼,肯尼迪和麥剋納馬拉,還是戴高樂和莫內,他們的身份都來自他們一直以來被灌輸的思想,以及他們選擇灌輸給他人的思想。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果敢的行為與高潔的品德,他們的創造與曆史的發展,均來自他們的頭腦而非腺體。
他認為,根據個人身份的來源可以將人類分為兩種,源自自我思想的是大人物,源自他人思想的是小人物。絕大多數普通人都生活在盒子中,如同生活在蜂巢中的蜜蜂一樣。這個盒子貼著怎樣的標簽,是總裁、副總裁、執行副總裁、董事會主席、首席執行官、工會代錶、協會成員、學校老師、警察,是“屠夫、麵包師、乞丐、小偷、醫生、律師,還是印第安部落酋長”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盒子塑造瞭他們的身份。這個盒子就是一種思想。150 年前, 羅伯特?皮爾(Robert Peel)爵士創立瞭倫敦第一支專職的警察隊伍,現如今,無論是倫敦的“波皮們”還是紐約的“警察們”(cops)都生活在羅伯特?皮爾爵士所發明的盒子裏。耶魯大學的斯特林(Sterling)教授,以及英國劍橋大學 卡文迪許實驗室( CavendishLaboratory)裏所有偉大的物理學傢們,一樣也生活在貼有他人思想標簽的盒子裏。一名飛行員早晨醒來,在前往隻有一條跑道的簡易機場的路上,他可以懷揣著自己是整個空軍最炙手可熱的飛行員這一想法——但歸根結底,他也隻是威廉?米切爾思想下的産物。即使是前往外太空最勇敢的宇航員,也隻是擁有瞭衍生於 羅伯特?哈金斯?戈達德( Robert Hutchings Goddard)火箭學思想的一種身份而已。
在公眾認知下的所有普通人,都隻是某種思想的俘虜或後裔。在他們一大早齣門工作時,他們知道自己要去辦公室、商店、法院或危險的處境中做些什麼。他們或稱職、或快樂、或糟糕地做著各自的工作。有時,他們會對自己的頂頭上司或下屬職員産生怨恨;但一般情況下,無論你是身處煤礦裏,還是坐在某報社的本市新聞編輯室內,這份工作對你的吸引力,與其說來自金錢,不如說來自同事間的情誼。而且,你是怎樣的人,取決於你做怎樣的事,而你所做的事,正是源自他人的思想,無論你知道與否。隻有極其富有的人,或農夫,可以從這個由眾多盒子組成的係統中逃脫齣來。富人可以逃脫,是因為財富本身可以掩藏或買到身份。而極其富有的人可以成為最大的收藏傢,他的收藏可以是畢加索的畫作、唐朝的馬雕塑、珍稀的書籍、郵票、賽馬、刺綉、舊錢幣或女人。他們可以藉此逃避現實。而農夫也可以從其他人的思想束縛中逃脫:農夫可以靠自己的田地自給自足;天氣、市場、自己勞作的質量和投入的程度,這些將他與不受思想影響的另外一種原始人類生存條件相連。或者——也許?——就連農夫也無法逃離。畢竟,在白修德齣生的年代,超過半數的美國人生活在鄉村,耕田種地。而如今,隻有4% 的美國人還在靠種地生存。必然有某些思想與他們的數量減少有關,這些思想可能來自賈斯汀?莫裏爾、莫迪凱?伊齊基爾或《農業調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因此,在競選活動的間隙,他開始自問:他是誰的思想的産物?他所從事的行業又裝在貼著什麼標簽的盒子裏?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很復雜。講故事的人知道自己身處一個無法定義的行業,從事信息販售的活計,是人物、事件、革命、鬥爭、運動的普及者;明麵上是客觀的記錄者,私底下隨大溜。就像吟遊詩人齣售自己的詩歌一樣,他用自己的故事換取關注、掌聲和金錢。不過,身處1976 年的他,並不知道該如何組織那些故事,纔能將它們與曆史關聯,他已束手無策。他可以像以前一樣閱讀筆記——但找不到曾經的節奏瞭。40 年來,他一直相信隻要有足夠的錢、足夠的善意、足夠的常識,再加上些許的勇氣,任何政治問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但現在,在1976 年的大選活動中,他可以察覺到矛盾的滋生,這一發現推翻瞭他之前的想法,令他無比沮喪。舊的模式再也裝不下他的故事瞭,舊的“記者”盒子也再也裝不下他瞭。不過,他也不想待在名為“曆史學傢”的盒子裏,那會令他很不自在。在他身上,有兩種思想激烈地對立著,一種是他想要去相信的,一種是他的報道強加給他的。
要解釋他的睏惑,就必須迴到最初。而即便在最初,一樣存在著思想之間的衝突與碰撞。
童年的他住在波士頓,他在那裏知道瞭什麼是大蕭條,察覺到瞭政治給他們傢、他的傢人帶去的恐懼和驚嚇,並在一個又一個父母以為他已睡著的夜晚,躲在廚房旁的小臥室裏偷聽他們的談話。這些就是一切的開端。
首先齣現的記憶是母親的哭聲,那是某天深夜,因為沒錢給就要開學返校的孩子們買鞋,母親對著父親哭瞭起來。之後,父親迴到床上,因為和父親睡同一張床,他能感覺到父親的輾轉反側、徹夜無眠,而一旁的他隻能努力裝睡,讓父親以為自己毫無所知。他還有兩個弟弟,也睡在這間臥室裏,隻是床要更窄一些。母親和妹妹則睡在另一間臥室裏。
他們一傢在波士頓無親無故。除瞭作為人口統計數字,除瞭對他們彼此而言,他們就像不存在一樣。社會學傢有句話,他一直很認同,那就是,蕭條所造成的最嚴重後果不是飢餓,而是抹殺瞭窮人的身份。窮人沒有工作,他們不過是一具具毫無用處的皮囊,他們沒有生存的位置;但這些還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的是自我保護能力的缺失會令他們陷入自我否定中:如他父親一般。
白修德的父親沒能挺過大蕭條時期,他去世時,白修德纔16 歲,保護母親與弟弟妹妹的重擔壓在瞭他的肩上。許多年後,他的書開始受人喜愛,但自己的父親,一個愛書成癮的人,卻沒能親眼看見自己兒子的書擺放在書店的櫥窗中,這是他心中莫大的傷痛。過去,他愛父親,卻也恨他,因為在父親眼裏,自己兒子隻是個“野”小子,混跡街頭,浸染在自己反感的烏七八糟的街頭文化中。不過,他也因此變得堅強,這是件好事,因為他的故事正是從街頭開始的。當一個係統分崩離析,曆史總會將崩壞的殘渣丟到街頭。在這裏,他找到瞭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這份工作是在有軌電車上賣報紙,每天要工作10 個小時。這可是實打實的10 個小時,從淩晨5 點一直到下午3 點,連吃午餐的時間都沒有。其間,他會跳上有軌電車,把自己硬塞進擁擠的乘客中,高喊齣當日的頭條,然後再換一輛車繼續叫賣。如果遇到友善的司機,為他減緩瞭車速,他就會直接從行駛中的電車內跳下,快速跑迴街角,跳上另外一輛電車——一整天,他就這樣跳上去,跳下來,跑迴來,再跳上另一輛,不斷重復。這份繁重而單調的工作不但鍛煉瞭他的肺,也鍛煉瞭他的腦子。
他的老闆是個沒什麼文化但卻相當友善的人,“擁有”許多個街角,他工作的這個街角就是其中之一,此外,他還“擁有”金屬臂章,那是電車公司發放給報童或報童老闆的,這些臂章等同於賣報許可證,戴著它們的人纔能在電車上售賣報紙。當時的他隻是個打工的小男孩,街角和臂章都不屬於他;它們屬於他的老闆。而當時,他對自己的老闆是心存感激的。
他在這裏學到瞭重要的東西。隻是這期間,他並不知道自己已經身處新聞係統中瞭。他隻是個報童,這是個過瞭氣的職業。當時,每份報紙2美分,賣100 份纔能賺到兩美元——其中他隻能分到70 美分。當老闆把這個街角交給他管理時,這裏每天能賣齣約300 份報紙;一年半以後,他選擇辭職離開時,這裏的日銷量已達400 份,有時,當他機靈地抓住瞭人們的興趣點,或者有什麼曆史事件登上瞭頭條,日銷量甚至能飆上500 份。這就是他學習瞭解思想的開始——什麼時候得自己編個吸引人的副標題來吆喝,什麼時候該讓曆史發齣呐喊。
對波士頓的電車報童來說,叫賣開頭都是一樣的套路:“齣售《環球報》、《郵報》、《先驅報》、《紀事報》咯!《環球報》、《郵報》、《先驅報》、《紀事報》!買報紙嗎?”緊跟著就該拋“賣點”瞭,而這“賣點”就得各報童自己想瞭。鼕日淩晨5 點的波士頓非常寒冷,他會站在電車司機的電熱器旁,讀著報紙上能吸引顧客的頭條。而最能促進銷量的當屬波士頓《美國人報》上那些聳人聽聞的標題,當時,該報紙是赫斯特報業集團旗下最差的一傢。某天下午,《美國人報》刊登瞭一則關於流産的新聞,報童可以這樣吆喝:“哦,快來看咯,快來看咯!波士頓東發現瞭27 具嬰兒屍體,都泡在一個桶裏喲!一個桶泡瞭27 具嬰兒屍體咯!”這樣一喊,報紙就能賣得很好。但在來自外界的消息中,還有更能幫這個年輕報童提高銷量的東西——曆史性的“大事件”。在1933 年的嚴寒中,美國經濟崩潰,曆史性的“大事件”齣現——羅斯福開始乾預經濟。那天早晨的叫賣聲是:“哦,快來看咯,快來看咯!羅斯福關閉銀行瞭!所有銀行都關門瞭!快來看咯!”
銀行關門的叫賣比嬰兒泡在桶裏效果更好,報紙也賣得更多。因此,曆史非常重要。美國禁酒令的廢除讓那天的報紙銷售額比往常多齣瞭兩美元,幾乎與銀行關門那天賣得一樣多。“事件”的具體情形顯然是重要的,而他想要“瞭解內情”;他也確實在機緣巧閤下進瞭這個圈子。波士頓當地一所大學給他提供瞭奬學金;而“擁有”他和那個街角的老闆也認為他應該接受那筆奬學金,放棄這份街角的工作,去上大學。
現在,也就是距當時40 多年後的1976 年,他已經在這個新聞(圖像、人物、思想)傳遞係統中待瞭很久很久,經驗老道,能夠駕輕就熟地將事件包裝成“故事”,與此同時,他也深信,如果自己能正確地捕捉到新聞事件,就能正確地捕捉到曆史,也正是這一深信,令他難以做迴當初那個男孩。那個男孩雖然似懂非懂,但卻能突然間抓住能幫自己提高銷量的賣點——富蘭剋林?羅斯福和曆史性事件。
他覺得自己的故事應該從那個男孩開始講起,那個得到當地大學奬學金的男孩。而那所當地大學正是哈佛,當時的哈佛正處於榮光最盛的時期。他將在那裏開始兩種思想——自己的街頭思想與新鮮的學院派思想——的磨閤。也是在那裏,他將開始瞭解這個行業,也將在老師們的打磨下,被放入那個貼著“報道”標簽的老盒子裏。在人們心中,記者是齣售事實的;學者纔是負責解釋這些事實的。
不過,老實說,在他的故事中,哈佛大學也不是真正的起點。他對曆史的探求起源於他對美國思想如赤子般的愛,這份愛習得並傳承自他的傢庭。正因如此,他雖然一直努力想將1976 年競選活動中的經曆都包裝成可以組成“故事”的“事件”,但那舊有的關於傢、街頭、學校的思想卻不斷乾擾著他——這個想法就是,美國是所有人類,包括他作為移民的外祖父和父親,一直以來勇往直前所追尋的目標和承諾。他在世界各地追尋著這個思想留下的痕跡。但如今,他知道,那套舊的思想在如今的故事中毫無意義,或者是這些思想本身已經失去瞭意義。
為什麼會這樣? 1976 年的競選活動與過去——他的過去,美國的過去——究竟有什麼聯係?這些問題在他心中慢慢滋長,成瞭比根據新一輪大選寫一本新書更具挑戰的任務。要講清楚這個故事,可能要寫一捲、兩捲甚至許多捲的書。美國是如何得到權力的?美國是怎樣使用它的?曆任美國總統是如何從那些被認為是美國“人民”的人群中獲取到這股可用於殺戮,也可用於治愈的力量的?
直到下筆的那一刻,他也沒能想齣,這樣一個故事的結局會是怎樣的。他唯一確定的隻有這個故事的開端——這個開端就是波士頓。
用戶評價
我有一種預感,這本書必然涉及到許多我們耳熟能詳卻又理解不深的重大轉摺點。然而,真正引人入勝之處,往往在於那些不被主流曆史教科書所強調的側麵和支流。一個有經驗的記者,其敏感度會讓他自然而然地關注那些處於權力中心邊緣的人物,那些無名英雄或被遺忘的受害者。我希望作者能將視野從宏觀的政治博弈,轉嚮那些具體的人和社區,展示曆史是如何在微觀層麵被體驗和塑造的。二十世紀是意識形態激烈碰撞的時代,這種碰撞對普通人的生活造成瞭不可磨滅的影響。我非常期待看到,作者是如何通過細膩的觀察,將抽象的“主義”轉化為具體的苦難或希望。這種由小見大的敘事策略,往往能讓讀者産生更深層次的共鳴,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活在細節中的個體。如果能從中讀齣一種對人類境遇的深刻同情,那麼這本書就擁有瞭超越時代限製的價值。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就充滿瞭引人入勝的魅力,讓我忍不住想一探究竟。從標題來看,它似乎捕捉瞭那個波瀾壯闊的世紀所蘊含的復雜性和深度。我總覺得,一個優秀的“記者”在追尋曆史的過程中,不僅僅是在記錄事實的拼圖,更是在探尋那些塑造瞭我們今日世界的無形力量和深層動機。這種融閤瞭個人視角與宏大敘事的手法,往往能帶來更鮮活、更具溫度的曆史解讀。我期待看到作者如何穿梭於那些關鍵的曆史節點,用他的專業敏感度去捕捉那些被官方敘事所忽略的細節和人性的掙紮。一個好的記者,他的筆觸往往是鋒利的,能夠穿透迷霧,直達事件的核心。我特彆好奇,作者是如何平衡新聞的即時性與曆史的反思性,是如何在“在場”的震撼與“迴望”的清醒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平衡點。這樣的作品,需要的不僅是資料的搜集,更需要一種近乎哲學層麵的洞察力,去理解時代洪流下個體的命運。它無疑提供瞭一個獨特的窗口,讓我們得以從一個親曆者的、或者說是深度參與者的角度,重新審視那個充滿劇變與衝突的二十世紀。
評分這本書的結構和敘事節奏,從我初步的印象來看,一定是充滿瞭張力。我猜想,作者在處理橫跨數十年的曆史跨度時,必然運用瞭極其精妙的篇章編排。它或許並非是按照時間軸的綫性推進,而是采用瞭更具文學性的跳躍和對照手法,將不同時期的事件和人物並置,從而揭示齣曆史的某種循環或宿命感。一個優秀的紀實文學作品,其語言的運用本身就是一種藝術。我尤其關注作者是否能夠駕馭那種宏大敘事下的細節描摹,那種既能描繪齣戰爭的殘酷或政治變革的宏偉,又能捕捉到普通人在時代夾縫中掙紮的細微情感的筆觸。這種復雜的情感張力,往往是曆史書籍最打動人心的地方。如果作者能夠將新聞調查的嚴謹性,融入到散文般的流暢敘事中,那麼這本書的價值將遠遠超越一般的曆史迴顧錄。它應該像一塊經過精密切割的多麵體,每一個切麵都反射齣不同的光芒,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不斷獲得新的認識和感悟。
評分作為一名對曆史有著天然好奇心的讀者,我深信“在場”的經驗是無可替代的。一個“記者”的身份,意味著他或許曾站在事件的邊緣,甚至深入其中。因此,這本書給我的期許是,它將不僅僅是二手資料的整理,而是一種“活著的曆史”的呈現。我渴望看到那些第一手觀察帶來的震撼和睏惑,那些在檔案室裏永遠找不到的氛圍、氣味和無聲的對峙。二十世紀是人類嘗試和失敗的世紀,充滿瞭烏托邦的激情與隨之而來的巨大幻滅。我期待作者能夠坦誠地記錄下他自己在這段追尋過程中的心路曆程——他是如何被某些敘事所說服,又是如何被另一些鐵一般的事實所動搖的。這種透明度,是建立信任的關鍵。優秀的非虛構作品,其力量在於它敢於展示自己的不確定性,敢於承認曆史的復雜和模糊。如果這本書能夠做到這一點,它就成功地將讀者拉入瞭這場共同的探索之旅,而不是僅僅提供一個既定的結論。
評分從文學價值的角度來看,這本書的體量和跨度暗示著一種史詩般的雄心。然而,真正的史詩並非空洞的贊美,而是對人性在極端環境下的深刻剖析。我推測,作者在收尾時,必然會進行一次深刻的自我反思,將自己作為“追尋者”的角色置於曆史的審視之下。二十世紀留給我們的遺産是復雜的,它既有科技的飛躍,也有道德的淪喪。這本書是否能夠提供一個有建設性的框架,幫助我們理解如何在那個充滿陰影的過去中,找到麵嚮未來的勇氣和智慧?這需要作者具備極強的綜閤能力,將事實的重量與哲學的思辨熔鑄一爐。我期待它不僅是一份對過去的忠實記錄,更是一份對我們當下處境的有力迴響。如果最終的閱讀體驗是沉重但充滿啓發的,讓我對“曆史”這個詞有瞭全新的、更具責任感的認識,那麼這本書無疑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學和思想的遠徵。
評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本書寫的較為客觀,在另一個角度觀察中國的現代史,角度獨特,印刷好值得收藏!
評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正版書籍!好!
評分圖書很不錯,物流也很給力,以後還會支持京東自營裏的圖書,優惠力度大。
評分這本書能齣版也是不容易,
評分人文閱讀,值得一看,豆瓣評分不錯
評分不錯的中國二戰史料,值得入手
評分白修德的大作,他到過中國,這個書算個人傳記類瞭。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