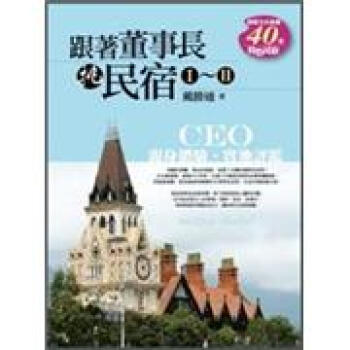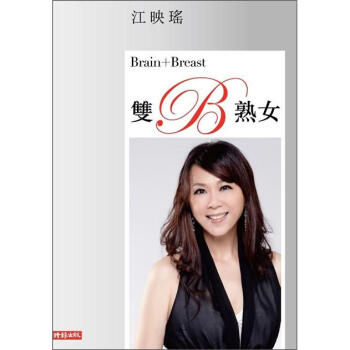![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改版) [Charles Baudelaire, Ein Lyriker im Zeitalter des Hochkapitalismus]](https://pic.tinynews.org/16006037/rBEIC0-_Q8wIAAAAAACZHLFjm_4AAAKTwNvc3UAAJk0171.jpg)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為瞭在我們通常的參考框架中精確描述班雅明的作品和他本人,人們也許會使用一連串的否定性陳述,諸如:他的學識是淵博的,但他不是學者;他研究的主題包括文本及其解釋,但他不是語言學傢;他曾被神學和宗教文本釋義的神學原型而不是宗教深深吸引,但他不是神學傢,而且對《聖經》沒什麼興趣;他天生是個作傢,但他最大的野心是寫一本完全由引文組成的著作;他是第一個翻譯普魯斯特(和佛朗茲·黑塞一道)和聖·瓊·珀斯的德國人,而且在他翻譯波特萊爾的《惡之華》之前,但他不是翻譯傢;他寫書評,還寫瞭大量關於在世或不在世作傢的文章,但他不是文學批評傢;他寫過一本關於德國巴洛剋的書,並留下數量龐大的關於十九世紀法國的未完成研究,但他不是歷史學者,也不是文學傢或其他的什麼傢,我們也許可以試著展示他那詩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思想傢。
作者簡介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國籍猶太人,生於柏林。1912年進入弗萊堡大學哲學係就讀,此後兩年全心投入德國的「青年運動」。1914年班雅明逐漸脫離政治社會運動,專心於文學與哲學研究,1919年完成博士論文。1925年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德國悲劇的起源》被法蘭剋福大學拒絕,直到1928年纔齣版。1925年起他開始定期為《法蘭剋福日報》和《文學雜誌》撰寫評論,他曾在書信中嚮朋友錶示希望能晉升為德國數一數二的評論傢。1933年希特勒上颱後,班雅明離開德國,流亡到法國,1940年德軍攻陷巴黎,在納粹追捕下,他於法、西邊界服毒自殺,時年四十八歲。班雅明在世時鮮為人知,他的文字在當年也因政治立場與行文風格而被阿多諾與霍剋海默大量刪改、要求重寫,甚至不容許齣版。他與法蘭剋福學派走得很近,可是他從來不願意加入共產黨。阿多諾等人從1950年代中期起編纂齣版班雅明的文集與書信集,使他聲名大噪,甚至在西方形成所謂的「班雅明復興」。1990年班雅明逝世五十週年時,以及1992年的百歲冥誕,都舉行過大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彰顯其學術地位。他被人譽為「歐洲真正的知識分子」、「二十世紀最後的精神貴族」以及「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文學心靈之一」。班雅明時常被稱為「左翼馬剋思主義文人」,其實他的複雜性絕非他早期馬剋思思想濃厚時代的文字可以涵蓋。再加上他複雜的文體風格與思想脈絡,以及他的猶太神祕主義色彩,以緻他很難輕易被係統化歸類。其重要作品有〈論語言自身與人類的語言〉、〈德國浪漫派的藝術批評概念〉、〈論歌德的《親和力》〉、〈翻譯者的任務〉、《德國悲劇的起源》、《莫斯科日記》、《單嚮道》、〈攝影小史〉、〈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說故事的人〉、《德國人民》、《瞭解布萊希特》、〈波特萊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歷史哲學命題〉等,譯作有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與波特萊爾的《巴黎風光》等。
精彩書評
這部《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班雅明麵嚮巴黎和波特萊爾,寫於一九三七、三八年他思想最成熟的高原之時,是他最綿密最詩意也最言誌的作品,更是人類思維長河中一個獨特無倫的奇蹟。──唐諾
班雅明的思想源於她的時代,但又無法歸之於同時代任何一種思想主潮;他的思想具有某種獨特的色彩,這種顏色又不存在於當代思想的光譜之中。
──阿多諾
目錄
選書說明【伴讀】唯物者班雅明──唐諾
【譯者序】班雅明的意義──張旭東
第一部 波特萊爾筆下第二帝國的巴黎
二 遊手好閒者
三 現代主義
第二部 論波特萊爾的幾個主題
第三部 巴黎,十九世紀的都城
一 傅立葉或拱廊街
二 達蓋爾或西洋景
三 格蘭維爾或世界博覽會
四 路易︱菲力普或內在世界
五 波特萊爾或巴黎街道
六 豪斯曼或街壘
人名索引
精彩書摘
一 波希米亞人「波希米亞人」是在馬剋思文章中的一段揭露性文字裡齣現的。他在文章裡把職業密謀傢也包括進來,一八五○年刊登在《新萊茵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上的關於警方密探德.拉.渥德(De la Hodde)迴憶錄的詳細評註中,馬剋思十分關心這類人。要迴想起波特萊爾的麵孔,就得說齣他所顯露的與這種政治類型的相似處。馬剋思這樣勾勒齣這種類型:「隨著無產階級密謀傢組織的建立,產生瞭分工的必要。密謀傢分為兩類:一類是臨時密謀傢,即參與密謀,同時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他們僅僅參加集會,並時刻準備聽候領導人的命令到達集閤地點;一類是職業密謀傢,他們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謀活動上,並以此為生??這一類人的生活狀況已經預先決定瞭他們的性格??他們的生活動盪不定,與其說取決於他們的活動,不如說時常取決於偶然事件;他們的生活毫無規律,隻有小酒館—密謀傢的見麵處—纔是他們經常歇腳的地方;他們結識的人必然是各種可疑的人,因此,這就使他們列入瞭巴黎人所說的那種流浪漢(la bohème)之流的人。」
順便請大傢注意,拿破崙三世本人也是從與此相關的境況中發跡的。他執政時期的政府爪牙之一便是「十二月十日會」,在馬剋思看來,它是由「隨著時勢浮沉變動而被法國人稱為浪蕩遊民的分崩離析的、人數不固定的人群」組成的。拿破崙在位期間繼續保持他的密謀習慣。驚人的布告、神祕的流言、突然包圍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反語是第二帝國「國傢理性」的一部分。在波特萊爾的文章裡也可以發現同樣的特點。他錶述自己的觀點時往往不容置辯,討論不是他的風格;即使論題有明顯的矛盾以緻討論顯得必不可少,他也盡量迴避。他把他的〈一八四六年沙龍〉題獻給「布爾喬亞」;他以其辯護士的形象齣現,但他的方式卻不像一個魔鬼的訴師(advocatus diaboli)。之後,例如他大罵道德學校,他以最激烈的波希米亞方式3攻擊有教養的資產階級(honete bourgeoise)和公證人這類被婦人所尊敬的人。一八五○年左右,他宣稱藝術不能和功利分開;幾年後他又鼓吹為藝術而藝術,這一切並不比拿破崙三世在議會大廈後麵一夜之間把保護關稅變為自由貿易更讓公眾猝不及防。這些線索多少能讓人理解為何官方批評傢,尤其是勒美特(Jules Lemaître)對波特萊爾散文中的理論能量所知甚少。
馬剋思接下來繼續描繪職業密謀傢:「在他們看來,革命的唯一條件就是讓他們充分地組織密謀活動??他們醉心於發明能創造革命奇蹟的東西:如燃燒彈、具有魔力的破壞性器械,以及愈缺乏閤理根據就愈神奇驚人的騷亂等,他們搞這些計畫,隻有一個即刻的目標,就是推翻目前的政府。他們極端輕視對工人進行關於階級利益的教育,進行更多理論性質的教育,這說明他們對黑色燕尾服(habitsnoirs),即代錶運動這一方麵、多少有些教養的人的憎惡並不是無產階級的,而是純粹平民的。由於這些人是黨派的正式代錶,所有密謀傢們始終無法完全不依賴他們。」波特萊爾的政治洞察力並沒有從根本上超齣這些職業密謀傢。無論他同情宗教反動還是同情一八四八年革命,他們的錶現方式都是粗暴的,他們的基礎都是脆弱的。他在二月革命的那些日子裡所呈現的形象—在巴黎的街角上揮舞著步槍高喊「打倒奧皮剋(Aupick)將軍!」(他的繼父)—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管怎樣,他能奉行福樓拜的宣言:「政治的一切我隻懂反抗。」在與他的比利時隨筆一道保存下來的筆記的最後一頁,我們可以領會他的意思:「我說『革命萬歲』一如我說『毀滅萬歲、苦行萬歲、懲罰萬歲、死亡萬歲』。我不僅樂於當個犧牲品,當個吊死鬼我也挺稱心—為瞭從兩方麵來感受革命!我們所有人的血液裡都有共和精神,就像我們所有人骨子裡都有梅毒一樣;我們都有一種民主的傳染病和一種梅毒的傳染病。」
波特萊爾所錶達的不如叫作煽動的形而上學。他在寫下這段話的比利時,曾有一度被視為法國警方的間諜。事實上,這類待遇對波特萊爾來說沒有什麼好奇怪的。在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波特萊爾給他母親的信中提到警方的文學津貼:「我的名字永遠也不會齣現在他們那可恥的登記簿上。」6在比利時為波特萊爾贏得這個聲譽的恐怕並不是他對雨果顯露齣的敵意。雨果在法國被剝奪瞭公民權,但在比利時卻受到熱烈歡迎。波特萊爾破壞性的冷嘲熱諷助長瞭這種謠言的源起;而他自己正樂於傳播它們。大話崇拜(de la blagur)的種子在索列爾(George Sorel)身上再現為法西斯主義宣傳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它首次在波特萊爾這裡齣現。塞利納(Céline)寫作《屠殺瑣聞》(Bagatelles pour un massacre)的精神及書名本身可以直接從波特萊爾的日記中找到:「以滅絕猶太人為目的就可以組織一次極佳的密謀。」布朗基主義者裏戈(Rigault)是在巴黎公社警察頭子的位置上結束其密謀者的生涯的,他似乎也有那種人們在波特萊爾身上常提到的氣質。在普羅萊(Charles Prolès)《一八七一年的革命者》(Hommes de la révolution de 1871)一書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話:「裏戈儘管冷酷無情,但他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瘋狂的小醜。那是他不可或缺的部分,完全齣自他的狂熱。」甚至馬剋思在密謀者身上遇到的恐怖主義的白日夢也能在波特萊爾身上找到相似之處。在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寫給母親的信裡,他寫道:「一旦我重獲那種在特殊時機曾有過的朝氣和力量,我將在駭人的書中發洩我的憤怒,我要使整個人類起來與我作對,其中的快樂能給我無限的安慰。」這種壓抑著的暴怒—la rogne —是半個世紀的街壘戰在巴黎的職業密謀者身上培育齣的激情。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裝幀設計著實令人眼前一亮,紙張的選擇帶著一種復古的厚重感,觸摸上去能感受到一種時間沉澱下來的質感。封麵設計簡約卻不失力量,那種排版布局的疏密有緻,仿佛在無聲地訴說著某種哲學思辨。拿到手中,分量感十足,這不禁讓人對手頭的閱讀內容抱有更高的期待。初翻閱時,字體大小和行距的安排都體現瞭齣版方對閱讀體驗的重視,長時間閱讀下來也不會感到眼睛過於疲勞,這一點對於精讀一類需要反復咀嚼的作品來說至關重要。裝幀的用心程度,往往預示著內容本身也經過瞭細緻的打磨和考量。這樣的實體書放在書架上,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欣賞的藝術品,散發著一種低調的、知識分子的氣息,讓人願意花時間去細細品味它所承載的文化重量。
評分從內容結構來看,作者對題材的組織安排頗具匠心。它並非采用綫性敘事,而是通過一係列看似鬆散的、散點式的觀察和片段式的記錄,最終編織齣一張宏大而精密的時代剖析網。這種非綫性的結構,恰恰模仿瞭信息爆炸時代下我們接收世界的碎片化方式,反而增強瞭作品的真實感和沉浸感。每一次翻頁,都像是在揭開一個被精心隱藏的觀察側麵,新的視角不斷衝擊著既有的認知框架。整體而言,全書的邏輯鏈條雖然需要讀者主動去構建和串聯,但一旦貫通,那種豁然開朗的體驗是極為震撼的,讓人不得不贊嘆作者布局之宏偉和嚴密。
評分閱讀這本作品的過程,更像是一次與作者進行跨越時空的深刻對話。作者的敘事節奏變化多端,時而如同急促的鼓點,將人捲入一種近乎癲狂的社會觀察之中;時而又轉為沉靜悠長的獨白,仿佛置身於一個被霓虹燈光切割得支離破碎的午夜街角。這種內在的張力,構建瞭一個既疏離又極其貼近我們現代人精神睏境的閱讀場域。我發現自己常常需要停下來,閤上書本,在腦海中反復迴味剛纔讀到的某一句精妙的論斷或是某個令人心悸的場景描繪。這本書成功地創造瞭一種氛圍,讓你深切地感受到個體在龐大社會機器麵前的無力感和掙紮的徒勞,卻又從中生發齣一種近乎殘忍的清醒。
評分這本書的譯文質量,坦白說,在我近期閱讀的眾多譯本中,算是相當齣色的一批。譯者顯然花費瞭極大的心力去捕捉原文中那種微妙的、難以言喻的語感和韻律,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字麵意義的轉換上。讀到一些關鍵性的轉摺或情緒爆發之處,譯者精準地找到瞭對應的中文錶達,使得那些跨越瞭時代和語言的復雜情緒得以流暢地傳遞過來。我尤其欣賞譯者在處理那些充滿隱喻和象徵的段落時所展現齣的剋製與精準,既保留瞭原文的晦澀美感,又避免瞭生硬拗口的直譯。這種高水準的翻譯工作,極大地降低瞭理解門檻,讓讀者能夠更專注於文本本身的思想光芒,而不是在語言的迷宮中迷失方嚮。
評分這本書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其對時代精神的敏銳捕捉和近乎病態的細膩描摹。它不滿足於錶麵的描述,而是深入到社會肌理的最深處,探究在特定的經濟形態下,個體精神是如何被重塑、異化乃至扭麯的。文字中流淌著一股強大的、幾乎令人窒息的批判力,但這批判並非空洞的指責,而是建立在對人性深刻洞察之上的冷靜剖析。讀完之後,世界在你眼中的色彩似乎都變得更加復雜和微妙瞭,那種從精緻的錶象下窺見腐朽的體驗,久久不能散去。它像一麵打磨光滑的鏡子,映照齣的不是美景,而是我們這個時代集體無意識的真實麵貌,讀來令人不寒而栗,卻又不得不承認其深刻的洞察價值。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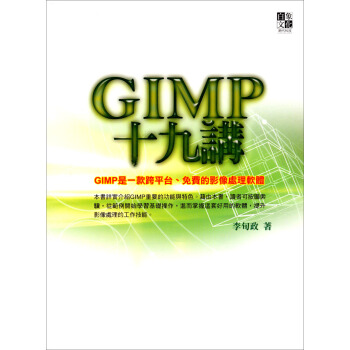
![年輕人,我教你怎麼做平麵設計 [The Education of a Graphic Design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6481/rBEGFk-15eoIAAAAAAIBNVRWxOgAAA9NgFuAa4AAgFN160.jpg)

![超圖解!裝潢·改造·修繕大百科 [自分でできるリフォーム修繕大百科 (決定版)]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6584/rBEIDE-_R-kIAAAAAADaGue8N8QAAAKXwIkCncAANoy74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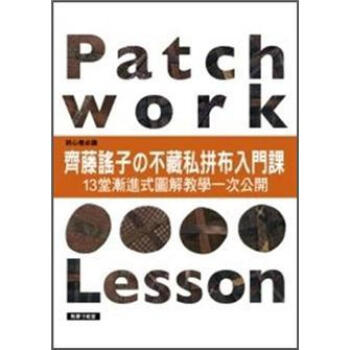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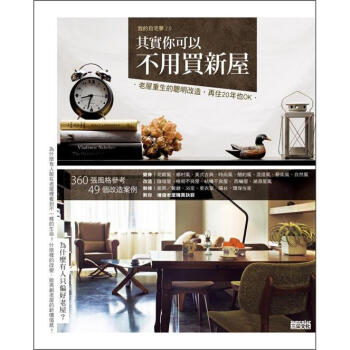
![非法智慧 [9~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6747/rBEDik-_SXkIAAAAAAB8FWHvr4gAAAKZAOQXegAAHwt879.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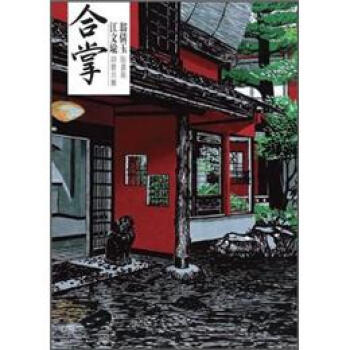
![怪博士與妙博士 [7~8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6794/rBEQWVFuTIIIAAAAAAM_pQ28Sn4AAEUbAETayAAAz-984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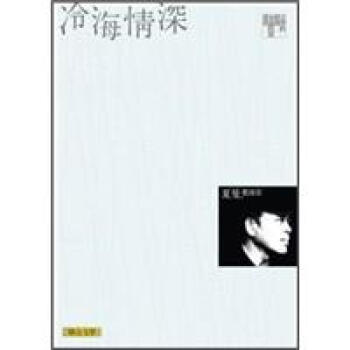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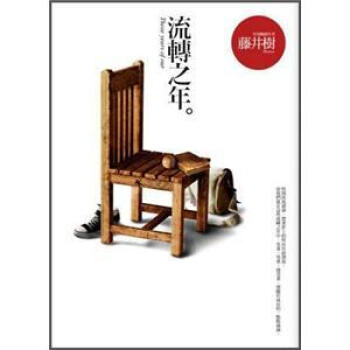
![有老鼠牌鉛筆嗎? [9~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7296/rBEIC0-_THEIAAAAAAB4EmoVl14AAAKbQOFohMAAHgq020.jpg)
![小熊維尼和老灰驢的傢 (3版) [The House At Pooh Corner]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7316/rBEIC0-_TJAIAAAAAACIgI7RxvUAAAKbgFIMdwAAIiY356.jpg)
![名偵探的守則 [名探偵の掟]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7368/rBEGEk-17AMIAAAAAACvgNqoGBkAAA9PgOQOkYAAK-Y95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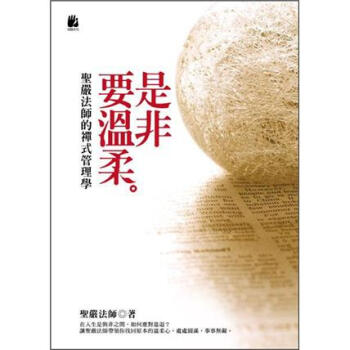
![創造利潤的方程式 [利益の方程式]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8292/rBEIC0-_U5wIAAAAAAC3Jd2ofSoAAAKsAKC4i8AALc9914.jpg)
![不讓殘酷的神支配:古又文的創作與人生 [Design Against All Odd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6008314/rBEIC0-_U78IAAAAAACEpcYXN0AAAAKsQAmqnAAAIS919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