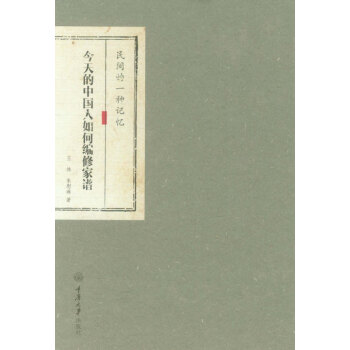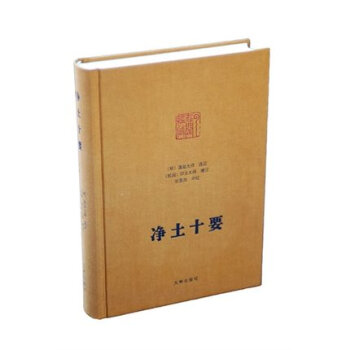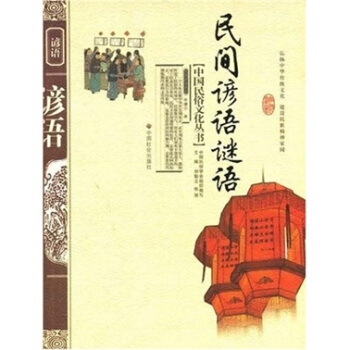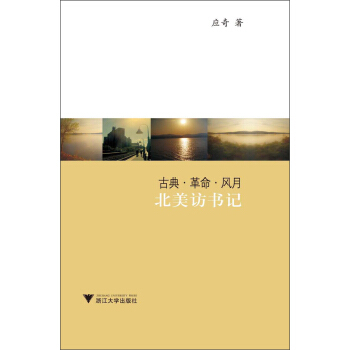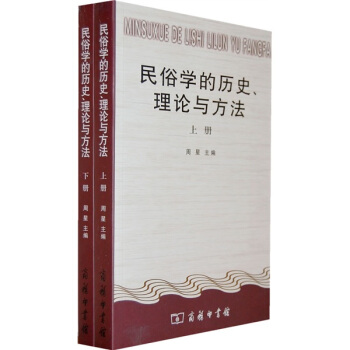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全2册)》从最初的构思到出版问世,前后历经6年之久。其间得到已故钟敬文教授的关心、中国民俗学会多位负责人的支持和人事部专家司对相关课题的部分资助,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全2册)》论文的各位作者、译者以及拥有原作版权的出版社、杂志和个人分别以无偿或象征性地收取一定版税让渡相关权利的善意,编者深表感念。商务印书馆副编审李霞博士为《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全2册)》的出版尽心尽责,也令我非常感激。《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全2册)》编者欢迎并期待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内容简介
《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全2册)》的主题为“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旨在较为集中地介绍中国及各主要国家民俗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学术传统和流派、研究的方法和技术等。编者假定的读者群为爱好民俗学的本科生,尤其是刚刚跨人专业门槛的民俗学或相关专业的硕士和博士课程研究生、中国民俗学会会员及特别关心民俗文化问题和中国民俗学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编者期待《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全2册)》能有幸成为民俗学专业基础性的中文读本。中国民俗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现已成为中国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园地的“显学”之一。近些年,与中国民俗学有关的各类理论著述、学科史和学术思想史研究、民俗志和田野调查报告、专题研究成果及通俗类读物陆续问世,越来越多地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及中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国内不少大学的院系也相继在本科教学中设置了不少民俗学类课程,拥有民俗学及同类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大学研究生院也正在迅速增加。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国社会明显和持续地出现了重新认识并进而复兴传统民俗文化的动向。不仅大学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全社会都出现了对于民俗和民俗学知识的需求。《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全2册)》正是为对应此种专业教育和社会公众的知识需求编辑出版的。
尽管民俗学的国际学术交流一直以来颇为活跃,国际学术界共享的民俗学理念也颇为众多,但考虑到不同国家的民俗学基本上是在各自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其成长轨迹和学术传统的流脉毕竟各有特色,故《民俗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全2册)》拟以五组论文分别介绍中国、日本、韩国、北美和德国的民俗学。
目录
上册导言
中国民间文艺学史诸流派
20世纪“民间”概念在中国的流变
论蒙古族现代民俗学的形成与发展
从书面到口头: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反思
“内在的”和“外在的”民间文学
文本和生活:民俗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向
从“传承”的角度理解文化遗产
天时与人时——民众时间意识探源
“俗信”:支配中国民俗生活的基本观念
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衣食”民俗
成吉思汗龙年大祭的田野考察
日本民俗学学术史及研究法略述
日本民俗学百年要略
日本民俗学的新视野——从两部日本民俗学概论谈起
日本民具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独树一帜的物质文化研究中心 民俗学之存在意义——从村落社会发展起来的一门构想性科学
展望比较民俗学
名为”灵魂”的记忆装置——围绕”民俗”概念的素描
现代社会与民俗学 [
民俗知识的动态性研究:冲绳之象征性世界的再考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对话——围绕“田野工作”展开的讨论
下册
韩国民俗学的发展和研究课题
韩国民俗学的发展历程
韩国民俗学的近况
韩国和朝鲜神话研究之比较
民俗的时间、空间和近代的时间、空间——祭仪时空间的变化
哭泣的文化人类学:韩、日、中的比较民俗研究
美国当代民俗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
论欧美现代民间文学话语中的“民”
口头诗学与民族志
语境中的民俗——美国表演理论述评
反反“民俗”
为民俗学正名
新展望之后:20世纪后期的民俗研究
女性主义理论与民俗研究:20年迈向理论的轨迹
我是民俗学家而你不是——民俗学实践中泛化与分界的策略对抗
民俗学在加拿大
德国民俗学的回顾与展望
民俗主义:一个概念的挑战
关于时间和空间的秩序——来自民俗学的评论
地点·工作·身体:现代欧洲的民俗志——第34届德国民俗学会大会综述
著、译者简介
后记·鸣谢
精彩书摘
上册中国民间文艺学史诸流派”
刘锡诚
引言
回顾和梳理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学术史,必然会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有没有出现过流派或学派?如存在着和存在过的话,都是一些什么流派,代表人物是谁?代表作和主要观点是什么?什么时候形成?后来的发展状况怎样?
在流派或学派问题上,笔者是多元论者。除最近常说的“民俗学派”(钟敬文,1999)之外,至少还出现过歌谣研究会和以沈雁冰、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派”,以顾颉刚、杨宽、童书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闻一多、马学良为代表的“民族学派”,以郑振铎、赵景深为代表的“俗文学派”,以何其芳、周文、吕骥、柯仲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以钟敬文、江绍原等为代表的民俗学派等。
判断一个流派的形成和存在,笔者以为要从四个方面去考察:1.流派是历史性产物,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存在,如这种条件不存在了,相应的流派也就消亡。2.流派有一个基本队伍。3.有自己的纲领。4.必须有其代表作。因历史文化背景的制约,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出现的流派或学派,大都发育不很成熟,也不完善。即使有流派或学派存在,也会有一些有成就的学者不属于任何流派。有的学者先是属于这派,后又成为另一派,各流派或学派之间也不是水火关系,往往是既有差别,又有交叉和融汇。
用户评价
对于方法论部分的讲解,这本书可以说是做到了极致。我曾尝试阅读过一些民俗学的研究著作,但往往被其中晦涩的研究方法所困扰,而这本书则为我扫清了这些障碍。作者以极其清晰、系统的方式,将民俗学研究的各种方法一一呈现,从传统的田野调查技巧,到现代的数字人文方法,都进行了详尽的介绍。他不仅讲解了“如何做”,更重要的是讲解了“为什么这么做”,以及在不同研究情境下,选择何种方法更为合适。我尤其喜欢书中关于“民族志”的详细阐释,从早期以观察者为主导的研究方式,到后来强调与被研究者建立平等对话、共同参与的叙事转向,作者都给出了非常生动的案例说明。书中对访谈技巧、问卷设计、影像记录等具体操作层面的指导,也十分实用,让我受益匪浅。此外,作者还探讨了研究伦理问题,强调了尊重被研究者、保护隐私的重要性,这对于每一个 aspiring 的民俗学研究者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知识。读完这一部分,我感觉自己不仅掌握了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理解了研究方法背后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评分这本书简直是一场民俗学知识的盛宴!从一开始,作者就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长河,探寻民俗学的起源与演变。我特别喜欢书中对早期民俗学家们研究方法的详尽描述,那些充满时代印记的田野调查、文献考据,无不展现了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民间文化的深切热爱。阅读过程中,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些先驱者们在乡野田间、在古籍堆中,一丝不苟地搜集、整理、分析民间故事、习俗、歌谣的场景。书中对不同学派的兴起和争论的梳理也十分清晰,无论是历史学派的宏大叙事,还是功能学派的社会功能分析,亦或是结构主义学派的符号解读,作者都能够深入浅出地阐释其核心思想和研究贡献。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理论的简单罗列,而是通过大量的具体案例,将抽象的理论具象化,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比如,在讲述神话学派时,作者引用了大量跨文化的神话原型故事,并将其与现代社会的某些心理现象联系起来,读来既有趣又发人深省。全书的结构设计非常合理,从宏观的历史脉络到微观的研究方法,层层递进,条理清晰,即使是对民俗学不太熟悉的读者,也能轻松进入这个迷人的学科领域。
评分这套书给我带来的最深刻的感受,是民俗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在理解人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它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对当下和未来的启示。书中对民俗学研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变迁、身份认同的构建,以及数字时代的新型民俗现象,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的视角非常宏大,他将民俗学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野中,探讨其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我尤其被书中关于“地方性知识”和“文化传承”的讨论所吸引,这些内容让我重新思考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保持文化的根基和特色。书中的一些分析,如对网络流行语、亚文化现象的民俗学解读,也让我眼前一亮,认识到民俗学并非只关乎“过去”,它也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以适应时代的需求。这套书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让我对民俗学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激发了我进一步探索和学习的兴趣。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叙事方式,真的是我读过的学术著作中难得的体验。它没有那种枯燥乏味的学术腔调,而是充满了人文关怀和学术热情。作者在梳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穿插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鲜活的案例,使得整本书读起来像是在听一位博学而富有魅力的学者娓娓道来。我特别喜欢作者在描述一些历史人物和研究事件时,所展现出的那种敬意和情感。比如,在介绍某个早期民俗学家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深入边远地区进行考察时,文字中流露出的不仅仅是对其学术贡献的肯定,更是对其人格魅力的赞赏。书中对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俗现象的描写,也充满了诗意和想象力,让我能够感受到世界各地的民间文化是多么的丰富多彩。有时,我甚至会因为书中某个故事的精彩而停下来反复品味。这种将学术深度与文学趣味完美结合的写作方式,无疑极大地提升了阅读体验,也让我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吸收了大量的知识。
评分这套书的理论深度和广度着实令人惊叹!我之前一直觉得民俗学只是研究一些民间故事和传统习俗,但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它是一门多么复杂而又深刻的学科。作者在理论部分的论述,不仅仅是简单地介绍各种理论流派,而是深入挖掘了这些理论背后的哲学思想、社会背景以及对民俗现象的解释力。我尤其欣赏书中对“文化表征”、“意义生成”、“社会构建”等关键概念的深入剖析,这些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理解民间文化的方式。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思考,书中所讨论的理论是如何影响我们对身边日常生活的理解的。例如,关于“仪式”的理论,书中不仅分析了其象征意义,还探讨了仪式在维护社会秩序、传承文化认同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让我对许多我曾习以为常的节日庆典有了全新的认识。书中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民俗学中的影响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使得我对当代民俗学研究的前沿动态有了更清晰的把握。总而言之,这本书为我构建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精细的民俗学理论框架,让我能够以更批判、更具洞察力的视角去审视和分析民间文化现象。
评分很喜欢的书,赶紧买过来。
评分一开始落了上册没邮递,不过京东美眉很快给补上了,在邮递途中,期盼我的上册赶快送到啊。关键是没法开始就看下册啊。
评分很有用的书,绝对正版!
评分东西非常好呀!
评分民俗内容保罗万象。女娲神话在神州大地上分布甚广。据《女娲溯源》作者调查,“就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而言,女娲神话的主要传承者,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是中国广大领域上的汉民族。在笔者目前所搜集到的247个明确有‘女娲’出现的神话中,有235个是汉民族中传播的,占总数的95%以上。它们的分布地点遍及华北、中南、华东、西南、西北、东北等各个地区,除迄今尚未见到内蒙、西藏、云南、海南等省以及北京、天津二市的相关记录外,女娲神话在汉民族中的传播几乎遍布于全国各省区。而在少数民族中,女娲极少出现,现在搜集到的明确与她相关的神话共有12则。其中苗族3则、藏族2则、瑶族1则、水族1则、毛难族1则、土家族2则、仡佬族1则、蒙古族1则。”(3)继而,《女娲溯源》一书分别制作了“汉民族女娲神话数量分布表”和“少数民族女娲神话分布表”,后者中四川仅仅列出川南苗族当中流传的女娲神话3则,如“女娲阻止天狗吃月”、“伏羲女娲的子孙蝴蝶人因捣蛋被天爷灭绝”等,而没有涉及四川境内的羌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神话。除此之外,该书中针对相关文物古迹还制作了“女娲信仰分布表一”和“女娲人首蛇身像的分布——女娲信仰分布表二”,前者以地区划分,在西南地区这部分列出二例,即峨嵋的女娲洞遗迹和忠县的补天石化作“石宝寨”传说;后者按照朝代(自汉至明)及地区划分,列举了重庆沙坪坝石棺、郫县犀浦东汉墓、彭县画像砖墓、崇庆画像砖墓、新津画像石、金堂姚渡画像砖墓、成都天迴山崖墓石棺、简阳鬼头山东汉岩墓石棺、乐山张公桥崖墓石刻、宜宾公子山崖墓石棺、泸州大驿坝石棺、渠县沈君阙等。总的说来,该书中不见有涉及羌区女娲神话传说的文字。羌人相信万物有灵,其供奉的神灵也多。据2004年出版的《羌族词典》,羌族信仰的神灵有30多种,大致可分四类:(1)自然界诸神,如天神、地神、山神、树神、火神、羊神和其他牲畜神;(2)家神,各地不一,有的地方多达13尊,包括莫初(历代祖先)、活叶依稀(男性祖先)、迟依稀(女性祖先)、亦吉(保护家中平安之神)、密怕露(保佑男子工作之神)、西怕露(保佑女人工作之神)、斯卓吉(掌管活人灵魂之神)、玉莫(掌管死人灵魂之神)等;(3)劳动工艺之神,如建筑神、石匠神、铁匠神、木匠神等;(4)寨神,又称地方神、社神,随各地传统而异,有的是石羊、石狗,有的是雄鹰。接着,该词典立条目介绍了玉皇大帝、观音、龙神、水神、灶神、谷神、力久士(财神)、不谷于湟且(仓神)、吉兹阿(媳妇神)、吉哈厄西且(大门神)、牛马二王、毒药猫、阴差、瑕支姑娘、莎朗女神、倮倮士(雪隆包神)、陆家士(左门神)、独迪士(右门神)、俄巴巴瑟、木巴瑟、如句瑟、木比塔、木姐珠、蒙格瑟、八渣瑟、中柱神、角角神、姜子牙、关圣帝君等数十种神灵,其中有羌人独奉的也有来自道教、佛教的,但没有提往前追溯,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先后进入岷江上游走访羌区的人士,国外有英国的陶然士和美国的葛维汉,国内有庄学本、胡鉴民、冯汉骥、钱安靖等,他们笔下有好些文字涉及尔玛人的民间信仰及神话传说,但是基本上不见有女娲神话及信仰在羌民中流传的田野记录。199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神秘的白石崇拜——羌族的信仰和礼俗》,是由羌、汉学人合著的,曾得到神话学家袁珂称赞,其首章用了80页的篇幅介绍“羌族的诸神”,书中所举48位神灵中亦无女娲(尽管有观音、鲁班、城隍等)。难道在川西北羌族聚居区,女娲神话传说真的没留下踪迹么?不然。当今民俗学界,《中国女神》一书就说女娲神话在羌民中有流传,尽管没有举出具体例子(该书第三章曾引述“羌族伏羲兄妹”故事,这个文本是《羌族民间故事选》编者当年从汶川搜集的,但故事中并未说妹妹之名是“女娲”)。该书作者在谈到中国女神系统的包容性特征时指出:“中国女神的包容性有两层意义:一为对外族神话文化的包容吸收,即民族文化交流;二为对外国神话文化的包容吸收,即国际文化交流。”就前者言,“民族文化交流,如女娲神话流传于汉、苗、藏、水、壮、土、布依、瑶、仡佬、羌、畲、维吾尔等族之中。”(4)事实上,考察川西北岷江、涪江上游羌族地区便知道,古老的女娲神话在羌族民间社会中是有传播的,尽管可确指的踪迹不算多,但也不乏族群特色,值得关注。譬如,2007年10月有走访者从茂县三龙乡桌子坝羌民口头采录了一首用羌语演唱的民歌,其汉语记音如下:“哦不得呢哎斯勒哎阿勒卓,哦兹得呢呀什不呀哦哦呢角呀,哦呀哟嗯呀索则呀哦哦勒学呀。”搜集者将此歌归类为《历史歌》,并介绍歌词大意为:“有了天,才有地;在大洪水之后,才有了人类。女娲造出了男和女,男结婚,女嫁人”(5)这位羌民姓杨,1921年出生,是年逾八旬的老人。据说,这是在尔玛人婚礼上演唱的古歌(据我所知,川西北羌族传统婚礼上通常是唱天仙女木姐珠,尔玛人奉木姐珠为本民族的先祖,相信是木姐珠为他娲的神话传说总体上数量有限,影响亦不甚强(羌族释比做法
评分东西非常好呀!
评分很好的一本书,多家论文集,有启发
评分很有用的书,绝对正版!
评分很有用的书,绝对正版!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中信书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精)/理想国译丛 [美]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400704915/57562389N9f03ba33.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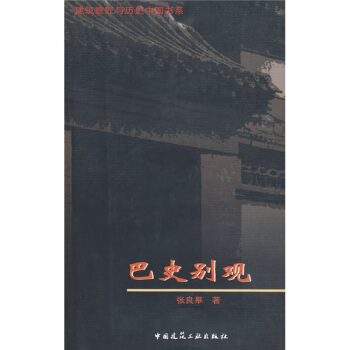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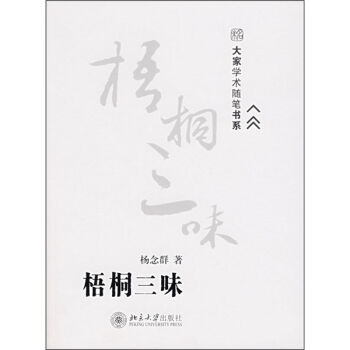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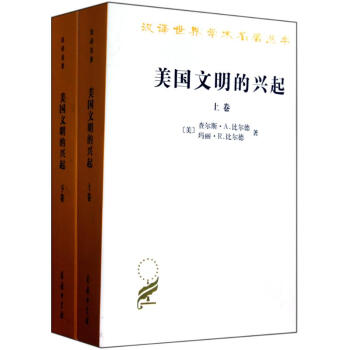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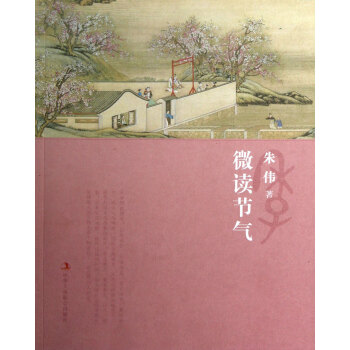
![社会、历史背景下的跨文化交际(第4版)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Context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214330/22b2487f-d5a0-44f7-9322-dc6dca47ba2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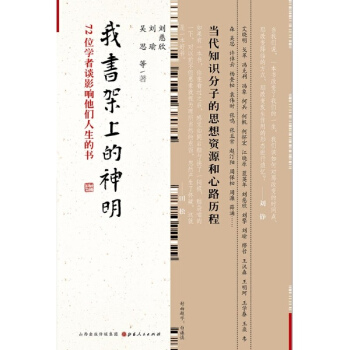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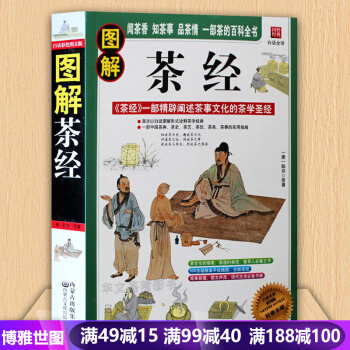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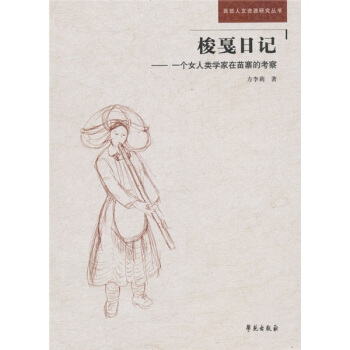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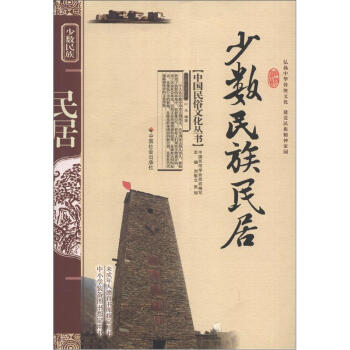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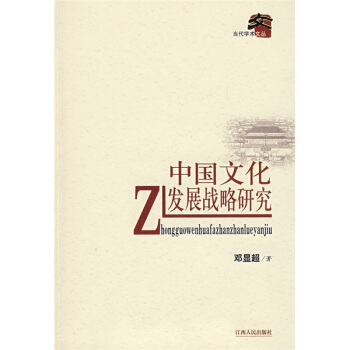
![卫礼贤之名:对一个边际文化符码的考察 [The Name of Richard Wilhelm Survey on a Borderline Cultural Cod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0917785/2167ef7b-8562-4a3b-8b9b-e6ea35acf34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