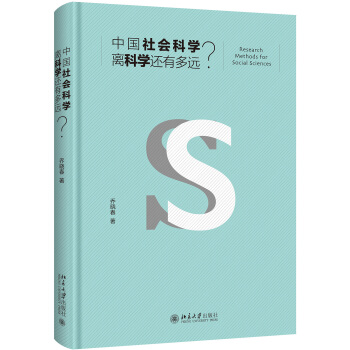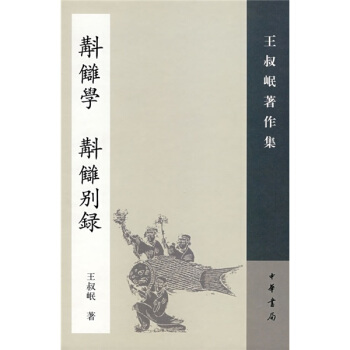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王叔岷的《校雠学》一书,广为中外学者引用。此补订本是在此基础上,将可以修订的问题及条例进行补充,例证太多的则进行删减。因此,《校雠学 校雠别录》更为严谨与充实。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整体架构和论证过程,展现了一种罕见的宏大视野和精微分析相结合的特点。作者似乎从一个非常高远的维度审视了所探讨的主题,然后逐步深入到最细微的结构和案例分析中去。每一次论点的展开,都建立在扎实的前期铺垫之上,使得后续的推导显得水到渠成,无可辩驳。我注意到,作者在处理历史脉络和理论发展时,总能清晰地勾勒出不同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避免了传统研究中常见的片段化和孤立化倾向。这种结构上的严密性,让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强烈的“全景图”的把握感,不会感到迷失在细节的泥淖中。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揭开了一层新的帷幕,看到更广阔的图景,这种逻辑上的层层递进和结构上的完美闭环,是极其难得的。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封面采用了一种典雅的深蓝色调,纹理细腻,仿佛能让人触摸到历史的尘埃。书页的纸张质感也相当不错,厚实而不失韧性,油墨的印刷清晰锐利,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初次翻阅时,我注意到作者在章节编排上的用心良苦,逻辑清晰,层层递进,让人很容易跟随其思路深入探索。特别是一些关键概念的提出,作者似乎总能找到一个非常精妙的角度去阐述,既保持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不失文采,读起来丝毫没有那种枯燥乏味的学究气。装帧上的细节处理,比如书脊的烫金工艺,都体现了出版方对这部作品的重视,让人觉得手捧的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对于注重阅读体验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在物理层面的呈现,无疑是加分良多,极大地提升了阅读过程中的愉悦感和仪式感。
评分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深切感受是其蕴含的批判性思维的光芒。作者并非简单地复述已有的观点或知识,而是在不断地提问、质疑和挑战既有的范式。尤其是在对一些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理论进行审视时,作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提出的反思角度往往直击要害,发人深省。这种思想的锋芒,让人在阅读时时刻保持一种警觉和活跃的状态,不断地在脑中进行着与作者观点的对话与碰撞。它不是一本提供标准答案的教科书,而更像是一面映照我们认知局限的镜子。很多我过去习以为常的看法,在这本书的冲击下,不得不被重新审视和解构,这种思想上的“震荡”与重塑,才是阅读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评分从内容广度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涉猎范围之广令人称奇,它仿佛搭建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平台。作者在论证过程中,不动声色地融入了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乃至社会学的观察视角,使得单一主题的探讨拥有了丰富的维度和更深厚的土壤。这种跨领域的融会贯通,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也让它能够吸引到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即便是非专业人士,也能从中获得许多启发。例如,当讨论某一核心概念时,作者能够迅速地将其置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进行对比分析,这种多维度的切入,让原本可能略显单薄的议题变得丰满立体起来。整体而言,这本书在知识的广度、深度的结合上,以及思想的穿透力上,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准,是一部让人受益匪浅的佳作。
评分我对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和行文节奏感到非常惊喜,它巧妙地在学术深度与通俗易懂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作者的文字功底深厚,遣词造句既准确又富有韵味,即便是在论述一些复杂的问题时,也能用生动的比喻和清晰的结构将复杂的思想娓娓道来。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事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沉稳而又充满洞察力的笔触,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带领读者穿越迷雾,直抵核心。阅读过程中,我几乎能感受到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那种对所研究领域的热爱与执着。有些段落,读完后甚至会让人停下来,细细品味其中蕴含的哲理,那种知识的甘醇仿佛在舌尖久久不散。这种行文的流畅度和思想的穿透力,使得阅读过程本身就变成了一种享受,而不是一种负担。
评分西莊史學宗趣,一則曰治史宜考典章制度,再則曰治史與治經不同。惟其謂治史宜考典章制度,故于校勘本文、補正訛脫外,最詳於職官輿地典章制度;惟其謂治史與治經不同,故深惡宋儒以議論求法戒,凡自矜筆削而附于夏五郭公者均深斥之,尤不喜褒貶人物,以為空言無當也。
评分二、古文、籀文、篆文、隶书、草书、俗书、楷书之相乳
评分一、不认不漏之难
评分二 三位老师
评分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
评分此书为“王叔岷著作集”之一种,将王叔岷的《校雠学(补订本)》与《校雠别录》两书合为一册。
评分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钱穆有一句话:我们要用抗战的精神来读书才对得起前方抗战的将士。
评分杜甫(712-770),字子美,汉族,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评分叔岷先生是近现代以来校雠史上扛鼎人物,欲窥校雠学门径,此书不可不读。全书除前言外似从台版影印,字大行疏,但墨色较淡。价格稍贵。竖排繁体,印刷没有我在旧书店看到的给人的感觉好,另外虽然价格稍贵,不过这本书确实很经典。斟雠之业,盛于干、嘉,高邮王氏,允推巨擘。后之学者,惟在材料上求胜而已,工力迄未能逮也。岷之留意整理故籍也,自读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始。十八年来,涉猎渐广,体悟日深,于王氏治学方法之缜密,态度之谨严,陈义之精审,愈益叹服焉!岷之从事斟书也,自斟荘子始。民国三十年秋,由故乡简阳赴南溪李庄之栗峰,寄读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山居清胜,摒绝尘杂,伏案三载,写成庄子校释五卷。虽成书太早,说多未定,然已立雠定古籍之基础。因斟庄子,涉及郭象注之材料,亦同时搜辑;与庄子关系至关系至巨之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三书,亦随时料理。三十五年秋,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至鉅之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三书,亦随时斟理。三十五年秋,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南京,定居峨嵋新邨,绩理积稿。三十六年夏,历史语言研究所以重金洽购江安傅沅叔先生所藏南宋蜀本南华真经十卷,曾撰校记一篇,以补庄子校释之未备二疋岁冬,写成列子补正四卷,采用四部丛刊影北末本为底本。叔岷先生是近现代以来校雠史上扛鼎人物,欲窥校雠学门径,此书不可不读。全书除前言外似从台版影印,字大行疏,但墨色较淡。价格稍贵。 王叔岷号慕庐,四川简阳人。1935年,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4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傅斯年、汤用彤先生。后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9年后,任台湾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1963年后,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1973年,自中研院史语所及台湾大学中文系退休,仍担任史语所兼任研究员及中国文哲所筹备处咨询委员。 主要著述 :《诸子斠证》、《庄子校诠》(全二册)、《庄学管窥》、《左传考校》、《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史记斠证》(全五册)、《列仙传校笺》、《陶渊明诗笺证稿》、《钟嵘诗品笺证稿》、《刘子集证》、《斠雠学(补订本)·校雠别录》、《古籍虚字广义》、《慕庐论学集》(一)(含《慕庐演讲稿》、《慕庐杂著》、《慕庐杂稿》)、《慕庐论学集》(二)(含《吕氏春秋校补》、《世说新语补正》、《文心雕龙缀补》、《颜氏家训斠注》)。王叔岷先生(1914-2008),名邦濬、字叔岷、号慕庐、以字行,是台海华人圈广受推崇的历史语言学家、校雠名家,研究方向主要为先秦诸子、校雠学。王叔岷先生1914年出生于简阳县(今成都市东郊洛带镇下街),1933年,先生考入由国立成都大学、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大学、公立四川大学合并的“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后又考取北大文科研究所就读硕士,师从傅斯年、汤用彤等,毕业后留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王叔岷先生因1948年随史语所迁台,国共两党分治,其在大陆的知名度并不高。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先生先后在新加坡大学、台湾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等校教书,课余勤于著述,前后用17年完成巨著《史记斠证》,退休后完成集大成之作《庄子校诠》。王叔岷先生1992年后几次往返大陆旅游,并于2000年获台湾行政院文化奖后开始长住大陆,大陆文化界始关注先生的学术造诣,2007年中华书局引进出版了《王叔岷著作集》共15本。2008年8月,王叔岷先生仙逝于成都龙泉驿区其长子家中。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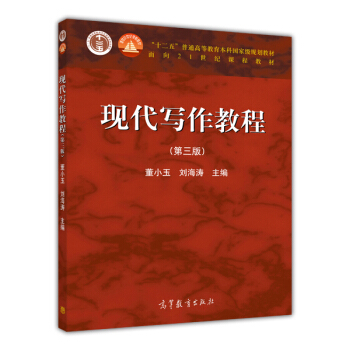
![专业学位硕士论文写作指南(第2版) [Guidance to Professional Master′s Disserta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04494/54a12f07Nd072f394.jpg)
![初识传播学:在信息社会正确认知自我、他人及世界 [A First Look at Communication The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20995/573a838bNb199483d.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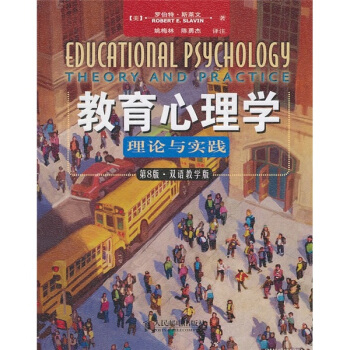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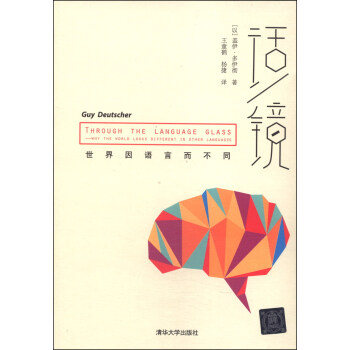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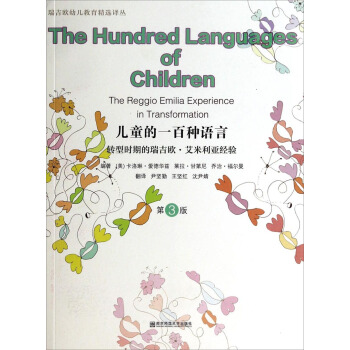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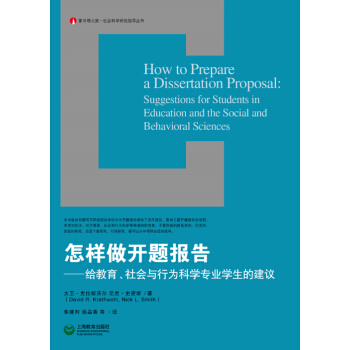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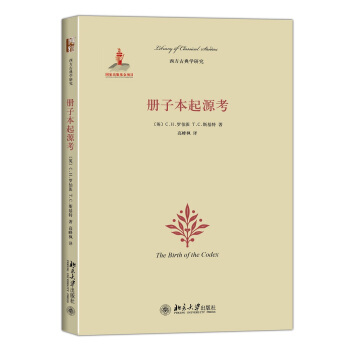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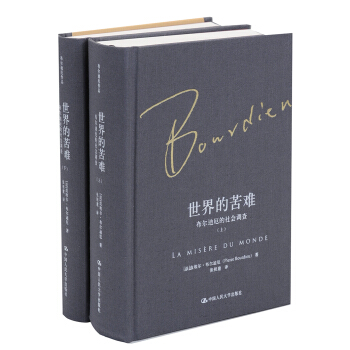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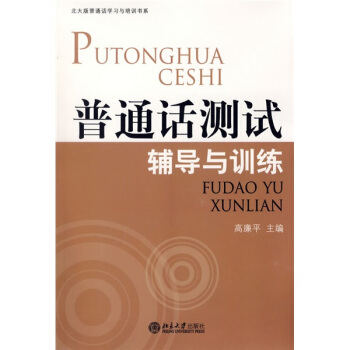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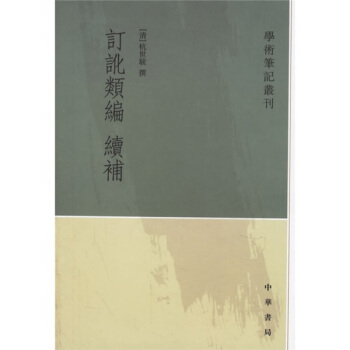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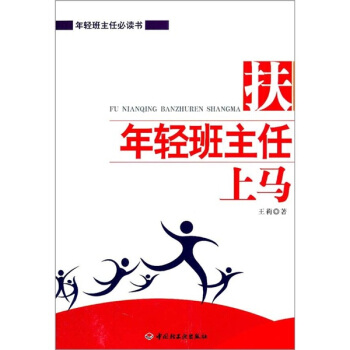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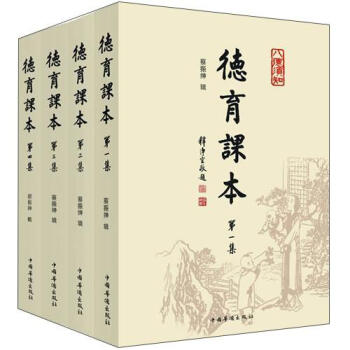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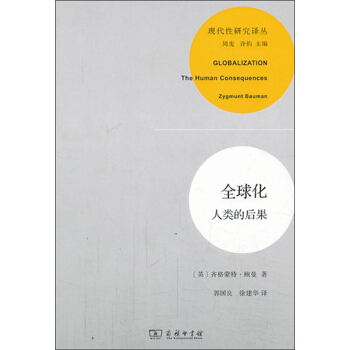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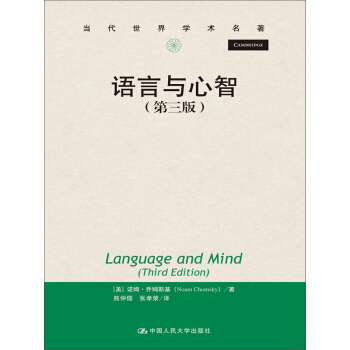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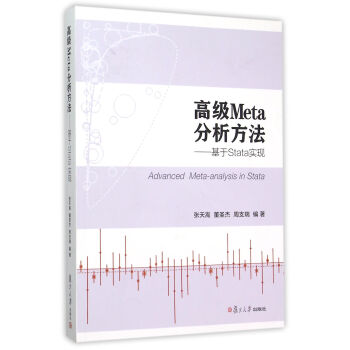
![哈佛医学生的历练 [White Coat: Becoming A Doctor At Harvard Medical 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908388/570d333bN124d7fa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