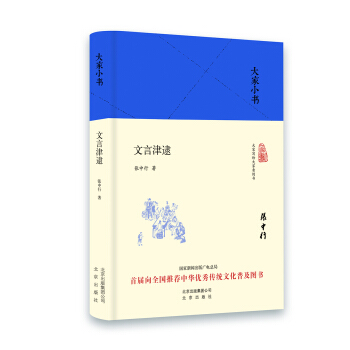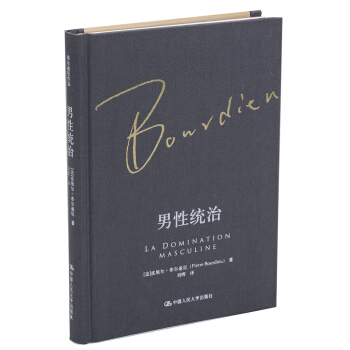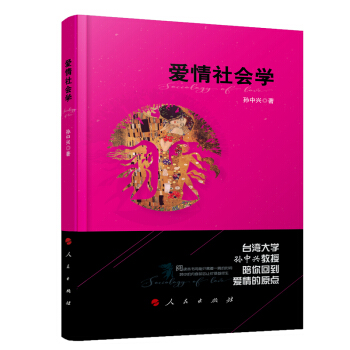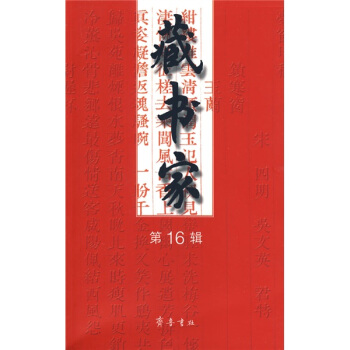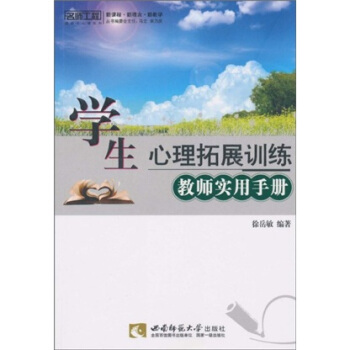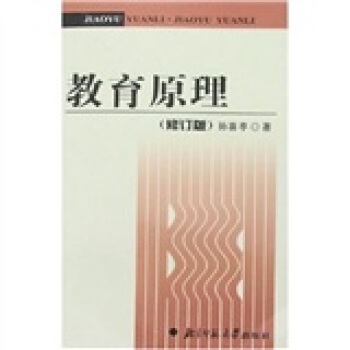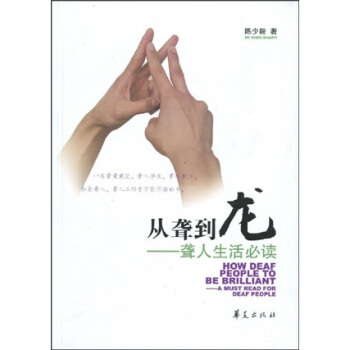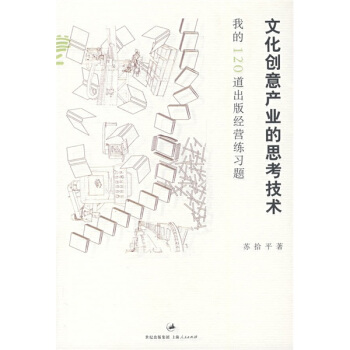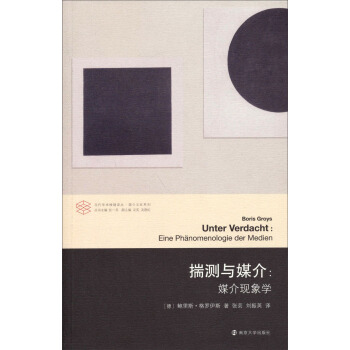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揣测与媒介:媒介体现象学》以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艺术档案的存留管理方式及其意义为视角,通过各种哲学,社会学新思想对媒介体本体的揣测进行分析与哲学思辨。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亚媒介空间,概述了《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揣测与媒介:媒介体现象学》研究的缘起,分析视角以及意义,简述了亚媒介主体和符号流,以及媒介体作为讯息时的情况;第二部分分别借助对莫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曼纳、乔治·巴塔耶和雅克·德里达等多位当代欧美哲学大师在媒介体领域见解的研究分析,得出揣测,时间与媒介体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提出了不少独具慧眼的哲学思索,值得阅读与研究。内容简介
当今的艺术往往以揣测为源:艺术展现的只是日常的表象,人们总在琢磨其背后隐匿的秘密。只有某种诡谲的、色彩斑斓的画面才会彻底唤起我们的注意。《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揣测与媒介:媒介体现象学》中向我们解释了揣测怎样在不同的媒介中起作用,以及为什么自马勒维奇与杜尚以来,人们总是在为“现代艺术中究竟何为艺术,何为俗物”这类问题争论不休。艺术是值得人们去揣测的东西,就好比将一把铲雪锹或者一小撮米放在博物馆中一件广受认可的艺术品旁边,任由人们去讨论,这就一定会引起揣测。这类争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可能为在物质上有限的艺术作品开启了一个潜在的可以无限反思的空间。通过《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揣测与媒介:媒介体现象学》作者论证了艺术与媒介间广泛的现象学,同时也把其先前一本著作《论新事物》中的一些论题进行了拓展。
作者简介
鲍里斯.格罗伊斯1947年生,纽约大学俄罗斯和斯拉夫学系全球杰出教授(gIoba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设计大学艺术与媒介学院资深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整体艺术品斯大林割裂的苏联文化》(1988)、《论新事物》(1992)、《思考的艺术》(2008)等。 张芸,1965年生,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德国艾希斯泰特天主教大学博士。 刘振英1960年生,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硕士,现任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内页插图
目录
导论I 亚媒介空间
亚媒介主体和符号流
媒介真相及其例外状况
媒介本体揣测与哲学怀疑
媒介真诚性的现象学
他者的目光
媒介成了讯息
特例情况与媒介真理
Ⅱ 揣测经济
莫斯:象征交换或水下文明
克洛德·列维一斯特劳斯:曼纳或漂浮不定的能指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me):与太阳较劲的破它来示
雅克·德里达:紧缺的时间及其幽灵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搭乘过山车的崇高
符号的时间
揣测就是媒介
参考书目
精彩书摘
媒介真相及其例外状况在媒介表面流动的符号流不可能是真正无限的——这也就像人们并不一定需要通过假设一个无限神性的主体性来设想在亚媒介的空间中藏匿的、暗中左右着符号流的主体。单一的一“自然的”或者通过技术生产的——媒介载体基本上都要对符号进行两种运作:存储和传输。操作符号的整个媒介经济就是通过这两种运作来进行运转。符号只能通过这两种运作流动,而且是通过特别建立的媒介渠道从一种符号的存储器转移到另外一种。所有符号载体的存储能力以及联系着它们渠道的传输能力是受限制的和有限的(bcgrcnzt und endlich)。仅这一点就足以使关于无限符号流的言论变得不足为信。
实际上,哪种符号载体能够承载无限的符号游戏或者无限的符号流呢?符号可以是物质的——它们首先是物品,是世界中的物件。符号和媒介载体也同样是真实的、物质的和有限的:书本、银幕、电影、计算机、博物馆、图书馆以及石块、动物、人类、社会和国家。所有媒介经济的运作都仅仅是通过这些有限的媒介载体来进行,因而与符号打交道的可能性也只是有限的几种。在任何地方人们都不可能遇上无限数量的符号和无限的符号流——这仅仅是出于非常简单的原因,因为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着用于存储无限数量的符号或者进行传输的,能够具备无限存储能力的符号载体。这样关于符号的无限海洋和无限符号流的话语听起来尽管很美,但鉴于现有媒介载体的有限性和由此形成的可估算性以及它们之间进行交换吋种种操作的可能性,这个话语实际上十分不可信。
这就意味着,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有限符号经济的、在暗中左右和控制着这种交换的有限主体。应该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涉及标记的过程。如果愿意这样看,人们或许可以宣称,不存在一个有限的——甚至是无限的——一主体能够生产与控制在媒介的经济框架之内储存和交换的符号意义。事实上,在这种运作中可能产生的意义和效果是无法估测和无法控制的。这里涉及的是亚媒介的、操纵性的主体,它并不顾及符号的意思、意义及所指来使用符号。符号经济的主体不能理解为意义的生产者,生产者凭借它自身的意图赋予符号意义并通过自我意识的清晰性和准确性来保证符号意义的稳定性。这样一个生产意义和控制意义的开明主体会理所应当地遭到后结构主义的完全解构。
……
前言/序言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人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則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申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士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咸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if)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內。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兔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掌握得相当出色,它不像那种堆砌术语的学术专著,反而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推着读者不断向前探索。特别是在论述“符号的数字漂移”时,作者采用了近乎侦探小说的笔法,层层剥开信息茧房的表象,直抵其运作的核心机制。我发现,作者在批判技术异化时,并没有陷入悲观主义的泥淖,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建设性的张力,试图在被规训的现实中,寻找主体可以重新介入的微小缝隙。这种在批判与希望之间摆荡的姿态,极具感染力。对于那些关注社会学和传播学交叉领域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具前瞻性的对话平台,它没有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提出的问题本身,就足以让整个领域为之一振。
评分从结构上看,这本书的逻辑链条异常坚固,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建立在前一个概念扎实的基础上,如同精密的建筑设计。我特别欣赏作者对“中介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反复锤炼与深化。他不仅仅是描述媒介如何连接事物,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种连接本身如何成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书中对“时间压缩”在数字媒介中的体现的讨论,极其精辟,它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总有一种“永不停止”的焦虑感。这种对时间本体论的挖掘,远超出了媒介研究的传统范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域”,让我们得以从宏观的历史脉络和微观的个体感知层面,同时把握当代媒介文化的复杂性。读完后,我感觉自己仿佛获得了一副特殊的眼镜,能够看穿日常信息流动的表层,直抵其深层的结构性肌理。
评分阅读此书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对自我认知边界的不断试探与重构。我一直以为自己对新媒体有相当的敏感度,但作者通过对“感知规训”的细致剖析,让我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观看”方式,早已被底层技术逻辑预设和框定。这种对主体能动性的反思,是全书最锋利的部分。它迫使我们跳出“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去审视技术如何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时间感交织,共同编织出一个“媒介场域”。书中引用的那些看似不相关的跨学科案例——从早期电影理论到最新的社交媒体算法——被巧妙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张严密的理论之网。这种跨学科的整合能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这不是一本轻松的读物,它需要严肃的智力参与,但回报是巨大的,它会永久性地改变你观察世界的方式。
评分整本书的行文风格,仿佛是在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穿越一片迷雾笼罩的知识丛林。它不像是一本标准的教科书,更像是一系列精心布局的哲学沉思录。作者在处理媒介本体论问题时,展现出一种近乎诗意的语言张力,将冰冷的理论包装在富有画面感的描述之下。我特别喜欢其中关于“拟像”与“真实”界限消融的章节,那段文字仿佛把我直接拉入了巴特勒和德波的对话现场,但又注入了全新的时代语境。这种处理方式避免了纯粹的理论复述,而是让理论鲜活起来,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经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虽然有些地方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完全捕捉到其细微的语义变化,但这恰恰是其价值所在——它要求读者投入时间与心力去“共建”意义,而不是被动接受。阅读过程中,我时常停下来,望向窗外,思考那些日常的屏幕反射出的光芒,那光芒背后隐藏的复杂结构,这本书提供了解码的视角。
评分这本关于媒介文化现象学的著作,其论述的深度和广度令人印象深刻。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对媒介现象的表面描摹,而是深入挖掘了我们与技术、与信息世界互动时所产生的存在论层面的变化。那种将媒介视为一种“拓扑学结构”的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媒介环境的理解边界。我尤其欣赏作者对“在场感”和“缺席感”之间微妙张力的探讨,这直接触及了当代社会中个体经验的碎片化本质。读完后,我开始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媒介互动,比如刷手机时的那种近乎无意识的沉浸,不再仅仅是技术习惯,而更像是一种被重塑的感知模式。书中的理论框架,虽然有时显得晦涩,但一旦领会其精髓,便能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用以剖析那些光怪陆离的数字景观。对于任何希望超越“媒介使用指南”层面,真正进入媒介哲学深处的人来说,这本书无疑是提供了一把精巧的钥匙。
评分书不好我不会买。最喜欢阅读和看电影。
评分特价时买的书。很便宜。送货到楼下,很方便。
评分很好,京东的东西放心。。。
评分艺术是值得人们去揣测的东西,就好比将一把铲雪锹或者一小撮米放在博物馆中一件广受认可的艺术品旁边,任由人们去讨论,这就一定会引起揣测。这类争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可能为在物质上有限的艺术作品开启了一个潜在的可以无限反思的空间。通过《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媒介文化系列·揣测与媒介:媒介体现象学》作者论证了艺术与媒介间广泛的现象学,同时也把其先前一本著作《论新事物》中的一些论题进行了拓展。
评分好的,刚才通过上课、学习的举例,想必你也明白什么叫“思维自由性”了吧!没错,电影会对人的思维自由性产生束缚,然而读书则不会,所以——得出结论,读书的过程中,人会经历更多的思考。再加上文字的表达力胜过电影,那么——这样一看,电影若想超越原著真的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啊!你看,这是平方性的叠加!这是平方性的益处叠加!读书,书中的文字表达力更强;读书,思维的自由性更强。从而得到益处的叠加,好上加好的是——读书能获得的,真的比看电影多很多。更何况,多读书还能提升写作水平,“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而看多了电影,能提升拍电影的水平吗?即使可以,谁会给你拍电影的机会?所以说,读书的实用性还要强于电影。
评分好书,读起来很有收获。
评分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的学术著作质量不错。
评分还没开始读,看起来还不错
评分内容简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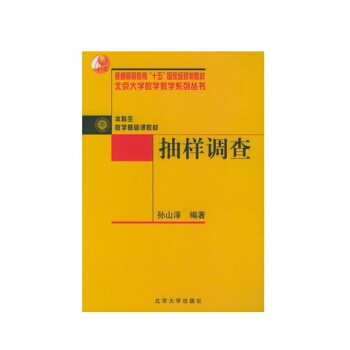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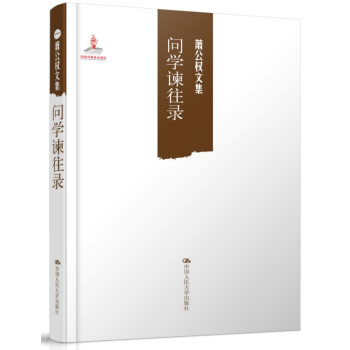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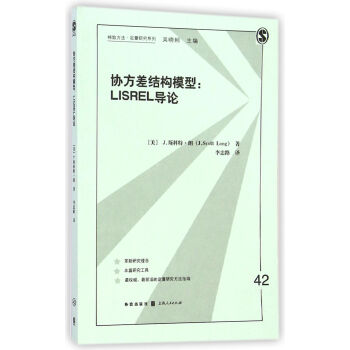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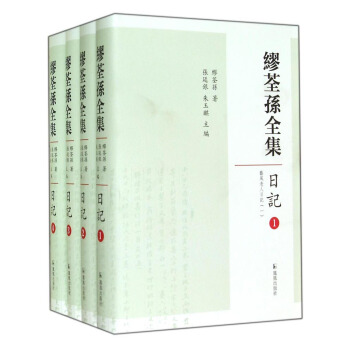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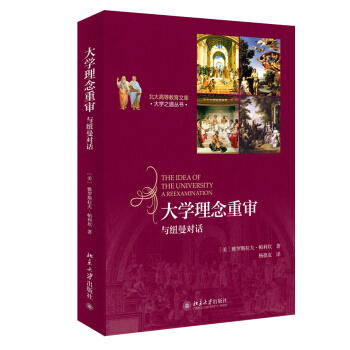
![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5) [Annual Report on China’s Education(201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79031/553992c7N80549e62.jpg)
![文学写作实用教程:从基础准备到文体写作的具体指南 [Creative Writing Practical Guide: The Essentials of Compos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07488/558a64eeNc4c925c6.jpg)
![就业蓝皮书:2015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 [Chinese 4-year College Graduates' Employment Annual Report(201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714839/558cff78N704a3705.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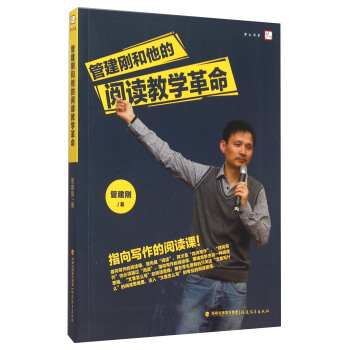

![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 [Enchanting a Disenchanted World: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835739/5678fd0fN07447f9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