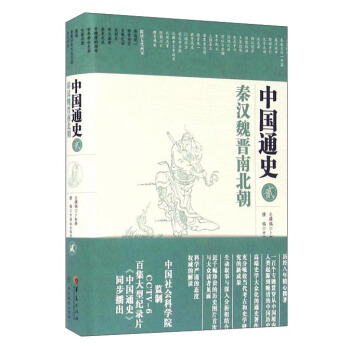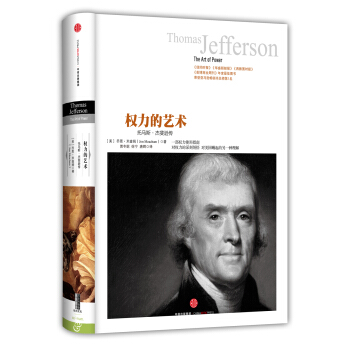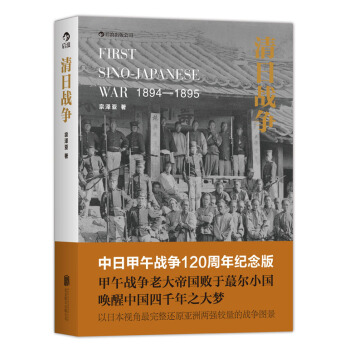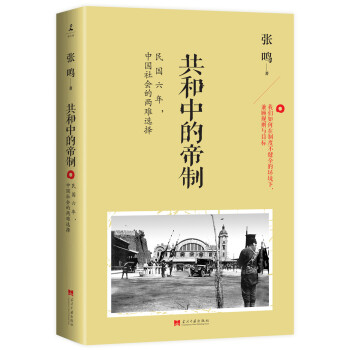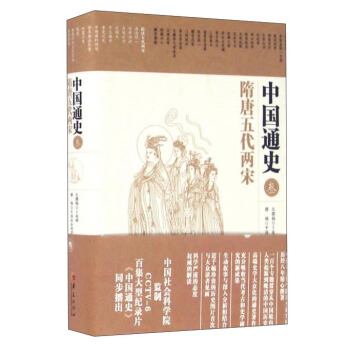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讨论明清之际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以及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为有关历史生活的想象,提供了丰富、感性的内容。
海报:
内容简介
继《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话题”“人物”(明遗民),《续编》的“制度”“言论”“心态”,《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尝试经由被认为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更为日常的生活世界。本书讨论的,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以及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士大夫与“家庭”“家族”有关的言说与叙述,与他们的其他活动,以富于个性的方式联系着,为我们有关历史生活的想象,提供了丰富、感性的内容。作者简介
赵园,1945年生,河南尉氏人。196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1年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师从王瑶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目录
自序夫妇一伦
规范夫妇一伦的努力
父母/妻子
日常的处夫妇
妻/妾
“古风妻似友”
流离、播迁中的夫妇
结语
附录一:关于冒襄的《影梅庵忆语》
附录二:诗文中清初流人的“殊方”经验
父子及其他
君/父
“肃若朝典”
严、慈之间
人子之事亲
兄弟
士大夫对家族的经营
附录:“此朕家事”
余论之一
余论之二
征引书目
文学·伦理·人的世界
——由现当代中国文学到明清之际(代后记)
精彩书摘
文学·伦理·人的世界——由现当代中国文学到明清之际(代后记)
对本文的题目作一点说明。
回头清点自己三十余年的学术工作,有必要首先提到的,是文学之于我,文学研究之于我的“学术生涯”,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与专业训练之于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后的学术工作。我一再申明,尽管我涉足了文学以外的领域,却始终更是一个文学研究者。作品集、文集,是我几十年间学术工作的入手处,无论对象领域有何变动。明清之际士人的文集,也仍可归入广义的“文学”,尽管未必都有文学史的地位。以文学文本为考察材料,旨趣或在文学之外,但以什么为考察材料绝非不重要。这当然要考虑到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不同的特质,其对于使用的限定,还应当计及文学文本中可能的信息含量,文字层面可能具有的丰富意蕴。
对于我下文将要谈到的与“伦理”有关的论域,作品集、文集无疑特具研究价值。即如其中有更具体情境中的“忠/孝”“君/父”,更感性、个人的“家人父子”。这也是我坚持由文集中取材的基本考量。周绍泉、落合惠美子、侯杨方《明代黄册底籍中的人口与家庭——以万历徽州黄册底籍为中心》一文说:“历史上的家庭问题,一向是社会史和人口史学者关注的重点。然而,在家庭史的研究中,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即没有一种资料是与家庭完全对应的。这里所说的‘家庭’,是指以特定的婚姻形态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同居、合产、共爨’的社会基本单位。”(收入张国刚主编《家庭史研究的新视野》,引文见该书第218—219页)在这种情况下,或许士人文集这一种“资料”可以派上用场。当然也因此,我的讨论不免受制于材料。文集作为材料,便利处在具体感性,受限之处则在缘具体个人的陈述,未必能形成“总体判断”。我也因此不得不在作类似判断时持审慎态度。个体经验在提供历史生活的“丰富性”时,不免片段零碎,或可为既有的综论拾遗补阙,却未必可据以作一概之论,即如关于其时普遍的伦理状况——“一概之论”也正是我一向避免的。
我认可梁漱溟所说“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 。我们这代大陆人文学者曾耳熟能详的,就有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即“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古代中国所谓的“五伦”,确也是士赖以界定自身的最重要的“关系”。“五伦”,父子、夫妇、兄弟居其三,系于血缘,较之君臣也较之朋友、师弟子等,作为关系更“天然”,是人的生活世界赖以构成的最基本的关系。经由上述“关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打开。
也如所做关于“明清之际”的其他题目,我关心的更是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体验的家庭伦理。当然,“伦理”不限于家庭伦理。无论对于现代中国还是明清之际的知识人,我对其伦理处境与伦理经验的关注也不限于此。我一再讨论的,即有“忠”“节”一类范畴,知识人的处家/国、公/私、生/死等等。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考察,也涉及了私域与公域,以及非常时期的政治伦理、职业伦理。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家庭伦理。
五四新文化运动锋芒所向,“家族制度”首当其冲,具体即在父子(等差秩序)、夫妇(婚姻制度)。最被认为振聋发聩的,即有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1917年2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6号)、李大钊的《万恶之原》(1919年7月13日《每周评论》第30号),等。李大钊在该文中说:“中国现代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上述“战斗檄文”之外,影响更为深远的,应当是鲁迅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致幼者》等(均见《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鲁迅所主张的“幼者本位”(《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与清末民初影响了一代知识人的“进化论”相关。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及其后的,既有由背叛家庭到反抗社会,也有“背叛”之后的回归。
上述“时代主题”的文学样本,即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作为青年的启蒙教材,影响了几代知识人关于传统社会、家族制度的想象与认知。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拙著《艰难的选择》,关于家庭、婚姻问题的讨论,应当是我以学术方式探讨家庭伦理的最初尝试。该书下篇有“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一章,附录则收入了论文《“五四”时期小说中的婚姻爱情问题》《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
《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一文说:“较之有关‘家庭社会学’方面,我的兴趣更在于认识现代知识者。”“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高觉新型’”则尝试由“子”一代,由“觉醒了的‘人之子’”,分析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家”,说高觉新“附属于、隶属于‘家’,是那个‘家’的一部分”,“失去了自己的生存目的”(《艰难的选择》第287页),说高觉新“是祖父的长孙,父亲的长子……而不是‘人之子’”(第288页。按“人之子”见鲁迅《随感录》四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322页)——关注所在始终在知识人,他们伦理实践中的经验与感受。
于今读来感到刺目的,是《艰难的选择》使用的一套概念。“宗法封建性”云云,已渐被弃之不用;“封建社会”代之以“传统社会”。但“宗法封建性”一类表述特有的历史感,却难以为其他表述所替代。回头看,《艰难的选择》的有关论述,仍然不是流行命题的简单演绎。在上面提到的几篇文字中,即力求重现知识人伦理处境、伦理生活的复杂性,既谈到了“反抗”,也写到了他们对于“宗法制的过去”、对于“家”的眷恋。
写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地之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以乡村为“传统文化的渊薮”;所论某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以父子对比结构小说,其中的子之于父,也不免是“历史进化论的思维模式和乐观信念的人物关系化”(第68—69页),却由于将考察范围延伸至该书写作的1980—1990年代之交,所展示的图景有了显然的不同,即如写到了乡民的“准祖先崇拜”,“类似祭祖的仪式行为”;写到了父子间的文化传承(第74—75页)。类似内容,难得见之于五四新文学。
写作《艰难的选择》的1980年代,我所属的一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与五四新文学作者有情绪、精神上的呼应与共鸣,包括对“未来”的乐观,对变革的渴望。当然,也乐观得肤浅,渴望的目标并不明晰。那种乐观,由遥远的事后看去,不免令人心情复杂。新/旧、过去/未来、光明/黑暗二分的思维与想象,于反顾中有了讽刺意味。在近年来“国学热”持续升温、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氛围中,读当年批判性地写到的“古旧的追怀”,不免有荒诞之感。这是新文学作者当写作时,也是我1980年代写作上述学术文字时逆料未及的。重读之下,像久历沧桑的老人翻看旧相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对于上述现象,不便仅用了“循环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简单地打发,有必要作深度的讨论。1980年代学术文本中包含的丰富信息,有可能为清理1917—1949年、1949年之后、1980年代的学术文化提供契机。至于我自己,基本的研究方式固然在此期间形成,对某些现象、问题的敏感,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两段学术工作“一以贯之”。看似“两橛”,实则并非如此。
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相关,阶级斗争语境中被污名化的“家族”“宗族”,“文革”后又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有人提出重评“宗族制度”。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难点毋宁说在重评与家族、宗族有关的阶级论述。近一时期,不惟宗族史,与民间信仰、地方社会有关的考察,也包含了关于20世纪中国革命之于社会改造,尤其乡村基层社会改造的反思。这甚至正是有关论述的问题意识。我发现这种反思有逐步深化之势,有关谈论也渐由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到较为明晰、直接——尽管问题依旧有敏感性。考虑到“宗族势力”“民间信仰”长期被作为“打击对象”,上述讨论的艰难展开,当然应当被视为一种进步。
近年来家族小说(以至个人的家族历史叙事)的兴盛,像是对五四新文学的隔代回应,包含于其中的情怀却大有不同。无论由家族展开当代史叙述,还是追怀一种消失中的文化,“家族”都不再是仅有负面意义的符号。而在事实上,一方面伦理状况在急剧变化中,同时却继续上演着古老的伦理故事的现代版。由社会的某些面相看,中国还相当古老。上文提到的拙作《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一文,有“宗法封建的家族制度,造成精明狠辣的主子和吃祖业的不肖子弟”云云(《艰难的选择》第412页)。即使不再使用老套的“宗法封建”之类说法,你对“吃祖业的不肖子弟”也决不陌生,更无论最为人诟病的世袭权力、“权贵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
我自己则直到将要告别学术工作之际,才稍稍接触了作为史学的一个分支的宗族史,作为有关明清之际家庭伦理考察的一部分背景。而在写《艰难的选择》等学术作品的1980年代,宗族史研究尚未兴起;即使1990年代的有关著作,也像是仍未脱出我们曾经熟悉的主流论述。 探讨明清之际的家庭伦理,宗族史不在我的论题之内,属于“相关论域”,在我讨论的问题的延长线上。我无意于重返五四新文学。我距那一段学术经历已经遥远。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作为一个过程重新考察,只能寄望于较我年轻的学人。
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处父子、夫妇。
我的经验与知识储备,使我在踏进“明清之际”之初,就被那些非严格“思想史”的方面吸引,关注的更是知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他们的伦理生活。不消说“明儒”不止存在于理学基本范畴、命题中,还在他们的伦理实践中,在他们与理学无关的其他文字、表述中。
关于五伦中的君臣、兄弟、朋友,我已有论述。 五伦之外,士大夫重要的伦理关系,尚有师弟子。 五伦有公认的伦序,具体的排列顺序又有因人之异;有通行的规范,又有个人取向,尤其在极重朋友、师弟子的明清之际。流风所被,不免于畸轻畸重,即如以重朋友而轻妻子为标榜——我在考察中涉及了这一点。正在进行中的关于士大夫的处“父子”“夫妇”的分析,力避为已有的“宗族史”“婚姻史”作注脚,尝试将“总体史”所不能涵括的现象纳入考察范围。“宗族史”“婚姻史”更关心典章制度,作为材料的,通常是正史、方志、刑事档案等等,士大夫的特殊经验难以在其中获得位置。此外,“通史”模式不能不多所省略,重归纳而轻分析,这就使得关于特定时段特定人群的伦理经验的探讨有了伸展的余地。
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的处夫妇一伦,材料之丰富出我意料。已完成的论文如《言说与伦理践行之间——明清之际士大夫与夫妇一伦(之一)》《常态与流离播迁中的妻妾——明清之际士大夫与夫妇一伦(之二)》,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刘梦溪主编之《中国文化》2012年秋季号上;《冒襄的〈影梅庵忆语〉》,刊《书城》杂志2012年第12期。对父子一伦的考察,却使我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你不难读到知识人笔下的妻、妾,或含蓄或一往情深,却难以读到儿子笔下形神兼具的父亲。由此也不难推想父子这一种关系的“压抑性”,儿子受制于其家庭角色,书写尊长时的诸不敢、不宜、不便、不忍。
五四新文学有关作品,批判的锋芒所向,主要为“家”的男性长辈,所谓“封建家长”,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老太爷、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等等。上文提到的拙作《现代小说中宗法封建性家庭的形象与知识分子的几个精神侧面》一文中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父与子,“分别代表着的是两个时代。人物之间有时表现为对立,有时仅仅表现为‘差异’”(《艰难的选择》第418页)。明清之际的父与子却同属一个时代,以至同一人的两个角色。我的旨趣也与考察五四新文学不同;作为“士大夫研究”的一部分,对于明清之际,我的兴趣在其时知识人的不同家庭角色,不自居于“子”的、“妇”的立场。
并不符合沟口雄三先生的理想化的设想,我不是“空着双手”进入这段历史的。 我的手中,就有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历、经验。我不可能卸脱了这一种“背景”,只能要求自己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避免过分地“介入”,力求贴近明清之际的历史生活。尤其是,避免带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我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生成的问题意识考察明清之际;关于明清之际知识人的处父子、夫妇,努力呈现现象的丰富性、差异性。事实是,只有不受限于“宗法封建性”一类意识形态预设,换一副眼光,才能由据说面目严冷的刘宗周那里,感受其人对于妻的温情;由陈确的文字间,察觉其接受有缺陷的婚姻时保有的幽默感,对其妇的辛劳的体恤;由冒襄的文集中读出对其妻的艰难处境的深切同情。父子亦然,那些为人父者对于其子,态度在严、慈之间,苛酷不情与通达之间。某些被古代文学学科依其标准筛除的文字,令你窥见了古代中国人如此丰富的生活世界。这在我,也是走出五四新文化式的思路的过程——尽管并非出于事先的设计。
与已有专业间的对话却不止赖此进行。事实是,妇女史、宗族史等学科,早已在对话五四新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只不过有的明确标出,有的隐含在论述中而已。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一书绪论“从‘五四’妇女史观再出发”中说:“伦理规范和生活实践中间,难免存在着莫大的距离和紧张。儒家社会性别体系之所以能长期延续,应归之于相当大范围内的灵活性,在这一范围内,各种阶层、地区和年龄的女性,都在实践层面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中译本第7页)有必要注意该书副标题中的一系列限定:明末清初,江南,才女。著者无意于概其余。尽管如此,对于我所属专业,上述判断仍然具有挑战性。
对于国外汉学的有关论述,我也不无保留。据说自1990年代初起,国外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跳出了‘男女不平等’的框架而立足于发掘、再现妇女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和历史空间中的生活经历及社会角色”(《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妇女史卷》主编姚平撰写的“前言”,见该书第2页)。收入该卷的高彦颐、金滋炫、皮歌特合著《〈古代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女性与儒教文化〉前言》说,该书旨在“复原女性的主体性和历史的复杂性”,力求更正“过去认为亚洲的妇女是传统或儒教家长制(Confucian partriarchy)的牺牲品”这种“简单化的理解”,“因为‘妇女’和‘儒家传统’都不是统一的或者无限的范畴”(第1页)。“‘妇女’和‘儒家传统’都不是统一的或者无限的范畴”,的确如此。该“前言”还说,女性在他们的考察中,“既不是反叛者也不是牺牲品。她们作为协商(negotiation)的主体,接受了一些官方的惯例而反抗了其他部分”(同上)。但就我接触的材料而言,她们中确有“反叛者”和“牺牲品”。妇女的反叛与牺牲,并非出于意识形态的建构。“既不是”“又不是”,似乎在自我设限,预先作了排除、省略。但该“前言”说,“我们所使用的儒教话语,定义了一个普遍的、没有分化的女性,以此作为女性的他者(Other)”,的确值得反思。该书的选题涉及了一些被大陆的主流论述长期无视以至刻意遮蔽的面向。但我也想到,为此而“跳出”“‘男女不平等’的框架”,是否会带来新的遮蔽。国外汉学有关论述的启发性是无可怀疑的,我却不认为大陆的妇女史研究有必要随国外汉学风向而转移。“革命”式的“翻转”,对于学术工作并不适用。袪蔽,发未发之覆,是推进学术的有效路径,但发覆不同于推倒重来。我一再谈到与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有关的学术经历之于我此后工作的意义。这一点即使由这一具体角度,也得到了证明。
我必须承认限于语言能力也限于阅读范围,我对所引用的文字容或有误读误解,有与对方宗旨的错位,但对话肯定是有益的;即使不免于误解的“对话”,仍然刺激了思考,尤其对于形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思维逻辑。
我还应当承认,在不断移动位置、改换考察对象的过程中,并不曾有“觉今是而昨非”之感。有校正,有充实、丰富,却不曾落实到绝对意义上的正/误、是/非。“家族”之为“制度”,其压抑性是显而易见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有坚实的根据。纵然由变化了的尺度衡量,与“宗法制”有关的价值,也绝非都具有正面的意义。至今也仍然有必要问“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如何对待“幼者”,出走的娜拉是否应当寻求职业独立以支持其意志独立。只是今天的父与子、长者与幼者、女性地位与两性问题,较之五四时期远为复杂而已。在这种意义上,是否仍然可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或更准确地说,并未实现在其“理想的”状态上?发生在快速现代化、城镇化中,在革命造成的破坏与市场化造成的破坏的废墟上,新的伦理规范、新的道德远未生成。
考察古代中国知识人的伦理处境与伦理实践,我的基本的价值立场,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即使此后有诸种调整,仍不足以推翻我所服膺的五四先驱(如鲁迅)的某些基本判断。但如上文所说,我无意将面对中国现代文学时的问题意识直接带进另一研究领域。进入明清之际,我更希望经由文献,尽我所能地触摸历史的感性面貌(至少保持这样的意愿),复原其时知识人生活世界原本的丰富与生动,历史人物作为个体,其伦理境遇与应对方式的无可穷尽的差异性。我敏感于“差异”,多种多样的差异,各种层面上的差异——往往有意想之外的发现。这令我相信还有诸多历史面向有待打开,通史、断代史所未及的那些面向,宏观考察、大叙事所不能笼盖的那些面向。
当代政治文化中的家庭、宗族。
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处父子、夫妇的考察尚在进行中,我已着手对“文化大革命”由伦理的方面加以考察。新近完成初稿的,就有关于“文革”中人伦的变与常,关于私人信件、日记在“文革”中,关于“文革”之于私人财产与公共财物的分析,总题为“有限视角下‘文革’中的‘私域’与‘公域’”。“今古齐观”的“今”与“古”,在我的学术经验中,不止指文学,也指时世。“今”,包括了当下,进行时的当下。“当下”不一定被我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对象,对当下的关切,却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学术思考与选择。
读明清之际乃读古人;隔了数百年的岁月,即使努力设身处地,仍难以如对今人、近事那样痛痒相关。无论读顾颉刚、吴宓,还是读聂绀弩、顾准,都令我心情复杂,甚至陷溺其中、难以自拔。“中年哀乐”,尚须赖丝竹陶写,何况我已老耄!这是否也是今古“齐”观的一点代价?当代史上的那些近事,你亲历的年代,你与它撕扯不开,难以保持“价值中立”。但我在去年岁末接受一家媒体的访谈时,仍然说,在关于当代政治文化的考察中“严守学术工作的伦理规范”,是“学术工作者应当有的操守”(《答〈南方都市报〉问》,刊该报2013年12月19日)。学术作品也属于“易碎品”。保持学术工作的品质,至关重要。这与有没有勇气不相干。
上述种种,均属人的世界,也惟千差万别才成其为“人的世界”。
我曾经说自己的路径,是“经由人物进入历史”。学术自述中也一再说,自己“固然感兴趣于‘思想的历史’,却也关心着映现在思想中的‘人的历史’。这兴趣又是由文学研究延续下来的”(《〈自选集〉自序》,《赵园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也说,“或也由于文学研究中的积习,我力图把握‘人与思想’的联结,在生动的‘人的世界’寻绎‘思想’之为过程”(《〈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后记》,《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说自己“依旧为‘人物’所吸引,为人物光明俊伟的气象所吸引,为他们正大的人格所吸引,时有触动、感动,以至感慨不已。……与这些不同时段的‘知识人’同在的感觉,是学术之于我的一份特殊赐予”(《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后记)。以上所说的“人物”,既包括文学人物(文学形象与文学作者),也包括历史人物,明清之际的士大夫,以至当代人物,当代知识者。维系了几十年间的学术工作的,就有探究“人的世界”的兴趣与热情。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经世取向,我曾由功利/非功利的角度讨论。我自己,始终有(无关乎“学术成就”的)非功利的动机,纯粹学术兴趣以外的兴趣。具体到本题,应当说,人伦中有无尽深广的“人的世界”。我的学术工作的连续性,不缘于刻意的设计,而出于持续的关怀。在我,只有借诸人物,历史才是可以想象的。
1917—1949年的中国文学、1980年代的中国文学(通常称作“新时期文学”)——明清之际的思想言论——1966—1976年的中国政治与文化,构成了我学术工作的对象范围。这些时间段在我的工作中的关联,由上文不难知晓。伦理问题只是我的学术工作中具有“贯穿性”的题目之一。更具有“贯穿性”的,自然是“知识人”这一特定对象。
不能会通古今、兼通中西,是我所属一代大陆学术工作者的短板亦宿命。先天的缺陷,并非总能由后天的努力弥补。 即使不能不因陋就简,面对考察对象不预设立场,不因既有成见而剪裁“事实”,仍然是我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回头盘点,在这一点上似乎尚能问心无愧。经验,经历,通常不直接进入学术,但有可能是类似“底色”的东西。有些吸引了我持久关注的题目,的确要溯源至此。在这一点上,我所属的大陆一代学人,与纯粹学院背景的学人有所不同。我珍视这种差异。如同由此而来的先天不足,阅历所给予的,也是使我们成其为我们的东西。至于因水平所限的立论的偏颇,知识方面的“硬伤”,则只能引为教训,并寄希望于后来者。
2014年4月
前言/序言
自 序《易·家人》卦,《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伦常,人伦日用,是古代中国——不限于古代,也不限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面。人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五伦,即古代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部分。人被其社会关系界定。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至朋友、师弟子中,父子、夫妇、兄弟系于血缘,较之君臣(也较之朋友、师弟子),作为关系被认为更天然。经由上述“关系”,士大夫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向你充分打开。由基本的伦理关系入手,讨论社会秩序的形态,或有可能避免架空之论。
在本书中,我尝试经由被认为最为重要的家庭关系“父子”“夫妇”,进入明清之际士大夫更为日常的生活世界。当然,这不意味着前此所讨论的士大夫的那些面向不属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本书更强调“日常性”“日用伦常”及“家庭”这一特定范围而已。即使较之草民更为经典(主要即《礼》)所规范,士大夫的生活世界也绝非有关规范的演绎,从未失去其丰富性,这使他们的人生呈现出人各不同的面貌。士大夫与“家庭”“家族”有关的言说与叙述,与他们的其他活动,以富于个性的方式联系着,为我们有关历史生活的想象,提供了丰富、感性的内容。
本书讨论的,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经验中的家族、家庭,他们所面对的伦理关系。我关心的,当然还有他们对有关经验、体验的表述。有能力表述,正是士大夫之为士大夫;作选择性的表述,也为士大夫所擅长。因而言述策略至关重要。我不能不随时意识到我的考察对象的自我陈述中掺入的自我想象,以至对理想状态的期望;出诸子孙的记述也难免于溢出(美化、理想化)。只不过对于我的目的,自我想象、期待另有研究价值——关于士人所认为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即使他们的缺陷感,也映射着所向慕的人生境界。知识人生活中的世俗层面与精神层面,在其伦理实践中往往贴合在了一起,诗的与琐屑日常的经验难以剥离。这一点在我看来,亦古今所同。
本书有关考察的特别之处,或许更在材料。所用材料,主要来自士人文集——这也是我此前的“士大夫研究”主要的材料来源。文集中有更感性、更个人、更具体情境中的“家人父子”。这也是我由文集中取材的基本考量。古代士人的传记文字少有今人所认为的私密性内容。涉及尊长,更有所不写。纵然如此,这些文献仍然更接近于知识人的生活场域。经由不同文字的比对,倘若幸运,你有可能辨认出讳饰,剔出过情的渲染,即使并不因此就能自信逼近了“真相”。
我的这项研究,方法论方面并没有“创新”之处。美国汉学家伊沛霞说自己的目标“是揭示宋代社会盛行的婚姻的假设前提,特别是与我们不同的那些,同时列举史料记载的反例及它们与假设前提间的紧张”(《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中译本第39页)。我的方法也大致类似,即关注伦理的规范性要求之内与之外,经典(如《周礼》)与个人化的伦理实践,规范所能抵达的范围、限度(可规范与不可规范),知识人在此限度内外如何处置其家庭内部关系,其间的模糊地带,无论父子,还是夫妇、兄弟。
即使严格意义上的儒家之徒也会有逸出,即如吕坤的说母不必从子。吕坤思想的“逸出”尚不限于此。我关注差异性,包括对于《礼》之为“经”的个人化的诠解,实践中人各不同的取向,为此不断致力于搜寻主流论述之外的论述,纵使它们是零星、片段的,不能用现成的逻辑之线贯穿。我没有兴趣更没有能力构建“理论模型”,关注始终在现象、形态的多样性,感兴趣于纷杂、个别性、特殊性、诸种歧异,使未被作为史料者进入考察范围;即使不能引发结构性的调整,也有助于修正定论,虽则只是局部、枝节的。
日本的几代学人,关于明、清江南的商品化,阶层分工的构成和社会秩序间的关系,有深入的研究。我缺少这种宏观的视野,也没有足够的材料支持这方面的判断,选择的是一些个例——士大夫的伦理处境,发生在他们个人历史中的伦理事件。进入“家人世界”的路径也仍然是文学的,得失均与此有关。较之史学著述,更依赖士人的自我表述与相互记述。严格意义上的“私人记述”的稀缺,不能不使家庭伦理考察遭遇困难。 伊沛霞抱怨道:“不幸的是,很少有丈夫或妻子记述自己的婚姻生活;第一手资料极为少见。”(《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中译本第135页)还说,“只有很少的士人写过妾及自己与她们的关系”(同书第199页)。我没有把握比较,因此难以确知是否我较为幸运——毕竟有本书所引用的士大夫记述其婚姻生活的材料,有写妾而公认名篇的《影梅庵忆语》;与钱柳、龚顾有关的材料也堪称丰富。
尚有文集之外的传记材料,墓志铭、家传、年谱、家谱、族谱等,亦可令人一窥士大夫家居情景,尽管有关记述不尽可据信。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二有“家谱不可信”条,说颜师古“精于史学,于私谱杂志不敢轻信,识见非后人所及”(《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第315页)。基于我的目的,对包括家谱在内的文集中的记述,一般不作真/伪考辨。那不是我为自己提出的任务。这些传记材料,或为正史所不采,却不但对于了解某个具体人物,且对探察一时期的士大夫的生活状态,均有意义。毛汉光《唐代妇女家庭角色的几个重要时段:以墓志铭为例》,认为正史以政治史为主,“唐代墓志人数多于两《唐书》,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为独立之资料,并不同于两《唐书》”;该文所用墓志乃“自然抽样”,较能“代表一般社会人物”。“正史成于一人或数人之手”,“墓志铭并没有统一的撰者”,“应可反映出当时人普遍的观念”(鲍家麟编著《中国妇女史论集》四集第147页),尽管其内容“绝大部分为社会中产以上(包括官宦、士人等)为多,农民、工人等未见”(同书第148页)。还应当说,无论父子还是夫妇,小说、戏曲中的材料都远为丰富——尤其平民、底层民众的伦理生活,大可作为考察士大夫的参照或背景。可惜我无力扩展取材范围。那一部分材料更适于由有关专家处理。
家庭伦理作为古代社会变化缓慢的部分,仍然随时有种种有趣的现象发生。诸种“变动”的征兆,或终于汇为“潮流”,或倏兴倏灭,都参与构成着历史生活的丰富性。至于家族、家庭,在关于特定时段士大夫的考察中,不应只作为一部分“背景”。即使古代中国,知识人的家庭生活也与其社会活动相关。当然,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中,血缘外尚有地缘、业缘(由古代中国发达较早的行业组织,到近代的商会、行会、“学会”),有关伦理均值得深入考察。对于个人,这也是其世缘,与斯世所结的缘。
人事体察与人情体贴是一种能力,尤应为文学研究者所具备。人伦即检验此种能力的考察对象。有“体察”“体贴”,才能由文字(或许只是极有限的文字)间读出人情,读出人的世界。有些能力,非学而后有,即如对人、对人事的了解。文学阅读,文学分析的训练,阅历与反刍、咀嚼的习惯,都有助于培养这方面的能力。此外,你从事学术工作的“当下”,势必影响到你的状态,甚至进入了考察过程,成为你的学术作品的一部分。
《颜氏家训·兄弟》:“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尽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因前此已著有《易堂寻踪》,本书与兄弟有关的部分从简。为便于阅读,正文的征引尽可能节制,而将对于正文的补充说明以及我以为有启发性的论述放在“余论”中,以便读者参考。至于篇章排序,则既然“有夫妇而后有父子”,将“夫妇”排在“父子”之前,也说得过去。尽管“父子”一伦依其重要性,被认为在“夫妇”之上;而“五伦”的顺序/价值观,至今也仍没有真的过时。
这本小书,应当是我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的收官之作。这不是说我将由这一时段抽身。事实是,无论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化,都已成为我的人生的一部分,不再能剥离。我仍然会时时反顾,但较为系统、规范的考察,或就此结束。也因写在这一时刻,动力不足、精神涣散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但想到即使在最佳状态下的写作,也难免于“未完成”“半成品”,也就稍为安心。
2010年岁末去香港开会,机舱外是圣诞节前的冬夜,深蓝的天上悬了一弯冷月。将脸贴在冰凉的机窗上,看到了一颗颗闪灼的星。倘若不是视力衰退,想必会如儿时,看到一天星斗、横亘其间的银河的吧。久居都市,已不记得上次看到繁星是什么时候。2008年初夏在敦煌,听那里的工作人员说,当地天很低,伸手可及,像是能将星星摘下来。还真有同行的朋友夜间到室外看天,或因了不走运,一无所见。
漂浮在高空,窗外是零下50多度的低温,在机舱灯下写笔记,写在一张报纸的空白处,多少感觉到一点奇特,在这个飞向温暖南方的冬夜。二十年后旧地重游,曾经住过三个月的香港中文大学的曙光楼,在那里阅读明清文献的大学图书馆,每周一次乘城铁前往的沙田的新城市广场,令人感慨。一个过程的开始与结束,人生中的一度轮回,在大历史中微末不足道,对于个人,却有可能意味深长。
此外应当说明的是,本书作为代后记的一篇,发表在2014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发言时我回顾了最初在这所大学读明清的情景,看起来像是机缘巧合。你在世间并非总有机会结下这种缘。在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考察告一段落之时,我应当向这所大学致谢。我不但在她的图书馆中有了最初的选题,且在写作本书期间两次受到由这所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的推动。我还应当感谢台湾“中研院”的吕妙芬先生的有关著作,感谢刊发本书中文字的《中国文化》《学术研究》《书城》等刊物。至于我在明清之际这一时段流连期间得到的来自大陆、台湾学术界的鼓励,我已一再表达了谢意。
在我,这是一次美好的学术之旅,尽管由我个人短暂的一生衡量,艰辛而漫长,却收获了充实与快乐。
2014年11月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学术气质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绝非故作高深、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象牙塔”之作。作者高超的文字功力在于,他能将繁复的社会结构和复杂的宗法观念,用一种近乎散文的流畅感呈现出来,让一个非专业读者也能领略到其中的精妙。我特别关注了其中对几位士大夫在仕途起伏中如何处理家庭责任的描述,这部分内容极具现实意义。他们如何在朝堂的倾轧与家庭的温情之间走钢丝?这种权衡取舍,折射出的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伦理的“人道主义”困境。这不仅仅是历史故事,更像是对我们自身在面对多重身份和责任时的深刻反思。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与一位睿智的长者对谈,他从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抛出问题,引导你去探索人性与社会规范交织下的复杂图景。
评分这部书的文字里,我仿佛看见了那个遥远时代的剪影,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挣扎与坚守,都化作了笔下的点滴。作者的叙事如同清晨的薄雾,缓缓地、层层叠叠地铺展开来,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自有动人心魄的力量。我尤其欣赏其中对细节的捕捉,那些家具的摆设,衣着的纹理,甚至一个眼神的流转,都像是被时间的洪流打磨过的琥珀,晶莹剔透,让人可以窥见彼时的风土人情。读到那些关于家庭内部微妙关系的描写时,我常常会心一笑,因为人类的情感内核似乎从未改变,只是包裹着不同的外衣罢了。这本书没有给我宏大的历史叙事,却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可以驻足休憩的角落,让我得以放下手中的俗务,静静地品味那份跨越时空的共鸣。它更像是一坛陈年的老酒,初尝平淡,回味却悠长,需要细细咂摸才能体会出其中蕴含的醇厚与复杂。
评分这本书给我的最大感受是“沉浸”,完全没有那种被生硬地拉入历史场景的违和感。文字的流动性极佳,读起来有一种古琴低吟般的韵律。我喜欢作者选择的视角,它不是高高在上的史学家评判,更像是一位亲历者或是一位体贴入微的观察者,他带着一份近乎慈悲的理解,去描摹那些人间的悲欢。比如书中对几位重要人物在遭遇人生重大转折时的心理刻画,那种克制到近乎压抑的情绪表达,让我深感那个时代对情感外露的禁锢,以及内在情感的汹涌。这种内敛的力量,才是最能打动我的地方。它不直接告诉你“悲伤”,而是让你通过他们举止的僵硬、言语的迟疑,自己去体会那份无声的痛楚。读完合上书本,房间里仿佛还残留着旧式熏香的味道,那是一种混合着书卷气和生活烟火的独特气息。
评分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是富有挑战性的,它要求读者具备相当的耐心和对古代社会结构的敏感度。我发现自己时常需要停下来,去反复咀嚼那些看似寻常却暗藏玄机的对话和行为。作者的笔法严谨考究,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这使得整部作品的基调显得非常沉稳。它不像那些畅销历史小说那样追求情节的跌宕起伏,而是更像是一幅用工笔细描的古代生活风俗画,需要你凑近了,屏住呼吸,才能看清那些隐藏在丝绸褶皱下的针脚。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对于“规矩”的论述,那些无形的束缚和内在的驱动力,是如何塑造出一个士大夫家庭的日常运作的。这种深入骨髓的文化渗透,远比单纯的政治事件描写来得震撼,它揭示了那个时代“人”的生存状态,那种既享受特权又承受重压的矛盾体。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打开了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里面装满了那个时代沉甸甸的记忆和智慧。
评分我很少用“爱不释手”来形容一本书,但这部作品的某些章节,我确实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它的魅力在于它的“真实感”,不是那种被美化或戏剧化的真实,而是那种带着泥土气息、充满烟火气的、活生生的真实。那些看似琐碎的家庭日常叙事,恰恰是构建整个时代风貌最坚实的基石。通过对这些微观场景的细致描绘,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整体脉搏。作者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力令人叹服,他似乎能看穿那些繁文缛节下的真实意图。这种对人性的洞察,超越了时代背景的限制,依然能激起当代读者的强烈共鸣。这本书仿佛是一把钥匙,轻轻转动,便开启了通往另一个时空的门,让人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评分噶啥还可以那啥还可以啦,书不错哦
评分这本书不错,虽然没看,但是看着还不错
评分好书,内容不错,值得一读。
评分赵媛的经典著作。精装本值得收藏。
评分好书,京东自营的送货速度真快呀!
评分学术专著不错,就是纸张差了点。总体还可以。
评分挺不错~~~~~~~~~~~~~~
评分挺好的书!品相很好,速度还很快!不错不错!
评分推荐阅读,经典作品,。。。。。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