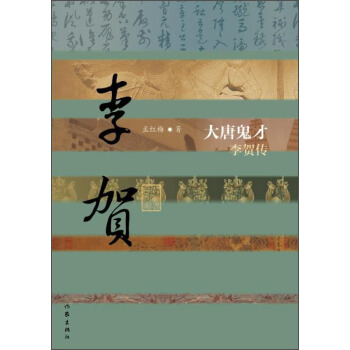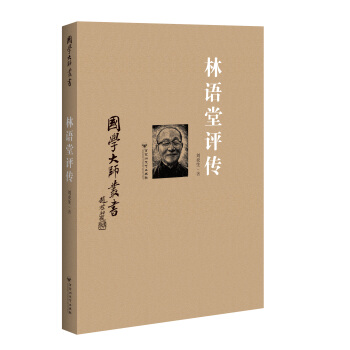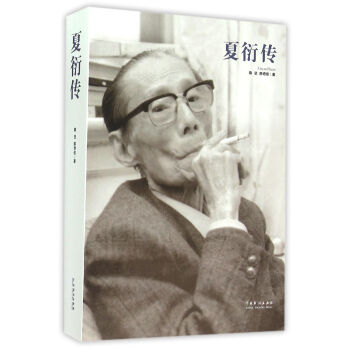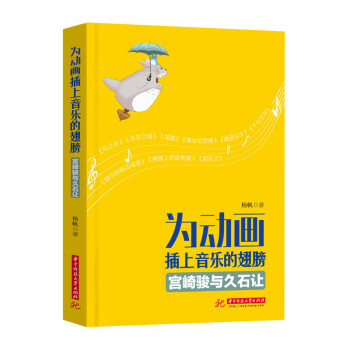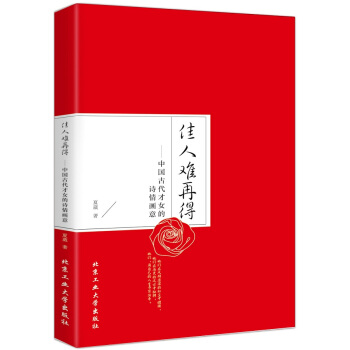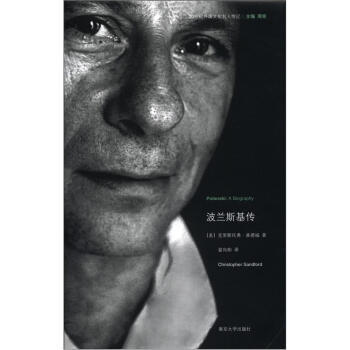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传记:波兰斯基传》以详尽的史料、精彩客观的叙述展现其充满传奇色彩,又不无坎坷心酸,且颇具争议的人生。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桑德福(Christopher Sandford),在电影和音乐评论界已有二十多年的从业史。他是大西洋两岸活跃的作者,得到《滚石》杂志的推荐。他已经出版的传记包括“滚石+主唱米克·贾格尔、主音吉他手基思·理查德,吉他宗师艾力克·克莱普顿,摇滚变色龙大卫·鲍伊,“甲壳虫”的保罗·麦卡特尼以及硬汉派演员史蒂夫·麦奎因。而他最畅销的“涅柴乐队”主唱柯特·科本的传记正在拍成电影。克里斯托弗具有英美双重国籍,目前在美国西雅图和英国的萨利轮流居住。他已婚并有一子。晏向阳,大学英语教师,业余从事文学翻译,中国译协会员。已出版的译著有《剖析恶魔》、《通往天堂的最后一站》、《乌鸦日记》、《时空飞侠》系列等。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我们希望有一些杰出的天才,把我们自己用色彩和激情展示出来,当然他们必须符合社会模式,并且能够接受可靠的管理。——英国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列
我就是景观,我在表演。
——罗曼·波兰斯基
目录
第一章 导演的剪辑第二章 希特勒时期
第三章 斯大林时期
第四章 “布尔什维克”男孩的奇迹
第五章 曼森家族
第六章 莎士比亚、性和超现实主义
第七章 审判
第八章 惊狂记
第九章 罗曼假日
第十章 奥斯卡
精彩书摘
尽管从一个永远的外来者的角度来“解释”波兰斯基的事业对他的传记作者来讲很有吸引力,可是我却认为事实正好相反。莎朗·塔特一位伦敦的密友回忆他们婚礼上“一些特别的事”时说,“波兰斯基说,尽管他很熟悉犹太和天主教的仪式,他个人却是个不可知论者。他和真正的宗教人士能有的共同之处就是放逐感。而这种感觉并非来自他的外国血统,而是人性本身。这种对这个星球的生活尤其是60年代的好莱坞生活深刻的陌生感,会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白痴。”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波兰斯基这个名字只和两类标题联系在一起:第一类是“怪物”一词的各式变换,《环球》和《明星》杂志都用这些词来报道他因为涉嫌强奸而被捕,随后又逃跑的事件;第二类是同样丰富的资料证明他是个受害者,是那些喜欢炒现饭的、小心眼的恶棍们在试图利用美国的司法制度,很可能还和CIA有勾结。这种观点近些年来在波兰斯基移居的法国尤其有市场。(读者要是想趟这趟浑水的话,可以对照看一下米亚·法罗把波兰斯基描绘成一个“对全人类来说都很重要的勇敢的好人”和洛杉矶《事实》声称要把他阉了的社论)在这两大对立的集团中,当事人自己却悄然消失了。影迷和批评家们之所以这么积极地想从他的影片中挖掘出他生活的细节的原因之一是波兰斯基自己是如此的低调。他很少接受访问,也从来不向八卦杂志Hello!展示自己美丽的家,甚至在通过英国高等法院成功追究一次诽谤行为时也用的是录像。这可是英国司法史上第一次允许索赔人通过电视屏幕来参与庭审。
1983年,当波兰斯基坐下来写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开始这样反思:“至少从我记事开始,幻想和现实之间的界限总是无可救药地模糊不堪。”有些传说,比如说把他描绘成恶棍的传记会比经过他授权的流传更久,这是他无法控制的。要说波兰斯基这些年来非比寻常的成功多少和他丰富的想象力有关恐怕没人会有异议。他的角色感,以及相应的模仿技能其实源自于他早年生活中,大概是在战争期间开始的独特的凄惨经历。那时这些都是极为现实的生存手段。波兰斯基在书中提到,他们被迫搬到克拉科
夫犹太区后不久,他和一个朋友就曾假装“我们是德国孩子”,到为德国国防军军人及其家属保留的电影院里看了一次电影——这种把戏只这么用过一次,后来大多数时候用都是为了逃生。其中有一两次可能在多年后的复述中有所修饰。之后随着名誉和声望的提升,尤其是专业演出经验的积累,他为了应付各种情况而采取更加夸张、戏剧化的手法了。在他五十岁的生日之前,波兰斯基一位巴黎的同事计划在一场盛大的晚会上用一段特别的录像来让他高兴一下。这人于是花了“好几天绞尽脑汁地”来策划实施,最终却还是放弃了。“唯一可能有效的就是弄条变色龙,让它从屏幕上爬过去。”他说。
1970年,在他拍出了《罗斯玛丽的婴儿》之后,声誉达到了顶峰。再加上受他妻子和朋友被杀影响,波兰斯基拍了一部特别恐怖的《麦克白》。因为要找演员,他联系了四十一岁的新西兰演员特伦斯·贝勒。贝勒当时在《神秘博士》及其他一些电视连续剧中表现不错,但是按他自己说的,还“绝不是电影明星”。贝勒提到了波兰斯基鲜为人知而又出人意料的谦虚故事。只要是对电影有利,他其实是非常谦逊的。那次他们俩坐在一个办公室的地板上一起吃水果。“我告诉他我当时已经签了另一个合同,
”贝勒说,“罗曼答道:‘那么,我们就把你赎出来。’我跟他说那可能行不通。罗曼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他可以大幅修改《麦克白》的时间表来凑我的档期。我觉得这样做对他来讲太不寻常了,不知是因为他真的想要我还是因为我最初拒绝了他。不管是因为哪一样,他都没有必要这么做的,尤其是以他当时的声誉。”实际上,贝勒对波兰斯基地位的看法似乎比他自己还清楚。因为后者总说他只是个“《麦克白》剧组”的普通一员。(这可不是装腔作势。)波兰斯基一生中充满了意外的转折。其中有一次,这位导演直奔一座罗马豪宅,在那儿拍摄了一部完全自我放纵的影片《什么
?》,这是一部性虐待的闹剧,就算当时70年代中期性方面极其开放的电影观众都彻底被这部影片雷倒了。
“总有一天他们会记住我的。”肯-泰南认为这就是波兰斯基敢于“肆无忌惮”的由头。这个人几乎忘了自己生活中大多数时候都处于身份危机中。1978年,洛杉矶的检察官精英们不得不加班来确认此人的国籍。而他的另外一些档案资料,比如他的姓名,多年来也同样被证明是难以确认的,尤其是在一个能把干巴巴的“木棒”斯希科隆包装成索菲亚·罗兰,把马里奥·莫里森装扮成约翰·韦恩的行业里。根据1962年春天他提供的护照,此人出生时叫作罗基莫德·罗曼·蒂埃里·波兰斯基。他的父亲是名艺术家,显然是把原来的姓氏利亚布林改成了这个艺名。小时候,他被叫作罗姆克或者罗摩·波兰斯基,直到纳粹占领波兰,他就改名叫罗曼·维尔克,听起来像是天主教徒。青春期开始时,他有了一个响亮的别名叫“普克”,不久就被一个女朋友换成了“臭小子”。
……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我总是认为,伟大的人物,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绝伦的史诗。这本书,便是对这样一位史诗般人物的忠实记录。我沉浸在他的人生故事中,感受着时代的变迁,也体味着艺术的升华。书中关于他如何从一个年轻的电影学徒,成长为世界级的导演的历程,充满了艰辛与奋斗。他对于电影语言的创新,对叙事方式的突破,都为电影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我被书中对他在创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的描述所打动,尤其是他如何在巨大的压力下,依然能够保持艺术的纯粹性,这种精神令人敬佩。他的人生,并非没有争议,但他却用自己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的艺术价值。这本书让我对他的电影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让我更加欣赏他那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艺术精神。
评分我一直对那些能够用镜头语言深刻剖析人性的导演充满敬意,而这本书,则为我揭示了其中一位大师的内心世界。他的人生,是一场与命运的抗争,也是一场对艺术不懈的探索。书中详尽地描述了他如何在逆境中保持创作的初心,如何在争议中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我尤其被书中对他在特定时期创作思路的剖析所打动,那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捕捉,都让我为之赞叹。他仿佛一位炼金术士,将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人性的光明与黑暗,都熔铸成一件件璀璨的艺术品。读这本书,不仅仅是了解一个人的生平,更是理解一种艺术的诞生过程,理解那些伟大的作品是如何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中孕育而生的。他的一些电影,曾经让我感到困惑和不安,但读完这本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看似尖锐的表达,都源于他对现实最真切的感受和最深刻的思考。
评分阅读这本书,仿佛开启了一扇通往另一个时空的大门,让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一位伟大的灵魂是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塑造自我,又如何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世界。书中对这位艺术家的童年经历的描绘,让我看到了他内心深处最初的悸动和对未知的好奇,这些早期的印记,无疑为他日后非凡的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作者以一种旁观者的审慎,又带着一种近乎崇拜的笔触,描绘了他如何在困境中成长,如何在挑战中蜕变。我特别欣赏书中对他在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艺术抉择的细致梳理,那些艰难的决定,那些充满风险的尝试,都展现了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勇气和智慧。他的人生,是一部充满复杂性和多面性的画卷,而这本书,则巧妙地将这些色彩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了一位真实而伟大的艺术家的形象。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就像是在与一位老友进行一场深入的灵魂对话。作者的叙述风格,充满了睿智与幽默,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故事娓娓道来。我惊喜地发现,这位在镜头前总是带着几分疏离感的艺术家,在书中却展现出了如此真实而鲜活的一面。他年轻时的叛逆与激情,中年时的沉淀与反思,都让我看到了一个完整而立体的艺术灵魂。书中对于他早期艺术探索的描绘,充满了青春的躁动和对未知世界的好奇,这种纯粹的艺术冲动,即使在多年之后,依然能让我感受到一股强大的力量。他的人生,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每一次挑战,每一次突破,都仿佛是在为他的艺术生涯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我尤其喜欢书中对他在不同创作阶段的心理活动进行的揣摩,那种对艺术的热爱,对表达的渴望,让我深深地被他吸引。
评分这本书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在我翻开扉页的瞬间,就将我带入了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一位艺术巨匠的成长轨迹,他早年的经历,充满了时代的烙印,既有战火纷飞的残酷,也有艺术萌芽的生机。我仿佛能听到彼时华沙街头的回响,感受到那个年轻人在贫瘠土壤中对影像艺术的炽热追求。从他对光影的独到运用,到他对叙事结构的精妙把握,无不体现着他超越时代的才华。每一个镜头,每一次构图,都仿佛饱含着他对生活最深切的体悟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他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充满了坎坷与磨难,但他却以惊人的毅力,将这些经历转化为创作的养分,淬炼出一部部惊世骇俗的杰作。书中对于他早期电影的分析,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电影美学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更加理解了他后来作品中那股独特的、混合着不安与疏离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渊源。
评分非常好,非常适用,适合初学者。
评分大爱!
评分抽空拿起这本书,[ZZ]写的的书,觉得写得很好,这是朋友介绍我看的,非常喜欢[ZZ]的书了。除了他的书,我和老婆孩子还喜欢看郑渊洁、杨红樱、黄晓阳、小桥老树、王永杰、杨其铎、晓玲叮当、方洲,莫言。他们的书我都很喜欢。[SM],大家去看一下,不错,价格也划算,比实体书店买便宜好多还省车费。 这本书的内容直得一读[BJTJ],认真赏读了一下,写得很棒,[NRJJ],内容也很很感人。[QY],一本书多读几次,[SZ]。 快递送货也给力。还送货上门。超赞。 [SM],太棒了。买书就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经常有优惠活动,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BJTJ],书,让人生更精彩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从古至今,爱书、惜书、读书都为世人所推崇。人们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增长本领,提升品位,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一个人的一生中之所以能不断提高,与其始终如一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今天你读书了吗?有一位学者曾这样说:“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从民族发展的角度看,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在一定意义上说,读书就意味着教育。 读书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艺术。 当你枯燥烦闷时,读书能使你心情愉悦;当你迷茫惆怅时,读书能平静你的心,让你看清前路;当你心情愉快时,读书能让你发现身边更多美好的事物,让你更加享受生活。“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读书是一种提升自我的艺术。 读书是一种学习的过程。一本书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叙述一段人生,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的正是这个道理。读诗使人高雅,读史使人明智。读每一本书都会有不同的收获。“悬梁刺股”、“萤窗映雪”,自古以来,勤奋读书,提升自我,是每一个人的毕生追求。读书是一种最优雅的素质,能塑造人的精神,升华人的思想。 读书是一种充实人生的艺术。
评分随便翻翻,挺能折腾的
评分非常好,非常适用,适合初学者。
评分张国荣禁色的蝴蝶,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张国荣禁色的蝴蝶可谓迄今为止,以张国荣为主题,最具思想深度的一本著作。既值得海内外哥迷珍藏回味,更应该引起广大社会读者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作者洛枫是一位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一位诗龄不短的诗人,同时,她也是一名哥迷。这本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以张国荣作为演艺者的角度出发,论辩和论证他在舞台上、电影里的艺术形象——或许,先从张国荣的生命历程及其与香港流行文化历史的关联说起,再阐释他的演艺风华。,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书是非常明智的。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抹杀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中国人讲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思想,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从而获得对于道的体悟,唯道集虚。这在传统的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中国古代的绘画,提倡留白、布白,用空白来表现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和广博深广的人生意味,体现了包纳万物、吞吐一切的胸襟和情怀。让我得到了一种生活情趣和审美方式,伴着笔墨的清香,细细体味,那自由孤寂的灵魂,高尚清真的人格魅力,在寻求美的道路上指引着我,让我抛弃浮躁的世俗,向美学丛林的深处迈进。合上书,闭上眼,书的余香犹存,而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缀叶如雨的冲淡清幽境界。愿我们身边多一些主教般光明的使者,有更多人能加入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我们的生活,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中,作者分析了张国荣的种种艺术形象,包括性别易装、异质身体、水仙子形态、死亡意识等,以丰富的资料搜集及问卷作基础,分析媒体对张国荣生前死后的论述以及张国荣迷的歌迷文化。通过作者的理性解读与诗意书写,我们得以了解张国荣是一个很有自觉意识的演员,他明白每个演出的处境,同时更知道在处境的限制中能够做些什么,进而让自我的演出超越限制而升华存在,在给予每一个角色活泼灵动生命的同时,也使他自己因那角色而蜕变出万千不同的姿彩。
评分随便翻翻,挺能折腾的
评分张国荣禁色的蝴蝶,超值。买书就来来京东商城。价格还比别家便宜,还免邮费不错,速度还真是快而且都是正版书。张国荣禁色的蝴蝶可谓迄今为止,以张国荣为主题,最具思想深度的一本著作。既值得海内外哥迷珍藏回味,更应该引起广大社会读者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作者洛枫是一位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一位诗龄不短的诗人,同时,她也是一名哥迷。这本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以张国荣作为演艺者的角度出发,论辩和论证他在舞台上、电影里的艺术形象——或许,先从张国荣的生命历程及其与香港流行文化历史的关联说起,再阐释他的演艺风华。,买回来觉得还是非常值的。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看的很杂,文学名著,流行小说都看,只要作者的文笔不是太差,总能让我从头到脚看完整本书。只不过很多时候是当成故事来看,看完了感叹一番也就丢下了。所在来这里买书是非常明智的。然而,目前社会上还有许多人被一些价值不大的东西所束缚,却自得其乐,还觉得很满足。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和发展,人们对物质需求已不再迫切,但对于精神自由的需求却无端被抹杀了。总之,我认为现代人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开阔进取,寻找最大自由的精神。中国人讲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思想,于空寂处见流行,于流行处见空寂,从而获得对于道的体悟,唯道集虚。这在传统的艺术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中国古代的绘画,提倡留白、布白,用空白来表现丰富多彩的想象空间和广博深广的人生意味,体现了包纳万物、吞吐一切的胸襟和情怀。让我得到了一种生活情趣和审美方式,伴着笔墨的清香,细细体味,那自由孤寂的灵魂,高尚清真的人格魅力,在寻求美的道路上指引着我,让我抛弃浮躁的世俗,向美学丛林的深处迈进。合上书,闭上眼,书的余香犹存,而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一个皎皎明月,仙仙白云,鸿雁高翔,缀叶如雨的冲淡清幽境界。愿我们身边多一些主教般光明的使者,有更多人能加入到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的队伍中来。社会需要这样的人,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我们的生活,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中,作者分析了张国荣的种种艺术形象,包括性别易装、异质身体、水仙子形态、死亡意识等,以丰富的资料搜集及问卷作基础,分析媒体对张国荣生前死后的论述以及张国荣迷的歌迷文化。通过作者的理性解读与诗意书写,我们得以了解张国荣是一个很有自觉意识的演员,他明白每个演出的处境,同时更知道在处境的限制中能够做些什么,进而让自我的演出超越限制而升华存在,在给予每一个角色活泼灵动生命的同时,也使他自己因那角色而蜕变出万千不同的姿彩。
评分非常好,非常适用,适合初学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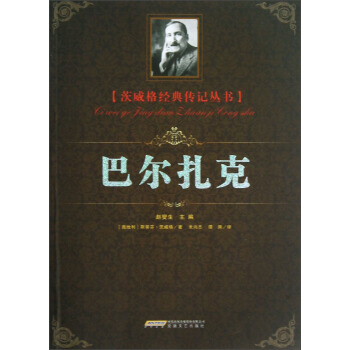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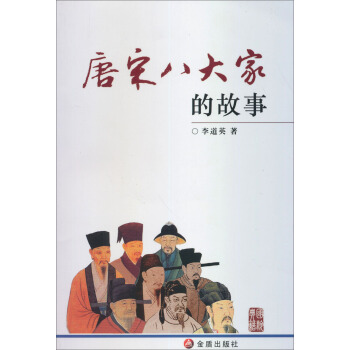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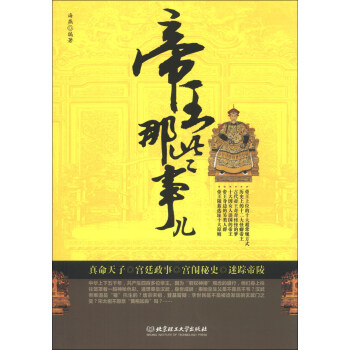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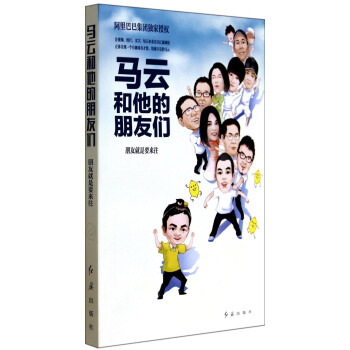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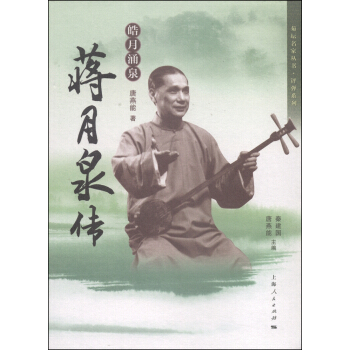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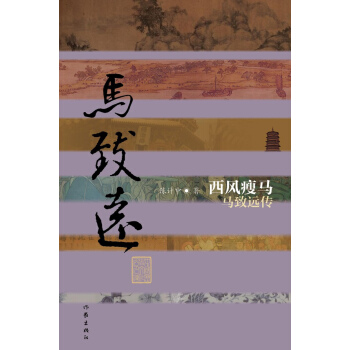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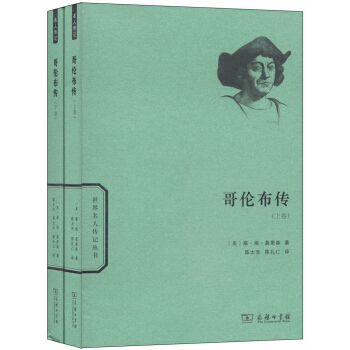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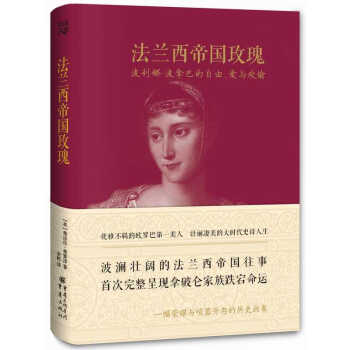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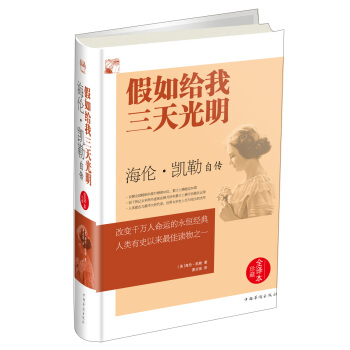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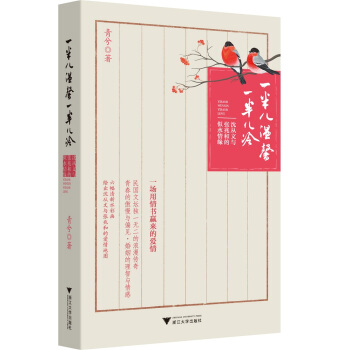
![狄更斯传 [Dicke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609276/54a90ee8N74bc063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