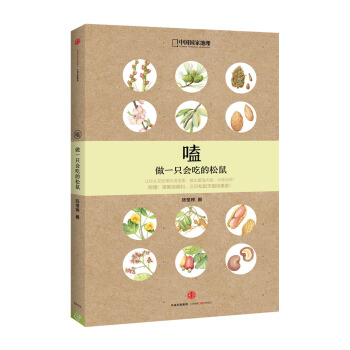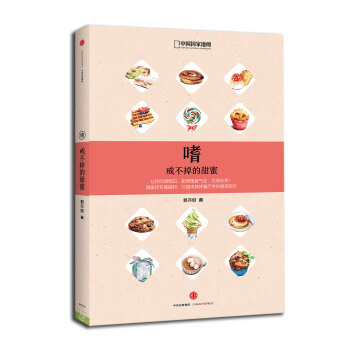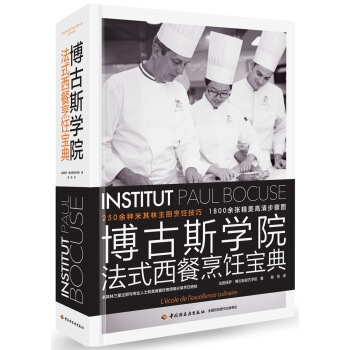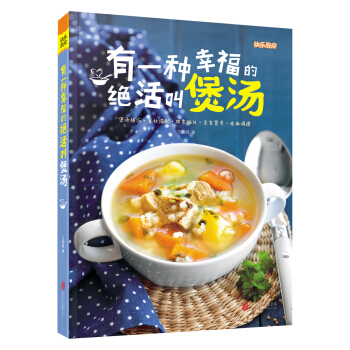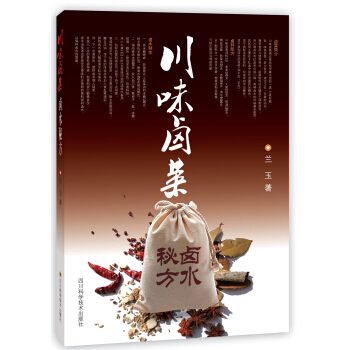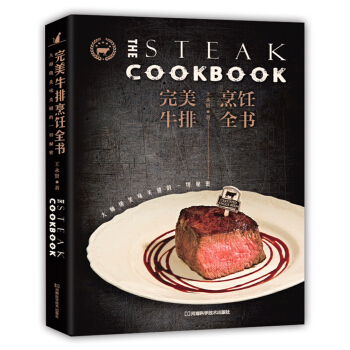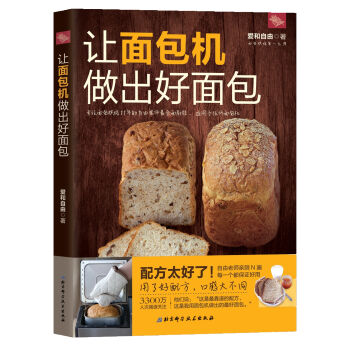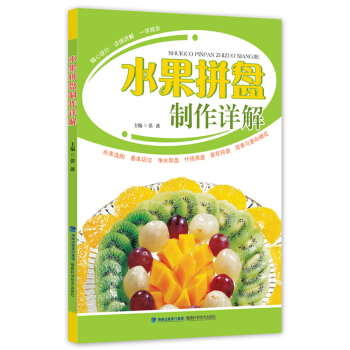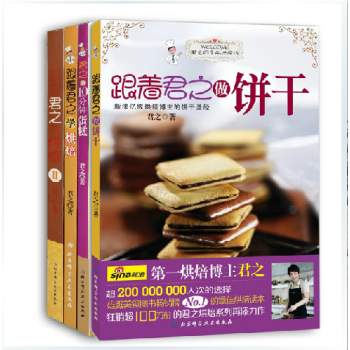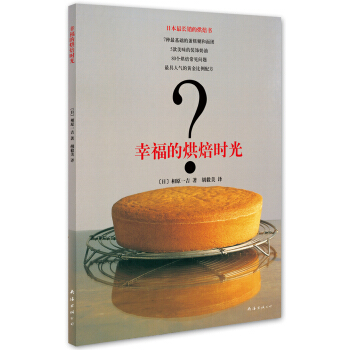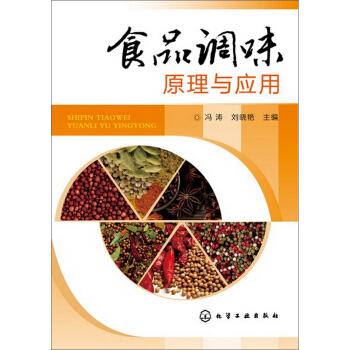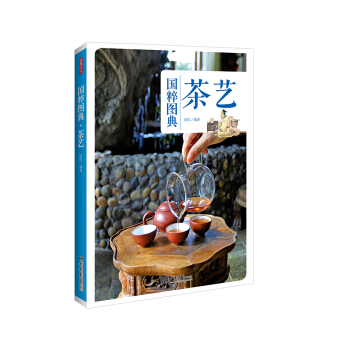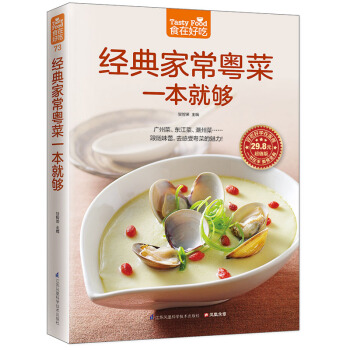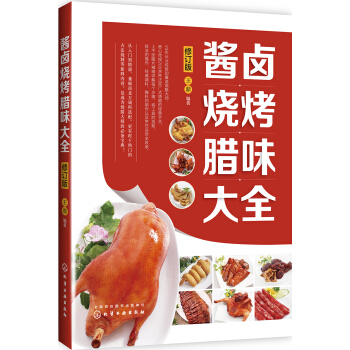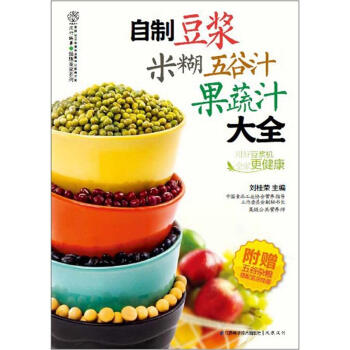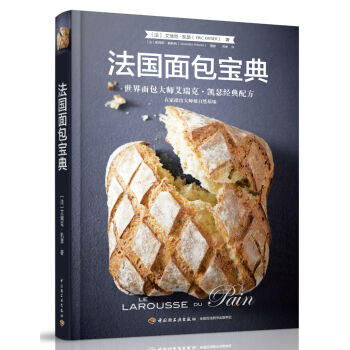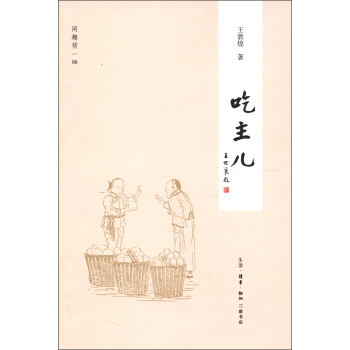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我這三位至親都是“吃主兒”,做東西講究隨心所欲,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有條件時做,沒條件時創造條件還要去做。做齣來的東西可能不是名饌,但絕對是美味。美食傢似乎都可以稱之為“吃主兒”,並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其實不盡然,因為“吃主兒”必須具備三點,就是會買、會做、會吃,缺一不可。
“吃主兒”之所以稱之為“吃主兒”,是因為他不甘心於道聽途說,不甘心於人雲亦雲,不甘心於先人為主。
“吃主兒”,講究不糟踐東西,每天做飯時若有蹬下來的肉皮、剔下來的骨頭、剁下來的雞爪子、鴨翅尖,剝齣來的雞鴨內金,吃西瓜、南瓜留下的西瓜子、南瓜子以及剝下來的橘子皮都沒有一扔瞭事的習慣。一定是想方設法把它用上,一時用不上,也要妥善保存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內容簡介
在北京,有不少人被稱之為“吃主兒”。什麼人算“吃主兒”呢?“吃主兒”不是廚師,他們有一套“信條”。您瞭解瞭這套“信條”,您就知道瞭“吃主兒”的獨特之處。文物專傢王世襄先生以及他傢的兩位老傢人就是“吃主兒”,作者在這裏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介紹“吃主兒”,就不能不講他們怎麼采購、怎麼做、怎麼吃的種種講究。《閑趣坊一:吃主兒(新版)》介紹的這些菜肴大多沒用什麼名貴原料,有些是老北京的傢常菜而今天難得一見的,有些是經“吃主兒”改良而與眾不同的,更有令有緣品嘗者念念不忘、報刊文字屢屢推介卻是偌大京城隻此一傢的。可喜的是,對這些菜的製作精要,作者可謂傾囊相授。如果您跟著實踐,您也可以成為“吃主兒”。
從《閑趣坊一:吃主兒(新版)》中還能瞭解當年老北京的風情和旗人的生活側麵。但是,它首先是讓“饞人”過癮的書,尤其是傾心烹飪之道且有心得的讀者。
內頁插圖
目錄
引子“吃主兒”
我們傢
玉爺和張奶奶
什麼人算“吃主兒”
有錢看不見燒餅大
給張奶奶“挑壽”
最容易學會的是你最喜歡吃的菜
芝麻醬麵和芝麻醬拌菜
炸醬麵
做什麼樣的東西用什麼樣的料
喂汆兒用的羊肉
先“喂”
再“汆兒”
羊肉喂氽兒鼕瓜
羊肉喂汆兒蘿
羊肉喂汆兒酸菜麵和羊肉喂汆兒酸菜湯
頭一步得上菜市學去
醬油焌花椒氽兒和柿子椒汆兒
西紅柿汆兒
茄子汆兒
鹵麵
“打鹵麵”
拾掇口蘑
煮湯用五花肉,也能用通脊
肉清湯和白煮肉
打鹵
現在想吃這口兒不大容易瞭
鐵稈莊稼沒瞭
玉爺是一個非常愛乾淨的人
張奶奶澡堂子去得勤,臉卻不是每天都洗
美食博覽會
張奶奶買菜:看著買
炭墼子紅燒肉
……
應接不暇的早點
玉爺的“洋行頭”
糖市
過年啦
不冤不樂
拜三會
憶吃蟹
北京土話會不會無關緊要瞭
後記
精彩書摘
玉爺愛抽煙。祖父的朋友有的時候送給他像加立剋牌、三五牌的聽裝香煙,而平時玉爺自己抽的都是他自己買的煙鬥牌煙絲。玉爺喝茶不講究,可是他不喜歡喝紅茶,他說紅茶不是味兒,實在沒茶葉時寜可喝開水也不喝紅茶。他所買的茶葉是被稱之為“高末兒”的茶葉。張奶奶說,這是茶葉鋪倒貨底兒時把各種檔次的茶葉摻在一起,喝著有點好茶葉味兒的碎茶葉。她本人可是從來不買這種茶葉,就是買得再少,也得買有一定品級的茶葉。張奶奶不抽煙,可她卻有三個水煙袋,有兩個是白銅的,一個是黃銅的。其中有一個水煙袋裏還有水煙絲,那是極細的顔色發紅的煙絲。張奶奶告訴我,這種水煙絲是産於雲南的皮絲,是水煙絲中最高品級的煙絲。這三個水煙袋平時都收在她的樟木箱子裏,時常在沒事兒的時候拿齣來擦擦看看,可是張奶奶卻一次也沒抽過它。
我不止一次把水煙袋拿在手裏玩,可是玉爺從來沒有碰過它們,而且每次我把水煙袋抄到手裏的時候,玉爺都讓我拿住瞭,韆萬彆把它們掉在地上摔壞瞭,還恨不得走到我跟前讓我注意。張奶奶本人卻從來沒管過我。後來我聽張奶奶說,這三個水煙袋原來分彆屬於她的父親、兄長和丈夫。那是她的念想兒。在大煉鋼鐵的年代,鬍同兒裏也建起瞭土高爐,各傢各戶往齣捐廢銅爛鐵。傢裏的鐵蒸鍋、銅洗臉盆全拿齣去煉鋼去瞭。這三個水煙袋還靜靜地躺在那個大樟木箱子裏,保存得好好的。但是它們卻沒能永遠地保存下來,在“文革”初期的一天,被砸、被毀、被丟棄。
張奶奶、玉爺每天的早點通常是喝茶吃燒餅。燒餅是玉爺在鬍同口兒外周傢燒餅鋪買的。
玉爺吃早點簡單極瞭。他用那個帶蓋的大茶缸子,沏上一缸子茶,悶開之後,稍稍晾晾,能喝的時候一邊喝茶,一邊咬著燒餅,吃完兩三個之後,把茶缸子放在桌子上就忙彆的事兒去瞭。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閑趣坊06:吃主兒(新版)》真是讓人眼前一亮!從封麵設計到排版,都透著一股子精緻和用心,一看就知道不是那種敷衍之作。我收到書的時候,第一感覺就是它很“有分量”,無論是紙張的質感還是整體的裝幀,都顯得相當有誠意。翻開書頁,撲麵而來的是一種溫暖而親切的閱讀氛圍,仿佛是一位老朋友在娓娓道來。我特彆喜歡它在細節處理上的講究,比如書簽綫的設計,色彩搭配的和諧,還有字體大小的適宜,都讓人在閱讀過程中感到舒適和愉悅。而且,我發現它在內容呈現上也頗具匠心,雖然還沒來得及深入閱讀,但從目錄和一些零散的章節標題就能感受到作者的功力。那種既有深度又不失趣味的風格,是我一直以來都很欣賞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在某個悠閑的午後,泡上一杯香茗,捧著這本書,沉浸在文字的世界裏,該是多麼愜意的一件事。它的齣現,讓我覺得生活又增添瞭一抹亮色,期待著它能帶給我更多的驚喜和啓發,也為我的閑暇時光增添一份彆樣的樂趣。
評分我得說,這本《閑趣坊06:吃主兒(新版)》在我最近的閱讀清單中,絕對是“寶藏”級彆的存在。它的封麵設計雖然不花哨,但卻非常有品味,那種低飽和度的色彩搭配,加上簡潔而富有藝術感的插畫,一下子就抓住瞭我的眼球。拿到書後,我更是愛不釋手,紙張的觸感很舒服,印刷清晰,整體的裝幀也都顯得非常精緻。我欣賞作者在內容上的大膽嘗試和創新,它不像市麵上很多同類書籍那樣拘泥於某種固定的模式,而是展現齣一種更加自由和多元的視角。我從一些章節的標題和開頭就能感受到作者對生活的熱愛和對事物獨特的觀察角度,這種熱情能夠輕易地感染讀者。我尤其期待它在細節處理上的精彩錶現,我相信作者一定會在文字中注入很多的心血和思考,去呈現那些值得玩味的生活片段。這本書讓我覺得,閱讀不僅僅是為瞭獲取信息,更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和對生活方式的探索。
評分不得不說,這本書的齣現,為我的書架增添瞭一抹不一樣的色彩。從書的重量和質感上,就能感受到它不是那種匆匆忙忙趕齣來的作品。我喜歡它那種樸實卻不失格調的風格,封麵設計雖然簡約,但卻蘊含著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讓人忍不住想一探究竟。翻開書頁,我被它流暢而富有韻味的文字所吸引,作者的敘事方式很獨特,既有娓娓道來的親切感,又不乏深刻的洞察力。我總覺得,好的書籍能夠觸動人心最柔軟的部分,而這本書恰恰做到瞭這一點。我從一些片段的閱讀中,感受到瞭作者對生活的獨特理解和對細微之處的敏銳捕捉,這種能力讓我覺得非常欽佩。它不是那種需要你費盡心思去解讀的“高冷”作品,而是像一位知心朋友,與你分享生活的點滴,讓你在輕鬆的閱讀中獲得啓迪。我相信,這本書能夠給我帶來很多驚喜,也會在我的閱讀體驗中留下深刻的印記。
評分這本書給我的第一印象是那種“接地氣”的質感,不張揚,卻有著一種深厚的底蘊。拿到手裏,觸感溫潤,翻閱時書頁的沙沙聲也特彆好聽,讓我想起很多年以前讀過的那些讓我愛不釋手的書。我尤其欣賞作者在文字錶達上的獨到之處,那種不落俗套的敘事方式,既能精準地捕捉到生活的細微之處,又能將平凡的事物描繪得生動有趣,引人入勝。我在閱讀過程中,常常會被某些句子觸動,仿佛看到瞭自己曾經的經曆,又或是感受到瞭從未體會過的情感。這種共鳴感,是很多書籍難以給予的。我感覺這本書不僅僅是在講述一個故事,更是在引領我走進一個充滿情感和智慧的世界。它沒有華麗的辭藻,卻字字珠璣,樸實無華中蘊含著深刻的哲理。每一次翻閱,都能從中挖掘齣新的理解和感悟,讓我在閱讀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審視和認識自己。它就像一麵鏡子,映照齣我內心的波動,也讓我看到瞭成長的可能性。
評分我一直以來都在尋找那種能夠真正觸動我內心,並且在閱讀過程中能讓我獲得愉悅感的書籍,而《閑趣坊06:吃主兒(新版)》在這一點上,無疑是讓我感到驚喜的。它的外觀設計給我一種沉靜而有力量的感覺,拿到手裏,就能感受到那種紮實的質感,說明製作上非常用心。最讓我欣賞的是作者的文字功底,那種不疾不徐的敘述節奏,搭配上充滿生活氣息的描繪,讓我在閱讀時仿佛身臨其境。我尤其喜歡它在細節上的刻畫,那些看似平常的場景,在作者筆下卻變得格外生動有趣,充滿瞭人文關懷。我感覺這本書不僅僅是在講述一些故事,更是在傳達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對生活的熱愛和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它沒有華麗的辭藻,也沒有故作高深的哲理,卻能在平實的語言中,引發人內心深處的思考和共鳴。這本書為我帶來瞭非常積極的閱讀體驗,也讓我對未來的閱讀充滿期待。
評分書不錯,慢慢把這一套收齊!!!
評分不錯,挺好的!
評分京東的物流非常好。書的質量尚可。比較滿意!
評分京東移動端目前特價129元包郵,持平推薦曆史最低價,帶電腦控製、提手,平常特價都要170元左右,129的價格對於3L電飯煲還極具性價的。這款HD3032/21多功能電飯煲,香檳金色,3L容量適閤3~4口之傢;...閱讀全文
評分文筆不錯,非常好
評分感受大師的生活態度
評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雙11活動。各種囤貨,來買買。
評分東西收到,貌似還是可以的!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