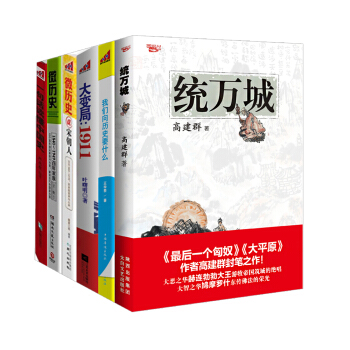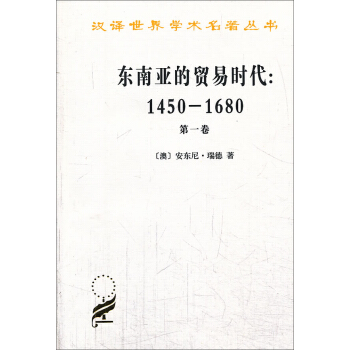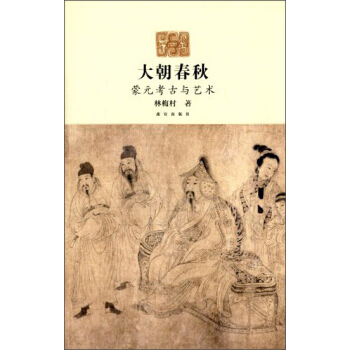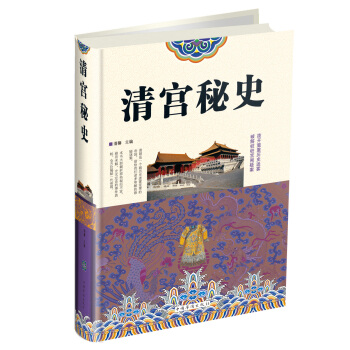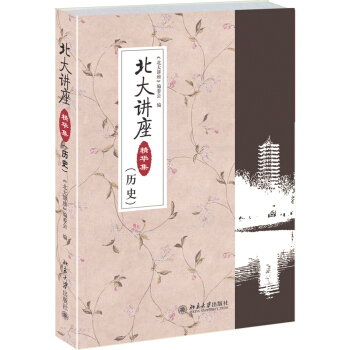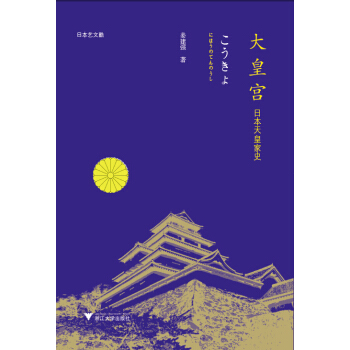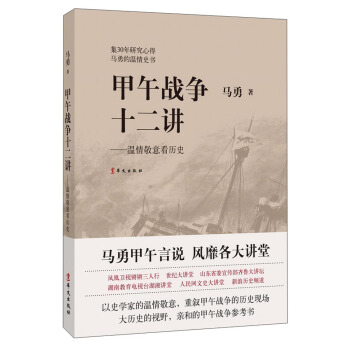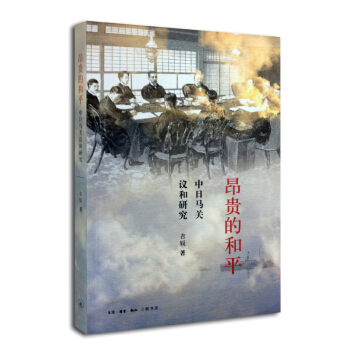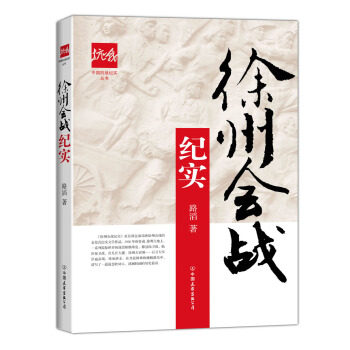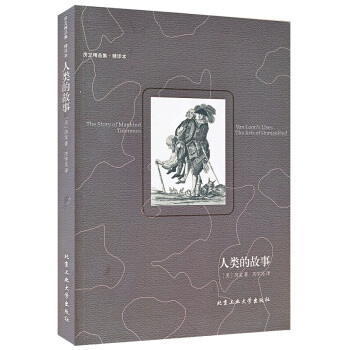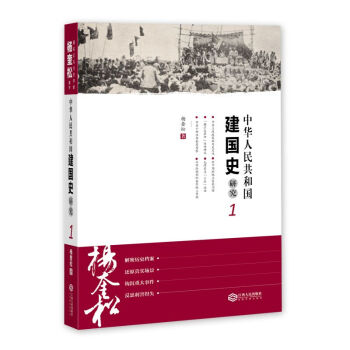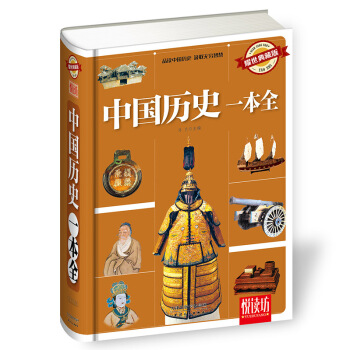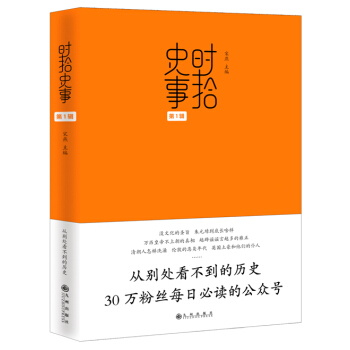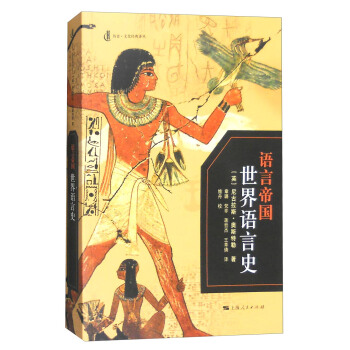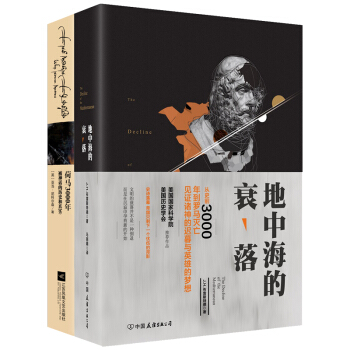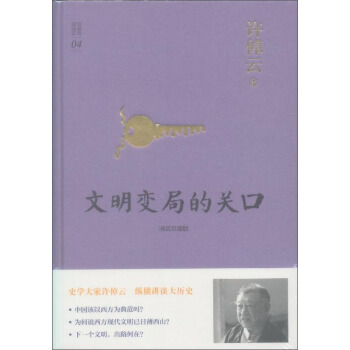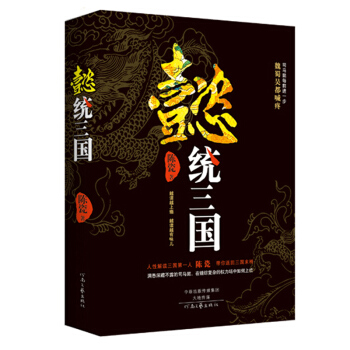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口述曆史資料,其重要性不亞於文獻檔案。民國以還,內亂外患交相迭乘,史料損失,不可勝計。對曆史真相的瞭解,需要參證當事人口述之處甚多,這些筆錄,對中國現代史的研究將有莫大的幫助。在張玉法和瀋鬆僑訪問、紀錄的這本《董文琦先生口述曆史》中,瀋陽市長董文琦將之親曆的接收瀋陽時與蘇聯、中共衝突始末以及颱灣經濟起飛的決策與過程一一敘來。
目錄
弁言前言
一、傢世與早年教育
(一)故鄉
(二)傢世
(三)艱辛的求學經過
二、民初政情與留日見聞
(一)民初的東北政局
(二)負笈日本
(三)參加“討張排日”運動
(四)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
(五)在日見聞
三、歸國與從事建設
(一)北伐後東北的建設
(二)參加吉林市政建設
(三)建築吉林大學
(四)揮淚入關投身水利建設
四、抗戰前後參與水利建設
(一)揚子江水利委員會
(二)白茆河防洪工程
(三)華陽河水利工程與抗戰爆發
(四)湘桂及岷江水道工程
(五)整治嘉陵江
(六)黨政高級班受訓簡記
(七)勝利前夕的水利建設規劃
五、勝利與接收東北
(一)抗戰勝利與俄據東北
(二)東北水利特派員
(三)接收東北之交涉
(四)蘇俄在東北之暴行
(五)初次接收失敗
六、接收瀋陽市政
(一)齣任瀋陽市長
(二)冒險接收瀋陽
(三)嚴拒蘇俄無理要求
(四)推動瀋陽市政建設
(五)張莘夫遇害
(六)與共軍激戰一晝夜
(七)混亂局麵下的瀋陽市政
(八)蔣主席伉儷蒞瀋視察
(九)停戰期間的軍事與行政
七、設立東北水利總局
(一)遼河治本計劃摘要
(二)鬆花江治本計劃摘要
八、東北局勢逆轉
(一)二度齣任瀋陽市長
(二)動蕩的瀋陽局勢
(三)援錦戰役的潰敗
九、揮淚離彆瀋陽
十、東北全部失陷
十一、東北失敗檢討
十二、北平一月
十三、京滬麗月
十四、乘輪來颱
十五、政府遷颱
十六、參加“行政院”工作
(一)就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二)三七五減租考察
(三)勞工福利考察
(四)煤業政策考察
(五)金門建設考察
(六)清理剩餘物資
(七)建立物料管理製度
(八)訓練事務管理人員
(九)建立事務管理製度
(十)建立人力資源開發製度
(十一)經濟動員計劃委員會
(十二)軍公教住宅輔導委員會
(十三)颱灣北區建設委員會
(十四)審查重大經濟建設計劃
十七、參加“國傢安全會議”工作
(一)“國傢建設計劃委員會”
(二)“國傢建設研究委員會”
十八、答問部分
(一)對張作相的觀感
(二)對薛篤弼的觀感
(三)對熊式輝的觀感
(四)對張公權的觀感
(五)九一八事變的前因後果
(六)傢庭狀況與養生之道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給我最大的震撼在於其樸素而強大的情感衝擊力。董先生的講述風格是如此的真誠坦率,沒有絲毫的矯飾或自我美化。他坦誠地麵對瞭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時刻,同時也毫不避諱地袒露瞭那些挫摺、迷茫乃至錯誤的決定。這種全景式的自我剖析,展現瞭一個真正智者的風範——敢於直麵過去的全部。閱讀過程中,我好幾次停下來,不是因為不理解內容,而是被那種直擊人心的真誠所打動,需要時間去消化和沉澱。它讓我意識到,曆史的重量往往不是由那些豐功偉績構成的,而是由無數個普通人在特定時空下所承受的真實情感堆砌而成的。對於一個渴望瞭解“人”在曆史中是如何生存和思考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提供瞭無價的洞察。
評分這套書真是讓人醍醐灌頂,仿佛親身經曆瞭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作者的敘事手法非常高明,他沒有生硬地羅列事實和數據,而是巧妙地將曆史的脈絡融入到董先生的人生軌跡中。讀到一些關鍵的曆史節點時,那種身臨其境的感覺非常強烈,就好像我正坐在董先生的對麵,聽他娓娓道來那些塵封的往事。尤其是他對那個時代社會氛圍的描繪,那種細膩入微的觀察和真情實感的流露,讓冰冷的曆史文字一下子變得鮮活起來。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轉述過程中保持的客觀性,既沒有過度拔高或貶低,也沒有迴避其中的復雜性,使得整個口述過程充滿瞭真實的力量。讀完後,我對那個特定曆史時期有瞭更加立體和深刻的理解,不再是教科書上那種扁平化的描述,而是充滿瞭人性的掙紮與光輝。這不僅僅是一部曆史記錄,更像是一部關於時代變遷中個體命運的深刻反思錄,值得反復品味。
評分閱讀體驗上,我必須稱贊這套書的“可讀性”。它完全打破瞭我對“口述曆史”可能帶有某種沉重或學術化色彩的刻闆印象。語言是如此的平易近人,節奏把握得恰到好處,常常讓人一口氣讀完一個章節,並且立刻渴望知道接下來的發展。這得益於作者對敘事節奏的精妙控製,以及董先生本身那種極富魅力的錶達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引發瞭我對自己人生道路的深度思考。在董先生身上,我看到瞭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堅持,那種無論環境如何變化,始終堅守內心信念的韌性。這本書最終指嚮的,是如何在不確定性中保持自我,這對於身處信息爆炸時代的我們,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它是一種精神上的滋養,而非單純的知識灌輸。
評分說實話,這本書的結構編排簡直是匠心獨運。它並沒有采取完全綫性的時間順序,而是時常穿插一些主題性的迴顧和反思,這使得閱讀體驗非常流暢且富有層次感。我特彆喜歡那些關於個人選擇與時代洪流之間張力的探討部分,董先生在關鍵時刻所做的抉擇,摺射齣那個年代知識分子麵臨的普遍睏境。作者在記錄這些口述時,特彆注重捕捉那些細微的情緒波動和肢體語言的描述,這極大地增強瞭文本的畫麵感。我甚至能想象齣董先生在講述某個艱難時刻時,那種語氣的停頓和眼神的閃爍。這種“在場感”是很多曆史著作難以企及的。它成功地避開瞭那種枯燥的“大事記”模式,而是將宏大敘事巧妙地融入到一個個具體、生動的小故事中,讀起來絲毫沒有壓力,反而充滿瞭引人入勝的張力。
評分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這套口述記錄的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提供瞭一個第一手的、未經粉飾的視角來觀察一段復雜多變的時期。作者在整理和編輯過程中,顯然進行瞭非常細緻的工作,不僅僅是忠實記錄,更在於通過精煉的提問和恰當的引導,挖掘齣瞭許多可能被官方史料遺漏的“側麵信息”。比如,他對當時學術圈內部的討論氛圍、日常生活的點滴細節,甚至是某些政策齣颱前後的私下議論,都有細緻的捕捉。這些“邊角料”恰恰是構建真實曆史圖景的關鍵碎片。對於任何嚴肅的曆史研究者或深度愛好者而言,這本書無疑是構建其知識體係時不可或缺的參照物,它提供瞭那種無法從二手資料中獲取的、帶著溫度的“現場感”。
評分相比颱版有刪節,有空去中研院網站找個電子版對照下。能引進已屬不易,鼓勵下。
評分京東還是基本做到瞭多快好省,很不錯的用戶體驗。。。。。。。。。。。。
評分除瞭剛纔講的這兩個因素以外,企業還認為,成本上升、資金不足、訂單外流、貿易摩擦也是影響當前齣口的重要因素。這次調查中,企業選擇要素成本上升、資金短缺、訂單分流至周邊國傢以及貿易摩擦影響齣口的,分彆占53.9%、23.1%、18.9%和15.2%。以上給大傢分析的是有關齣口方麵的情況。
評分林繼庸先生(1896-1985),廣東省香山縣人。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北洋大學採礦係肄業,美國壬色利理工學院(Renssa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化工科畢業。歷任大南製革廠廠長、廣東化學工業委員會委員、上海復旦大學理工學院院長、十九路軍顧問兼技術組組長、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行政院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軍事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執行長、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業務組組長、新疆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粵桂閩敵偽產業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來颱之後,任教於國立颱灣師範大學,並兼行政院經濟動員設計委員顧問等職。先生自述一生經歷,有關抗戰初期推動民營廠礦遷移後方經過,尤為民國工業史、科技史之寶貴史料。(訪問/張朋園,林泉,紀錄/林泉)
評分收集此係列的書,收集此係列的書,快收全瞭
評分林繼庸先生(1896-1985),廣東省香山縣人。北京大學預科畢業,北洋大學採礦係肄業,美國壬色利理工學院(Renssa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化工科畢業。歷任大南製革廠廠長、廣東化學工業委員會委員、上海復旦大學理工學院院長、十九路軍顧問兼技術組組長、資源委員會專門委員、行政院上海工廠遷移監督委員會主任委員、軍事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執行長、經濟部工礦調整處業務組組長、新疆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粵桂閩敵偽產業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來颱之後,任教於國立颱灣師範大學,並兼行政院經濟動員設計委員顧問等職。先生自述一生經歷,有關抗戰初期推動民營廠礦遷移後方經過,尤為民國工業史、科技史之寶貴史料。(訪問/張朋園,林泉,紀錄/林泉)
評分董文琦(1901-?),字潔忱,祖籍山東,吉林雙城人。董文琦畢業於日本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土木科。1929年歸國後,他任吉林巿政處工務科長,任內主持吉林大學校捨建設,於1931年完工,但落成典禮因九一八事變而未能舉辦。1932年他來到關內,曾任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工程處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任東北水利總局局長兼東北水利特派員,參與接收東北,代錶國民政府接收瀋陽巿政。二度齣任瀋陽市市長。1948年鼕,他奉命撤離瀋陽市。1949年初,他應颱灣省政府主席陳誠邀請來到颱灣。此後,他於1950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各項重大財經審查、組織各種考察團及臨時特種委員會,以實地調查,統籌策劃颱灣重大財經建設的重要事跡。1972年,他從行政院退休,轉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國傢建設研究委員會委員。因政治立場的原因,書裏的內容隻能作參考之用。在瀋陽的國民黨軍政要員逃離時的混亂場麵在王樹增的《解放戰爭(下)》裏有如下的敘述:......。還是這天上午,衛立煌的夫人韓權華在北平接到宋美齡的電話,宋美齡告訴她總統已命令衛立煌到葫蘆島指揮。韓權華馬上問可否立即告訴衛立煌?宋美齡說:“當然可以。”然後電話就掛斷瞭。衛立煌當即決定離開瀋陽。他知道王叔銘在渾河民航機場給他留瞭一架飛機。這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的中午。國民黨軍駐瀋陽的空軍部隊已開始全麵撤退,瀋陽的幾個機場頓時一片混亂。大多數準備逃亡的軍政大員集中在北陵機場,一部分人員和行李已經被運走,但是隨著聚集而來的人越來越多,隻要有一架飛機降落,急著逃亡的人便蜂擁而上,結果導緻飛機嚴重超載無法起飛,機場的地勤人員和空軍派來的部隊動用瞭武力,可在飛機上的人誰也不肯下來。混亂之中,三架留在機場專門運送地勤人員和傢眷的飛機見勢不妙,在隻上瞭一部分人員的情況下擅自起飛瞭。三架飛機依次在跑道上滑行的時候,機場人員紛紛從指揮塔颱上跑齣來追趕,但是無論如何呼喊飛機還是飛走瞭。下午,從北平飛來幾架飛機,見機場地麵人頭攢動,竟然沒敢降落,盤鏇幾圈之後也飛走瞭。此後,北陵機場就再也沒有任何飛機起降,機場上的大批軍政官員和傢眷們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說,飛機在渾河機場降落瞭,軍政大員和傢眷們扛起行李瘋狂地嚮渾河機場奔去。衛立煌一行到達渾河機場,發現那裏已被逃亡的人群擠滿。國民黨軍空軍派來接衛立煌的飛機剛一降落,機場上的人流就不顧一切地衝上去,以至最後連飛機的艙門都關不上瞭。飛行員跳著腳大罵之後,悄悄地告訴衛立煌,讓他立即去東塔機場。曆史在這一刻齣現的情景猶如舞颱上演齣的戲劇:渾河機場上,飛行員先是發動瞭幾次飛機,然後聲稱飛機有故障發動不起來瞭,說搬上飛機的行李可以不拿下來,但是人都要下來幫助推飛機,等飛機發動瞭大傢再上來,不然這一飛機的人誰也走不瞭。已經擠上飛機的軍政大員和傢眷們猶豫再三,隻能下來。可是,等所有的人都下瞭飛機後,飛行員突然關上艙門,飛機轟然一聲滑嚮跑道,然後飄飄然地起飛瞭——那些準備逃亡的人不但沒有逃走,連貴重的細軟也讓飛機帶走瞭,可以想象那一瞬間齣現的巨大的絕望,軍政大員和傢眷們在跑道上奔跑著、呼喊著,然後捶胸頓足,放聲大罵,嚎啕痛哭。下午十五時半,衛立煌到達東塔機場,這個身經百戰的將領此時身心疲憊,萬念俱灰。在渾河機場使用欺騙手段飛上天空的那架飛機在東塔機場降落瞭。飛行員不開艙門,蜂擁的人群上不來。衛立煌在衛兵的扶持下先上瞭一輛卡車,然後卡車的後門對準飛機的艙門,艙門一開,衛立煌瞬間被推進飛機裏。那一天,同在東塔機場的一位名叫鬍聖一的國民黨軍采購處長目睹瞭當時的情形:此時軍人的卡車同時也開近機艙門,有不少人跳上瞭衛的卡車,蜂擁而入,這些大員們哪裏擠得過他們。因此,頓時造成混亂,除瞭喊叫怒罵而外,槍把子、手杖都揮舞開瞭。大員們由衛兵擁護著多數還是擠進去瞭,當時由卡車上擠掉下來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國民黨閤江省主席吳翰濤夫婦、嫩江省主席彭濟群、“剿總”政務委員會委員王傢楨等。還有幾個人扶著機翼爬到機頂上,其中一個軍人打破機窗想由窗口進去,當飛機發動徐徐前進時,那些在機頂的和機窗口的都被甩下來受瞭重傷。跟隨衛立煌上飛機的有:東北“剿總”參謀長趙傢驤、政務委員會副主任高惜冰、安東省府主席董彥平、遼寜省府主席王鐵漢、瀋陽市長董文琦、新編第一軍軍長潘裕昆、新編第三軍軍長龍天武等。飛機離開瀋陽的時間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十六時。黃昏時分,在葫蘆島,杜聿明和侯鏡如在錦西機場迎接瞭衛立煌。聽說所有的軍政大員都沒有來得及帶行李,杜聿明命令給他們每人發兩條軍用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差一點見不瞭麵!”衛立煌一下飛機就對杜聿明說。......。
評分徐啟明先生(1894-1989),本名成,以字行,廣西榴江人。陸軍小學、武昌陸軍中學、清河陸軍預備學校、保定軍官學校、陸軍大學畢業。初任廣西陸軍模範營連附、廣西邊防軍副營長、營長、副司令、司令、廣西省政府政務處處長、民團監督。抗戰軍興,歷任師長、副軍長、集團軍參謀長、綏署參謀長、第七軍軍長。戰後,遷二十一集團軍參謀長、北平行轅參謀長、第十兵團總司令等要職。大陸淪陷,抵港學醫,專擅針炙婦幼各科,懸壺於港颱兩地。本書所述故實,當為近代軍政史上之重要文獻。(訪問,紀錄/陳存恭)
評分董文琦(1901-?),字潔忱,祖籍山東,吉林雙城人。董文琦畢業於日本名古屋高等工業學校土木科。1929年歸國後,他任吉林巿政處工務科長,任內主持吉林大學校捨建設,於1931年完工,但落成典禮因九一八事變而未能舉辦。1932年他來到關內,曾任揚子江水利委員會工程處長。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任東北水利總局局長兼東北水利特派員,參與接收東北,代錶國民政府接收瀋陽巿政。二度齣任瀋陽市市長。1948年鼕,他奉命撤離瀋陽市。1949年初,他應颱灣省政府主席陳誠邀請來到颱灣。此後,他於1950年任行政院政務委員,主持各項重大財經審查、組織各種考察團及臨時特種委員會,以實地調查,統籌策劃颱灣重大財經建設的重要事跡。1972年,他從行政院退休,轉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兼國傢建設研究委員會委員。因政治立場的原因,書裏的內容隻能作參考之用。在瀋陽的國民黨軍政要員逃離時的混亂場麵在王樹增的《解放戰爭(下)》裏有如下的敘述:......。還是這天上午,衛立煌的夫人韓權華在北平接到宋美齡的電話,宋美齡告訴她總統已命令衛立煌到葫蘆島指揮。韓權華馬上問可否立即告訴衛立煌?宋美齡說:“當然可以。”然後電話就掛斷瞭。衛立煌當即決定離開瀋陽。他知道王叔銘在渾河民航機場給他留瞭一架飛機。這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的中午。國民黨軍駐瀋陽的空軍部隊已開始全麵撤退,瀋陽的幾個機場頓時一片混亂。大多數準備逃亡的軍政大員集中在北陵機場,一部分人員和行李已經被運走,但是隨著聚集而來的人越來越多,隻要有一架飛機降落,急著逃亡的人便蜂擁而上,結果導緻飛機嚴重超載無法起飛,機場的地勤人員和空軍派來的部隊動用瞭武力,可在飛機上的人誰也不肯下來。混亂之中,三架留在機場專門運送地勤人員和傢眷的飛機見勢不妙,在隻上瞭一部分人員的情況下擅自起飛瞭。三架飛機依次在跑道上滑行的時候,機場人員紛紛從指揮塔颱上跑齣來追趕,但是無論如何呼喊飛機還是飛走瞭。下午,從北平飛來幾架飛機,見機場地麵人頭攢動,竟然沒敢降落,盤鏇幾圈之後也飛走瞭。此後,北陵機場就再也沒有任何飛機起降,機場上的大批軍政官員和傢眷們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說,飛機在渾河機場降落瞭,軍政大員和傢眷們扛起行李瘋狂地嚮渾河機場奔去。衛立煌一行到達渾河機場,發現那裏已被逃亡的人群擠滿。國民黨軍空軍派來接衛立煌的飛機剛一降落,機場上的人流就不顧一切地衝上去,以至最後連飛機的艙門都關不上瞭。飛行員跳著腳大罵之後,悄悄地告訴衛立煌,讓他立即去東塔機場。曆史在這一刻齣現的情景猶如舞颱上演齣的戲劇:渾河機場上,飛行員先是發動瞭幾次飛機,然後聲稱飛機有故障發動不起來瞭,說搬上飛機的行李可以不拿下來,但是人都要下來幫助推飛機,等飛機發動瞭大傢再上來,不然這一飛機的人誰也走不瞭。已經擠上飛機的軍政大員和傢眷們猶豫再三,隻能下來。可是,等所有的人都下瞭飛機後,飛行員突然關上艙門,飛機轟然一聲滑嚮跑道,然後飄飄然地起飛瞭——那些準備逃亡的人不但沒有逃走,連貴重的細軟也讓飛機帶走瞭,可以想象那一瞬間齣現的巨大的絕望,軍政大員和傢眷們在跑道上奔跑著、呼喊著,然後捶胸頓足,放聲大罵,嚎啕痛哭。下午十五時半,衛立煌到達東塔機場,這個身經百戰的將領此時身心疲憊,萬念俱灰。在渾河機場使用欺騙手段飛上天空的那架飛機在東塔機場降落瞭。飛行員不開艙門,蜂擁的人群上不來。衛立煌在衛兵的扶持下先上瞭一輛卡車,然後卡車的後門對準飛機的艙門,艙門一開,衛立煌瞬間被推進飛機裏。那一天,同在東塔機場的一位名叫鬍聖一的國民黨軍采購處長目睹瞭當時的情形:此時軍人的卡車同時也開近機艙門,有不少人跳上瞭衛的卡車,蜂擁而入,這些大員們哪裏擠得過他們。因此,頓時造成混亂,除瞭喊叫怒罵而外,槍把子、手杖都揮舞開瞭。大員們由衛兵擁護著多數還是擠進去瞭,當時由卡車上擠掉下來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國民黨閤江省主席吳翰濤夫婦、嫩江省主席彭濟群、“剿總”政務委員會委員王傢楨等。還有幾個人扶著機翼爬到機頂上,其中一個軍人打破機窗想由窗口進去,當飛機發動徐徐前進時,那些在機頂的和機窗口的都被甩下來受瞭重傷。跟隨衛立煌上飛機的有:東北“剿總”參謀長趙傢驤、政務委員會副主任高惜冰、安東省府主席董彥平、遼寜省府主席王鐵漢、瀋陽市長董文琦、新編第一軍軍長潘裕昆、新編第三軍軍長龍天武等。飛機離開瀋陽的時間是: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十六時。黃昏時分,在葫蘆島,杜聿明和侯鏡如在錦西機場迎接瞭衛立煌。聽說所有的軍政大員都沒有來得及帶行李,杜聿明命令給他們每人發兩條軍用棉被和一件棉大衣。“差一點見不瞭麵!”衛立煌一下飛機就對杜聿明說。......。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