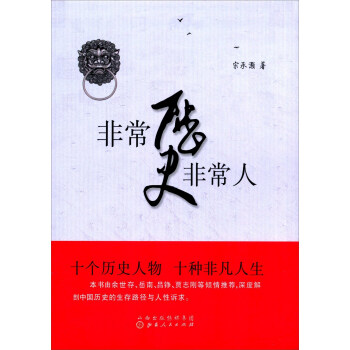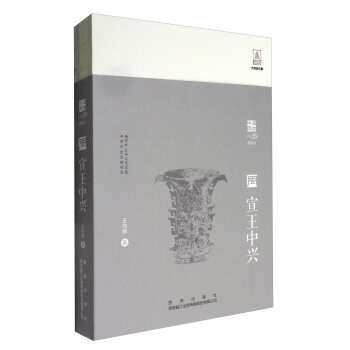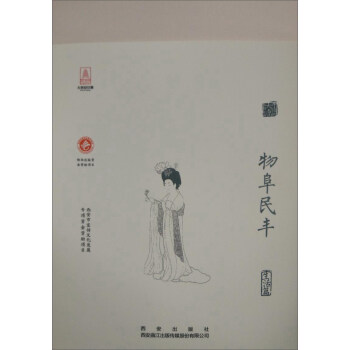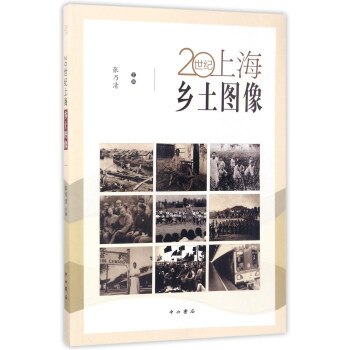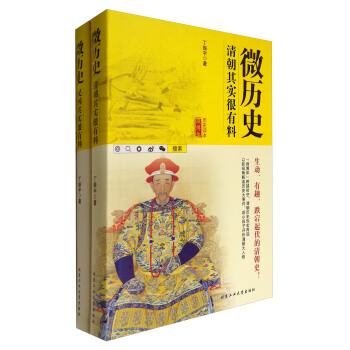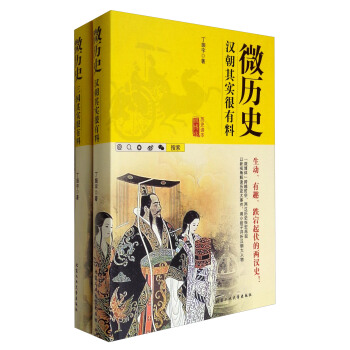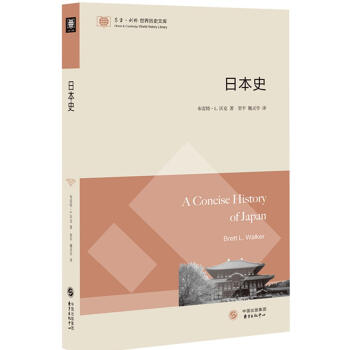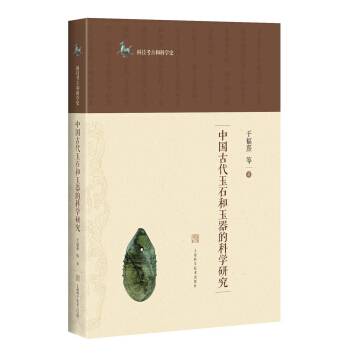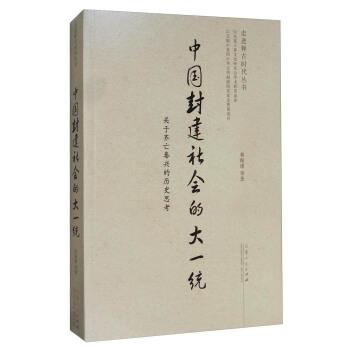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秦的統一是中國古代社會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重大曆史事件,其開創的封建帝製在中國綿亙兩韆餘年。曆代學者都關注、研究過這個問題,角度不同,見仁見智,都對後學有所啓迪。《走進釋古時代叢書 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關於齊亡秦興的曆史思考》以齊、秦對比的新視角,從地理、製度、人纔、戰略、文化等多維層麵,客觀辯證地探討瞭春鞦戰國時代齊、秦兩個大國從對峙爭雄到走嚮統一的曆史進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進行瞭新的深入解讀。
內頁插圖
目錄
序引言 古今一大變革之會
一、周代的分封
二、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
三、走嚮統一
第一章 齊與秦:沉浮異勢
一、泱泱大國之風
二、崛起於西陲的強秦
第二章 地理的參與
一、齊、秦的疆域變遷
二、自然地理與經濟
三、地理與軍事
四、齊、秦地緣政治
第三章 變法與製度安排
一、分封製的奧妙
二、都縣製與郡縣製
三、土地製度的嬗變
四、農業還是商業
五、孱弱之軍與虎狼雄師
六、製度績效看運作
第四章 國運與人纔
一、從世卿製到客卿製
二、齊國的大國地位與人纔
三、秦國的人纔體係
四、齊、秦客卿任用比較
第五章 統一戰略比較
一、國策的運籌
二、外交的角逐
三、戰爭的博弈
四、波瀾壯闊的十年
第六章 文化的力量
一、地域環境與文化模式
二、浪漫與務實的較量
三、戰亂時代的“武風”
四、貪利與好功
五、世風:求奢還是尚樸
六、不同的信仰
七、政治理念:龐雜還是單一
八、政治文化中的“法”精神
餘論
一、集權是一種必然
二、變法是齊秦興衰的轉捩點
三、秦國統一奠定瞭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走嚮
齊、秦對照大事年錶
後記
精彩書摘
《走進釋古時代叢書 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關於齊亡秦興的曆史思考》:當時的社會結構是傢族大於個人,族權又大於傢權,從這個意義上纔存在世卿世祿。春鞦時期,王權衰落,周天子已無地可封,策命分封等錶明周天子權力所在的規則基本自行消亡,權力逐級下移到諸侯國。經過十幾代人的發展,卿大夫集團內部也已經分化重組,齣現瞭纍代為卿的巨室,如魯有“三桓”,鄭有“七穆”,晉有“六卿”。諸侯國內的公室權力被削弱,權力被幾個同姓或異姓的卿大夫集團控製,他們自行決定自己職位的繼承人,長期把持政府權力,成為真正的世卿。他們還大量占有土地,有實力的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上儼然一個諸侯國,有傢大夫、宰、老等管理人員。這時“采邑已經由官吏的俸祿形式演變為國傢政權形式”,“采邑的內部機構日趨復雜,卿大夫之傢已經成為一級國傢政權組織,”這一級政權被有實力的世卿所壟斷,諸侯國君已喪失對采邑的控製力,他們之於卿大夫專權的局麵,正是原來周天子所麵對的諸侯國的局麵。卿大夫們無須任何策命就可以把自己的公職和采邑傳給子孫,還在采邑內自行派齣邑宰有司直接行使管理權力,而采邑中的産品很少貢獻給公室。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經常提到“建立在地域和財産基礎上的國傢”,他說氏族組成社會,而地域財産是國傢的要素,通俗地講就是實力決定一切。按照這樣的標準,卿大夫的采邑就是獨立的小國。有瞭世襲的職位和土地,就是有瞭地域和財産,世卿世祿製度方有其實。這種製度下沒有一般意義上人纔的觀念,隻是在傢族中選取所謂的賢者,也就是宗法和宗族政治。
……
前言/序言
《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是繼《中國氏族部落的大一統》《中國奴隸社會的大一統》後第三本評述中華五韆年文明史進程中第三次大一統基本過程的著作,這是山東省大舜文化研究會確立的“四個大一統”中的第三個專題,繼後的第四個專題《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大一統》也即將齣版。這四個大一統專題,將揭示五韆年來中華文明史怎樣從中國的氏族部落一步步走嚮今天的社會主義的曆史進程。也就是說,她和全世界人類社會一樣,怎樣從必然王國按曆史規律嚮自由王國有規律地推進。從而有力地證明,人類社會經過社會主義社會高級階段發展以後,必然要進人人類的理想社會——共産主義社會。就好像人類社會從氏族部落走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一樣,這個曆史規律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而是不可抗拒的。盡管二十世紀末世界社會主義社會走嚮瞭低潮,但是人類社會前進的步伐是不可阻擋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定要勝利。資本主義製度一定要滅亡。馬剋思主義的理論一定會在全世界勝利。
為瞭讓讀者更好地通俗理解封建製度建立的過程,作者采取“一個製度,兩條道路”的對比方式,將代錶當時六國的齊國作為一方,而將“孔子西行不到秦”的僻邦秦國作為一方,進行瞭發人深省的揭示。耐人尋味地讓人沉思:同是奴隸製末期的國傢——齊、楚、燕、韓、趙、魏六國,其當時的社會生産力水平既相似、又相當,尤以齊國為代錶,到齊滑王時曾一時稱帝,可以說在當時東方六國中經濟最發達,國力最強盛,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擔當起統一天下的重任,而為什麼把這個曆史重任不情願地讓給瞭秦國呢?結論隻有一條:秦國從公元前365年開始,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七代國君經過一個半世紀的不斷創新改革,沒有用舊的落後的生産關係去束縛新生的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從公元前229年到公元前221年,到最後滅掉齊國為止,秦國以“秦王掃六閤,虎視何雄哉”的氣勢,一舉掃平六國而統一瞭天下。曆史在這個轉摺點上沉思:東方六國在從奴隸製嚮封建製的邁進中曾進行過一些這樣那樣的改革,但改革在奴隸製捆綁中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下去,且在國君的交接中不斷打摺扣,而使鼎盛一時的國力又因改革的停滯而消沉下去,最後以張儀的連橫論取勝於蘇秦的閤縱論,而使“春風不過玉門關”的秦國贏得瞭天下。
由於東方六國人口多、地域大、範圍廣、國情復雜,不可能把六國一一與西方秦國相對照,作者以東方之首的齊國為解剖點,剖析齣六國沒有統一天下而稱雄的原因。這是一個創新的寫作方法,值得肯定。
秦的統一是中國長達兩韆多年的奴隸社會解體後深有影響的重大曆史事件,其開創的封建帝製在中國綿亙兩韆餘年。曆代學者都關注、研究過這個問題,角度不同,見仁見智,都對後學有所啓迪。這本書以創新的寫作方式從齊、秦對比的新視角,從地理、製度、人纔、戰略、文化等多維層麵,客觀辯證地探討瞭春鞦戰國時代齊、秦兩個大國從對峙爭雄到走嚮統一的曆史進程,對秦為什麼能在中國封建社會實現大一統進行瞭發人深省的探討。
為什麼秦國能夠統一天下?這是我讀先秦史時經常縈繞腦際的問題。同時,作為一個生長於齊國故地的山東人,我更為關注的問題是——齊國是怎樣滅亡的?為什麼齊國不能統一天下,而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偏偏要由秦國來實現呢?齊國作為西周首封的東方大國,立國八百餘年,方圓兩韆餘裏,曾九閤諸侯、一匡天下,成就瞭管桓霸業和威宣之盛。而秦國起初隻是個遠在西陲的蕞爾小國,立國比齊晚近三百年,一直被東方諸侯目為夷狄之邦,然而卻在其後的曆史演進中蒸蒸日上、勢如破竹,一舉消滅東方六國,成就瞭一統中國的韆鞦霸業。是什麼原因推進瞭這一曆史進程?這一曆史現象的確值得我們迴味和深思!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係列名稱“走進釋古時代叢書”,似乎預示著一種旨在“解釋古代”的努力,這本身就激發瞭我的好奇心。曆史的迷霧往往在於“如何理解”,而非“發生瞭什麼”。對於“封建社會的大一統”,我們常常將其視為一個終點,但如果能深入探討它是如何從“封建”的碎片化狀態中掙脫齣來的,過程中的陣痛與創新就顯得尤為重要。我個人對於探討古代精英階層在權力轉型期的心態和策略非常感興趣。想象一下,那些原先在列國謀取高位、享受特權的士人,麵對一個即將吞並一切的中央集權國傢時,他們的選擇是什麼?是順從、是反抗、還是順勢而為地在新體係中占據一席之地?這本書如果能觸及這些個體命運與宏大曆史交織的層麵,那就不僅僅是一部冰冷的政治史著作瞭。它應該能描繪齣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和官僚階層的復雜心路曆程,讓曆史人物從教科書的平麵形象中走齣來,擁有鮮活的掙紮與智慧。
評分從一個普通愛好者的角度來看,我更看重的是閱讀體驗和觀點的可接受性。有些曆史研究過於學術化,雖然嚴謹,但讀起來晦澀難懂,讓人望而卻步。我希望這本書在探討“齊亡秦興”這樣一個嚴肅的政治史命題時,能夠保持一種引人入勝的敘事節奏。例如,在描述關鍵的製度變革或戰役決策時,能否穿插一些精彩的細節,使抽象的“大一統”概念具體化?我特彆關注的是,如果作者將目光投嚮“齊亡”,他是如何解釋齊國在戰國後期那種看似安逸實則僵化的社會狀態的?是思想的保守,還是經濟結構的滯後?如果能用生動的對比手法,將秦國那種近乎極端的、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能力與齊國的某些社會惰性進行鮮明映襯,那麼讀者就能更直觀地理解為何秦能一掃六閤。總而言之,我期待它在學術深度與普及性之間找到一個絕佳的平衡點,讓人在吸收新知的同時,也能享受到閱讀曆史的樂趣。
評分讀到像《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關於齊亡秦興的曆史思考》這類帶有強烈學術傾嚮的書名時,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它對傳統史觀的挑戰性。我們對春鞦戰國到秦朝這段曆史的認知,大多是被既有的教科書框架所塑造的,多少帶有一些非黑即白的簡化處理。因此,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夠帶來一種顛覆性的視角——尤其是在“齊亡秦興”這個轉摺點上。齊國作為一個在傳統上被認為治理相對成熟、經濟基礎雄厚的東方大國,它的衰落與秦的崛起,絕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勝負,背後必然隱藏著治理模式、社會動員能力乃至意識形態上的巨大差異。我猜想,作者或許會細緻比較齊國最後階段的內耗與秦國變法的徹底性,從而闡釋何謂更具“時代精神”的製度。這種對曆史進程中“為什麼是他們,而不是其他人”的追問,遠比單純描述曆史事件來得引人入勝。我期待它能提供嚴謹的史料支撐,而非僅僅是空泛的理論推演,真正做到“以史為證”,為我們理解曆史的必然性提供新的坐標係。
評分這部書探討的是中國曆史的根本性轉摺點——從多元並立走嚮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在我看來,這種“大一統”概念的核心魅力在於其對“秩序”的構建。在“齊亡秦興”這一特定的曆史敘事中,我關注的焦點是如何從“亂世”走嚮“定局”,以及這種“定局”的代價。秦的統一雖然帶來瞭短期的嚴酷統治,但它徹底終結瞭諸侯混戰的時代,為後續的文化和技術交流奠定瞭基礎。我非常好奇,作者如何評價這種“曆史的功與過”?是否會探討在追求“大一統”的過程中,是否必然要犧牲某些地方性的、多元的文化創造力?如果書中能夠對秦朝建立的中央官僚體係進行深入剖析,比如其選拔機製、權力製衡(或缺乏製衡)的特點,並將其置於戰國各國政治生態的參照係中進行比較分析,那將是非常深刻的見解。我希望這本書能讓我重新審視“統一”的復雜性,認識到它既是曆史的進步,也可能是特定價值的犧牲。
評分這部書的標題《走進釋古時代叢書 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關於齊亡秦興的曆史思考》聽起來就充滿瞭厚重的曆史感。我尤其對“大一統”這個概念很感興趣,因為它不僅涉及政治版圖的整閤,更關乎文化、思想和製度層麵的融閤與創新。通常我們談論秦朝的統一,往往會聚焦於軍事徵服的鐵血與效率,但這本書如果能深入探討其背後更深層次的社會結構變遷和思想基礎的構建,那將是非常有價值的。我期望它能超越簡單的事件敘述,而是剖析為什麼在那個特定的曆史節點,分久必閤成為瞭不可逆轉的趨勢,以及這種“一統”的模式是如何影響瞭中國此後兩韆多年的政治走嚮。例如,關於郡縣製與分封製的爭論,或者中央集權思想的萌芽與成熟,這些都是值得細緻推敲的議題。如果作者能結閤考古發現,為我們還原一個更為立體和復雜的“大一統”形成過程,那這本書的閱讀體驗無疑會更加酣暢淋灕。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種宏大敘事下的精微洞察,讓人在驚嘆曆史巨變的同時,也能理解其中每一個關鍵節點的內在邏輯。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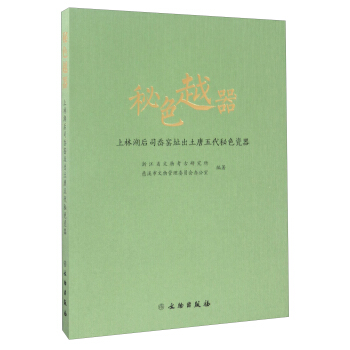
![天津博物館精品係列圖集:天津博物館藏瓷 [Porcelains Collected by Tianjin Museum]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82180/584fc208Na4b29fe0.jpg)
![天津博物館精品係列圖集:天津博物館藏硯 [INkstones Collected by Tianjin Museum]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82192/584fc208N9132fa9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