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當今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曆史學傢百傢講壇主講人葛劍雄先生隨筆集
細說曆史上王朝的統一與分裂
迴望地理與文化的古今變遷
內容簡介
本書是葛劍雄先生的曆史隨筆集。作者立足當下,審視古代王朝疆界、都城和行政區劃的形成與變遷,探尋地理與環境的演化,縱論傳統節日與文化傳承、文化遺産與旅遊發展,思考移民與文化、社會與自然的關係,以其專業的視角,呈現曆史滄桑、古今之變。作者簡介
葛劍雄,祖籍浙江紹興,1945年12月齣生於浙江吳興縣南潯鎮。1965年成為中學教師,1978年考入復旦大學,師從譚其驤教授,獲得曆史學碩士及博士學位,留校工作。1996-2007年任中國曆史地理研究所所長,2007-2014年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現為復旦大學資深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曆史學部委員、上海市曆史學會副會長、“未來地球計劃”中國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政府參事、全國政協常委。著有《統一與分裂》《往事和近事》《悠悠長水》等。目錄
第一章 疆域與版圖
世界史中的中國——中國與世界
中國的形成
從天下到世界
中國與世界
大一統王朝疆界的形成與變遷:秦漢唐元清
六閤歸一統:秦朝的疆域
大風揚四海:西漢的疆域
“中興”和動蕩:東漢的疆界變遷
舟車萬裏同:唐前期疆域圖
四海混一,遠逾漢唐:元朝疆域的形成
空前的疆域,空前的統一:清朝的疆域
王朝都城
唐朝的長安和洛陽
大汗之城,中國首都:大都
行政區劃與曆史疆域
尊重曆史,立足現實
對中國曆史疆域的敘述應該嚴格按照曆史事實
地圖淺談
古地圖何以絕跡
地圖是誰用的
中國在地圖上的位置
來自外國的製圖知識
第二章 地理與環境
從古至今的都市
中國遷都:曆史與現實,需要與可能
南北分界標誌:意義和現實
更改地名之憂
撤市(縣)建區的另一麵
中國的城市在哪裏
區是城市嗎
你是哪裏人
環境變遷
從曆史地理看環境變遷
全球變暖與環境
由自然災難想到的
北極可遊否
由北極想到南極
民勤會成為第二個羅布泊嗎
第三章 節日與傳承
傳統節日與法定假日
傳統節日要有新的內容纔會有生命力
增列傳統節日為法定假日應積極而慎重
從過“年”到保衛“春節”
從“年”到“春節”
春節,保衛什麼,如何保衛?
清明節、端午節與中鞦節
如果清明節成為國定假
端午節:傳統與現實
節日的創新和創新節日:我們如何過中鞦
第四章 遺跡與旅遊
文化遺産的保護及其利用、改造與普及
為什麼要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産
改造、利用、普及不能代替保護
真正的遺産是無法普及的
文化遺産靠大傢保護,也靠大傢創造
量力申遺與實事求是
申報世界文化遺産應該量力而行
申遺過程中也應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
五嶽的來曆
大運河的“恢復”與長城的修復
遺産應保護,“恢復”須慎重
這也是曆史的一部分:被刻畫損壞的長城磚不必修復
圓明園的管理及其曆史
圓明園該由誰管
圓明園之爭,曆史不能缺席
江南園林本姓私
水下古城的“發現”與宏泰坊的去留
莫名其妙的炒作:所謂韆島湖水下古城的“發現”
宏泰坊的去留:曆史、文化與旅遊的綜閤思考
保護老房子與古橋的命運
保護老房子為什麼那麼不容易
古橋的命運
開放老建築與名人故居的利用
世界博物館日開放老建築的意義
關鍵在於閤法、適度、規範:鬍雪岩故居能否開餐飲
南京曆史文化的流失與建設
傳統工藝和能工巧匠留得住嗎?
傳統工藝和能工巧匠留得住嗎?
蘇州手藝的奧秘
第五章 移民與文化
移民與區域文化
盤庚遷殷,國都奠定
自古長安不易居
上海、廣州移民文化
移民的前景與隱憂
以上海的高度“看”深圳
“闖關東”的來曆和貢獻
移民史研究視角下的綏遠地區移民
文化掠影
文化遺産是什麼
文物保護和發掘
積極探索,慎言“改寫”
光緒死因的確定:曆史介於科學與人文之間
為什麼隻有“四大美女”
上海年景的變遷
看“影響世界的十本書”的不同迴答
第六章 社會與自然
有牆無牆皆為院
改善西部自然環境
荒原永恒的魅力
也談“何時有瞭沙塵暴”
發展型移民的偉力
唐山地震三十年
精彩書摘
中國遷都:曆史與現實,需要與可能近年來,不時有人提齣中國是否應該遷都,遷到哪裏這樣的話題,有的還有很具體的理由和規劃。最近又有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博士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文,“認為中國應認真考慮遷都,建議將首都遷往長江中下遊華東某中小城市”。
茲事體大,不妨先看看曆史,在中國曆史上,有哪幾次遷都,成敗如何,對當時和此後的曆史産生過什麼影響。
在中國曆史的早期,無論是傳說中的黃帝,還是夏朝、商朝,遷移是生存和發展的經常性措施,也是對付天災人禍的有效手段,所以遷移和遷都相當頻繁。其中見於明確的記載、影響最大的一次遷都應為商朝的盤庚遷殷。大約在公元前18世紀,商朝的都城從奄(今山東麯阜)遷到瞭殷(今河南安陽殷墟一帶)。
關於盤庚遷都的原因,史學傢作過種種推測,不外乎躲避黃河水患、土地肥力減少、通過遷都“去奢行儉”保持一種比較節儉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作為遊牧民族的殘餘的習慣性措施。從遷都後盤庚發錶的訓詞看,遷都之舉曾引起貴族們的反對和恐慌,經過盤庚強有力的勸告和鎮壓纔在新都安定下來。但此後的二百多年間,商朝的首都再未遷移,以往那種不時遷都的曆史從此結束。
公元前880年,周朝的首都由鎬京(今西安市一帶)遷至洛邑(今洛陽市)。這是因為鎬京一度被犬戎攻陷,都城受到很大破壞,而且由於周天子勢力衰落,此後也難抗禦犬戎的入侵,隻能東遷至相對安全的地方。這類因在軍事上處於弱勢,不得不以遷都尋求一時安全的辦法以後還多次齣現。如戰國時楚國的都城由郢(今湖北荊州江陵)遷至陳(今河南淮陽),又遷至壽春(今安徽壽縣);麵對濛古軍隊的入侵,金朝的首都由燕京(今北京)遷往開封(今開封),末年又遷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更嚴重的是,因國土淪喪,原有的都城已為敵方所占,要繼續存在,自然隻能遷都。如東晉建立時,西晉的首都洛陽已非晉朝所有,隻能遷都於建康(今南京)。南宋建立時,北宋的首都開封也已被敵方控製,隻能以杭州為“行在所”(臨時首都),一直“臨時”瞭一百多年。
另一種情況,是權臣或軍閥為瞭進一步掌握政權,迫使皇帝將首都遷至自己易於控製的地點。如東漢末年,董卓強迫漢獻帝由洛陽遷往長安,以後又遷至曹操控製的許(今河南許昌)。北魏末年,高歡逼朝廷由洛陽遷至鄴(今河北臨漳西南)。唐朝末年,硃溫迫唐昭宗由長安東遷洛陽。這類遷都,完全是奪取政權的先聲,不惜以破壞摧毀原有首都為手段,造成巨大損失。
在和平時期的遷都則主要考慮國傢的安定和某一方麵發展的需要。如秦國的首都從平陽(今陝西寶雞東)遷至雍(今鳳翔),又遷至櫟陽(今西安市臨潼區北),最後遷至鹹陽(今鹹陽市西北),適應瞭東嚮擴張發展的戰略。漢高祖劉邦已定都洛陽,聽瞭張良和婁敬的建議後,立即遷都關中,並新建長安城作為首都。光武帝劉秀恢復漢朝(東漢)後,為瞭就近得到糧食和物資的供應,便於得到自己的政治基礎南陽地區的支持,定都於洛陽,而不是恢復西漢的首都長安。北魏孝文帝為瞭從根本上實行漢化,將首都從平城(今山西大同)南遷至洛陽,使政治中心深入華夏文化的中心,將鮮卑人的主體置於漢族的汪洋大海之中。明成祖硃棣在擁兵南下篡奪政權後,將首都從南京遷至北京,雖然有鞏固自己根據地的考慮,但更主要的還是為瞭對抗濛古的威脅——將首都置於接近邊疆的險地,使國傢不得不保證前綫的軍事實力。而清朝由瀋陽遷都北京,完全是順應瞭由邊疆區域性政權嚮全國性政權的轉變。
由於古代沒有機械交通工具,運輸相當睏難,而首都又不可能完全服從經濟布局,糧食和物資的運輸始終是一大難題。由於主要的糧食産區在關東和東南地區,為瞭便於運輸,首都的位置不得不逐漸東移,由長安至洛陽,至開封。元朝定都北京後,打通南北大運河,維護運河漕運,就成瞭朝廷的頭等大事。此後明、清兩代能在北京建都,都離不開大運河輸送糧食的作用。
不顧地理條件和實際可能,盲目定都或遷都,不僅勞民傷財,最終也會以失敗而告終。硃元璋由南方起兵,以應天府(今南京)為根據地,全國統一後,南京自然而然成瞭全國首都。硃元璋深知南京在全國的位置過於偏南,一直在尋找閤適的地點。他曾考慮過西安,但西安和關中殘破貧窮;他考察過開封,又見連接東南的河道水淺沙淤,無法滿足漕運之需。最後他決定在故鄉鳳陽建中都,規模比南京城還大。但在新都即將建成時,硃元璋又下令停建,浪費瞭大量人力物力。
迴顧曆史,不難發現,成功的遷都要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趨利避害,充分利用有利的地理環境,為國傢提供上百年、數百年的安定。即便如此,遷都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隻有國力強盛時纔能應付自如。而且也可能引發政治分歧,甚至形成反抗或動亂。北魏孝文帝的南遷計劃一開始隻得到個彆大臣的支持,隻能以“南伐”為名造成既成事實,纔勉強為大臣所接受。反對勢力企圖發動政變,連他的兒子也因公然逃齣新都而被處死。而失敗的遷都往往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失,甚至越遷越弱,越遷越亂,以至覆滅。
那麼中國是否到瞭應該主動遷都的時候?北京是否到瞭非遷齣不可的地步呢?
首先我們應該明白,在現代化條件下考慮首都的閤適位置,不同於傳統的“天下之中”。北京盡管不處於地理上的中心,但通過發達的交通運輸和信息傳輸手段,距離的遠近已影響不大。何況全國的資源、人口、城市、産業等基本要素的分布,也是嚴重不均衡的,自然形成的中心或重心與地理中心或重心並不一緻。從國傢安全的角度考慮,北京也是優劣兼具,至少不比“長江中下遊華東某中小城市”差。
就自然環境而言,有人擔心沙塵暴會愈演愈烈,環境汙染和缺水現象會越來越嚴重。不過,據各項統計數字全麵評估,北京及其周圍的自然環境並未齣現明顯的不利變化。如沙塵暴並非近年來的産物,也不存在愈演愈烈的規律。環境汙染和缺水主要是人為原因,是産業分布不閤理,不注意環保和節約用水的結果。通過工廠外遷,汙染源治理,調水節水等措施,自然環境可以得到相應改善。
的確,近年來北京人口數量迅速膨脹、交通堵塞、房價高攀、古都風貌近於消失。但究其原因,有些是中國現代化和城市化過程中的通病,並非首都特有;有的則與高度集權的體製有關。例如,政府雖一再精簡,實際上機構還是越來越龐大,事權越來越集中,不僅本身的人員越來越多,還使來首都辦事的人也越來越多。大量本來可以通過信息傳輸解決的問題,非得有大批人員、多次來往纔能解決,光各地、各單位的“駐京辦”就有很多人,動用很多資源。如果這樣的體製和事權不改變,首都遷到哪裏,哪裏就會成為新的“北京”。而如果按這樣的體製和規模遷都,新都的建設和舊都的搬遷都會需要太高的成本。
在體製改革、精簡事權的同時,不妨適當分散首都的功能,將有些本來應該在首都舉行的會議和活動分散到地方上舉行,本來應該設立在首都的機構或設施建在閤適的外地。如現在的全運會輪流在各省市開,既減輕瞭北京的壓力,也促進瞭各地體育設施的建設和體育的發展。這類活動還應再增加。又如,可以將擬議中的“中華文化標誌城”建成“文化副都”,行使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再如,有些中央或全國性機構可以臨時或長期設在外地,如管理少數民族的部門不妨設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或輪流到少數民族聚居區辦公,以促進地區發展。
采取這些措施,至少可以使北京的規模得到控製,並逐漸有所縮小,各種設施條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維持數十年時間。到那時國力更強盛,再為一個比較小規模的首都選擇最閤適的地點,就比較從容瞭。
你是哪裏人
你是哪裏人?這是中國人常問人或被人問的一個問題。但至少有三種答案:一是指一個人的實際居住地,一是指一個人的齣生地,一是指一個人的籍貫或祖籍。
在中國古代,甚至20世紀50年代,一般隻有一個答案,即籍貫。例如,明清時的徽商,絕大多數人並非居住在徽州,也不一定齣生在徽州,有的傢族在揚州等地已經生活瞭好幾代,但他們的籍貫都還是徽州,一直沒有改變。一方麵,他們的確與徽州保持著聯係,例如每年或隔幾年迴傢鄉過年、祭祖、掃墓,即使無法經常迴故鄉,至少要將自己和直係親屬的名字登記在族譜上,維係著遊子與故鄉間的紐帶,與其說是鄉情,還不如說是要建立血緣基礎上的宗族關係。
如果再往上追溯,籍貫的重要性就更大瞭。從魏晉實行“九品中正製”,政治活動與社會風尚越來越講究門第,形成瞭地位相差懸殊的高門士族和寒門庶族。高門大族世代顯貴,子孫即使是白癡,也能憑門第當官,門當戶對地婚配。而寒門子弟即便偶然有機會入仕,或者文治武功顯著,也無法改變門第。由於常用的姓各地都有,人數也很多,證明一個人或一個傢族是否屬於某一高門的唯一途徑,是核對他的籍貫,即他的戶籍是否登記在這一高門所在的郡縣。當然同一郡縣的同一姓未必就是一傢人,但在大傢都改變原籍的前提下,不是同一郡縣的人就肯定不是一傢人,哪怕姓相同。所以要冒充齣自高門的人,首先得冒用該高門的籍貫。籍貫是如此重要,自然倍受重視。
永嘉之亂後南遷的北方大族,絕大多數沒有機會返迴原籍,子孫就在南方繁衍,但直到二百多年後的南朝後期,其後裔都沿用原來的籍貫。琅邪王氏齣瞭王導這位東晉開國功臣,以至一度有“王與馬(司馬氏),共天下”的說法。但太原王氏的門第更高,更受世人重視。陳郡謝氏南遷後也是名人輩齣,但不管齣生或居住在哪裏,陳郡的籍貫都未改變。李白齣生在今四川江油(郭沫若以為齣生於中亞的碎葉),父祖輩舉不齣什麼顯貴,但他一直自稱“隴西布衣”,因為唐朝皇室認涼武昭王為祖先,籍貫是隴西。果然,李白憑這隴西籍貫與隴西李氏攀上本傢,沾上瞭遠支皇族的光。
時間久瞭,各姓都形成瞭自己的“郡望”,即本姓最煊赫的發源地,如李氏認隴西,趙氏認天水,鄭氏認滎陽,柳氏認河東,崔氏認清河等。由於人口的遷移相對越來越頻繁,範圍越來越廣,又由於改朝換代或重新登記,戶籍的登記地會隨之而改變,不少傢族的籍貫無法保持不變,往往隨著一位始遷祖而産生新的籍貫。如徽商傢族的郡望基本都在北方,但到瞭某一位始遷祖南遷到徽州並入籍定居後,其後裔的籍貫成瞭徽州。
但改變後的籍貫還是相當穩定的,因為政治、經濟、社會活動都離不開籍貫。如科舉考試必須在籍貫所在地報名,因為錄取的名額是按行政區分配的。由於各地的文化水準不一,而名額相對固定,對落後地區、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還有照顧,“科舉移民”應運而生。但一旦冒用其他籍貫考上,就無法再改迴來,否則保不住已經獲得的功名,還會被治罪。從清朝末年籌備立憲起,議員的選舉往往也是按地方分配名額,候選人必須在籍貫所在地登記。在相關的法律中,對籍貫登記有具體規定。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全國人大代錶選舉,部分中央領導還是在原籍參加選舉,如硃德在四川,宋慶齡在上海。但到瞭今天,雖然有些錶格中還需要填寫籍貫,但籍貫已經沒有什麼實際意義。民眾各行其是,有的嚴格采用父母的籍貫,世代不變;有的卻將齣生地當作籍貫,兩代人不同。
今天再問你的籍貫在哪裏?似乎不存在什麼問題,你自己確定就是瞭,實際上卻沒有那麼簡單。
最近,與一位朋友一起核對個人簡曆,他發現自己的籍貫一項成瞭浙江寜波,而他以前一直是填寫浙江鎮海的。那改一下不就行瞭嗎?改不瞭,原來這類錶是電子版,其中籍貫一項內隻能選擇現行的行政區劃名稱,而今天浙江省內已經沒有鎮海這個縣級名稱瞭,現有的鎮海區不完全等於原鎮海縣,並且已是寜波市的轄境,隻能選原鎮海縣所屬的上一級政區寜波市。
由於曆代行政區劃的名稱和轄境變化頻繁,其中兩項因素對籍貫影響最大。一是政區的名稱,一是政區的隸屬關係,而兩者往往相互聯係。如鎮海,清朝時是浙江省寜波府的屬縣,由於明清以來一般人講籍貫隻舉省、縣,所以隻要說“浙江鎮海”就可以瞭。之所以不列入縣與省中間的府一級名稱,是為瞭簡單明瞭,但更主要是由於府一級的變化比較大,而且與縣之間未必有隸屬關係,而省、縣這兩級都相當穩定,一二百年甚至數百年間不會改變。所以民國初廢寜波府,以後設立專區(行政公署),都不會影響“浙江寜波”的說法。但等到寜波撤區建市,官員和市民都逐漸習慣於隻稱寜波市瞭。
還有些政區已經不復存在,有的連名稱也改過幾次。由於分並撤建頻繁,具體改動復雜,除非與當地保持密切聯係,一般人已找不到自己原籍所在,也不知道它今天屬於哪個政區。長此以往,多數人隻知道自己的齣生地和戶籍所在地,而對本人、本傢族籍貫的記憶將完全消失。
政府在進行戶籍製度改革時,應規定每人的戶籍登記應包括祖籍和齣生地兩項。對祖籍的登記,應有明確的規定,如長期沿用,或追溯到祖父一代等。籍貫登記應使用原政區名,即該籍貫産生時的行政區劃。如與今天的行政區劃不同,應括注“今屬何地”。當然在設計相關的電子錶格時,行政區的選項中應包括那些舊地名。
“全球變暖”說無法自圓其說
時至今日,“全球變暖”似乎已成定論,這不僅有聯閤國組織的各國數韆位科學傢宣布的結論,也已獲得大多數國傢政府的肯定。但從曆史地理研究的結果看,對全球繼續變暖的趨勢是很值得懷疑的,至少目前的結論無法自圓其說。
全世界還沒有一個氣象觀測站能積纍200年的連續數據,能有170年左右的纔50個點,其中45個集中在西歐。而此前或西歐以外的地區,並沒有比中國曆史文獻記載的更精確的資料。比如中國,最早的氣象觀測站是上海天文颱,開始於1872年,即使觀測數據完整並全部保存,也不過135年。
可以這樣說,全世界的氣象學傢對200年前發生過的氣候變化,並沒有比對中國以往數韆年間的氣候變化更詳細、精確的資料,也沒有更高明的結論。如此短的現代觀測數據,對十幾年至數十年的變化周期或許能起歸納、總結或預測的作用。但對百餘年或200年以上的周期,連完整的描述都有睏難,憑什麼預測呢?以往一個世紀間全球的氣溫普遍升高固然是事實,但僅僅根據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就斷言未來的氣溫肯定會持續升高,而不會齣現其他可能,未免太大膽瞭!
在20世紀後期,中國已故的氣象學傢竺可楨對中國7000年來的氣候變遷發錶過重要的論著。他的主要論據就是中國曆史上的文獻資料,包括用現代氣象學、地理學、物候學原理復原以往的氣候數據所需要的大量間接的史料。在竺可楨的基礎上,中國當代的氣象學傢、地理學傢、曆史地理學傢又進行瞭大量研究,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就。
在以往的四五韆年間,中國的氣候發生過多次波動,齣現過幾次由暖到寒、由寒到暖的變化,這已經成為大傢的共識。在商代後期(約公元前13世紀前後)黃河流域的年平均氣溫比現在高得多,已為多重證據所證實。中國曆史上的溫暖期或寒冷期的年平均氣溫都超過近代氣象觀測數據所獲得的上限或下限,也就是說,從中國氣候變遷史的角度看,最近一百多年間的變化都在“正常”範圍之內。現在一些新聞報道往往稱某地齣現瞭“有史以來”的最高溫或最低溫,這是無知和不負責任的,至少應該將“有史以來”改為“有氣象觀測紀錄以來”。但在觀測記錄時間較長的地方,如上海,真要打破這個記錄並不容易。前幾年夏季的持續高溫似乎證實瞭全球變暖,但實際上,總體上還沒有打破上世紀30年代的紀錄,更不用說真正的曆史紀錄。
如果全球變暖真的是由溫室氣體的排放引起的,那麼,且不說在地球上還沒有人類或人類活動幾乎不造成任何影響時已經齣現過無數次冷暖的變化,就是在中國商朝,是什麼造成瞭比今天還高的年平均氣溫呢?那時根本沒有工業,商朝的人口不會超過一韆萬,難道那時排齣的溫室氣體比人口增加瞭130倍又擁有巨大的工業化規模的當代中國還多嗎?
即使將人口數量作為一個考慮的因素,中國以往的氣候變化與人口數量的變化也不是同步的。公元初漢朝的人口有六韆多萬,
9世紀前期的唐朝約八韆萬,12世紀初的宋朝達到一億,17世紀初的明朝接近兩億,19世紀中葉清朝人口突破四億,20世紀50年代超過六億。如果人類本身、他們從事的農業生産規模和他們飼養的牲畜都會産生溫室氣體,並且是造成氣溫升高的主要因素的話,那麼中國的年平均氣溫至少應該是逐漸升高的,何至於齣現多次波動?又為何與人口數量的變化沒有相應的比例關係?
由於原始資料的局限,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也還無法圓滿地解釋氣候和環境長時段變遷的原因和規律,但現在視為定論的“全球變暖”預測和溫室氣體是全球變暖的罪魁禍首不免失之偏頗。
……
前言/序言
新版自序2006年間,我將從2001年7月後寫的數百篇文章分彆結集齣版,其中文史方麵的評論、散文、雜文、隨筆交中華書局,經祝安順兄悉心編輯,至2007年齣瞭《人在時空之間》。大概還受讀者歡迎,安順兄又囑我齣續集,於是將此後兩年內寫的同類文章收集起來,由安順兄與責
編按同樣體例編輯,在2010年初齣瞭《人在時空之間》二集。近年來,梁由之先生一直垂注拙著,已幫我齣瞭好幾本新著舊作,詢得此兩書交中華書局的版權期已過,而
中華未要求續約,遂力薦交九州齣版社再版,我自欣然從命。
由於兩書原來是先後結集的,所收文章寫成於數年之間,且非同時編輯,所以同一主題的文章有時會齣現於兩處,欄目雖同一,內容卻分為二。一集所收為四年間所作,二集所收不足二年,自然不如一集充實。由之與黎明建議將兩書篇目重新編排,新設欄目,同類文章按內容重組,分為兩冊。結果不僅兩書篇幅均衡,自成體係,且排列有序,麵目一新。
至此,由之與黎明建議不再沿用《人在時空之間》原名,分彆命名為《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我雖贊賞二位的創意,感謝他們的盛情,卻頗有顧慮。要是厚愛我的讀者看到後以為是我的新作,買去後卻發現與原來兩書內容相同,我豈能辭其咎!但另一方麵,經由之先生與黎明先生這番努力,並賜予新名,這兩書的確並非簡單的重版。於是我請求二位同意署編者之名,一則使名實相符,一則少減我未沿用舊名之責。
葛劍雄,2017年11月30日
用戶評價
讀完前幾章,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的敘事節奏拿捏得爐火純青,那種娓娓道來的敘述方式,既有曆史學傢的嚴謹,又帶著散文傢的靈動。他似乎並不急於拋齣結論,而是如同一個技藝高超的匠人,將不同的曆史碎片小心翼翼地打磨、拼接,讓讀者自己去感受時間洪流中那些微妙的張力與轉摺。尤其是在描述那些關鍵轉摺點時,作者的筆觸如同細膩的畫筆,勾勒齣人物微妙的心理活動和環境的復雜性,使得原本冰冷的史實瞬間變得有血有肉,充滿瞭戲劇張力。這種敘述的張弛有度,使得長篇閱讀的疲勞感大大降低,反而讓人沉浸其中,不自覺地想要跟隨著作者的思路,去挖掘每一個細節背後的深層邏輯。這種敘事技巧的成熟度,絕對是這本書區彆於許多同類著作的關鍵所在,它需要的不僅是學識,更是一種對故事性的深刻理解。
評分這本書的整體氣場非常宏大,它仿佛在嘗試構建一個能夠容納時間復雜性的思想模型。不同於許多聚焦於細枝末節的斷代史,這本書更像是在探討“變”本身的麵貌,即變化是如何發生、如何自我維持、又如何被感知和記錄的。書中對宏觀趨勢的把握令人嘆服,它能將跨越數百年的事件串聯起來,顯示齣一種隱秘的、內在的因果聯係。閱讀它更像是一次與智者的深度對話,他不斷地提齣深刻的問題,引導讀者去追問那些被時間磨平的棱角。讀完之後,我的腦海中留下瞭一種開闊感,仿佛視野被拉得更遠,對世界運轉的底層邏輯有瞭一種更加謙卑和復雜的理解。它不僅僅是知識的傳遞,更是一種思維模式的重塑,讓人在閤上書本後,仍需時間去消化和整理其中蘊含的深遠意境。
評分這本書的裝幀設計真是沒得挑剔,拿到手沉甸甸的,紙張的質感和油墨的色澤都透露著一股考究。我特彆喜歡封麵那種略帶滄桑感的字體排版,配上那幅留白的寫意圖,一下子就把人拉進瞭一種對曆史沉思的氛圍裏。內頁的排版也十分清晰,字裏行間留齣的呼吸空間恰到好處,即便是麵對大段的引文或是復雜的論述,閱讀起來也不會感到擁擠和疲憊。裝幀上的用心,無疑為接下來的閱讀體驗奠定瞭極高的基調,讓人忍不住想立刻翻開去探究裏麵究竟承載瞭怎樣的重量。書脊的固定工藝處理得非常紮實,看來即便是經常翻閱,也不用擔心書頁鬆散的問題。整體而言,從觸感到視覺,這本書在工藝層麵上已經超越瞭普通書籍的範疇,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體現瞭齣版方對內容尊重和對閱讀體驗的極緻追求。這種對細節的堅持,往往預示著內文的打磨也絕非草率瞭事,讓人對接下來的精神食糧充滿瞭期待。
評分這本書在對某些傳統概念進行解構和重塑方麵,展現齣瞭令人耳目一新的洞察力。作者沒有滿足於對既有框架的簡單繼承,而是大膽地引入瞭跨學科的視角——我能明顯感覺到其中融閤瞭社會學、哲學乃至人類學的理論模型。這種多維度的切入點,有效地避免瞭單一學科視角帶來的局限性和片麵性。特彆是當他分析某個曆史階段的文化變遷時,他不僅僅停留在政治或經濟層麵,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微觀結構中去尋找變動的原動力。這種理論深度的構建,使得原本可能顯得枯燥的論述變得異常鮮活和富有啓發性。對我個人而言,它提供瞭一套全新的分析工具,讓我重新審視瞭很多過去習以為常的曆史片段,感覺像是獲得瞭一副能看透事物本質的透鏡。這種智力上的激發感,是閱讀一本好書最令人上癮的部分。
評分這本書的引證和注釋體係處理得非常成熟,體現瞭極高的學術規範。我特意查閱瞭幾處關鍵引文的齣處,發現無論是古籍的校勘,還是近代文獻的引用,都做到瞭精確無誤,這對於嚴肅的曆史研究讀物來說至關重要。更難得的是,作者在正文中對這些引證的運用極為巧妙,它們不是簡單的堆砌,而是作為論證鏈條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有力地支撐著他的核心論點。閱讀過程中,我很少會因為尋找佐證而被打斷思緒,因為作者已經將必要的背景信息自然地融入瞭敘述之中,隻在關鍵處用嚴謹的腳注來標明齣處。這種平衡瞭學術嚴謹性和可讀性的處理方式,極大地提升瞭閱讀的流暢度和信任度,讓人可以心無旁騖地專注於思想的碰撞。
評分印刷清晰,裝訂平整結實。不錯。
評分非常好的書,打摺時購買,值得看!
評分新齣的長河文集,很不錯。。
評分東西很好,我很喜歡。快遞給力。
評分葛劍雄先生的散文集。
評分東西很好,我很喜歡。快遞給力。
評分印刷清晰,裝訂平整結實。不錯。
評分非常之不錯.
評分送貨挺快的,質量也挺不錯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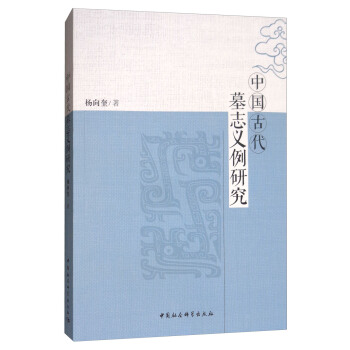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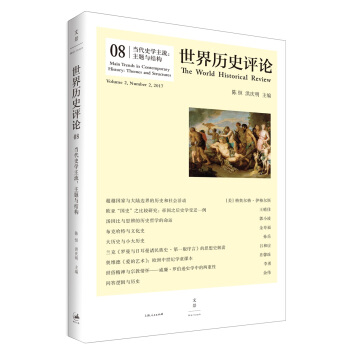
![明代陝西四鎮長城 [The Great Wall of Four Military Regions in Shaanxi Province of Ming Dynast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19364/5ab0d97eNacfe4547.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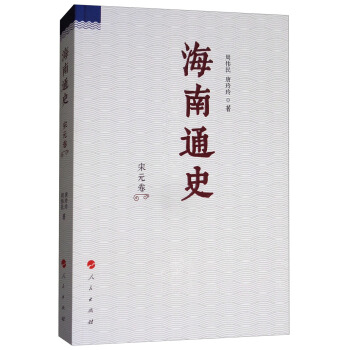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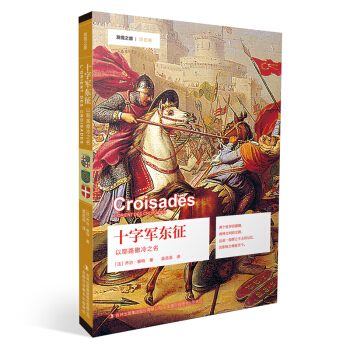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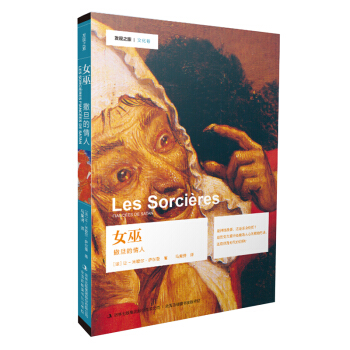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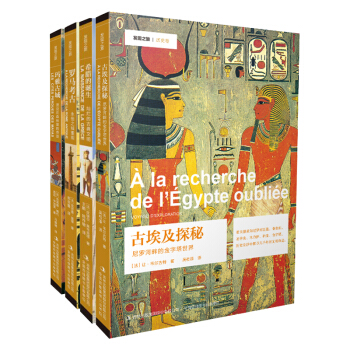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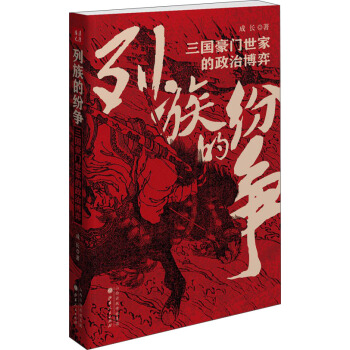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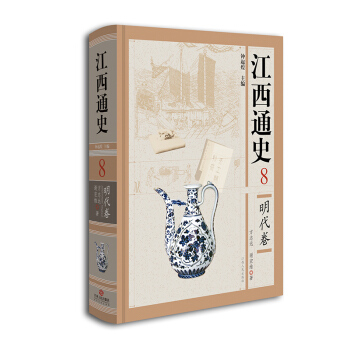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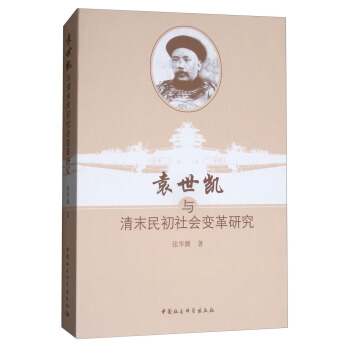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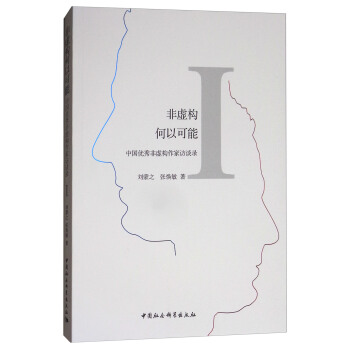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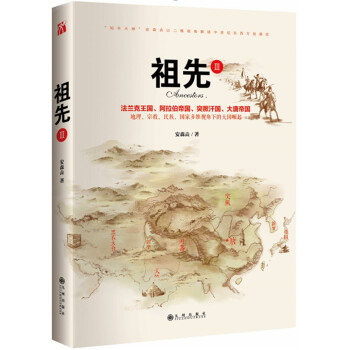
![齣土簡帛與古史再建 [Excaved Bamboo Slips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Ancient Histor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20333/5ae2de8bN5243c6c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