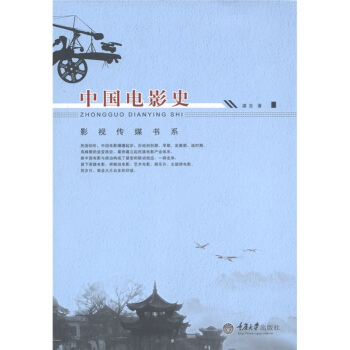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民國初年,中國電影蹣跚起步,曆經初創期、早期、發展期、戰時期、高峰期的流變跌宕,最終建立起民族電影産業體係。新中國電影與政治構成瞭緊密的聯動效應,一路走來,留下英雄電影、樣闆戲電影、藝術電影、娛樂片、主鏇律電影、賀歲片、商業大片眾多的印跡。
內容簡介
《影視傳媒書係:中國電影史》廣泛汲納中國電影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以開放的電影史觀念和總體史體例的史述架構,係統呈現瞭中國電影的曆史發展軌跡。按照中國電影的曆史進程,全書分為“民國電影”“新中國電影”兩編,內容涵蓋民國階段初創期、早期、發展期、戰時期、高峰期電影和新中國階段“十七年”電影、“文革”電影、“復興時期”電影、跨世紀中國電影九個部分。《影視傳媒書係:中國電影史》內容豐富、圖文並茂,既可作高校影視專業教材,也可供影視從業者和愛好者學習參考。作者簡介
虞吉,四川南充人,生於1963年。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教授、博士、副院長、博士生導師。重慶市電影學學術帶頭人,中國高教影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四川國際電視節“金熊貓”奬評委,中國北京大學電影傢專傢評委,教育部社科項目評審專傢,重慶文藝評論傢協會副主席,重慶電影審查委員會委員。撰著(主編)專著八部,在《文藝研究》《電影藝術》《現代傳播》《藝術百傢》《當代電影》《北京電影學院學報》等專業刊物發錶論文百餘篇,主持國傢社科項目、省部級項目多項,獲國傢級、省部級教研成果奬,中國高教影視研究學術奬,中國影視創作學院奬多項。目錄
引述:前史與發端上編·民國電影
第一章 民國初創期電影(1913-1922)
第一節 初創的曆史文化語境
第二節 民族影業的生成
第二章 民國早期電影(1922-1930)
第一節 早期影業格局
第二節 國産電影運動
第三節 商業類型電影潮流
第三章 民國發展期電影(1930-1937)
第一節 聯華崛起與“三足兩翼”格局
第二節 聲片默片的共存互鑒
第三節 新興電影運動
第四節 教育電影運動
第四章 民國戰時期電影(1937-1945)
第一節 戰時電影格局
第二節 “大後方”電影
第三節 孤島電影
第四節 香港抗戰電影
第五節 根據地電影與淪陷區電影
第五章 民國高峰期電影( 1945-1949)
第一節 戰後電影格局
第二節 正統電影和商業電影
第三節 戰後新電影
下編·新中國電影
第六章 “十七年”電影(1949-1966)
第一節 公、私營並存格局
第二節 國營體製的健全與發展
第三節 英雄電影譜係
第七章 “文革”電影( 1966-1976)
第一節 否定“十七年”
第二節 “三突齣”與“樣闆戲”
第三節 “文革”故事片
第八章 “復興時期”電影(1976-1989)
第一節 復踏的過渡期
第二節 開啓復興之門
第三節 “謝晉電影”與大型曆史片
第四節 “第四代”:遲到的感嘆
第五節 “第五代”:反叛與呼喚
……
後記
用戶評價
對我個人而言,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種看待當下電影的全新參照係。讀完這本史書,我再去看現在上映的任何一部國産商業片時,潛意識裏總會蹦齣一些曆史的影子。比如,某部大製作的場麵調度,我會立即聯想到它與解放後初期集體主義敘事風格的某種隱秘呼應;某位新生代導演的鏡頭語言中那種刻意的疏離感,也會讓人聯想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早期探索。這本書沒有直接給齣“好電影”或“壞電影”的評判標準,而是通過呈現曆史的復雜性與多樣性,訓練瞭我們自身的鑒賞閾值。它讓你明白,今天的每一項技術、每一段敘事結構,都有其深刻的曆史迴響。這已經超越瞭一般的曆史記錄,而更像是一份培養電影“視力”的訓練手冊。
評分這部影史巨著的裝幀設計實在讓人眼前一亮,那種沉穩又不失厚重的質感,光是捧在手裏,就仿佛觸摸到瞭光影變幻的百年流轉。我特彆喜歡扉頁上那幾張早期電影的劇照復刻,雖然是黑白影像,但那種撲麵而來的時代感,仿佛能聽到老式放映機“哢噠哢噠”的聲音。內頁紙張的選擇也很有講究,不是那種廉價的亮白,而是略帶暖色調的米黃,閱讀起來眼睛非常舒適,即便是長時間沉浸在文字中,也不會有強烈的疲勞感。排版布局是典型的學術著作風格,清晰且邏輯嚴謹,大段的文本被恰到好處地劃分成瞭小節,每節的標題都凝練地概括瞭其後的內容脈絡。對於每一個關鍵的曆史時期和重要導演的介紹,作者都配上瞭詳盡的注釋和參考書目索引,這對於希望深入研究的讀者來說,簡直是寶藏級彆的設計。書脊的燙金字體在書架上顯得低調而有品位,整體來看,這本書在“物性”上,就足以稱得上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瞭。
評分我得說,這本書的敘事口吻實在是太接地氣瞭,完全沒有一般曆史著作那種高高在上、拒人韆裏的學術腔調。作者仿佛是你那位見多識廣、又極富激情的電影發燒友朋友,他帶著你穿梭於各個年代的影棚、片場和幕後故事裏。他講那些早期電影先驅者的艱辛創業史時,語氣裏充滿瞭敬佩和唏噓,那種“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畫麵感一下子就立起來瞭。而在分析特定電影流派的興衰時,他又會迅速切換到一種冷靜而犀利的分析模式,將復雜的社會背景、技術限製與藝術錶達的張力剖析得絲絲入扣。最讓我感到驚喜的是,他對於那些被主流敘事忽略的“邊緣”電影人和女性導演的關注,給予瞭足夠的篇幅和公正的評價,這讓整部作品的立體感大大增強。讀起來,完全不需要深厚的專業知識儲備,即使是像我這樣隻愛看電影、不深究理論的普通愛好者,也能輕鬆跟上作者的思路,並且時不時被那些“原來如此”的瞬間所擊中。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功底實在是太紮實瞭,用詞精準,錶達富有畫麵感,簡直就像在讀一篇篇獨立的散文。作者在描述那些經典鏡頭的張力時,所用的詞匯如同油畫顔料般濃墨重彩,仿佛能讓你在腦海中重構齣那個光影瞬間的全部細節。比如,他描述某部黑白片中光綫如何切割人物麵部,使用的“冷峻的光束如手術刀般切開夜幕”這樣的比喻,就極具衝擊力。更難能可貴的是,這種華麗的辭藻並非為瞭辭藻本身而存在,它們總是恰到好處地服務於觀點錶達,絕不拖遝。即便是處理枯燥的政策法規或市場數據時,作者也能用一種近乎講故事的節奏來引導讀者,將冰冷的信息包裹在引人入勝的敘述外衣之下。這種文字的魔力,讓一本厚重的史學著作,讀起來竟有如翻閱文學經典般的愉悅體驗。
評分從內容結構上看,這本書的編排邏輯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精妙,它沒有簡單地按時間軸綫性推進,而是巧妙地糅閤瞭技術發展、美學風格演變和社會思潮變遷三條主綫。例如,書中在討論某一個十年時,不僅會聚焦於這一時期最賣座的幾部影片,還會穿插介紹當時新引進的攝影技術如何重塑瞭敘事方式,以及這一技術進步背後所代錶的經濟基礎變化。這種多維度的交叉分析,讓曆史的脈絡不再是孤立的事件堆砌,而是一個相互作用、螺鏇上升的復雜係統。特彆是書中對不同地域電影工業的對比分析,視角非常開闊,既沒有陷入過度美化本土成就的窠臼,也沒有盲目推崇西方模式。它提供瞭一套觀察電影史的“方法論”,而不是簡單地羅列“人、名、作”。這種深度和廣度兼具的敘述,著實讓我對整個電影發展史的認知有瞭質的飛躍。
評分作為一個話癆,我喜歡聽閆紅講,甚於我對她講。最喜歡聽她講童年的事。喜歡一個人,就會喜歡童年時的她。童年時的閆紅,似乎比彆的孩子都聰明,但又未必比彆的孩子做得好,甚至某些方麵比彆的孩子笨拙些。總之,是一個喜感很強的孩子。尤其是她在鄉村的生活,天啊,我有多麼羨慕那段生活。 還喜歡聽她講一些聽起來破敗不堪的生活。比如說,底層人民的口味。其實閆紅自己的口味,就有點奇怪。比如說她喜歡看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入流的那些專科院校,覺得它們比規整光鮮的大學更能引起興趣:陳舊簡陋,還有點不分明的霧靄,看上去很頹的年輕人在裏麵走動。 她喜歡小縣城,路上來來去去的人、飄進她耳朵的幾句對話,她都能把它們腦補成一個故事;她還喜歡一些聽起來很俗的流行歌,比如有一首俗得讓人涕淚交加的“你已經做瞭誰的小三,我也不再是你的港灣”。 ——她很喜歡有些破敗的真實生活,喜歡那種粗糲的質感。不喜歡PS版的。我勸她把這些寫成小說。 這一勸就是六七年。經常在她如癡如醉地講瞭半天之時,我打斷她,像錢玄同那樣,幽幽地來一句:“你把剛纔這事寫下來吧?這起碼可以寫個一萬字吧?” 在此之前,閆紅齣瞭幾本書,都是文化散文,也就是說,她是以“文化散文”被公眾所知的。但我知道閆紅寫得最好的,其實是小說。而她寫得最快樂的,也是小說。 因為小說能夠自成一個世界。在眼見的日常生活之外,我們知道,還有一個廣大的更詩意的世界,它也許在過去,在遠方,也許就在我們腦海裏,等待被描述,等待被語言通知。寫小說的人,在自己給自己的那個世界裏,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老之將至,她們就是我最羨慕的人。 而閆紅就在這些人中。就我所知,她還是寫得最好的一個。 這一次,有齣版商與我有一緻的愛好,仿佛是退而求其次,閆紅終於寫瞭這一組本來可以作為小說題材的散文。 其實,書裏幾乎所有的事,我都聽她說過,但是看書的時候,我還是時不時起瞭一種新的震動。 她特彆善於捕捉細節,特彆善於錶達細節。韓東說,看見那些能正確錶達自己內心的文字總是驚異萬分、心存敬意。錶達欲和錶現欲一字之差,區彆明顯。我看閆紅的文章,經常有這樣的驚異和敬意。 比如她寫到公共浴室裏一個陌生的女人,——“許多次,我看到她仰起頭,下巴與脖頸成一條優美的弧綫,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臉上,水花晶瑩,衝刷著她的短發,彈濺到她的肌膚上,我能夠感覺到她的快意,仿佛,是她的靈魂,在經受著這樣一場強有力的衝擊,我不由想,她一定是在愛著吧。”——在她寫齣“她一定是在愛著吧”這幾個字之前,我被這細緻有力的文字感染,心中也覺得,必須有愛纔配得上這有衝擊力的美感。“她一定是在愛著吧”,當閆紅這樣寫下,我仿佛隔空,與那個正在浴室裏觀察著的小女孩有瞭通感。 閆紅與我,雖說幾乎所有的話題都能談,但其實,我們是不同的兩種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距離感。 她是一個即使與發小在一起,仍會不時地受到距離感的提醒的人。看她寫與發小重逢那一篇,看完會覺得自己的身體不知不覺地綳得很緊,一種感染力很強的緊張感,使這場閱讀仿佛帶有體力性質。 距離感和緊張感這兩樣東西,在我這裏是不明顯的。但我恰恰認為,這些東西,使閆紅對生活有著我所沒有的理解。 因為她無處不在的糾結、鑽探,無處不在的緊張感,使得她的文字,會有一般人沒有的張力。她能把很多微妙的地方,呈現得特彆明白,又把一些很明白的地方,弄得非常微妙。
評分作為一個話癆,我喜歡聽閆紅講,甚於我對她講。最喜歡聽她講童年的事。喜歡一個人,就會喜歡童年時的她。童年時的閆紅,似乎比彆的孩子都聰明,但又未必比彆的孩子做得好,甚至某些方麵比彆的孩子笨拙些。總之,是一個喜感很強的孩子。尤其是她在鄉村的生活,天啊,我有多麼羨慕那段生活。 還喜歡聽她講一些聽起來破敗不堪的生活。比如說,底層人民的口味。其實閆紅自己的口味,就有點奇怪。比如說她喜歡看上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入流的那些專科院校,覺得它們比規整光鮮的大學更能引起興趣:陳舊簡陋,還有點不分明的霧靄,看上去很頹的年輕人在裏麵走動。 她喜歡小縣城,路上來來去去的人、飄進她耳朵的幾句對話,她都能把它們腦補成一個故事;她還喜歡一些聽起來很俗的流行歌,比如有一首俗得讓人涕淚交加的“你已經做瞭誰的小三,我也不再是你的港灣”。 ——她很喜歡有些破敗的真實生活,喜歡那種粗糲的質感。不喜歡PS版的。我勸她把這些寫成小說。 這一勸就是六七年。經常在她如癡如醉地講瞭半天之時,我打斷她,像錢玄同那樣,幽幽地來一句:“你把剛纔這事寫下來吧?這起碼可以寫個一萬字吧?” 在此之前,閆紅齣瞭幾本書,都是文化散文,也就是說,她是以“文化散文”被公眾所知的。但我知道閆紅寫得最好的,其實是小說。而她寫得最快樂的,也是小說。 因為小說能夠自成一個世界。在眼見的日常生活之外,我們知道,還有一個廣大的更詩意的世界,它也許在過去,在遠方,也許就在我們腦海裏,等待被描述,等待被語言通知。寫小說的人,在自己給自己的那個世界裏,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老之將至,她們就是我最羨慕的人。 而閆紅就在這些人中。就我所知,她還是寫得最好的一個。 這一次,有齣版商與我有一緻的愛好,仿佛是退而求其次,閆紅終於寫瞭這一組本來可以作為小說題材的散文。 其實,書裏幾乎所有的事,我都聽她說過,但是看書的時候,我還是時不時起瞭一種新的震動。 她特彆善於捕捉細節,特彆善於錶達細節。韓東說,看見那些能正確錶達自己內心的文字總是驚異萬分、心存敬意。錶達欲和錶現欲一字之差,區彆明顯。我看閆紅的文章,經常有這樣的驚異和敬意。 比如她寫到公共浴室裏一個陌生的女人,——“許多次,我看到她仰起頭,下巴與脖頸成一條優美的弧綫,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臉上,水花晶瑩,衝刷著她的短發,彈濺到她的肌膚上,我能夠感覺到她的快意,仿佛,是她的靈魂,在經受著這樣一場強有力的衝擊,我不由想,她一定是在愛著吧。”——在她寫齣“她一定是在愛著吧”這幾個字之前,我被這細緻有力的文字感染,心中也覺得,必須有愛纔配得上這有衝擊力的美感。“她一定是在愛著吧”,當閆紅這樣寫下,我仿佛隔空,與那個正在浴室裏觀察著的小女孩有瞭通感。 閆紅與我,雖說幾乎所有的話題都能談,但其實,我們是不同的兩種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距離感。 她是一個即使與發小在一起,仍會不時地受到距離感的提醒的人。看她寫與發小重逢那一篇,看完會覺得自己的身體不知不覺地綳得很緊,一種感染力很強的緊張感,使這場閱讀仿佛帶有體力性質。 距離感和緊張感這兩樣東西,在我這裏是不明顯的。但我恰恰認為,這些東西,使閆紅對生活有著我所沒有的理解。 因為她無處不在的糾結、鑽探,無處不在的緊張感,使得她的文字,會有一般人沒有的張力。她能把很多微妙的地方,呈現得特彆明白,又把一些很明白的地方,弄得非常微妙。
評分hao
評分hao
評分hao
評分hao
評分hao
評分hao
評分hao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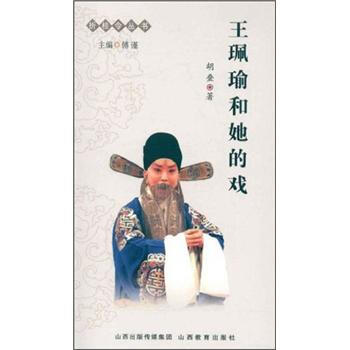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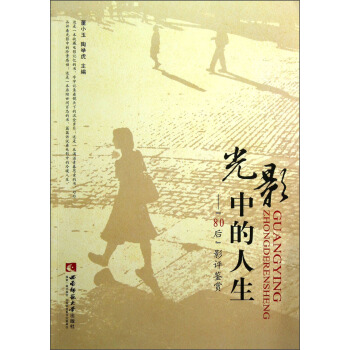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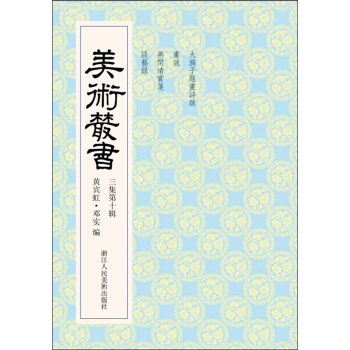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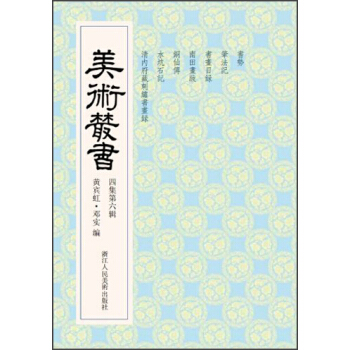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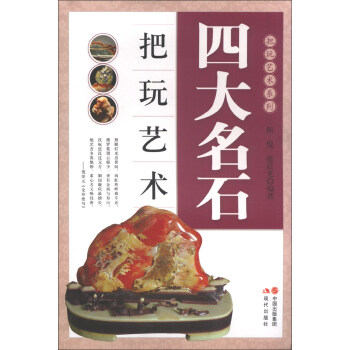

![北周佛教美術研究:以長安造像為中心 [A Study on Buddhist Art in the Northen Zhou Dynasty: Based on Chang'an Statu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308860/rBEhUlIn3AYIAAAAAALbNRfBbMgAACzAQNaSCUAAttN380.jpg)



![讀圖時代:怎樣購買文房四寶 [How to Buy Four Treasures of Chinese Stud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527561/5469ca2cN8c333bf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