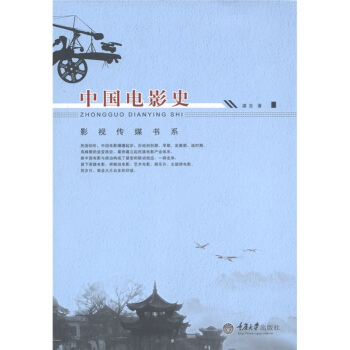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民国初年,中国电影蹒跚起步,历经初创期、早期、发展期、战时期、高峰期的流变跌宕,最终建立起民族电影产业体系。新中国电影与政治构成了紧密的联动效应,一路走来,留下英雄电影、样板戏电影、艺术电影、娱乐片、主旋律电影、贺岁片、商业大片众多的印迹。
内容简介
《影视传媒书系:中国电影史》广泛汲纳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开放的电影史观念和总体史体例的史述架构,系统呈现了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轨迹。按照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全书分为“民国电影”“新中国电影”两编,内容涵盖民国阶段初创期、早期、发展期、战时期、高峰期电影和新中国阶段“十七年”电影、“文革”电影、“复兴时期”电影、跨世纪中国电影九个部分。《影视传媒书系:中国电影史》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既可作高校影视专业教材,也可供影视从业者和爱好者学习参考。作者简介
虞吉,四川南充人,生于1963年。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博士、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重庆市电影学学术带头人,中国高教影视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评委,中国北京大学电影家专家评委,教育部社科项目评审专家,重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重庆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撰著(主编)专著八部,在《文艺研究》《电影艺术》《现代传播》《艺术百家》《当代电影》《北京电影学院学报》等专业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项目、省部级项目多项,获国家级、省部级教研成果奖,中国高教影视研究学术奖,中国影视创作学院奖多项。目录
引述:前史与发端上编·民国电影
第一章 民国初创期电影(1913-1922)
第一节 初创的历史文化语境
第二节 民族影业的生成
第二章 民国早期电影(1922-1930)
第一节 早期影业格局
第二节 国产电影运动
第三节 商业类型电影潮流
第三章 民国发展期电影(1930-1937)
第一节 联华崛起与“三足两翼”格局
第二节 声片默片的共存互鉴
第三节 新兴电影运动
第四节 教育电影运动
第四章 民国战时期电影(1937-1945)
第一节 战时电影格局
第二节 “大后方”电影
第三节 孤岛电影
第四节 香港抗战电影
第五节 根据地电影与沦陷区电影
第五章 民国高峰期电影( 1945-1949)
第一节 战后电影格局
第二节 正统电影和商业电影
第三节 战后新电影
下编·新中国电影
第六章 “十七年”电影(1949-1966)
第一节 公、私营并存格局
第二节 国营体制的健全与发展
第三节 英雄电影谱系
第七章 “文革”电影( 1966-1976)
第一节 否定“十七年”
第二节 “三突出”与“样板戏”
第三节 “文革”故事片
第八章 “复兴时期”电影(1976-1989)
第一节 复踏的过渡期
第二节 开启复兴之门
第三节 “谢晋电影”与大型历史片
第四节 “第四代”:迟到的感叹
第五节 “第五代”:反叛与呼唤
……
后记
用户评价
我得说,这本书的叙事口吻实在是太接地气了,完全没有一般历史著作那种高高在上、拒人千里的学术腔调。作者仿佛是你那位见多识广、又极富激情的电影发烧友朋友,他带着你穿梭于各个年代的影棚、片场和幕后故事里。他讲那些早期电影先驱者的艰辛创业史时,语气里充满了敬佩和唏嘘,那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画面感一下子就立起来了。而在分析特定电影流派的兴衰时,他又会迅速切换到一种冷静而犀利的分析模式,将复杂的社会背景、技术限制与艺术表达的张力剖析得丝丝入扣。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他对于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边缘”电影人和女性导演的关注,给予了足够的篇幅和公正的评价,这让整部作品的立体感大大增强。读起来,完全不需要深厚的专业知识储备,即使是像我这样只爱看电影、不深究理论的普通爱好者,也能轻松跟上作者的思路,并且时不时被那些“原来如此”的瞬间所击中。
评分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看待当下电影的全新参照系。读完这本史书,我再去看现在上映的任何一部国产商业片时,潜意识里总会蹦出一些历史的影子。比如,某部大制作的场面调度,我会立即联想到它与解放后初期集体主义叙事风格的某种隐秘呼应;某位新生代导演的镜头语言中那种刻意的疏离感,也会让人联想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早期探索。这本书没有直接给出“好电影”或“坏电影”的评判标准,而是通过呈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训练了我们自身的鉴赏阈值。它让你明白,今天的每一项技术、每一段叙事结构,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回响。这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历史记录,而更像是一份培养电影“视力”的训练手册。
评分这部影史巨著的装帧设计实在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又不失厚重的质感,光是捧在手里,就仿佛触摸到了光影变幻的百年流转。我特别喜欢扉页上那几张早期电影的剧照复刻,虽然是黑白影像,但那种扑面而来的时代感,仿佛能听到老式放映机“咔哒咔哒”的声音。内页纸张的选择也很有讲究,不是那种廉价的亮白,而是略带暖色调的米黄,阅读起来眼睛非常舒适,即便是长时间沉浸在文字中,也不会有强烈的疲劳感。排版布局是典型的学术著作风格,清晰且逻辑严谨,大段的文本被恰到好处地划分成了小节,每节的标题都凝练地概括了其后的内容脉络。对于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和重要导演的介绍,作者都配上了详尽的注释和参考书目索引,这对于希望深入研究的读者来说,简直是宝藏级别的设计。书脊的烫金字体在书架上显得低调而有品位,整体来看,这本书在“物性”上,就足以称得上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了。
评分从内容结构上看,这本书的编排逻辑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精妙,它没有简单地按时间轴线性推进,而是巧妙地糅合了技术发展、美学风格演变和社会思潮变迁三条主线。例如,书中在讨论某一个十年时,不仅会聚焦于这一时期最卖座的几部影片,还会穿插介绍当时新引进的摄影技术如何重塑了叙事方式,以及这一技术进步背后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变化。这种多维度的交叉分析,让历史的脉络不再是孤立的事件堆砌,而是一个相互作用、螺旋上升的复杂系统。特别是书中对不同地域电影工业的对比分析,视角非常开阔,既没有陷入过度美化本土成就的窠臼,也没有盲目推崇西方模式。它提供了一套观察电影史的“方法论”,而不是简单地罗列“人、名、作”。这种深度和广度兼具的叙述,着实让我对整个电影发展史的认知有了质的飞跃。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功底实在是太扎实了,用词精准,表达富有画面感,简直就像在读一篇篇独立的散文。作者在描述那些经典镜头的张力时,所用的词汇如同油画颜料般浓墨重彩,仿佛能让你在脑海中重构出那个光影瞬间的全部细节。比如,他描述某部黑白片中光线如何切割人物面部,使用的“冷峻的光束如手术刀般切开夜幕”这样的比喻,就极具冲击力。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华丽的辞藻并非为了辞藻本身而存在,它们总是恰到好处地服务于观点表达,绝不拖沓。即便是处理枯燥的政策法规或市场数据时,作者也能用一种近乎讲故事的节奏来引导读者,将冰冷的信息包裹在引人入胜的叙述外衣之下。这种文字的魔力,让一本厚重的史学著作,读起来竟有如翻阅文学经典般的愉悦体验。
评分hao
评分作为一个话痨,我喜欢听闫红讲,甚于我对她讲。最喜欢听她讲童年的事。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童年时的她。童年时的闫红,似乎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但又未必比别的孩子做得好,甚至某些方面比别的孩子笨拙些。总之,是一个喜感很强的孩子。尤其是她在乡村的生活,天啊,我有多么羡慕那段生活。 还喜欢听她讲一些听起来破败不堪的生活。比如说,底层人民的口味。其实闫红自己的口味,就有点奇怪。比如说她喜欢看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入流的那些专科院校,觉得它们比规整光鲜的大学更能引起兴趣:陈旧简陋,还有点不分明的雾霭,看上去很颓的年轻人在里面走动。 她喜欢小县城,路上来来去去的人、飘进她耳朵的几句对话,她都能把它们脑补成一个故事;她还喜欢一些听起来很俗的流行歌,比如有一首俗得让人涕泪交加的“你已经做了谁的小三,我也不再是你的港湾”。 ——她很喜欢有些破败的真实生活,喜欢那种粗粝的质感。不喜欢PS版的。我劝她把这些写成小说。 这一劝就是六七年。经常在她如痴如醉地讲了半天之时,我打断她,像钱玄同那样,幽幽地来一句:“你把刚才这事写下来吧?这起码可以写个一万字吧?” 在此之前,闫红出了几本书,都是文化散文,也就是说,她是以“文化散文”被公众所知的。但我知道闫红写得最好的,其实是小说。而她写得最快乐的,也是小说。 因为小说能够自成一个世界。在眼见的日常生活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广大的更诗意的世界,它也许在过去,在远方,也许就在我们脑海里,等待被描述,等待被语言通知。写小说的人,在自己给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老之将至,她们就是我最羡慕的人。 而闫红就在这些人中。就我所知,她还是写得最好的一个。 这一次,有出版商与我有一致的爱好,仿佛是退而求其次,闫红终于写了这一组本来可以作为小说题材的散文。 其实,书里几乎所有的事,我都听她说过,但是看书的时候,我还是时不时起了一种新的震动。 她特别善于捕捉细节,特别善于表达细节。韩东说,看见那些能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总是惊异万分、心存敬意。表达欲和表现欲一字之差,区别明显。我看闫红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惊异和敬意。 比如她写到公共浴室里一个陌生的女人,——“许多次,我看到她仰起头,下巴与脖颈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脸上,水花晶莹,冲刷着她的短发,弹溅到她的肌肤上,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快意,仿佛,是她的灵魂,在经受着这样一场强有力的冲击,我不由想,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在她写出“她一定是在爱着吧”这几个字之前,我被这细致有力的文字感染,心中也觉得,必须有爱才配得上这有冲击力的美感。“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当闫红这样写下,我仿佛隔空,与那个正在浴室里观察着的小女孩有了通感。 闫红与我,虽说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能谈,但其实,我们是不同的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距离感。 她是一个即使与发小在一起,仍会不时地受到距离感的提醒的人。看她写与发小重逢那一篇,看完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知不觉地绷得很紧,一种感染力很强的紧张感,使这场阅读仿佛带有体力性质。 距离感和紧张感这两样东西,在我这里是不明显的。但我恰恰认为,这些东西,使闫红对生活有着我所没有的理解。 因为她无处不在的纠结、钻探,无处不在的紧张感,使得她的文字,会有一般人没有的张力。她能把很多微妙的地方,呈现得特别明白,又把一些很明白的地方,弄得非常微妙。
评分hao
评分hao
评分作为一个话痨,我喜欢听闫红讲,甚于我对她讲。最喜欢听她讲童年的事。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童年时的她。童年时的闫红,似乎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但又未必比别的孩子做得好,甚至某些方面比别的孩子笨拙些。总之,是一个喜感很强的孩子。尤其是她在乡村的生活,天啊,我有多么羡慕那段生活。 还喜欢听她讲一些听起来破败不堪的生活。比如说,底层人民的口味。其实闫红自己的口味,就有点奇怪。比如说她喜欢看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入流的那些专科院校,觉得它们比规整光鲜的大学更能引起兴趣:陈旧简陋,还有点不分明的雾霭,看上去很颓的年轻人在里面走动。 她喜欢小县城,路上来来去去的人、飘进她耳朵的几句对话,她都能把它们脑补成一个故事;她还喜欢一些听起来很俗的流行歌,比如有一首俗得让人涕泪交加的“你已经做了谁的小三,我也不再是你的港湾”。 ——她很喜欢有些破败的真实生活,喜欢那种粗粝的质感。不喜欢PS版的。我劝她把这些写成小说。 这一劝就是六七年。经常在她如痴如醉地讲了半天之时,我打断她,像钱玄同那样,幽幽地来一句:“你把刚才这事写下来吧?这起码可以写个一万字吧?” 在此之前,闫红出了几本书,都是文化散文,也就是说,她是以“文化散文”被公众所知的。但我知道闫红写得最好的,其实是小说。而她写得最快乐的,也是小说。 因为小说能够自成一个世界。在眼见的日常生活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广大的更诗意的世界,它也许在过去,在远方,也许就在我们脑海里,等待被描述,等待被语言通知。写小说的人,在自己给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老之将至,她们就是我最羡慕的人。 而闫红就在这些人中。就我所知,她还是写得最好的一个。 这一次,有出版商与我有一致的爱好,仿佛是退而求其次,闫红终于写了这一组本来可以作为小说题材的散文。 其实,书里几乎所有的事,我都听她说过,但是看书的时候,我还是时不时起了一种新的震动。 她特别善于捕捉细节,特别善于表达细节。韩东说,看见那些能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总是惊异万分、心存敬意。表达欲和表现欲一字之差,区别明显。我看闫红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惊异和敬意。 比如她写到公共浴室里一个陌生的女人,——“许多次,我看到她仰起头,下巴与脖颈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脸上,水花晶莹,冲刷着她的短发,弹溅到她的肌肤上,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快意,仿佛,是她的灵魂,在经受着这样一场强有力的冲击,我不由想,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在她写出“她一定是在爱着吧”这几个字之前,我被这细致有力的文字感染,心中也觉得,必须有爱才配得上这有冲击力的美感。“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当闫红这样写下,我仿佛隔空,与那个正在浴室里观察着的小女孩有了通感。 闫红与我,虽说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能谈,但其实,我们是不同的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距离感。 她是一个即使与发小在一起,仍会不时地受到距离感的提醒的人。看她写与发小重逢那一篇,看完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知不觉地绷得很紧,一种感染力很强的紧张感,使这场阅读仿佛带有体力性质。 距离感和紧张感这两样东西,在我这里是不明显的。但我恰恰认为,这些东西,使闫红对生活有着我所没有的理解。 因为她无处不在的纠结、钻探,无处不在的紧张感,使得她的文字,会有一般人没有的张力。她能把很多微妙的地方,呈现得特别明白,又把一些很明白的地方,弄得非常微妙。
评分作为一个话痨,我喜欢听闫红讲,甚于我对她讲。最喜欢听她讲童年的事。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童年时的她。童年时的闫红,似乎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但又未必比别的孩子做得好,甚至某些方面比别的孩子笨拙些。总之,是一个喜感很强的孩子。尤其是她在乡村的生活,天啊,我有多么羡慕那段生活。 还喜欢听她讲一些听起来破败不堪的生活。比如说,底层人民的口味。其实闫红自己的口味,就有点奇怪。比如说她喜欢看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入流的那些专科院校,觉得它们比规整光鲜的大学更能引起兴趣:陈旧简陋,还有点不分明的雾霭,看上去很颓的年轻人在里面走动。 她喜欢小县城,路上来来去去的人、飘进她耳朵的几句对话,她都能把它们脑补成一个故事;她还喜欢一些听起来很俗的流行歌,比如有一首俗得让人涕泪交加的“你已经做了谁的小三,我也不再是你的港湾”。 ——她很喜欢有些破败的真实生活,喜欢那种粗粝的质感。不喜欢PS版的。我劝她把这些写成小说。 这一劝就是六七年。经常在她如痴如醉地讲了半天之时,我打断她,像钱玄同那样,幽幽地来一句:“你把刚才这事写下来吧?这起码可以写个一万字吧?” 在此之前,闫红出了几本书,都是文化散文,也就是说,她是以“文化散文”被公众所知的。但我知道闫红写得最好的,其实是小说。而她写得最快乐的,也是小说。 因为小说能够自成一个世界。在眼见的日常生活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广大的更诗意的世界,它也许在过去,在远方,也许就在我们脑海里,等待被描述,等待被语言通知。写小说的人,在自己给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老之将至,她们就是我最羡慕的人。 而闫红就在这些人中。就我所知,她还是写得最好的一个。 这一次,有出版商与我有一致的爱好,仿佛是退而求其次,闫红终于写了这一组本来可以作为小说题材的散文。 其实,书里几乎所有的事,我都听她说过,但是看书的时候,我还是时不时起了一种新的震动。 她特别善于捕捉细节,特别善于表达细节。韩东说,看见那些能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总是惊异万分、心存敬意。表达欲和表现欲一字之差,区别明显。我看闫红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惊异和敬意。 比如她写到公共浴室里一个陌生的女人,——“许多次,我看到她仰起头,下巴与脖颈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脸上,水花晶莹,冲刷着她的短发,弹溅到她的肌肤上,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快意,仿佛,是她的灵魂,在经受着这样一场强有力的冲击,我不由想,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在她写出“她一定是在爱着吧”这几个字之前,我被这细致有力的文字感染,心中也觉得,必须有爱才配得上这有冲击力的美感。“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当闫红这样写下,我仿佛隔空,与那个正在浴室里观察着的小女孩有了通感。 闫红与我,虽说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能谈,但其实,我们是不同的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距离感。 她是一个即使与发小在一起,仍会不时地受到距离感的提醒的人。看她写与发小重逢那一篇,看完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知不觉地绷得很紧,一种感染力很强的紧张感,使这场阅读仿佛带有体力性质。 距离感和紧张感这两样东西,在我这里是不明显的。但我恰恰认为,这些东西,使闫红对生活有着我所没有的理解。 因为她无处不在的纠结、钻探,无处不在的紧张感,使得她的文字,会有一般人没有的张力。她能把很多微妙的地方,呈现得特别明白,又把一些很明白的地方,弄得非常微妙。
评分hao
评分hao
评分作为一个话痨,我喜欢听闫红讲,甚于我对她讲。最喜欢听她讲童年的事。喜欢一个人,就会喜欢童年时的她。童年时的闫红,似乎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但又未必比别的孩子做得好,甚至某些方面比别的孩子笨拙些。总之,是一个喜感很强的孩子。尤其是她在乡村的生活,天啊,我有多么羡慕那段生活。 还喜欢听她讲一些听起来破败不堪的生活。比如说,底层人民的口味。其实闫红自己的口味,就有点奇怪。比如说她喜欢看上世纪80年代或90年代初不入流的那些专科院校,觉得它们比规整光鲜的大学更能引起兴趣:陈旧简陋,还有点不分明的雾霭,看上去很颓的年轻人在里面走动。 她喜欢小县城,路上来来去去的人、飘进她耳朵的几句对话,她都能把它们脑补成一个故事;她还喜欢一些听起来很俗的流行歌,比如有一首俗得让人涕泪交加的“你已经做了谁的小三,我也不再是你的港湾”。 ——她很喜欢有些破败的真实生活,喜欢那种粗粝的质感。不喜欢PS版的。我劝她把这些写成小说。 这一劝就是六七年。经常在她如痴如醉地讲了半天之时,我打断她,像钱玄同那样,幽幽地来一句:“你把刚才这事写下来吧?这起码可以写个一万字吧?” 在此之前,闫红出了几本书,都是文化散文,也就是说,她是以“文化散文”被公众所知的。但我知道闫红写得最好的,其实是小说。而她写得最快乐的,也是小说。 因为小说能够自成一个世界。在眼见的日常生活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广大的更诗意的世界,它也许在过去,在远方,也许就在我们脑海里,等待被描述,等待被语言通知。写小说的人,在自己给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老之将至,她们就是我最羡慕的人。 而闫红就在这些人中。就我所知,她还是写得最好的一个。 这一次,有出版商与我有一致的爱好,仿佛是退而求其次,闫红终于写了这一组本来可以作为小说题材的散文。 其实,书里几乎所有的事,我都听她说过,但是看书的时候,我还是时不时起了一种新的震动。 她特别善于捕捉细节,特别善于表达细节。韩东说,看见那些能正确表达自己内心的文字总是惊异万分、心存敬意。表达欲和表现欲一字之差,区别明显。我看闫红的文章,经常有这样的惊异和敬意。 比如她写到公共浴室里一个陌生的女人,——“许多次,我看到她仰起头,下巴与脖颈成一条优美的弧线,水柱重重地打在她脸上,水花晶莹,冲刷着她的短发,弹溅到她的肌肤上,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快意,仿佛,是她的灵魂,在经受着这样一场强有力的冲击,我不由想,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在她写出“她一定是在爱着吧”这几个字之前,我被这细致有力的文字感染,心中也觉得,必须有爱才配得上这有冲击力的美感。“她一定是在爱着吧”,当闫红这样写下,我仿佛隔空,与那个正在浴室里观察着的小女孩有了通感。 闫红与我,虽说几乎所有的话题都能谈,但其实,我们是不同的两种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的距离感。 她是一个即使与发小在一起,仍会不时地受到距离感的提醒的人。看她写与发小重逢那一篇,看完会觉得自己的身体不知不觉地绷得很紧,一种感染力很强的紧张感,使这场阅读仿佛带有体力性质。 距离感和紧张感这两样东西,在我这里是不明显的。但我恰恰认为,这些东西,使闫红对生活有着我所没有的理解。 因为她无处不在的纠结、钻探,无处不在的紧张感,使得她的文字,会有一般人没有的张力。她能把很多微妙的地方,呈现得特别明白,又把一些很明白的地方,弄得非常微妙。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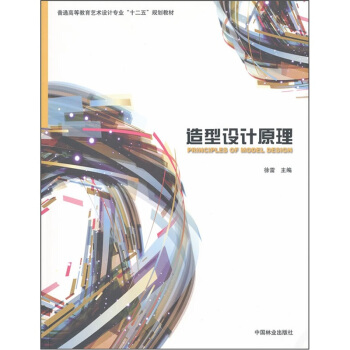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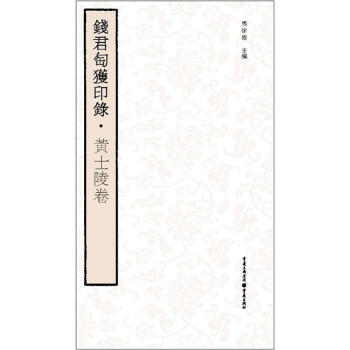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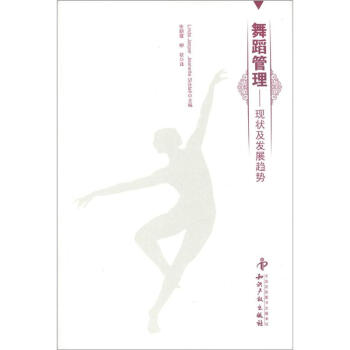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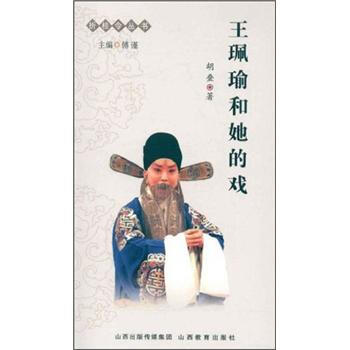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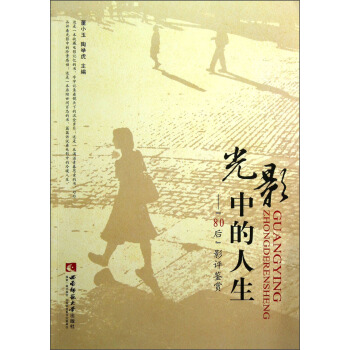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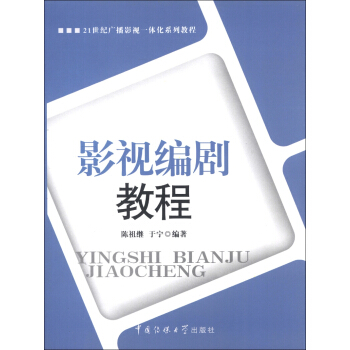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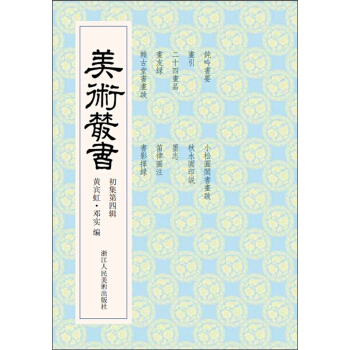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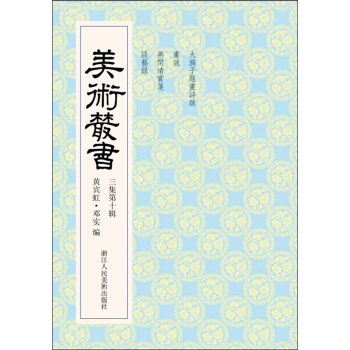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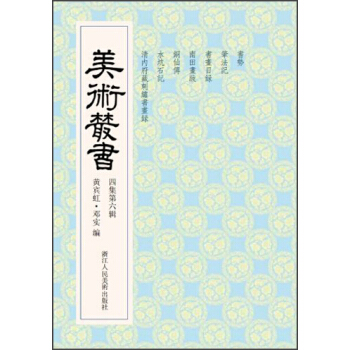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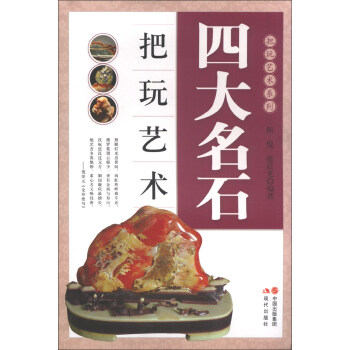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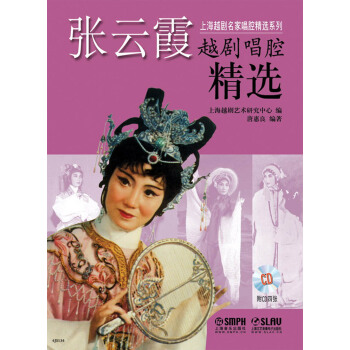
![北周佛教美术研究:以长安造像为中心 [A Study on Buddhist Art in the Northen Zhou Dynasty: Based on Chang'an Statu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308860/rBEhUlIn3AYIAAAAAALbNRfBbMgAACzAQNaSCUAAttN38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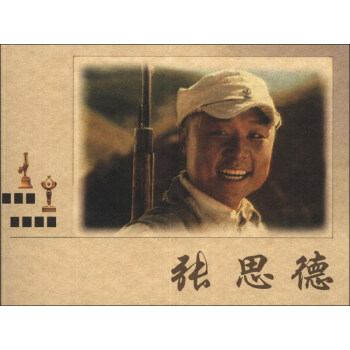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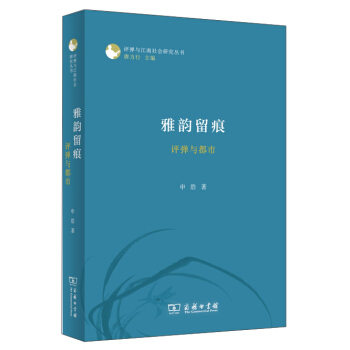

![读图时代:怎样购买文房四宝 [How to Buy Four Treasures of Chinese Stud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527561/5469ca2cN8c333bf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