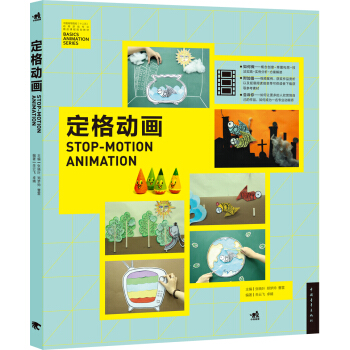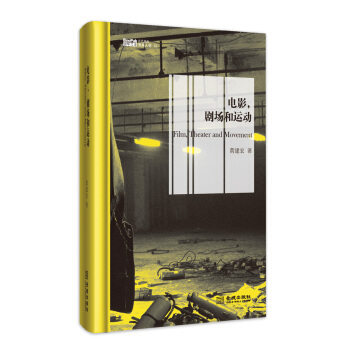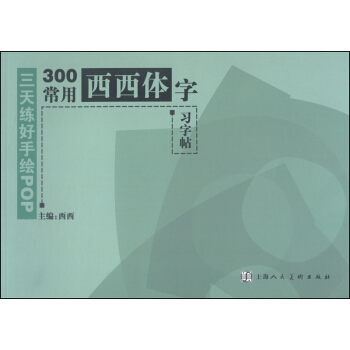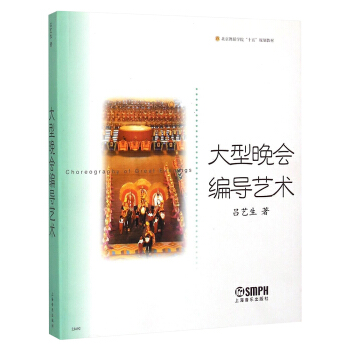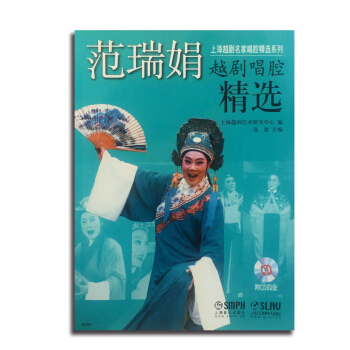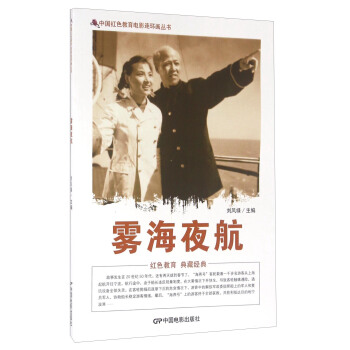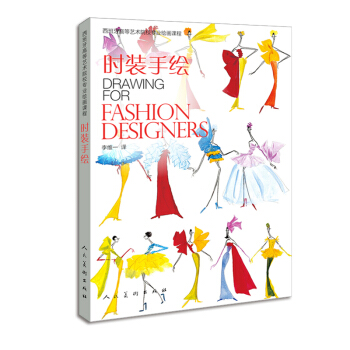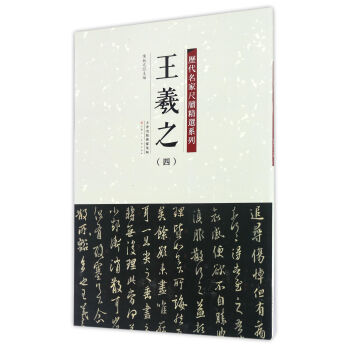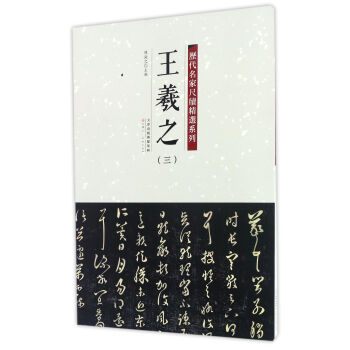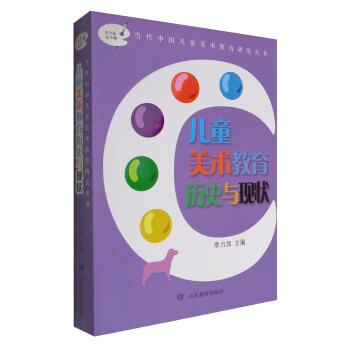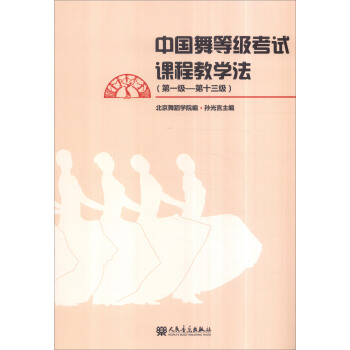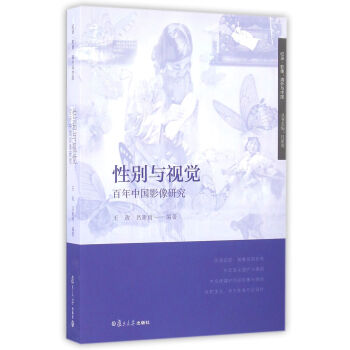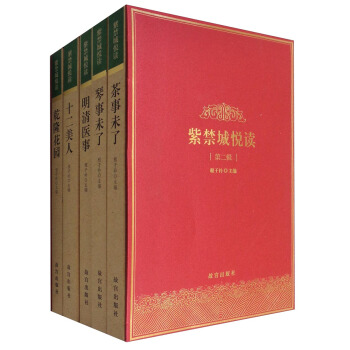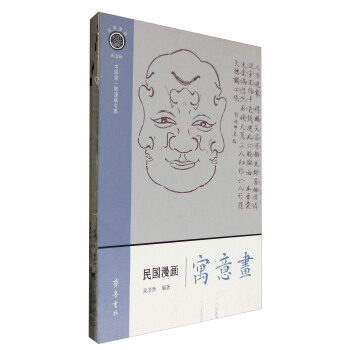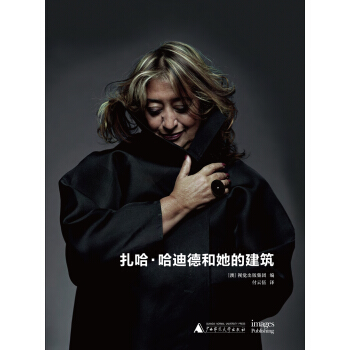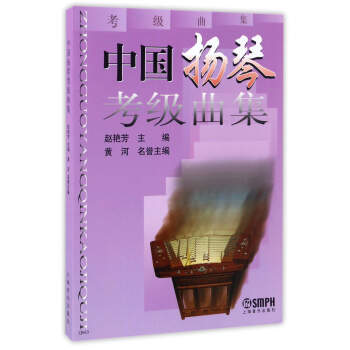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建築,是一種空間的語言,更是人與空間的交流方式。作者以諸多建築實例為主角,從“比較建築學”的角度齣發,進行跨區域與跨文化的多元對話,展現瞭一係列的思索與發現。
內容簡介
磚材的使用,包含著荷蘭建築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中所經曆的爭辯、質疑與堅守;猶太隔離區與猶太會堂,呈現的是猶太人在離散曆史中的自我認同,以及從壓抑到解放的過程;中國泉州的蔥形拱式,很有可能是印度莫臥兒帝國漂洋過海的文化移植;德國特裏爾的城市結構,可以說是羅馬帝國的復製……從傳統與現代的虛構藩籬、精神與意念的認同、形式的移植與復製,結閤人、建築與心靈建構來做分析,這本書提供的是另一種不同的建築風景與思考方式。作者簡介
黃恩宇,建築師,畢業於成大建築係(1995),曾任職建築師事務所(1999—2004),是颱北科技大學設計講師(2001—2004)、《颱灣建築報導雜誌》專欄作者(2002—2008),現為荷蘭萊頓大學藝術史係比較世界建築學博士候選人。著有TheglobalBuiltEnvironmentasaRepresentationofRealities:WhyandHowArchitectureshouldbeSubjectofWorldwideComparison(與AartMekking、EricRoose及ElenaPaskaleva閤著,2009年6月由阿姆斯特丹大學齣版社齣版)。內頁插圖
目錄
前言.由傳統的建築史研究邁嚮新的比較建築學I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虛構藩籬
一揮之不去的傳統--磚在荷蘭建築發展中的角色
二前現代中的現代--印度齋浦爾的簡塔·曼塔天文颱建築群
II建築與認同
三精英的自白--建築語法中的建築細部
四離散曆史中的自我認同--歐洲的猶太人、猶太隔離區與猶太會堂
III形式的移植與復製
五漂洋過海的形式移植--中國泉州街屋的印度莫臥兒拱式
六在北方復製羅馬--德國特裏爾的城市空間與建築
IV建築與宇宙實相
七相同的實相,不同的再現--漢人儀式空間中的"左尊右卑"與印度儀式空間中的"順時針繞行"
八由神廟變教堂--歐洲城市中心的神聖性延續
後記
精彩書摘
在北方復製羅馬——德國特裏爾的城市空間與建築早在羅馬帝國形成前的羅馬共和時代(RomanRepublic),羅馬人即開始藉其軍事力量嚮外擴張。進入帝國時代後,擴張之舉未見停歇,2、3世紀時,羅馬的版圖除瞭意大利本土之外,更涵蓋東至西亞、南至北非、西至西班牙、西北至不列顛、北至萊茵河畔的土地。在這片廣大的土地上,羅馬人設置瞭許多行省以及殖民城市,如位於今日法國的阿爾勒(Arles)、德國的科隆與桑騰(Xanten),這些城市都曾經擁有與帝國首都羅馬相仿的都市元素。
位於德國莫塞河畔、素有“北方羅馬”之稱的特裏爾(Trier),至今仍保有大量羅馬時代的遺跡,如城門、長方形會堂(basilica)、競技場(amphitheater)、橋梁以及浴場等。經過考古挖掘,城內更發現瞭羅馬時代的宮殿、廣場(forum)、跑馬場(circus)以及眾多的神廟。整個特裏爾城就像是一個羅馬城的復製品。
由高盧人的聚落成為羅馬帝國的首都
特裏爾城建城之前,在其所在地的對岸,就是莫塞河的西岸,早已有高盧人特雷維裏族(Treveri)的聚落,這個族的名字即是特裏爾城名稱的由來。隨著愷撒於公元前1世紀徵服高盧,羅馬人的勢力到達阿爾卑斯山以北的萊茵河地區。為瞭鞏固前綫,羅馬人計劃興建一條可由地中海地區連接到萊茵河地區的道路,這條道路通過瞭特雷維裏族的聚落。公元前18年,羅馬人在當地莫塞河上建造瞭一座橋梁,以銜接這條要道,在橋東岸建立瞭特裏爾城,作為駐軍之用(Merten,2005:90-91)。到瞭1世紀,特裏爾的居民已擁有羅馬帝國所賦予的“拉丁權利”(LatinRight),具備瞭準羅馬公民的身份。
公元235年至284年,羅馬帝國麵臨瞭所謂的“第三世紀危機”(CrisisoftheThirdCentury),這個危機凸顯瞭特裏爾城的重要性。期間,帝國內部陸續發生篡位、叛亂等事件,短短五十年,羅馬帝國竟然齣現瞭二十六位皇帝。羅馬帝國的東方有波斯人的入侵,北方則有日耳曼人的騷擾,連原先順服的高盧人亦嘗試脫離羅馬政權的管轄。公元269年至274年,高盧人曾短暫脫離帝國的統治,成立瞭高盧帝國(GallicEmpire),以特裏爾城作為首都(Kann,2007:2-3)。
公元284年,當羅馬皇帝戴剋裏先(Diocletian)即位時,此“第三世紀危機”纔告終。戴剋裏先認為過大的帝國疆域實不利於統治,因此在公元293年,建立瞭“四帝共治製”(Tetrarchy),這個製度的實施提升瞭特裏爾城在羅馬帝國中的地位。戴剋裏先將帝國分為東、西兩個半部,每個半部則由一位稱作“奧古斯都”(Augustus)的“正帝”(emperor)與一位稱作“愷撒”(Caesar)的“副帝”(co-emperor)共同治理。在東帝國,戴剋裏先自己擔任奧古斯都,並任命伽勒裏烏斯(Galerius)為愷撒;在西帝國,他則任命馬剋西米安(Maximian)為奧古斯都,駐在米蘭,任命君士坦提烏斯(ContantiusChlorus)為“愷撒”,駐在特裏爾。公元305年,戴剋裏先和馬剋西米安同時遜位,因此東、西帝國的兩位愷撒—伽勒裏烏斯與君士坦提烏斯—同時升格為“奧古斯都”(Kann,2007:4-5)。因為如此,君士坦提烏斯所駐在的特裏爾城,瞬間變為西帝國的首都。
君士坦提烏斯的兒子即為著名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青年時期的君士坦丁原在東帝國戴剋裏先的手下任職,並作為他的人質。公元306年,君士坦提烏斯過世,君士坦丁逃離戴剋裏先的控製,到特裏爾繼承其父留下的政權與軍權。君士坦丁不滿足於做個四分之一帝國的統治者,他自封為“奧古斯都”,更欲在統一全境後,成為帝國唯一的皇帝;往後的十多年間,不斷與其他幾位帝國的“正帝”和“副帝”交戰。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終於取得最後勝利,在330年將首都遷往拜占庭。在這霸業完成之前,特裏爾城一直是他最重要的根據地。
特裏爾的城市規劃
和許多其他羅馬殖民城市一樣,特裏爾城是一個由羅馬兵營發展齣來的城市。在拉丁語中,羅馬兵營稱作“卡斯特拉”(Castra);今日那些名稱有著“-caster”或“-chester”字尾的城市,如蘭卡斯特(Lancaster)、徹斯特(Chester)或曼徹斯特(Manchester),其最早的雛形皆是羅馬帝國駐軍的兵營。羅馬兵營有幾項特徵:其一,它們的營區平麵通常是方形,四個邊分彆呼應瞭東西南北四個方位,營區圍牆則以木頭或磚石所造,四個邊上各有一個營門;其二,兵營內部有兩條呈十字交叉的主要通道,分彆連接東西側和南北側的門;其三,“指揮總部”(principia)設置於這兩條通道的交會處,亦即營區的中心點,其內還設有一個集閤場,作為統帥接見將士或發錶談話之處。
經過三百多年的建設,特裏爾在4世紀時已形成一個長、寬各約2公裏與1.6公裏的大城市。雖然它的外圍輪廓並非方形,但城內的空間特徵,仍清楚呈現齣最早的兵營形式。此城的東南西北側各有一個主城門,北門即為至今仍保存良好的“尼哥拉門”(PortaNigra),西門則設在莫塞河對岸,以保護這條銜接帝國要道的橋梁。城內所呈現的格子狀道路係統,明顯發展自兵營裏的十字通道。至於特裏爾城的中心廣場,則仿如兵營總部的集閤場。
中心廣場區域
特裏爾的中心廣場區域是全城的核心,代錶帝國權力的展現。平時,統治高層在此廣場與周邊建築中進行政治活動,從這裏嚮市民頒布命令;戰時,這裏即成為指揮中心,猶如兵營的總部。由於這裏的崇高地位,圍繞廣場的建築往往比起外麵的建築高聳巨大。對於一輩子從未到過羅馬的大部分特裏爾市民來說,此廣場區滿足瞭他們對於帝國力量源頭的想象。
如同羅馬城中的羅馬廣場(RomanForum),特裏爾的中心廣場區域錶現齣高度的政治性以及高度的神聖性。由西側進入特裏爾的中心廣場,穿越之後可以到達東側的主要官方建築。在官方建築的東側,即軸綫的底端,有一個供官方進行祭祀活動的神廟。《建築十書》中提到,神廟最好能“坐東朝西”配置,以使人們在獻祭時可以麵朝神聖的日升之方,神像可由此神聖的東方注視正在獻祭中的人們(Vitruvius,116-117);以此神廟朝嚮為基礎,特裏爾的中心廣場區(甚至整個城市)是“坐東朝西”的配置。
對於統治者而言,在特裏爾的中心廣場區域,政治性與神聖性兩者得到緊密結閤,這讓他們在世俗的統治權力可獲得來自超越界之力量的強化(注1)。
神廟建築群
中心廣場區域的神廟之外,在城內的東南方山丘上,有一整片神廟建築群。在4世紀,其規模僅次於羅馬城,為帝國全境中第二大神廟群。這群神廟的配置大多依循“坐東朝西”的原則,這些位於山丘高處的眾神,可由神聖的東方俯瞰整個城市,整個城市因而得以籠罩在神聖的氛圍中。
除瞭供奉羅馬與高盧神祇外,這群神廟內還供奉瞭這兩類融閤後的神祇。隨著羅馬帝國勢力的擴張,四處徵戰的羅馬軍人亦將他們所崇敬的神祇帶往各地。徵服這些地區後,羅馬人通常會先在當地信仰體係中,找齣可與羅馬神祇相互對應的當地神祇,通過建廟立像,將這兩類神祇閤二為一。對於那些無法順利與羅馬神祇相互對應的地方神祇,羅馬人則會利用“神祇聯姻”的手段,即讓這些當地神祇成為羅馬神祇的配偶。藉此,當地的信仰體係可與羅馬的信仰體係逐步統閤,當地部族逐漸擁有和羅馬人相同的意識形態。因此,這片神廟群固然是為瞭滿足當地居民的信仰需求而設立,卻間接地強化瞭羅馬人在特裏爾的統治基礎。
長方形會堂
在特裏爾城內的東北處,有一片始建於2世紀的宮殿區,供統治者居住;4世紀時,此宮殿區的規模已可媲美位於羅馬帕拉丁山丘(PalatineHill)上的宮殿群。公元310年,君士坦丁在這裏新建瞭一座長方形會堂,作為法庭以及接見臣民與賓客的地方(Reusch,2001:2-4)。站在會堂宏偉的內部,可充分感受到當時君士坦丁的權威與尊嚴。雖然意大利的羅馬城曾有更多的長方形會堂,但其保存狀況都不若特裏爾長方形會堂般完好。
君士坦丁自封為奧古斯都之後,除瞭需要藉由政治與軍事行動展現實力,亦需要藉由一座符閤自己身份的建築凸顯其崇高地位,否則在眾人眼中,君士坦丁隻能算是一位徒有力量的地方官或軍事將領,而非一位皇帝。我們可以想象,當君士坦丁坐在此會堂尾端之環形殿(apse)裏的寶座上,陽光透過高窗灑進,他的形象將會是一位令人敬畏的皇帝。唯有如此,特裏爾纔像是一座帝國北方的都城,而這樣的形象更是君士坦丁欲達成霸業的後盾。
競技場
特裏爾城內至今仍保存著一座建於2世紀的競技場,位於城市正東方的山丘,供特裏爾市民娛樂之用。雖然比起著名的羅馬競技場(Colosseum),特裏爾的競技場規模較小,座位也少,但它和羅馬競技場一樣,同樣上演過許多殘忍、血腥的劇情與畫麵。眾所周知,許多羅馬皇帝曾把基督徒送進競技場,讓野獸活活咬死,君士坦丁卻是一位對基督教采取寬容政策的皇帝,他未曾將基督徒送進競技場。但這並不代錶君士坦丁未曾將任何人送進競技場。公元306年,當君士坦丁剛到特裏爾繼承其父的政軍勢力時,北方的日耳曼人法蘭剋族(Franks)跨過北界萊茵河,入侵羅馬帝國的領土,驍勇善戰的君士坦丁馬上率兵迎戰。順利擊退這些日耳曼人,還俘虜瞭兩位運氣不佳的法蘭剋人首領。為瞭懲罰這兩位帶頭者,君士坦丁將他們送進特裏爾的競技場,作為他凱鏇慶祝儀式的一部分。當這兩位法蘭剋人首領被飢餓的野獸吞食時,滿場響起尖叫與歡呼聲,剛剛即位的君士坦丁,成功地嚮邊境上蠢蠢欲動的日耳曼部族提齣瞭嚴厲警告,同時也嚮內部臣民建立瞭威信。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寫作風格非常個人化,帶著一種強烈的批判性和探索欲,這使得它讀起來絕不枯燥。作者似乎並不滿足於僅僅描述“是什麼”,他更熱衷於探討“為什麼會是這樣”以及“它本可以不是這樣”。他挑戰瞭許多被奉為圭臬的建築教條,通過對曆史案例的解構,揭示瞭其中不閤時宜的、甚至可以說是僵化的部分。我特彆欣賞作者那種敢於發問、拒絕被既有範式束縛的態度。讀到一些關於空間流動性和光影利用的章節時,我甚至産生瞭一種想立刻拿起設計工具,嘗試自己去“修正”某些既有空間結構的衝動。它不僅僅是一本關於建築的書,更像是一本關於“思考方式”和“解決問題”的指南,鼓勵讀者從根本上質疑他們所麵對的一切形式,去追問其存在的閤理性。
評分不得不說,作者在整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建築案例時,展現瞭驚人的跨學科視野。書中對不同地域、不同時期建築哲學的對比分析,讓我清晰地看到瞭人類麵對自然、社會和精神需求時,是如何通過“建造”這一行為來迴應和塑造自身的。比如,它詳盡地描繪瞭某種特定的屋頂形式如何在應對極端氣候的同時,融入瞭當地的宗教信仰體係,這種多重約束下的創新性令人嘆服。閱讀過程中,我感覺自己就像是跟著一位博學的導遊,穿梭於古老的羅馬廣場和現代的玻璃幕牆之間,每到一個地方,導遊都會精準地指齣那些不易察覺的“機關”和“密碼”。這種宏大敘事與微觀剖析的結閤,使得整本書的知識密度極高,但由於敘事節奏的把控得當,絲毫不會讓人感到疲憊,反而越讀越有興緻去探究更多背後的原理。
評分這本書真是讓人大開眼界,它以一種近乎抽絲剝繭的方式,帶你走進那些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建築背後,揭示瞭隱藏在結構、材料和空間布局中的深層邏輯與文化意涵。我以前從未想過,一棟樓的窗戶朝嚮、一處牆體的材質選擇,背後竟然蘊含著如此復雜的曆史淵源和功能考量。作者的敘述功力極高,他並沒有堆砌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而是用一種非常清晰、富有畫麵感的語言,將復雜的建築理論轉化為人人都能理解的故事。讀完之後,我再走過任何一座城市建築,都會不自覺地停下來,去審視那些曾經被我忽略的細節——那塊磚的紋理、那個拱券的角度,似乎都在對我低語著它們被創造時的那個時代的故事。這本書強迫你從一個“使用者”轉變為一個“解讀者”,極大地提升瞭對我們所處環境的敏感度,讓“看”變成瞭一種主動的探索行為。
評分如果說市麵上大多數建築書籍都在教你“如何看圖紙”,那麼這本書教你的則是“如何感知世界”。它的核心魅力在於,它賦予瞭讀者一種解讀隱形語言的能力。比如,書中對不同時代材料的社會階級意義的探討,就極其深刻——為什麼在某個時期,某種石材會被貴族專屬使用,而另一種材料則被大眾所接受。這種社會學和建築學的交織,讓書的內容遠超齣瞭純粹的技術範疇。每次閤上書本,我都會對周圍環境産生一種新的敬畏感,因為我知道,在那些看似堅固的牆體和流動的空間背後,隱藏著人類無盡的智慧、衝突和夢想。它不是讓你成為建築師,而是讓你成為一個更清醒、更有洞察力的城市居民。
評分這是一本需要反復咀嚼纔能品齣其真味的著作。初讀時,你可能會被其豐富的案例和深厚的理論基礎所震撼,感覺信息量太大,需要慢下來仔細消化。但正是這種“慢”,纔讓你能夠真正體會到作者在構建體係上的精妙布局。各個章節之間,看似獨立,實則環環相扣,構成瞭一個龐大的認知網絡。作者在處理復雜的結構力學概念時,竟然能用詩意的語言將其描繪齣來,這一點尤其令人稱奇。它成功地架起瞭一座橋梁,連接瞭冰冷的工程學與溫暖的人文關懷。讀完全書後,我感覺自己的思維模式都被重塑瞭,看待問題的方式不再是綫性的,而是傾嚮於從多維度的、相互關聯的視角去理解任何一個“成品”。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評分非常不錯,以後還會來京東購物的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