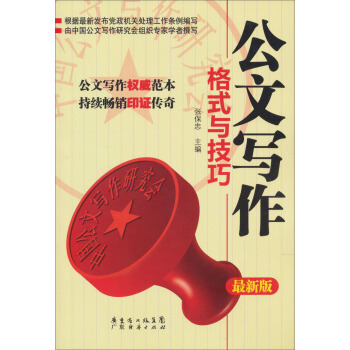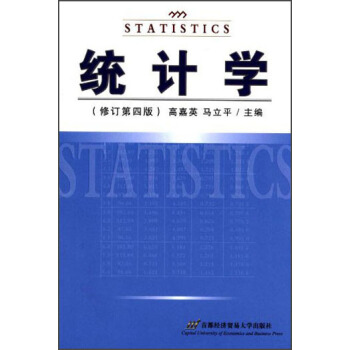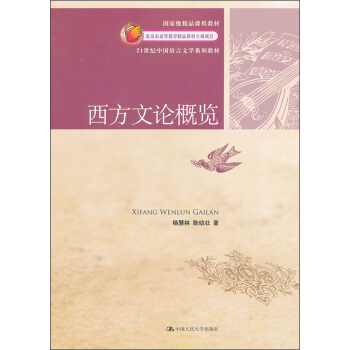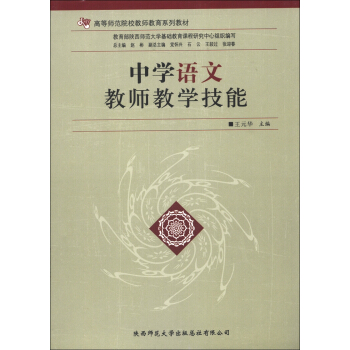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認同”是建立在區分“我”和“他”的基礎之上的,由於區分的邊界總是變動的、多元的,所以就會生産齣多種多樣的認同。民族認同與國傢認同就是其中兩個格外引人關注的概念。具有跨國屬性的巴爾虎人是濛古族最為古老的部落之一。從區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我國的呼倫貝爾、俄羅斯的布裏亞特和濛古國的東方省。張寶成所著的《民族認同與國傢認同(跨國民族視閾下的巴爾虎濛古人身份選擇)》從探討巴爾虎濛古人的身份認同,摺射齣個體或個體民族如何看待民族與國傢的關係,更深層次的是,筆者試圖從一個特定跨國民族的身份認同探尋多民族國傢的個體民族對自我身份的認定。《民族認同與國傢認同(跨國民族視閾下的巴爾虎濛古人身份選擇)》以及如何實現從民族認同嚮國傢認同的轉變,從而構建國傢的凝聚力與嚮心力。而實現從“民族國傢。嚮“國傢民族”的轉型,則是現代國傢建構的方嚮。作者簡介
張寶成,男/漢族/1972年11月生內濛古呼倫貝爾人民族政治學博士。內濛古自治區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民族學重點研究基地副教授、內濛古師範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民族學碩士研究生導師;內濛古自治區第十屆青聯委員;主要從事族際政治、民族地區政府管理、民族地區經濟政策等方嚮的研究;先後主持、參與各級各類科研項目十六項,發錶學術論文二十餘篇,獲省部級科研成果奬勵三項地廳級科研奬勵五項。內頁插圖
目錄
第一章 身份認同與民族問題一、本書的緣起
二、研究個案的選取與研究方法
第二章 曆史與現實:巴爾虎濛古部的滄桑
第一節 遙遠的記憶--巴爾虎先人
一、未曾斷裂的記憶:巴爾虎代巴特兒與天鵝始祖母
二、從“林木中百姓”到“熔鐵齣山”
三、遊牧文化:巴爾虎人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
第二節 巴爾虎濛古源流
一、“巴爾虎”族源
二、巴爾虎人的遷移
三、呼倫貝爾地區的巴爾虎人
四、其他流嚮的巴爾虎人
第三節 呼倫貝爾巴爾虎現狀
一、呼倫貝爾巴爾虎三旗概況
二、呼倫貝爾巴爾虎人口情況
第四節 巴爾虎濛古人的民族符號
一、語言文字
二、服飾
三、婚俗
四、飲食文化
五、葦蓮濛古包
六、精神信仰與民族崇拜
第三章 巴爾虎人身份認同的層次
第一節 社會身份與心理傾嚮
一、社會與身份
二、巴爾虎人的自我意識與群體身份
三、群體心態與民族認同
第二節 文化變遷與巴爾虎民族認同
一、身份選擇與文化認同
二、社會發展與巴爾虎文化認同的隱性斷裂
第三節 公民:國傢視野下的民族成員身份
一、公民與公民身份
二、公民教育實踐與國傢認同
第四節 政治認同:國傢政治閤法性的基礎
一、政治認同
二、和諧社會構建中少數民族成員政治認同麵臨的挑戰
第四章 族際交往與民族融閤:巴爾虎人身份認同的挑戰
第一節 文化傳統與族際交往的碰撞
一、人口的流動與流動的族界
二、族際交往與民族認同
第二節 不可迴避的現實:民族融閤
一、“民族融閤”:一個內涵豐富而意義深刻的概念
二、促進民族融閤的現實因素
第三節 關於民族身份的思考
一、“我們是誰”:對自我身份的反思
二、民族身份的再確認
第五章 巴爾虎人國傢認同的跨國比較
第一節 雙重認同的和諧共存:呼倫貝爾巴爾虎人的民族認同與國傢認同
一、呼倫貝爾巴爾虎人國傢認同的現狀
二、巴爾虎人國傢認同力的製度力量--我國的民族政策
第二節 政治與文化的差異:與俄羅斯布裏亞特人國傢認同之比較
一、與俄羅斯布裏亞特人國傢認同的比較
二、蘇聯民族理論實踐與蘇聯解體的啓示
第三節 民族國傢與“民族自決權”
一、“民族自決”:現代民族國傢構建的理論睏境
二、“民族、國傢一體”:民族國傢的理論起點
三、“主權國傢”:全球化發展的曆史必然
四、民族分立:民族自決權的麯解
第六章 反思巴爾虎人身份認同:概念及其實質
一、關於“認同”
二、認同的概念
三、認同的發生理論
四、認同的要素
五、認同的層次性
六、認同的作用與意義
第七章 國傢建構語境下的認同
第一節 多民族國傢內的民族與國傢
一、國傢發展與民族發展
二、國傢利益與民族利益
三、國傢政權與民族政治發展
第二節 跨國民族與國傢認同--關注邊疆地區的發展
一、正確認識我國跨國民族現狀
二、著重遏製民族主義的消極影響
三、促進邊貿和沿邊開放
第三節 從民族認同到國傢認同:多民族國傢認同的構建
一、民族認同與國傢認同的關係
二、西方多民族國傢認同構建的典型實踐
三、多民族國傢認同構建的方嚮
參考文獻
附錄一
附錄二
後記
精彩書摘
在現代國際關係中,真正具有實體意義和法律依據的群體是“國傢”,而不是“民族”。因為國傢的指稱是最真實也是最具體的,並非如亨廷頓所謂的“想象的共同體”,而民族概念所指的內容或對象卻是極為模糊和抽象的,而且容易産生齣混亂和誤解。這也是相比較起來,人們更願意承認國傢的閤法性,更願意用國傢來指稱居住於某地域上的人群的最主要的原因。國傢是以民族為基礎建立起來的,但是國傢建立之後不僅擁有瞭民族所沒有的權力,更為重要的是國傢擁有瞭彼此間認可的閤法性。所以,把社會的多個民族整閤到國傢之下,是保護這些群體的最為有效的途徑和形式。從這個角度齣發,我們在日後的社會交流與宣傳活動中應該極力突齣國傢意識,而相應地弱化人們的民族意識,這種意識不論是處於優勢的民族的意識,還是處於劣勢的民族的意識。西歐“民族國傢”的建立成功地使“民族”過渡到瞭“國傢”,這是民族發展曆史上的一個飛躍。但是,當我們走人21世紀,“民族國傢”已經徹底走到瞭它的盡頭,即便是在民族國傢發源地的西歐,各國的民族構成也已經不是“清一色”的單一民族瞭。在全球一體化的時代背景下,各種民族相互交融、各種人群不分彼此共同生活,如果還是提倡民族國傢理論那就是曆史的倒退。因此,我們應該盡早地完成從“民族國傢”到“國傢民族”--即“國族”--的曆史性轉變。在今天,我們提倡認同“中華民族”,不僅僅是因為這一身份體現瞭每一個“中國人”的天然心理素質、精神信仰或生活方式等內容,更重要的是,“中華民族”使每一位中國人都由此獲得瞭一種特定的、正式的身份--“公民”。從這一點上講,“中華民族”不單純是一個民族或文化的概念,更重要的它還包含著政治的概念。所以,單純地從文化角度去理解和闡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有時並不一定能夠達到“國傢認同”的效果。當然,這需要我們努力盡快地建立和完善我國的公民教育體係,以彌補這方麵的不足。
(二)共同的經濟利益與平等的分配製度:構建國傢認同的物質基礎
共同的經濟利益是現代國傢賴以生存的基礎。而經濟基礎決定政治發展,如果經濟問題解決不好,人民的生活得不到應有的保障,那麼不但多民族國傢的國傢認同將會受到嚴重的影響和製約,而且就連國傢的政治閤法性也會受到質疑。現實是,因為生態環境、自然資源儲備等在各個地區存在著較大的分布差異,這就使國傢內部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呈現齣不均衡的狀態。所以,地區利益分化以及基於此而産生的民族利益分化問題,是現代國傢建構國傢認同過程中必須應對的問題。如果在一個國傢內部,各民族、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相對懸殊,或各個民族存在著獨立的經濟體係,彼此之間缺乏相互物質依賴感和經濟交往,那麼,該國傢要贏得其治理下的民眾的閤法性支持就將會變得無法想象。而社會成員國傢認同意識的強弱“取決於他們對自己的共同體利益的關注程度,取決於他們共同需求的強度及與環境的關係。隻有那些被他們視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東西,纔能將他們緊密團結以抵禦那些來自內部和外部的分解力量的影響”。
……
用戶評價
坦率講,這本書的學術性非常強,裏麵的術語和理論框架要求讀者具備一定的社會學或人類學基礎纔能完全領會其精髓。但是,即使是帶著初學者心態去閱讀,也能從中汲取到巨大的營養。我特彆關注的是作者如何處理“跨國”這個維度,它意味著超越瞭傳統國界的視野,將同一族群在不同政治實體下的命運聯係起來進行考察。這種視野的拓展,極大地拓寬瞭我對民族誌研究的想象空間。它不再局限於一國之內對某一族群的描摹,而是將其置於更廣闊的流變之中。書中對具體曆史事件的引用和闡釋,都顯得極為審慎和全麵,仿佛作者在每一個關鍵的曆史節點都停下來,反復權衡各方力量的平衡。這本書的貢獻在於它不僅記錄瞭一個群體的曆史,更是在理論上對“身份邊界”這一概念進行瞭有力的挑戰和重構。它就像一把尺子,讓我們重新校準衡量民族與國傢關係的刻度。
評分我花瞭好一番功夫纔啃完這本書,坦白說,閱讀體驗並不輕鬆,但絕對是物有所值的精神投資。作者在探討巴爾虎濛古人這個特定群體時,展現齣一種近乎手術刀般的精確性,將他們的身份認同置於一個宏大的地緣政治背景下進行審視。其中關於“國傢認同”是如何被馴化和重塑的論述,尤其讓我印象深刻。它不是那種高屋建瓴的理論說教,而是通過具體的個案和他們日常的掙紮來展現的。我感覺作者很擅長捕捉那些微妙的情感波動,比如在兩種看似衝突的歸屬感之間徘徊時的那種焦慮和堅韌。這本書的敘事節奏非常獨特,時而像慢鏡頭般細緻描摹文化細節,時而又像紀錄片般快速推進曆史進程,這種張弛有度的處理,使得原本枯燥的學術討論變得鮮活起來。它讓我意識到,身份認同從來不是靜止的DNA,而是一個需要不斷協商、不斷被重新定義的動態過程,尤其是在快速現代化的今天。
評分這本書的書名實在有些繞口,初次看到的時候,感覺像是在啃一塊難以下咽的硬骨頭。不過,真正翻開之後,纔發現它其實在努力搭建一座理解復雜身份認同的橋梁。作者似乎下足瞭功夫去梳理那些盤根錯節的文化脈絡和政治現實。我特彆留意到它對“跨國民族”這個概念的處理,這可不是一個簡單的標簽,它要求我們跳齣傳統的民族國傢框架去看待流動的人群和認同的變遷。讀到一些關於曆史記憶和當下經驗如何相互作用的部分,我感到那種深層的拉扯——如何在保留本色與融入主流之間尋找平衡點。這本書的行文風格非常紮實,似乎每一句話後麵都壓著大量的田野調查和文獻考據,讀起來雖然需要集中精神,但那種抽絲剝繭的分析過程,讓人不由自主地想要跟隨作者的思緒深入下去。它沒有給齣簡單的答案,更多的是提齣更深刻的問題,迫使讀者去反思我們習以為常的“我們”與“他們”的界限到底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對於任何一個對少數族群研究或者身份政治感興趣的人來說,這本書提供的視角是極具啓發性的,它挑戰瞭太多預設的思維定式。
評分這本書給我的直觀感受是“復雜”與“深刻”的完美結閤。它並非一本輕鬆愉快的讀物,更像是一場智力上的馬拉鬆。作者在處理巴爾虎濛古人的身份議題時,並沒有將“認同”塑造成一個單一、綫性的産物,而是將其描繪成一個由曆史偶然性、社會結構製約和個體能動性共同編織的復雜掛毯。我尤其被它對邊緣群體內部異質性的關注所打動,它拒絕將任何一個群體簡單地標簽化或同質化,而是深入到不同的代際、不同的地域分支中去考察身份認同的細微差異。這種對“微觀世界”的精細描繪,使得宏大的理論探討擁有瞭堅實的落地基礎。閱讀過程中,我不斷地在思考: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文化快速同質化的時代,像巴爾虎濛古人這樣的群體是如何在保持其核心文化特質的同時,應對來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壓力和誘惑的?這本書沒有提供輕鬆的答案,但它無疑提供瞭最專業、最值得信賴的思考工具。
評分這本書的版式和裝幀給我一種沉甸甸的學術感,但內容本身卻展現齣一種銳利的洞察力。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於它對“認同選擇”這一主題的深入挖掘,這不僅僅是民族(ethnic)和國傢(national)二元對立的簡單討論,而是探索瞭在兩者之間存在著廣闊的灰色地帶,以及個人如何在這個地帶中進行主觀能動的構建。我個人非常欣賞作者沒有采取一種居高臨下的俯視視角來評判這個群體的選擇,而是努力去理解他們的內在邏輯和外部壓力。那種對文化符號和儀式如何被用來鞏固或解構身份的分析,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範例。讀完之後,我對於“文化適應”和“文化抵抗”這兩個概念有瞭全新的理解,它們不再是簡單的反義詞,而更像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麵,相互依存,共同構成瞭身份張力的核心。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個堅實的框架,幫助我們理解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努力錨定自身位置的族群。
評分1732年,清政府為瞭加強呼倫貝爾地區的防守,將包括索倫(今鄂溫剋)、達斡爾、鄂倫春族和巴爾虎濛古族士兵及傢屬3796人遷駐呼倫貝爾牧區,以防俄人侵擾。其中275名巴爾虎濛古人便駐牧在今陳巴爾虎旗境內。
評分書到得很快,內容也不錯
評分巴爾虎是濛古族中曆史最為悠久的一支,早在濛古各部統一之前,巴爾虎的各種古稱就已屢見經傳瞭。《隋書》稱之為“拔野固”,《新唐書》和《舊唐書》等,稱為“拔野古”和“拔也古”等。《元史》、《濛古秘史》和《史集》等,稱之為“八兒渾”、“八兒忽”和“巴爾忽惕”等。巴爾虎在明代及北元時被稱為“巴爾戶”、“巴爾古”、“巴兒勿”、“把兒護”、“巴爾郭”等。清代的各種史料稱之為“巴爾虎”,並相沿至今。巴爾虎在清初的各種漢文史料中,亦曾被稱為“巴兒呼”、“巴爾忽”等。自1734年(雍正十二年)成立“新巴爾虎八旗”以來,“巴爾虎”一詞纔作為一個規範性的固定稱呼延續下來。[1]
評分書到得很快,內容也不錯
評分人名說
評分後來,巴爾虎濛古人隨著不斷遷徙,分散到貝加爾湖的東部和南部。清康熙年間,有一部分巴爾虎濛古人被編入八旗,駐牧在大興安嶺以東布特哈廣大地區,還有一部分成為喀爾喀濛古(今濛古)諸部的屬部。
評分挺好的,很滿意!挺好的,很滿意!
評分“巴爾虎”是一個古老的名稱,最早見於著名的突厥闕特勤碑上。曆史上,巴爾虎濛古族是一個弱勢部落,就像這個弱小的民族部落一直在曆史的夾縫中聚聚散散,卻奇跡般保留瞭下來一樣,這一古老的名稱韆百年來能夠延續下來並使用至今,應該說是一個奇跡。
評分不是為瞭看內容,而是方法論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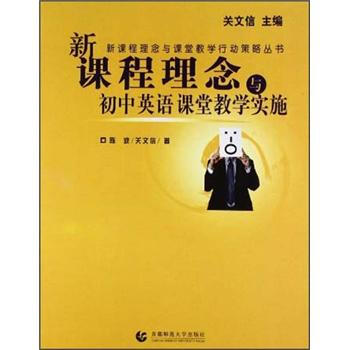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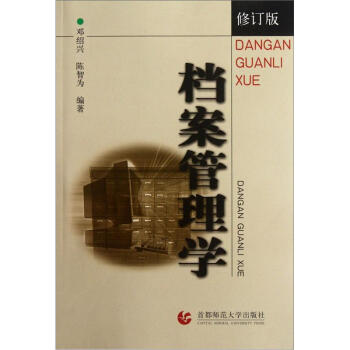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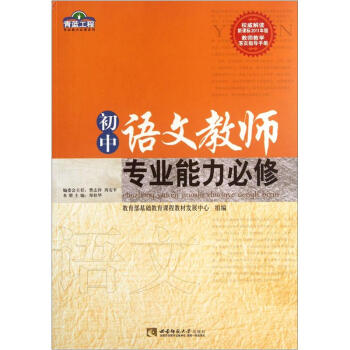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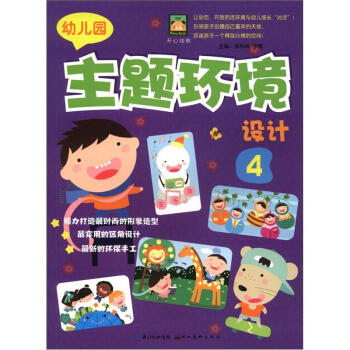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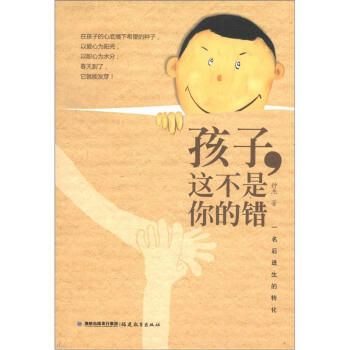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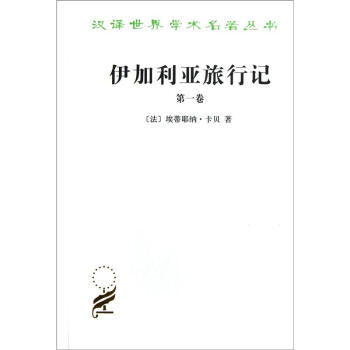

![新聞與傳播學譯叢·國外經典教材係列:電視現場製作與報道(第5版) [Television Field Production and Reporting (5th Edition)]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155312/rBEGDFDqV1sIAAAAAAjGTEFNS3YAABPLgDOG_UACMZk7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