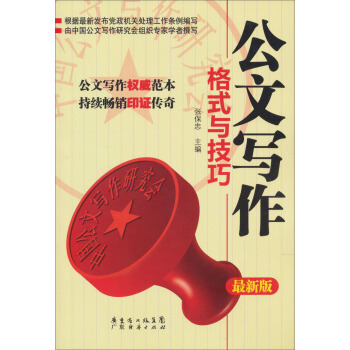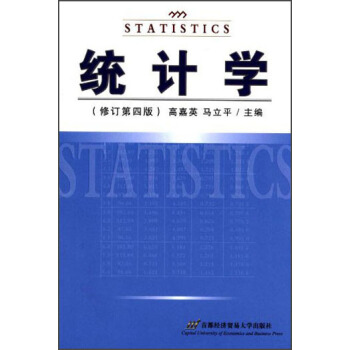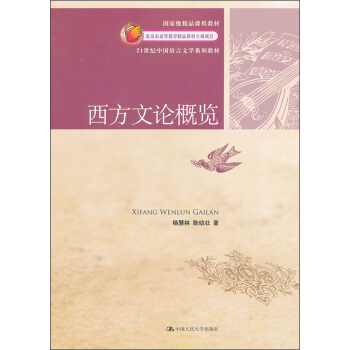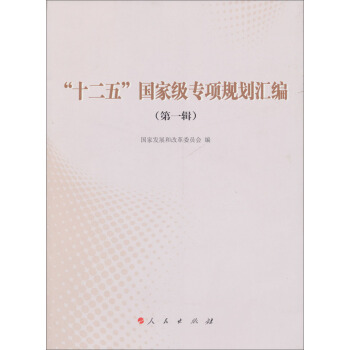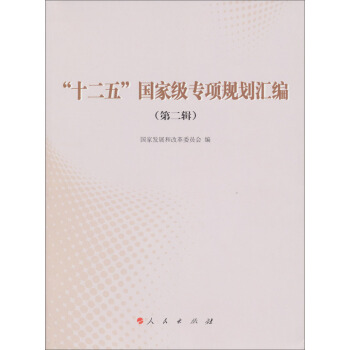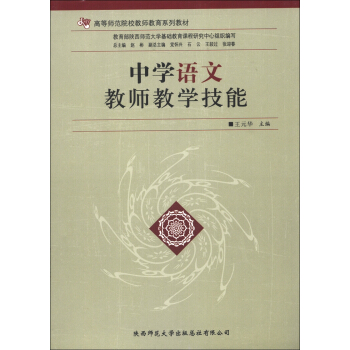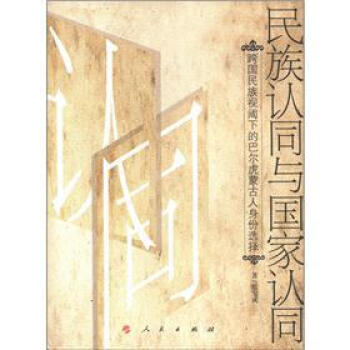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认同”是建立在区分“我”和“他”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区分的边界总是变动的、多元的,所以就会生产出多种多样的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就是其中两个格外引人关注的概念。具有跨国属性的巴尔虎人是蒙古族最为古老的部落之一。从区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呼伦贝尔、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和蒙古国的东方省。张宝成所著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从探讨巴尔虎蒙古人的身份认同,折射出个体或个体民族如何看待民族与国家的关系,更深层次的是,笔者试图从一个特定跨国民族的身份认同探寻多民族国家的个体民族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跨国民族视阈下的巴尔虎蒙古人身份选择)》以及如何实现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从而构建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实现从“民族国家。向“国家民族”的转型,则是现代国家建构的方向。作者简介
张宝成,男/汉族/1972年11月生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民族政治学博士。内蒙古自治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民族学重点研究基地副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青联委员;主要从事族际政治、民族地区政府管理、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等方向的研究;先后主持、参与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十六项,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励三项地厅级科研奖励五项。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身份认同与民族问题一、本书的缘起
二、研究个案的选取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 历史与现实:巴尔虎蒙古部的沧桑
第一节 遥远的记忆--巴尔虎先人
一、未曾断裂的记忆:巴尔虎代巴特儿与天鹅始祖母
二、从“林木中百姓”到“熔铁出山”
三、游牧文化:巴尔虎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第二节 巴尔虎蒙古源流
一、“巴尔虎”族源
二、巴尔虎人的迁移
三、呼伦贝尔地区的巴尔虎人
四、其他流向的巴尔虎人
第三节 呼伦贝尔巴尔虎现状
一、呼伦贝尔巴尔虎三旗概况
二、呼伦贝尔巴尔虎人口情况
第四节 巴尔虎蒙古人的民族符号
一、语言文字
二、服饰
三、婚俗
四、饮食文化
五、苇莲蒙古包
六、精神信仰与民族崇拜
第三章 巴尔虎人身份认同的层次
第一节 社会身份与心理倾向
一、社会与身份
二、巴尔虎人的自我意识与群体身份
三、群体心态与民族认同
第二节 文化变迁与巴尔虎民族认同
一、身份选择与文化认同
二、社会发展与巴尔虎文化认同的隐性断裂
第三节 公民:国家视野下的民族成员身份
一、公民与公民身份
二、公民教育实践与国家认同
第四节 政治认同: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基础
一、政治认同
二、和谐社会构建中少数民族成员政治认同面临的挑战
第四章 族际交往与民族融合:巴尔虎人身份认同的挑战
第一节 文化传统与族际交往的碰撞
一、人口的流动与流动的族界
二、族际交往与民族认同
第二节 不可回避的现实:民族融合
一、“民族融合”:一个内涵丰富而意义深刻的概念
二、促进民族融合的现实因素
第三节 关于民族身份的思考
一、“我们是谁”:对自我身份的反思
二、民族身份的再确认
第五章 巴尔虎人国家认同的跨国比较
第一节 双重认同的和谐共存:呼伦贝尔巴尔虎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一、呼伦贝尔巴尔虎人国家认同的现状
二、巴尔虎人国家认同力的制度力量--我国的民族政策
第二节 政治与文化的差异:与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国家认同之比较
一、与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国家认同的比较
二、苏联民族理论实践与苏联解体的启示
第三节 民族国家与“民族自决权”
一、“民族自决”: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理论困境
二、“民族、国家一体”:民族国家的理论起点
三、“主权国家”: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必然
四、民族分立:民族自决权的曲解
第六章 反思巴尔虎人身份认同:概念及其实质
一、关于“认同”
二、认同的概念
三、认同的发生理论
四、认同的要素
五、认同的层次性
六、认同的作用与意义
第七章 国家建构语境下的认同
第一节 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与国家
一、国家发展与民族发展
二、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
三、国家政权与民族政治发展
第二节 跨国民族与国家认同--关注边疆地区的发展
一、正确认识我国跨国民族现状
二、着重遏制民族主义的消极影响
三、促进边贸和沿边开放
第三节 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构建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二、西方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典型实践
三、多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方向
参考文献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精彩书摘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真正具有实体意义和法律依据的群体是“国家”,而不是“民族”。因为国家的指称是最真实也是最具体的,并非如亨廷顿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而民族概念所指的内容或对象却是极为模糊和抽象的,而且容易产生出混乱和误解。这也是相比较起来,人们更愿意承认国家的合法性,更愿意用国家来指称居住于某地域上的人群的最主要的原因。国家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是国家建立之后不仅拥有了民族所没有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拥有了彼此间认可的合法性。所以,把社会的多个民族整合到国家之下,是保护这些群体的最为有效的途径和形式。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在日后的社会交流与宣传活动中应该极力突出国家意识,而相应地弱化人们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不论是处于优势的民族的意识,还是处于劣势的民族的意识。西欧“民族国家”的建立成功地使“民族”过渡到了“国家”,这是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飞跃。但是,当我们走人21世纪,“民族国家”已经彻底走到了它的尽头,即便是在民族国家发源地的西欧,各国的民族构成也已经不是“清一色”的单一民族了。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各种民族相互交融、各种人群不分彼此共同生活,如果还是提倡民族国家理论那就是历史的倒退。因此,我们应该尽早地完成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即“国族”--的历史性转变。在今天,我们提倡认同“中华民族”,不仅仅是因为这一身份体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天然心理素质、精神信仰或生活方式等内容,更重要的是,“中华民族”使每一位中国人都由此获得了一种特定的、正式的身份--“公民”。从这一点上讲,“中华民族”不单纯是一个民族或文化的概念,更重要的它还包含着政治的概念。所以,单纯地从文化角度去理解和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有时并不一定能够达到“国家认同”的效果。当然,这需要我们努力尽快地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公民教育体系,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二)共同的经济利益与平等的分配制度:构建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
共同的经济利益是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而经济基础决定政治发展,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不好,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那么不但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将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和制约,而且就连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现实是,因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储备等在各个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分布差异,这就使国家内部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所以,地区利益分化以及基于此而产生的民族利益分化问题,是现代国家建构国家认同过程中必须应对的问题。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悬殊,或各个民族存在着独立的经济体系,彼此之间缺乏相互物质依赖感和经济交往,那么,该国家要赢得其治理下的民众的合法性支持就将会变得无法想象。而社会成员国家认同意识的强弱“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共同体利益的关注程度,取决于他们共同需求的强度及与环境的关系。只有那些被他们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东西,才能将他们紧密团结以抵御那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分解力量的影响”。
……
用户评价
这本书给我的直观感受是“复杂”与“深刻”的完美结合。它并非一本轻松愉快的读物,更像是一场智力上的马拉松。作者在处理巴尔虎蒙古人的身份议题时,并没有将“认同”塑造成一个单一、线性的产物,而是将其描绘成一个由历史偶然性、社会结构制约和个体能动性共同编织的复杂挂毯。我尤其被它对边缘群体内部异质性的关注所打动,它拒绝将任何一个群体简单地标签化或同质化,而是深入到不同的代际、不同的地域分支中去考察身份认同的细微差异。这种对“微观世界”的精细描绘,使得宏大的理论探讨拥有了坚实的落地基础。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地在思考: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文化快速同质化的时代,像巴尔虎蒙古人这样的群体是如何在保持其核心文化特质的同时,应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巨大压力和诱惑的?这本书没有提供轻松的答案,但它无疑提供了最专业、最值得信赖的思考工具。
评分我花了好一番功夫才啃完这本书,坦白说,阅读体验并不轻松,但绝对是物有所值的精神投资。作者在探讨巴尔虎蒙古人这个特定群体时,展现出一种近乎手术刀般的精确性,将他们的身份认同置于一个宏大的地缘政治背景下进行审视。其中关于“国家认同”是如何被驯化和重塑的论述,尤其让我印象深刻。它不是那种高屋建瓴的理论说教,而是通过具体的个案和他们日常的挣扎来展现的。我感觉作者很擅长捕捉那些微妙的情感波动,比如在两种看似冲突的归属感之间徘徊时的那种焦虑和坚韧。这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独特,时而像慢镜头般细致描摹文化细节,时而又像纪录片般快速推进历史进程,这种张弛有度的处理,使得原本枯燥的学术讨论变得鲜活起来。它让我意识到,身份认同从来不是静止的DNA,而是一个需要不断协商、不断被重新定义的动态过程,尤其是在快速现代化的今天。
评分这本书的版式和装帧给我一种沉甸甸的学术感,但内容本身却展现出一种锐利的洞察力。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对“认同选择”这一主题的深入挖掘,这不仅仅是民族(ethnic)和国家(national)二元对立的简单讨论,而是探索了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广阔的灰色地带,以及个人如何在这个地带中进行主观能动的构建。我个人非常欣赏作者没有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来评判这个群体的选择,而是努力去理解他们的内在逻辑和外部压力。那种对文化符号和仪式如何被用来巩固或解构身份的分析,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范例。读完之后,我对于“文化适应”和“文化抵抗”这两个概念有了全新的理解,它们不再是简单的反义词,而更像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身份张力的核心。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框架,帮助我们理解那些在全球化浪潮中努力锚定自身位置的族群。
评分坦率讲,这本书的学术性非常强,里面的术语和理论框架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社会学或人类学基础才能完全领会其精髓。但是,即使是带着初学者心态去阅读,也能从中汲取到巨大的营养。我特别关注的是作者如何处理“跨国”这个维度,它意味着超越了传统国界的视野,将同一族群在不同政治实体下的命运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这种视野的拓展,极大地拓宽了我对民族志研究的想象空间。它不再局限于一国之内对某一族群的描摹,而是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流变之中。书中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引用和阐释,都显得极为审慎和全面,仿佛作者在每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都停下来,反复权衡各方力量的平衡。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它不仅记录了一个群体的历史,更是在理论上对“身份边界”这一概念进行了有力的挑战和重构。它就像一把尺子,让我们重新校准衡量民族与国家关系的刻度。
评分这本书的书名实在有些绕口,初次看到的时候,感觉像是在啃一块难以下咽的硬骨头。不过,真正翻开之后,才发现它其实在努力搭建一座理解复杂身份认同的桥梁。作者似乎下足了功夫去梳理那些盘根错节的文化脉络和政治现实。我特别留意到它对“跨国民族”这个概念的处理,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它要求我们跳出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去看待流动的人群和认同的变迁。读到一些关于历史记忆和当下经验如何相互作用的部分,我感到那种深层的拉扯——如何在保留本色与融入主流之间寻找平衡点。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扎实,似乎每一句话后面都压着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考据,读起来虽然需要集中精神,但那种抽丝剥茧的分析过程,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跟随作者的思绪深入下去。它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更多的是提出更深刻的问题,迫使读者去反思我们习以为常的“我们”与“他们”的界限到底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对于任何一个对少数族群研究或者身份政治感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的视角是极具启发性的,它挑战了太多预设的思维定式。
评分贊贊贊贊贊
评分后来,巴尔虎蒙古人随着不断迁徙,分散到贝加尔湖的东部和南部。清康熙年间,有一部分巴尔虎蒙古人被编入八旗,驻牧在大兴安岭以东布特哈广大地区,还有一部分成为喀尔喀蒙古(今蒙古)诸部的属部。
评分贊贊贊贊贊
评分“陈”“新”由来
评分人名说
评分真的不错 是好书 还会来京东的 物流好 发货快 而且是正版的
评分巴尔虎是蒙古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早在蒙古各部统一之前,巴尔虎的各种古称就已屡见经传了。《隋书》称之为“拔野固”,《新唐书》和《旧唐书》等,称为“拔野古”和“拔也古”等。《元史》、《蒙古秘史》和《史集》等,称之为“八儿浑”、“八儿忽”和“巴尔忽惕”等。巴尔虎在明代及北元时被称为“巴尔户”、“巴尔古”、“巴儿勿”、“把儿护”、“巴尔郭”等。清代的各种史料称之为“巴尔虎”,并相沿至今。巴尔虎在清初的各种汉文史料中,亦曾被称为“巴儿呼”、“巴尔忽”等。自1734年(雍正十二年)成立“新巴尔虎八旗”以来,“巴尔虎”一词才作为一个规范性的固定称呼延续下来。[1]
评分真的不错 是好书 还会来京东的 物流好 发货快 而且是正版的
评分很不错的书,值得珍藏,偶尔看看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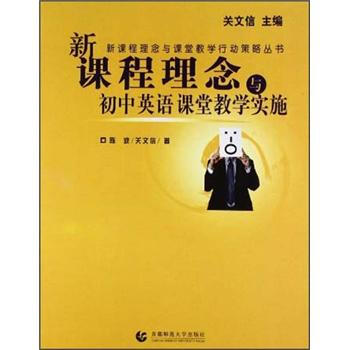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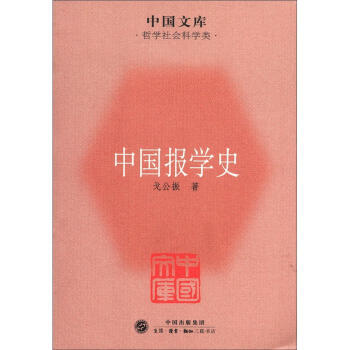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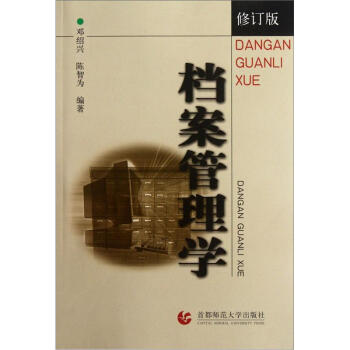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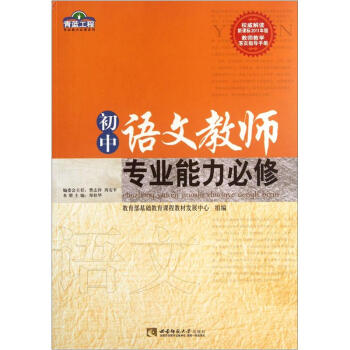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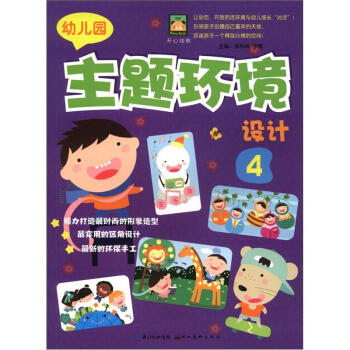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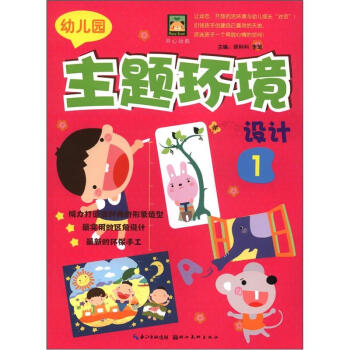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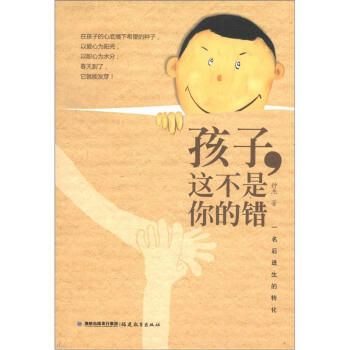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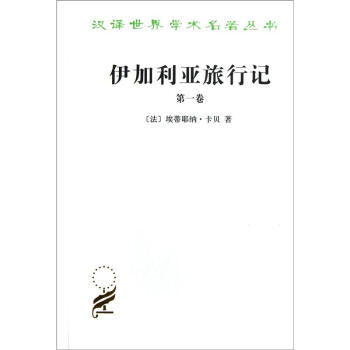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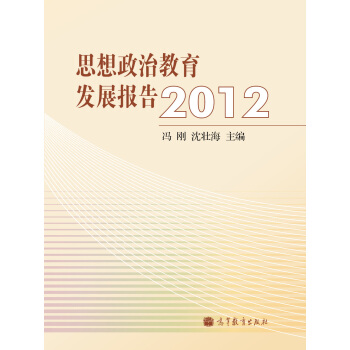
![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电视现场制作与报道(第5版) [Television Field Production and Reporting (5th Editi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55312/rBEGDFDqV1sIAAAAAAjGTEFNS3YAABPLgDOG_UACMZk7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