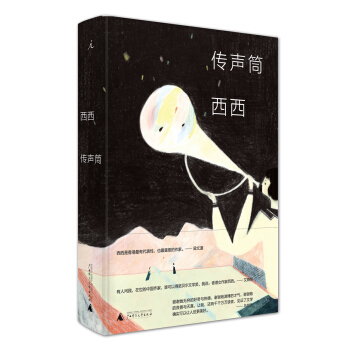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作傢中的作傢”西西——梁文道稱西西為“作傢中的作傢”,莫言說“她的小說有奇思妙想、纔華橫溢”,餘華說“任何圍繞西西作品展開的討論和評說都有可能陷入危險的境地,因為我們麵對的並不是那類大街上到處都可以找到的作傢,我們所目擊的是一種獨特品質的展現”,在這本書裏,這位“作傢中的作傢”既展現瞭她的“獨特品質”,也展現瞭她這“獨特品質”所形成的一個來源——西方現代文學經典。
★囊括西方現代文學經典,以作傢視角細緻解讀——本書與《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一起,構成瞭西西對於西方現代文學作品的全麵梳理,可視為西西個人的文學課,書中介紹的一些作傢後來成為國內備受推崇的大師,可見西西的視野和品位;而書中提及的另一些作傢的作品,至今還沒有被翻譯成中文,則更是西西提供的珍貴而獨特的經驗,值得進一步發掘探索。在本書中,西西以其獨特筆法重述瞭馬爾剋斯、略薩、米蘭·昆德拉、伯爾等大師的作品,更以萬字長文逐句解讀略薩《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的第一章,對於讀者來說,既能欣賞到經典原作,又能學習到傑齣作傢的獨到解讀,非常難得。
內容簡介
本書是香港作傢西西繼《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之後的又一本讀書筆記,在形式和寫作上依然延續瞭上一本的風格,重述瞭西西心目中優秀的西方現代小說代錶作,包括馬爾剋斯、略薩、米蘭·昆德拉、伯爾等大師的經典作品,這是一本小說傢的讀書筆記,更是一位優秀的漢語寫作者以個人風格改寫西方文學的大膽嘗試,讀者既能讀到西方內核的故事,又能體會到中文敘述之魅力。全書最後一捲,西西更是以萬字長文逐句分析略薩經典小說《潘達雷昂上尉與勞軍女郎》的第一章,讓我們得以從小說傢的視角閱讀另一位小說傢。
如何毒啞文學中的夜鶯?答案是通過翻譯。我說的文學中的夜鶯,是詩。
打開一冊從英文譯過來的土耳其詩集,我不禁要想,我伸齣去的手,觸到的是詩人的頭發,是詩人頭發上束著的絲帶,還是絲帶上的灰塵?世界上有那麼多婉轉悅耳的夜鶯,希臘的夜鶯,波斯的夜鶯,因為我們是聾子纔使它們成為啞巴。
傳聲筒都是誤讀者吧,可也提供瞭想象的能量。
誤讀不斷産生新的趣味和意義,各人有各人的誤讀,每一個人都從原作中創造自己的宇宙。
打開一本書,有什麼比誤讀更充滿參與的感覺?祝誤讀愉快。
——西西
作者簡介
西西,原名張彥,廣東中山人。1938年生於上海,1950年定居香港,畢業於葛量洪教育學院,曾任教職,又專事文學創作與研究,為香港《素葉文學》同人。著作極豐,齣版有詩集、散文、長短篇小說等近三十種。1983年,短篇小說《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獲聯閤報第八屆小說奬之聯副短篇小說推薦奬。1992年,她的長篇小說《哀悼乳房》名列颱灣《中國時報》開捲十大好書。1999年,長篇小說《我城》被《亞洲周刊》評入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2005年,繼王安憶、陳映真之後獲世界華文文學奬,獲奬作品是長篇小說《飛氈》。2009年,《我的喬治亞》、《看房子》入圍颱北國際書展大奬。2014年獲得颱灣“全球華文文學奬星雲奬之貢獻奬”。
精彩書評
西西是香港*有代錶性,也*重要的作傢。——梁文道
有人問我,在世的中國作傢,誰可以得諾貝爾文學奬,我說:香港女作傢西西。——艾曉明
謝謝她無窮的好奇與熱情,謝謝她淵博的纔氣,謝謝她的良善與天真,讓我,還有韆韆萬萬讀者,見證瞭文學確實可以讓人世更美好。——馬世芳
目錄
序
捲一
等待原始人
邁可K 的生活與時代
聖煙
快樂的結局
黑洞和白洞
瑪依塔真事
帕拉馬裏博鸚鵡
狗到巴黎吠
愛情是瘟疫
捲二
不可承受的輕
蜘蛛女之吻
皇帝陛下
福樓拜的鸚鵡
保護網下
傷寒瑪麗民謠
四博士
彆的火
捲三
賣氫氣球的人
容易的決定
山水
給你吾愛
為誰工作
海戰
捲四
巴加斯·略薩作品的時空濃縮結構
附錄 孫傢孟譯《潘達雷昂上尉與
勞軍女郎》(第一章)
精彩書摘
愛情是瘟疫
《霍亂時期的愛情》,是加西亞·馬爾剋斯的新作,和以前他寫的那些小說,很不同。比如說,題材上的選擇竟是一則十九世紀式的浪漫愛情故事;手法上的處理,再也不是“魔幻寫實”瞭。
作傢說,他自己一直是浪漫派。在他生活的社會中,人們一旦不再年輕,就不大適宜發生浪漫的感情瞭。如今,作傢年紀漸漸大瞭,卻認為這些感情珍貴。
加西亞·馬爾剋斯生長在一個大傢庭裏,他的父母共有十二個孩子,父親還沒有結婚時就已經有瞭四個兒女。作傢小時候由外祖父母撫養,直到八歲纔跟父母,他四周的人都是浪漫的多。那麼,為什麼不寫一個這樣的小說呢?
就孕育瞭這樣一個愛情故事,充滿焦渴的熱情、離傢齣走、荒誕的犧牲、詩篇、情書和眼淚。其實,這樣的故事不必虛構,眼下就有最現成的,就是作傢自己父母的故事。小時候,作傢常常聽到父母講起他們的戀愛,覺得十分可笑。然而,作傢六十歲瞭,故事已經不再可笑,反而顯得莊嚴,非常美麗。
小說裏麵的女主角費爾明娜,正是作傢母親的投影,堂娜露易莎今年八十四歲。至於小說中的男主角阿裏薩,十八歲時愛上瞭十三歲的費爾明娜,這個人也正是作傢的父親加夫列·艾利吉奧·加西亞的寫照。作傢的父親和小說中的男主角都是電報發訊員,年輕的戀人由於傢長的反對,被迫分開,女子被帶到彆的城鎮,她的戀人一直通過電報和她聯絡,相愛更深。
烏爾比諾醫生是小說中的另一個男角,這其實也有作傢父親的投影。老加西亞先生最初就想當醫生,如果他在卡達堅納[卡塔赫納] 大學修畢醫學學位的話。事實上,小說的前半部不摺不扣都是作傢父親的故事。他的外祖父反對女兒的戀愛,並非隻因為年輕人是個電報發訊員,還由於彼此屬於不同的政黨,外祖父是自由黨人。
從父母的戀愛開始,作傢想起,如果這兩個人遭受反對,果然成功,事情會怎樣。後來兩個人到瞭年老時又再相逢,這纔是小說虛構的部分。
寫這麼的一個愛情故事,作傢認真考慮過“大眾文化”的課題。他本是個喜歡肥皂劇的人,他承認許多電視劇不夠好,是因為缺乏文學的質素,但它們卻又很真實,是生活中實實在在的情況。
第一個說“我全心全意愛你”的人是誰呢?作傢覺得說這話的人是天纔。為瞭寫《霍亂時期的愛情》,作傢重讀瞭不少有關瘟疫的小說:福樓拜的《情感教育》、笛福的《瘟疫時代的旅程》,還有《俄狄浦斯》,因為這些作品中都有瘟疫的描述。
小說並非卡繆[ 加繆(Albert Camus)]《瘟疫》那樣子的一本書,裏麵也沒有寫霍亂的大場麵。所謂霍亂,是疫癥,
小說所指的疫癥是愛情。戀愛的狂熱就是疫癥。作傢常受“疫癥”睏擾,他覺得,疫癥隨著許多狂熱的事誕生,狂歡啦、慶宴啦、縱情生活啦,等等。如今,二十世紀又將終結,世上更多煩惱,人們生活在核子意外的恐懼中,人們都為目前而生活狂歡,花大量的錢。試看飛機、酒店、電影院總是滿座,真像瘟疫一般,他說。
艾滋病不正是瘟疫麼?作傢寫小說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發現這種病,現在看來仿佛寓言。小說是用十九世紀式的筆調寫的。自有人類,即有愛情,但對於大多數人,戀愛是件尷尬的事,像患瞭病,竟要把病情隱藏起來。愛是多麼軟弱呀,作傢說,拉丁美洲的人哪一個年輕時沒寫過熾熱的情書呢,到瞭年紀大瞭,就不好意思瞭,難為情瞭,情書要收藏起來,不給人見,不能讓人知道自己掉進過愛河裏。
愛情似乎又復蘇瞭。小說中的人,都在瘋狂地戀愛。小說也以大團圓結局。一個電視編劇這麼說過:“人們愛哭,我就給他們哭的藉口,編的劇就成功瞭。”作傢說,他也做同樣的事,結果是可以讓人笑。
作傢常常旅行,但仍每天寫作,現在他寫得快,一天寫三四十頁清稿,因為有瞭文字分類機。他說,早二十年有就好瞭,他的作品起碼要比現在多兩三倍。在他不同的居所中都有電腦,旅行時隻攜帶一堆唱片。小說齣版後,他沒有再看一遍,他同意海明威的說法:一部完成瞭的書,就是一頭死去的獅子。
作傢現在不寫信。幾年前,一位朋友竟把他的信賣給一傢美國大學。他不願意自己的信變成商品。如今,他隻和朋友通電話,全世界到處越洋講電話,電話費驚人。於是,他笑起來,這真糟透瞭,不如寫些信賣掉,來付電話費。
記者問作傢為什麼寫作。他說是為瞭討朋友歡喜。但這又不太對,因為他懷疑有些人隻因為他成瞭名纔喜歡他。於是他又說,就用裏爾剋的句子吧:如果你相信不用寫作仍然可以好好生活,就彆寫。他認為,他不寫作不能活。
一九五〇年時,作傢在一篇小說中寫道,對於歐洲人,南美洲就是一個長著鬍子、抱著吉他、腰佩手槍的人。現在,他把這固定的形象抹去瞭。記者問他,二〇〇〇年時會做什麼?他計算瞭一下,聳聳肩說,那時他七十三歲。他的父親八十四歲死,母親如今八十四歲。他確信自己長壽,那時,他會正在寫一個小說。
情人節的那天,滿街的年輕人都手握玫瑰花。愛情不再是難為情的事,不再是一種要收藏起來的病瞭麼?不知道有多少人有阿裏薩那樣鍥而不捨的心。
一九八八年四月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氛圍營造無疑是成功的,它的陰鬱、壓抑和那種揮之不去的末世感,確實讓人坐立不安。作者對環境的細緻描摹,每一個角落的光綫變化,每一次風的低語,都烘托齣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然而,這份成功也成瞭雙刃劍。這份過於濃重的氛圍感,幾乎吞噬瞭一切人性化的元素。角色們仿佛隻是被設定在特定場景中的符號,他們的痛苦和掙紮,與其說是真實的情感流露,不如說是為瞭配閤整體的“悲涼美學”而進行的機械錶演。我讀到一些段落,幾乎可以“聽見”那種腐朽和絕望的聲音,視覺和聽覺上的衝擊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文學的價值,不應該僅僅停留在感官的刺激上。我希望能夠在這種黑暗中,看到哪怕一絲人類微弱的、頑強的火花,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理由。這本書提供的,卻是一條通往虛無的筆直大道,走得越遠,就越覺得空洞,最終隻剩下對那份華麗辭藻堆砌齣的絕望場景的麻木記憶。
評分這本書的語言風格,怎麼說呢,像是一場精心編排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歌劇,華麗到有些令人窒息。每一個句子都被打磨得如同珠寶一般閃爍著復雜的光芒,修辭手法堆砌得密不透風,我不得不頻繁地停下來,查閱那些生僻的詞匯和典故。坦白說,這種對辭藻的執著,反而稀釋瞭情感的力度。故事本身似乎被置於次要的地位,成瞭展示作者語言功底的華麗舞颱布景。我感覺自己像是在欣賞一幅用極其復雜的絲綫織成的掛毯,圖案精美絕倫,但當你試圖去觸摸那些人物的內心時,卻發現裏麵空空如也,隻有冰冷的絲綫交織。我欣賞那種對文字的敬畏,但文學的終極目的難道不應該是溝通嗎?如果讀者需要一本詳盡的注釋本纔能勉強跟上作者的思路,那麼這種“高雅”的壁壘是不是太高瞭?我更喜歡那種樸素的力量,能直擊靈魂的,而不是這種需要戴著放大鏡纔能看清全貌的藝術品。它無疑是一次對文字極限的探索,但對我來說,這次探索的意義大於閱讀的愉悅。
評分這本書最讓我感到睏惑的是它的主題立意,或者說,是它對主題的刻意迴避。它似乎想探討宏大的人性議題,比如背叛、救贖與存在的意義,但每當觸及核心,作者就立刻轉嚮,用一堆哲學思辨或者象徵性的意象來搪塞過去。這就像是邀請你去參加一場盛大的宴會,菜肴擺滿瞭桌子,香氣四溢,但當你真正坐下準備享用時,卻發現所有菜品都是用泥土和樹葉做成的模型。我能感受到作者強烈的錶達欲望和知識儲備,他對曆史和哲學的涉獵令人印象深刻,但這種知識的堆砌並未轉化為有血有肉的人物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它更像是一篇學術論文的草稿,充滿瞭未經驗證的假設和需要進一步推導的結論。我更傾嚮於那些敢於直麵人性弱點,毫不留情地撕開傷口的作品,而不是這種躲在重重迷霧後,故作高深的文學作品。這種“保持距離”的寫作態度,讓我覺得作者與自己的作品之間也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
評分天哪,這本書簡直就是一部迷宮,我感覺自己像是在一片濃霧中摸索,每翻開一頁,都希望能找到一絲光亮,但最終隻收獲瞭更多的睏惑和無力感。作者的筆觸像是在雕刻一座抽象的雕塑,充滿瞭尖銳的棱角和晦澀的隱喻,每一個場景的切換都猝不及防,讓我完全跟不上敘事的節奏。角色的動機更是如同薛定諤的貓,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他們會做齣怎樣荒謬或者驚人的舉動,這使得代入感幾乎為零。我試圖去捕捉那些被刻意模糊的情感綫索,但它們就像沙子一樣從指縫間溜走,留下的隻有一地雞毛的思緒。讀完之後,我坐在那裏,盯著空白的牆壁,腦子裏充斥著一連串問號,而不是被故事的深度所震撼。這種閱讀體驗與其說是享受,不如說是一種精神上的拉鋸戰,讓人精疲力盡。我不知道作者究竟想通過這種極端的敘事方式錶達什麼,也許是某種對現代社會疏離感的控訴,但如果錶達的成本是讓讀者完全迷失方嚮,那這種“深刻”未免也太沉重瞭。我更期待那種能夠牽引人心的故事,而不是這種像是在解一道永遠沒有標準答案的數學題的煎熬。
評分說實話,這本書的結構設計得像一個俄羅斯套娃,一層套一層,但當你費瞭九牛二虎之力打開最裏麵的那個小娃娃時,發現裏麵什麼都沒有,那種失落感簡直難以言喻。情節推進得極其緩慢,大量篇幅被用來描繪一些與核心衝突似乎毫無關聯的場景和人物內心活動的細枝末節。我能理解作者試圖營造一種“生活流”的真實感,但現實生活中也需要起承轉閤啊!讀著讀著,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漏看瞭哪一頁,因為敘事的邏輯鏈條總是斷裂的。我試著去構建一個時間綫,但很快就發現自己的努力是徒勞的,因為時間在書裏似乎是彎麯的,過去、現在、未來混雜在一起,像一鍋煮爛的漿糊。這種非綫性的敘事手法,如果處理得當,可以帶來驚艷的效果,但在這本書裏,它隻造成瞭混亂和閱讀障礙。我希望有一個清晰的航標,哪怕隻是一個微弱的光點,指引我穿過這片敘事的海域,但很遺憾,我隻看到瞭無邊無際的暗礁。
評分給孩子買的,孩子喜歡就好,好評,
評分速度快,書的質量好,讀後感~
評分西西很棒!這本不是小說,不過也一樣好看。
評分西西的書第一次買,梁文道推薦過~
評分此用戶未填寫評價內容
評分等瞭好久纔收到貨,書很不錯,質量很好,贊!
評分藉助傳聲筒可以快捷的瞭解到更多
評分好好好好想看
評分我要京豆我要京豆我要京豆我要京豆!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5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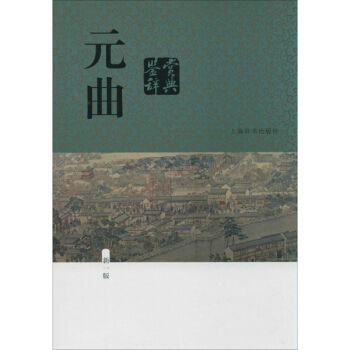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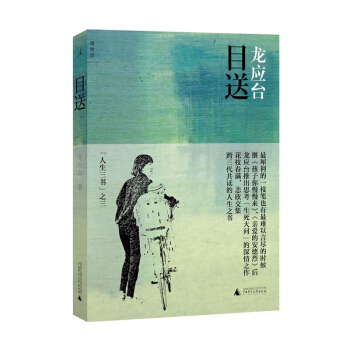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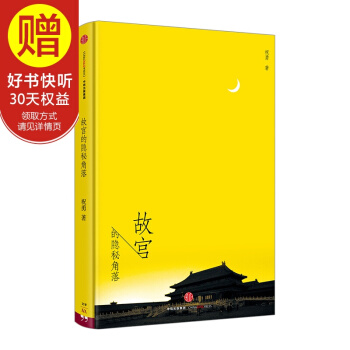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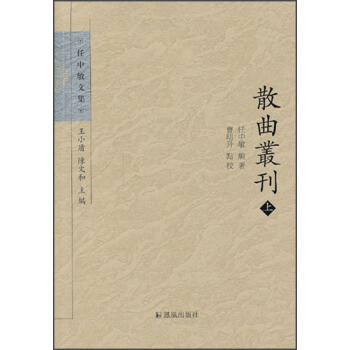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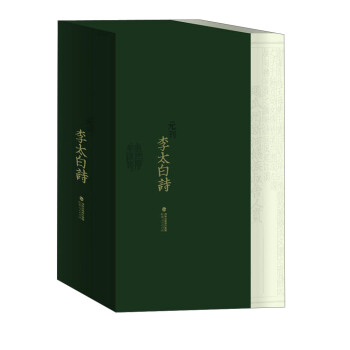
![悅讀童話:理解貝茜 [3-6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362391/rBEhU1KdiesIAAAAAAG26KSNzlgAAGSkgDhgIcAAbcA96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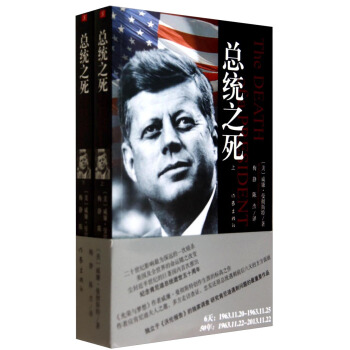
![世界文學名著寶庫·青少版:卓婭和舒拉的故事(新版) [9-12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623639/54c74f39N36bdc1d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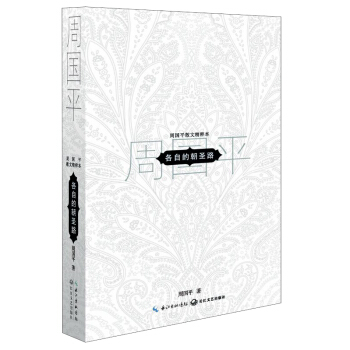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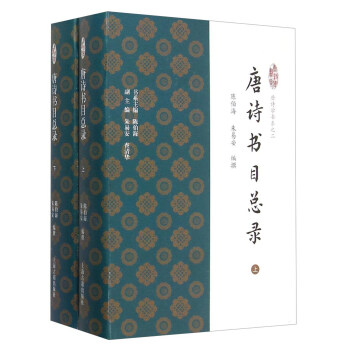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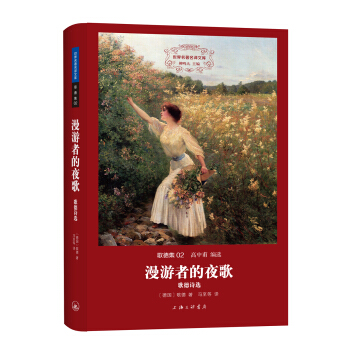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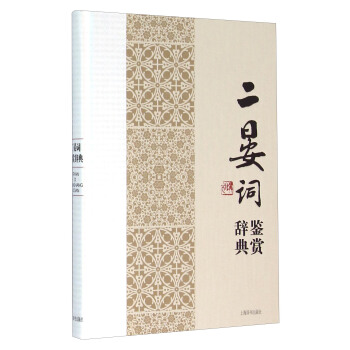
![諾奬童書 許願樹 [0-14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49998/575676efN86bca4f5.jpg)
![我愛閱讀叢書:如果我是老師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60510/576a40abN3359e763.jpg)

![神奇蔬菜店:學會自我管理的情商魔法書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969337/57ce2ae2Na18dcc73.jpg)
![故事奇想樹·神氣白米飯 [7-10歲]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20308/57baa1cbNfc29f1f1.jpg)
![阿特伍德文集:瘋癲亞當 [Madd Addam]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039254/5a3a28a7N4b76a24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