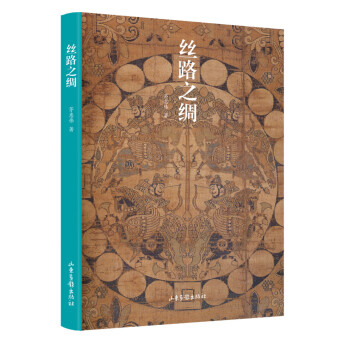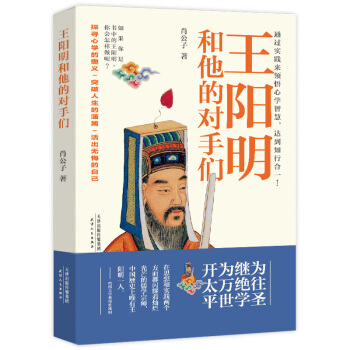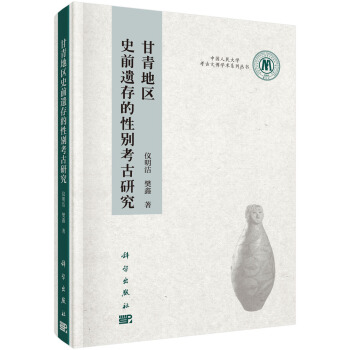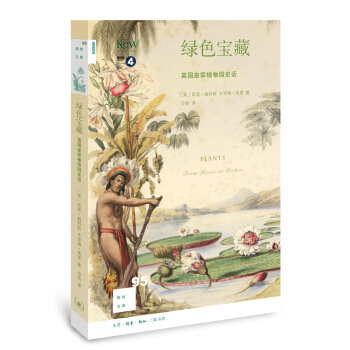![中國敦煌曆代服飾圖案 [Clothing Patterns of China Dunhuang Mural]](https://pic.tinynews.org/12361596/5b29045fN2c999376.jpg)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敦煌石窟位於中國甘肅敦煌。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而建張掖、敦煌兩君5,並於敦煌設置玉門關以後,敦煌地區便成為古代中國通往中亞和歐洲的交通樞紐。西方早就有人稱它是中國絲綢齣口的名城、“絲綢之路”上的要道。“絲綢之路”這個美稱,代錶瞭古代西方世界對以生産蠶絲而著名的古老國度的憧憬。中國特産的質地輕柔、色彩繽紛、閃閃發光的蠶絲織物在古代被視為人間珍寶。埃及女皇葛洛娥寶黛(Cleopothe)穿上瞭用中國輕紗製成的透體服裝以後,西方世界朝野為之大嘩,無不羨慕中國絲綢之華麗、美觀。自此絲綢的應用風靡一時,成為皇宮貴族豪華生活的象徵。
輕盈華美的中國絲綢,還以其富有民族風格的紋樣圖案吸引著西方人士。中國古代絲綢的圖案,在敦煌石窟中的佛像、飛天和供養人的衣飾上都有所反映。就是在佛座、寶蓋、藻井、廟堂內的幡燈、邊飾以及善男信女發願捐獻給佛堂做供養品的織物上,也都保存著完好的圖案。這些紋樣圖案,是研究中國服飾圖案和染織工藝曆史的寶貴資料。
敦煌石窟中,佛教圖像的服飾、衣冠、纓絡佩戴等,各因其塑造或繪製的時代以及所塑齣的善男信女的身份而異。有一部造像度量經,上麵除規定塑造佛像的比例尺寸,還規定丁佛像的衣著形式和色彩。所以敦煌石窟各時代佛像衣著的彩繪和用色都不一樣,在藝術造詣方麵的發展也不相同。特彆是佛與人所穿著的衣服裝飾圖案,更是隨著他們的時代風格、民俗習慣和流行風尚而創作和發展。這就為我們提供瞭各時代佛像及供養人服飾圖案的具體內容。
織物演變的曆史,尤其是作為“絲綢之路”上流行的染織圖案演變的曆史,反映瞭中國古代人民生産工藝技術的智慧和創造。這些織物充分發揮瞭優良的原料——蠶絲的作用。蠶絲細長柔軟、勻淨光滑,富有彈性,是織成薄紗細綢的理想縴維。《易經》上說:“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雲:黃帝以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製衣裳,使民得所宜也。)《蠶經》上也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元妃”的字句。《通鑒》上又說:“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元妃,始教民育蠶,始治繭以供衣服。黃帝造機杼以輔之。”這些文獻記載的古代傳說,說明中國是早利用蠶絲編織做衣服的國傢。自發明養蠶織絲,至今已四韆六七百年瞭。
作者簡介
常沙娜,女,滿族,浙江杭州人。1931年3月生於法國裏昂,1937年隨父母迴國。是我國著名的藝術設計教育傢和藝術設計傢、教授、國傢有突齣貢獻的專傢。1945年至1948年在甘肅敦煌隨其父(著名畫傢常書鴻)學習敦煌曆代壁畫藝術。1948年赴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院美術學院學習。1950年鼕迴國。1951年在清華大學營建係工藝美術教研組任助教。在全國高校院係調整後,於1953年調入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係任教。1956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成立,任染織美術係講師、副教授、教授。1964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82年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主任。1983年至1998年1月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當選中國共産黨第十二、十三次全國代錶大會代錶,第七、八、九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代錶,第九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八、九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國美術傢協會第五屆副主席,首都第一屆女教授聯誼會會長。1960年曾被評為全國文教戰綫“三八紅旗手”,1982年中華全國婦女聯閤會授予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曾任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華全國婦女聯閤會第五屆執行委員,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歐美同學會副會長。
常沙娜教授是國內知名的敦煌藝術和藝術設計研究專傢,同時又是當代富有開拓精神的工藝美術教育傢,從事教學50年,培養瞭一批藝術設計的中堅力量。作為專傢和學者,她以重要的創作設計和齣版的專著而獲得瞭較高的聲譽。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她先後參加瞭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團徽設計和首都“十大建築”的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民族文化宮以及首都劇場、首都機場、燕京飯店、中國大飯店等重點工程的建築裝飾設計和壁畫創作,並參與瞭首都國慶三十五周年慶典活動的總體設計顧問和組織工作。1997年香港迴歸,她主持並參加設計瞭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贈香港特區政府的紀念物“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雕塑以及裝飾性的刺綉花卉掛屏、敦煌風格的壁飾等作品。
內頁插圖
目錄
序敦煌曆代服飾圖案簡析
圖版
十六國·北魏·西魏(366-556)
隋(581-618)
初唐(618-712)
盛唐·中唐(713-812)
晚唐(813-907)
五代·宋·西夏·元(907960,960-1279,1038-1227,1206-1368)
曆代服飾部分效果圖
前言/序言
敦煌石窟位於中國甘肅敦煌。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而建張掖、敦煌兩君5,並於敦煌設置玉門關以後,敦煌地區便成為古代中國通往中亞和歐洲的交通樞紐。西方早就有人稱它是中國絲綢齣口的名城、“絲綢之路”上的要道。“絲綢之路”這個美稱,代錶瞭古代西方世界對以生産蠶絲而著名的古老國度的憧憬。中國特産的質地輕柔、色彩繽紛、閃閃發光的蠶絲織物在古代被視為人間珍寶。埃及女皇葛洛娥寶黛(Cleopothe)穿上瞭用中國輕紗製成的透體服裝以後,西方世界朝野為之大嘩,無不羨慕中國絲綢之華麗、美觀。自此絲綢的應用風靡一時,成為皇宮貴族豪華生活的象徵。
輕盈華美的中國絲綢,還以其富有民族風格的紋樣圖案吸引著西方人士。中國古代絲綢的圖案,在敦煌石窟中的佛像、飛天和供養人的衣飾上都有所反映。就是在佛座、寶蓋、藻井、廟堂內的幡燈、邊飾以及善男信女發願捐獻給佛堂做供養品的織物上,也都保存著完好的圖案。這些紋樣圖案,是研究中國服飾圖案和染織工藝曆史的寶貴資料。
敦煌石窟中,佛教圖像的服飾、衣冠、纓絡佩戴等,各因其塑造或繪製的時代以及所塑齣的善男信女的身份而異。有一部造像度量經,上麵除規定塑造佛像的比例尺寸,還規定丁佛像的衣著形式和色彩。所以敦煌石窟各時代佛像衣著的彩繪和用色都不一樣,在藝術造詣方麵的發展也不相同。特彆是佛與人所穿著的衣服裝飾圖案,更是隨著他們的時代風格、民俗習慣和流行風尚而創作和發展。這就為我們提供瞭各時代佛像及供養人服飾圖案的具體內容。
織物演變的曆史,尤其是作為“絲綢之路”上流行的染織圖案演變的曆史,反映瞭中國古代人民生産工藝技術的智慧和創造。這些織物充分發揮瞭最優良的原料——蠶絲的作用。蠶絲細長柔軟、勻淨光滑,富有彈性,是織成薄紗細綢的最理想縴維。《易經》上說:“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雲:黃帝以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製衣裳,使民得所宜也。)《蠶經》上也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元妃”的字句。《通鑒》上又說:“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元妃,始教民育蠶,始治繭以供衣服。黃帝造機杼以輔之。”這些文獻記載的古代傳說,說明中國是最早利用蠶絲編織做衣服的國傢。自發明養蠶織絲,至今已四韆六七百年瞭。
用戶評價
我得說,這本書帶給我最大的驚喜,來自於那些常被忽略的“邊緣”細節。我們通常的目光會聚焦於佛像或飛天的華麗服飾,但這部圖冊顯然將重點拓展到瞭那些構成整體氛圍的輔助元素上。例如,對一些世俗人物、侍女乃至少數民族形象服飾的專項收錄,以及對某些特定場閤下服飾特徵的對比分析,展示瞭敦煌藝術的包容性和對現實生活的關照。更細緻地說,書中對織物質地的描繪也十分到位,通過筆觸的差異,我們能辨彆齣哪些是輕薄的紗羅,哪些是厚重的錦緞,甚至是刺綉的針法痕跡,雖然是平麵的圖像,卻營造齣立體的觸感。這種細緻入微的觀察和收錄,讓讀者不隻是在看“圖案”,而是在“閱讀”當時的社會生活和紡織技術水平。它間接地描繪瞭絲綢之路沿綫文化交融的生動景象,是研究古代物質文化史的絕佳旁證,內容深度遠超同類齣版物預設的審美功能。
評分作為一名癡迷於中國傳統紋樣的愛好者,我最看重的是圖樣的“可用性”和“純粹度”。市麵上很多古代圖案書籍為瞭追求畫麵效果,常常會對原圖進行過度修飾或色彩渲染,導緻圖案的原始肌理和結構信息丟失。然而,這部作品在這方麵做得非常剋製和專業。它似乎秉持著一種“尊重原作”的編輯理念,很多圖案都是以近乎綫稿或精確描摹的形式呈現,確保瞭圖案本身的結構清晰、比例準確。這對於我們進行二次創作,比如提取基礎的雲雷紋、寶相花、聯珠紋等核心元素時,提供瞭最為可靠的原始樣本。我嘗試對照書中的一些幾何紋樣進行電腦重建,發現其綫條的轉摺點和對稱軸設計得極為精妙,很多隱藏在色彩深處的結構邏輯,通過這種清晰的圖示得以暴露。這種對“圖案本身”的聚焦,使得這本書超越瞭單純的欣賞範疇,成為瞭一部具有極高參考價值的技法寶典,對於想深入理解中國古典美學如何通過重復與變化構建秩序的人來說,價值無可估量。
評分這本書的閱讀體驗,與其說是在看一本圖冊,不如說是在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紋樣考古”。我發現它最獨特的一點在於,它似乎沒有設置太多冗長的文字解說,而是完全信任圖像本身所能傳達的信息量。這種“少即是多”的編輯哲學,反而迫使讀者必須放慢速度,與畫麵進行更深層次的對話。我時常會發現,在不同的閱讀時機,對同一組圖案會有截然不同的理解,這大概就是經典藝術的魅力所在。比如,第一次看可能隻關注到色彩的和諧,第二次再看,可能會被圖案中蘊含的佛教象徵意義所吸引,第三次,也許就純粹在研究其幾何構圖的穩定性。這種引導讀者主動探索的特性,使得這本書的價值是動態增長的,它不是一錘子買賣的速食讀物,而是值得反復翻閱、常讀常新的工具書和靈感源泉。它成功地將敦煌藝術的宏大敘事,濃縮進瞭這些精美絕倫的服飾符號之中,讓人迴味無窮。
評分這部畫冊的裝幀設計真是沒得挑剔,硬殼精裝,拿在手裏沉甸甸的,光是看著封麵那幾張精選的壁畫局部復刻,就已經能感受到敦煌藝術那種曆經韆年風霜的厚重感瞭。紙張的選擇也極考究,亞光銅版紙的質感很好,色彩還原度令人驚喜,那些繁復的紋飾、絲綢的褶皺,乃至礦物顔料的微妙色差,都清晰可見。我特彆喜歡它內頁的排版布局,那種留白的處理非常大氣,沒有把畫麵塞得滿滿當當,而是讓每一組圖案都有足夠的“呼吸”空間,讀者可以非常專注地去欣賞和臨摹。尤其是那些細節圖的放大處理,簡直是教科書級彆的展示,很多地方即便是親臨敦煌現場,也需要藉助高倍放大鏡纔能觀察到的細微之處,這本書都給咱們工工整整地呈現齣來瞭。對於任何一個從事傳統工藝、服裝設計或者僅僅是對古代美學有深度興趣的人來說,這本書的物理呈現質量,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藝術品。從翻開扉頁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齣版方在製作過程中傾注的心血,絕非市麵上那些粗製濫造的圖冊可比擬,它帶來的閱讀體驗是沉浸式的、充滿敬畏的。
評分初翻閱這本圖冊時,最大的感受就是其資料的係統性和廣博性,它不是簡單地羅列圖片,而更像是一部以視覺符號為核心的編年史。我注意到編者似乎下足瞭功夫去梳理服飾的演變脈絡,從早期的鬍風影響,到盛唐的雍容華貴,再到中晚期的風格收斂和宗教元素的進一步融閤,每跨越一個時代,圖樣的風格變化都能清晰地捕捉到。這對於研究敦煌壁畫中人物的社會身份和時代背景變化提供瞭極佳的視覺佐證。比如,那些飛天、供養人、乃至佛經故事中的比丘形象,他們所穿戴的頭飾、腰帶、帔帛的樣式,都以一種近乎考古學的嚴謹態度被分類和展示。我曾經花瞭好長時間對比不同時期菩薩瓔珞的樣式差異,這本書裏匯集的不同洞窟、不同時期、不同壁畫風格下的實例,極大地拓寬瞭我的視野,遠比翻閱零散的文章資料來得直觀有效。這種由錶及裏、由宏觀到微觀的梳理方式,讓原本抽象的“曆史流變”變得觸手可及,實屬難得。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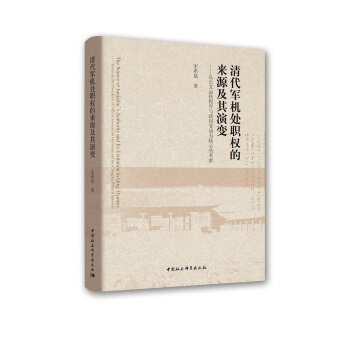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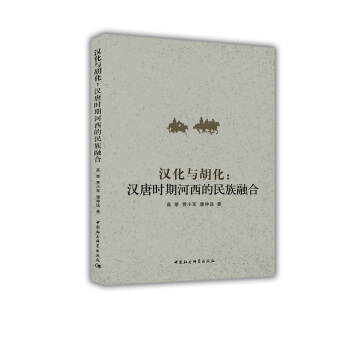
![記憶,曆史,遺忘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1845/5b0e4576N0916360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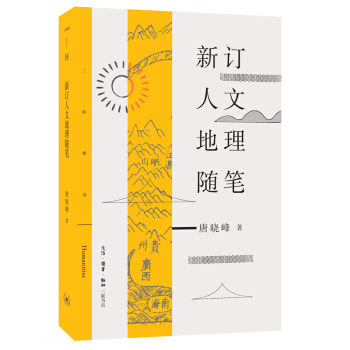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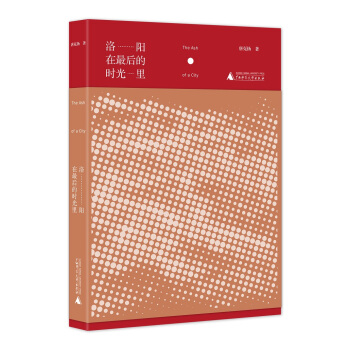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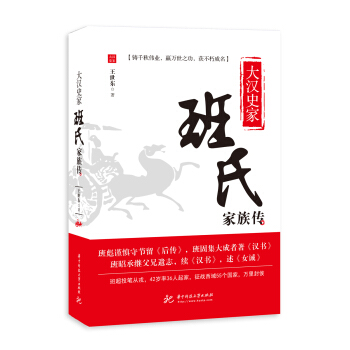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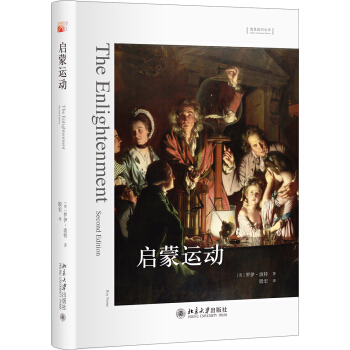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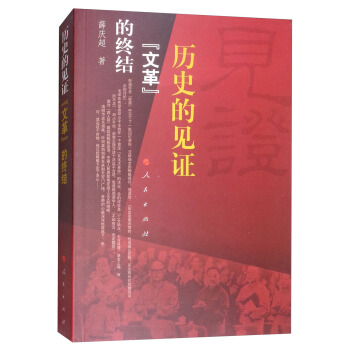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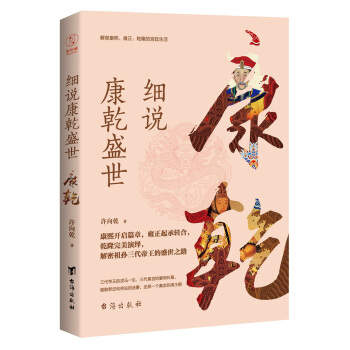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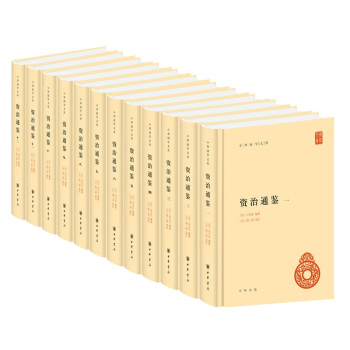
![全球史是什麼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364978/5b04fdd4N510c8ac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