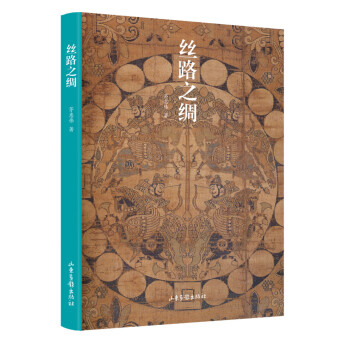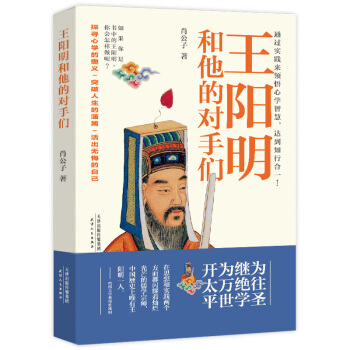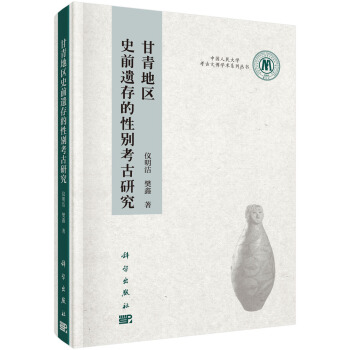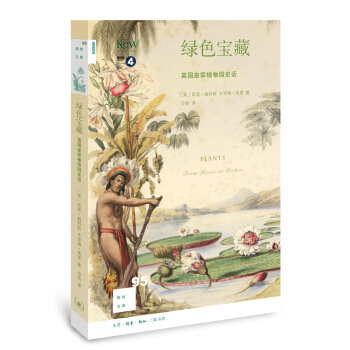![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 [Clothing Patterns of China Dunhuang Mural]](https://pic.tinynews.org/12361596/5b29045fN2c999376.jpg)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敦煌石窟位于中国甘肃敦煌。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而建张掖、敦煌两君5,并于敦煌设置玉门关以后,敦煌地区便成为古代中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交通枢纽。西方早就有人称它是中国丝绸出口的名城、“丝绸之路”上的要道。“丝绸之路”这个美称,代表了古代西方世界对以生产蚕丝而著名的古老国度的憧憬。中国特产的质地轻柔、色彩缤纷、闪闪发光的蚕丝织物在古代被视为人间珍宝。埃及女皇葛洛娥宝黛(Cleopothe)穿上了用中国轻纱制成的透体服装以后,西方世界朝野为之大哗,无不羡慕中国丝绸之华丽、美观。自此丝绸的应用风靡一时,成为皇宫贵族豪华生活的象征。
轻盈华美的中国丝绸,还以其富有民族风格的纹样图案吸引着西方人士。中国古代丝绸的图案,在敦煌石窟中的佛像、飞天和供养人的衣饰上都有所反映。就是在佛座、宝盖、藻井、庙堂内的幡灯、边饰以及善男信女发愿捐献给佛堂做供养品的织物上,也都保存着完好的图案。这些纹样图案,是研究中国服饰图案和染织工艺历史的宝贵资料。
敦煌石窟中,佛教图像的服饰、衣冠、缨络佩戴等,各因其塑造或绘制的时代以及所塑出的善男信女的身份而异。有一部造像度量经,上面除规定塑造佛像的比例尺寸,还规定丁佛像的衣着形式和色彩。所以敦煌石窟各时代佛像衣着的彩绘和用色都不一样,在艺术造诣方面的发展也不相同。特别是佛与人所穿着的衣服装饰图案,更是随着他们的时代风格、民俗习惯和流行风尚而创作和发展。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各时代佛像及供养人服饰图案的具体内容。
织物演变的历史,尤其是作为“丝绸之路”上流行的染织图案演变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生产工艺技术的智慧和创造。这些织物充分发挥了优良的原料——蚕丝的作用。蚕丝细长柔软、匀净光滑,富有弹性,是织成薄纱细绸的理想纤维。《易经》上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注云:黄帝以上,衣鸟兽之皮,其后人多兽少,事或穷乏,故以丝麻布帛而制衣裳,使民得所宜也。)《蚕经》上也有“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元妃”的字句。《通鉴》上又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元妃,始教民育蚕,始治茧以供衣服。黄帝造机杼以辅之。”这些文献记载的古代传说,说明中国是早利用蚕丝编织做衣服的国家。自发明养蚕织丝,至今已四千六七百年了。
作者简介
常沙娜,女,满族,浙江杭州人。1931年3月生于法国里昂,1937年随父母回国。是我国著名的艺术设计教育家和艺术设计家、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1945年至1948年在甘肃敦煌随其父(著名画家常书鸿)学习敦煌历代壁画艺术。1948年赴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学习。1950年冬回国。1951年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工艺美术教研组任助教。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于1953年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任染织美术系讲师、副教授、教授。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1983年至1998年1月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当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八、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副主席,首都第一届女教授联谊会会长。1960年曾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三八红旗手”,1982年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曾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五届执行委员,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常沙娜教授是国内知名的敦煌艺术和艺术设计研究专家,同时又是当代富有开拓精神的工艺美术教育家,从事教学50年,培养了一批艺术设计的中坚力量。作为专家和学者,她以重要的创作设计和出版的专著而获得了较高的声誉。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她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和首都“十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民族文化宫以及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中国大饭店等重点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并参与了首都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活动的总体设计顾问和组织工作。1997年香港回归,她主持并参加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赠香港特区政府的纪念物“永远盛开的紫荆花”雕塑以及装饰性的刺绣花卉挂屏、敦煌风格的壁饰等作品。
内页插图
目录
序敦煌历代服饰图案简析
图版
十六国·北魏·西魏(366-556)
隋(581-618)
初唐(618-712)
盛唐·中唐(713-812)
晚唐(813-907)
五代·宋·西夏·元(907960,960-1279,1038-1227,1206-1368)
历代服饰部分效果图
前言/序言
敦煌石窟位于中国甘肃敦煌。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而建张掖、敦煌两君5,并于敦煌设置玉门关以后,敦煌地区便成为古代中国通往中亚和欧洲的交通枢纽。西方早就有人称它是中国丝绸出口的名城、“丝绸之路”上的要道。“丝绸之路”这个美称,代表了古代西方世界对以生产蚕丝而著名的古老国度的憧憬。中国特产的质地轻柔、色彩缤纷、闪闪发光的蚕丝织物在古代被视为人间珍宝。埃及女皇葛洛娥宝黛(Cleopothe)穿上了用中国轻纱制成的透体服装以后,西方世界朝野为之大哗,无不羡慕中国丝绸之华丽、美观。自此丝绸的应用风靡一时,成为皇宫贵族豪华生活的象征。
轻盈华美的中国丝绸,还以其富有民族风格的纹样图案吸引着西方人士。中国古代丝绸的图案,在敦煌石窟中的佛像、飞天和供养人的衣饰上都有所反映。就是在佛座、宝盖、藻井、庙堂内的幡灯、边饰以及善男信女发愿捐献给佛堂做供养品的织物上,也都保存着完好的图案。这些纹样图案,是研究中国服饰图案和染织工艺历史的宝贵资料。
敦煌石窟中,佛教图像的服饰、衣冠、缨络佩戴等,各因其塑造或绘制的时代以及所塑出的善男信女的身份而异。有一部造像度量经,上面除规定塑造佛像的比例尺寸,还规定丁佛像的衣着形式和色彩。所以敦煌石窟各时代佛像衣着的彩绘和用色都不一样,在艺术造诣方面的发展也不相同。特别是佛与人所穿着的衣服装饰图案,更是随着他们的时代风格、民俗习惯和流行风尚而创作和发展。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各时代佛像及供养人服饰图案的具体内容。
织物演变的历史,尤其是作为“丝绸之路”上流行的染织图案演变的历史,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生产工艺技术的智慧和创造。这些织物充分发挥了最优良的原料——蚕丝的作用。蚕丝细长柔软、匀净光滑,富有弹性,是织成薄纱细绸的最理想纤维。《易经》上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注云:黄帝以上,衣鸟兽之皮,其后人多兽少,事或穷乏,故以丝麻布帛而制衣裳,使民得所宜也。)《蚕经》上也有“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元妃”的字句。《通鉴》上又说:“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元妃,始教民育蚕,始治茧以供衣服。黄帝造机杼以辅之。”这些文献记载的古代传说,说明中国是最早利用蚕丝编织做衣服的国家。自发明养蚕织丝,至今已四千六七百年了。
用户评价
这部画册的装帧设计真是没得挑剔,硬壳精装,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光是看着封面那几张精选的壁画局部复刻,就已经能感受到敦煌艺术那种历经千年风霜的厚重感了。纸张的选择也极考究,亚光铜版纸的质感很好,色彩还原度令人惊喜,那些繁复的纹饰、丝绸的褶皱,乃至矿物颜料的微妙色差,都清晰可见。我特别喜欢它内页的排版布局,那种留白的处理非常大气,没有把画面塞得满满当当,而是让每一组图案都有足够的“呼吸”空间,读者可以非常专注地去欣赏和临摹。尤其是那些细节图的放大处理,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展示,很多地方即便是亲临敦煌现场,也需要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观察到的细微之处,这本书都给咱们工工整整地呈现出来了。对于任何一个从事传统工艺、服装设计或者仅仅是对古代美学有深度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的物理呈现质量,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从翻开扉页的那一刻起,就能感受到出版方在制作过程中倾注的心血,绝非市面上那些粗制滥造的图册可比拟,它带来的阅读体验是沉浸式的、充满敬畏的。
评分初翻阅这本图册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其资料的系统性和广博性,它不是简单地罗列图片,而更像是一部以视觉符号为核心的编年史。我注意到编者似乎下足了功夫去梳理服饰的演变脉络,从早期的胡风影响,到盛唐的雍容华贵,再到中晚期的风格收敛和宗教元素的进一步融合,每跨越一个时代,图样的风格变化都能清晰地捕捉到。这对于研究敦煌壁画中人物的社会身份和时代背景变化提供了极佳的视觉佐证。比如,那些飞天、供养人、乃至佛经故事中的比丘形象,他们所穿戴的头饰、腰带、帔帛的样式,都以一种近乎考古学的严谨态度被分类和展示。我曾经花了好长时间对比不同时期菩萨璎珞的样式差异,这本书里汇集的不同洞窟、不同时期、不同壁画风格下的实例,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远比翻阅零散的文章资料来得直观有效。这种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的梳理方式,让原本抽象的“历史流变”变得触手可及,实属难得。
评分我得说,这本书带给我最大的惊喜,来自于那些常被忽略的“边缘”细节。我们通常的目光会聚焦于佛像或飞天的华丽服饰,但这部图册显然将重点拓展到了那些构成整体氛围的辅助元素上。例如,对一些世俗人物、侍女乃至少数民族形象服饰的专项收录,以及对某些特定场合下服饰特征的对比分析,展示了敦煌艺术的包容性和对现实生活的关照。更细致地说,书中对织物质地的描绘也十分到位,通过笔触的差异,我们能辨别出哪些是轻薄的纱罗,哪些是厚重的锦缎,甚至是刺绣的针法痕迹,虽然是平面的图像,却营造出立体的触感。这种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收录,让读者不只是在看“图案”,而是在“阅读”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纺织技术水平。它间接地描绘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交融的生动景象,是研究古代物质文化史的绝佳旁证,内容深度远超同类出版物预设的审美功能。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在看一本图册,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纹样考古”。我发现它最独特的一点在于,它似乎没有设置太多冗长的文字解说,而是完全信任图像本身所能传达的信息量。这种“少即是多”的编辑哲学,反而迫使读者必须放慢速度,与画面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我时常会发现,在不同的阅读时机,对同一组图案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这大概就是经典艺术的魅力所在。比如,第一次看可能只关注到色彩的和谐,第二次再看,可能会被图案中蕴含的佛教象征意义所吸引,第三次,也许就纯粹在研究其几何构图的稳定性。这种引导读者主动探索的特性,使得这本书的价值是动态增长的,它不是一锤子买卖的速食读物,而是值得反复翻阅、常读常新的工具书和灵感源泉。它成功地将敦煌艺术的宏大叙事,浓缩进了这些精美绝伦的服饰符号之中,让人回味无穷。
评分作为一名痴迷于中国传统纹样的爱好者,我最看重的是图样的“可用性”和“纯粹度”。市面上很多古代图案书籍为了追求画面效果,常常会对原图进行过度修饰或色彩渲染,导致图案的原始肌理和结构信息丢失。然而,这部作品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克制和专业。它似乎秉持着一种“尊重原作”的编辑理念,很多图案都是以近乎线稿或精确描摹的形式呈现,确保了图案本身的结构清晰、比例准确。这对于我们进行二次创作,比如提取基础的云雷纹、宝相花、联珠纹等核心元素时,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原始样本。我尝试对照书中的一些几何纹样进行电脑重建,发现其线条的转折点和对称轴设计得极为精妙,很多隐藏在色彩深处的结构逻辑,通过这种清晰的图示得以暴露。这种对“图案本身”的聚焦,使得这本书超越了单纯的欣赏范畴,成为了一部具有极高参考价值的技法宝典,对于想深入理解中国古典美学如何通过重复与变化构建秩序的人来说,价值无可估量。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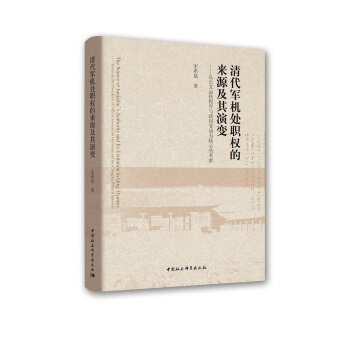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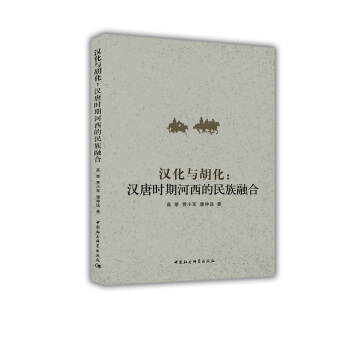
![记忆,历史,遗忘 [La Mémoire, l'Histoire, l'Oubli ]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61845/5b0e4576N0916360a.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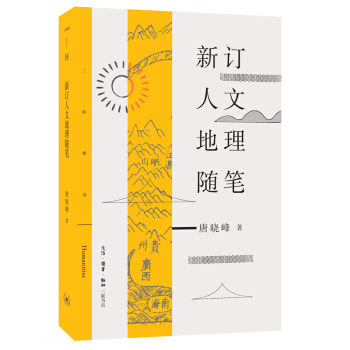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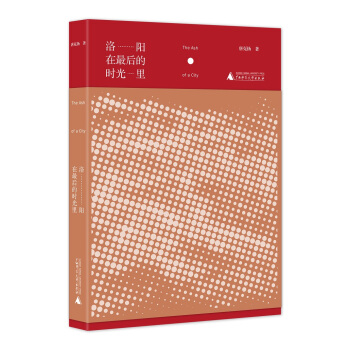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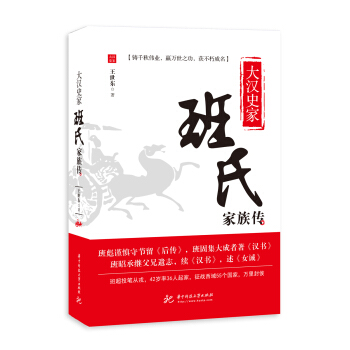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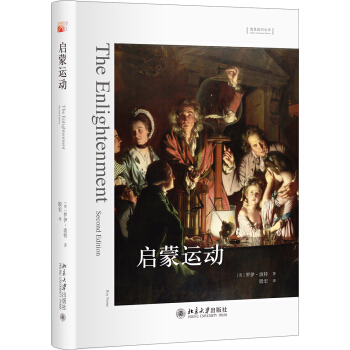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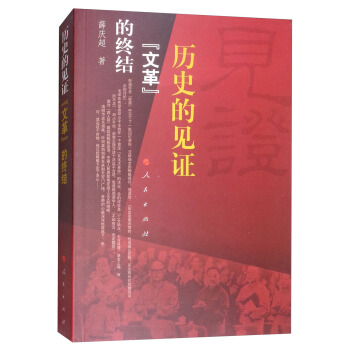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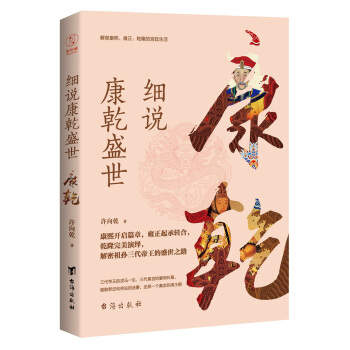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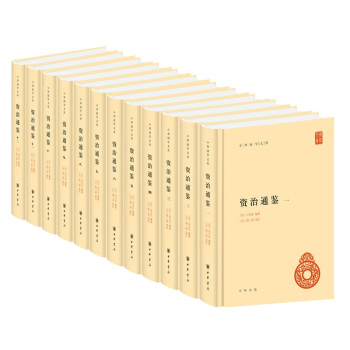
![全球史是什么 [What is Global History?]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64978/5b04fdd4N510c8ac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