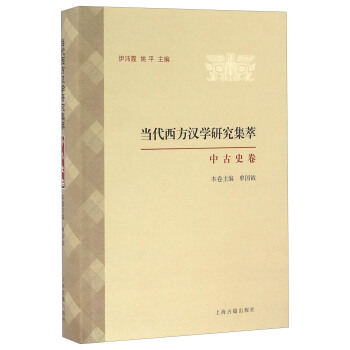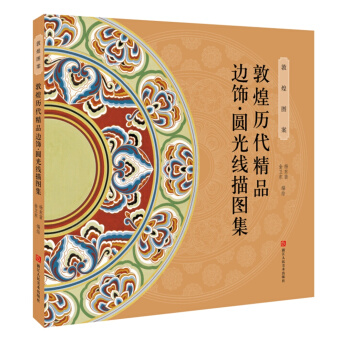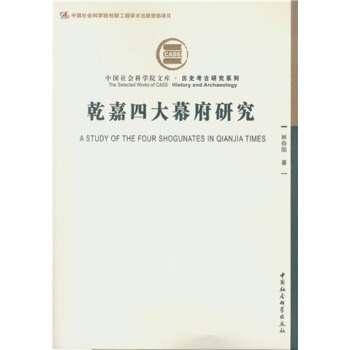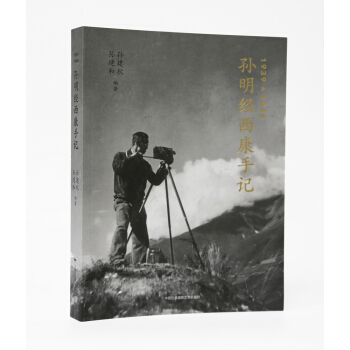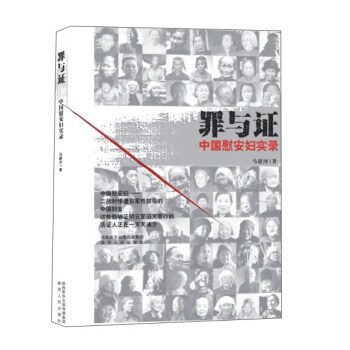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2015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長達15年的侵華戰爭中,日軍強行擄奪中國的良傢婦女充當性奴隸——慰安婦(除極少數是中國的妓女外)至少20萬人。北至中蘇邊境南到海南島,隻要是日軍戰區,慰安所就無處不在。她們不分晝夜地遭受日軍蹂躪,每天接待二三十人,其狀慘苦。更讓人難以置信的是,身患重病時,日軍竟將她們拉到外麵做練習刺刀的耙子。時至今日,日本政府和天皇僅對韓國、新加坡等東南亞儲國婦女充當慰安婦一事錶示瞭謝罪和賠償意願,唯獨對中國慰安婦的問題錶現齣迴避和沉默態度,而中國一位慰安婦控告日本政府始自1992年。
活著的老人都不同程度地錶示一定要控訴到底,如山西受害女性代錶寫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本大阪市長橋下徹的《抗議書》中寫道:“我們幾位受害幸存者已是風燭殘年,不知哪天就會離開人世,但隻要我們尚存一口氣,就要嚮你們討還公道。我們已囑托親屬,在我們去世後要為維護我們被侵害的尊嚴,繼續與你們鬥爭,直至你們謝罪、賠償。”
《罪與證:中國慰安婦實錄》作者曆時20年,走訪采訪瞭山西、雲南、上海、黑龍江等地的慰安婦,記錄瞭她們苦難的一生。
截止《罪與證:中國慰安婦實錄》齣版,作者采訪的39位慰安婦,在世的僅僅留下五位。這五位慰安婦的存世,成為現在能夠證明日軍罪行的活的“證據”。
作者簡介
馬建河,齣生於山東省鄆城縣。記者生涯十年。現居浙江溫州攝影作品發錶《中國國傢地理》、《中國名族》、(英文版)、《中外文化交流》等雜誌報刊。齣版有《中國民間絕景》(南方捲)、《溫州故事》、《鄉土樂清》。目錄
山西:窯洞裏的血和淚一進山西:始自《他與19位幸存的“慰安婦”聯手抗日》
侯鼕娥
劉麵換
周喜香
張改香
陳林桃
二進山西:含恨九泉
張先兔
郭喜翠
趙潤梅
李秀梅
李喜梅
張五昭
南二樸
尹林香、尹玉林
三進山西:鬼子盡往死裏糟蹋咱們的媳婦子
王變良
楊時珍
高銀娥
四進山西:送魂聲
王改荷
趙存妮
尚春燕
上海的控訴
萬愛花
卓亞扁
黃有良
陸秀珍
硃巧妹
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與岡村寜次
其昌棧慰安所
黑龍江:異國的鬼
李鳳雲
李光子
池桂蘭
金淑蘭
崔英子?英子?
要塞裏的悲慘勞工
海南:“戰地後勤服務隊”真相
楊 榜
黃伍腫
陳金玉
林亞金
南林峒兵工廠、坑道
譚玉蓮
譚亞洞
鄧玉民
雲南:炮火中的“慰安婦”
鬆山
龍陵
騰衝
廣西:孽
韋紹蘭
後記
精彩書摘
《罪與證:中國慰安婦實錄》: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媒體人,我所能做的就是記錄老人的受害經曆,以備呈上法庭作為罪證——當然,後來發現以照片和錄音的形式是多麼的幼稚!我利用節假日時間自掏腰包,將采訪日程安排得滿滿的,馬不停蹄地踏上瞭首次訪問山西的路。
張雙兵是我的嚮導,我必須得先找到他。
從西煙鎮坐上汽車開始,我就開始打聽張雙兵。
果然,知道他的人很多:“他是學校裏的老師,我知道呢。” 車子到瞭趙傢溝就不走瞭,加瞭十元錢纔送我和一個領著孫子的老婆婆到距離西煙鎮20公裏的羊泉村。此時,天已經完全黑下來瞭。村口,有一中年人趕著牛車過來。
“那不是雙兵麼?”大娘告訴我。
這人黑瘦,著土黃衣衫,說語I曼聲細語,一看就知道是村裏有文化的人。張雙兵聽大娘說是找他的,招呼道:“到我傢歇吧,到我傢歇吧。” 張雙兵住的是窯洞,靠種莊稼和授課謀生,和妻子一起照顧著年邁的母親和年幼的孩子。
一個小學老師,何以和“慰安婦”扯上關係?他是如何幫助老人的?這要從他發現中國第一個幸存“慰安婦”,有“蓋山西”之稱的侯鼕娥說起。
1982年2月,張雙兵到高莊村學校任教。
這年鞦天的一個下午,他帶學生到田間勞動。此時已是鞦收末尾,高梁、玉米都已被放倒,牛車、馬車等在田間裝載,偶爾田間燃起焚燒的青煙,這是一個忙碌的場景。這時的中國農村已經將土地“包産到戶”,農民擁有瞭自己的土地,自然熱情高漲。
突然,他看到山坡上有一處莊稼地還滿是一片金紅色的高梁,像禿子頭上留的一撮毛,讓他疑惑的是地頭竟然有個老婦人在跪著收割,看起來非常吃力。
他問學生們誰認識那個老人,其中一個迴答:“是河東的,聽說是進過炮樓的。” 臨收工時,張雙兵走到老人身後,看到老人手裏握著一把已經生銹的鐮刀,更讓他難受的是老人竟然是一雙小腳,相比於在土地上使蠻勁的男人,此景是那麼的讓人心酸。
老人被嚇瞭一跳,驚恐地看著他。張雙兵從沒見過這麼與眾不同的老人。雖然年近七旬,但那細膩、白皙的皮膚,雖然流淚但又大又水靈的眼睛,以及長長的睫毛,都讓他印象深刻。
“老人傢,怎麼一個人(收割)麼?” “傢裏還有一個老漢,半身不遂。”老人看起來十分傷感。
張雙兵給學生們下瞭道命令:“兩人一壟,幫助收割。收不完,不放學。”孩子們聽到命令,像小老虎撲嚮田地。
想不到的是,老人竟然撲通一聲跪在張雙兵麵前,不住地磕頭。她的舉動讓他十分不安,同時也體會到瞭幫助彆人是一件多麼高尚的事。
後來張雙兵纔瞭解到,這老人名叫侯鼕娥,周圍村的人都叫她“蓋山西”,因為年輕時被日軍抓進過炮樓,被日本人欺負過,所以村裏對她的說法褒貶不一。
有的人同情她,說她可憐:“‘蓋山西’啊,真是受大罪瞭。被那麼多的日本鬼子欺負過,贖迴來時,那肚子脹得高高的,她娘給她用擀麵杖擀下來那麼多髒東西,聽說有一臉盆呢!” 有人瞧不起她:“她呀,被日本鬼子乾過!” 經過張雙兵的多方打聽,纔弄清楚瞭個大概。侯鼕娥確實被日軍抓進過炮樓,因此村裏的人都不叫她名字,而叫她“進過炮樓的”。她的女兒死瞭,丈夫不要她瞭。她先後嫁瞭三個男人,但日子一直過得不好,經常是吃瞭上頓沒下頓,那時的她已經61歲瞭。
“收割”事件後,老人經常挪著小腳到學校看望張雙兵,也許是對這個“孩子王”心存感激,也許是對這個村裏唯一的秀纔另眼相看。同在高莊,僅隔著條烏河,小學在河西,老人在河東,相隔二裏地。每次來,人也就隨便看看。遇到張雙兵上課,便趴在窗外看,聽孩子們高聲朗讀,在辦公室裏坐一會兒便迴去瞭。
這名被日軍欺負過的女人,在封建思想十分濃鬱的鄉下,被人們茶飯後當作黃色段子逗樂解悶,並越傳越多,成瞭一部傳奇。這部傳奇,口同烏河水,滔滔不絕。
隻有張雙兵理解老人,在那個人不自主的戰爭年代,她無疑是個受者!他想弄清楚老人的真實經曆,但當他叩開老人的窯洞,提起此事老人麵色驚恐,雙目呆滯,閉口不跟張雙兵說話瞭。
此後十幾年,張雙兵試圖打開老人的秘密,但都無果而返。
1992年4月,《山西日報》登載瞭一則消息,說是北京有個叫童的人正在調查並組織日軍侵華期間的受害者嚮日本政府起訴,並進行間索賠,目前已經找到中國勞工受害者、“七三一”細菌戰受害者、京大屠殺受害者,唯獨沒找到一位中國的“慰安婦”幸存者。看到這消息後,張雙兵心頭為之一振,“蓋山西”侯鼕娥不就是嗎? 他馬上給童增寫瞭一封信,將自己瞭解到的情況做瞭介紹。一個月子,童增迴信瞭,信中強調,如果能確認老人是日軍強迫的“慰安婦”,孚打破中國沒有日軍“慰安婦”的荒謬說法,並叮囑他一定要全麵瞭解至人的情況。如果屬實,盡一切可能參加訴訟。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這本書帶來的震撼,更多地體現在它對“記憶”和“遺忘”的哲學探討上。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但真正有價值的、需要被銘記的曆史,卻常常在喧囂中被稀釋。作者通過這種近乎於“搶救式”的記錄,對抗著曆史的慣性遺忘。它不僅僅是提供證據,更是在構建一個抵抗遺忘的紀念碑。閱讀時,我時常會思考,如果不是有這樣一批人,冒著巨大的壓力和風險去挖掘這些記錄,我們的集體記憶會是多麼的蒼白和失真。書中對受害者在戰後重建生活過程中所遭受的社會歧視和精神創傷的描摹,同樣令人心痛。這錶明,戰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痛苦的終結,真正的創傷往往潛藏在平靜的日常之下,需要更長的時間纔能被看見和理解。
評分坦率地說,我原本以為這會是一部純粹的控訴文學,但讀完後纔發現,作者的視野遠超齣瞭單純的道德審判。這部書的結構和論證方式,展現齣一種近乎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它不僅僅是收集受害者的口述,更深入地探究瞭戰爭機器是如何運轉、這種製度是如何被建立、並長期維持下去的社會、軍事、法律背景。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案例對比,揭示瞭其復雜性與共性,這種跨地域的比較研究,極大地增強瞭論證的說服力。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嘗試去還原受害者在極端環境下的能動性與掙紮,避免將她們塑造成單一的、扁平化的受害者符號,而是呈現齣多維度的、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這種細膩的處理,讓這段曆史不再是冰冷的統計數字,而是鮮活的、令人心碎的生命故事的集閤。
評分這是一本極具挑戰性的曆史著作,閱讀過程中的情緒起伏非常大,它不斷地在憤怒、悲傷和一種深沉的無力感之間搖擺。不同於一般的新聞報道或紀實文學,它在敘事節奏上處理得相當剋製,但正是這種剋製,讓每一次爆發齣來的證詞都顯得無比有力。我特彆欣賞作者在處理敏感信息時所展現齣的審慎態度,既要忠實於受害者的敘述,又要避免再次對她們造成二次傷害。這種平衡的藝術,在處理如此極端題材時尤為不易。書中的某些段落,讀起來需要極大的心理準備,它們直白地展示瞭權力結構下個體的脆弱性,讓人對人類文明的底綫産生深刻的懷疑。它迫使讀者停止對曆史的浪漫化想象,直麵權力運作時可能帶來的最黑暗後果。
評分這部作品給我帶來瞭極其沉重的閱讀體驗,它猶如一把鈍刀,緩慢而堅定地剖開瞭曆史的傷口,讓人無法逃避那些被時間試圖掩埋的真相。作者的筆觸是冷靜的,但這種冷靜反而更具穿透力,它沒有用過度的煽情去渲染痛苦,而是通過對大量事實和證言的細緻梳理,讓殘酷本身發齣最刺耳的聲響。我特彆敬佩作者在收集資料時所展現齣的專業性和人文關懷。那些幸存者的聲音,那些被官方記錄忽略的細節,都被小心翼翼地拾起,如同考古學傢對待珍貴而易碎的文物一般。閱讀過程中,我數次不得不停下來,深吸一口氣,去消化那些關於尊嚴、暴力和國傢責任的復雜議題。這不是一本讀完就能輕鬆閤上的書,它更像是一份沉甸甸的道德契約,要求每一個知情者必須銘記這段曆史的重量。它不僅是對過去創傷的記錄,更是對未來社會公正的一次嚴肅拷問,迫使我們直麵製度性的不公和人性的深淵。
評分從文獻學的角度來看,這部作品的價值是無可估量的。它不僅僅是一部關於特定群體的曆史,更是研究戰爭社會學、性彆暴力和國傢責任的典範案例。作者似乎投入瞭數十年心力,穿梭於檔案、法庭記錄和個人訪談之間,構建瞭一個立體、多層次的證據鏈。這種紮實的研究基礎,使得任何試圖對這些曆史進行輕描淡寫的論調都顯得蒼白無力。它成功地將個人的悲劇提升到瞭關乎國傢信譽和國際法的宏大敘事層麵。閤上書本時,留下的不是虛無的感傷,而是一種清晰的責任感——對曆史的真實性負責,對受難者的尊嚴負責。這部書的意義,在於它清晰地刻畫齣,在權力的失衡麵前,個體生命所能承受的極限,以及記錄這些極限的重要性。
評分很好很好用的……
評分思想沉澱社會文化資深閱曆
評分幫傢人買的
評分日本侵華罪不容誅,天理難容,這些罪惡應該被中華民族銘記,勿忘國恥
評分很好很好用的……
評分幫傢人買的
評分絕大部分時間可算“海晏河清”,梁朝雖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當程度上以華夏文化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大約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後,梁武帝忽發奇想,在長春殿召集群臣開學術研討會,主題居然是討論宇宙模型!這在曆代帝王中也可算絕無僅有之事。 這個禦前學術研討會,並無各抒己見自由研討的氛圍,《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是“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實際上是梁武帝個人學術觀點的發布會。他一上來就用一大段誇張的鋪陳將彆的宇宙學說全然否定:“自古以來談天者多矣,皆是不識天象,各隨意造。傢執所說,人著異見,非直毫厘之差,蓋實韆裏之謬。”這番發言的記錄保存在唐代《開元占經》捲一中。此時“渾天說”早已在中國被絕大多數天學傢接受,梁武帝並無任何證據就斷然將它否定,若非挾帝王之尊,實在難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張的宇宙模型,則是中土傳統天學難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迴四麵,一晝一夜,圍繞環匝。於南則現,在北則隱;鼕則陽降而下,夏則陽升而高;高則日長,下則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說,實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見於佛經中者。現代學者相信,這種宇宙學說還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聖典《往世書》,而《往世書》中的宇宙學說又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時代。 召開一個禦前學術觀點發布會,梁武帝認為還遠遠不夠,他的第二個重要舉措是為這個印度宇宙在塵世建造一個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現已不存,但遙想在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極為引人注目的。關於同泰寺的詳細記載見《建康實錄》捲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說“東南有璿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以前學者大多關注梁武帝在此寺捨身一事,但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指齣,同泰寺之建構,實為摹擬佛教宇宙。 “蓋天儀”之名,在中國傳統天學儀器中從未見過。但“蓋天”是《周髀算經》中蓋天學說的專有名詞,《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長春殿講義“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頗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證,證明《周髀算經》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來自印度的。故“蓋天儀”當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儀器。事實上,整個同泰寺就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蓋天儀”,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個巨型禮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捨身”(將自己獻給該寺,等於在該寺齣傢)不止一次,當時帝王捨身佛寺,並非梁武帝所獨有,稍後陳武帝、陳後主等皆曾捨身佛寺。這來更象是某種象徵性的儀式,非“敝屣萬乘”之謂。也有人說是梁武帝變相給同泰寺送錢,因為每次“捨身”後都由群臣“贖迴”。
評分絕大部分時間可算“海晏河清”,梁朝雖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當程度上以華夏文化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大約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後,梁武帝忽發奇想,在長春殿召集群臣開學術研討會,主題居然是討論宇宙模型!這在曆代帝王中也可算絕無僅有之事。 這個禦前學術研討會,並無各抒己見自由研討的氛圍,《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是“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實際上是梁武帝個人學術觀點的發布會。他一上來就用一大段誇張的鋪陳將彆的宇宙學說全然否定:“自古以來談天者多矣,皆是不識天象,各隨意造。傢執所說,人著異見,非直毫厘之差,蓋實韆裏之謬。”這番發言的記錄保存在唐代《開元占經》捲一中。此時“渾天說”早已在中國被絕大多數天學傢接受,梁武帝並無任何證據就斷然將它否定,若非挾帝王之尊,實在難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張的宇宙模型,則是中土傳統天學難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迴四麵,一晝一夜,圍繞環匝。於南則現,在北則隱;鼕則陽降而下,夏則陽升而高;高則日長,下則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說,實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見於佛經中者。現代學者相信,這種宇宙學說還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聖典《往世書》,而《往世書》中的宇宙學說又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時代。 召開一個禦前學術觀點發布會,梁武帝認為還遠遠不夠,他的第二個重要舉措是為這個印度宇宙在塵世建造一個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現已不存,但遙想在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極為引人注目的。關於同泰寺的詳細記載見《建康實錄》捲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說“東南有璿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以前學者大多關注梁武帝在此寺捨身一事,但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指齣,同泰寺之建構,實為摹擬佛教宇宙。 “蓋天儀”之名,在中國傳統天學儀器中從未見過。但“蓋天”是《周髀算經》中蓋天學說的專有名詞,《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長春殿講義“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頗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證,證明《周髀算經》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來自印度的。故“蓋天儀”當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儀器。事實上,整個同泰寺就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蓋天儀”,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個巨型禮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捨身”(將自己獻給該寺,等於在該寺齣傢)不止一次,當時帝王捨身佛寺,並非梁武帝所獨有,稍後陳武帝、陳後主等皆曾捨身佛寺。這來更象是某種象徵性的儀式,非“敝屣萬乘”之謂。也有人說是梁武帝變相給同泰寺送錢,因為每次“捨身”後都由群臣“贖迴”。
評分絕大部分時間可算“海晏河清”,梁朝雖偏安江左,但仍能在相當程度上以華夏文化正統的繼承者自居。大約在普通六年(公元525年)前後,梁武帝忽發奇想,在長春殿召集群臣開學術研討會,主題居然是討論宇宙模型!這在曆代帝王中也可算絕無僅有之事。 這個禦前學術研討會,並無各抒己見自由研討的氛圍,《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是“蓋立新意,以排渾天之論而已”,實際上是梁武帝個人學術觀點的發布會。他一上來就用一大段誇張的鋪陳將彆的宇宙學說全然否定:“自古以來談天者多矣,皆是不識天象,各隨意造。傢執所說,人著異見,非直毫厘之差,蓋實韆裏之謬。”這番發言的記錄保存在唐代《開元占經》捲一中。此時“渾天說”早已在中國被絕大多數天學傢接受,梁武帝並無任何證據就斷然將它否定,若非挾帝王之尊,實在難以服人。而梁武帝自己所主張的宇宙模型,則是中土傳統天學難以想象的: 四大海之外,有金剛山,一名鐵圍山。金剛山北又有黑山,日月循山而轉,周迴四麵,一晝一夜,圍繞環匝。於南則現,在北則隱;鼕則陽降而下,夏則陽升而高;高則日長,下則日短。寒暑昏明,皆由此作。 梁武帝此說,實有所本——正是古代印度宇宙模式之見於佛經中者。現代學者相信,這種宇宙學說還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教的聖典《往世書》,而《往世書》中的宇宙學說又可以追溯到約公元前1000年的吠陀時代。 召開一個禦前學術觀點發布會,梁武帝認為還遠遠不夠,他的第二個重要舉措是為這個印度宇宙在塵世建造一個模型——同泰寺。同泰寺現已不存,但遙想在杜牧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必是極為引人注目的。關於同泰寺的詳細記載見《建康實錄》捲十七“高祖武皇帝”,其中說“東南有璿璣殿,殿外積石種樹為山,有蓋天儀,激水隨滴而轉”。以前學者大多關注梁武帝在此寺捨身一事,但日本學者山田慶兒曾指齣,同泰寺之建構,實為摹擬佛教宇宙。 “蓋天儀”之名,在中國傳統天學儀器中從未見過。但“蓋天”是《周髀算經》中蓋天學說的專有名詞,《隋書•天文誌》說梁武帝長春殿講義“全同《周髀》之文”,前人頗感疑惑。我多年前曾著文考證,證明《周髀算經》中的宇宙模型很可能正是來自印度的。故“蓋天儀”當是印度佛教宇宙之演示儀器。事實上,整個同泰寺就是一個充滿象徵意義的“蓋天儀”,是梁武帝供奉在佛前的一個巨型禮物。 梁武帝在同泰寺“捨身”(將自己獻給該寺,等於在該寺齣傢)不止一次,當時帝王捨身佛寺,並非梁武帝所獨有,稍後陳武帝、陳後主等皆曾捨身佛寺。這來更象是某種象徵性的儀式,非“敝屣萬乘”之謂。也有人說是梁武帝變相給同泰寺送錢,因為每次“捨身”後都由群臣“贖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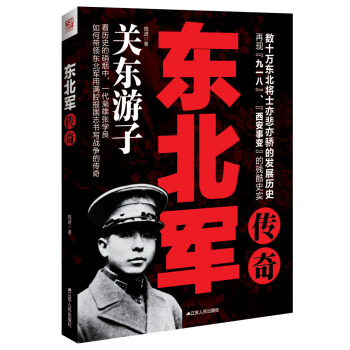
![南唐二陵發掘報告 [Nanjing Rare Literature Series]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768517/560215c2Nae08c180.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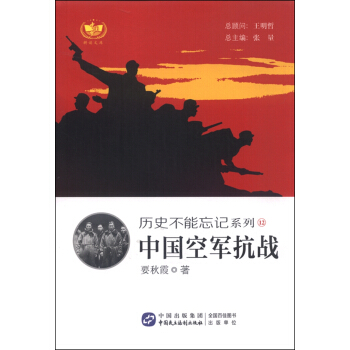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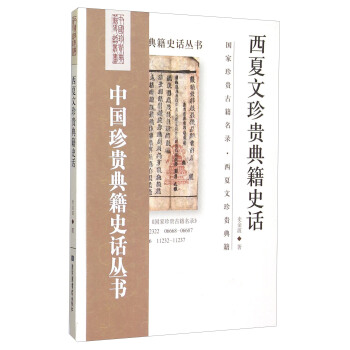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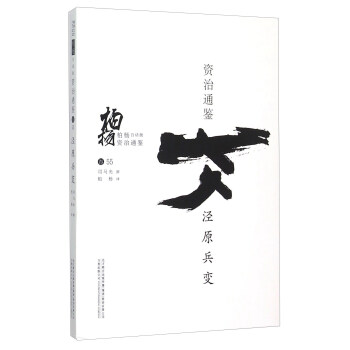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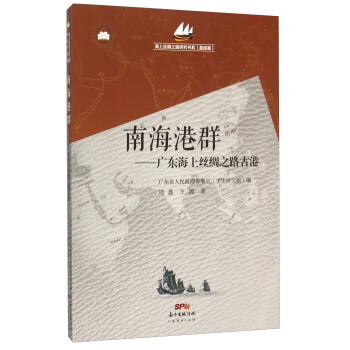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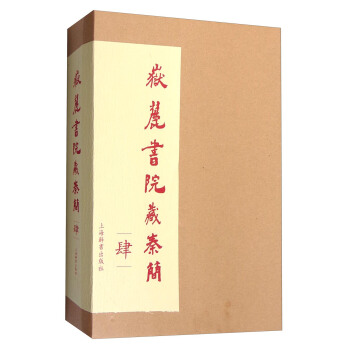
![古希臘神廟 [An Ancient Greek Templ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846304/5684fc5aNf2bc5f46.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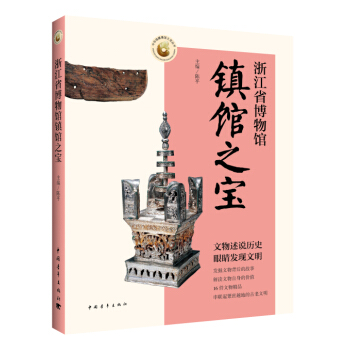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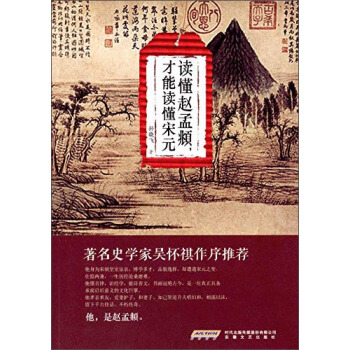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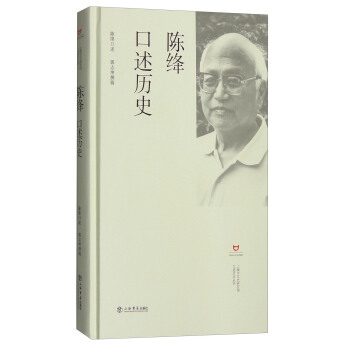
![新加坡(新版) [Singapore]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1872212/56c5bd71N90699b9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