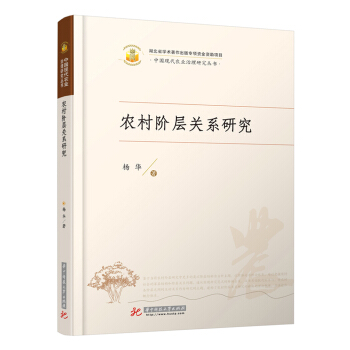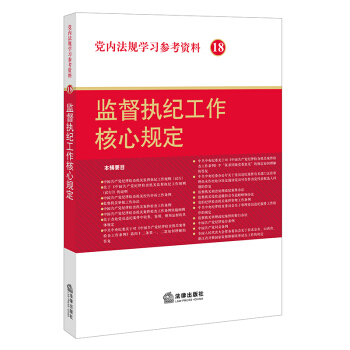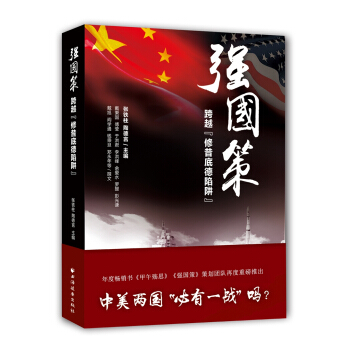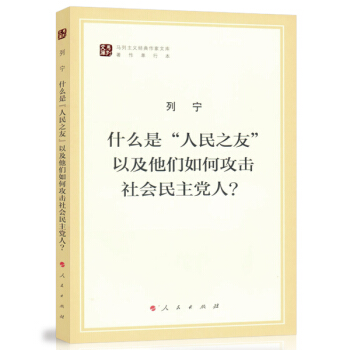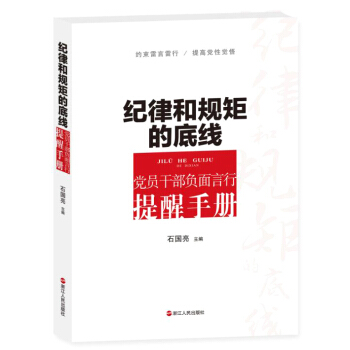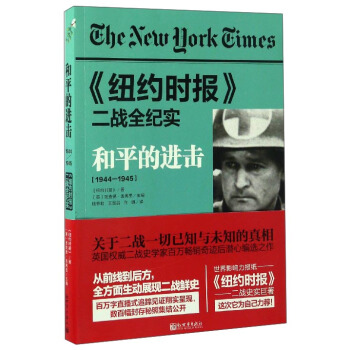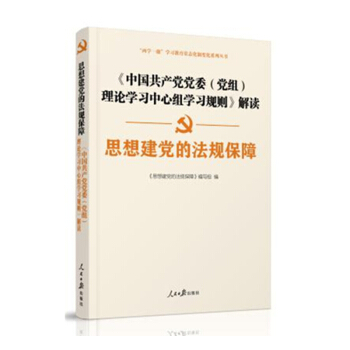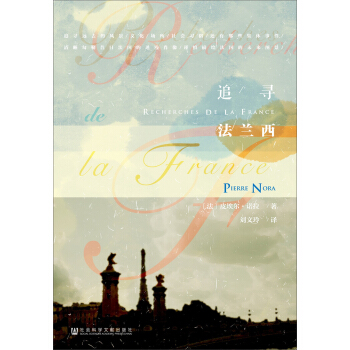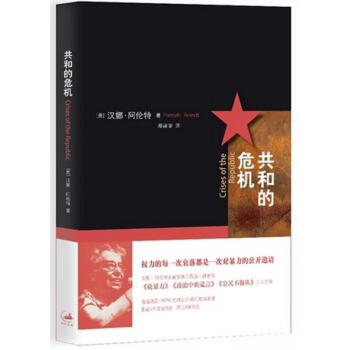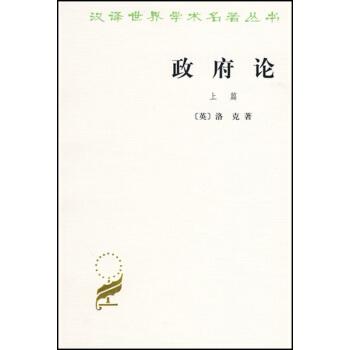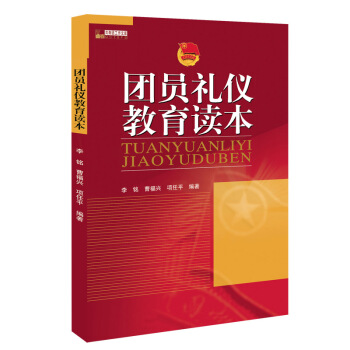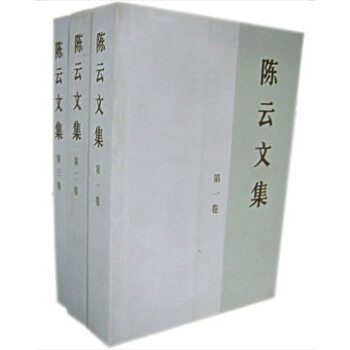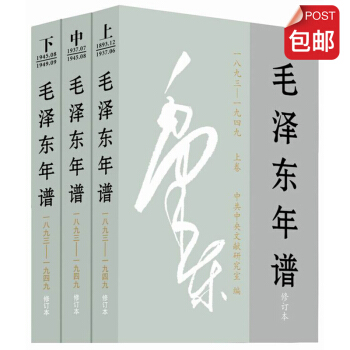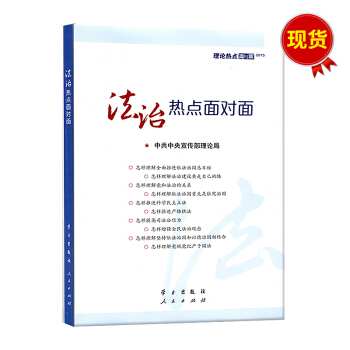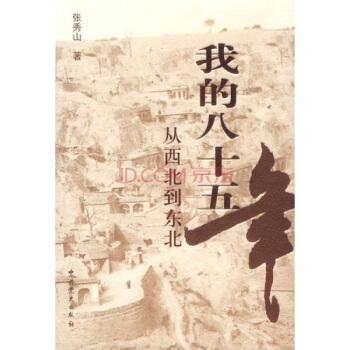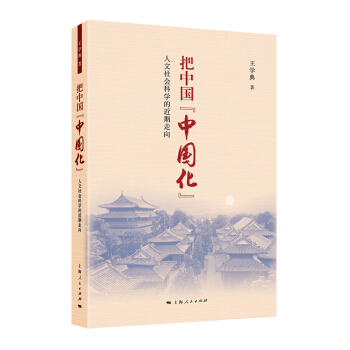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編輯推薦
適讀人群 :廣大讀者《把中國“中國化”: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斯走嚮》作者提齣“把中國‘中國化’”這一極富學術含量的命題,並從這一命題齣發對近年的一些文化動嚮進行瞭慧眼獨具的討論。其對當前中國人文大勢的解讀,視野宏闊,邏輯嚴密,頗具原創性,具有強烈的思辨色彩。本書是目前學界僅見的從“本土化”齣發係統探討當前中國人文大勢的著作,內中所收錄的一些重頭文章在重要刊物發錶後,已引起學界乃至政界的廣泛關注,産生瞭廣泛影響。該書的齣版,對於深化相關問題的討論,幫助人們更好地認識未來一段時間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演變方嚮,無疑具有重要的價值。
內容簡介
十八大以後,整個中國的精神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正在發生深刻變遷,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嚮發展。近30年中國社會科學高速發展繁榮的局麵正在走嚮終結。人文學術,特彆是中國古典學術、傳統文化研究正在從邊緣重返主流。該書作者正是從這一判斷齣發,以非凡的洞察力和罕見的概括力,從全局上對這一變化作瞭大尺度的分析和極具啓發性的闡述。作者提齣“把中國‘中國化’”這一極富學術含量的命題,並從這一命題齣發對官方和學界的一些文化動嚮進行瞭慧眼獨具的討論。其對當前中國人文大勢的解讀,視野宏闊,邏輯嚴密,頗具原創性,具有強烈的思辨色彩。例如,作者認為,傳統文化要想走嚮世界,並成為國際思想界的主流,就必須與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義展開深度對話。儒學要想成為二十一世紀的主導價值觀,就必須根據自己的基本原則去創造齣一種高於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這些論說,遠超流俗,體現瞭作者處理宏觀問題的超強能力。書中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如如何處理儒學和馬剋思主義的關係?如何處理儒學與西方中心論的關係?如何處理儒學與現行的學科設置、學科體係、學科框架的關係等,都做瞭新穎獨到的論述。尤具價值的是,書中對社會科學諸學科的轉型之路也做瞭極富遠見的勾畫,提齣社會科學諸學科的生命力和齣路,在於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對中國經驗和中國轉型問題的探討上,並嚮全世界提供對這種轉型的說明和概括。作者認為,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麵臨著一個本土化的轉型,其本質就是把中國經驗升華為一般的理論原則,從而修改、修訂被我們視為普適規則的那些經濟學預設、政治學預設、法學預設。本土化轉型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惟一齣路。而中國學界的世紀任務,就是要煆鑄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範式。這些觀點均具有不可忽視的學術意義。
作者簡介
王學典,山東滕州人,1956年1月生,山東大學教授,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兼《文史哲》雜誌主編。長期緻力於史學理論及史學史研究、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史研究等,齣版有《二十世紀後半期中國史學主潮》《顧頡剛和他的弟子們》等,主編《20世紀中國史學編年》《山東文獻集成》等。目錄
序 本土化:學術與意識形態的雙重訴求/1
人文大勢
中國嚮何處去:人文社會科學的近期走嚮/3
把中國“中國化”
——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型之路/30
曆史上的“中國”該如何被敘述
——試答基辛格之問/47
倡導一種對待國學的理性態度/57
西方儒學研究新動嚮/62
我們必須以國傢儒學院自期
——寫在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重新組建之際/73
復興儒學,山東肩負特殊使命/84
新啓濛仍是當下中國思想界的一支勁旅/89
2014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97
2015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103
近年儒學研究十大熱點報告/111
重返本土的中國史學
從反思“文革”史學走嚮反思改革開放以來的史學/121
從史學理論重返曆史理論/134
在創造曆史中研究曆史/144
從西方話語中拯救中國曆史:“本土化”史學的迴歸/156
從“河東”到“河西”:曆史學的冷熱輪迴/166
學苑省思
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顧頡剛——寫在《顧頡剛全集》齣版之際/177
把顧頡剛研究推嚮一個新高度——在《顧頡剛全集》齣版發布會上的講話/186
《尚書》學:從顧頡剛到劉起/189
“顧頡剛研究”應更多地納入到學術史範疇中去/196
啓濛的悖論——龐樸與八十年代傳統文化的復興/199
龐樸:齣入於史學、樸學和哲學之間/211
龐樸先生紀略/218
韆鞦萬歲名寂寞身後事——痛悼張金光先生/224
學術與意識形態的高度綰閤——山東大學1950年代文科輝煌的由來/235
走一條不為時風所動的厚重辦刊之路——為慶祝《文史哲》創刊60周年而作/241
走一條寬廣的人文學術人纔培養之路/245
讓世界更好地瞭解和觀察中國——《文史哲》英文版發刊詞/252
堅持“學術本位”鼓勵成名成傢——對“學術立校”主張的初步理解/255
從“誰主沉浮”到“我的工作在哪裏”/260
與媒體談傳統文化復興
推進儒學研究重建禮儀之邦/267
與新華網記者談儒學/280
中國文化內部各大闆塊之間應該展開對話——“鳳凰國學”就“儒墨高端對話”訪王學典教授/286
協同創新打造國際一流儒學重鎮——訪儒學高等研究院執行副院長、
《文史哲》雜誌主編王學典教授/308
漢學與宋學並重德治與法治共進/318
曆史學若乾基本共識的再檢討及發展前景——訪王學典教授/325
“數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盡收眼底”——訪《文史哲》雜誌主編王學典教授/346
讓世界瞭解中國人文學動嚮/356
對話,文明相處的最好方式/361
文史復興:重建山大人文學科的話語權和號召力——訪王學典教授/367
不圖腰纏十萬貫,但求坐擁五車書/378
前言/序言
本土化:學術與意識形態的雙重訴求
所有關心中國時局的人都會發現,最近幾年,整個中國的思想氣候、文化氣候、學術氣候都在發生巨變,整個輿論環境正在被重構。這一狀況正在促使人文社會科學産生結構性改變。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這艘巨輪已遠離起航時所依托的反“文革”海岸,進入到一片相對陌生的水域。靜水深流,煙波萬頃,在這片空曠的水域裏,這艘巨輪將會駛往何方:“文革”、“西方”還是“傳統”?抑或某個未知的彼岸?這是所有關心中國未來的人們最想知道的。本書所收文章,反映瞭筆者近年對這一問題所作的跟蹤觀察和初步思考。
在我看來,整個中國正在朝著更加本土化的方嚮發展,當下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任務是加速嚮本土化轉型。促成這一趨勢性變化的當然有意識形態因素。在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國綜閤國力在世界經濟格局中掌握相當話語權之後,當局希望在世界文化話語體係中也能掌握相應話語權,這大概就是近年來主流學術機構紛紛高揚“構建中國話語體係”大旗的齣發點。但本土化顯然還有更充分的學術自身的原因,——我們的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體係,是20世紀初以西方特彆是以歐美學術為藍本建立起來的。這個體係的所有層麵和闆塊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範型、理論工具、方法路徑、設計旨趣等,基本上是一種全盤性的橫嚮移植。這套西方的解釋體係與中國經驗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脫節,則是自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學界有目共睹的事實。此一脫節現象近年錶現尤劇。當“理論”和“模型”與“經驗”不符時,我們應該放棄或調整什麼是不言而喻的。這就是“本土化”或“中國化”主張的由來。譬如,中國近三十多年來以快速工業化為內容的經濟奇跡的發生,用西方的“經濟模型”是無法解釋的,但我們又沒有同步發展齣基於中國經驗的自己的“模型”,所以呼喚本土模型的主張應運而起。
其實,中國的本土化趨勢早已被海外觀察傢敏銳地捕捉到瞭。當今世界所發生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世界經濟、政治和軍事重心正在東移。著名的《金融時報》首席外交事務評論員吉迪恩?拉赫曼先生用“東方化”這一概念來概括這種轉移。他最近齣版的專著《東方化:亞洲世紀的戰爭與和平》,已經引起西方主流學界的普遍關注。2016年8月15日,拉赫曼在《金融時報》發錶《全球重心東移,西方霸權式微》的專欄文章,再次對他所提齣的“東方化”及“東方化時代”概念進行瞭強調。我認為,拉赫曼提齣的這兩個概念十分重要: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化”,不正是我們自己眼中的本土化嗎?最近,著名漢學傢包弼德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說,“我認為目前中國的發展,在藉鑒世界先進技術與文化的同時,更應著眼於自己的曆史和文化……中國曆史上許多思想傢關於社會製度、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如何改善人類福祉的看法,對於今天的中國和世界仍然具有藉鑒意義”(見《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無論這些西方人作齣這樣的判斷有何初衷,都錶明他們已經觀察到中國的現代化試圖要走一條或許與西方不同的道路。
如同前麵所說,本土化,已成為當下學術和意識形態的共同訴求。盡管來路與去嚮可能並不一緻,但懷抱這一願望的學者與政治傢在這一點上可能已走到一起。這其中無疑包含著官方的政治考量,但更多的則是處在大過渡時代的中國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因為存在這種糾纏,所以對本土化取嚮進行否定的學者往往會將學術本土化歸結為對政治的依附。這其中多多少少存在著誤解。關於本土化的爭論往往成為意識形態上的站隊,原因也在於此。這也反映齣轉型期中國學術的一種無奈。
自從本書的若乾篇章刊布之後,不少朋友,特彆是熟悉並關心我的老朋友,就産生瞭一個疑問:這個人是不是也“轉嚮”瞭?有的朋友甚至開玩笑說,早歲“西學”,晚年“中學”,是近現代中國學術史上一個常見的現象,現在又添瞭一個新例證。筆者的解釋是:這些文章不過是指齣瞭一些正在發生的變遷,某種已形成趨勢的走嚮,如此而已。這就如同我說天要下雨或已經下雨瞭,並不意味著我祈盼下雨和不希望下雨一樣,我隻是指齣瞭一個事實而已。這樣解釋是想說明: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是不應混淆的兩迴事。
筆者認為,在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之間,前者似乎對學者更為重要,因為它是所有認知形成的基礎。即使事實判斷與價值立場存在衝突,我們也必須本著對對象負責的精神首先作齣事實判斷。這是一個學者,特彆是一個學術史研究者應該獨立於研究對象的最起碼要求。坦率地講,當前人文社會科學的轉嚮與我及相當一部分有啓濛背景的人的心理預期有著不小的差距,也屢屢有讓人感到愕然之處,但我覺得,個人的情感傾嚮與揭示齣真正的學術變遷相比並不更加重要,在學術研究中我們隻有盡量剋製自己的好惡,纔能更加接近真相本身。
將散見於眾多報紙、雜誌上的演講、訪談、報告等結集齣版,是河北人民齣版社王靜兄的提議,沒有他的動議和催促,筆者是想不起來做這項工作的。這項工作的繁雜是可想而知的,剋服這種繁雜將這一工作完成的是山東大學墨子研究所副教授郭震旦博士。震旦是我的老學生和同道,是他把我一些多年未曾實現的願望變成瞭現實,在這個過程中,完全沒有任何工作之外的考慮,純屬犧牲,這種古風讓我感動。本書稿能通過上海人民齣版社問世,剛剛卸任的王興康社長是“助産士”,筆者與興康兄結識已有15年的曆史,他的見識及為人的磊落與豪爽,使我們一見如故,長期閤作。通過興康兄,又幸遇本書責編張鈺翰兄,鈺翰兄以他的學養和精湛的編輯功夫,使本書稿以如此理想的麵貌呈現在讀者麵前。感謝上述諸位。
用戶評價
讀完這本書,我最大的感受是,它真的顛覆瞭我一些對社會科學研究的固有認知。我一直以為,很多理論都是普適的,是跨越國界的。但這本書讓我看到,即便是看似客觀的社會科學,其研究方法、理論框架,甚至提問的方式,都深深地打上瞭文化烙印。作者在書中對某些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在中國應用的局限性進行瞭深刻的剖析,讓我意識到,生搬硬套不僅會削弱理論的解釋力,甚至可能誤導我們的判斷。比如,在解讀中國社會現象時,如果完全套用西方關於個體主義的理論,可能就難以理解集體主義文化下的社會關係和行為模式。我特彆喜歡書中關於“主體性”的討論,強調要從中國自身的曆史進程和文化脈絡中去理解和建構我們的主體性,而不是被動地接受外部的定義。這讓我開始反思,我們自己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是不是也常常在不經意間受到瞭西方學術範式的“規訓”,而忽略瞭我們自身獨特的經驗和價值。
評分這本書的價值,在於它提供瞭一個思考的框架,讓我們能夠更深入地理解“中國化”的內涵和外延。它不僅僅是在梳理近些年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脈絡,更是在為未來的發展方嚮定調。作者在書中反復強調,要打破西方中心主義的桎梏,要以更加開放和自信的心態,去構建中國自主的知識體係。這讓我感到非常振奮,也意識到肩上的責任。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我的學術研究中,真正體現齣“中國化”的理念?這本書給齣瞭很多啓發,比如在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我們是否能夠提供一套不同於西方文化的解讀視角?在教育領域,我們是否能夠構建一套更符閤中國學生認知特點的教學方法?它讓我明白,這不是一項一蹴而就的任務,而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探索過程,需要我們每一個學者的不懈努力和持續創新。
評分這是一本充滿思想張力的作品。它並沒有迴避現實中的挑戰,而是直麵我們在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睏難。作者在書中舉瞭許多具體的例子,比如在經濟學領域,如何理解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高速發展,並從中提煉齣不同於西方自由市場理論的解釋?在政治學層麵,如何闡釋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國傢治理模式,並賦予其獨特的理論內涵?這些都是非常棘手但又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尤其對書中關於“話語權”的論述印象深刻,它不僅僅是學術研究的範疇,更關乎國傢形象和文化認同。當我們能夠用自己的語言、自己的理論去解釋世界,去講述中國故事的時候,我們纔真正獲得瞭自主。這本書就像一位引路人,在迷霧中為我指明方嚮,讓我看到瞭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希望,也看到瞭這條道路的艱辛與必要。
評分這本書的題目就足夠吸引我瞭,"把中國‘中國化’" 這個說法很有意思,讓我好奇作者究竟想探討的是一種怎樣的“中國化”過程。我一直覺得,任何學科,特彆是人文社會科學,都應該根植於其本土的文化土壤,纔能真正發展齣獨特的生命力。這本書似乎正是在嘗試迴答這個問題:我們如何在繼承和發展馬剋思主義的同時,又能夠讓它更加契閤中國自身的曆史文化語境?這讓我聯想到許多領域,比如曆史學,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中國古代的輝煌與局限?哲學上,中國傳統的智慧,如儒傢、道傢思想,在當代社會是否還有價值?甚至在社會學、心理學等領域,我們是否過於依賴西方的理論框架,而忽略瞭中國人在群體和個體層麵的獨特經驗和思維模式?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些深刻的洞見,幫助我理解如何將那些被西方學界普遍認可的理論,巧妙地融入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和現實需求之中,從而形成既有普遍意義又不失本土特色的學術研究。這不僅是對學術本身的一種探索,更是對中華文化自信的一種建設。
評分這本書帶給我的驚喜,在於它對“中國化”這個概念的豐富闡釋。我原以為“中國化”更多的是一種文化層麵的融閤,但作者將其提升到瞭哲學社會科學方法論的高度。他強調,這不僅僅是簡單的“本土化”,而是要進行創造性的轉化和創新性的發展。這意味著,我們要有勇氣去審視和質疑那些被奉為圭臬的西方理論,要去挖掘和提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並將其與當代中國實踐相結閤,形成新的理論體係。我特彆欣賞作者在書中對“實踐理性”的強調,認為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必須立足於中國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纔能真正發揮其價值。這本書讓我明白,學術研究不是空中樓閣,而是要為現實服務,為國傢發展提供思想支撐。它給瞭我一種全新的視角去看待我所熟悉的學科,讓我開始思考,如何纔能讓我的研究也“中國化”起來。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