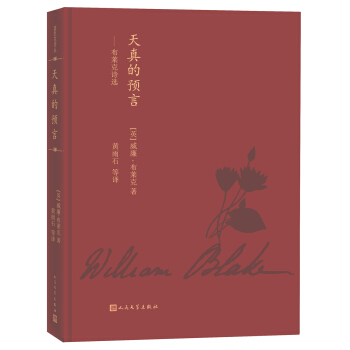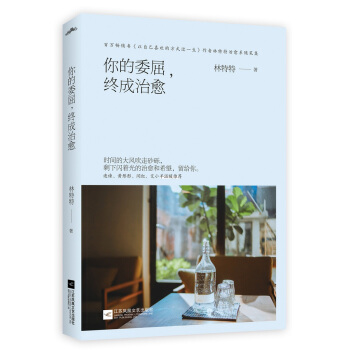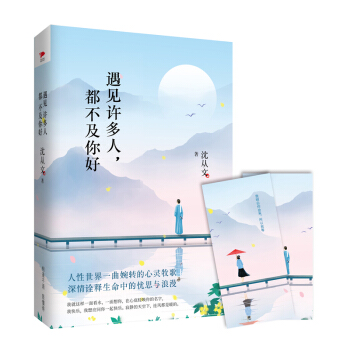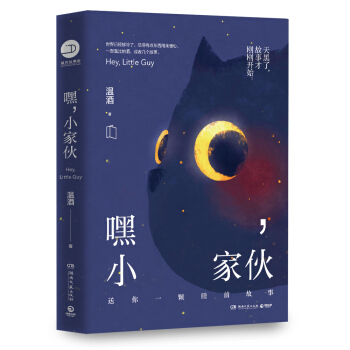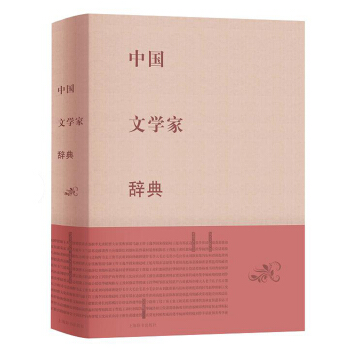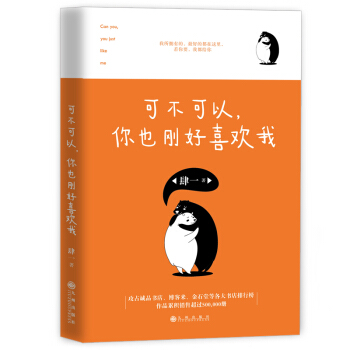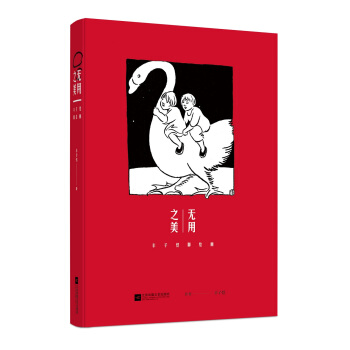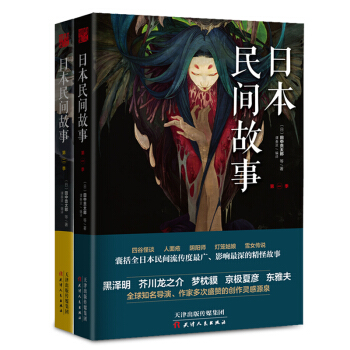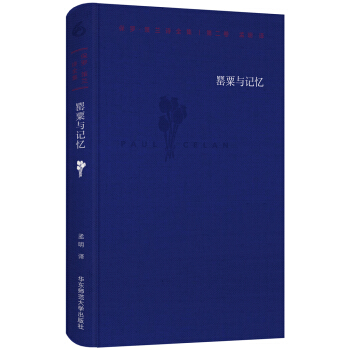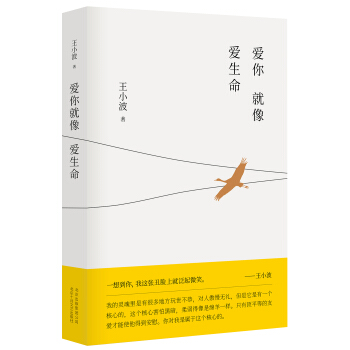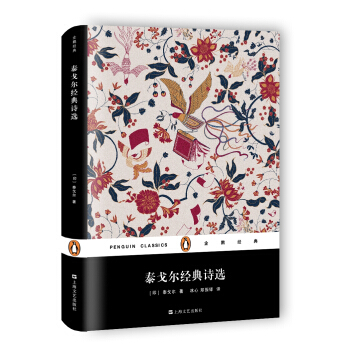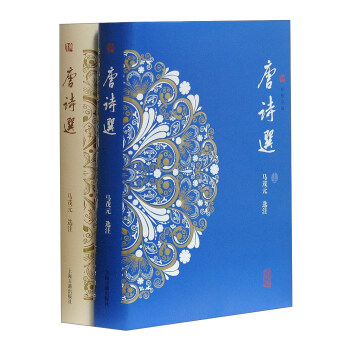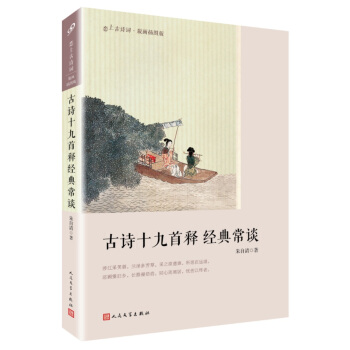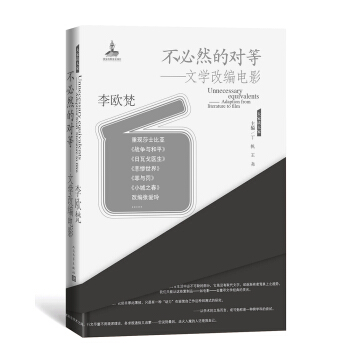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内容简介
我写这本书,有一个潜在的目的,姑且称之为“后启蒙”:经由现今来重新认识过去,也经过电影来重新认识文学,特别是中外文学的经典。……这个“后”字,至少有两个涵义:一指现今的所谓“后现代”社会;另一个“后”字则指的是“后”来居上的学问——电影,我认为现今已是经由电影来重新认识文学经典的时候了。——李欧梵
民初的文人有一个喜欢看戏的传统,他们不单止看,更爱研究戏曲,当然也有一些人沉溺其中的,捧戏子的大有人在。到了三十年代,电影开始发展,由无声演变到了有声,从美国的荷里活影响到了中国。舞台上的戏曲表演受到了冲击,看戏演戏都相应少了。原来喜欢看戏的人不一定改看电影,但是,许多以前不看戏的人,却被电影吸引住了。
欧梵从来不是个戏迷,却是一个影迷。他告诉我他看的首部电影是《鹿苑长春》,那时他一家逃难到了南京——父母带他去看的。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格力哥利柏。……我想这童年的兴趣,引发了他日后对电影的迷恋是其来有自的。到了大学期间,他更开始在报纸杂志里写影评,逐渐深入钻研,现在的这部书——《文学改编电影》更不是纯粹单靠兴趣而可以写成的,非要深度的学养不可。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老影痴的观影札记。
——李子玉
(李欧梵夫人)
目录
目录前言
导论:改编的艺术
第一部分:莎士比亚的重现与再重现
四个版本四种阅读:从《哈姆雷特》到《王子复仇记》
角色决定论:三部《奥赛罗》的电影表述
五十年代《惑星历险》:《暴风雨》的科幻演绎
第二部分:名著名片之间:不必然的对等
一流和二流小说:英国十九世纪文学电影
必然的缺失:细谈《战争与和平》之改编
看电影不如看原著:《安娜卡列尼娜》透视人生真谛
被放大的爱情:比读《齐瓦哥医生》的小说与电影
文学电影之形神合一:读珍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及《理智与感情》
可能是改编最多的名著:雨果的《悲惨世界》
白描手法刻划灵魂深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
第三部分:一人有一个卡夫卡
忠实、执迷与超越:一人有一个卡夫卡
经典与平庸:两部《一树梨花压海棠》的对读
《迷失决胜分》:活地阿伦式的《罪与罚》
此情不渝,至死方休:李安的《断背山》
二流小说拍山神采:重访《苏丝黄的世界》
毛姆和《彩色面纱》:“爱在遙远的附近”?
第四部分:最陌生的自家人:谈中国文学名著之改编
最难拍的现代文学作品:从五位中国作家说起
国片不及粵片:重读曹禹的《雷雨》与《原野》
壮观的空洞:《赤壁》作为改编反例子
光环背后的负担:从《小城之春》说起
气氛和细节:张爱玲小说的改编问题
借影像吸引年轻一代窥观历史:看李仁港《三国之见龙卸甲》
后记
精彩书摘
《大家读大家:不必然的对等:文学改编电影》:角色动机说
哈姆雷特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了,所谓《王子复仇记》讲的,就是哈姆雷特为被叔父毒死的父亲报仇的故事。我在中学时代初次听到这个故事,以为它和中国文学中孝子代父报仇的传统故事一模一样,长大了以后才知道故事的含义绝不及此。在台大外文系念书时,老师教我们分析哈姆雷特这个角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为什么犹豫再三,迟迟不报父仇?最后虽然成功了,但自己也被杀死,他的悲剧是来自内在个性或是外在环境?然后讨论他的“恋母情结”:如果他母亲不立即改嫁给谋杀自己亲夫的弟弟的话,王子是否就不报仇了?或者说就失去一个最重要的心理动机?
角色动机说[外加一点佛洛依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是我们当年做学生时代惯用的方法,想至今仍然是中学生读此剧的切入点。然而新一代的评论家和莎翁研究专家就不这么唯此独尊了。有人开始研究莎翁剧本的来源:原是一个流传颇广的十二世纪丹麦王朝的故事。更有人把此剧和其他莎翁作品放在莎氏所处的伊利莎伯女王时代的政治环境来探讨,并凸显权力和宗教等问题,而莎翁的各个戏剧角色也成了整个时期(即文艺复兴以降)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文化史,这是美国学界所谓的“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的论点。我个人的兴趣则不在此,因为我对于英国的政治史一无所知,也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宗教信仰和“地狱观”(例如王子父亲的鬼魂从何而来?又回归何处?)毫无研究。既然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不如暂且不顾此剧的内容和哲理而谈谈演出问题。
改编之困难
莎剧的表演也是一门专门学问,和剧本的版本学同等重要。四百年来莎剧在英美演出的历史悠久,早有各代惯例,近年来的趋势是将之“现代化”:把场景和故事拉到近代或当代,最近(2001)还有一部改编的影片竟然把故事搬到当今纽约曼克顿的金融中心!如此改编之后,所有的表演已经不再是重演经典,而是创意式的引申或重塑。换言之:同样的故事,如果发生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甚至二十一世纪初的话,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哈姆雷特的个性是否因而有所改变?或仅是改穿当代服装而已?
另一个问题是舞台。十七世纪初的环球剧院(Globe Theater,专演出莎剧的剧场)是没有什么布景的,而且女角往往由男性饰演,因此影片《写我深情》(Shakespeare in Love)(1998)就大做文章了[此片值得一看再看,因为剧本有名家史塔柏(TomStopard)参与,实在写得好,内中引经据典,指涉甚多,初看时可能会漏掉],该片中的舞台就颇有仿古的真实感。这又和中国京剧的传统相似,但演出还是写实得多。近年来的舞台改编大多以这种象征性的简单布景为依归,可以发挥演技和其他视觉艺术(如灯光或荧幕视屏)的空间也更大。这就很自然地进入电影改编的范围了。
电影并非舞台,在空间的调度和运用上也较舞台灵活得多,然而电影也受时间的限制,除了少数例外:如班纳的影片,它需要在两个多小时之内把故事说完,因此在片中的“戏剧结构”也受到影响。为了让观众感到高潮起伏,不能让独白或旁枝情节(digression)太多或太长,所以难免删节原著文字。所以改编时必须拿捏得恰到好处,这并不容易。况且在语言上不能改为当代白话英语,而要沿用莎氏原来的古英文,所以更难上加难。无论如何,台词还是最重要的,不能完全被视觉影像所取代;换言之,电影的“蒙太奇”传统不见得完全用得上(当然也有例外,奥逊·威尔斯的莎剧影片如《午夜钟声》就是最好的证明)。
把这一切的因素考虑在内,我还是认为奥利花的《王子复仇记》仍然是所有改编影片中最好的经典。
……
前言/序言
后记民初的文人有一个喜欢看戏的传统,他们不单止看,更爱研究戏曲,当然也有一些人沉溺其中的,捧戏子的大有人在。到了三十年代,电影开始发展,由无声的演变到了有声,从美国的荷里活影响到了中国。舞台上的戏曲表演受到了冲击,看戏演戏都相应少了。原来喜欢看戏的人不一定改看电影,但是,许多以前不看戏的人,却被电影吸引住了。
欧梵从来不是个戏迷,却是一个影迷。他告诉我他看的首部电影是《鹿苑长春》(港译《绿野恩仇记》,TheRearling,1946),那时他一家逃难到了南京——父母带他去看的。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是格力哥利柏(GregoryPeck)。前年我和欧梵一同在家欣赏了这部片子,他感慨地说:“唉!时间过得真快,转瞬间几十年过去了,我看这电影的时候,仍然是个幼童,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老翁了!”我很喜欢这部电影,尤其是男主角的俊俏更令我钟情。欧梵的慨叹是我对他的羡慕——才几岁大的小孩,就有机会看电影,而且是一部十分好看的电影。我想这童年的兴趣,引发了他日后对电影的迷恋是其来有自的。到了大学期间,他更开始在报纸杂志里写影评,逐渐深入钻研,现在的这部书——《文学改编电影》更不是纯粹单靠兴趣而可以写成的,非要深度的学养不可。
学养这东西,需要逐渐累积下来。欧梵是个学者,他对于任何学问都持有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一般人认为电影这门子被当作消遗的玩儿而已,而他却本着追求学问的心态来看待它。几十年下来,他看过的电影可算是不计其数,对于他少年时代看过的,他可以如数家珍的告诉我,这套片子谁是导演、男女主角是谁,连情节也记得一清二楚,多年后重看、三看,更加是体验良深了。他之能把导演和演员的名字一一记得,是他有意把他们姓甚名谁刻意背诵下来的吧?
在我来说,看电影只看它的情节,遇到剧情感人的,我会泪流满脸,欧梵总在旁边安慰我说:“老婆不要哭,这只演戏而已。”我知道演员在演戏,但是我是个普通而浅薄的电影欣赏者,而他欣赏电影的功力是我无法望其项背的。他时常有意无意的跟我分析电影里的镜头如何调动,又说故事并不太重要,最重要的倒是形式的表达,这当然是有深度欣赏能力者才说得出来的话。
近年来,他每天晚上,若在家里呆着,一定看一至两出电影。他喜欢的电影并不限于荷里活电影,也有欧洲的、日本的、和香港的。而且种类繁多:言情、科幻、武打,样样喜欢,唯独不爱恐怖片,偶然也陪我看一些专给小孩子看的温馨剧情片,看见我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涟涟时,他会递来纸巾给我抹眼泪,我会不好意思的拥着他娇笑,这时候真可说是我俩的温馨时光,看完往往怀着甜蜜的心情寻梦去。
自前年开始,他答应了三联书店的李安小姐写这本书后,对电影的痴迷简直到达了走火入魔的程度。白天他沉迷于阅读文学作品,翻箱倒筐的,把与电影相关的文学原著都找出来了,晚饭后,一定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一套又一套的经典电影,有的时候,一出电影有好个版本,他无一遗漏的,全部仔细地看完,有些拷贝甚至旧得模糊不清,他照看如仪,真是乐此而不疲。我这个专为剧情而看电影的人,看完了第一套版本,已没有耐性陪他看往后更多的版本了。他一人独自欣赏,仍然看得眉飞色舞,事后絮絮不休的跟我讲解电影中的细节,然后逐字逐句的写将下来,谁说他不是一个影痴?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老影痴的观影札记。
李子玉
用户评价
最近偶然翻到一本关于文学改编电影的书,名字叫做《大家读大家:不必然的对等:文学改编电影》。虽然我并没有机会细读这本书,但仅仅从这个书名,我就已经脑补出了无数精彩的探讨。我想,这本书一定是对经典文学作品如何被搬上银幕,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不必然”的对等关系的深刻解读。比如,一部备受赞誉的小说,在改编成电影时,导演和编剧是如何在保留原作精神内核的同时,又要适应电影的叙事节奏和视觉语言的?作者是不是会深入剖析那些成功的改编案例,比如《教父》系列对马里奥·普佐小说的再创造,又或者是《肖申克的救赎》如何将斯蒂芬·金的短篇小说拓展出如此深邃的人生况味?反之,那些改编失败的作品,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了与原作的“不必然对等”?是过于忠实于原著的细节,反而失去了电影的生命力?还是为了追求商业上的成功,而大刀阔斧地删减和改动,最终失去了原著的神韵?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哲学意味,“不必然的对等”——这暗示着改编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种再创造,一种新的阐释,一种在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协商与碰撞。我甚至可以想象,作者会引用大量的理论,比如符号学、叙事学,甚至是电影美学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文学的魅力,又能领略到电影艺术的博大精深。这本书,就像是一把钥匙,能够开启我对于文学与电影之间复杂关系的全新认知。
评分读到《大家读大家:不必然的对等:文学改编电影》这个书名,我的脑海里立刻涌现出无数关于电影改编的经典与争议。我总觉得,文学作品是读者心中最私密的宇宙,而电影改编,则是将这个宇宙呈现在大银幕上的尝试。这种尝试,注定充满了“不必然的对等”。作者大概是在探讨,为何有些改编能让原著“活”得更好,甚至超越原作,比如《银翼杀手》之于菲利普·K·迪克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电影用独特的视觉风格和深刻的哲学思考,赋予了故事新的生命。而有些改编,则会让人扼腕叹塘,比如某些名著被拍成平庸之作,失去了原著的精髓,徒留一个熟悉的壳。这本书或许会剖析不同改编策略的优劣,比如是注重忠实原著的细节,还是抓住原作的精神内核进行再创作。我想,作者一定会对“对等”这个词进行深刻的辩证,它不是简单的翻译,不是一一对应的映射,而是在两种媒介之间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一种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同时,又能够发挥电影自身优势的巧妙平衡。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些经典的案例分析,无论是成功的典范,还是警示的失败,都能让我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文学改编的复杂性与艺术性。这本书,或许能让我不再简单地以“还原度”来评判一部改编电影,而是去理解它如何在新的艺术形式中,重新解读和演绎原有的故事。
评分看到《大家读大家:不必然的对等:文学改编电影》这本书的名字,我立刻联想到了那些让我反复回味的改编作品。我坚信,优秀的文学改编电影,绝不仅仅是把小说情节搬上银幕那么简单。它是一种跨媒介的对话,一种在两种不同艺术语言之间进行的“翻译”和“再创作”。“不必然的对等”,这几个字精准地概括了改编过程中的核心挑战。我相信,这本书的作者一定会详细阐述,这种“不必然”体现在何处。也许是电影需要牺牲掉原著中一些细腻的心理描写,转而依靠演员的表情和肢体语言来传达;也许是电影为了视觉上的冲击力,而对某些情节进行了戏剧化的改编;又或许,电影会从原著中提炼出某个核心主题,并围绕它构建一个全新的故事。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些鲜活的案例,比如,导演是如何在改编《傲慢与偏见》时,既保留了简·奥斯汀的讽刺与智慧,又赋予了电影独特的时代魅力。或者,当改编科幻小说时,电影如何用视觉特效来具象化那些只存在于文字中的奇思妙想。这本书,或许能让我从一个更具批判性的角度去审视那些改编电影,不再仅仅是被动接受,而是能主动去分析导演的改编思路,理解他们在这场“不必然的对等”中,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最终带来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评分《大家读大家:不必然的对等:文学改编电影》——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学术气息和探索的野心。我个人对文学改编电影的兴趣由来已久,尤其是那些能够引发我深入思考的作品。我猜这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哪些小说被改编成了哪些电影,而是会深入挖掘改编过程中那层复杂而微妙的“不必然的对等”关系。作者可能是在探讨,文学的内涵与电影的视听语言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张力?当文字的想象力遇上影像的具象化,会发生怎样的化学反应?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些经典的改编,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不同版本的电影都在努力捕捉原著中那份属于爵士时代的迷醉与失落,但每一个版本又因其导演的独特视角而呈现出不同的“对等”程度。这本书或许会分析,一些改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在“对等”中找到了创新点,比如《阿甘正传》虽然改编自同名小说,但电影对人物命运的展现方式,更具传奇色彩,而电影中的许多经典场景,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符号。反之,那些失败的改编,又是因为何种原因,导致了与原著的“不必然对等”演变成了“失联”?我期待这本书能提供一套分析框架,帮助我理解文学改编电影背后的创作逻辑,以及在不同艺术形式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对话”与“转化”。
评分《大家读大家:不必然的对等:文学改编电影》——这个名字本身就激起了我强烈的阅读欲望。我对文学改编电影一直抱有复杂的情感,既期待着喜欢的文字能以更直观、更具冲击力的视听方式呈现,又时常因为改编中的“跑偏”而感到失望。这本书的书名,“不必然的对等”,正触及了我一直以来对改编电影的困惑。我猜测,作者一定会在书中深入探讨,为什么成功的改编电影,往往不是对原著的简单复刻,而是对原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再创造。它可能是在视觉风格上,赋予了故事全新的想象,比如《指环王》系列对托尔金宏大奇幻世界的完美呈现。又或者是在叙事结构上,进行了精妙的调整,使其更符合电影的节奏和观众的观影习惯。当然,也可能是在人物塑造上,通过演员的演绎,赋予了角色新的深度和维度。但同时,书中肯定也会剖析那些改编的“陷阱”。是否过度追求原著的细节,反而让电影显得冗长乏味?是否为了迎合市场,而删减了原作中引人深思的部分,导致故事变得肤浅?“不必然的对等”,我想表达的正是这种关系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它不是一种必然的、直接的对应,而是一种充满博弈、妥协与创新的过程。这本书,也许能让我理解,为什么一部改编电影,可以拥有超越原作的生命力,也可以轻易地扼杀掉原作的灵魂。
评分"雨果写《九三年》,他一开始在设置这三个人物时,特别注意利用人类经验中最直接最可感的情感来做文章。他先划分革命者与叛乱者水火不容的阵营。朗德纳克是敌视革命的叛乱者。这时作家又设置了一个很“巧”的情节,在一次较量中,朗德纳克及其部下被革命军包围在一个塔楼里,戈万带领革命军步步逼近,要活捉朗德纳克,在最后的危急关头,朗德纳克居然侥幸逃脱,这就又埋下了巨大隐患,下次他还将卷土重来,对抗革命军。这时,在朗德纳克逃离塔楼、逃离戈万围捕之后,他突然发现塔楼上着起火来,而在火光中竟然有三个孩子的身影;远处又传来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哭喊声,在呼喊人们、呼喊上帝去救她的三个孩子。于是朗德纳克返回塔楼,从塔楼中救出三个孩子。正是由于他的返回,他被革命军抓获,成为戈万的俘虏。 "
评分这套书是家新先生推荐的,值得一看
评分評論
评分本书为作家叶兆言解读国外经典作家作品的随笔散文集,所谈论的作家既有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也有略萨、奈保尔。本文集兼具小说家的敏锐与批评家的执着,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位文学大家的私人阅读史
评分读作家深入解读国外名家作品
评分一切不过是轮回。
评分这一套书都不错,这次全买了,好好看看了。
评分寄来时候是塑封的,包装很满意
评分叙事学是文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本成果所开展的“空间叙事研究”则是此领域中新的理论方向,是目前叙事学研究中最有发展前景、最具学术潜力的领域之一。其研究目的,是对传统叙事学重视不够甚至严重忽视的叙事的空间维度或叙事作品的空间元素进行系统考察,进而对叙事与空间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属于文艺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对于叙事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对于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具有较为重大的价值。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