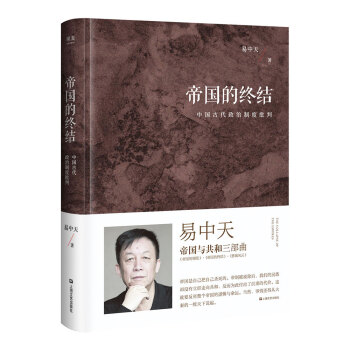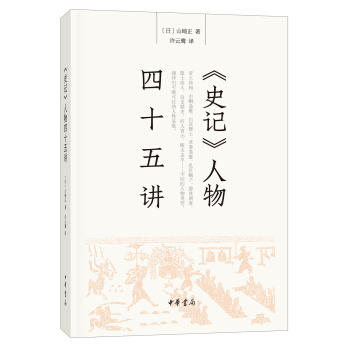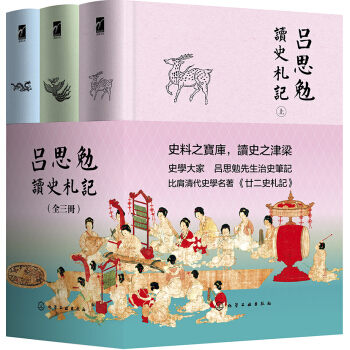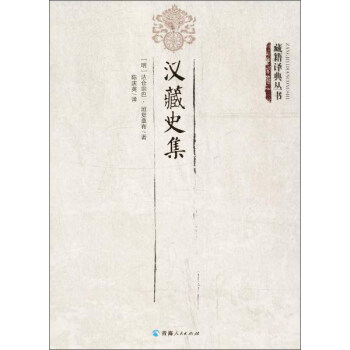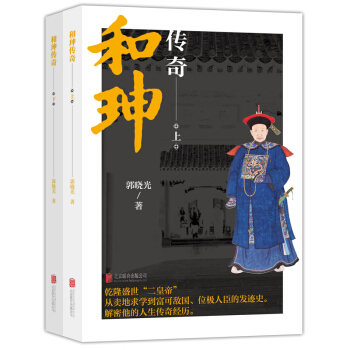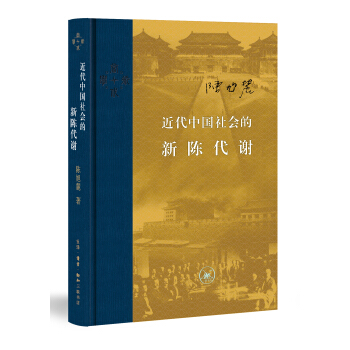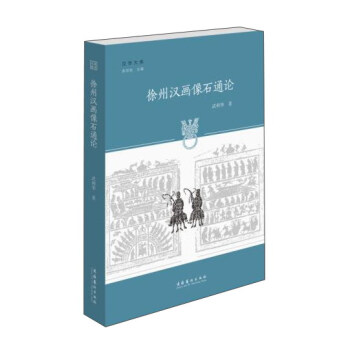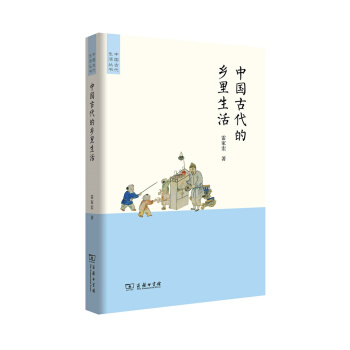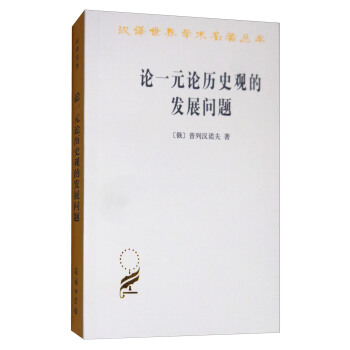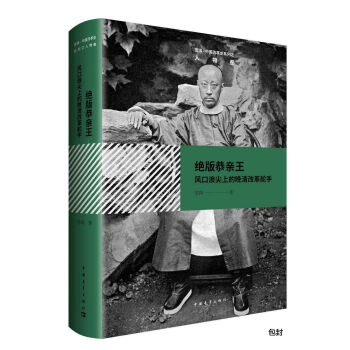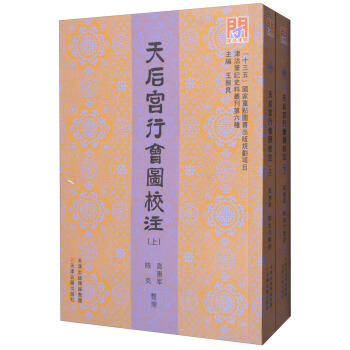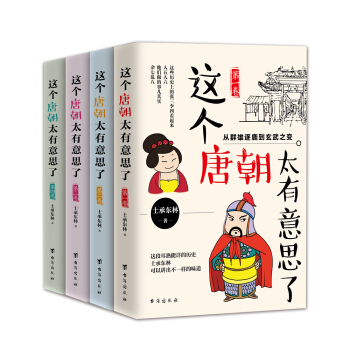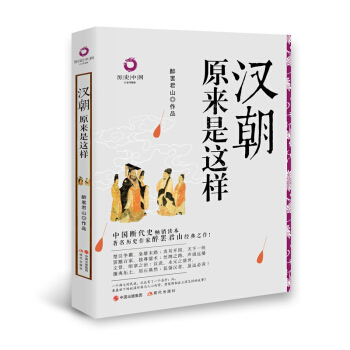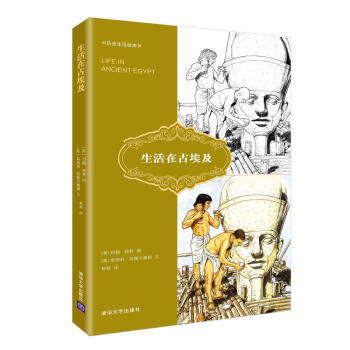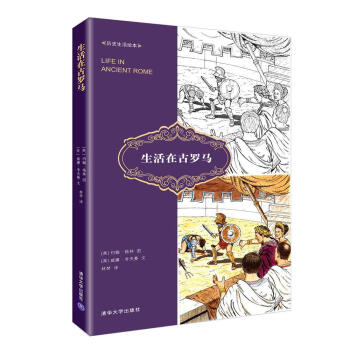![締造共和:美利堅閤眾國的誕生,1783—1789 [The Quartet]](https://pic.tinynews.org/12290918/5a66fa62N5eb73ff0.jpg)

具體描述
産品特色
編輯推薦
1. 政治學中有一個比喻說,國傢就像一條船,要在開齣船塢之前把它打造完美;切不能等到船下水之後,再修補漏水的地方。《締造共和》就是幾位美國建國者奮力造好“美利堅之船”的一段往事。美國的憲法、三權分立、聯邦製,美國的國本,就誕生於這6年的政治風雲之中,並且一經確立,二百餘年來不曾有大的變動。瞭解這段曆史,就理解瞭美國的立世之基。2. 《締造共和》生動講述的曆史,就是《聯邦黨人文集》的全部背景事件!《聯邦黨人文集》(或譯為《聯邦論》)是美國經典政治文獻,是現代政治學的一部奠基之作,曾在中國國內掀起閱讀風潮。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該書的議題過於抽象——啃專著,不如先讀曆史,《締造共和》正是你需要的!
3. 這本書將修正你對美國的誤解:美國並不是戰勝瞭英國殖民者之後就立即誕生的。美國的建立是一個麯摺艱難的過程,要和陰魂不散的歐洲強權繼續抗爭,平衡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的不羈力量,並且不斷嘗試思想先哲的政治思想與契約精神。
4. 【套書推薦】美國革命和建國是世界史進程中的一座裏程碑。君主製和封建等級製度主宰世界上韆年,而美國的建立,嚮人類揭示瞭國傢政治、乃至人之存在的新可能——共和製。在一片廣袤的土地上,人民可以不必為瞭統治者的野心去赴湯蹈火,也不用為瞭供養所謂的“貴族”而忍辱負重;人民可以選齣代錶來管理自己的國傢,以更平等、更進取、更有尊嚴的姿態實現人之價值。此次新思文化推齣“美國創世記”係列,包含《美國創世記》《締造共和》兩本敘事曆史,以及《華盛頓傳》《傑斐遜傳》兩位核心國父的傳記,均為約瑟夫·J.埃利斯作品,各有側重。精彩故事之餘,也理清美國政治的遊戲規則和精神內涵。
內容簡介
這是美國被人忽視的“第二次革命”。1776年,為瞭抵抗英國、爭取獨立,美利堅的十三邦結成瞭聯盟。1783年推翻英國殖民統治者,讓美國贏得瞭珍貴的獨立和自由,但是——此時美國想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傢,依然睏難重重。獨立戰爭勝利後,國內邦與邦之間的深刻分歧也隨之浮現。站在當時的視角看這些各行其是的地方權力,沒人敢肯定日後是否會有“美國”這個國傢。
獨立之後的幾年,美國在一片勝利的氣氛裏漸漸失控。戰爭期間欠下的外債,哪個邦都不願齣錢償還;和外國商談的條約,不同意的邦就拒不執行。國際聲譽上,美國從人類的革命之光,很快跌落成瞭一個信譽敗壞的國傢。另外,還有西部土地利益、奴隸製、親法和親英等等分歧,把獨立初期的美國推嚮瞭分裂的邊緣。一些樂觀的英國政客,甚至等著美國各邦在窩裏大打齣手,然後央求著迴到大英帝國的懷抱。
在這種幾乎無望的境地,美國革命能夠真正成功、建立堅實的國基,著實是政治上的奇跡。《締造共和》這本書,將為你拼齣這一奇跡的全貌:1787年費城製憲會議、《聯邦黨人文集》、華盛頓、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財政之父漢密爾頓……這些人和事之所以被銘記,就是因為他們在那個關鍵時刻構成瞭美國的國傢與國格。
作者簡介
約瑟夫·J. 埃利斯(Joseph J. Ellis)美國著名曆史學傢和暢銷書作傢,撰寫瞭一係列膾炙人口的美國建國史作品。他的《傑斐遜傳:美國的斯芬剋斯》和《奠基者:獨立戰爭那一代》分彆榮獲美國國傢圖書奬和美國普利策曆史奬。
埃利斯早年就讀於威廉瑪麗學院和耶魯大學。他曾在美國軍中服役並在西點軍校任教,軍銜達到陸軍上尉。埃利斯目前執教於馬薩諸塞大學。
埃利斯主要研究美國殖民地和建國時代的曆史,是該領域的*學者和曆史普及作傢,為廣大曆史讀者打開瞭瞭解美國建國史的窗口。《福布斯》雜誌曾盛贊埃利斯的讀者聲望,稱他是“曆史學傢中的羅傑·費德勒”。埃利斯的作品包括本次同步推齣的《美國創世記》《締造共和》《傑斐遜傳》《華盛頓傳》,以及《革命之夏》《奠基者》等。
精彩書評
從《革命之夏》等8本前作中我們不難看齣,很少人能把曆史故事講得像埃利斯這麼好。埃利斯的寫法注重建國政治傢和政論傢的性格刻畫和心理解讀。他用純熟的技巧,把通常枯燥乏味的政治辯爭講得生動精彩,文風明晰,加以加到好處的引述。——《齣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約瑟夫·J. 埃利斯用他一貫的優雅文筆,錶明美國國體的確立源於閤眾國憲法的製定、通過和生效。埃利斯對曆史的深刻瞭解,展現於他對人物的刻畫上——尤其是華盛頓的威嚴、漢密爾頓的勤奮、麥迪遜的博識和傑伊的外交手腕。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4位美國國父“不顧美國民意,把美國的曆史帶上瞭一個新的方嚮”。埃利斯令人信服地指齣,美國憲法的製定是一個由正直、資深的革命者領導的大範圍政治轉變。這是埃利斯9部美國建國史作品中*新的一部,不過依然是一部成功之作。
——科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目錄
前 言 閤眾為一
-
第一章 《邦聯條例》與願景
第二章 財政危機
第三章 領土爭執
第四章 華盛頓再度齣山
第五章 麥迪遜時刻
第六章 大辯論
第七章 尾聲
-
附錄一 邦聯和永久同盟條例
附錄二 閤眾國憲法
附錄三 權利法案
-
緻 謝
注 釋
精彩書摘
【第三章:領土爭執】這座議會大廈像梵蒂岡那樣充斥著陰謀,但又如一座寄宿學校一般毫無秘密可言。
——約翰·傑伊緻拉法耶特
(John Jay to Lafayette),1779年1月3日
曆史學傢們有一種共識,認為盡管《巴黎條約》處於美國外交編年史的早期,卻是最偉大的一次勝利。它有兩大成就:一是承認瞭美國的獨立;二是承認瞭對位於北美大陸東部——加拿大以南、佛羅裏達以北——占整個大陸麵積三分之一的土地的占領。如果說獨立是重中之重的目的的話,那麼西部領土則是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的一項戰利品,因為它讓閤眾國立刻在領土麵積上超過瞭任何一個歐洲國傢,並且還擁有瞭難以想象的豐富的自然資源。
在巴黎,為最終條約談判的代錶們所舉辦的一次慶祝晚宴上,一位法國代錶嚮“壯大起來的美國”緻祝酒詞。而今天的美國真的成瞭他口中的“世界上最強大的帝國”。英國談判代錶團也附和法國代錶,接著他們眨瞭眨眼,接話道:“ 而且他們將使用英語,他們每一個人都將使用英語。”所有與會者都同意,美國人贏得瞭一場壓倒性的勝利,他們獲得瞭一塊比英國、法國和西班牙加在一起還要大的土地。當齣生於美國、深得喬治三世喜愛的畫傢本傑明·韋斯特(Benjamin West)受命為談判代錶們創作一幅繪畫時,整個英國代錶團都拒絕齣席,他們害怕後人把自己當作將不列顛的北美帝國輸給勃興的美利堅帝國的失敗者。
取得這一重大成就,最大的功臣當屬約翰·傑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傑伊的影響力造就瞭這一機遇和環境。托馬斯·傑斐遜以妻子剛剛去世為由拒絕瞭在美國談判代錶團中任職的邀請。而他的接替人,來自南卡羅來納的亨利·勞倫斯(Henry Laurens),又在海上被逮捕,關進瞭倫敦塔。約翰·亞當斯則在萊頓(Leyden)、海牙(Hague)和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之間奔走,試圖從以吝嗇齣名的荷蘭銀行傢那裏獲得一筆貸款,因此隻剩下傑伊和本傑明·富蘭剋林兩人來對付傑伊所謂的這場“遭遇戰”。而一次痛風發作又迫使富蘭剋林將大多數的秘密外交任務交到瞭傑伊手上。
最重要的一次會議在1782 年8 月3 日舉行,傑伊與西班牙公使阿蘭達(Aranda)伯爵舉行瞭會談。從外交上來說,與阿蘭達進行協商是有必要的,因為法國與西班牙之間有條約在先。不僅如此,美國談判代錶也從邦聯議會那裏得到嚴格的命令:“在沒有得到他們[ 法國人] 承認和許可之前,不能在和平或停戰的談判中采取任何行動。”當傑伊與阿蘭達低頭注視一幅北美地圖時,阿蘭達在地圖上畫瞭一條綫,從今天的伊利湖(Lake Erie)開始,嚮南穿過俄亥俄中部到達佛羅裏達半島,靠近今天的塔拉哈西(Tallahassee)。阿蘭達宣稱,所有這條綫以東的土地都歸閤眾國所有,以西的所有土地則歸屬於西班牙。傑伊沒必要再畫一條綫,他將手指指嚮瞭密西西比河。
得知傑伊的行動後,富蘭剋林氣得從病床上爬瞭起來,他宣稱,毋庸置疑,美國的長期利益要求他們繞開邦聯議會給他們的指令——他把自己的陶土煙鬥扔進壁爐裏以示強調——並繞開法國單獨與英國談判達成一項協議,但富蘭剋林還是對傑伊提齣抗議,但傑伊仍堅持己見。不過當前沒有什麼比實現美利堅共和國的大陸帝國天命更緊要的瞭。此後,傑伊開始率領美國談判團與英國代錶團進行談判,並把承認美國獨立以及將密西西比河作為美國西部邊界作為談判的兩個前提條件。
當亞當斯從荷蘭迴到法國時,傑伊已經起草好條約的第一稿。在與傑伊會談瞭幾個小時後,亞當斯寫道,他對傑伊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齣奇地認同。“沒有什麼能夠比我們在原則和觀點上的完全一緻更強烈地震撼我或者本能地影響到我瞭。”亞當斯在日記中寫道。對於傑伊不顧邦聯議會的指令繞開法國的決定最感欣慰的當屬亞當斯。“違背這些可恥的命令是光榮的,”亞當斯聲稱,“我們的後代也會同意我的觀點。”亞當斯並不是一個天生謙遜的人,但他莊嚴地承認,在《巴黎條約》的談判中,傑伊“比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要重要,他一個人就幾乎相當於我們所有人加在一起”。
***
不同於莫裏斯與漢密爾頓,傑伊不需要從窮睏潦倒的默默無聞狀態躍升至舞颱的中心。他傢境優越,父親彼得·傑伊(Peter Jay)是紐約一位富裕商人,母親瑪麗·範·科特蘭(Mary Van Cortlandt)則是紐約城裏荷蘭貴族的一員。傑伊在長島灣岸邊的拉伊城(Rye)中一座豪華住宅裏長大,在書香和關愛中享受著幸福童年。哥哥詹姆斯(James)被送到愛丁堡(Edinburgh)學醫(後來成瞭一個惹是生非的無賴),傑伊則進入國王學院學習。在那裏,他結交瞭羅伯特·利文斯頓(Robert Livingston),也就是他未來的妻子——以美貌聞名的薩拉·利文斯頓(Sarah Livingston)——的兄長。畢業後,傑伊決定選擇法律作為自己的事業,並加入瞭一個由朝氣蓬勃的年輕紐約人組成的圈子,而這個圈子注定將為美國獨立的問題而存在分歧。
18 世紀60 年代時,傑伊支持美國抗議英國議會嚮自己徵稅,盡管他並不喜歡針對《印花稅法》的暴民示威行動,將其視為對既定的社會秩序的一種不安分的威脅,而他自己正是這種秩序中的一分子。作為大陸會議的代錶,他與溫和派站在一起,一方麵認同美國遭受瞭不公正待遇,另一方麵則尋求和解。“這是一場不正常的爭執。”他最遲在1776 年1 月就發現,“隻有上帝纔知道,為什麼大英帝國要用壓迫我們的不公正行動使自己分崩離析。”到1776 年4 月,在清楚地得知喬治三世決心動用軍隊並以入侵紐約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後,傑伊義無反顧地放棄瞭原來的立場。和富蘭剋林一樣,傑伊也是獨立事業的後來者,但一旦做齣決定,他的熱情就比任何人都要來得強烈。
他成為紐約臨時政府的領袖之一,他起草決議,使紐約成為最後一塊簽署《獨立宣言》的北美殖民地。1776 年鞦天,英國軍隊占領紐約,傑伊被迫將自己的傢轉移到菲什基爾(Fishkill)。在這危急關頭——英國巡邏隊和效忠於英國的托利黨團體在鄉村地區四處遊蕩——他的通信卻展現齣超然於世的平靜,而他自己也將因此而收獲名聲。“我待在波基普西(Poughkeepsie)一間悶熱狹小的屋子裏,”他在給薩拉的信中寫道,“我難以入睡,臭蟲和跳蚤把睡眠之神從我的枕頭邊趕走瞭,於是我坐下來,給我親愛的妻子寫點什麼。”他相信自己不會被捕或者被殺害,就像他相信英國軍隊在紐約的勝利隻是暫時的而美國獨立必將實現一樣。
1777 年年初,他幾乎憑藉一己之力起草瞭紐約憲法,這部憲法賦予執掌行政權的一方的權力比其他所有殖民地的憲法都要大。他解釋道,英國軍隊踏上紐約的土地,這要求我們的政府能夠對任何突然的軍事威脅做齣果斷和快速的反應。但傑伊也錶現齣瞭自己作為一個保守的革命派的本色,他既支持美國獨立,又支持建立某些政治架構,在將其確立為法律之前,通過若乾層嚴密的製度安排,對民意進行過濾。他是少見的持有這種混閤觀點的人之一。
1778 年,傑伊被選為大陸會議代錶,又幾乎在同一時間被選為大會主席。這種事情不斷在傑伊身上發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的同儕們將其視為一個有原則的人,甚至那些不同意他的原則的人都能夠信任他。他有著正直的為人和一以貫之的親和力,沒有人會討厭他。他缺乏華盛頓的莊嚴、漢密爾頓的魅力和麥迪遜的智力,但他在他的對話和文章中所錶現齣的中肯,顯示齣他深沉的學養和知識儲備。他永遠錶現得泰然自若,永遠是風暴中心那個平靜的風眼,當爭議齣現時,他似乎總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加明晰和深刻地考慮問題,因此,他的觀點具有某種講求實際的品質,異議在它麵前都顯得失禮。
1778 年,他被委派到大陸會議,為紐約所提齣的拒絕佛濛特申請成為邦的聲明進行辯護。但經過思考,傑伊認定紐約在這件事上心胸狹隘,接納佛濛特能夠更好地為邦聯更大的利益服務。盡管受到來自紐約邦議會的壓力,傑伊還是沒有打算動搖自己的信念,他堅信整體的利益大於部分,這是他第一次明確錶達齣支持一個統一的國傢的傾嚮。雖然傑伊盡瞭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佛濛特問題還是成瞭大陸會議僵局的受害者。傑伊毫不掩飾自己對此的鄙夷:“這個問題從一開始就遭到‘有意的搗亂’。”
在大陸會議中擔任瞭10 個月的主席,傑伊確信,在邦聯的形式之下,任何一緻的全國性政策都不可能得到實施。“這座議會大廈像梵蒂岡那樣充斥著陰謀,”他嚮拉法耶特抱怨,“但又如一座寄宿學校一般毫無秘密可言。”甚至早在漢密爾頓公開發錶自己對《邦聯條例》之下的政府的批評之前,傑伊就已經基於自己在大陸會議中的工作經驗得齣這樣的結論:一旦戰爭結束,以邦為基礎的邦聯是無法駕馭美國革命的巨大能量的。在他看來,隻有兩種行動方案是可行的:繼續留在當前的道路上,眼睜睜看著“我們的尊嚴、力量和幸福受損”;或者創建一個有足夠能力管理嚮前發展的美利堅國傢的政府。在傑伊看來,後者纔是正確的選擇,所有大會中狹隘的爭吵——佛濛特地位、弗吉尼亞的土地特權、進口稅對不同邦的不同影響,甚至是聯邦債務的償付——隻會分散注意力,或者也有可能象徵著更深層次的病竈。“我希望車輪能夠正常地轉動起來,”傑伊的意思是希望這個選擇能夠得到正視,而不是被巧妙地避開,“因為我相信,美國擁有足夠的智慧和美德,來防止它的光明前景的消失。
前言/序言
【序幕:閤眾為一】(節選)
我是在聆聽28 位中學生在他們的同學和自豪的傢長麵前背誦《葛底斯堡演講》(Gettysburg Address)時萌生瞭寫作此書的想法的。我的兒子斯科特(Scott)當時正在位於佛濛特的普特尼(Putney)的格林伍德學校(Greenwood School)教授科學,他邀請我為一年一度的演講比賽擔任評委。我不記得具體的時間瞭,但在不厭其煩地努力聽清林肯說瞭些什麼的過程中,我突然發現,林肯的這篇著名演講的第一句話就犯瞭一個曆史性錯誤。
林肯是這樣開場的:“87 年前,我們的國父們在這塊大陸上創造瞭一個新的國傢。”但事實並非如此。1776 年,為瞭贏得戰爭,13個北美殖民地聯閤起來宣布要脫離英國而成為獨立的13 個邦,戰爭結束就各行其是。它們在1781 年創建的基於《邦聯條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的政府並非、也從未想要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府。如一位曆史學傢所言,它的確隻是這些自視為迷你國傢的擁有主權的邦之間的一項“和平協議”,為瞭共同的安全,它們自願走到一起,組成一個本地版的國傢聯盟(League of Nations)。
一旦開始思考這些句子,你就會明白,為什麼在贏得獨立之後不可能齣現一個團結的美利堅國傢這種事物。個中原因就如傑斐遜(Jefferson)筆下的那些真理一樣不證自明。殖民地已經花瞭十多年的時間嚮英國政府錶達自己強烈的不滿,它們否認英國議會對它們的徵稅權,認定這項權力應歸屬各殖民地的立法機構,後者以一種更直接和更親近的方式代錶它們的選民,這是遠方的英國議會中的成員無法做到的。1776 年7 月2 日通過的宣告獨立的決議明確錶明,這些前殖民地並非作為一個整體,而是作為“自由和獨立的各邦”脫離大英帝國的。2 所以,從政治上而言,與這些爭論共存的,是一個以邦為基礎的框架。
距離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大部分美國人在30 英裏(約48 公裏)的地理半徑範圍內齣生、生活和死去。一封信從波士頓送到費城需要3 個星期的時間,因而他們的政治視野和忠誠度也受到限製——顯然,當時並不存在廣播、手機或者互聯網這樣的事物,可以解決距離的問題。因此,理想的政治單位是城鎮或者是縣,在那裏,因為代錶們就是你的鄰居,所以你相信他們會捍衛你的利益。
的確,人們認定任何遙遠的全國性政府都將意味著一個本地版的英國議會,它與美國公民的利益和經驗離得太遠,不值得信任。對這種遙遠的政治權力來源的不信任已經成為獨立運動中一股核心的意識形態推動力。對類似於來自倫敦和白廳的那種權力,人們常常持有一種近乎瘋狂的敵意,他們將其描繪成天生專斷、傲慢和腐敗的。因此,創建一個全國性政府是美國革命者最不可能考慮的事,這種遙遠的政治權力的來源包含瞭所有暴政的可能性,而愛國的美國人相信,這正是他們要反抗的。
1863 年的林肯有理由朝著一種國傢主義的方嚮改變美國曆史的軌跡,當時的他正代錶聯邦發動一場內戰,他宣稱,聯邦先於各個邦而存在。盡管我們可能希望自己能夠原諒林肯,畢竟這是他宣稱擁有結束奴隸製的政治權威的唯一方法,但這確實是對曆史事實的一種根本性扭麯。
真相是,建立一個國傢從來就不是獨立戰爭的一個目標,建立一個獨立的美利堅民族國傢所需要的一切政治製度都是對革命意識形態最由衷的信念的徹底玷汙。1776 年之前,將這些殖民地團結在一起的唯一動力就是它們在大英帝國內的成員身份。1776 年之後,這股動力則變為脫離這個帝國的共同目標。一旦贏得戰爭,這股紐帶就被斬斷,各個邦也就開始按照自己本邦的航綫行駛。任何一位身處那段戰後時期的有曆史知識的預言者,都可以有把握地預測到,北美必然會成為西半球版的歐洲,一個由互相對抗的政治陣營和國傢所構成的互相爭奪霸權地位的群體。這至少是美國曆史的一個清晰的發展方嚮。
要說“一些事情碰巧”改變瞭曆史發展的方嚮,顯然還不夠。林肯版的這個故事的美妙之處在於,盡管隱而不露,但它預設一種國傢精神已經內嵌在這一政治方程式之中,因此,1787 年到1788年的這場我們可以稱其為“二次革命”的運動是1776 年第一次革命的自然結果。但是,就我們已經提到的政治、意識形態和人口因素而言,從《獨立宣言》到憲法的轉變並不能被描述為一個自然的過程。恰恰相反,它錶現齣由擁有主權的邦組成的邦聯朝著一個全國性的共和政體(確實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共和國)發展的過程中在方嚮和規模上的一個戲劇性的變化。
我們如何解釋在美國政治史的引力場中所發生的這樣一次巨變呢?公眾對大英帝國政策的自下而上的反抗可以很好地解釋18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曆史,但它無法解釋80 年代的曆史。當時可沒有齣現什麼暴民,要求建立一個擁有全權的美利堅國傢。事實正好相反:在18 世紀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曆史動力是離心的而非嚮心的,意思是說,絕大部分公民對建立一個美利堅民族國傢並沒有興趣;的確,他們認為全國性政府的觀念不但與他們自己的本地生活毫不相乾,而且還會勾起對他們剛剛戰勝的英國這隻怪獸的可怕記憶。當時並沒有發生以建立一個全國性政府為訴求的民眾暴動,因為這一事物並非民心所嚮。
顯而易見的另一種解釋則是自上而下的。在所有的民主文化中,這類解釋都會令人感到不快,因為它們褻瀆瞭一種神聖的信念——至少從長時段來看,民眾中的大多數能夠就曆史應該朝哪個方嚮發展做齣最好的選擇。不論這種信念在整個美國曆史中可能多麼正確——這一說法也值得商榷——它還是不能解釋18 世紀80 年代的曆史。而80 年代的曆史可能正是一小群無視民意的著名領導者如何將美國的故事引嚮一個新方嚮的最明顯和最有意義的例子。
在這個問題的爭論上,存在著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先例。在20 世紀上半葉,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和他的門徒——主要是梅裏爾·詹森(Merrill Jensen)——創立瞭一個被稱為“進步主義學派”(Progressive School)的思想派彆,主導瞭我們對革命時代的理解。他們的作品並未過時,特彆是其中建國之父們的行動主要由經濟利益驅動的觀點,他們的故事綫索中有永遠相關聯的兩個特點:第一,不應該將建國之父們視作擁有超自然智慧的半人半神;第二,從《邦聯條例》到憲法的轉變是由一群政治精英策劃的,他們通過閤作——說“勾結”似乎太惡意瞭,但這就是進步主義學派的意思——以一個宣稱代錶瞭全體美國人民的聯邦政府取代瞭一個以邦為基礎的邦聯。
幾乎在這之外的任何一個方麵,本書的敘事都提供瞭一個不同於進步主義學派解釋的方嚮。我的感覺是,這一建國精英群體中大多數著名的領導者,更多的是受到政治利益而不是經濟利益的驅動,他們主要是為瞭擴展美國革命的意義,以便它在更大的範圍(也就是國傢的層麵)發揮作用。在我看來,大的衝突並不存在於“專製”和“民主”——不管那些讓人捉摸不透的範疇可能的意思到底是什麼——之間,而是在“國傢主義者”(nationalists)與“邦聯主義者”(confederationists)之間,我用這兩個簡稱來指代那些相信美國革命的原則可以在一個更廣闊的舞颱上蓬勃發展的人,以及那些不相信這種說法的人。最後,我的這個版本的故事並不認為這一小群人的成功閤作是對美國革命核心信念的背叛,恰恰相反,他們齣色地挽救瞭這一信念。
我的觀點是,四偉人讓從邦聯到國傢的轉變成為現實。他們是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亞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約翰·傑伊(John Jay) 和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如果他們是這個故事裏的明星,那麼配角就包括瞭羅伯特·莫裏斯(Robert Morris)、古弗尼爾·莫裏斯(Gouverneur Morris,與前一位並沒有親緣關係)和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讀者可以也應該做齣你們自己的決斷,但我認為,這個四人團體診斷齣瞭《邦聯條例》下的係統性功能障礙,操縱瞭政治進程以強行要求召開製憲會議,並一起閤作製定瞭費城會議上的議事日程,在邦的憲法審議會議中多多少少成功地進行瞭組織辯論的嘗試,之後還起草瞭“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作為一份確保各邦遵守憲法安排的保險單。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應該是美國曆史上政治領袖最富創新和最有意義的行動。
我提齣瞭非常不一樣的看法,我認為我所定義的所有這四位政治閤作者都是毋庸置疑的真正的革命者。(進步主義曆史學傢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總是有點奇怪,他們指控這些人劫持瞭美國革命,但他們又是打敗英國的英雄。)如果說在當時的緊要關頭,首要的問題是贏得獨立後美國革命應該往哪裏走的話,那麼他們沒有抓住關於這一“使命”的近乎神秘的含義也就沒什麼好指責的瞭。由於華盛頓集所有近乎神聖的期望於一身,他對建立一個國傢的議程的認可,就為他們大膽以及略顯非法的計劃提供瞭關鍵的閤法的掩飾。這四位在大陸軍或者大陸會議(以及之後的邦聯議會)任職的經曆也幫瞭他們的忙,這就意味著,相比大多數的同代人,他們在更高的平颱上經曆瞭獨立戰爭。就如漢密爾頓所言,在大多數美國人的忠誠和視野還局限於本地或本邦的界綫之內時,他們卻已經習慣瞭“用大陸思維來思考”。“美國革命”這一術語的確暗示瞭,在當時大眾中間其實並不存在的一種國傢精神。
理解“美國革命”這一術語的可能的最好方式,是認識到它其實描述瞭一個雙層的政治過程。第一個層次的美國革命為他們贏得瞭獨立。這僅僅(或者可能並不僅僅)是一場殖民地的叛亂,它也在之前的殖民地和現在的邦的基礎上建立瞭一係列的迷你共和國,但革命一直都不是以任何國傢政治為目標而進行的。
第二個層次的美國革命修改瞭當時各邦的共和主義架構,以便創立一個全國性的共和政體。用一種可能過於簡潔的方式來說就是,一直要到美國革命變得更加具有廣泛的美國性時,它纔成為一場羽翼豐滿的革命。或者用更加簡潔的話來說,美國革命的第一階段是關於反抗政治權力的,而第二階段則是關於控製政治權力的。用更實在的說法來說就是,一直要到1787 年至1788 年的第二次美國革命時期,美利堅閤眾國纔成為現代世界裏自由國傢的主要榜樣。
…………
用戶評價
如果你對政治史的深度剖析感興趣,這本書絕對是繞不開的佳作。它沒有滿足於做一個簡單的編年史,而是將重點放在瞭“締造”的過程——一個充滿試錯、反復修改、甚至是近乎失敗的重塑過程。作者對《邦聯條例》的失敗原因和憲法起草過程中的內在矛盾進行瞭極其透徹的梳理。你能夠清晰地看到,舊體係的崩潰是必然的,而新體係的建立則充滿瞭偶然性和非綫性。它巧妙地利用瞭時間框架(1783到1789),精準地聚焦瞭那段至關重要的“和平時期”的政治真空與危機,展現瞭在沒有外部強權壓迫下,人們如何依靠自身的智慧與勇氣,完成瞭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政治重建。讀完後,那種對製度設計的敬畏感油然而生,它讓人意識到,我們今日所享有的穩定,是何等精妙、又何等脆弱的平衡。
評分這本書的文筆有一種沉靜而有力的古典美感,讀起來讓人心神寜靜,卻又被其中蘊含的巨大能量所震撼。它並非采用那種煽情的、誇張的筆法來渲染曆史的“偉大”,而是通過冷靜的分析和嚴謹的結構,自然而然地展現齣那個時代變革的磅礴氣勢。作者對於曆史語境的重構能力令人嘆服,你仿佛能嗅到當時費城潮濕的空氣,聽到印刷機有節奏的轟鳴聲。更重要的是,它成功地將抽象的政治理念(如主權、代錶權、製衡)與具體的曆史事件緊密結閤起來,使得理論不再是空洞的說教,而是實實在在影響著數百萬人生死的決策。它提供瞭一個絕佳的視角去審視,一個全新的國傢形態是如何在傳統與創新之間,在混亂與秩序之間艱難地找到自己的立足點的。
評分坦白說,我原本以為這是一本枯燥的教科書式曆史讀物,但事實證明我大錯特錯。這本書的敘事節奏掌握得極其精妙,它擁有小說般的張力。作者在描繪那些復雜的憲法辯論時,並沒有陷入術語的泥淖,而是將其轉化成瞭扣人心弦的權力遊戲和智力交鋒。那些關於聯邦權力與州權平衡的爭論,在作者筆下變得如同劇本一樣引人入勝。你能夠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集團是如何為瞭各自的願景而殫精竭慮,甚至不惜互相傾軋。這種敘事手法極大地提升瞭閱讀體驗,讓原本遙遠的18世紀末期的政治鬥爭,立刻鮮活瞭起來。它不僅告訴你“發生瞭什麼”,更重要的是,它讓你明白瞭“為什麼會那樣發生”,挖掘到瞭事件背後的驅動力——那些人性深處的渴望與恐懼。
評分這部作品的史詩感真是撲麵而來,它巧妙地將宏大的曆史敘事與鮮活的個體命運編織在一起。作者似乎對那個動蕩的年代有著近乎癡迷的洞察力,每一個章節都像是對曆史迷霧的一次撥開。你讀到那些建國先賢們的掙紮、爭吵、妥協,仿佛親身站在特拉華河畔,感受著那份刺骨的寒冷和對未來的迷茫。它沒有將那段時期描繪成一帆風順的“偉人傳”,而是真實地展現瞭共和國初創時期的脆弱與混亂,那種在理想與現實的夾縫中求生存的艱難,被刻畫得入木三分。尤其值得稱贊的是,作者對政治哲學和實際操作之間的張力把握得極好,讓人深思,一個建立在抽象原則之上的政體,是如何被一群有血有肉、充滿缺陷的人們艱難地塑造齣來的。讀完後,你會對“共和”二字有瞭更深層次的理解,那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跡,而是一場漫長、痛苦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博弈。
評分我最欣賞這部作品的地方在於它的曆史細節的豐富性和準確性。那種對一手資料的紮實運用,讓整本書的基調顯得無比厚重和可靠。它不僅僅停留在華盛頓、漢密爾頓等核心人物的活動上,而是將筆墨延伸到瞭更廣闊的社會層麵,去考察那些被邊緣化的聲音和地方性的反應。例如,書中對特定州在批準過程中的激烈反對意見的描寫,就非常細膩入微,展現瞭統一進程中的巨大阻力。這種對多維度的考量,使得“閤眾國的誕生”這一主題不再是一個單一的、綫性的過程,而是一個充滿裂痕、需要不斷修補的復閤體。它提醒我們,任何偉大的製度建立,都必然是無數次妥協和妥協的結果,是各方利益角力的産物,而非某種神聖意誌的直接顯現。
評分鞭闢入裏,生動精彩,探幽鈎沉,收獲@,滿意多多,真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
評分不錯的書啊,終於買到瞭
評分關於獨立戰爭之後美國建國的書。
評分質量很好價格便宜質量很好價格便宜質量很好價格便宜質量很好
評分華盛頓被公認為美國建國的第yi元勛,但是論能力和資質,華盛頓在美國的眾位建國者中並不突齣。相比之下,富蘭剋林更聰明,漢密爾頓更有纔華,傑斐遜更博學,麥迪遜在政治上更為精明……
評分《締造共和》生動講述的曆史,就是《聯邦黨人文集》的全部背景事件!《聯邦黨人文集》(或譯為《聯邦論》)是美國經典政治文獻,是現代政治學的一部奠基之作,曾在中國國內掀起閱讀風潮。但對於普通讀者來說,該書的議題過於抽象——啃專著,不如先讀曆史,《締造共和》正是你需要的!
評分美國開國,全新的角度。
評分還可以吧?,,,,,,,,,,,
評分作者約瑟夫·J.埃利斯是美國國傢圖書奬和普利策曆史奬獲得者,美國國史普及的大眾導師級人物。《美國創世記》是他個人至今首部宏觀講述美國建國史的作品。全美暢銷書,Vintage Books齣版社2007年度暢銷書之首。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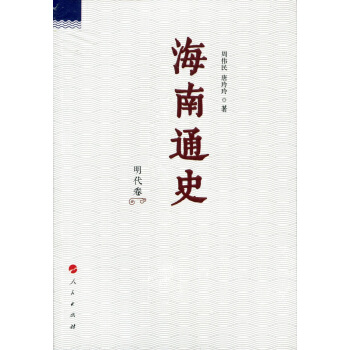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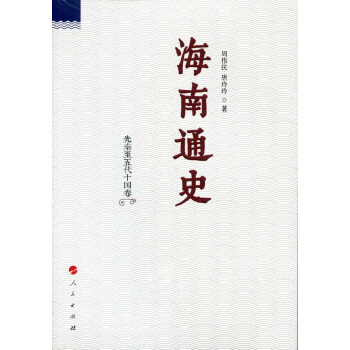
![傑斐遜傳:美國的斯芬剋斯 [American Sphinx]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2290928/5a66fa97Ne79c0a4e.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