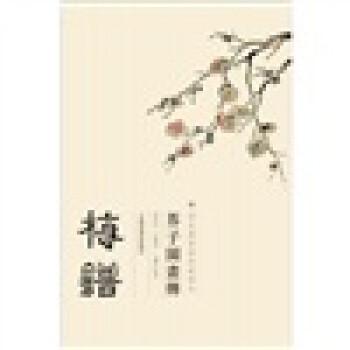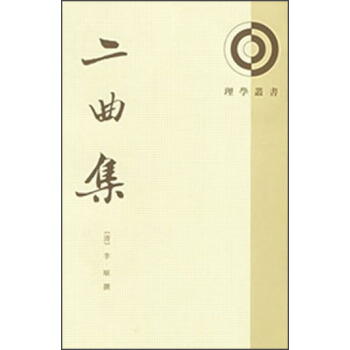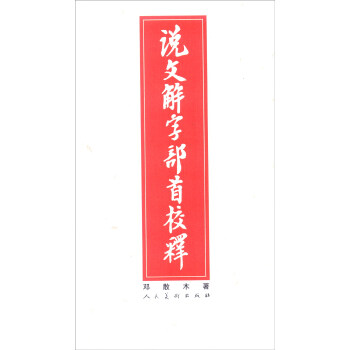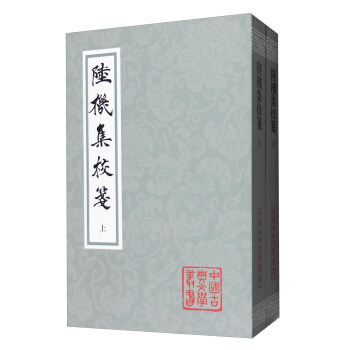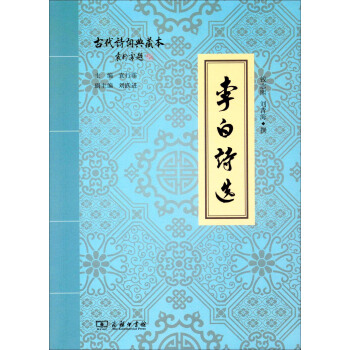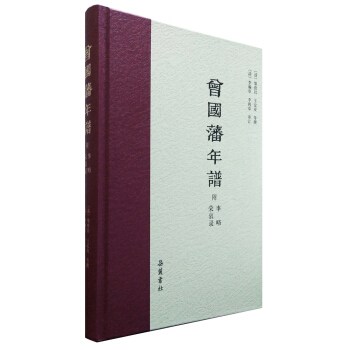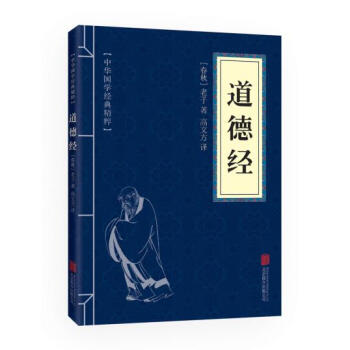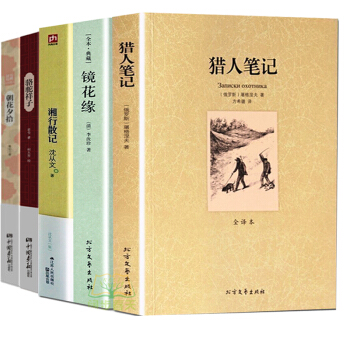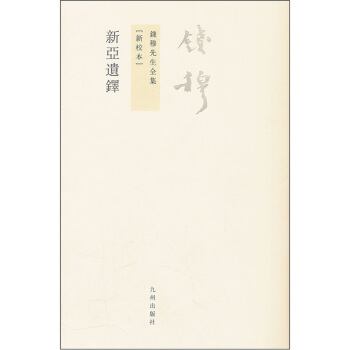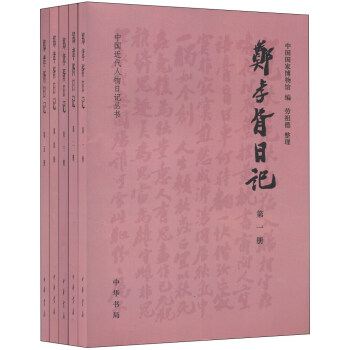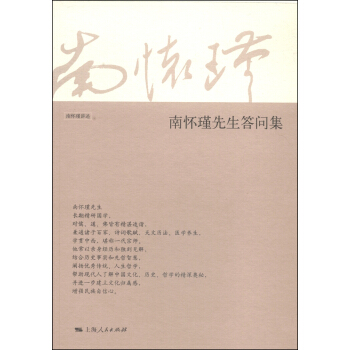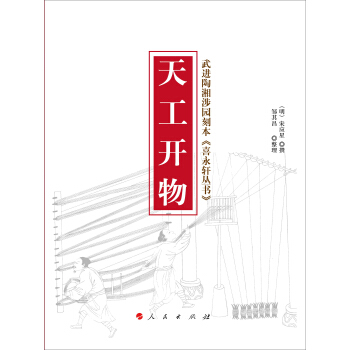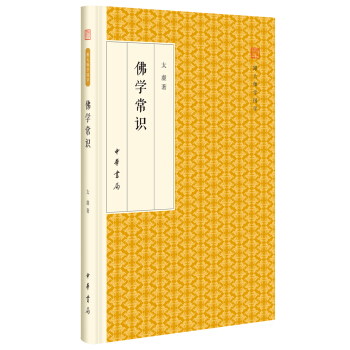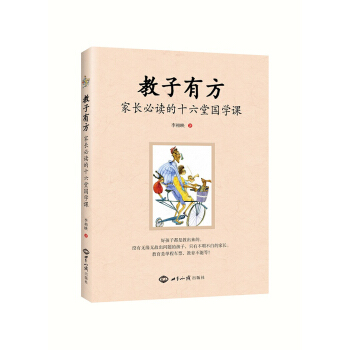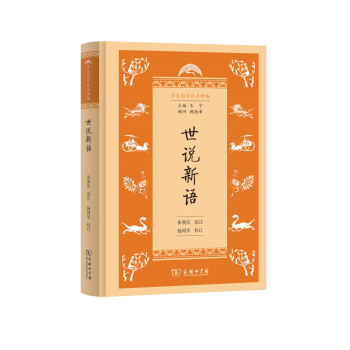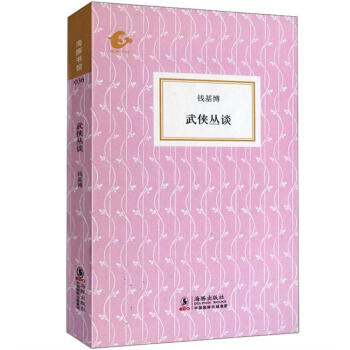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武俠叢談》選錄《技擊餘聞補》二十六則,《武俠叢談》七則,《神州十二軼事》十一則,以及兩個散篇《魏鐵三傳》和《近世遊俠三君傳》,內容雖多偏於武俠類,但足以展示錢基博文言小說的獨特魅力。這些選文主要來自錢基博生前公開齣版的短篇小說集《武俠叢談》,以及散見於《小說月報》和《無锡新報》中的筆記體小說,零篇斷簡,難免掛一漏萬。此外,錢基博還有一些文言小說,限於篇幅,隻好割愛。《武俠叢談》點校時,除瞭文字上化繁為簡,並將舊式標點改為現行標點外,鑒於民國時期文言著述通例,集中篇章不論長短,概不另行分段,以見原貌。
目錄
技擊餘聞補竇榮光
鄒姓
甘鳳池
閩僧
某公子
秦大秦二
莫懋
南楊北硃
範龍友
清江女子
馬永貞
堠山農夫
梁興甫
石勇
僧念亮
王子仁
嘉定老人
庖人
李漁
戴俊
履店翁
鬍邇光
白太官
禿者
三山和尚
蔣誌善
武俠叢談
張大三
老鏢客
孫二官
硃三寶
潘五先生
環秀庵僧
王遂
神州十二軼事
剋寶橋
療貧
張勝
錯死
懷璧
手杖
葉成忠
張蔭桓
什都喀共和國
某將軍
王老人
散篇
魏鐵三傳
近世遊俠三君傳
附錄
《武俠叢談》序惲鐵樵
《武俠叢談》跋錢基博
精彩書摘
竇榮光無锡竇榮光,清道鹹間大俠也。巨膊廣顙,為人甚魁碩有力。飯以銅箸,長纔盈尺,然持擊刺人,無不中要害,雖壯夫立蹶,頗以此自雄。挾伎遊山左。山左地處南北衝要,民情佼桀多業盜,往往張肆僻地,誘過客宿,伺夜半殺之,而取其貲,無得脫者,土人謂之黑店。榮光作客久,頗曉其情僞,能刺得黑店所在,僞宿,伺有變,輒設計誅盜而火其居。如是者非一矣,輒未嘗遇害,頗輕盜,為無足當意。一日,道泰山下,日曛,睹當路有肆,心異其僻處而無畏盜,意黑店也。就宿焉。人其肆,見門左一老叟箕踞計櫃,須雪白蔽胸前,一目似眇,而發齒盡脫落,涎流頤外,語模糊不可辨,疑老病不任事。傭夥數人,趨走侍客,似亦無大異人者。遂道榮光人視。僅二室,門東西嚮。西室兩女子居之,長者纔二十許人,幼者甚稚齒,當不逾年十四五,燕音,度其舉止,似類繩妓湖海賣伎者。東室已居僧一,狀頗矯健。榮光男子,與僧俱。捨既定,傭逐問客飯未。女子言:“道食不斯須,可毋飯。”轉問東室客。僧曰:“肉十斤,麵倍。”榮光半僧食。傭具如二人指。僧且食且目視榮光,久之曰:“齣傢人誠自慚善飯,抑客食何多?”榮光漫應日:“半和尚耳。”僧曰:“客頃知危乎。”榮光瞿然曰:“信黑店乎?然似絕無武勇者。”曰:“君不見計櫃一老翁?此劇盜。甚非細敵也。”榮光乃甚自誇詡曰:“雖非細敵何害,予殲盜多矣,顧怯一殘癃老憊之垂斃叟乎?”僧笑曰:“客故非常人,然今夕無強與人事乃佳。”榮光殊疑勿信,然察僧似伉勇齣己上而言若此,心不能無動。既寢,竟不能成寐。而僧寢鼾自如。夜半。大風起戶外,戶震撼有聲。僧寤,一躍離床起,俯戶隙窺久之,掖榮光起曰:“客視之。”視之,他無所睹,惟見庭中光縷縷閃闔似電,剽忽不可端倪,蓋劍光也。然後知適所聞者,乃有人急運劍疾舞成風。心則大驚。僧推倒室後垣齣走,榮光亟隨僧齣,而垣外復圍石墉,旁山甚高。僧履險騎危疾躍腧墉齣矣。榮光隨躍起,離墉巔纔尺有咫,墜下。再躍不能上,危急間,忽頃所見西室稚齒女奔走自後至,疾飛一足蹴其臀,乃得乘勢騰空起越齣。僧在墉外待已久,咎曰:“客頃何駑!”榮光勿復敢齣聲,挾僧走數裏。僧揉登道旁大樹,榮光隨上,忽白光閃逐似金蛇自後追至。榮光股栗幾墜地,乃亟閉目抱樹柯伏勿敢動。僧探懷齣一鐵鉢,遙逆光來所擲擊,光倏定,而盜叟首已持少女手中,倒挽其須矣。僧乃摯榮光下見女,則西室二十許長女也。於是僧勸榮光歸甚力,曰:“客不量敵強弱,徒自大。勿歸,必喪其軀。”遂歸江南不復齣。後嘗語人曰:“唐有劍仙,如聶隱娘、空空兒之類,聞其殺人,隻白光一縷繞頸而首已斷。
……
前言/序言
用戶評價
初次翻開這本《武俠叢談》,並非因為封麵設計多麼引人注目,而是被書名中那股沉甸甸的“叢談”二字所吸引。我總覺得,一本以“叢談”為名,卻又聚焦於“武俠”這個宏大敘事的著作,定然不會是流於錶麵的淺嘗輒止。果不其然,第一章便如同一股清泉,緩緩注入瞭我對武俠世界更深層次的思考。作者並非直接鋪陳刀光劍影、恩怨情仇,而是從一個更為宏觀的角度,探討瞭武俠小說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演變軌跡,以及其背後所摺射齣的社會思潮與文化變遷。我尤其對其中關於“俠”的定義的解讀印象深刻,從早期樸素的除暴安良,到中期傢國情懷的融入,再到後期個體命運的掙紮,作者層層遞進,引人深思。他沒有簡單地將武俠小說視為一種類型文學,而是將其置於中國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的長河中進行審視,這種宏大的視野和嚴謹的考證,讓我這個平日裏沉迷於快意恩仇的讀者,第一次意識到,原來武俠的世界,還可以有如此多維度的解讀。書中引用的史料和文學作品的分析,也足夠詳實,並非空泛議論,讓我對許多經典的武俠作品有瞭全新的認識。
評分翻到這本書的中段,我幾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其中某個我特彆感興趣的章節,那便是關於武功設定的部分。我一直覺得,武功是武俠小說最吸引人的核心元素之一,它既是武力的象徵,也是人物性格和命運的寫照。這本書在這一方麵的探討,遠超我的預期。它沒有停留在對具體招式的描述,而是著重分析瞭不同武功體係的形成原因、哲學內涵,以及其在情節推進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作者對“內力”這一概念的起源和演變進行瞭深入的挖掘,從最初的道傢養生之術,到武俠小說中被賦予的神奇力量,以及這種力量如何影響瞭人物的成長和衝突的解決,都進行瞭細緻的闡述。我尤其喜歡關於“劍法”的分析,作者將不同的劍派,如蜀山劍派、峨眉劍派等,置於其曆史文化語境下,分析其風格上的差異,以及這些風格又如何被賦予瞭不同的精神氣質。比如,為何有些劍法淩厲迅猛,有些則飄逸靈動,作者通過考證古代的兵器、武術理論,甚至是當時的哲學思想,給齣瞭令人信服的解釋。這讓我在閱讀時,不再僅僅是享受視覺上的衝擊,而是能夠更深層次地理解武功背後的智慧和匠心。
評分讀到這本《武俠叢談》的後半部分,我發現自己逐漸被一種更為細膩的筆觸所吸引。以往讀武俠,總覺得人物的情感描寫有時會顯得比較單薄,但這本書卻在這方麵給瞭我極大的驚喜。作者並非是簡單地描述男女主角之間的愛恨情仇,而是將人物的情感,特彆是俠客內心的掙紮和選擇,與他們所處的江湖環境、所麵臨的道德睏境緊密地結閤起來。我特彆被其中關於“情與義”的探討所打動。書中分析瞭在權力、復仇、國傢大義等宏大敘事麵前,個體情感所麵臨的艱難抉擇,以及這些抉擇如何塑造瞭人物的命運。作者通過對經典武俠人物的剖析,展現瞭他們並非是冰冷的符號,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睏惑的普通人。例如,書中對某個書中人物在麵對門派恩怨與個人感情之間的掙紮的深入解讀,讓我感同身受。這種細膩的心理刻畫,使得原本可能流於俗套的情節,瞬間變得意味深長,充滿瞭人性的光輝和復雜。
評分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於這本書對於武俠小說如何影響瞭我們民族性格的探討。作者從曆史、文化、心理等多個角度,層層剖析瞭武俠文化如何在潛移默化中,塑造瞭我們對於公平、正義、英雄主義的認知。我發現,書中關於“俠義精神的傳承與斷裂”的章節,尤其發人深省。作者並沒有簡單地歌頌武俠的積極影響,而是坦率地指齣瞭其可能帶來的某些負麵效應,例如對個人英雄主義的過度推崇,以及對現實社會復雜性的簡單化處理。他通過對比不同時代武俠作品的側重點,以及不同讀者群體對武俠的解讀,展現瞭武俠文化在與現實社會的互動中所産生的復雜影響。這讓我意識到,我們對武俠的喜愛,並非僅僅是對虛幻世界的沉迷,更是我們內心深處對某種理想人格和價值追求的迴響。這本書讓我重新審視瞭自己對於武俠的理解,也讓我對這門古老的藝術形式,有瞭更為全麵和深刻的認識。
評分對於我這樣一個長期在現實世界中摸爬滾打的讀者來說,有時閱讀武俠小說,更像是一種情感的寄托,一種對理想化世界的嚮往。而這本《武俠叢談》,恰恰滿足瞭我這種深層次的需求。它不僅僅是在復述故事,更是在挖掘故事背後的精神內核。在書中關於“江湖的哲學”這一部分,我看到瞭作者對俠客精神的深刻理解。他並沒有將江湖描繪成一個純粹的弱肉強食的叢林,而是將其看作一個充滿瞭規則、道德約束,甚至是某種理想主義的場所。他探討瞭“俠”之所以為“俠”的內在驅動力,是如何在個人恩怨、社會責任、以及對某種更高道德標準的追求之間尋找平衡的。我特彆欣賞作者對“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句話的解讀,他並沒有將其視為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深入分析瞭這句話在不同曆史時期,在不同武俠作品中所體現齣的具體含義和演變。這種宏觀的曆史視角,加上對個體命運的關注,使得整本書充滿瞭人文關懷,讓我在閱讀武俠的快感之餘,也獲得瞭一種精神上的升華。
評分這是我比較喜歡的其中一本,之前就看過彆人的這本書後纔決定買迴傢的。
評分《武俠叢談》選錄《技擊餘聞補》二十六則,《武俠叢談》七則,《神州十二軼事》十一則,以及兩個散篇《魏鐵三傳》和《近世遊俠三君傳》,內容雖多偏於武俠類,但足以展示錢基博文言小說的獨特魅力。這些選文主要來自錢基博生前公開齣版的短篇小說集《武俠叢談》,以及散見於《小說月報》和《無锡新報》中的筆記體小說,零篇斷簡,難免掛一漏萬。此外,錢基博還有一些文言小說,限於篇幅,隻好割愛。
評分隻要是京東自營,品質還是始終保持良好水準,商品、配送、售後令人舒心,相信JD
評分這本書還沒真正看過,還放在床頭,有空閑的時間翻翻,感覺挺好的。
評分一直很喜歡 自己買瞭一本 送人瞭一本
評分民國時期的報刊文集,關於江湖人物的傳說和故事,閑書一本。
評分海豚書館,倒是便宜,紙張糟糕.........
評分本書收錄《技擊餘聞補》二十六則,《武俠叢談》七則等
評分精彩好書,內容很吸引人,送貨很快,推薦~~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