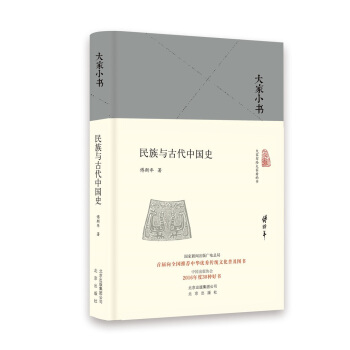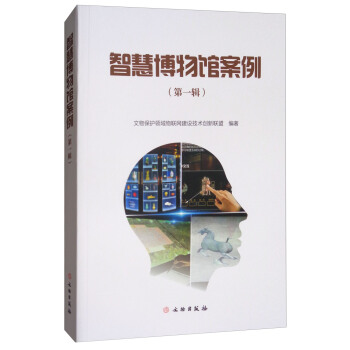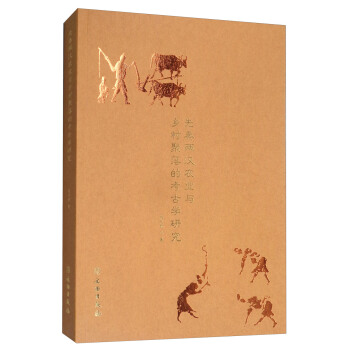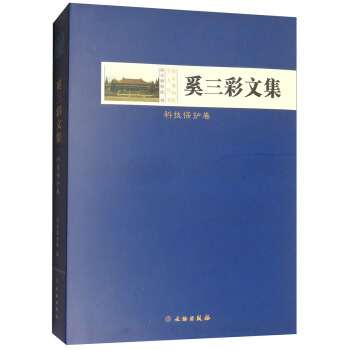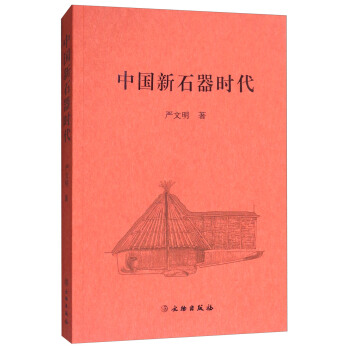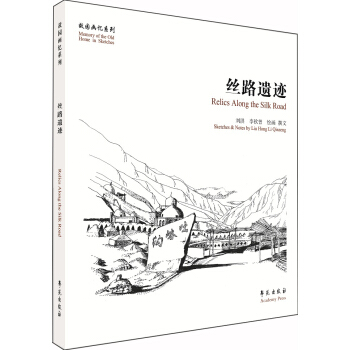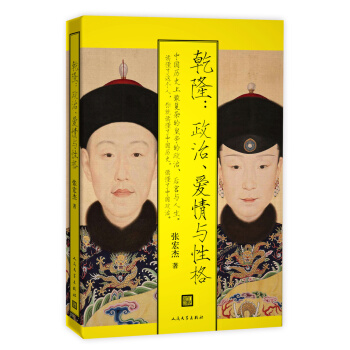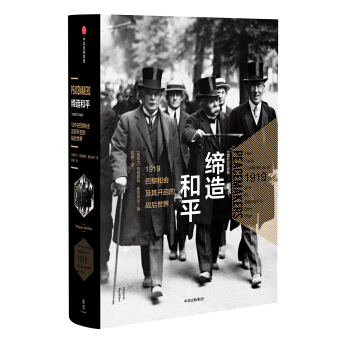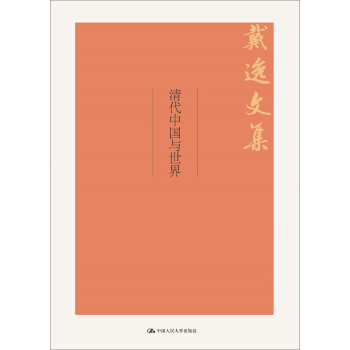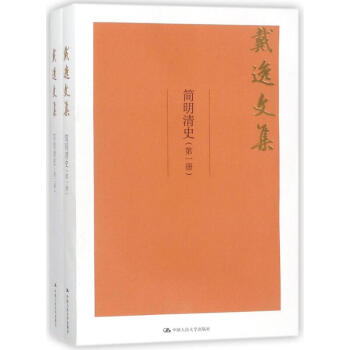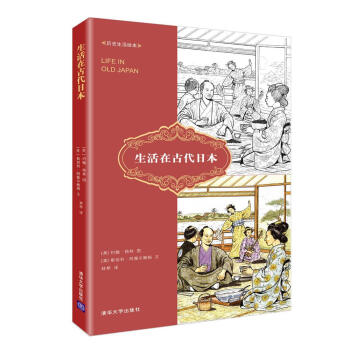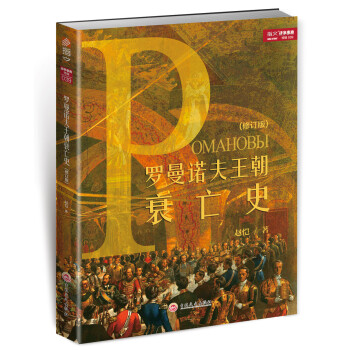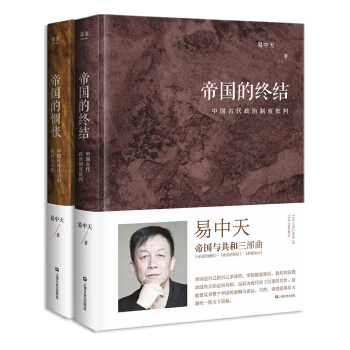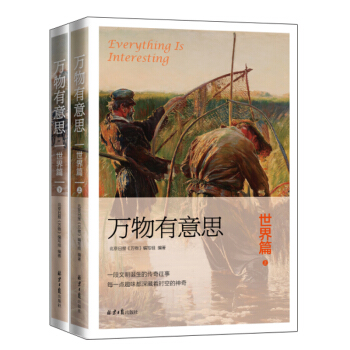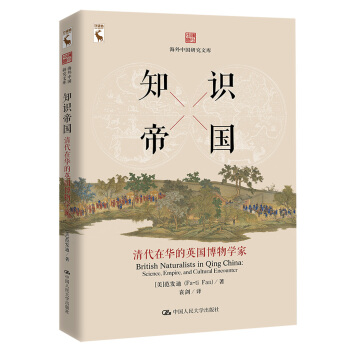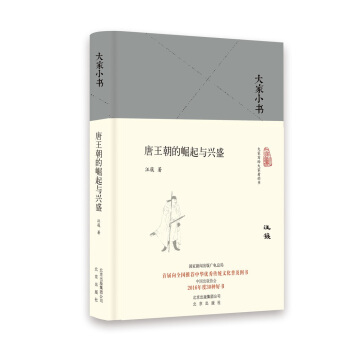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汪篯同志在陈寅恪先生门下专攻隋唐史多年,很多文章是受陈先生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的影响而写成的,师徒相承之迹,跃然纸上
内容简介
本书辑选汪篯先生生前唐史相关论文,围绕唐朝的骑兵、门阀、禁军、吏治等问题,探究唐朝崛起与兴盛的原因。字里行间也显示出汪先生深厚的学养和扎实的功力。作者简介
汪篯(1916—1966),江苏江都人。中国当代历史学家,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47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师从陈寅恪先生。先后任北大历史系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教授,文革初去世。毕生从事隋唐史研究,身后文稿札记集为《汪篯隋唐史论稿》,计二十二篇。精彩书评
汪篯同志所用史料无不细加考校,从无信手拈来、滥事引用之处。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对于今天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无疑也是应当继续承袭的。————胡如雷
目录
唐室之克定关中唐初之骑兵
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
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
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
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
唐玄宗时期之禁军及其统帅
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
精彩书摘
在隋末群雄并起时,雄踞山东的有李密、窦建德等,他们虽终于以兵力不敌归于失败,但绝不是没有能力的人,所以都很受山东人的拥戴。窦建德死后,刘黑闼、徐圆朗于武德四年七八月间复起于山东[ 《旧唐书》卷一《高祖纪》。黑闼是窦建德余党,圆朗是李密旧部[ 《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附徐圆朗传》。
他们在举事时,即以复用建德旧属之文武和师效建德之设法行政为号召,一时建德的旧臣故将如王琮、刘斌、范愿、董康买、高雅贤及其他文武,或加重用,或复本位。[ 《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这时山东人所表现的态度,是先有“兖、郓、陈、杞、伊、洛、曹、戴等八州豪猾皆杀其长吏以应”[ 《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附徐圆朗传》。
圆朗,魏又有“山东豪杰多杀长吏以应黑闼,上下相猜,人益离怨”[ 《通鉴》卷一九○唐高祖纪武德五年十二月甲子条。
唐室既系起兵于太原,而其后又以关中为根据地,其与山东人之间,自易发生隔阂。以故在唐初有变时,多用山东人去安抚山东。在李密归降以后,唐所用的山东安抚大使是宗室淮安王神通,副使则崔民干。胡三省说:“崔民干,山东望族,故使副神通以招抚诸郡县。”[ 《通鉴》卷一八六唐高祖纪武德元年十月庚辰条胡注。
这是极能洞烛隐微的。可是李密虽经降顺,而其部将徐仍据旧境,未曾纳地,于是随从李密入关的魏徵,又以山东人的资格,自请安辑山东,劝说徐归附。[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此后高祖在武德二年四月又派了定州新乐人郎楚之去安抚山东。此郎楚之便是大业中以山东人在朝廷结党被韦云起劾告配流的那个人[ 《旧唐书》卷七五《韦云起传》。
大概山东人很信服他[ 《通鉴》卷一八七唐高祖纪武德二年四月甲辰条。
凡此数例,都是以表现唐高祖尽量设法,让山东人感到相当满意。
在高祖晚年,隐太子和太宗明争暗斗时期,太宗和建成都有利用山东豪杰的计划。先发动的是建成一方面。建成是听了魏徵、王珪的劝告,谋得征讨刘黑闼行军元帅的位置,因而进行结纳山东英俊的。[ 《旧唐书》卷六四《高祖诸子传隐太子建成传》。
后发动的是太宗一方面。太宗是在紧要关头,才派了郑州荥阳人张亮到洛阳,阴引山东豪杰以作为万一失败的退路基础的。[ 《旧唐书》卷六九《张亮传》。
太宗这一方面发动得太晚,所以张亮出去,根本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建成、元吉这一方面,则在山东羽翼已就,在隐、巢被杀后,山东的形势又大为恶化起来。“是时,河北州县素事隐、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乱。”[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魏徵本来是山东人,原先曾在李密部下典掌过书记,又曾被窦建德俘虏过去,署用为太子舍人。归唐以后,劝说拥有大片山东土地的徐降唐的是他,建议建成在山东结纳豪杰的主谋者又是他,他和山东人必是保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聪明的太宗,在赦免了他赞助建成的罪状以后,就派他去安抚河北。他这次出来,果然不辱使命,当在路途上碰到了被逮捕的太子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时,他就自作主张地把他们贷宥。这样,山东人才觉得有了保障,山东便没有发生问题。太宗大喜,从此对魏徵更加信任。[ 《旧唐书》卷七一《魏徵传》。
这是魏徵报效太宗国士之知的第一声,也是魏徵更受太宗国士之遇的初径。
山东人对李唐皇室素无好感,对于太宗尤多嫌忌,而山东地区实为建都关中的李唐皇室经济上的生命线。唐初,财政上的收入,主要靠着租庸调,河北是当时蚕绵之乡,“天府委输,待以成绩”[ 《通鉴》卷一九○唐高祖纪武德五年十二月壬申条考异引《太宗实录》。
山东、河北户口之众,绝非其他各地所可比拟(四川除外)。[ 《旧唐书》卷三八、卷三九《地理志》;《新唐书》卷三八、卷三九《地理志》。
假如这一地区发生变乱,纵使能很轻易地把它平定,但是那加给朝廷的威胁,总是够大的。山东既有人才,这些人若不吸收用,便会成为促成变乱的因素。老谋深算的太宗,对于这一问题,当然是曾经有过斟酌的。
……
前言/序言
汪篯先生,江苏江都人,1916年生于扬州,1934年秋进入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七七”事变后,他随校到达昆明,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39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做研究生,仍在昆明西南联大。1942年秋到1946年秋在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员,并在五华中学兼课。他善诗文,对唐诗饶有兴趣,特别爱好杜诗。1947年6月,汪篯先生辗转来到北平,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具体工作则是在清华大学协助陈寅恪先生写《元白诗笺证稿》。北京解放后,他回到北大,1951年以后一直在北大历史系工作,先后任副教授、教研室副主任,1963年晋升为教授,1966年6月10日含冤去世,终年五十岁。
汪篯先生一生主要从事隋唐史的研究。他曾受业于陈寅恪先生,因此,在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都深受陈寅恪先生影响。正如胡如雷先生在《读〈汪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一文中所说,汪篯先生在解放前的“很多文章是受陈先生的学术观点、治学方法的影响而写成的,师徒相承之迹,跃然纸上。譬如陈先生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西魏、北周、隋、唐诸朝的上层统治集团例行所谓关陇本位政策,很多复杂的政治斗争均与此有关。《论稿》承其余绪,并加以发挥,在《唐太宗之拔擢山东微族与各集团人士之并进》《唐太宗树立新门阀的意图》《唐高宗王武二后废立之争》及《唐室之克定关中》诸文中都明显而系统地贯串着这一重要论点……陈寅恪先生过人的优点之一,是观察问题目光敏锐,往往能从常人所忽略的细微之处发现能说明重大现象的契机,这样写成的文章异常引人入胜,汪同志确实也具有同样的优点……陈寅恪先生治学谨严,每条史料都经过核校诸书方始引用,无一字一句苟且,此点素为后学所景仰。汪同志在这方面也继承了陈先生的学风,所用史料无不细加考校,从无信手拈来,滥事引用之处”。
对于具体的历史研究,汪篯先生经常强调认识历史问题需要有一个过程。对历史上一些重要制度和规律性问题,他认为“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经过几次反复,才能比较接近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因此,他不囿于前人所说,也不坚持自己曾经有过的某些看法,而是在吸取别人成果和自己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因此,他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例如,他对北魏至隋唐均田制的研究,是从1956年开始的,到1964年虽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看法,但他认为有许多看法还不成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此期间,他不仅对均田制的认识不断深化了,而且研究领域也大为扩展。他不仅研究和考释了北魏、北齐和唐的田令,研究了包括敦煌西魏和唐的户籍簿在内的与田令实行有关的材料,而且上溯商、周、两汉的土地占有情况;他不仅研究了这些时期的土地问题,而且还探索了这些时期的生产力状况以及阶级斗争在土地制度变化中的作用。在研究工作中他总是这样不断深入,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求历史发展的本质。
他在研究中很注意对比研究。他总是把历史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力图从纷繁的历史线索中找出社会发展的规律,划分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他很重视前后的对比。他不仅在秦汉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还下了很大的功夫钻研商、周和战国的历史,为此还研究了金文以及《尚书》和《诗经》。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对宋以后的历史不熟悉,准备有机会进行钻研。他还很注意把外国历史和中国历史,把欧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对比,既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点,又注意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力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找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各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他在研究中不仅注意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而且非常注意各个阶段中的数量关系,经常进行各种统计和计算。从宰相的各种家庭出身到各官僚集团的成员,从各地区的人口到各地区的物产,从古代的耕地面积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耕地面积,他都进行过统计。在统计时,他注意分析,尽量按照事物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加以分类,而不是把几十年乃至数百年的人或事凑在一起简单地加以平均。在统计时,他也注意对比,把几个朝代的数字进行对照,以便从中发现变化的轨迹。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确实非常考究,纸张的质感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给人一种厚重、权威的感觉。初翻开时,那些精美的插图和地图立刻抓住了我的眼球,它们不是那种敷衍的配图,而是经过精心考量和制作的,与正文的叙述形成了完美的互补。尤其是一些手绘的城池布局图,线条流畅,细节丰富,仿佛能带着读者穿越回那个恢弘的时代,亲眼目睹盛唐的繁华景象。装帧的字体选择也十分到位,既有古典的韵味,又不失现代阅读的清晰度,看得出出版方在制作过程中投入了极大的心血。虽然我还没有完全沉浸到内容之中,但仅凭这外在的工艺,就足以让我对它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感觉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件值得珍藏的艺术品。对于那些注重阅读体验和收藏价值的读者来说,单是这份精良的制作,就值回票价了。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在学术的严谨和文学的优美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平衡点。它不像某些学术专著那样晦涩难懂,充满了生僻的专业术语,相反,作者似乎非常擅长用富有画面感的现代汉语来描绘那些尘封已久的场景和人物的内心世界。读到激动人心的历史节点时,语言会变得激昂有力,仿佛能听到战鼓声声;而在描绘宫廷的日常生活或文人的雅集时,笔调又会转为细腻婉约,充满了生活气息。这种灵活多变的文字处理能力,极大地丰富了阅读体验,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我对那个遥远时代的风貌和精神气质有了更为鲜活和立体的感知。
评分这本书的行文风格展现出一种沉稳而富有洞察力的笔触,作者似乎对史料的驾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注意到,在描述一些关键的历史事件和人物转折点时,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事实,而是深入挖掘了背后的社会动因和文化心理,使得整个叙述逻辑严密,层层递进。比如,在论述某一重要制度的演变时,作者不仅引用了官方史书的记载,还巧妙地融入了当时文人的诗歌、碑文中的只言片语,这种跨文本的印证方式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和趣味性。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像是在跟随一位博学的老者,他既能高屋建瓴地把握宏观的时代脉络,又能精准地捕捉到微观的个体命运,这种叙事节奏的掌控力非常罕见。
评分这本书在结构编排上展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清晰度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平衡艺术。它似乎并没有采用那种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线性推进方式,而是更倾向于主题式的划分,将历史的复杂性拆解成若干个易于理解的模块。每一个章节的起承转合都处理得极为自然,读者在读完一个主题的深入探讨后,不会感到信息过载或逻辑断裂,反而能更清晰地建立起不同历史侧面之间的联系。这种结构安排的好处是,即便是对那个时代背景不甚熟悉的读者,也能凭借清晰的章节指引,逐步建立起对整个历史时期的认知框架。这种匠心独运的组织方式,无疑极大地降低了理解深度历史著作的门槛,使得知识的传递过程变得高效而愉悦。
评分我对作者在史料运用上的那种严谨态度印象深刻。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书中对许多重大历史论断的提出,都有明确的注释来源和旁证材料作为支撑,这种扎实的学理基础,让文字显得掷地有声,充满了毋庸置疑的可靠性。这不同于一些流于表面的通俗历史读物,它真正做到了“述而不作”与“以史为鉴”的完美结合。即便是一些常被后世曲解的典故或人物评价,作者也展现出了批判性的审视,避免了陷入固有的窠臼,而是努力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种对细节的执着和对史实的敬畏感,让我在阅读时倍感安心,深知自己正在接触的是一份经过时间检验的、具有学术价值的珍贵文本。
评分书籍使人增长知识,是生活和工作的好帮手!
评分正版图书,活动入手,内容还算可以,买书如山倒
评分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价廉物美,性价比高!
评分大家小书系列,收了不少了,遇到感兴趣的,还是要拿下
评分又是大家小书系列中的一本,收了。
评分发货速度独步全网,促销力度冠绝全网。
评分经典大家作品,京东活动给力,价格实惠质量好,下次购物继续来京东。
评分经典大家作品,京东活动给力,价格实惠质量好,下次购物继续来京东。
评分非常不错的书,非常有价值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