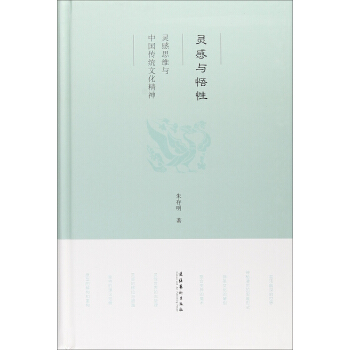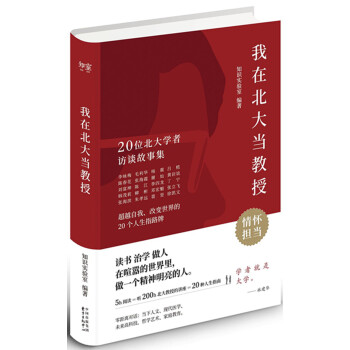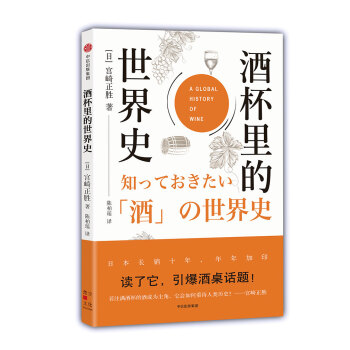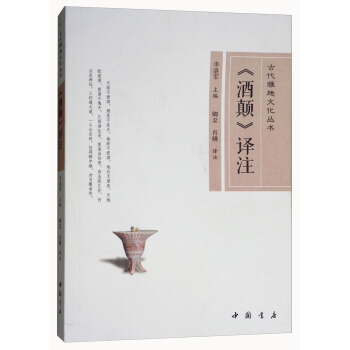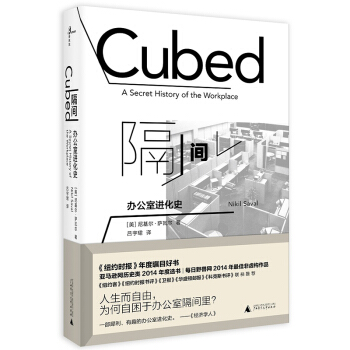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汪曾祺以文名,散文和小说别具一格,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位戏剧家,自《范进中举》始,编剧二十余年。常谓戏曲:作廿四史观,当三百篇读。本书所选文章,皆与戏曲有关,或忆人,或说事,或点评戏曲,更有关注中国戏曲发展的深沉之作。在他的笔下,裘盛戎、程砚秋、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一代名家音容笑貌如在眼前,《十五贯》《四进士》《打渔杀家》《沙家浜》等名剧名段台前幕后一览无余。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等。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多种。
目录
且说过于执
笔下处处有人——谈《四进士》
飞出黄金的牢狱
从戏剧文学的角度看京剧的危机
打渔杀家
名优逸事
尊丑
中国戏曲有没有间离效果
《贵妃醉酒》是京剧吗?
京剧格律的解放
名优之死——纪念裘盛戎
两栖杂谈
听遛鸟人谈戏
从赵荣琛拉胡琴说起
戏曲和小说杂谈
提高戏曲艺术质量
流派要发展,要有新剧目——读李一氓《论程砚秋》有感
应该争取有思想的年轻一代——关于戏曲问题的冥想
细节的真实——习剧札记
我是怎样和戏曲结缘的
用韵文想
苏三监狱
建文帝的下落
杨慎在保山
戏台天地——《古今戏曲楹联荟萃》序
太监念京白
《西方人看中国戏剧》读后
关于“样板戏”
我的“解放”
中国戏曲和小说的血缘关系
艺品和人品
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
关于《沙家浜》
读剧小札
川剧
《中国京剧》序
谭富英佚事
京剧杞言——兼论荒诞戏剧《歌代啸》
浅处见才——谈写唱词
动人不在高声
小议新程派
精彩书摘
样章
马·谭·张·裘·赵
——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
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是北京京剧团的“五大头牌”。我从一九六一年底参加北京京剧团工作,和他们有一些接触,但都没有很深的交往。我对京剧始终是个“外行”(京剧界把不是唱戏的都叫做“外行”)。看过他们一些戏,但是看看而已,没有做过任何研究。现在所写的,只能是一些片片段段的印象。有些是我所目击的,有些则得之于别人的闲谈,未经核实,未必可靠。好在这不入档案,姑妄言之耳。
描述一个演员的表演是几乎不可能的事。马连良是个雅俗共赏的表演艺术家,很多人都爱看马连良的戏。但是马连良好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一般都说马连良“潇洒”。马连良曾想写一篇文章:《谈潇洒》,不知写成了没有。我觉得这篇文章是很难写的。“潇洒”是什么?很难捉摸。《辞海》“潇洒”条,注云:“洒脱,不拘束”,庶几近之。马连良的“潇洒”,和他在台上极端的松弛是有关系的。马连良天赋条件很好:面形端正,眉目清朗——眼睛不大,而善于表情,身材好——高矮胖瘦合适,体格匀称。他的一双脚,照京剧演员的说法,“长得很顺溜”。京剧演员很注意脚。过去唱老生大都包脚,为的是穿上靴子好看。一双脚腨里咕叽,浑身都不会有精神。他腰腿幼功很好,年轻时唱过《连环套》,唱过《广泰庄》这类的武戏。脚底下干净,清楚。一出台,就给观众一个清爽漂亮的印象,照戏班里的说法:“有人缘儿。”
马连良在做角色准备时是很认真的。一招一式,反复捉摸。他的夫人常说他:“又附了体。”他曾排过一出小型现代戏《年年有余》(与张君秋合演),剧中的老汉是抽旱烟的。他弄了一根旱烟袋,整天在家里摆弄,“找感觉”。到了排练场,把在家里琢磨好的身段步位走出来就是,导演不去再提意见,也提不出意见,因为他的设计都挑不出毛病,所以导演排他的戏很省劲。到了演出时,他更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秦香莲》里秦香莲唱了一大段“琵琶词”,他扮的王延龄坐在上面听,没有什么“事”,本来是很难受的,然而马连良不“空”得慌,他一会捋捋髯口(马连良捋髯口很好看,捋“白满”时用食指和中指轻夹住一绺,缓缓捋到底),一会用眼瞟瞟陈世美,似乎他随时都在戏里,其实他在轻轻给张君秋拍着板!他还有个“毛病”,爱在台上跟同台演员小声地聊天。有一次和李多奎聊起来:“二哥,今儿中午吃了什么?包饺子?什么馅儿的?”害得李多奎到该张嘴时忘了词。马连良演戏,可以说是既在戏里,又在戏外。
既在戏里,又在戏外,这是中国戏曲,尤其是京剧表演的一个特点。京剧演员随时要意识到自己的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没法长时间地“进入角色”。《空城计》表现诸葛亮履险退敌,但是只有在司马懿退兵之后,诸葛亮下了城楼,抹了一把汗,说道:“好险呐!”观众才回想起诸葛亮刚才表面上很镇定,但是内心很紧张,如果要演员一直“进入角色”,又表演出镇定,又表演出紧张,那“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的“慢板”和“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二六”怎么唱?
有人说中国戏曲注重形式美。有人说只注重形式美,意思是不重视内容。有人说某些演员的表演是“形式主义”,这就不大好听了。马连良就曾被某些戏曲评论家说成是“形式主义”。“形式美”也罢,“形式主义”也罢,然而马连良自是马连良,观众爱看,爱其“潇洒”。
马连良不是不演人物。他很注意人物的性格基调。我曾听他说过:“先得弄准了他的‘人性’:是绵软随和,还是干硬倔强。”
马连良很注意表演的预示,在用一种手段(唱、念、做)想对观众传达一个重点内容时,先得使观众有预感,有准备,照他的说法是:“先打闪,后打雷。”
马连良的台步很讲究,几乎一个人物一个步法。我看过他的《一捧雪》,“搜杯”一场,莫成三次企图藏杯外逃,都为严府家丁校尉所阻,没有一句词,只是三次上场、退下,三次都是“水底鱼”,三个“水底鱼”能走下三个满堂好。不但干净利索,自然应节(不为锣鼓点捆住),而且一次比一次遑急,脚底下表现出不同情绪。王延龄和老薛保走的都是“老步”,但是王延龄位高望重,生活优裕,老而不衰;老薛保则是穷忙一生,双腿僵硬了。马连良演《三娘教子》,双膝微弯,横跨着走。这样弯腿弯了一整出戏,是要功夫的!
马连良很知道扬长避短。他年轻时调门很高,能唱《龙虎斗》这样的乙字调唢呐二黄,中年后调门降了下来。他高音不好,多在中音区使腔。《赵氏孤儿》鞭打公孙杵臼一场,他不能像余叔岩一样“白虎大堂奉了命”,“白虎”直拔而上,就垫了一个字:“在白虎”,也能“讨俏”。
对编剧艺术,他主张不要多唱。他的一些戏,唱都不多。《甘露寺》只一段“劝千岁”,《群英会》主要只是“借风”一段二黄。《审头刺汤》除了两句散板,只有向戚继光唱的一段四平调;《胭脂宝褶》只有一段流水。在讨论新编剧本时他总是说:“这里不用唱,有几句白就行了。”他说:“不该唱而唱,比该唱而不唱,还要叫人难受。”我以为这是至理名言。现在新编的京剧大都唱得太多,而且每唱必长,作者笔下痛快,演员实在吃不消。
马连良在出台以前从来不在后台“吊”一段,他要喊两嗓子。他喊嗓子不像别人都是“啊——咿”,而是:“走!”我头一次听到直纳闷:走?走到哪儿去?
马连良知道观众来看戏,不只看他一个人,他要求全团演员都很讲究。他不惜高价,聘请最好的配角。对演员服装要求做到“三白”——白护领、白水袖、白靴底,连龙套都如此(在“私营班社”时,马剧团都发理发费,所有演员上场前必须理发)。他自己的服装都是按身材量制的,面料、绣活都得经他审定,有些盔头是他看了古画,自己琢磨出来的,如《赵氏孤儿》程婴的镂金透空的员外巾。他很会配颜色。有一回赵燕侠要做服装,特地拉了他去选料子。现在有些剧装厂专给演员定制马派服装。马派服装的确比官中行头穿上要好看得多。
听谭富英听一个“痛快”。谭富英年轻时嗓音“没挡”,当时戏曲报刊都说他是“天赋佳喉”。而且,底气充足。一出《定军山》,“敌营打罢得胜的鼓哇呃”,一口气,高亮脆爽,游刃有余,不但剧场里“炸了窝”,连剧场外拉洋车的也一齐叫好——他的声音一直传到场外。“三次开弓新月样”“来来来带过爷的马能行”,也同样是满堂的彩,从来没有“漂”过——说京剧唱词不通,都得举出“马能行”,然而《定军山》的“马能行”没法改,因为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花腔,“行”字是“脑后摘音”,改了即无此效果。
谭富英什么都快。他走路快。晚年了,我和他一起走,还是赶不上他。台上动作快(动作较小)。《定军山》出场简直是握着刀横窜出来的。开打也快。“鼻子”“削头”,都快。“四记头”亮相,末锣刚落,他已经抬脚下场了。他的唱,“尺寸”也比别人快。他特别长于唱快板。《战太平》“长街”一场的快板,《斩马谡》“见王平”的快板都似脱线珍珠一样溅跳而出。快,而字字清晰劲健,没有一个字是“嚼”了的。五十年代,“挖掘传统”那阵,我听过一次他久已不演的《朱砂痣》,赞银子一段,“好宝贝!”一句短白,碰板起唱,张嘴就来,真“脆”。
我曾问过一个经验丰富、给很多名角挎过刀、艺术上很有见解的唱二旦的任志秋:“谭富英有什么好?”志秋说:“他像个老生。”我只能承认这是一句很妙的回答,很有道理。唱老生的的确有很多人不像老生。
谭富英为人恬淡豁达。他出科就红,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他不和别人争名位高低,不“吃戏醋”。他和裘盛戎合组太平京剧团时就常让盛戎唱大轴,他知道盛戎正是“好时候”,很多观众是来听裘盛戎的。盛戎大轴《铫期》,他就在前面来一出《桑园会》(与梁小鸾合演)。这是一出“歇工戏”,他也乐得省劲。马连良曾约他合演《战长沙》,他的黄忠,马的关羽。重点当然是关羽,黄忠是个配角,他同意了(这出戏筹备很久,我曾在后台见过制作得极精美的青龙偃月刀,不知因为什么未能排出,如果演出,那是会很好看的)。他曾在《秦香莲》里演过陈世美,在《赵氏孤儿》里演过赵盾。这本来都是“二路”演员的活。
富英有心脏病,到我参加北京京剧团后,就没怎么见他演出,但不时还到剧团来。和大家见见,聊聊。他没有架子,极可亲近。
他重病住院,用的药很贵重。到他病危时,拒绝再用,他说:“这种药留给别人用吧!”重人之生,轻己之死。如此高洁,能有几人?
张君秋得天独厚,他的这条嗓子,一时无两:甜,圆,宽,润。他的发声极其科学,主要靠腹呼吸,所谓“丹田之气”。他不使劲地摩擦声带,因此声带不易磨损,耐久,“顶活”,长唱不哑。中国音乐学院有一位教师曾经专门研究张君秋的发声方法——这恐怕是很难的,因为发声是身体全方位的运动。他的气很足。我曾在广和剧场后台就近看他吊嗓子,他唱的时候,颈部两边的肌肉都震得颤动,可见其共鸣量有多大。这样的发声真如浓茶酽酒,味道醇厚。一般旦角发声多薄,近听很亮,但是不能“打远”,“灌不满堂”。有别的旦角和他同台,一张嘴,就比下去了。
君秋在武汉收徒时曾说:“唱我这派,得能吃。”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君秋食量甚佳,胃口极好。唱戏的都是“饱吹饿唱”,君秋是吃饱了唱。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他一抹嘴:“苦哇!”就上去了,“忽听得唤苏三……”在武汉,住璇宫饭店,每天晚上鳜鱼汆汤,二斤来重一条,一个人吃得干干净净。他和程砚秋一样,都爱吃炖肘子。
(唱旦角的比君秋还能吃的,大概只有一个程砚秋。他在上海,到南市的老上海饭馆吃饭,“青鱼托肺”——青鱼的内脏,这道菜非常油腻,他一次要两只。在老正兴吃大闸蟹,八只!搞声乐的要能吃,这大概有点道理。)
君秋没有坐过科,是小时在家里请教师学的戏,从小就有一条好嗓子,搭班就红(他是马连良发现的),因此不大注意“身上”。他对学生说:“你学我,学我的唱,别学我的‘老抖身子’。”他也不大注意表演。但也不尽然。他的台步不考究,简直无所谓台步,在台上走而已,“大步量”。但是着旗装,穿花盆底,那几步走,真是雍容华贵,仪态万方。我还没有见过一个旦角穿花盆底有他走得那样好看的。我曾仔细看过他的《玉堂春》,发现他还是很会“做戏”的。慢板、二六、流水,每一句的表情都非常细腻,眼神、手势,很有分寸,很美,又很含蓄(一般旦角演玉堂春都嫌轻浮,有的简直把一个沦落风尘但不失天真的少女演成一个荡妇)。跪禀既久,站起来,腿脚麻木了,微蹲着,轻揉两膝,实在是楚楚动人。花盆底脚步,是经过苦练练出来的;《玉堂春》我想一定经过名师指点,一点一点“抠”出来的。功夫不负苦心人。君秋是有表演才能的,只是没有发挥出来。
君秋最初宗梅,又受过程砚秋亲传(程很喜欢他,曾主动给他说过戏,好像是《六月雪》,确否,待查)。后来形成了张派。张派是从梅派发展出来的,这大家都知道。张派腔里有程的东西,也许不大为人注意。
君秋的嗓子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非常富于弹性,高低收放,运用自如,特别善于运用“擞”。《秦香莲》的二六,低起,到“我叫叫一声杀了人的天”拔到旦角能唱的最高音,那样高,还能用“擞”,宛转回环,美听之至。他又极会换气,常在“眼”上偷换,不露痕迹,因此张派腔听起来缠绵不断,不见棱角。中国画讲究“真气内行”,君秋得之。
我和裘盛戎只合作过两个戏,一个《杜鹃山》,一个小戏《雪花飘》,都是现代戏。
我和盛戎最初认识是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到天津去看戏——好像就是《杜鹃山》。演员知道裘盛戎来看戏,都“卯上”了。散了戏,我们到后台给演员道辛苦,盛戎拙于言辞,但是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朴素的,他的谦虚是由衷的谦虚。他是真心实意地来向人家学习来了。回到旅馆的路上,他买了几套煎饼子摊鸡蛋,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他咬着煎饼子的样子,表现了很喜悦的怀旧之情和一种天真的童心。盛戎睡得很晚,晚上他一个人盘腿坐在床上抽烟,一边好像想着什么事,有点出神,有点迷迷糊糊的。不知是为什么,我以后总觉得盛戎的许多唱腔、唱法、身段,就是在这么盘腿坐着的时候想出来的。
盛戎的身体早就不大好。他曾经跟我说过:“老汪唉,你别看我外面还好,这里面——都娄啦!”(西瓜过熟,瓜瓤败烂,北京话叫做“娄了”。)搞《雪花飘》的时候,他那几天不舒服,但还是跟着我们一同去体验生活。《雪花飘》是根据浩然同志的小说改编的,写的是一个看公用电话的老人的事。我们去访问了政协礼堂附近的一位看电话的老人。这家只有老两口。老头子六十大几了,一脸的白胡茬,还骑着自行车到处送电话。他的老伴很得意地说:“头两个月他还骑着二八的车哪,这最近才弄了一辆二六的!”盛戎在这间屋里坐了好大一会儿,还随着老头子送了一个电话。
《雪花飘》排得很快,一个星期左右,戏就出来了。幕一打开,盛戎唱了四句带点马派味儿的〔散板〕:
打罢了新春六十七哟,
看了五年电话机。
传呼一千八百日,
舒筋活血,强似下棋!
我和导演刘雪涛一听,都觉得“真是这里的事儿”!
《杜鹃山》搞过两次,一次是一九六四年,一次是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九年那次我们到湘鄂赣体验了较长时期的生活。我和盛戎那时都是“控制使用”,他的心情自然不大好。那时强调军事化,大家穿了“价拨”的旧军大衣,背着行李,排着队。盛戎也一样,没有一点特殊。他总是默默地跟着队伍走,不大说话,但倒也不是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很能理解他的心情。虽然是“控制使用”,但还能“戴罪立功”,可以工作,可以演戏。我觉得从那时起,盛戎发生了一点变化,他变得深沉起来。盛戎平常也是个有说有笑的人,有时也爱逗个乐,但从那以后,我就很少见他有笑影了。他好像总是在想什么心事。用一句老戏词说:“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的这种神气,一直到死,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里。
那趟体验生活,是够苦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更难受,不生火,墙壁屋瓦都很单薄。那年的天气也特别。我们在安源过的春节,旧历大年三十,下大雪,同时却又打雷,下雹子,下大雨,一块儿来!盛戎晚上不再穷聊了,他早早就进了被窝。这老兄!他连毛窝都不脱,就这样连着毛窝睡了。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没有叫一句苦。
用户评价
这本《说戏——汪曾祺说戏散文41篇》,于我而言,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之所以如此期待,是因为我曾在汪曾祺先生的其他作品中,窥见了他那深邃的文化底蕴和超然的生活智慧。他笔下的京剧、昆曲,并非是枯燥的技艺讲解,而是融入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对时代变迁的观察,以及他对那些鲜活生命体的深刻理解。每当读到他写戏,总觉得他不仅仅是在写戏,更是在写人,写那些在戏里戏外,有着各自悲欢离合的人生。这41篇散文,我想一定是他将自己对戏曲艺术的理解,以及他生命中那些与戏曲结缘的故事,用他那独有的,如同“刮风”般轻柔,“下雨”般绵密,却又“有根有据”的笔触,一点一滴地呈现出来。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在这些篇章里,是否会有他对于某个经典唱段的独到见解,是否会有他对某个著名戏曲人物的生动描摹,亦或是他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与戏曲结下的不解之缘。这本书,我想会是一次绝佳的,与汪曾祺先生“说戏”的契机,也是一次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戏曲的绝佳途径。
评分这本《说戏——汪曾祺说戏散文41篇》仿佛是一坛陈年的老酒,散发着温润而醇厚的香气,未曾开启,已让人心生向往。我一直认为,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以一种极其贴近生活的方式,去解读和呈现那些看似高雅甚至有些疏远的艺术形式。他不会用晦涩的术语去分析戏曲,而是会从一个普通观众,或者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的视角,去讲述戏里的故事,去描绘戏中的人物,去品味那些唱词背后的人情冷暖。我期待在这41篇文章中,能够读到他对于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有着怎样的独到见解;能够看到他如何用他那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捕捉舞台上稍纵即逝的精彩瞬间;更能够感受到,他将戏曲中的“情”与“理”,巧妙地融入到他对人生百态的感悟之中。这本书,对我而言,不仅仅是关于戏曲的读物,更像是一次与汪曾祺先生一同在时光的长河中漫步,去体味那些流传下来的艺术精髓,去感受那份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
评分对于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我总是带着一种“淘金者”的心情去翻阅。他总能在看似寻常的字里行间,挖掘出最动人的情感,最深刻的哲理。《说戏——汪曾祺说戏散文41篇》,这个书名本身就充满了诱惑力。我脑海中勾勒出的画面,是汪先生坐在书案前,点燃一炉沉香,慢慢地,不紧不慢地,讲述着他与戏曲的故事。这些故事,想必不是照本宣科的介绍,而是带着他特有的,那种“讲究”又“不落俗套”的个人色彩。他或许会从某个戏曲人物的服饰、唱腔,引申出他对人情世故的理解;又或许会从某个生僻的戏曲典故,触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尤其期待,在这41篇散文中,能够感受到他对戏曲的热爱,对艺术的尊重,以及他那份对生活永不磨灭的欣赏。这本书,我想会是一次让我再次沉浸在汪曾祺先生那温润而充满智慧的世界里的绝佳体验,也是一次深入领略中国传统戏曲独特魅力的难得机会。
评分刚收到这本书,还没来得及细读,但从书名和封面设计上,就已经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汪曾祺先生,这位在当代文坛上享有盛誉的作家,以其独特的笔触描绘了无数鲜活的人物和生动的场景。“说戏”二字,本身就带着一种娓娓道来的亲切感,仿佛置身于一个老朋友的叙旧会,听他聊起那些他眼中、心中、脑海里,关于戏曲、关于人生、关于过往的点点滴滴。我一直很欣赏汪先生文字的“家常”与“雅致”,他能将最朴素的生活细节写得有滋有味,又能将最寻常的事物赋予诗意的光辉。这本书选取的“戏”,或许不仅仅是舞台上的戏曲,更可能是人生百态,是世事变迁,是岁月留痕。我期待着在这41篇散文中,能够再次感受到那种“从容”、“闲适”的文学韵味,体味到汪先生笔下那种“有情有趣”的生活态度。尤其是在当下这个节奏飞快、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静下心来,沉浸在这样一篇篇温润的文字中,本身就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这本书,我想一定会成为我案头常备的读物,不时翻阅,总能从中汲取新的感悟与力量。
评分对于汪曾祺先生的文字,我一直抱持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喜爱。他的散文,总有一种“不期而遇”的惊喜,仿佛是在不经意间,为你打开了一扇通往美好世界的大门。《说戏——汪曾祺说戏散文41篇》这个书名,就足以勾起我无限的好奇。我脑海中浮现的,不是那些板着面孔讲戏的评论家,而是像汪先生这样,带着一份生活的热情和对艺术的尊重,将戏曲中的人情世故、悲欢离合,娓娓道来。我猜想,这本书中,定然少不了那些京剧名伶的传奇故事,也少不了他对昆曲婉转悠扬的细腻描绘。或许,他还会从戏曲的某个细节,触及到更深层的文化意涵,或是引申出他对人间烟火的感悟。我特别喜欢汪先生的那种“淡淡的”写作风格,不张扬,不煽情,却能直抵人心,让你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文字所打动,所感染。我想,这本书,一定又是一次让我得以窥见汪曾祺先生内心世界的绝佳机会,也是一次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戏曲魅力的宝贵契机。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创意经济新思维:面向价值思考 [Creative Industry New Thinking:Value Oriented Thinking]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40993/5afd471eN2b2edd1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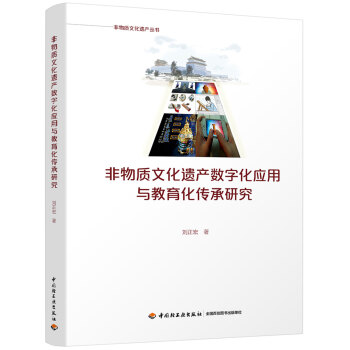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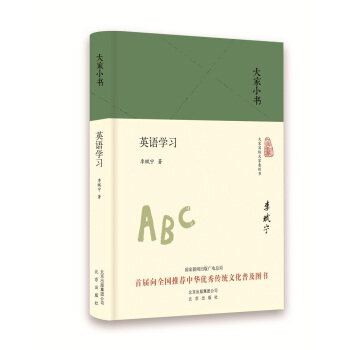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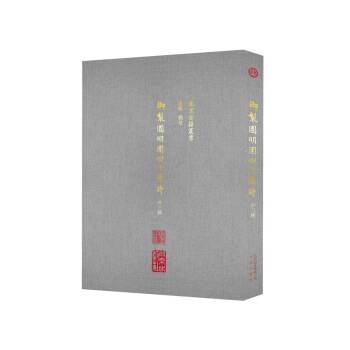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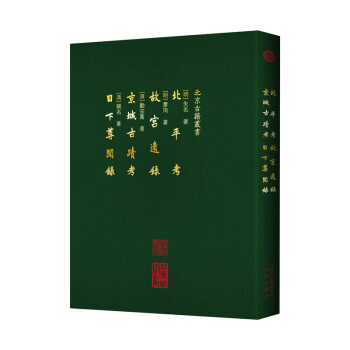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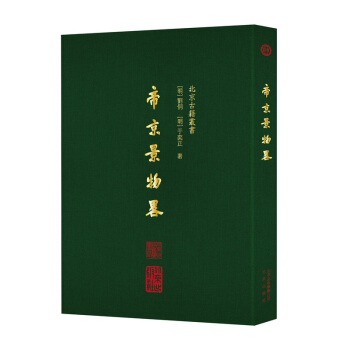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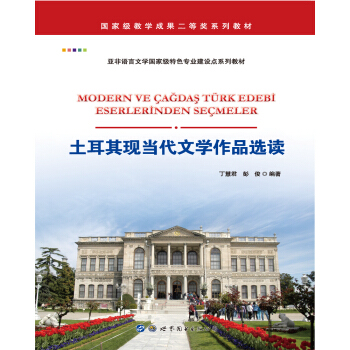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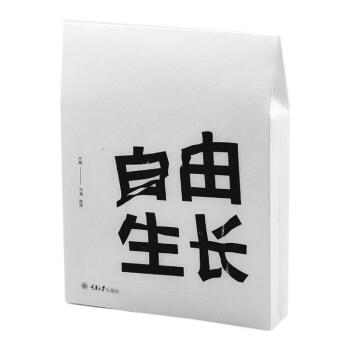
![岩石上的信仰 [Research on Mask Rock Art in North of China ]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344815/5af402cdN8db9da6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