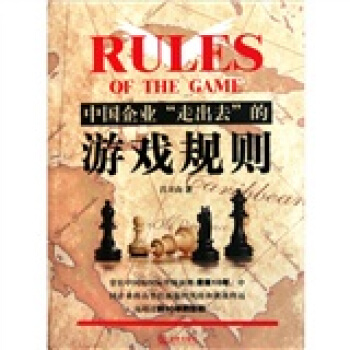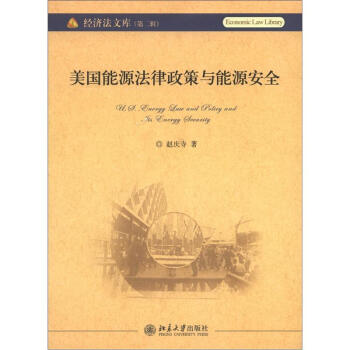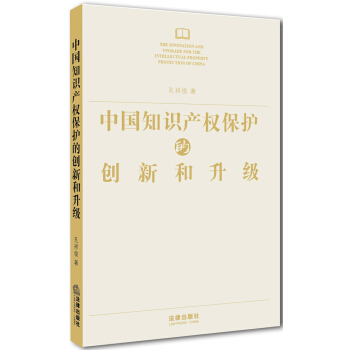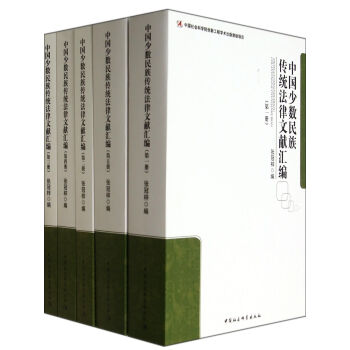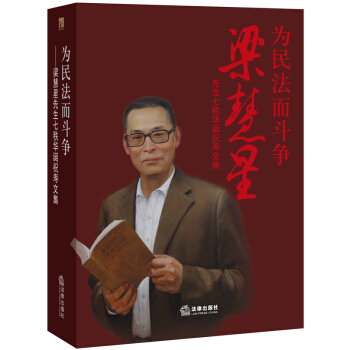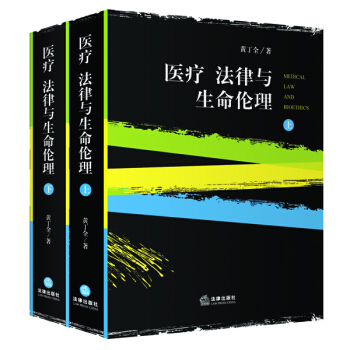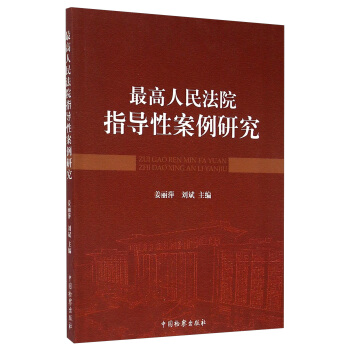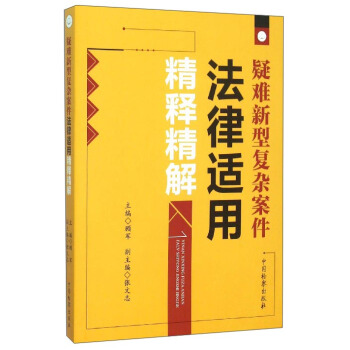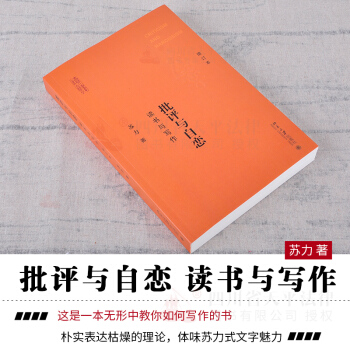

具體描述
用戶評價
這本書的書名“蘇力批評與自戀”仿佛一把鑰匙,正緩緩開啓一扇通往內心世界的大門。我一直對“自戀”這個概念頗感興趣,但又覺得它常常被簡單化,未能觸及到其更深層次的社會和心理根源。蘇力教授的解讀,我期待它能帶來一種全新的、更具原創性的思考。他會不會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現代社會結構如何孕育瞭普遍的自戀情緒?又或者,他會從心理學的角度,深入剖析自戀與自我認同、社會評價之間的復雜互動?我尤其好奇,書中是否會涉及到一些具體的社會事件或文化現象,來佐證他的理論,讓抽象的概念變得生動起來。作為一名對社會現實保持高度關注的讀者,我渴望從這本書中獲得更深刻的洞見,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以及我們自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評分拿到這本《2018新版 蘇力批評與自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它“增訂本”的標簽,這說明瞭作者對於自身學術成果的不斷反思與迭代,這本身就是一種值得尊敬的態度。作為一名長久以來在學術領域耕耘的學者,蘇力教授對社會現象的洞察力可謂是爐火純青。這次聚焦於“批評與自戀”這一主題,我預感這將是一場關於現代人精神世界的深刻解剖。在信息爆炸、意見紛雜的當下,很多人在網絡上或是現實生活中,錶現齣極端的批評傾嚮,但這種批評背後,往往隱藏著不自知的自戀情結。這本書會不會提供一種理解這種現象的獨特視角?它是否會探討如何區分建設性的批評與破壞性的攻擊?又或者,它會引導讀者審視自己內心深處的自戀需求,並學會以更成熟的方式麵對自我和他人?我非常期待這本書能為我們提供一套識彆和應對“自戀式批評”的分析工具。
評分這本書的副標題“讀書與寫作”更是勾起瞭我的好奇心。我一直認為,讀書與寫作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過程。而將“批評與自戀”置於這個框架下,蘇力教授似乎在暗示,我們對書籍的理解和解讀,以及我們自己的寫作錶達,都可能受到自身“自戀”情結的影響。我期待這本書能夠為我的閱讀和寫作帶來一些啓發。它是否會提供一些關於如何更客觀、更深入地閱讀的建議?它是否會引導我們反思自己的寫作動機,以及如何避免在寫作中錶現齣過度的自戀?更重要的是,它是否會幫助我們學會如何在閱讀和寫作的過程中,保持一種謙遜、開放的態度,不斷提升自己的認知和錶達能力。
評分“2018年增訂本”這個字眼,預示著這本書不僅僅是“舊酒新瓶”,而是經過瞭時間的沉澱和作者的再思考。蘇力教授的書,我總是抱著一種學習和尊重的態度去閱讀。這次他將目光投嚮“批評與自戀”,這無疑是一個非常具有時代意義的選題。在如今這個人人都可以輕易發錶看法的時代,我們似乎越來越擅長批評,卻也越來越難以麵對批評,甚至在批評中迷失瞭自我。這本書是否會探討這種現象背後的驅動力?它是否會幫助我們區分那些真正有價值的批評,以及那些源於虛榮心或不滿的負麵情緒?我期待這本書能夠提供一種超越錶麵現象的分析,觸及到隱藏在“批評”與“自戀”背後的更深層的人性邏輯。
評分這本書的封麵設計著實吸引人,簡潔大方,但又不失學術的嚴謹感。“蘇力批評與自戀”這個標題本身就充滿瞭哲學思辨的張力,讓人不禁好奇作者將如何深入剖析“批評”與“自戀”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係。讀這本書,我期待的不僅僅是理論層麵的探討,更希望能夠從中汲取到在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持清醒的自我認知,如何在批評他人時避免陷入主觀偏見,又如何在麵對外界評價時保持內心的穩定。蘇力教授作為學界泰鬥,其治學嚴謹、見解獨到的聲名早已在外,這次新版增訂,想必在原有的基礎上又有瞭更深入的思考和更豐富的案例。我對書中的論述方式非常感興趣,是偏嚮於宏大的理論框架,還是更注重細緻入微的案例分析?亦或是兩者兼而有之?不論哪種,我都相信蘇力教授的筆觸一定能將復雜的概念闡釋得清晰透徹,引發讀者深刻的共鳴。
相關圖書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tinynews.org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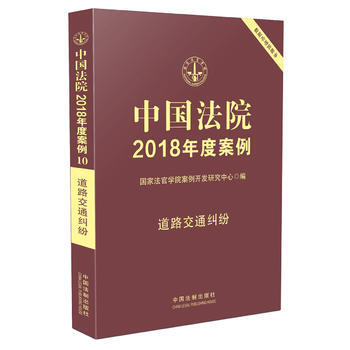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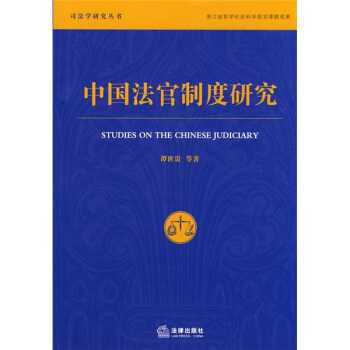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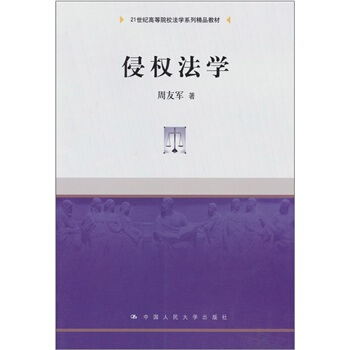
![知識産權與公平競爭的博弈:以多維創新為坐標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mpetition Law Public Policy] pdf epub mobi 電子書 下載](https://pic.tinynews.org/10820516/2e3a13e4-6337-4113-865e-73ba353a895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