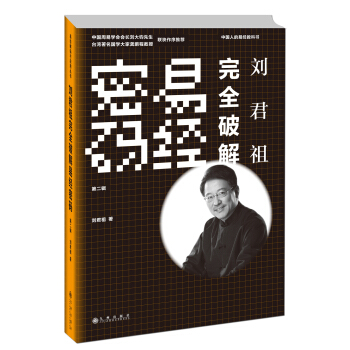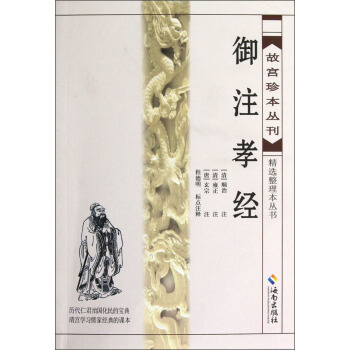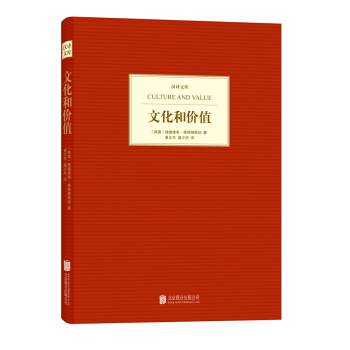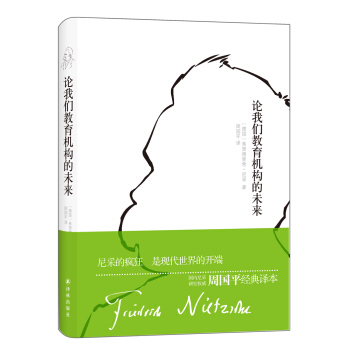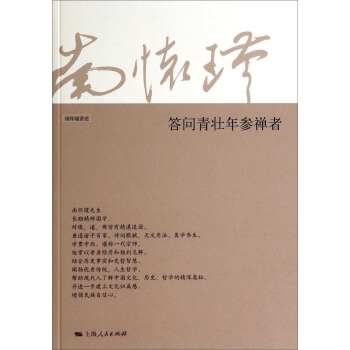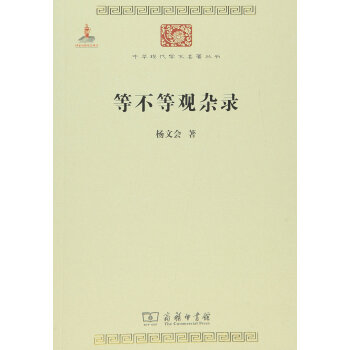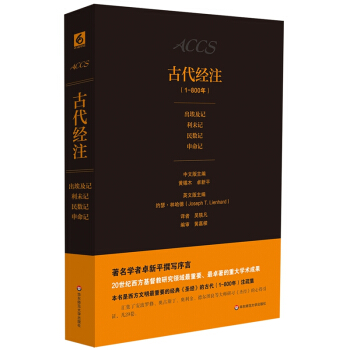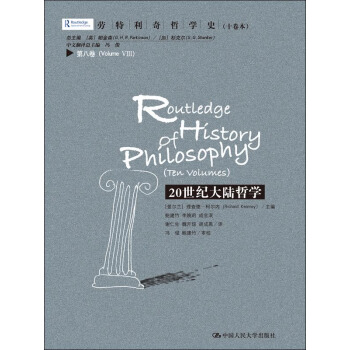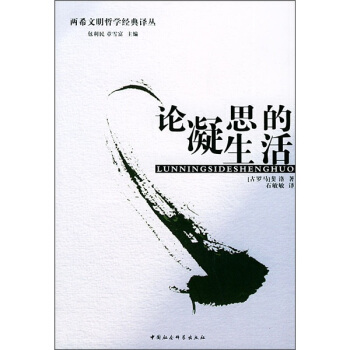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斐洛是希腊化犹太教的代表人物,是沟通希腊哲学、犹太传统与早期基督教思想的典范。《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论凝思的生活》的七篇斐洛(Philo)著作主要是伦理方面的,或者说是斐洛对于摩西五经有关经文所作的伦理上的神学解释。因此,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伦理神学文集”。因为在斐洛,伦理的概念就是要体现宗教虔诚的本质。目录
两希文明哲学经典译丛总序中译本导言
中译者前言
论亚伯的生出及亚伯与他兄弟该隐的献祭
论恶人攻击善人
论该隐的后裔并他的流放
论美德
论赏罚
善人皆自由
论沉思的生活或恳求者
译名对照表
精彩书摘
西方文明有一个别致的称呼,叫做“两希文明”。顾名思义是说,西方文明有两个根源,由两种具有相当张力的不同“亚文化”联合组成,一个是希腊—罗马文化,另一个是希伯来—基督教文化。国人在地球缩小、各大文明相遇的今天,日益生出了认识西方文明本质的浓厚兴趣。这种兴趣不再停在表层,不再满意于泛泛而论,而是渴望深入其根子,亲临其泉源,回溯其原典。我们译介的哲学经典处于更为狭义意义上的“两希文明时代”——即这两大文明在历史上首次并列存在、相遇、互相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这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历史时代,大约涵括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八百年左右的时期。对于“两希”的每一方,这都是一个极为具有特色的时期,它们都第一次大规模地走出自己的原生地,影响别的文化。首先,这个时期史称“希腊化”时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余威之下,希腊文化超出了自己的城邦地域,大规模地东渐教化。世界各地的好学青年纷纷负笈雅典,朝拜这一世界文化之都。另一方面,在这番辉煌之下,却又掩盖着别样的痛楚;古典的社会架构和思想的范式都在经历着巨变;城邦共和体系面临瓦解,曾经安于公民德性生活范式的人感到脚下不稳,感到精神无所归依。于是,“非主流”型的、非政治的、“纯粹的”哲学家纷纷兴起,企图为个体的心灵宁静寻找新的依据。希腊哲学的各条主要路线都在此时总结和集大成:普罗提诺汇总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路线,伊壁鸠鲁/卢克来修汇总了自然哲学路线,怀疑论汇总了整个希腊哲学中否定性的一面。同时,这些学派还开出了与古典哲学范式相当不同的、但是同样具有重要特色的新的哲学。有人称之为“伦理学取向”和“宗教取向”的哲学,我们称之为“哲学治疗”的哲学。这些标签都提示了:这是一个在巨变之下,人特别关心人自己的幸福、宁静、命运、个性、自由等等的时代。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的哲学。那个时代的哲学会不会让处于类似时代中的今人感到更多的共鸣呢?
另一方面,东方的另一个“希”——希伯来文化——也在悄然兴起,逐渐向西方推进。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定居经商,带去独特的文化。后来从犹太文化中分离出来的基督教文化更是日益向希腊—罗马文化的地域慢慢西移,以至于学者们争论这个时代究竟是希腊文化的东渐、还是东方宗教文化的西渐?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与希腊文化是特质极为不同的两种文化,当它们终于遭遇之后,会出现极为有趣的相互试探、相互排斥、相互吸引,以致逐渐部分相融的种种景观。可想而知,这样的时期在历史上比较罕见。一旦出现,则场面壮观激烈,火花四溅,学人精神为之一振,纷纷激扬文字、评点对方,捍卫自己,从而两种文化传统突然出现鲜明的自我意识。从这样的时期的文本入手探究西方文明的特征,是否是一条难得的路径?
还有,从西方经典哲学的译介看,对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基督教经典的译介,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做了可观的工作;但是,对于“两希文明交汇时期”经典的翻译,尚缺乏系统工程。这一时期在希腊哲学的三大阶段——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哲学、晚期哲学——中属于第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分别都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但是第三阶段的译介还很不系统。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的两希哲学的研究与译介传统是严群先生和陈村富先生所开创的,长期以来一直追求沉潜严谨、专精深入的学风。我们这次的译丛就是集中选取希腊哲学第三阶段的所有著名哲学流派的著作:伊壁鸠鲁派、怀疑派、斯多亚派、新柏拉图主义、新共和主义(西塞罗、普鲁塔克)等,希望向学界提供一个尽量完整的图景。同时,由于这个时期哲学的共同关心聚焦在“幸福”和“心灵宁静”的追求上,我们的翻译也将侧重介绍伦理性—治疗性的哲学思想;我们相信哲人们对人生苦难和治疗的各种深刻反思会引起超出学术界的更为广泛的思考和关注。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在希伯来—基督教传统中属于“早期教父”阶段。犹太人与基督徒是怎么看待神与人、幸福与命运的?他们又是怎么看待希腊人的?耶路撒冷和雅典有什么干系?两种文明孰高孰低?两种哲学难道只有冲突,没有内在对话和融合的可能?后来的种种演变是否当时就已经露现了一些端倪?这些都是相当有意思的学术问题和相当急迫的现实问题(对于当时的社会和人)。为此,我们选取了奥古斯丁、斐洛和尼撒的格列高利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哲的特点是“跨时代人才”,他们不仅“学贯两希”,而且“身处两希”,体验到的张力真切而强烈;他们的思考必然有后来者所无法重复的特色和原创性,值得关注。
这些,就是我们译介“两希文明”哲学经典的宗旨。
另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本丛书中各书的注释,凡特别注明“中译者注”的,为该书中译者所加,其余乃是对原文注释的翻译;二是本译丛也属于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系列研究计划之一。我们希望以后能推出更多的翻译,以弥补这一时期思想经典译介之不足。
前言/序言
用户评价
从阅读体验来说,这本书的排版和用纸质量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这对于长时间阅读来说至关重要。我通常是一个比较容易分心的人,但捧着这本实体书时,那种纸张的触感和油墨的清香,似乎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阅读结界”,有效地隔绝了外界的干扰。在内容上,它对我个人信仰体系的冲击是巨大的,尤其是在关于“时间观”和“自由意志”的探讨部分。作者没有试图去说服我接受某个既定的结论,而是通过层层递进的思辨,引导我主动去审视自己过去习以为常的预设。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写作手法,它尊重读者的主体性,将“理解”变成了一种读者自身的“建构”过程,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灌输。读完后,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消化这些内容,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小型的“认知重塑”,对很多困扰已久的问题都有了新的理解框架。
评分这本书的语言风格是那种典型的“学者的诗意”,它既有哲学思辨的精确性,又充满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我发现自己经常需要放慢速度,甚至需要反复阅读同一个句子,不是因为理解困难,而是因为句子本身蕴含的美感和多义性。作者在运用隐喻和象征手法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会用自然界中最朴素的现象来比喻最复杂的形而上学问题,这种降维处理让深奥的概念变得可触摸、可感知。比如,他对“静默”的描述,与其说是对一种状态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种对心灵深处声音的捕捉与再现。这种细腻入微的笔触,让人感觉作者不仅是站在知识的顶端进行俯视,更是深入到体验的泥土中与万物同呼吸。对于那些追求阅读深度和美学享受的读者来说,这本书绝对不会令你们失望。
评分我是一个对历史和思想脉络很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在梳理思想传承方面做得极为出色。它没有采取那种生硬的编年史式的叙述,而是巧妙地穿插了大量的历史场景和人物侧写,让人仿佛置身于那个思想碰撞的年代。比如,作者在谈及某个关键转折点时,会引用大量当时学者的书信或手稿片段,这些“一手资料”的引入,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感和现场感。我尤其赞叹作者在构建逻辑链条时的严谨性,每一步论证都像是精心打磨的榫卯结构,环环相扣,让人找不到任何可以被轻易攻破的薄弱环节。然而,这种严谨并不意味着枯燥,相反,作者总能在关键节点抛出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反问,将读者的思绪从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抽离出来,重新聚焦于“我该如何安放我的生命”这一永恒的命题。这种张弛有度的节奏把握,让阅读过程充满了发现的乐趣。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在于它对“内在秩序”的强调。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外部噪音无穷无尽的时代,我们很容易迷失在各种即时反馈和外部评价之中。这本书却像是一盏坚定的灯塔,不断地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自身存在的核心。它没有过多地讨论社会规范或伦理教条,而是聚焦于个体精神世界的自洽与丰盈。作者提供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那就是,外在世界的混乱往往是我们内在秩序失衡的外化表现。因此,真正的改变始于对内心疆域的勘探与整理。我尤其喜欢作者对“审慎”的论述,那不是胆怯或保守,而是一种基于深刻理解后做出的最负责任的选择。这本书是那种读完之后,你会把它郑重地放在书架上,并在未来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会忍不住想再次翻阅的“生命工具书”。
评分这本书的封面设计极具吸引力,那种深邃的蓝色调和古朴的字体,让人一眼就能感受到它所承载的厚重与智慧。我记得我是在一个周末的下午,在一家安静的咖啡馆里翻开它的。初读之下,我立刻被作者那精妙的文字功底所折服。他仿佛拥有某种魔力,能将那些看似遥远、晦涩的哲学概念,描绘得如同眼前可见的景象。那种娓娓道来的叙事方式,不像是在阐述理论,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深刻的内心对话。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不同思想流派时的那种平衡感,他既没有偏颇地推崇某一家,也没有将它们简单地对立起来,而是努力去探寻它们背后共通的人性关怀与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读完开篇的几章,我感觉自己的思维一下子被拉高了一个维度,开始以一种更宏观、更包容的视角去审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琐事。这本书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往更深层次思考的大门,而不是简单地提供答案。
评分价格实在,不错,质量很好
评分价格实在,不错,质量很好
评分谁是乌托邦的真正敌人
评分两希文明译丛,很好的一套书。
评分乌托邦是宏大叙事,作为宗教后启蒙时代的产物,那种继承过来的普世性冲动,难免对文化多元的现代理念形成挑战。在卡尔•贝克尔看来,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与其说是引领潮流的哲学家,不如说是新天国中的牧师。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伯林对启蒙主义的批判、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质疑都是合理的,并且是有限度的。他们决非恶意颠覆而意在良性修缮。
评分《梵语文学读本》选读的都是梵语文学中的一些经典性作品。《薄伽梵歌》出自史诗《摩诃婆罗多》,是印度古代最著名的一部宗教哲学长诗。佛教诗人马鸣的《佛所行赞》是古典梵语叙事诗的早期典范作品。迦梨陀娑是享有最高声誉的古典梵语诗人。我们选读了他的抒情诗集《时令之环》、叙事诗《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其中的《罗怙世系》可以说是学习梵语的必读书目。胜天的《牧童歌》是古典梵语抒情诗的晚期优秀作品。以上都是诗体作品。波那的《戒日王传》则是一部散文叙事作品。
评分反乌托邦也是乌托邦
评分不必讳言,雅各比有意回避了乌托邦的真正敌人:后现代主义。熟悉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欧陆哲学的人都应清楚,以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想,实质上已构成了对乌托邦的最重大打击。雅各比在此避重就轻,不仅有损该作的全面与客观,而且也让人怀疑他学术上的诚实。
评分凝思在其时变得不可能但异常迫切的一个选择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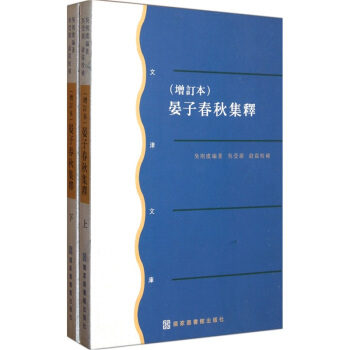
![维真基督教文化丛书·爱与正义:尼布尔基督教伦理思想研究 [Love and Justice:A Study of Reinhold Niebuhr's Christian Ethic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1100452/rBEHZlB7pvUIAAAAAAEr0on3vvgAABu1gLJ-9wAASvq99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