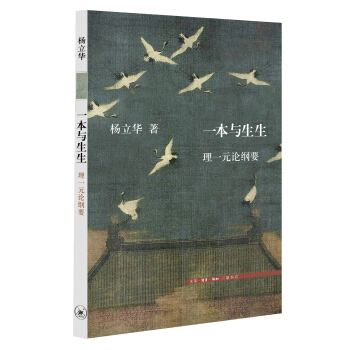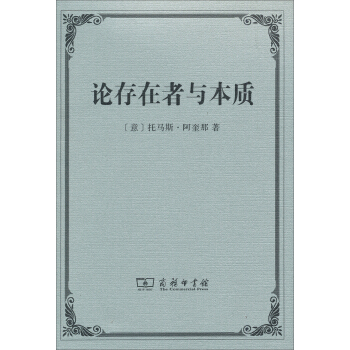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论存在者与本质》由“引言”与六章正文组成。“引言”针对西方哲学逻辑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哲学传统,发挥亚里士多德和阿维森纳的思想,强调区分逻辑学与本体论,强调区分本质概念和存在概念的本体论和实存论性质。
第1章“存在者与本质这两个词的普遍意义”提出了从现实存在者出发达到事物本质的认知路线(与其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相呼应,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作为在复合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一方面强调物质实体的本质并非如柏拉图主义所言,仅仅由形式构成,而是由形式和质料组合而成;另一方面又强调了质料乃物质实体个体化原则(individuationis principium)。
第三章“本质与属相、种相和种差的关系”针对希腊哲学将属相、种相等逻辑概念理解为本质的逻辑中心主义路线,强调指出属相和种相并非物质事物的本质本身,它们是由“理智活动”完成的,是作为“在理智中所具有的存在本身生发出来的偶性”相关于本质的。
第四章“作为在脱离质料的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讨论了区别于物质实体的精神实体(如天使等)的本质不是由质料与形式复合而成的,而是单单由形式构成的。进一步强调了在受造物中存在与本质相区别的原则。(这是阿奎那对西方哲学史是一项基本贡献,至现代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作了铺垫。)
第五章“在不同存在者中所发现的本质”和“作为在偶性中所发现的本质”,突出强调了上帝的本质特征在于“单纯性”:A,上帝既没有质料也没有偶性;B,上帝的本质即存在。由于A,上帝的本质区别于物质实体;由于B,上帝的本质区别于精神实体。并且,既然无论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其存在都是“由他存在”而非“自己存在”,从而也就通过对本质学说的讨论深层次地论证了存在即活动或创造活动这一重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公式,而且也为基督宗教神学的创世学说作了理论铺垫。
该著是阿奎那哲学和神学著作中具形而上学意蕴的著作,在西方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正因为如此,该著历来受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重视。
当今西方出版界有三个较为流行的英文译本:(1)Armand Maurer译本;(2)Joseph Bobik译本;(3)George G. Leckie译本。
可以说,研究阿奎那的哲学和神学,不研究此书便很难上升到其理论制高点。
内页插图
目录
引言第一章 “存在者”与“本质”这两个词的普遍意义
第二章 作为在复合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
第三章 本质与属相、种相和种差的关系
第四章 作为在独立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
第五章 在不同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
第六章 作为在偶性中所发现的本质
结论
附录一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对托马斯《论存在者与本质》的一个当代解读
一、对侉统j罗辑丰义思维范式的颠覆:实存概念VS逻辑概念
二、面向存在者本身:事实存在VS逻辑存在
三、本质的发现:本质的实存性、特殊性与构成
四、走向作为“纯粹活动”的“纯粹存在”
从存在者到存在本身
五、作为形而上学革命家的托马斯的理论得失
海德格尔vS吉尔松
附录二 人名外中文对照表
附录三 人名中外文对照表
附录四 著作名外中文对照表
附录五 著作名中外文对照表
附录六 主要术语外中文对照表
附录七 主要术语中外文对照表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存在者”与“本质”这两个词的普遍意义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一如哲学家在《形而上学》第5卷中所说,对存在者(ens)本身可以用两种方式加以解说:按照一种方式它可以区分为十个范畴;按照另一种方式它则可以意指命题的真实性。这样两种方式之间的区别在于:按照第二种方式,任何事物,凡是能够对之形成一个肯定命题的,就可以被称作存在者,即使那命题并没有肯定什么东西实际存在,亦复如此。这样一来,缺乏(privationes)和否定(negationes)也就可以算作存在者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肯定是与否定相对立的”以及“盲是存在于眼中的”。但是,按照第一种方式,则没有什么能够说成是存在者,除非能够指出有什么事物实际上存在。这样一来,盲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不再能够说成是存在者了。
因此,“本质”这个词就不是由言说存在者的第二种方式(secundomodo)产生出来的。因为按照这种方式,一些事物虽然被称作存在者,但是却并不具有本质,这在缺乏的情况下很清楚。毋宁说,“本质”这个词是由言说存在者的第一种方式产生出来的。因此,评注家在亚里士多德解说存在者的两种方式的地方评论说:“只有按照第一种方式解说的存在者才可以说是内蕴有一件事物本质的东西。而且,既然如上所述,按照这种方式所言说的存在者可以区分为十个范畴,则所谓本质就应当意指那些为所有自然事物(omnibusnaturis)所共有的东西,各种不同的存在者就是据此归属到各种不同的属相和种相之下的,如人性乃人的本质,如此等等。
由此看来,既然事物用以充当其属相和种相的东西即是表明这件事物是其所是的定义所意指的东西,则哲学家们因此也就用“实质”这个词取代本质一词。哲学家常常称之为一件事物藉以成为该物的东西,即那种使一件事物成为其所是的东西。本质也被称作形式(folxna),因为如阿维森纳在《形而上学》第2卷中所说,每一件事物的真实性都是藉形式表示出来的。
……
用户评价
这本书带给我的冲击,更多是源于其对日常经验的颠覆性重塑。我们通常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但作者通过其独特的视角,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揭示了我们认知的局限性。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巧妙地穿插了一些看似不经意的日常案例,但这些案例一旦被置入作者的理论框架下,立刻焕发出令人不安的意义。这种“用日常来解构日常”的手法,极其高明。它避免了纯粹抽象理论的枯燥,使得那些深奥的哲学命题变得触手可及,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困惑——我们所依赖的“触手可及”的现实,其根基是否真的如此稳固?这本书的文字有一种奇特的节奏感,时而如疾风骤雨,思绪万千;时而又如同古井无波,沉静深远,让人在紧张与放松之间反复拉扯,有效地保持了读者的精神参与度。我甚至觉得,这本书应该被放在哲学系的入门教材中,因为它教会了读者如何真正开始质疑。
评分如果说大多数哲学著作是在探讨“世界是什么”,那么这本书则更像是在质问“我们如何能声称知道世界是什么”。它的重心似乎完全偏向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交叉地带,以一种近乎批判的精神,对人类心智的自我认知进行了彻底的审视。我特别喜欢作者对待历史观点的态度——他没有简单地继承或反驳前人,而是将历史上的主要思想流派视为一系列必要的、但终究是有限的“尝试”,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似乎更具穿透力的路径。这本书的“硬核”程度毋庸置疑,它对逻辑一致性的追求到了近乎偏执的程度,这使得那些习惯于“差不多就行”的读者可能会感到吃力。但我相信,对于那些真正致力于探究真理的求知者而言,这种严苛正是其价值所在。这本书更像是一把精密的瑞士军刀,它能精准地切割那些模糊不清的哲学迷雾,但使用它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谨慎,否则很容易伤到自己。
评分读完之后,我的第一感觉是,这简直是一部用纯粹的逻辑铸就的史诗。它的语言风格极其凝练,像是一块块打磨光滑的黑曜石,每一句都沉甸甸地,蕴含着难以言喻的力量。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思辨时所展现出的那种近乎冷酷的客观性。他似乎完全抽离了个人情感和时代偏见,仅仅以思想的推演为导向,构建起一套自洽的、宏大的理论体系。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在攀登一座思想的悬崖峭壁,每一步都需要精确计算,容不得半点虚浮。我能想象到,这本书在学界会引发多么激烈的争论,因为它不仅挑战了既有的范式,更像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观察世界”的棱镜。它的结构安排也很有匠心,从基础性的预设开始,逐步向上搭建,直到触及那个最顶端、最令人不安的结论。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被作者牵引到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疆域。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它更像是一份对人类理性极限的严肃考察报告。
评分这本新书的问世,简直像是在平静的学术湖面上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思想的层层涟漪。我首先被它那几乎令人窒息的哲学深度所吸引。作者似乎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现实表皮,直抵事物运作的底层逻辑。阅读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吸收知识,不如说是在经历一场智识上的“洗礼”——那些原本以为坚不可摧的观念,在作者犀利的剖析下,变得摇摇欲坠。全书的论证结构缜密得令人叹服,每一个章节的过渡都如同精密机械的咬合,无懈可击。它不像很多当代哲学著作那样,沉溺于晦涩的术语和故作高深的姿态,反而有一种古希腊哲人那种直面世界本源的勇气和坦诚。我发现自己经常需要停下来,合上书本,在房间里踱步良久,试图消化那种扑面而来的“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正是通往真正洞见的第一步。作者对概念的界定极为苛刻,不放过任何一个模棱两可的词汇,这使得阅读体验充满了挑战,但也带来了巨大的满足感,因为你感觉到自己正在被引导着去思考那些最根本的问题,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选择性遗忘的问题。这本书不适合抱着轻松心态翻阅,它需要你投入全部的专注力,去参与这场深刻的思辨之旅。
评分这部作品散发着一种令人敬畏的智力重量感。它并非那种追求“广度”的书籍,它更像是钻探一口深井,力求直达地心。作者似乎对任何肤浅的解释都抱持着一种近乎蔑视的态度,他要求读者不仅要理解他的论点,更要理解他为何必须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构建这个论点。我感受到了作者在文字背后投入的巨大心力,那种为了穷尽一种可能性而进行的长久思索的痕迹清晰可见。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审视身边的物质和非物质对象——一切都似乎被置于一个待审视的、不确定的光线下。这本书的文字布局和章节安排也极具设计感,充满了古典的对称美和现代的解构张力,这使得阅读体验在智力激荡之余,也带来了一种审美的愉悦。它不是一本能让你读完后感到轻松愉快的书,但它绝对是一本能让你读完后,对“思考”这件事本身产生全新敬畏的鸿篇巨制。
评分第一章“存在者与本质这两个词的普遍意义”提出了从现实存在者出发达到事物本质的认知路线(与其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相呼应,并为之奠定了基础)。
评分多瑪斯.阿奎那的神修是神學家的神修,他修持甚嚴,幼時曾在蒙第.卡西諾(Monte Cassino)的本篤會隱修院(Benedictine Abbey)的學校,開始早期教育,學會祈禱和研讀聖經,練就一套本篤會規的沙漠教父修行工夫:獨居深思、嚴守靜默、酷愛禁食、持續靜觀和謹言慎行,造就了他縝密的神、哲學思維,並寫出多項流傳至今的巨著。
评分¥12.60(5.M8折)
评分第五章“在不同存在者中所发现的本质”和“作为在偶性中所发现的本质”,突出强调了上帝的本质特征在于“单纯性”:A,上帝既没有质料也没有偶性;B,上帝的本质即存在。由于A,上帝的本质区别于物质实体;由于B,上帝的本质区别于精神实体。并且,既然无论物质实体还是精神实体,其存在都是“由他存在”而非“自己存在”,从而也就通过对本质学说的讨论深层次地论证了存在即活动或创造活动这一重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公式,而且也为基督宗教神学的创世学说作了理论铺垫。
评分奎纳家族是伦巴底望族,与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保持着密切关系。阿奎纳年轻的时候就是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是中世纪最有名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他的《神学大全》被认为是神学和法律部的权威。[1]被称为‘神学界之王’。
评分性的定义是依照它的具体的意义确定的, 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如果这样, 该主体就将
评分附录四
评分“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无论一个人于存在者处把握到的是什么,这种把握总已经包含了对存在的某种领会。”这种观念正是我们的感知。[2]但“存在”的“普遍性”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如果存在者在概念上是依照类和种属来区分和联系的话,那么“存在”却并不是对存在者的最高领域的界定;ουτε το ον γενοζ〔存在不是类〕。[3]存在的“普遍性”超乎一切族类上的普遍性。按照中世纪存在论的术语,“存在”是“transcendens〔超越者〕”。亚里士多德已经把这个超越的普遍〔者〕的统一性视为类比的统一性,以与关乎实事的最高族类概念的多样性相对照。不管亚里士多德多么依附于柏拉图对存在论问题的提法,凭借这一揭示,他还是把存在问题置于全新的基础之上了。诚然,连他也不曾澄明这些范畴之间的联系的晦暗处。中世纪的存在论主要依循托玛斯主义和司各脱主义的方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讨论,但是没能从根本上弄清楚这个问题。黑格尔最终把“存在”规定为“无规定性的直接性”并且以这一规定来奠定他的《逻辑学》中所有更进一步的范畴阐述,在这一点上,他与古代存在论保持着相同的眼界,只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与关乎实事的“范畴”的多样性相对的存在统一性问题,倒被他丢掉了。因此人们要是说:“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那可并不就等于说:它是最清楚的概念,再也用不着更进一步的讨论了。“存在”这个概念毋宁说是最晦暗的概念。“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这就造成了另外的新的问题。这是从它的最高普遍性推论出来的。[4]这话有道理——既然定义来自最近的种加属差。确实不能把“存在”理解为存在者,enti non additur aliqua natura:令存在者归属于存在并不能使“存在”得到规定。存在既不能用定义方法从更高的概念导出,又不能由较低的概念来表现。然而,结论难道是说“存在”不再构成任何问题了吗?当然不是。结论倒只能是:“存在”不是某种类似于存在者的东西。
评分作为O在独立实体中所发现的本质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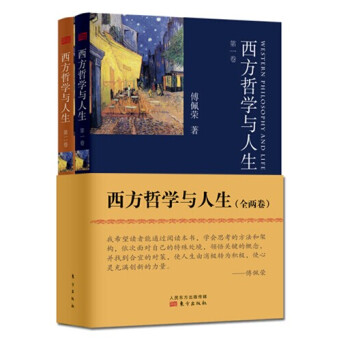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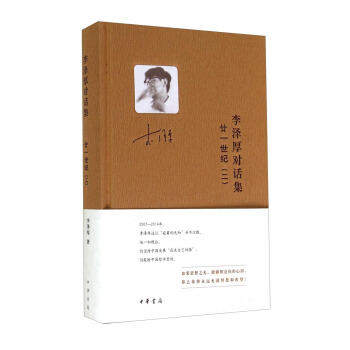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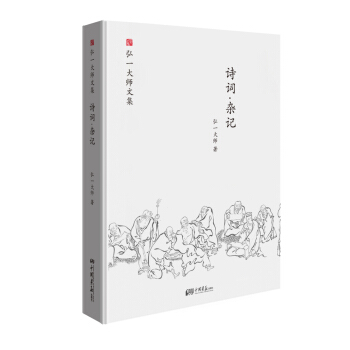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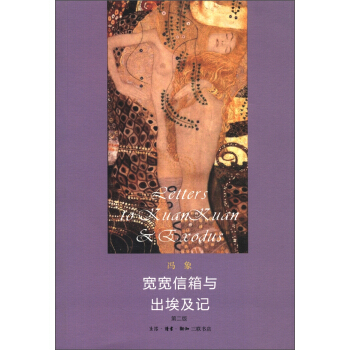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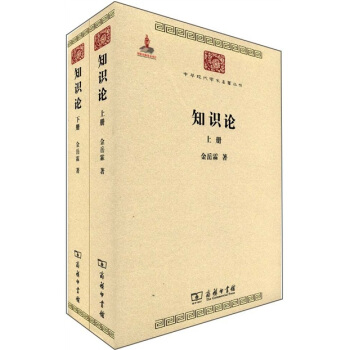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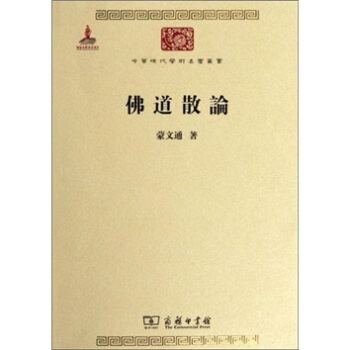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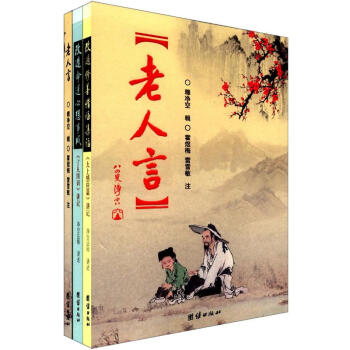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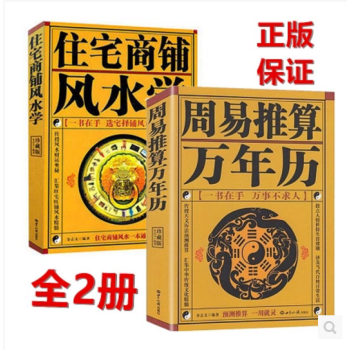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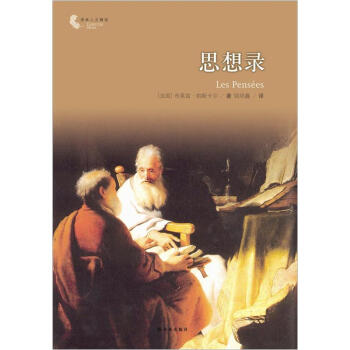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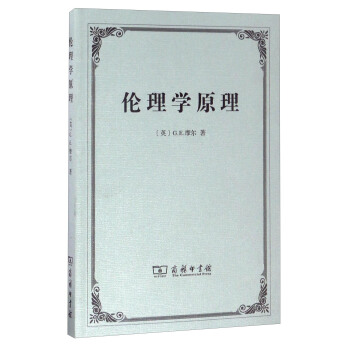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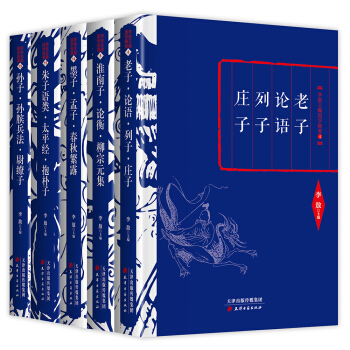
![论道德的谱系:一篇论战檄文(新版)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71146/58ff13c4N1a870426.jpg)
![神话的智慧 [La sagesse des myth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193776/591a9806Nb12890cd.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