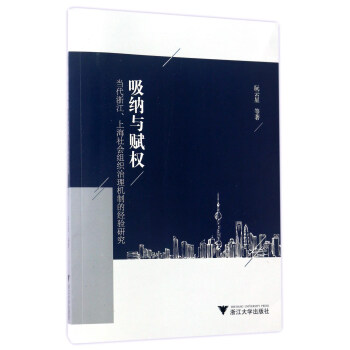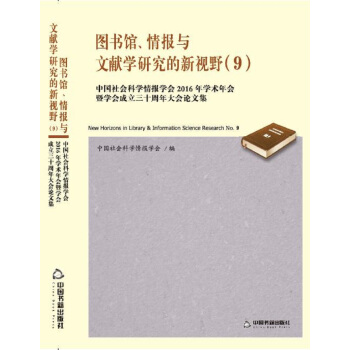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期刊的创刊号收藏在藏书界颇为热门,现代已经难寻,当代也非容易。★一本“经眼录”既是个人的阅读史,也是一本工具书,是了解十年期刊演变的一条途径。
★看似默默无语者,必有自己的另一番天地。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十年”是报纸和期刊发展的黄金期,这一时期的创刊号正成为当下收藏界的热点之一。李勇军先生已出版相关类的图书四种。这部书稿是对作者所著《新中国期刊创刊号1949-1959》图书的延伸、拓展,这部书稿与前著有着互为补充的关系。
内容简介
《创刊号经眼录:1949-1959》选取三十余种有代表性的期刊单独成篇,并以“链接”的形式附列十数个标题。另外在相关叙述中以整段文字或以图片形式介绍创刊号近百种。是一部期刊的发展史。本书稿由我社签约作者李辉先生作序。作者简介
李勇军,1970年生,河南兰考人,编审、杂志主编,首届河南省优秀编辑(2002)首届河南省优秀期刊编辑(2008)。内页插图
目录
1949《东北青运通讯》
青年期刊“卑微”的童年/新中国是怎样在大学建团的/佳木斯被服厂案例
1950
《中国农报》
是报,还是刊?/创刊“特大号”/关于承印单位北京市生产教养院印刷厂/赔钱发行、大量赠阅是“官办”
附:关于《中国农报·增刊》
《武汉数学通讯》
创刊号仅印400册/曾昭安:刊物的灵魂人物/第一次“全国数学大会”/改名《数学通讯》
附:《数学教学》《数学教学月刊》与《中学数学》
1951
《历史教学》
新中国最早的历史专业期刊/徐特立、马叙伦先后题写刊名/《文史哲》的创刊消息
《外科学报》
《内科学报》的“姊妹刊”/包罗“与外科学有密切关系的各学科”/总编辑:许殿乙/我国外科期刊的第一个商业广告
《新史学通讯》
中国新史学会的“新”/郭沫若三题刊名/因肃反运动第一次停刊
《语文教学》
两个《语文教学》/不容忽视的大众书店/创刊号“三版本”
《中国数学杂志》
总编辑:华罗庚、傅种孙/毛泽东亲题刊名的内情/苏步青的古文学修养/改名《数学通报》
附:关于《数学学报》
1952
《语文知识》
以“通俗的语文刊物”为号召/编辑者:上海新文字工作协会/提倡“横写横排”/周有光是“汉语拼音之父”吗
1953
《文艺月报》
巴金担纲主编/唐弢指出:比较严肃,不够活泼,短文章也不够多/成为“批判胡风”运动的重灾区
附:《上海文学》和《收获》
《档案工作》
先出“第十八期”,再出“第一期”/其“前身”《材料工作》/中队民大学最早的档案专修科/“对外保密的内部刊物”
附:《材料工作通讯》是创刊,还是“前身”?
《护士与卫生员》
“护士”与“卫生员”之间/没有定价,也没有经售单位/关于“终刊的话”
《出版业务》
宋原放主编的一份稀见内刊/严格的出版计划/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印制内情
1954
《文艺学习》
一份深受欢迎的青年刊物/第一作者胡耀邦/最高单期印数300650册/因“反右”而停刊
《解剖通讯》
是“小型”刊物,也是“大型”刊物/李赋京与“蒲城李氏”家族/两年“磨”两期的“年刊”
附:《解剖学通报》与《解剖学报》
《建筑》
朱德元帅题写刊名?/不一定把“学习苏联”摆在首位/一错再错的总期数
附:《建筑译述》《建筑译丛》与《城市建设译丛》
……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前言/序言
在刊物的密林里穿行——《创刊号经眼录》序
李辉
因出版《藏与跋》一书,结识了李勇军,他是我的责编。勇军话不多,客套话更是不会说。两人见面相聚,直奔主题,寥寥几句,便缄默无语。我想了想,这种情形颇有点儿过去与黄裳先生面对的那种感觉。
看似默默无语者,必有自己的另一番天地。果不其然,一日,他寄来《新中国期刊创刊号(1949—1959)》一书,令我为之感叹。未想到,两年之后勇军又完成这本《创刊号经眼录》。这是前面一本书的自然延伸与拓展,他所梳理的仍是1949—1959十年之间创办的期刊,两相呼应,可以说将这十年间中国新创办期刊的大致状况,有了更为系统的叙述。
期刊的创刊号收藏在藏书界颇为热门,现代已经难寻,当代也非容易。试想一下,勇军叙述的这些期刊,距离我们其实已经超过半个世纪,若想一一收藏,几乎不可能。那么,正好有勇军的这两本书,不妨从中获取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好像听勇军说过,他并不意在收藏,而在于对出版的一种热情,在于对历史的关注。多年来,他不声不响地穿行在创刊号的密林里,查阅、阅读、辨析……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刊物,呈现十年间期刊的演变。创刊号的酝酿、问世,往往与文化需求、政治需求密切相关,借他的细心梳理,一本又一本创刊号的问世过程、内容介绍、主编与作者的阵容,诠释这一个十年之间的出版格局与变化,在斑驳碎影之中,可以看到一些容易忽略的细节。
我自从在大学开始研究现代文学,诸多期刊的阅读必不可少。与勇军勾勒的这十年的期刊有所不同,现代出版史上,往往同人杂志居多。犹记得,当年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借阅那些泛黄期刊,最让人为之沉醉而快乐。首先要看的当然是创刊号。每种杂志的创刊号,最能体现创办者的出版理念与文学追求,创刊号上发表的创刊词、开卷的话、寄语等,帮助我们从中了解刊物名称的由来,编者的情绪、心情、主张。若遇到感兴趣的,便将之抄录下来,留待日后研究或摘录所用,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习惯。翻阅勇军《创刊号经眼录》书稿时,他所转引的许多刊物的创刊词,读来颇感亲切,仿佛看到他坐在图书馆翻阅这些杂志,自己的身影也在一旁闪动。
回想起二十几年前,我写作《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1929年创办的《红黑》《人间》两本刊物,颇为难找,最后才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出来,将两本刊物的创刊词一一抄录。
创刊号《红黑》的“创刊词”,由胡也频所写。他这样详述刊物名称缘由:
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现代那勃兴的民族就利用这两种颜色去表现他们的思想——这红与黑,的确是恰恰适当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并且也正合宜于文艺上的标题,但我们不敢窃用,更不敢掠美,因为我们自信并没有这样的魄力。正因为我们不图自夸,不敢狂妄,所以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一句土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这意义,是再显明没有了。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
创刊号《人间》的“卷首语”由沈从文所写,与胡也频一样,用词也颇为激烈,可以说集中呈现他们作为文坛新人此时的心情与心境:
开始,第一卷本刊,出了世,没有什么可说。几个呆子,来作这事,大的希望,若说还有,也不过希望另有许多呆子来作本刊读者而已。
……所谓一群,人数真是怎样稀少!三个吧。五个吧。比起目下什么大将,高踞文坛,文武偏裨,背插旗帜,走狗小卒,摇旗呐喊,金钱万千,同情遍天下者,又真是如何渺渺小小之不足道!然而为了一种空空的希望,为了我们从这事业上可以得到生活的意义,干下来了。
我最后可说的话,是先在此来为本刊悼。
就现代文学刊物的创刊号来说,创办者的创刊词通常都写得精彩,相比而言,《创刊号经眼录》里的文学刊物的创刊词,少了当年创办者的愤世嫉俗、慷慨激昂,少了当年创办者的挥洒自如、文采飞扬。其实,这也正是时代变迁之后历史演变的写照。同人刊物不再出现,创办者常常为机关、单位,尽量摒弃个人色彩与个人主张,以体现集体性与政治意识。这也是《创刊号经眼录》的重要性所在,勇军借众多创刊号的整合、勾勒,如实地把现代与当代不同时代期刊出版的历史转折,令人信服地加以叙述。于是,一本“经眼录”既是个人的阅读史,也是一本工具书,是了解十年期刊演变的一条途径。
研究期刊需要耐得住寂寞,勇军恰好有此秉性。我猜想,他现在或许已经开始第二个十年的创刊号研究。接下来另一个十年,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各类期刊的命运与历史的关联更加密切,期刊与办刊者随时代潮流涌动而起伏跌宕。最值得勇军费心搜集与研究的,恐怕是1966—1969年期间全面开花的“文化大革命”刊物。这些创刊号若要收藏与研究,谈何容易。何况它们又非正式出版物,很难有延续性。但是,就其出版特殊性而言,这是当代中国刊物前所未有的现象,若要研究,便不能舍弃而过。
显而易见,新的一本《创刊号经眼录》,对勇军是新的挑战。以他的耐得住寂寞的秉性,以他对出版的热爱,他应该仍将如过往一样,默默地接受这一挑战。几年之后,如果他再次呈现一部新著,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
写于2016年5月26日,北京
用户评价
这套书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尤其是那些关于那个特定年代的社会变迁的描绘,简直是身临其境。作者的笔触细腻入微,把当时的氛围捕捉得淋漓尽致。比如,书中对那些初创时期集体生活场景的描写,那种既有理想主义的光芒,又带着朴素的艰辛的复杂情感,真是令人动容。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述中展现出的那种历史的厚重感,仿佛每一次的事件背后,都蕴含着深远的意义和无数普通人的命运纠葛。读着读着,我常常会停下来,去想象那些鲜活的面孔,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奋斗与迷茫,都通过文字变得具体可感。这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更像是一部充满生命力的编年史,让人对那个时代产生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同情。那种时代特有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也被作者很巧妙地融入了叙事之中,读起来丝毫没有枯燥之感,反而充满了韵味。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审视一个国家在转型期所经历的那些关键性的、塑造未来的时刻。
评分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我对这个跨度十年的时段有些疑虑,担心内容会显得松散或重复,但事实证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作者的叙事线索组织得非常清晰有力,紧密围绕着核心的变革主题展开,使得这十年如同一个有机整体,脉络分明。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充满争议和复杂性的历史事件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克制而又充满洞察力的笔法。他没有简单地进行褒贬,而是努力去还原事件发生时的全部语境,让读者自己去得出结论,这体现了一种高度的史学良知。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站在一个高处俯瞰,既能看到那些决策者的远虑,也能感受到基层的细微震动。这种多层次的叙事结构,使得作品的耐读性极高,每一次重读,都会因为自身阅历的增加,而对书中某些情境产生新的共鸣。这是一部值得被反复阅读和珍藏的佳作。
评分这是一部需要细嚼慢咽的作品,因为它蕴含的信息密度非常高,但处理得却异常优雅。我发现自己常常需要放慢速度,去体会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因为这些细节往往是理解那个时代精神肌理的关键线索。比如,对于当时生活物件的描述,对于特定称谓的使用习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元素,却共同构建起一个真实可感的过去。作者在史料的筛选和运用上显示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但最可贵的是,他成功地将那些冰冷的数据和文件,重新赋予了情感的温度和人性的光辉。读完全书,我感觉自己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漫长旅程,不仅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它激发了我对“时代精神”这个概念进行深入思考的兴趣。这本书的叙事张力,不是靠戏剧性的冲突堆砌出来的,而是源自于历史必然性和个体选择之间产生的永恒张力。
评分这本书的文字功底实在是令人叹服,它的语言风格自成一派,既有旧时代特有的庄重典雅,又不失现代叙事的流畅与锐利。我特别留意了作者对情绪的捕捉和表达,那种在特定历史语境下,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微妙的、难以言喻的挣扎与期盼,被刻画得入木三分。举例来说,书中描述几次重大的集体行动时,那种集体意识的觉醒与个体意志的磨合,那种充满激情又带着一丝惶恐的复杂心绪,读起来简直让人屏住呼吸。而且,作者在结构安排上也很见功力,章节之间的过渡自然而然,仿佛是时间自身的流动,让人完全沉浸其中,忘记了自己是在阅读一本“历史记录”。这种流畅性是很多严肃作品难以企及的。它不仅仅是在讲述“发生了什么”,更是在探讨“人们是如何感受并应对这一切的”,这才是真正打动读者的核心所在。
评分我对这套书的整体感觉是,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宏大而又充满细节的叙事框架。叙述的节奏把握得相当到位,时而紧凑,如同一场疾风骤雨般的变革;时而舒缓,像是在历史的河流边静静地回望。这种张弛有度的处理,使得即便是对于不熟悉那个年代背景的读者来说,也能轻松地跟上作者的思路。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能把抽象的政策和宏观的走向,转化成一个个鲜活的、可以触摸到的生活片段。读到某些高潮迭起的部分,我甚至能感受到那种历史洪流的强大推力,那种不容置疑的前进姿态。同时,作者在描写普通人的反应时,又充满了人性的温暖与真实,避免了将历史人物扁平化处理的倾向。这种平衡感,让整部作品既有史诗的格局,又不失个体生命的温度。每一次翻阅,都会有新的感悟,它就像一坛老酒,越品越有滋味,让人对那个“破晓”的年代有了更立体、更具层次的认识。
相关图书
本站所有内容均为互联网搜索引擎提供的公开搜索信息,本站不存储任何数据与内容,任何内容与数据均与本站无关,如有需要请联系相关搜索引擎包括但不限于百度,google,bing,sogou 等
© 2026 book.idnshop.cc All Rights Reserved. 静思书屋 版权所有

![研究生创业教育/创新创业教育译丛 [Teaching Entrepreneurship to Postgraduat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86280/5863836cN77e1a7e9.jpg)

![财富的秘密 [The Richese Man in Babylon]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86544/586cc024Nfc7b68a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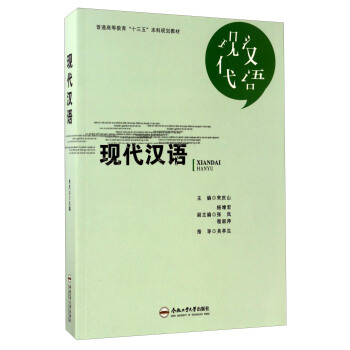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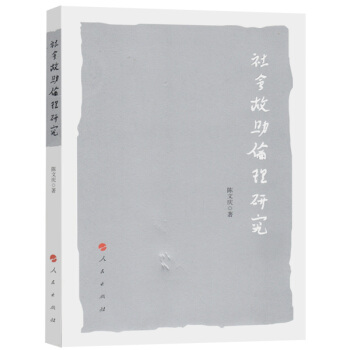
![案例研究:原理与实践 [Case Study Research: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87919/5930fb12N8d8ba898.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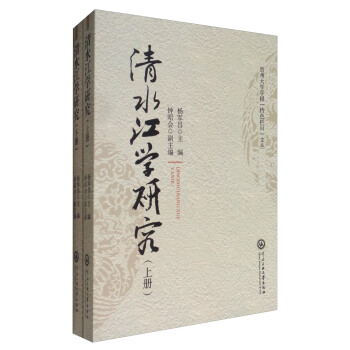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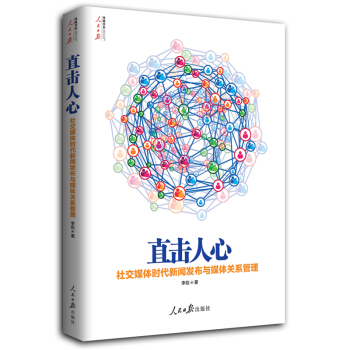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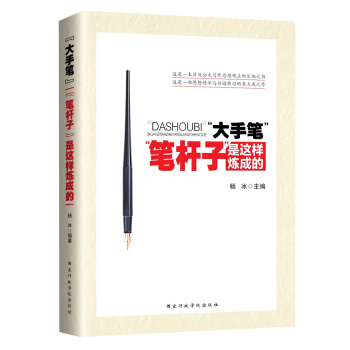
![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附光盘)/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丛书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2423/593a5337N46f793c7.jpg)
![世界教育思想文库:课程 [The Curriculum]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2473/593a533fN38fad8e0.jpg)
![软力量丛书 融合与创新:“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研究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A Study of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3739/59634cf5Ne763b714.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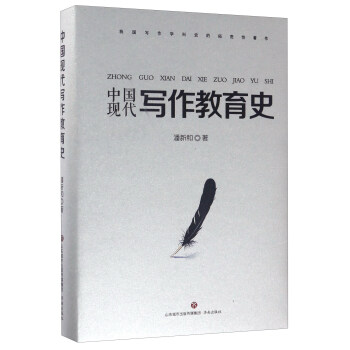
![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状况研究 [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下载](https://pic.tinynews.org/12094607/59634cf6N86a10e42.jpg)